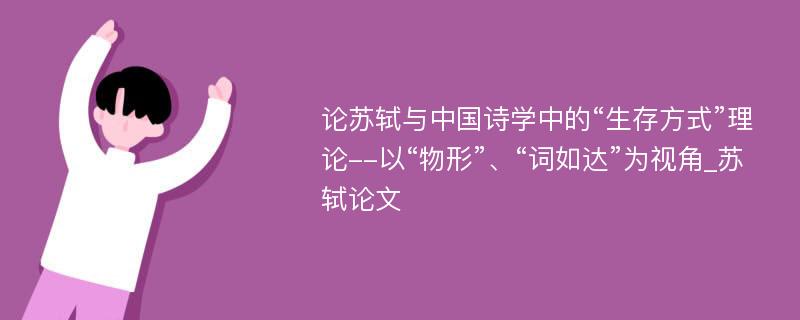
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从“随物赋形”“辞至于达”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随物赋形论文,诗学论文,活法论文,中国论文,苏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0)02-0217-04
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活法”说,是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的后期西昆体诗人胡宿(996-1067)最先提出,而非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1084-1145)[1]44-52。胡宿《文恭集》卷五《又和前人》诗云:“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2]胡宿还提出了与“活法”说一脉相承的“平淡、自然、清丽、豪壮”等诗学主张[1]44。胡宿去世数十年后,吕本中作《夏均父集序》,言:“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3]这里,吕本中阐释的“活法”说内涵,至少包括两层意义:其一,“活法”即“灵活地仿效、效法”义;其二,“活法”即“灵活的诗法、句法、语法”,既包括诗歌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流畅与圆通、明白与自然,又包括诗歌鉴赏中对原诗句直觉、自由、随意、创造性的理解和想象。
从胡宿到吕本中,数十年间,“活法”说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经过对文献的爬梳和考证,我们发现,苏轼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苏轼“随物赋形”“辞至于达”等主张进行研考,证明苏轼实为“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云: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辞达,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文集》卷四十九)
类似的话还见于苏轼《自评文》,其文云: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集》卷六十六)
上引文字虽是评谢民师,但“行云流水”云云,应是苏轼写作经验的“夫子自道”。
苏轼“行云流水”之论有两层意思,一是诗文创作纯任自然,毫无拘执,明白畅达,如“行云流水”一样“活泼泼地”。《汉语大词典》收有“行云流水”词条,即以《与谢民师推官书》为始见例;二是诗文创作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在《滟澦堆赋》亦言:“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文集》卷一)苏轼的“随物赋形”,是针对客观事物的不同形态予以形象生动的描绘,其意旨正是遵循创作规律的体现。文章无定“形”,然具体到每一篇文章或一首诗一阕词,它们却都是有“形”的,其“形”则是因所遇之事物——即内容——而定者,此亦今人所言:内容决定形式,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必须遵循的“活法”。“随物赋形”当是苏轼的重要发明,《汉语大词典》收“随物赋形”词条,即以苏轼《画水记》“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为始见例。
同样,苏轼所言“辞至于能达”亦有两义:一是指文辞或言辞的表述明白畅达。考《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苏轼认为屈原、贾谊及欧阳修等皆可谓“辞达”者。而扬雄则未也。扬雄主要表现于“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他和司马相如之文都不是“自然流出”的。在苏轼看来,唯有“自然流出”者才是“辞达”之文。南宋绍兴二年进士第一人张九成,在《论语绝句》一百首之《辞达而已矣》中即承苏轼此说而云:“扬雄苦作艰深语,曹操空嗟‘幼妇’词。晚悟师言‘达而已’,不须此处更支离。”[4]胡适评此诗云:“这一首是作者作白话诗的宣言书,可以当作他这一百首诗的题词读。”[4]张九成与苏轼对“辞达”的理解(如追求“平淡”“自然”)有一致之处。
“辞达”之另一义,指文章的一切“行止”必须要受以“辞”是否达“物”这个规则的限制。即未“达”时,则须“行乎所当行”;若“止”则“不及”矣。已“达”,则“当止乎不可不止”;若“行”,则“过”矣。
清陆珑其《四书讲义困勉录》卷十八引陶石篑(明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云:
是意乃辞之主宰,而辞特意之发见。意在,则行乎所当行;而意达,则止乎不得不止。(《四库全书》本)
怎样才能“辞达”呢?苏轼认为“辞达”就是把“了然于心”的“事物”之“妙”恰如其分地“了然于口与手”,即用文字、线条、声音通过口与手恰如其分地表达描绘出“事物之妙”。所谓“事物之妙”,就是指事物的“常理”,“常理”,亦即“神理”之意。苏轼云:“万物之中有妙于物者焉,此其神也。”(《易传》卷九)“辞达”即表达出“妙于物”之“神”。刘熙载云:“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曰‘达’、曰‘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5]“微妙”,即“神妙”。
考苏轼《众妙堂记》释“妙”(《文集》卷十一)可知,文中所言张道士的学生所读的《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玄”,指“道”。句意谓:得“道”,便进入“众妙之门”了。可见,“道”和“妙”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道”的特征就是“妙”,或称“妙有”。因此,称“道”、称“妙”、称“妙有”、称“理”、称“意”,称“神”,都是指同一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即事物所具有的表现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张道士等人看来,真正的得道者,是“无挟”——“无待”“技”与“习”而全凭“空”且“静”的,其“妙”是“径造”——“直达”的。如生物中的蜩与鸡,它们或“登木而号”不知停止;或“俯首而啄”不知仰头;这只是它们的本能而已。但当蜩茧蜕变、母鸡伏卵时,它们“无视无听,无饥无渴”,完全处于“无挟”“空”“静”之境,从而集中神力,等待时机,在瞬息之间,忽而化茧为蜩,破蛋成鸡,其“真妙”是“有待”的“圣智”和靠“技”与“习”成巧的庖丁、郢人所达不到的。这也是苏轼所谓“静则得,动则失”之意(《雪堂记》,《文集》卷十二)。
因为“辞达”是“以形传神”,所以苏轼认为“辞达”不易。个中原因,乃“求物之妙”至难,它“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苏轼甚至说过:“风不可抟,影不可捕,童子知之。”(《雪堂记》,《文集》卷十二)其次,即便有“能了然于心”者,他也不一定“能了然于口”;即便有能了然于口者,但他也不一定“能了然于手”!用苏轼另外的话来说其难处就是,“比者止于片言只字谢德于门下,而其诚之所加,意有所不能尽,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见于笔舌者,止此而已”(《谢吕龙图》三首之一,《文集》卷六十)。对于不能“辞达”,一点办法都没有。苏轼认为:“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的“辞达”者,都是“希世之异人。”(《王安石赠太傅制》)
“辞达”虽难,却是为文者必须遵循的法则。因为“文用”的大小,正取决于“辞达”的程度。所以,苏轼一再强调,“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答王庠书》,《文集》卷四十九)。可见,还有什么比“辞达”——“传神”之作更好的呢?
与“随物赋形”“辞至于达”相联系的,是苏轼的“平淡绚烂”说。苏轼《与二郎侄书》云:“凡文字,少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苏轼佚文汇编》卷四)又《答鲁直》五首之二云:“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这种由绚烂而至于平淡的主张,使苏轼和重质不重文者划清了界限。
苏轼所言“平淡绚烂”,其实是一种“枯澹”,也就是“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其《评韩柳诗》云: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文集》卷六十七)。
文中之“澹”即“淡”。苏轼还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云;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同上)。
“淡而有味”的主张,不仅使苏轼的“平淡”和“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评玄言诗语)迥然有别,并让其“辞达”说有了“重理趣”的基本要求。这也就是苏轼说的“寄妙理”。苏轼“辞达”对“达理”的要求是有“理趣”,即苏轼自谓“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也。故刘熙载云:“东坡长于趣”(《诗概》)。他的一些小诗,饱含人生哲理,极富理趣。如广为传诵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集》卷二十三)
此诗貌似观山,实际上却形象而深刻地阐发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奥秘,即欲见事物真相,必须超拔出自身处境的局限,从高处远处做全面立体的“活”的观照。仅二十八字,比一篇冗长的哲学论文诠释得更全面更精彩。
苏轼之“辞达”——“以辞达物之意”,实包含“文”“质”二义,即文中所言之“文理自然”之“文”和“理”。大致说来,所谓“文”或“辞”,殆即苏轼《净因院画记》中之“常形”;所谓“意”或“质”,则当是《记》中之“常理”。如此,则“辞达”,又可理解为以“常形”达“常理”,做到“常形”与“常理”的和谐统一。故苏轼《答虔倅俞括》云: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矣。(《文集》卷五十九)
文中之“是”即指“理”,“达是”即“达理”。
与“随物赋形”“辞至于达”“自然平淡”之论相关联的,还有“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说。考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
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李贽《骚坛千金诀·诗议》引学士方孝孺论及诗学“活法”时言:“作诗最重丰致,意欲圆,语欲活,气欲流畅。藏深思于寓盐之中,发天趣于模题之外,可也。”可见,唯有藏深思于寓盐之中,而发天趣于模题之外,才能达到“圆”“活”“流畅”之境界,而此境界正是中国诗学“活法”说所具之要义。
怎样才能做到苏轼所言“随物赋形”“辞至于达”“平淡绚烂”呢?一句话:心领神会。明代方孝孺在《苏太史文集序》中曾称苏轼与庄周、李白一样,都是“神于文者”;而方孝孺的《与舒君书》中又谓其为“辞达”者。
苏轼的“平淡”说是对唐代的韩愈、陆龟蒙,宋代的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等有关立论的继承。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即云“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昌黎集》卷五)、陆龟蒙《甫里先生传》亦云“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敌阵,卒造平淡而后已”(《甫里先生文集》)。而梅尧臣则尤多有向往平淡之语,在《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中说,“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欧阳修也认为梅尧臣“平生苦于吟咏,以闲适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六一诗话》);至于王安石,他的《题张司业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也与其师欧阳修的说法意同。不仅如此,梅尧臣关于“造平淡”的一些具体做法,苏轼也有承袭。苏轼在《题柳子厚诗》中说:“诗须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可见,“自然平淡”是苏轼“辞达”对“辞”的基本要求。它使苏轼的诗文不重蹈两晋玄言诗文“淡乎寡味”的覆辙而充满了理趣和情味,这也影响到有宋一代“主理”的诗文创作。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即承其“达理”之说而有所发展。张氏《答汪信民书》(《张右史文集》卷五八)在苏轼“达理”之上,特别加了一个“达事”。但对于此二者,他仍然偏重于“达理”。其《答李推官书》一文,以水作喻论说阐释,而以水作喻则出于苏轼。张耒说,为何有文?它是为“知理者”而设。因为有的“知理者不能言”,世上能“言”的“知理者”虽多,却只有能“文”的“知理者”之“文”才能独自流布。此乃苏轼“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意。张耒指出历代之人皆以“文”为“寓理之工具”。“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是不可能的。这些重“理”之论,亦是苏轼文中之意。而接下来以水喻文之论是张耒文章最精彩的部分,文中描摹水之“奇变”云:长江、黄河、淮河、海河之水,“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涛波,激之为风飚,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鼋喷薄出没”。如此奇观的发生,是“势自然耳”,是流水“因其所遇而变生”者也,是“不求奇而奇至矣”。此亦苏轼所谓“行云流水”,“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之意。张耒还对“辞达”之“辞”提出了要求,即主张简直,反对繁曲。他并不一味反对文之“奇”,只反对人为之奇,而自然如水之奇变者,他是赞同的。此与苏轼“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之说不异。前面说到,苏轼“辞达”即“以常形”达“常理”之意。而“常理”即“神理”。如此,则张耒的“达理”之说,也就是苏轼“以形传神”之意了。
明袁宗道《论文下》亦认为“辞达”即达理。文中除言明“辞达”是“达”理外,精彩的言论,也似乎是抓住了扬雄等人以“模拟”为“辞达”的病根。清人叶燮在“达理”“达事”之外,又加上了一个“达情”。其于《原诗·内篇上》云:
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清诗话》)
叶燮的论述,把苏轼“以辞达物之意”之“意”所包含的内容及“辞达”与“活法”的关系补述得更加完备清楚了。
综上所论,苏轼提出的“随物赋形”“辞至于达”“平淡绚烂”等诗文创作的重要学说,既是对唐宋前辈学者的继承,又对其后数百年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活法说”的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