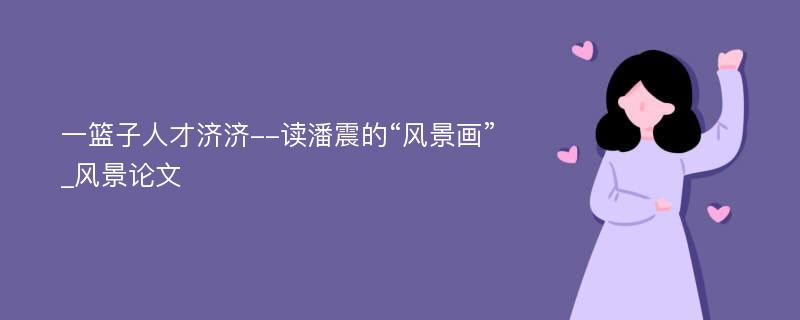
一只盛放才气的篮子——读潘真的《岁月#183;风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只论文,才气论文,篮子论文,岁月论文,风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是个北方的土佬,也还有点小聪明,比如说,买衣服要买上海出的,同样的材料做工考究些;买书要买上海出的,同样的内容错别字少些;临到读文章不由一愣,再按这个思路说下去,读文章要读上海人写的,会不会成为一种愚蠢?放下潘真的这本书,我安慰自己,以后怎么变不敢定,至少眼下还可以这么说,说了还不是愚蠢。
潘真的这本书叫《岁月·风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 月出版,是她的第二本书。第一本叫《永远的雨季》,我也看过。第一本封底有她的照片,黑白的,不太清晰,却分明是个纯真的少女。第二本封面也有她的照片,彩色的,很清晰,却分明是个少妇了。
变的是年岁,不变的是她的才情。看《永远的雨季》,你不知她的忧愁,忧愁也是一种快乐。看《岁月·风景》,你不知她的性别,人世的沧桑,抹去了胸前的凹凸,也抹去了脸上的红颜,剩下了一个苍老的嗓音在叙述过往。只有在或开头或结尾那朗朗的一粲,你会惊异于自己的颟顸,这聪慧的江南女子,她遮蔽了你,却又不失时机地提醒一下你。
作为上海《联合时报》的记者,职责与版面的双重限定,不可能像先前那样任情地涂写。面对的又多是成就斐然的长者,她收敛了自己的稚纯,也收敛了惯用的词句,不再铺张,甚至不再想象,把想象留给读者,只把清晰的事实,还有凝聚了的语句,留在白净的纸上。这是一种冷酷的训练,才女们会气得泪眼汪汪,才子们会气得仰天长啸。
潘真很从容。缘于专业的训练,缘于绝大的自信。她相信自己的才气足可应付裕如。至少这些限制,对她不会构成危害。限制会扼杀才气,人们多这么说,那得看你怎么看。限制也会成全才气。若才气真是一种气的话,它该是散漫无边的,不可捉摸的,而限制如同一个篮子,只有装进篮子里,人们才会看见,才会欣赏,才会赞叹。
法术种种,我这浊眼也觑见了一二。这便是,先用简练而又准确的语言,交代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出身根底,再腾出笔墨抒写那些传神的片断,写的时候也绝不平铺直叙,而是用精巧的结构去补足已言的言外之意,难言的未尽之言。简练不在词语上,最大的简练在结构上。当然,用词的简练也是不可忽略的。且看《故乡的莫扎特》的开头一句—
在纽约目睹著名的林肯艺术中心为“莫扎特年”轰轰烈烈上演所有莫扎特的作品,去国十一年的裘寿平遥念起他的故乡上海。
品读之下,颇有点像《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莫扎特年、去国十一年、裘寿平、故乡、上海……,几乎全是名词,不用反复试验我也相信,要把这些干瘪的名词嵌在一个句子里,这个句子还能顺顺当当地念下来,最合适的怕也只能是这么一个不算太长的潘式句子了。
无论篇幅长短,事件的选择都那么精当,起初我把这看作一种过程,披沙沥金的陶冶,去芜存菁的筛选。这样想过之后,马上就暗笑自己的愚呆:真要这样写,只怕这本书未出版,它的作者早就英勇地倒下了。光“梧桐清音”这个专栏,几年间每周一篇,还要编报,还有别的事体,该是多么的劳累。仔细琢磨,你会发现,那些看似精心的选配,更多的来自一种直感。这么想了,就这么写了,不多不少,正好。若苦思而成,先就不会这么圆融无碍。至于事件的选择,你以为定然是仔细的挑选,以我的猜想,有时怕也只有那么多,原本就不容她去选择。只能说她还会写,没有露出那份窘相。
她确实会写,有些篇章构思之精巧,不亚于欧·亨利的小说。比如打头的那篇《一个写书人的故事》,写的是词曲专家陈明源历尽艰辛,总算出版了一本专著,却不得不自己在福州路上摆摊销售。事情的经过本来就让人鼻酸欲泪,临到末尾,作者的笔头轻轻一拐,写道:望着他一丝不苟地为每一位读者签名、盖章,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抬头,但见一方红布在阴冷处瑟瑟,上书:“出版改革,作者自销”。一读到这里,你准得会心地一笑,叹一声,真是个聪慧刁钻的女子。
还有写白杨的那篇,开头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中写了这位名演员几桩人生大事,是大事,却一点也不枯燥,专从那些有意蕴的小处写起。比如写白杨的赴美,就说她恰遇到在台湾重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饰她演过的那个角色的女演员。写她与台湾的联系,便说她经常给江峡彼岸著名的女作家林海音写信问候,你以为她俩也是文艺事业上的交往吧,错了,“林是我初中时代的同窗,你说巧不巧?”一巧,不是这件事多么巧,巧在作者把它安排在全文的结尾处。一个是名演员,一个是名作家,该写一大段的,就这么说完就完了。
由这些精巧的处理,我想到了节俭,由节俭我想到上海人的精明,反来复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本质的东西没有包容进去。不失乡佬的本色,我又想到了上海的衣服,上海的书,我甚至想到了上海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怎就那么耐看,那简朴里,实在都隐藏着一种奢华。对了,内里的奢华,正是潘真散文艺术的质素。书里众多士女饱经忧患的人生,作者见多识广的胸襟,还有那支挥洒自如的笔,都是一种奢华,若没有这些奢华,怎会有这一篇篇俏皮的文章,怎会有这一本厚厚的书?
也不是没有遗憾。潘真的第一本书前,有夫君朱先生的序,这本书上也有。两本书又都有师友的序。横竖不过是一本书,何必考虑得这么周全。再说,书里的作家,应当是属于读者的,这时候夫君还守在一旁,也让人觉得威重有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