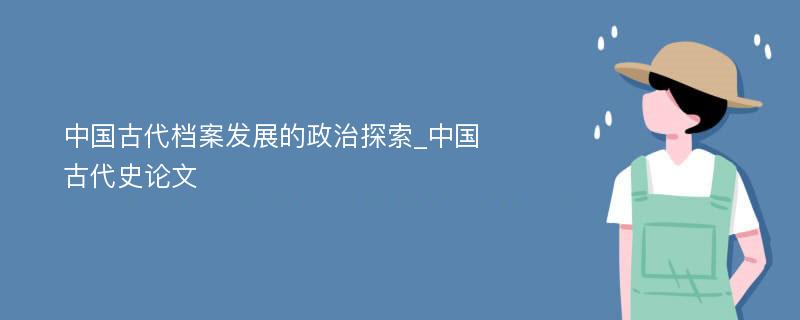
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政治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古代论文,政治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6)02-137-142
古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除了受到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制约之外,社会政治结构对其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完备而系统的宗法制度和严密的专制制度之影响尤深。
一、宗法制度的完备和延续对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
宗法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几千年、影响特别深远的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它约产生于商代后期。[1] (P44)西周春秋时期,宗法制度与政治统治相结合,达到了最发达、发展最充分的时期。战国秦汉以后历代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宗法制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存在形式虽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一脉相承,它以宗庙制度、分封制度、家族制度等为主要形式制约和规范着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并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
(一)宗庙制度与古代中国档案事业
宗法制度的首要是宗庙制度。商代几乎所有先王都立有尊庙.西周建立后,更将宗庙祭祀制度化。秦汉以后宗庙祭祀制度被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古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与宗庙祭祀制度关系密切。
1.宗庙是古代中国许多重要档案形成和保藏的重要场所
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商代甲骨档案,主要是在宗庙中形成的。商人信奉神权,凡是商王的活动和国家大政都要请命神祖,卜问吉凶,祈求保祐和赐福。甲骨刻辞档案绝大部分是商王在宗庙进行占卜活动的成果。周代的重要政治活动都要在宗庙举行,从而在宗庙形成了许多政务档案。周王继承王位、诸侯国君即位、卿大夫就任官职都要在宗庙中举行仪式。天子举行分封诸侯、任命官职的“策命”仪式也是在宗庙中进行。《礼记·祭统》说:“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太庙,示不敢专也。”此外,宗庙还常常是举行盟誓并形成盟书档案的地方。①
商周时期在神权政治影响下,王朝中央重要档案置于宗庙保藏。从考古发掘情况看,甲骨档案主要出土在宗庙建筑左右半穴居式地下室的圆窦和方窖中。周代的档案收藏机构“天府”即周代宗庙之收藏机构。《周礼》卷二十:“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秦汉以后,宗庙仍是形成和保藏档案的重要场所。西汉高祖刘邦建国,以铁券制作符契文书颁赐功臣,所形成的铁券符契即保藏于宗庙。《汉书·高帝本纪》载“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东汉以后历代沿用此制。明清两代的皇史宬延续了历代宗庙收藏档案的遗风。
重要档案形成于宗庙并藏之于宗庙,是因为宗庙在古代中国的世俗政治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头等位置,宗庙是帝王统治权的源泉。所谓“君权神授”,帝王乃天之子,而古时“王者天太祖”[2] (“礼三本篇”),即尊祖为天。王朝的统治权力源自于祖、源自于天,宗庙是一切政治权力之源。所以作为统治权力的一切象征和凭证都要珍藏于宗庙。
各类重要典法和官府文书、王室谱牒等重要档案与象征王室权力的各种镇国宝器形成和收藏于宗庙,亦强化了宗庙的至高地位。即所谓“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3] (“张仪列传”)。消灭一个国家也以“毁其宗庙,迁其重器”[4] (“梁惠王下”)为标志。
2.宗庙制度对古代中国档案的载体形式有直接影响
殷商宗庙祭祀占卜是甲骨档案形成的直接原因。在商人看来,“麟凤龟龙,谓之四灵”,[5] (“礼运”)龟是首选的“通神灵物”。故龟甲成为商人祭祀占卜的重要材料并成为商朝档案的重要载体。而使用牛胛骨作为祭祀占卜和记录的材料,除了因为牛胛骨与龟甲一样适合于占卜和书写之用,更重要的原因是牛也是敬神事祖的主要牺牲。
西周宗庙祭祀的发展促进了金文档案的形成。西周出现以青铜器作为书写材料的金文档案是宗法政治发展的要求和结果,也是青铜器自夏商以来主要作为祭器发展的结果。西周时期,神权政治已退居其次,宗法制度得到了空前发展并渐趋完备,并形成了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的等级制度。[5] (“王制”)因此作为与神明沟通的卜筮活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相应地因卜筮而产生的甲骨档案也成为历史;而尊宗敬祖的宗法祭祀活动要求作为主要祭祀器物的青铜祭器的相应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以青铜器为载体的金文档案。[6] (P169)
西周各级贵族将这些作为祭器和礼器的青铜器视为等级的标志和名位的象征,称之为“重器”。“各级贵族都要在钟、鼎、盘、盂等器物上铸字铭文,以显示其名位而传后世子孙。特别是周初,姬姜宗族子弟,因其辅助文、武伐商有功,分封授爵,成为大权贵,他们把自己或父辈的贡献以及王的赐命铭铸在青铜器上成为名位凭证”。[7] (P59)另外,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祭祀者往往追述祖先的功烈,告祭自己的荣誉(尤其是得到周王的封赐),并将之铭铸于青铜祭器,以加强自己在宗法中的地位.如著名的毛公鼎铭。
(二)宗法分封制度与古代中国档案事业
周代开始实行分封制。西汉以后历代对分封制度有所沿袭。分封制度在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产生有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分封促使大量誓约档案的产生。
1.周代分封产生了大量的盟誓档案
西周的分封制度包括对诸侯的分封和王臣的任命。诸侯接受周王的封号、承认周王室的天下共主地位,并不仅仅停留于口头承认或朝觐周王,他们还要参加周王室召集的会盟,与周王室订立盟约,在盟约中确定诸侯与周王的臣属关系以及诸侯的权责范围、诸侯之间的关系等。《吕氏春秋·诚廉》、《尚书·微子之命》等文献对此有详细记载。克罍铭文记载了周王室分封召公时与召公会盟的史实。[8] 这种会盟在东周时仍有孑遗.如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与誓,封爵之”[9] (P404)。
周代分封诸侯卿士产生了大量的盟誓档案。这些盟誓档案除了要保藏于“盟府”,受封者还要将受封的情况铭刻于青铜器物,保藏于宗庙。
2.历代分封产生大量符契档案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中原后,一改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实行皇帝中央集权的统治,但很快亡国。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仿周代实行分封,“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百四十有三人为侯,……始作铁券”。[10] (“高帝本纪”)形成了铁券档案,也称为铁券丹书或称为丹书铁契、金书铁券,分左右二者,左颁功臣,右藏内府,这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符契文书。
西汉以后历代分封不断。帝王在封赠诸侯和功臣时,都要颁赐诰券(即铁券)。因分封而产生了大量的铁券符契档案。《东观汉记·孝桓皇帝》中记载:“盖登有璧二十,圭五,铁券十一。”《明会典》卷六载:“国初,因前代之制,列爵五等,非有社稷军功者不封;……所封公侯伯皆给诰券,或世或不世各以功次为差。”《万历野获编》卷五也载:“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词,底刻身及子孙免死次数;质如绿玉,不类凡铁,其字皆用金填。”
(三)家族制度的延续与古代中国谱牒档案的长盛不衰
春秋时期,以周天子为天下之宗的宗法制度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以家族制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宗法制度得到了延续和发展,直到清代,乃至今天,仍以各种形式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家族制度的延续对古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影响最直接地体现为谱牒档案事业的长盛不衰。
1.家天下的延续与皇帝玉牒的长盛不衰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2] (P46-47)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王室谱系的修纂和管理。
在西周宗法制度下,王的嫡长子和不同等级的贵族有着世袭王位和各种爵位的特殊权利,而谱牒正是这种特殊权利的文字凭证。为此,周统治者特别设立了专门官员来掌管王室谱牒档案。② 诸侯国也设有官员掌管诸侯宗族事务和谱牒。周代世系档案的编纂体例为后世帝王所沿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丞相之下设立宗正,掌管皇族谱牒和皇族事务。此后历代王朝都设有宗正官掌管皇族谱牒。唐置宗正寺掌修皇族谱牒,设置修玉牒官。宋沿唐制,宗正寺掌叙宗派属籍,置玉牒所,掌修皇族的世系谱牒。以帝系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分等级纂修皇族宗亲五种族谱: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皇帝玉牒、仙源类谱和宗支属籍。明清设宗人府掌修皇族谱牒,每十年纂修一次玉牒。[11] (P73-74)
2.世家大族的发展与隋唐以前官修谱牒的兴盛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宗法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始终非常稳固。经过两汉时期较长时间的安定环境,东汉后期,一些强宗豪右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门阀世族。这些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为了保持优越的门第望族地位和既得利益,防止寒门混入世族,都十分重视对谱牒的编纂。
历朝政府也十分重视谱牒档案的编修和管理。隋唐以前历代王朝都设有图谱局,负责编修和收藏天下族谱,以作为选官任职的参考。③ 秦王朝“保存有各种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官吏名籍和官籍,还有市民的市籍等”。[7](P92)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门阀政治的盛行,官修谱牒发展到最高峰。唐代谱学家柳芳曾指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之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12] (“柳冲传”)
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科举制,限制了门阀势力的发展,经过隋末战争,世家大族受到巨大冲击。但是,旧的豪门士族仍有相当的势力。故唐初围绕着谱牒的修撰,新旧地主势力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唐太宗时重新修订的《氏族志》100卷最终作为官方权威谱牒颁行于天下,使得这场较量以新地主的胜利而告终,世家大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后来又经武则天和唐宪宗时又分别修编天下谱牒,形成《姓氏录》和《元和姓纂》等两部大型官修谱牒,世家大族势力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官修谱牒的工作至此也画上了句号。
3.家族制度的非政治化与宋元明清私修谱牒的发展
隋唐以后,宗族组织不再成为构成国家统治的政治力量,家族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非政治化状态。宋代不再设官府谱局,除皇家玉牒外,不再组织纂修谱牒。但是宗族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其社会功能反而突出。为了发挥宗族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宋代提倡私家修谱,以增强宗族的社会凝聚力,维护社会稳定。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特别下诏要求文武群臣修家谱,故宋代私家修谱风气极盛。许多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学士如欧阳修、王安石、苏洵、司马光等,都亲自主持私家修谱,创制谱例。
元明清三代,私家修谱继续发展。尤其是清代,中国的宗族活动相当发展,统治者看到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支持宗族编修家谱。康熙、雍正皇帝都曾以圣谕的形式鼓励百姓修家谱,清代私家修谱的风气更盛。这种风气延续到民国时期。
二、专制制度的强化对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深刻地制约和规定了古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
(一)专制制度的强化与古代中国档案官吏地位的变迁
古代中国专制制度呈现出逐渐强化的轨迹,其主要特征是君权的强化与作为百官之总的宰相权位的削弱。相应地,古代中国档案官吏的地位也随着相权的削弱而渐趋下降。
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官员的商周史官,其地位相当显赫。如王国维所言:“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13] (“释史”)商代的史统称为巫和史,专掌占卜、记事和祭祀,地位极其尊贵,在很多情况下,巫拥有与商王同等的决策权。周代的史官机构称为太史寮,与卿事寮并列,是中央政府两大部门之一。史官以大史为首,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的太师、太保。周初的大史尹佚就与周公、召公、太公并称四圣。
西汉以后,随着皇权的加强,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档案官员的地位渐趋下降。西汉御史府是中央政府主管文书档案的主要机构。御史府的主要属官是御史中丞,其地位已远不及商周时期诸史官高贵显赫。汉武帝强化皇权,御史府与丞相府的职权受到削弱。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央逐渐形成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治的中枢系统,文书档案也由三省分管。隋唐时期,三省制度进一步完善,档案机构和档案官员的地位和权力进一步削弱。宋代官制紊乱,职权分散,三省的职权更为削弱,掌管档案的机构进一步分散,档案官吏职位普遍不高。明朱元璋干脆撤销中书省,宣布永远废除宰相,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君主专制集权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这时负责文书档案工作的机构主要是内阁。清代随着军机处的设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得到完全确立。明清时期,文书档案的主要领导机构内阁和军机处只不过是承旨办事,呈宣皇命,协助皇帝办理事务,其地位极低。
作为政务文书的制发和管理部门的古代中国档案机构及其官吏,是王朝中央上层建筑核心构成,但其权位的尊隆与君主专制的要求是不相容的。按照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要求,当档案机构及其主管官员地位上升到对君权构成威胁的时候,皇帝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削夺档案管理机构及其官员的权位。故古代中国档案机构每到一定时期就发生变换,往往由位卑权弱的亲信部门取而代之,其结果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档案机构及其官员权威的不断降低。
(二)专制制度下土地档案与户籍档案的完备
中国古代历朝对土地档案和户籍档案都非常重视,形成一整套土地和户口管理制度和档案制度,并日趋完备严密。
周代就已经有了管理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档案,称为版图。版是户籍档案,图是土地档案。《周礼·秋官·司民》载:“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礼记·内则》记周代人丁名籍档案的形成和保藏曰:“夫告宰名,宰辨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
战国时期,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征收而建立了上计制度,形成大量的计书档案。这些计书档案副本由郡县保留,正本交由中央存档。
西汉建立后,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计书制度,形成户籍和赋税统计上报的计簿档案。
南朝的户籍档案“黄籍”详细记录每户的情况,作为政府科派赋役和区别士族、庶族的依据。
隋唐时期,进一步加强了户籍、赋税和舆图档案的管理。配合租庸调法的施行,隋唐对户籍档案的编制十分严密。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大索貌阅”,核查户口,并实行“输籍法”,规定各户应纳税额,写成簿籍。唐初也进行了户口核查。唐代的户籍档案称为“手实”,赋役档案称为“计帐”。
宋代为解决沉重的军费、官俸和对外贡款等,对赋税户籍档案尤其重视,严格地编订了户籍,根据土地和资产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主户又分为五等,其户籍称“五等簿”或“版籍”,规定每三年修造一次。
随着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强化,明清两代的户籍和土地档案更加完备,管理也更为严密。明代记录土地、人丁和赋役的文书称为“黄册”;登记土地所有权的文书叫“鱼鳞图册”。“黄册”和“鱼鳞图册”总称黄册。明代黄册每十年编造一次,一式四份。黄册是明代最普遍、数量最多的文书。著名的后湖黄册库就是集中保管黄册的专门档案库,由中央直接领导。黄册档案不仅有一套严格的编制制度,而且其管理也有一整套详细具体的规定。如黄册档案的用纸、晾晒、放置、查阅和保卫等都有十分严格的制度。清因袭明制。
(三)档案载体形式的等级区分制度
古代中国档案的载体形式也因受到专制等级制度强化的影响而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区分。
1.金文档案的等级差别
青铜彝器的等级差别决定了金文档案的等级区分。周代的青铜器是作为世袭权力和地位凭证的礼器,青铜礼器的使用具有很强的等级区别。如用鼎,周代逐渐形成了规定用鼎数量及与鼎配合的簋、鬲的数目的列鼎制度。西周初年,列鼎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只是尚未有一定的规格。到了西周中期,列鼎制度进一步确立。此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列鼎制度在贵族墓葬中长期流行。如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的虢太子墓就陪葬有七鼎、六簋、六鬲、二壶以及甗、豆、盘、盉各一件。次一等的陪葬有五鼎、四簋、四鬲、二壶及豆、盘、匜各一件。末等有鼎、盘、匜各一件。
2.简牒档案的等级区分
我国古代简牒档案和书籍,在简牒材料的使用上也体现出一定的等级区分。主要表现为简牒尺寸大小的差异。如用简,“依照汉尺的长度,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二尺四寸(约55厘米多),用以写六经及传注、国史、礼书、法令,即《说文》所说的‘大册’之‘典’;其次为一尺二寸(约27厘米多),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八寸(约18厘米半),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书籍。”[14] (P191)关于用牒,“据王国维考证,秦汉以来的版牒,除三尺之椠外,最长的为汉尺二尺,其次为一尺五寸,再其次为一尺,最短的五寸。版牒,一般不用于抄写书籍,而用于公私文书、信件。二尺之牒,用以写檄书诏令;一尺五寸的牒多为传信公文;一尺牒多用以写书信,所以书信古称‘尺牒’;五寸牒多为通行证,是通过关卡哨所的凭证。此外,汉代天子诏书,还喜欢用一尺一寸之牒,所以汉代文献中常有‘尺一板’、‘尺一诏’、‘尺一’等语。”[14] (P192)
3.缣帛档案的等级区分
我国古代的诰与敕等文书档案通常是用绢或绫绵制成的。其使用亦非常讲究等级秩序。如明清的诰敕就是按官品等级授给的。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诰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敕命,妇人从夫品级。诰用制诰之宝,敕用制敕之宝。”诰敕是由神帛制敕局织造的,并且按颜色分为苍青黄赤黑五种。诰敕的形制是卷轴的,卷轴也有官品等级差别。一品官用玉轴,二品官用犀轴,三品、四品官用抹金轴,五品官以下用角轴。清代沿袭明制。[15] (P50)
4.纸质档案的等级区分
纸质档案的载体也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区分。如黄纸,最初社会上通用的纸为黄纸,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君主专制的强化,黄纸的使用逐渐成为朝廷所专用,往往是只有皇帝颁下的文书才可以使用黄纸。因为按照五行学说,黄色居五色之中央,象征着权利和尊贵。
唐代以后,随着纸张的普遍应用,在文书用纸方面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当时的纸张因原料、色泽各有差异,其用途也有严格区别,一方面便于辨别不同的发文机关和文书种类;另一方面也是等级区分的需要。唐代中书舍人起草诏令文书用黄纸;翰林学士起草文书用白麻纸;皇帝为赏赐、征召而颁发的敕书用白藤纸,慰问出征将士的敕书用黄麻纸,对邻近少数民族国家国王的赏赐敕书用五色金花白背纸,任命将相的告身文书用金花五色绫纸。
(四)档案管理和利用的高度集中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有中央档案库,对全国的档案实行集中管理。商代的甲骨档案集中在商都的宗庙建筑中保管。周代的中央档案库是“天府”。天下档案文书的正本几乎都要收藏于天府。国家大法典要收藏于天府,④ 地方的细末档案文书也要收入天府保藏⑤。秦始皇统一天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3] (“秦始皇本纪”),全国的档案文书正本都要集中到中央供皇帝查阅。随着档案文书的增多和细分,汉代统治者建立了更多的中央档案保藏处所来收集和保藏天下档案,著名的有石渠阁、兰台、东观,西汉还有麒麟阁、天禄阁等,东汉有石室、宣明、鸿都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各类档案主要集中保藏于三省,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档案馆库,如唐代的甲库。宋代设置架阁库等收藏各类档案文书,将县以上的国家机关的重要文件集中在中央档案库。明清两代的档案更为集中。如明代的黄册档案,由县具体负责编制,县以下的坊、厢、里等基层组织将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16] (“黄册”),各县经州府将黄册档案上报中央,集中收藏于后湖黄册库。
历代的档案集中于中央,其主要作用是为中央王朝治理天下服务,真正能够利用档案的除了皇帝,只是中央的主要官员和负责档案管理的部分官员。应用的范围也相当集中、狭窄。除了用于赋役征调,主要用于编修实录、编纂前朝历史,以为治国之鉴,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长期延续,专制制度持续并不断强化,是古代中国档案事业产生、持续和发展的政治渊源。古代中国档案从形式、类型、内容到管理、利用等都深受以宗法制度、专制制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和规制。古代中国档案的形式和类型是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产物;其内容主要是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等政治生活的反映;其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变迁以及档案的利用是为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和强化服务的。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档案事业史,深深打上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烙印。
注释:
①《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单穆公拥立王子猛(悼王),“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平王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崔杼杀死齐庄公,联合庆封拥立景公时,“盟国人于大宫(齐太公庙)”。在宗庙中盟誓并形成誓书档案的做法到唐代仍见于史籍记载。《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中记述:“太后(武则天)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宗庙),铭之铁券,藏于史馆。”
②《周礼·春官·小史》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典系世,辨昭穆”。郑玄注:“系世谓帝王系本之居,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
③《通志·氏族略一》载:“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由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之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于私书。”
④《周礼·春官·天府》载:“天府,掌祖庙之收藏与其禁令”。《正义》云:“国之大法典其正本咸藏之”。
⑤《周礼·夏官·司勋》郑玄注:“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功书,藏于天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