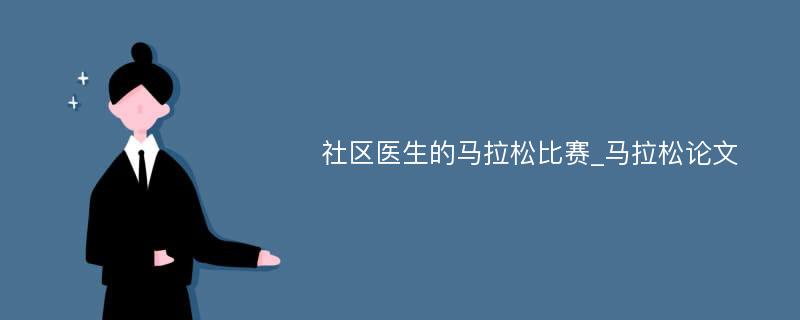
一个社区医生的马拉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拉松论文,医生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玮从小喜欢马拉松。他出生在东北,两脚丈量遍了小兴安岭的冰天雪地,从佳木斯的小学,一直跑到牡丹江边的医学院。大学毕业后,他怀揣一张当年上海知青的旧照片,一路南下找到了上海。也真是缘分,在那张泛黄的照片上,刘玮仅是上海知青怀里抱着的一个婴儿,才两个月大,但就凭着这点线索,刘玮在大上海找到了那位知青,最终又通过招聘,成了一名上海医生。 有段经历,对刘玮来说非常珍贵:他在上海一家医院主管过ICU(重症监护病房),时间长达6年之久。 这6年,他接触的都是危重病人。一面是贵重的呼吸机、生命体征监测仪、血氧饱和度监测仪……一面是痛苦的呻吟、求生的眼神、家属的泪水。ICU是医疗阵地最后一道防线,生命在这里睁大眼睛,狠狠瞪着死亡。许多患者重获新生,也有不少人最终逝去。刘玮没统计过两者比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6年,是他见证死亡最多的岁月。 当上社区医生后,刘玮才发现,那6年对自己产生了多大影响。对死亡做过那么多抵抗,才会对生命产生那么深的怜惜。这6年,被他看作是人生马拉松的前一小段。在这个赛段里,尽管自己手握最先进的设施、最强大的医疗手段,但还是被死亡和疾病远远甩在了后面。改当社区医生的2010年,才是他的转折点,就如马拉松途中那个“折返点”一样。他明白,要跑赢这个马拉松,那么在后半程,必须赶到疾病和死亡前面去。 “你认识刘医生,你就有希望多活10年。”蔚蓝小区一个居民跟我说。 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刘医生工作室”里。工作室设在居委会内,有20来平方米。病人排着队,刘医生和助手忙个不停。 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刘玮并不是这样“吃香”的。他上门推广家庭医生制签约,甚至还遭到过居民的奚落。女人轻蔑地看他,男人打手势请他出门:“对不起,我们不需要家庭医生。我们看病只去大医院。”一天下来,刘玮能听到无数次毫不客气的关门声。背着药箱转过身去,独自走在大楼后部冷冷清清的楼道里,刘玮只觉得气虚、胸闷、腿软。他突然发现,这感觉有点像马拉松途中出现的“极点”。在这最难熬的时刻,许多人会选择退出。但“老运动员”刘玮不会。他知道坚守或退却,全在这一念之间。如果选择退出,那多少个清晨的汗水,也就白洒了。跑了这些年马拉松,他对付“极点”已经有经验:一要有“定力”;二要深呼吸;三要想着超越后的轻快……每次摆脱“极点”,他都能品尝到挑战的喜悦。 现在他也不急。他懂这个理:只要放低身段,踏实去做,哪有老百姓不接受的好事。 “放低身段”,刘玮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不要把医生看成是病人的“救世主”,而要把自己当作居民的“自家人”—— 譬如这一天,他在医院门口看到这样一幕:三位老人相扶着,颤颤巍巍向他走来。中间的老太太,八十来岁;一边是她丈夫,也这个岁数;轮椅上是她老母亲,说是已有100岁! 刘玮想,这一家来看一趟病,也太艰难了吧!如果给他们建立家庭病床,定期上门诊治,老人们不就轻松了吗? 可惜一问,他们住得很远,不在自己辖区里。也就是说,他们是辖区外病人,没他刘玮什么事。 可惟其住得远,刘玮心里才格外痛。他问自己:如果这三位老人是你爷爷奶奶,你舍得吗? 刘玮的最后选择是:为他们建立家庭病床,就在自己辖区之外。老人走的路,以后他来走。面对这个加起来近300岁的老人之家,他没法无动于衷。 又譬如这一天,一对夫妻来医院,拿出一袋CT片子递给刘玮,说:“我家老娘最近查出了肿瘤。医生你看,还有什么办法吗?” 刘玮看着片子,问:“老太太几岁了?”答:“80多了。”问:“她知道自己患了肿瘤吗?”答:“我们瞒着她呢!” 刘玮放下片子,打量眼前这对夫妇。他发现,他俩气色也不好。一问,果然也是多病多灾的人,妻子还刚开过刀。 诊室里很静。刘玮默默移开视线。除了泪水外,他还在夫妻俩眼里,看到了绝望与无奈。全家都是病人,现在还增加了一个绝症!他问自己:如果你是这家的一员,会怎样? 他对夫妻俩说:“你们先不要急。老人的病情我再研究下,会尽快给你们一个回音。” 当天晚上,他用微信联系上了导师,一位工程院院士。院士跟他作了长时间的探讨,最后给了他一个验方,还详细附上了验方所需的40种蔬果杂粮的名字。 这对夫妇后来我遇上了。他们告诉我:从那天开始,刘医生给他们全家治了3年病。 “结果怎样?”我急问。 丈夫拿出手机,给我看老太太的照片:“你看,老娘精神好哇?3年来,她没吃一粒抗癌药,就吃刘医生开的验方。CT复查了几次,老娘的肿瘤就这样,一点都没扩散!你讲是奇迹哇?”“你们呢?你们身体怎样?”我又问。妻子说:“我们也很好!借老娘的光,刘医生也指导我们养身健身。你看我们现在!”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这样的事情一多,大街小巷男女老少,便都知道了刘玮的名字。 刘医生特别感谢居委的大姐们。她们有本事,一能帮他“拉场子”,二能给他“火上浇油”。每次会议结束后,她们都会让居民留下,把麦克风交给刘玮,请他给大家讲授医疗保健知识。刘玮珍惜这样的机会,每次都会认真备课,现场解答居民疑问,还进行简单的诊治示范。他的知识,他的口才,尤其是他诚恳的目光,打动了所有人。有的居民只跟刘玮“互动”了一次,便心悦诚服,问刘玮要名片、要电话…… 口口相传中,来找刘医生的居民越来越多。最后竟有2800多人——大多是老弱病残——争着要跟刘玮签约。“签字画押”的核心内容是:愿意把生命交给刘医生“管理”。 刘玮每签完一份协议,都觉得,在那场与死亡和疾病的赛跑中,自己又领先了一步… 看完所有病患,刘玮才有空跟我聊天。说得最多的,是全科医生的事情—— 在美国,人们90%的健康问题,都会交给家庭医生处理。家庭医生拥有全科医生执照。他们是患者就医的第一道门槛,不仅决定诊疗的基础方案,连转院、转诊等大事,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奔着一场特殊的“马拉松”,刘玮现在也上了这条跑道。通过严格考试,他取得了全科医生资格。他绝不是有些人眼里的“万金油医生”、“三脚猫医生”。即使与三甲医院拥有博士头衔的同行相比,他也一定毫不逊色—— 他发明的“腕式高血压治疗仪”,已经获得国家专利。他撰写的论文,有的发表在《世界中医药》《中华全科医师杂志》上,更有的发表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上。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在区中医院学推拿。他对我说:“许多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而要让患者远离无知,我自己必须更加充实。” 比起行医这场“马拉松”来,学习是一场更艰巨、更漫长的“马拉松”。 在这篇短文行将收尾的时候,关于刘医生的马拉松,我还要讲个小故事—— 这天,居民晁玉玲的老母亲突然提出,要戴一戴刘医生的马拉松奖牌。 这可是件稀奇事儿。刘医生接到电话有些激动。他愿意社区居民了解他是“马拉松哥”,但想不到的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患者,对此也感兴趣! 他一进门,就掏出那枚闪闪发光的马拉松奖牌,郑重其事挂在老太太胸前。 老太太笑了,脸也红了,眼睛分外明亮。也许,这是她第一次戴上金色的奖牌。那份激动与羞涩,把她带回到少女时代。 刘医生也笑了,搀住老人手,合了一张影。从进门到拍照,老太太一直看着他,念叨着三个字——“刘医生,刘医生!” 这里顺便介绍下:老太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她已经记不起自家人的名字。对着自己的亲女儿,她口口声声叫的是“老板”。 只有“刘医生”,她从来没有叫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