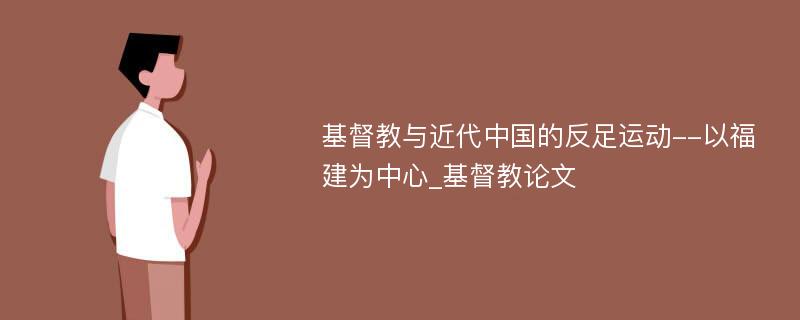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以福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福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教与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的反缠足问题,学术界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注:可参见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杨兴梅《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林维红《清季的妇女不缠足运动(1894-1911)》,《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6期;赖某深《民国时期废缠足陋习的历史考察》,《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李凤飞、暴鸿昌《中国缠足与反缠足的历史考察》,《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陈文联《论近代中国的戒缠足思潮》,《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等。)。但受史料不足的限制,既往的研究多关注民国时期,对晚清反缠足运动、尤其是基督教反缠足运动的研究相对薄弱。个别有所涉及,也多数是浅尝辄止,未能就这一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中,基督教的首倡之功、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不可否认。本文以近代福建为例,对基督教的反缠足运动略作探讨。
一、迷惑与思考:传教士对缠足的认识
当新教传教士来到福建,看到了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奇特现象——女人的小脚。他们苦苦思索,“究竟是什么英雄般的气概让中国妇女能忍受这种带给她们终生痛苦的风俗”[1](P308)。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说,她们深知缠足的折磨,当年她们痛苦的一幕历历在目。然而一旦做了母亲,她们为何又将女儿的双脚紧紧裹起,这也是传教士初来中国的困惑。“许多野蛮部落曾经发明一些残忍的手段来毁损和破坏人的身体,但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和优良传统的国家,仍然保留有这种行为,真是闻所未闻”[2](P18-19)。在对缠足习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后,传教士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中国妇女沿袭了缠足陋习。
第一,缠足千余年来代代相因,已经演变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中国人“把祖先流传下来的任何东西都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绝不允许人们有一指头的改革”[2](P30)。习俗并非意志与理性的产物,而纯出于自然,是人们约定俗成为一种心理和行为的默契。习俗出于自然,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日用之而不知,于不知不觉中铸就了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为,当一种异己的力量试图取而代之时,它便会显现出强大的反抗力量。它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和组织产生约束力,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观念心理和行为。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习俗具有稳定的传承性,一旦某种习俗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便开始形成一种标准化、模式化的存在状态,任何改革的建议都被视为对它极大的轻蔑和不尊。曾于上个世纪初来中国的美国人罗斯也认为,缠足“是每一个阶层的人们,无论是穷的还是富的,都必须遵循的习俗”[3](P182)。习俗的特征正在于它的传承性和顽固性,当传教士向人们宣扬天足思想时,多数人随即不假思索地给予否定,因为它违背了传统和习俗,至于正确与否则没有人考虑。
第二,大足女子受到社会的嘲弄,尤其是同性人的讽刺,使其无法完成个人社会化的角色转换。当小脚成为社会流行的模式,个别不愿意忍受痛苦而不缠足或没有资格缠足的女孩即成为社会的另类,她们不仅丝毫享受不到天足的便利,反而会因此大受责难。“在这里我可不敢例外,邻居们会嘲笑我、讽刺我。想想我可怜的女儿吧,同伴嘲笑她,邻居鄙视她,她的整个生活变得一团糟”[2](P33)。为什么不敢例外,母亲首先考虑的就是周围无形的压力和极度讽刺。在全社会普遍形成以小脚为美的情形后,缠足便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心理,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除开欲缠而没有资格缠的奴隶外,任何与之相违背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异端。一看到别人与自己的小脚不同,许多人便起而攻之,“快看刚划过的那两只船”[4](P114)。当来福建的传教士怀着极大的不解观察中国妇女的小脚时,她们也同样对外国女性的大脚感到惊奇。美以美会传教士柯林(J.D.Collins)抵达福州后,“这里的妇女对柯林夫人的那双天足尤感兴趣”[5](P40)。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必须具备社会化个性,而只有处于社会之中并经过社会的磨练,人才能成长为完全的人”[6]。也就是说,人必须取得社会的认可才能成长为具有“社会资格”的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社会认可的标准和模式各不相同。当缠足风俗在社会各个阶层风行后,它便具有了社会意义,成为等级区分的标志,代表了一种身份象征,并以此与贫寒妇女相区别。由于不缠足的女子破坏了社会普遍认可的小脚美的标准,她们无法与时代达成一致,自然也就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这意味着她们高贵的身份或追求高贵的心理即将被取消而与奴隶为伍。任何人都不愿如此,“她们宣称,即使再忍受一百倍的痛苦也比不缠足要好”[2](P76)。在缠足成为高贵的象征后,社会便要求任何处于这一阶层的人或努力追求进入这一阶层的人必须缠足。
第三,女性面临的现实问题,即由于男权社会畸形的审美观而给女性造成的婚嫁压力是妇女缠足的根源。令许多传教士感到不解的是,既然这是妇女自身的行为,为什么企图通过影响妇女进而让他们放弃缠足的任何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湖(J.Macgowan)认识到,这是由于中国的男子“不愿意妻子和女儿因缠足而遭受责难,也不希望找任何大脚女子为妻”[2](P56)。这里的论述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女子不缠足有损男子的面子。面子是近代来华外国人最迷惑的问题之一,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面子问题至关重要。一个家有大脚妻子和女儿的男子会受到周围人讽刺和挖苦,常常令其无地自容。当纤纤小足成为美的标志时,对天然之足刻意裹缠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其二,男子不愿娶大脚女子。当人们谈婚论嫁时,必然要嘱托媒人替男方问清女子的脚有多大,几岁缠的脚,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同意。“当一个女孩脚特别小时,朋友就会称赞她长大后肯定是个好母亲,当一个女孩即将出嫁时,人们关心的不是她是否漂亮,而是她的脚有多大”[7](P13)。在厦门的Pechnia地方,一位信徒的女儿因进入教会学校而不缠足,导致该女出嫁时遭到男性家长的反对,此事令传教士两面为难[8](P202)。在脚的大小与人的美丑直接相关的中国,缠足成为普通女子进入上层社会的途径。葛佩兰(KWOK Pui-lan)指出,“当三寸金莲成为上等阶层的象征,代表着良好的形象,而自然足成为低等社会的代表而为人们所鄙视时,即使是穷苦人家的父母,也坚持给女儿缠足,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嫁个富裕人家”[9](P110)。
第四,传教士也思考了问题的另一面,缠足毕竟是女性的行为,尽管它有着取悦男性社会的涵义,但女性自身对小脚美如何看待呢?毫无疑问,由于十分痛苦,最初女性是被动缠足,但当小脚美成为全社会的流行语言,许多女性便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追求。小脚美不但为男性所普遍认可,也为广大女性所接受。也就是说,此时小脚(缠足)成为女性的内在需求。在她们眼中,小脚就是美的,大脚就是丑的,这是中国缠足之风盛行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妇女看不起那些敢于丢弃裹脚布并大胆展示自己双脚的个别人,甚至一些已经加入天足会的基督教妇女后来又偷偷缠上,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她们认为那是丑陋的,是下层奴隶的作为。当小脚美的观念根深蒂固以后,“小脚”即成为广大妇女追逐的目标,即使是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一些女孩子,因为父母受传教士影响不愿意给她们缠足,而她们自己却找来带子自行裹脚。一个女孩由于缠足而濒临死亡,当医生责怪其父亲不顾女儿的死活强行给她缠足时,父亲感到很委屈,“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她自己想把双脚缠得紧紧的,她的目标是在当地没有人比她的脚更小”[2](P38)。一提到放足,许多妇女的第一反应就是“每个人都会笑话,我不会那么丢人”[10](P56)。关于这一点,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也认识到,“女子缠足习俗有力地揭示出中国人性格中先天的特质,特别是为了达到外观上这种所谓美的标准而甘愿忍受巨大而持久的痛苦”[11](P259),很显然,忍受痛苦就是为了追求美。没有女性自身审美观的改变,缠足习俗便不会消失。
面对重重压力,传教士从基督教的普遍道德出发,认为缠足是对上帝的侵犯,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缠足问题只有依靠上帝。
二、开风气之先:传教士的反缠足运动
其实,早在来华之初,部分传教士、尤其是医疗传教士已经就缠足问题展开争论(注:1869年,北京的德贞(J.H.Dudgeon)和广州的嘉约翰(J.G.Kerr)分别就这一问题在《教务杂志》上表述了各自的观点。)。福州的某些教会学校,已经成为反缠足的先行者。1869年,福州的一个传教士强烈要求教会迅速采取措施反对缠足,得到HOK-CHIU的回应,表示完全赞同上述说法,并认为当务之急是付诸行动[12]。
1874年,麦嘉湖率先在厦门成立天足会,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关于厦门天足会的情况,既往的论著也有所涉及,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天足会的一些基本情况还付之阙如(注: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厦门天足会论述非常简单,季礼斐(MacGillivrary Donald)云,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制止妇女缠足的组织1874年在厦门成立,出席会议的有传教士和本地妇女的代表,人们订立了一个誓约反对缠足,40多个妇女在上面签字;德炯(Gerald F.De Jong)云,1874年,厦门三公会发起成立了一个反对缠足的组织——天足会,这是提高妇女地位的重大步骤之一,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此类组织,他们订立了一誓约反对缠足,40多个妇女签字;相比之下,葛佩兰的叙述较为具体,但她把成立的组织称为“戒缠足会”,台湾魏外扬也持此观点。以上论述分别见MacGillivrary Donal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Shanghai,1907,p375;Gerald F.De Jong,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Michigan,1992,p128;KWOK Pui-lan,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1860-1927),Atlanta,1992,p110;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宇宙光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本文主要利用麦嘉湖的有关论述,并结合其他史料,期望就此问题进一步探讨。
1874年,麦嘉湖将准备召开妇女大会讨论缠足问题的会议通知发出后,在厦门犹如晴天霹雳四处传播开来,许多人向他暗示了此事的严重性。“我敢肯定如果按照你的计划行事,必然要引起混乱”[2](P49)。很快,麦嘉湖即发现召集妇女大会使他陷入了困境,不但中国妇女本身不晓得她们有聚众发泄不满或建言献策的权力,而且苛刻的习俗严格地限制了妇女的活动,家庭就是她们的全部生活空间。
会议召开之时,令麦嘉湖惊喜的是,有六七十人应邀前来。在集会上,麦嘉湖首先就召集她们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说明。他号召在上帝的召唤下迅速觉醒,组织起来反对缠足。发表完自己的演讲后,麦氏要求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在这次集会上,麦嘉湖特意选取了两位支持反缠足女士的言论来说明会议所取得的成绩。一位模样俊俏的年轻妇女认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为教会对待缠足的态度所深深忧虑。你的努力唤起了我的觉醒,它促使我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错误:我们基督徒竟然也赞同这种给我们自身和厦门的姐妹们带来如此痛苦的缠足陋习。我有七个女儿,人们告诉我如果不给她们缠足,将来长大以后找不到丈夫。好吧,她们能否找到丈夫我不在意,如果真的这样,我让她们全都留在家里陪我,给我煮饭[2](P59-60)。
一位老妇人指出:
为什么你这么长时间才召集我们开会呢?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最后几乎绝望。感谢上帝,它终于来了,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个罪恶的缠足了。唯一的遗憾,我仅仅能为反缠足运动做一点微小的贡献,我本人和我的女儿已经没有办法放足了,只要我活一天,就不会让我的孙女缠足[2](PP62-63)。
细解两位妇女的宣言,我们认为麦氏的描写似有不实之处,它不像是中国女性的言论,而更像麦嘉湖借她们表达自己的观点。
首先,麦氏本人也承认,他的15年努力没有什么效果,尽管有几个人回应他的呼吁,但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缠足。两位女性能讲出上述言论,值得怀疑。即使漂亮女士自身不在意她的女儿能否找到丈夫,不在意邻居的嘲笑和讥讽,乐意让她们在家里煮饭,但这并不等于她的女儿不在意,并不等于她的丈夫不在意。当时中国家庭以男性为核心的状况也决定了她的女儿缠还是不缠并不完全取决于她本人,甚至连其丈夫也不能独自决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为教会对待缠足的态度所深深忧虑”,这个忧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自麦氏的忧虑。可敬的老妇人既然她和其女儿已经缠足多年,很难说“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如果当年她能有如此觉悟,她的女儿也不会成为缠足的受害者。她可以不让自己的孙女缠足,同样这不能代表其孙女的意愿。
其次,我们注意到,麦氏所列举的两例均是反缠足的典型,但出席会议的其余人中是否有支持缠足的代表,他们对于缠足的看法如何,是否也像上述两例一样对于反缠足充满了憧憬和渴望?尽管麦嘉湖没有相关的论述,我们依然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探知一二。在成立天足会时,麦氏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誓约书让支持反缠足的人签字,“在开始时,极少有人冒险参加这一组织。许多妇女非常害怕,不敢迈出这大胆的一步”[2](P65)。很显然,缠与不缠并非她们自己能够做主。在天足会举行的第一次半年度会议上,许多人争论缠足是永远不能废除的。既然如此,我们很难相信在初次集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此,笔者认为,麦氏这里故意忽略了不同意见而突出了两位女士的看法,其实正是欲借此表达自己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麦嘉湖此次召集会议仍然取得了成功,废除缠足的建议得到了赞同。当然,这仅仅是麦氏召集集会的一步,在定下反缠足的基调后,麦嘉湖开始谋划成立天足会。有研究者指出,1874年麦嘉湖成立的这个组织名称为“戒缠足会”,其实不然。按照麦氏的说法,该组织名为“天足会”(The Heavenly Foot Society),并且,他就其名称做了详细的说明[2](P64)。麦氏的解释表明,中国妇女的双脚已经失去了天然模样,他的努力就是要恢复其原形,即上帝制造的人类的“天足”。所以,称该会为“天足会”更符合麦嘉湖的原意,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反缠足”、“戒缠足”。
天足会作为一个自愿的组织,没有任何强迫性,加入与否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当然,起初只有极少数有勇气的妇女在麦氏的誓约书上签字,根据他的回忆,天足会成立之时共有九人加入[2](P66)。为更彻底地对公众进行教育,麦氏决定每年分春秋季节召开两次会议,开会期间,发动人们就缠足问题公开辩论。在历次的讨论中,麦嘉湖均竭力说明尽管缠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但它的确是个荒谬的传统,而且在坐的许多男性无形中充当了妇女的残害者,缠足的妇女们是这个陋习的被害者,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它的帮凶。
成立天足会是麦嘉湖在华半个世纪的经历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之一。1891年,麦氏回国休养,期间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再次提及天足会,他认为厦门天足会的成立是其长期不懈努力教导妇女的结果,就是由于他的这种信念,放足将会不断被仿效,最终将会给这一陋习以毁灭性的打击[13]。
尽管困难重重,天足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每次会议结束,都会有新人加入,除此以外,最令人欣慰的是,不缠足女孩的数目不断增加,并且受到强烈的羡慕”[2](P75)。麦嘉湖的反缠足实践,得到厦门伦敦会的认可。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初三日,伦敦会漳泉和会在厦门关隘堂召开,受大会委托,麦嘉湖和其弟子黄承宜前往各地宣传天足思想。同年十月十四日,麦氏向和会汇报了宣传戒缠足的情况,并详列了不愿为女儿缠足的家长名单[14]。至1879年,自愿加入天足会的有80余家[15],到1894年,厦门天足会的成员已达800余人[16]。
1894年上海天足会成立以后,全国各地陆续设立了许多地方性的反缠足组织,厦门仍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不但在厦门市区广泛开展,而且还深入到乡村和民间。据民国初年归正会毕腓力(Philip Wilson Pitcher)牧师的统计,厦门地区的缠足陋习已经逐渐废除,当地的天足会领导了这一运动[17](P91)。在天足会的影响下,厦门民众对于缠足的认识较之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更为清醒,他们也更愿意配合有关的反缠足宣传。19世纪末,立德夫人(Mrs.A.Little)也对麦嘉湖在厦门的工作予以了高度赞赏,“20年前,迈克戈文(麦嘉湖)先生就在这里扶植废除裹脚运动。20年的成果相当令人满意”[18](P326)。厦门天足会的行动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各地的女传教士纷纷来信询问天足会是如何运作的,她们都没有发起过此类的活动,急切地想了解厦门妇女成功的经验”[2](P87)。天足会甫一成立,福州美以美会保灵夫人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号召福州教会向厦门学习,共同协作,力倡天足,以为全国之榜样,“愿我福州三会协力灭此恶风,即为全国基督徒开其路焉”[19],北京曹子渔欣闻厦门天足会有关信息,也“不禁拍案狂喜,中怀获慰,额手称庆”[20]。在厦门的推动下,福建、山东、河北、北京等地的反缠足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三、回应与颠覆:中国社会的反缠足实践和思潮
受史料的限制,我们目前还无法恢复和还原厦门社会、尤其是厦门女性自身在天足会影响下的反应。值得庆幸的是,笔者搜集到福州美以美妇女传道会1885到1918年的年度大会报告,这批宝贵的资料生动地介绍了该会在反缠足方面的活动。考虑到福州和厦门地理位置的相近以及麦嘉湖本人和福州教会的亲密关系(注:麦嘉湖的夫人即是福州美部会传教士弼来满(L.B.Peet)的长女。而且,在伦敦会和美以美会之间也有着教务上的往来,麦氏本人即曾经几次亲临福州参加美以美会大会,而福州著名中国基督徒谢锡恩也曾到厦门专门和麦氏商淡反缠足事宜。),笔者认为,福州妇女大会的若干情形仍能代表中国妇女在天足会影响下的变化。
1885年10月15日,福建省美以美会妇女大会在福州宣布成立。从大会组成人员看,传教士夫人或单身女传教士掌握大会的领导权,但数量众多的本地信徒和传道员构成了大会的主体,而且,就会议记录分析,中国信徒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能积极参与,发表自己的见解。
从1885年第一届成立大会开始,几乎年年的会议都要讨论缠足问题。在1897年的大会讨论中,与会的中国妇女代表就教会能为反缠足做些什么工作展开争论,大家一致认为,应尽力废除缠足的行为,而且教会应当在其中起主导性作用,并就如何开展工作向大会提出了七点建议[21](PP13-14)。这份由中国妇女起草的规章制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它改变了以往仅仅从道德角度劝说的做法,涉及到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女孩的婚姻大事,可以设想,如果男子们都愿娶大脚女人,则缠足风气自然熄灭,“当所有的丈夫都愿意娶天足女子时,缠足就会消失”[22]。而且,它的关注范围超越了基督教内部扩展到整个社会,在如何制止缠足上,她们强调不仅要劝说,而且要对顽固不化者进行惩处。
从具体个案分析,我们也可以明了许多妇女小脚观念的转变和基督教的天足宣传紧密相关。Ngu Hwoi Mu夫人从小双脚就被裹了起来,其实她心里很清楚,母亲非常喜欢她,并希望她长大以后能成为贵妇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她开始放足,但人们强烈的偏见让她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各处的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一涌而至,都想看看她为什么要放足,她的答案只有一个:“她感到放足是自己的义务,就像上帝从罪恶中把人类拯救出来一样,这样她就能更好地为上帝服务”[23](P5)。许金訇,福州地区第一个不缠足的女性,也是在其笃信基督教的父亲许扬美的监督下完成的。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非常渴望缠足时刻的到来,因为邻居总是在说,多漂亮的女孩子,可惜这双脚;多聪明的女孩子,可惜这双脚。“这双脚,这双脚”曾经让许氏羞愧难当。受丈夫影响,许夫人接受了天足思想进而不给许金訇缠足,当许氏说不缠足的女孩外人会议论时,许母答案是“告诉他们缠足的人进入不了天堂”[24](P79-80)。
以下我们主要通过对相关文本的阐释来具体说明天足会影响下中国人反缠足思想和观念的变迁。1879年,厦门天足会举行半年度会议,华人牧师叶汉章作戒缠足论,大力宣传天足思想[15]。叶汉章的这篇长文,在华人基督教反缠足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在基督教影响下中国人在缠足问题上的观念变迁及其内在缺陷。
首先,叶汉章指出了世人在疼爱子女上的两面性。一方面,叶氏认为父母们非常爱护其子女,另一方面,缠足是对子女最大的伤害,人们却漠然置之。
叶汉章的这一观点揭示了普通人对缠足的看法。在以小脚为美的畸形审美观的支配下,小脚成为一般妇女上升到上层社会的必备前提条件,而大脚面临着嫁不出去的危险。对每一个为女儿前途着想的父母而言,对每一个为自己所谓的尊严考虑的男子而言,小脚至关重要。因此,在家长们看来,给孩子裹脚不是深深的伤害,而是最大的爱。正是因为爱,人们才不顾一切地希望把女儿的脚缠得越小越好。这一人们广泛认可的做法被叶汉章指责为“名虽爱而实伤之”。叶氏的这一推论未必正确。缠足虽然给孩子带来莫大的痛苦,但与大脚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相比,当年的磨难根本微不足道。尽管每一个缠足的女子几乎因为痛苦都曾苦苦哀求过母亲不要为其缠足,但这决非是“到这个年龄孩子已经开始懂事”所致[2](P17),而恰恰是她们不懂事的结果。
其次,叶汉章以实例说明了小脚之痛苦和大脚之便利,“一老妇,年近八旬,执篙掌船,不歉方刚男子。观其首则两鬓垂秋也,而身犹康健有气力,乃自幼无缠足之故也。……缠小足之妇女罕能出门,缘其跬步艰难也”。叶氏所见确是实情,但却未涉及到小脚的内在涵义,使得他的批判缺乏针对性。
其实,叶氏的论述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小脚和大脚”(或者说痛苦和便利)代表着什么。伉爽子认为,小脚与大脚各得其所,各有所用,不必强求统一,“中国士大夫家贤女,但主中馈,以不预外事不出闺门为德,正不必放足以便大踏步日奔走于道路也;而且中国不缠之女多有之,乡间村妇,下贱女奴,不烦禁而多不缠矣,便奔走也”[25](P882)。伉爽子仅仅指出了事情的表象,还没有论及其关键。裹脚者因其足不出户,不需劳作,不缠足之人乃为了便于奔走。这里“小脚与大脚”分别代表了“士大夫家贤女和下贱村妇”。“贤”,多么高贵的表达,“下贱”,多么刺目的字眼,缠足与否俨然成了区分社会地位的标志。试问有谁不想过上等社会的生活呢?缠足固然痛苦,但它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地位,代表了养尊处优的悠闲生活;天足固然便利,但它却是下层民众、低贱阶层的代名词。即如叶氏所言,八旬老妇早该颐养天年却还要日日撑篙。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她们宁选小脚之痛苦而不取大脚之便利。
再次,叶汉章认为,缠足与否不是区分美丑的标志,并非脚越小越美丽,美丑在于容貌不在脚之大小。“或谓缠足与无缠足乃欲别妍媸耳。……夫人之妍媸在乎容貌之丑丽,不在其足之缠与不缠也”。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在“小脚美”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以后,美丑便与脚的大小紧密相连,或者说小脚和大脚成为区分一个人美丑的标准之一,即所谓“梳好头,荫好面,缠美足”。然而,由于观念的不同和实际问题的冲突,许多基督徒在讨论小脚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即使是他们认识到缠足与美丑无关,迫于压力也不得不为孩子缠足。在1877年来华传教士大会上,一位中国基督徒讲述了其女儿的遭遇。由于他信仰基督教,小时没有给女儿缠足,当她出嫁以后,其丈夫和他们的朋友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在她脚后跟下放了一块木头,绑得像个小脚一样,结果比年轻时缠足都要痛苦[26]。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宣传天足、提倡天足的阻力可想而知。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宣传天足观念的重要性。破除人们以小脚为美的陈旧观点,树立正确的美丑观对于反缠足运动有重大的意义。
四、泛宗教化:基督教反缠足运动的合理性及缺陷
尽管天足会为中国的反缠足运动四处奔走,但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夕,与中国庞大的妇女人口相比,天足者依然寥寥无几。20世纪20年代,福建省的反缠足运动还没有深入到农村,“在建宁,广泛且有决心的反缠足运动后来慢慢在城市上层阶级中实行,但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多少进展,在古田、邵武,除基督教外,没有多少机构采取措施来制止”[27](P96)。在福州,有些入教的妇女依然认为缠足是体面、时尚的象征,根本不打算放足。杨兴梅的研究也表明,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小脚美的观念在民间仍广泛存在,天足女性及其家庭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28]。
原因何在?以下我们结合传教士天足宣传的泛宗教化倾向具体分析其时代的合理性及内在缺陷。
无论是西方来华传教士还是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他们在论述天足观念时均存在强烈的泛宗教化倾向,均特别强调缠足是对上帝的危害,它违背了上帝的有关教导,“吾人身受上帝创造,保养筋髓”乃上帝的要求[19],在中国,“仅仅靠人类的争论解决不了缠足问题,只有神的力量能够把握它。这种力量就是基督教”[2](P38)。在中国基督徒的有关言论中,论及缠足之害也多以此为重要依据之一,“我们的身体如同精神一样,都是上帝赐予的,我们有责任保持它的天然状态”[29]。可以看出,在基督教世界,把缠足与信教联系起来,如果要加入教会,就必须放足,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亦即放足成为信教的象征。
这一观点的产生对早期基督教信徒的不缠足行为发挥了很大的心理支持作用。宗教心理学认为,“自心理学言之,……吾人对于上帝的信念,一如其他信念,乃一种心组,或心理的系统,其中连带着许多有力的情感原素”[30](P233)。也就是说,宗教信仰能够使人获得情感安慰。对基督教信徒来说,加入教会会使他们在内心产生一种坚定的观念,认为上帝无所不在。实际上,正是这种信仰,给放足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在动员女孩子与缠足习俗相抗争的过程中,强大的外部支持自然必不可少,许多妇女在放足时需要将脚放在温水中,有的甚至要在床上躺几天,面对亲戚邻居的冷嘲热讽,她们会倍感孤独和无助,迫切需要支持和鼓励,所有这些天足会都能够提供。事实证明,很多人正是在内心基督教信仰的支持下勇敢地顶住了一切外来压力,最终成为不缠足运动的受益者和先行者。一位放足的老妇人也表达了上帝在其放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上帝的指引下,我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获得成功”[2](P82)。
误区也正出现在这里。由于传教士有意无意的宣传以及基督徒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使基督徒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反缠足是对上帝的义务。因此,许多基督徒便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入教,就不能缠足。这一观点的普遍存在,使人们把反缠足和信教等同起来。近代中国社会,入教的信徒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自然是极少数,由于上述传教士的宣传泛宗教化倾向的存在,使得中国多数非教徒也同部分信徒一样将缠足还是不缠足作为区分信教与否的标准。对于绝大多数不信教的中国人而言,等同于基督教的天足自然没有什么吸引力,泛宗教化的宣传也无法让教外人士产生罪恶感,更无法让其产生任何响应。而且,即使在教会内部,由于传教士过分强调了缠足的反基督教性,也使得信徒没有意识到放足是对传统“小脚美”的彻底抛弃。换言之,对放足之人来说,她们放足仅仅是把它作为对上帝的义务,感觉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如此,而她们根本就没有思考小脚美丑的问题。在很多人眼里,小脚依然是美的,所以很多已经加入天足会的成员有时也偷偷地给孩子缠足,这并不是他们的信仰不真诚,“而是受到了小脚美观念的影响”[2](P75)。
以上我们分析了传教士在天足宣传上的泛宗教化倾向,这一倾向使许多基督教教徒在抛弃裹脚之时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支持,但直接排除了非基督教民众接受其思想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其影响的范围。在基督教内部,由于没有针对女性自身的观念进行变革,而且基督教本身也无法解决女性缠足的总根源,因而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可以认为,传教士以及基督教群体对缠足的理解,基本上是在宗教学设计的框架内进行,尚没有真正从深层次上触及妇女本身作为个人的内心感知和客观需要。因而,基督教的反缠足运动最终走向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