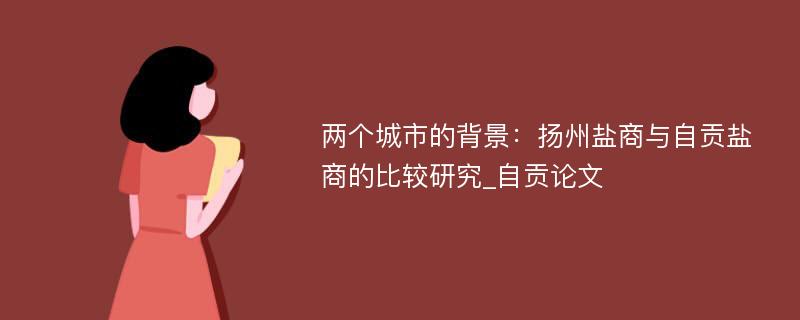
两个城市的背影——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盐商论文,自贡论文,扬州论文,背影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8)02-0022-08
盐商,是一个在中国漫长的盐业发展史,特别是清朝和民国的盐业发展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群体。在封建政府对盐业的生产经营予以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他们一头运作政策,一头运作市场,其谋略和胆识,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赞叹的。其中的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作为一时瑜亮、互有竞争的两大盐业重镇的生产经营组织者,他们的活动当更有代表性,也是值得我们去比较和研究的。
尽管同是盐商,但自贡盐商与扬州盐商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说,扬州盐商是纯粹的商人,是专营海盐买卖的“官商”。而自贡盐商不仅仅是商人,他们更准确的身份是盐业企业家,是集井盐开采、加工和市场拓展于一体的井盐生产的组织者。这种差异,是与两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的。
所谓扬州盐商,是指侨寓扬州,或者说坐镇扬州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但究其实,扬州盐商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扬州人。那么为什么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会选择扬州作为其聚集地呢?这和扬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关。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加之扬州附近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即江苏境内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两大片产盐区,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对于扬州盐商来说,市场就是他们的生命,通过垄断市场而低价获得商品、高价出售是他们的创富路径。由于淮扬自古就是税赋重地,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他们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个省份的巨大市场,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而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尤其是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可谓达到了极至。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扬州盐商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界8%的经济总量,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①,“扬州盐商”四个字也几乎就成了盐商的代名词。
自贡盐商从一开始就没有扬州盐商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创业历程和财富聚积途径与扬州盐商也迥然不同,而这一点,是由自贡的区位和资源条件所决定的。自贡地处四川南部,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商业基础十分薄弱,但自贡又有丰富的地下盐卤和天然气资源,早在东汉章帝年间,自贡地区便开始了井盐生产,经过历代的发展,先后开凿出1.3万多口盐卤和天然气井,出产了大量的井盐。自贡盐商都是靠创办井盐实业发家,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井盐业的经营从凿井取卤到盐的外销,都极富冒险性,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既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也潜伏着血本无归的危机,他们的投资风险远高于扬州盐商。自贡盐商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源和盐业专营体制的双重约束,他们的财富积聚必须依赖于更多地占有生产资料,更广泛地拓展销售市场。因此,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生产,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突破市场垄断,拓展市场,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正是凭着对财富的强烈渴望和对机遇的敏锐把握,自贡盐商筚路蓝缕,艰难打拼,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特别是清咸同年间和民国时期,先后两次“川盐济楚”的历史机遇,使自贡盐业步入鼎盛,也成就了自贡盐商“富甲全川”的豪富。从1887年至清末,自贡盐年产量一直保持在20万吨左右,占四川产额的十分之六,为全国销盐量的五分之一。在第一次“川盐济楚”期间,自贡盐商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年上交盐税170万两,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0%,“王三畏堂”成为中国19世纪中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资本集团;到第二次“川盐济楚”时,自贡盐税已占全川盐税收入的80%②。
客观地讲,自贡盐商无论是实力还是名气都远逊于扬州盐商,但就对盐业发展的贡献而言,自贡盐商却毫不逊色。如果说扬州盐商创造了空前的商业文明,那么自贡盐商在中国还处于农耕社会的时候,就已经创造出了独特的工业文明;如果说扬州盐商促进了一个城市的极大繁荣,那么自贡盐商就是直接推动了一个崭新城市的诞生。正是因为盐业的兴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众多城市遭遇沦陷噩运的危难时期,自贡却于1939年正式建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封建社会,盐课是政府仅次于田赋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税源。中国古代的盐业制度比较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质不外乎专卖制和征税制两种。前者是由国家经营,寓税于价;后者是由商人经营,课税于商。但产运销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一点是毫无例外的。在这种严厉管制之下,盐商的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可以说政策就是盐商的生命。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的发轫和衰败,无疑都受到了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性影响。
扬州盐商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清朝初年他们并非十分富有,但淮扬作为自古赋税重地的地位,使扬州盐商得到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极大支持,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一方面,他们受益于国家的引岸制度。当时清政府为了方便对行盐的管理,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区域,各区域所产之盐均按指定地域销售,而扬州盐商所在的两淮盐区,包括了江苏、安徽等六省的大部分地区,且尽是富庶之地,这为他们聚集财富创造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还受益于当时在两淮盐区所实行的特许专商制度。即政府授予若干资本雄厚的大盐商以贩盐专利,由其总领盐引,普通盐商不直接享有贩盐专利,而是必须先向政府特许的专商购买盐引,才能承引纳课并购盐贩运,其所纳课由专商代缴,一切经费亦由专商摊派。客观上造成了专商对盐的贩运和销售的垄断,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盐商由盛而衰,尽管也有战争等诸多因数的集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对两淮盐区盐业政策的改变。自道光十二年(1832)起,清政府在两淮盐区逐渐取消特许专商制度,开始推行盐票法,即取消行盐商人的世袭专卖特权,任何人只要纳税,就可以领盐贩运,且所贩盐可以在指定的地段自由销售③。这一盐业政策的改变,给扬州的大盐商们以致命的打击。在取消了特许专商制度之后,各地的小商贩竞相参与盐的运销,原有大盐商的垄断利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自贡盐商的兴衰也同样受到国家盐业政策的极大影响,且几经反复。应当说,由于自贡地处西南,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且最初自贡盐业生产的规模并不大,税收也不算丰厚,因此一开始国家的盐业政策便不曾对自贡地区有所倾斜,这一点本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这种政策便逐渐成为了制约自贡盐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从清朝到民国时期,自贡盐场所产之盐,其销区约分为附场票岸、边计岸、腹计岸、黔边岸、湘楚岸五部分。其中,湘楚岸原名济楚岸,本是淮南盐放销地区,太平天国战争后渐次成为自贡盐历史上的最大销区之一,济楚时年销量在40—120余万担之间,济湘济楚时年销量在70—200余万担之间,销量最高时可占到自贡盐全部产量的近一半。由于其他各岸销量较为稳定,因此,济湘济楚盐运销量的消长,直接影响自贡盐业生产的盛衰,也就必然成为自贡盐商们争取盐业政策的焦点和突破口。
清咸丰三年(1853),因太平军攻克南京,淮盐无法上运湘西、鄂西大部地区,两湖人民苦于淡食,清政府决定借拨川盐陆引2000张运济楚岸,此即川盐济楚之始④。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清政府又陆续调拨川盐运销两湖地区,带来了自贡盐业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繁荣。清咸同年间,富荣盐场平均年产盐21.8万吨,一跃成为四川最大的盐场。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沿海盐区相继沦陷,自贡盐奉令增产,第二次大批量进入湖南、湖北市场。抗战期间,自贡年均产盐24.45万吨,产量占全川的60%,仅盐税一项就占全省的80%以上⑤。生产的繁荣带来了盐场的兴旺,自贡盐商亦迅速崛起,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还积极为战争捐钱捐物,名噪一时。
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和抗战的胜利,国家逐渐恢复淮盐引岸,湘楚岸盐销量随之大规模减少,自贡盐商的繁荣也如昙花一现,迅速地衰落。从清同治七年(1868)起,曾国藩、沈葆桢等为恢复两淮盐区的引岸,多次奏请朝廷压缩川盐销楚数量,使得数十年内自贡盐在楚销岸一步步缩小,从年销售量125万担下降至45万担。八年抗战期间,川盐济湘济楚,最高销量达200余万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将自贡济湘济楚盐年定额各压缩为60万担⑥。一度的大量增产,其后又被大量压缩市场,给自贡盐场造成产浮于销、场盐积压的局面,生产受到极大压抑。民国37年(1948)自贡盐销量仅为3.8万吨,不到抗战期间平均年销量的六分之一,导致盐场凋敝,几个大的盐业世家,无不负债累累,有的场商竟至破产还债,盐场资本受到极大削弱。
在崇尚官本位和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盐商们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盐商们要想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不遗余力地去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只是相对于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而言,运作政策的目的各有侧重。扬州盐商作为盐业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考虑的是如何维护现有的引岸和专商制度,从而进一步巩固地位,垄断市场;而处于盐业政策对立面的自贡盐商,考虑的是如何突破现有政策,增加销岸,扩展市场,在两淮盐区中分得更大的一杯羹。
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盐商们直接运作政策的主要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报效”或“乐输”。也就是当国家因战争、赈灾以及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需要大量支出时,盐商们筹措款物给国家,以换取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一种则是交结权贵。与当权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在这方面,扬州盐商的意识之强、眼光之远、手笔之宏大,是令人叹服的,也是自贡盐商所不及的。
扬州盐商是具有“官商”身份的特权商人,凭借海盐运销的垄断特权获得巨额的垄断利润,但他们深知国家之所以会给予这样的政策,是因为扬州的盐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撑,只有持续不断地给国家创造税收才会有政策,而只有有了政策也才可能有自己的利润,因此,他们绝不与中央政府争利,而是利用中央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根本动机,一方面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盐税,一方面为自己攫取丰厚的利益,同时,他们出于利益需要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报效国家,或是直接报效皇帝,以此获得政府更加有力的支持,这无疑是深谋远虑之举。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盐商江春捐二百万两银子“以备犒赏”;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清政府极感军饷匮乏,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有时他们是间接回报政府即为地方做好事、促进地方稳定,如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聚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等。在扬州盐商们看来,这种“报效”或“乐输”是一石数鸟的好事,一方面可以取悦最高当权者,使之放心于地方的安宁和盐税的有保证;另一方面,可以与政府特别是盐务主管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以便于争取更多政策。同时,对公益的建设,如水上航道的疏浚和维护等,也利于其盐船的通行。当然,这种“报效”并不都是扬州盐商们所心甘情愿的,但客观上他们的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使政府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感受。
除热衷于报效国家之外,扬州盐商还不吝投入,大力结交当权者,与当时的统治集团高层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大盐商安麓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乾隆年间,扬州盐商更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都是由当地的大盐商代替地方官员接待的,为了给乾隆南巡修建临江行宫,就耗银二十万两,大盐商江春曾代表两淮盐商六次接驾,两次恭贺皇太后生日,还参加过皇帝所邀请的“千叟宴”;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中的重要人物,七海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经营的大公盐号就是淮盐运商中的巨户⑦。这些人物中,有的直接左右全国的政策,有的与当权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影响国家盐务的决策。两次川盐济楚之后,最终都恢复了淮盐在楚地的引岸,不能不说与扬州盐商所联系的政治力量有极密切的关系。
与扬州盐商比较起来,自贡盐商的“报效”,无论是规模还是层次,都要小得多。他们的捐资主要用于修桥铺路、疏浚河道、兴办义学等地方事业,特别是在抗战期间,自贡盐商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情结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慷慨解囊,共纾国难,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扬州盐商带有浓厚功利色彩的“报效”相比,自贡盐商们的这种捐献更为实际,也更值得赞赏。但总体而言,由于当时盐业政策对自贡盐业发展的严重制约,使自贡盐商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政策的对立面,更多时候,他们不是通过“报效”去争取政策,而是通过突破政策,甚至对抗政策的手段来获取利益,而这种与政策的对抗或突破并未完全得到政府的认同,并没有形成制度,因而他们的利益也就难以得到政府长期、有效的保护,甚至有时会使自己面临严重的危机,应当说,这是一种比较短视的行为。如以王余照为代表的自贡盐商,在反对官府“增抽水厘”和开办官运的问题上,同地方政府发生激烈对抗,甚至出现煽动盐工聚众捣毁官府水厘局的情况,最后王余照被官府通缉,被迫流亡他乡,元气大伤⑧。同时,自贡盐商交结的当权者中,也远没有如扬州盐商一般的人脉,既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王余照,虽然也曾广泛交结朝官,但京官中为其张言者,不过御史、部郎之流,无非制造一些舆论而已,没有一个像曾国藩那样的“庙堂人物”为其后盾,能够代表自贡盐商利益的实权派很少⑨。由此可以看出,扬州盐商的强势是与他们对政府和当权者的苦心经营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自贡盐商的确有不小的差距,这里面有实力不及、底蕴不够的因素,但更多地应当是意识上的问题吧。
随着产业的不断扩张和财富的膨胀,盐商们开始不仅仅满足于与当权者建立利益关系进而影响其决策,而是希望进入统治阶层,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
同清朝的其他成功商人一样,扬州盐商也热衷于捐官。据统计,从顺治元年至嘉庆七年(1644-1802)先后有180个盐商家庭成员通过捐纳得官⑩,但这只是他们获取社会地位的一种捷径而已。盐商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自己商人的属性,真正进入到统治阶层。因此,他们普遍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业儒仕进,通过科举的途径得到功名,反映出浓厚的崇儒情节。虽然现在无法确切地统计出有多少扬州盐商家庭成员成为士大夫进而进入统治阶级,然而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呈现出当时他们社会流动的一般趋势:盐商家庭一般经过两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多数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业,最终目的便是从政。值得注目的是,人数约三百或更少的盐商家庭,在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间,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11)。这些进入统治阶层的盐商子弟,便成为了扬州盐商在政坛的一支重要嫡系力量,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自贡盐商同样热衷于捐官,王余照曾受赏二品顶带,“李四友堂”、“胡慎怡堂”的弟兄子侄几乎人人捐官,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代,也是想方设法去争取参议、顾问之类的头衔,其出发点当是为了壮大自身的势力,加强同政府的联系,以便在经营中获取更大的利益。特别是民国后期,盐商们积极运作,通过在地方议会、商会等组织担任要职,对地方政治施以了较大影响。不过,这同扬州盐商致力于进入统治阶层的努力比较起来,其理念和层次都显得更低了一些,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除政策运作外,盐商们还十分注意对舆论的营造和引导,借以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并对统治阶层施加影响。在这方面,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都有强烈的意识,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用现在的话说,扬州盐商是把文化作为其核心竞争力来打造的,而显然他们获得了成功,因为时至今日,仅仅“扬州盐商”这几个字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与当时的文化传播是如此的紧密相连,以至于有“清朝时期中国的重要文化就在扬州”的说法。扬州盐商中确有一批有真才实学之人,他们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个人文化素养,喜好交结文人学士。至迟自十七世纪晚期起,扬州盐商便已经开始款待和资助士大夫,并逐渐形成风尚。他们揽才、引才、养才、济才,为文人、学者排忧解难,得到了当时名士的一致赞扬,一时“海内文士,半集维扬”(12)。自雍正三年起,马家的小玲珑山馆、程家的篠园、邓家的休园等就成为国家级的名士沙龙,定期举行文人“雅集”,并且有最丰盛的款待及优厚的报酬。乾隆初,扬州盐商还捐重金修建和资助书院,当时广储门外的梅花书院、三元坊的安定书院、府东的资政书院等都靠盐商财力支持,浓厚的学术氛围逐渐形成了秩然可观的“扬州学派”。一本《扬州画舫录》的记录表明,十八世纪时长江下游的有名文人,只有极少数和扬州盐商没有关系,包括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画派也是在扬州盐商的支持和催生下出现的。两者之所以结合,是因为士大夫们能够从盐商处得到物质的帮助,而盐商们也可以借助士大夫们获得良好的社会名声。因为文人严格说来虽非统治阶级,但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正式的社会力量,正是凭借着赞助各类文化活动,无论扬州盐商其出身如何,实已被士大夫认可是真正的社会菁英,并进而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
与扬州盐商有意识的“养士”行为相比,自贡盐商们的目光则要短浅得多。自贡盐商中少有附庸风雅之人,他们追求及时行乐和穷奢极欲的消费方式,以“王三畏堂”、“李四友堂”为代表的大盐商们自恃家资百万,任意挥霍,纵情声色,贪图享受,以致当时就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三畏堂的马儿,四友堂的娘姨”,从中不难看出盐商们的生活状态。自贡盐商对文化的赞助,更多地体现在捐资兴学,以及对本地戏剧、绘画等活动的扶持上,其规模偏小,且不成体系,因此难以引起士大夫们的关注和共鸣。时至今日,当我们对井盐文化进行整理和挖掘时,发现并没有留下多少系统性的、反映当时社会形态的文化遗存,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自贡盐商制造和影响舆论更为有效的办法,还应当是出资兴办报业,民国时期自贡地区主要的报纸有四种,其中《自贡民报》和《川中日报》就是由盐商出资创办的。这些报纸代表着盐商们的利益,其宣传重点就是盐业公会的活动和盐商的呼声,他们关注国民政府的盐业政策,写下了大量的时评和报道,为自贡盐商奔走呼号,对当时盐业政策的制定施加了一定的影响(13)。
无庸置疑,扬州盐商对于运作政策的手段和效果,都是自贡盐商所不能企及的。究其原因,除开财力、意识及文化底蕴等方面的因素外,扬州盐商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特殊的组织体系,也应当是有利于其运作政策的一个明显优势,而这与两淮盐区所实行的特许专商制度有直接关系。
道光十年以前,两淮实行的是特许专商制度,所谓专商就是介于官、商之间的人,是盐商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他们有政府专员的身份,有管理其他盐商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盐商们的代表,代表盐商的利益。由于专商是世代承袭,其他人要想挤进其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普通盐商完全是在专商的层级之下,由专商给予盐引而生存,对专商只有依附而难以对其地位形成冲击,所以客观上造成了专商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的局面。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扬州盐商形成了一种较强的求共同发展的意识,一旦需要开展运作,则出钱也好、出力也好,都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便于形成共识和统一的行动。
自贡盐商也有其完备的组织,但这种组织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内部的平衡。自贡盐商始终生存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中,对外面临着不同销岸的各地盐商的竞争,而在同一销岸内,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的竞争依然相当激烈。盐务管理部门为了加强对井灶户的管理,组建了场商联合办事处等组织,下设若干同业公会,如盐崖井公会、黑卤井公会、票盐公会等,公会之下设若干组,井灶户被分别编入这些组中。产额分配由同业公会层层摊配,盐务管理部门命令增产,名义上是按产额大小比例增加,实际上大户控制着的公会在分配上总是偏利大户,使之多占产额;如令减产,同业公会则是按成削减。盐务管理部门核给生产贷款,大户总是先得多得(14)。可见,这种均衡式的盐业生产所带来的内部竞争往往大于外部竞争,导致成立组织的目的主要在于调剂内部矛盾,而无暇顾及对外的政策运作和市场开拓。所以自贡盐商对外的政策运作往往是大户的单独行为,而且往往在运作的过程中还受到同业者的羁绊,这不能不说与他们缺乏整体凝聚力、缺乏整体的开拓精神有很大关系。
对盐商们来说,政策就是市场,而政府的管理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时机遇就是政策。自贡盐商正是以其在机遇面前的超强敏锐性和胆识,成功地开创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大好局面,这个机遇就是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太平天国战争初期,清政府借拨川盐陆引2000张运济楚岸,是为川盐济楚之始,但当时川盐陆引每张只有4包,每包200斤,2000张陆引盐不过只有1.6万担左右,且清政府为了维持淮商运权,借拨川盐只是一时权宜,并未规定常年运送,也没有将楚岸改为川盐引岸的打算。但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延续,在此后的15年间,楚岸缺盐,价高利厚,川商遂大量贩运川盐入楚,按当时界限森严的盐务引岸制度,川盐入楚,是越岸侵销,应作私盐论处。但因川商锲而不舍,贩盐数量甚巨,清政府禁不胜禁,乃迫于现实于咸丰六年(1856)在四川巫山、湖北巴东设关收税,“化私为官”,实际就是承认了川盐在楚岸倾销的合法性。当时每月济楚川盐水引900余张,运盐9万担,年运量达100万余担,其时自贡年平均产盐430余万担,济楚盐即占产量的四分之一,其后屡有增加,形成楚岸遍销川盐,以致“川楚商民均忘食淮旧制”(15)。从促使政策的变更到市场的扩张,再到产量的增加,造就了自贡盐业历史的第一个辉煌。这种局面严格来说并不是当时的清政府主动促成的,而是自贡盐商自己争取来的,也就是说先有了政策的突破,其后才是政府的认可,国家宏观政策的自下而上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不知道自贡盐商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这种国家政策自下而上的特质,但他们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政策不只是可以争取的,也是可以创造的,而这一点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屡屡得到重现。
如今,用现代的眼光再去翻阅盐商的历史,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都已经凝固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成为城市的背影。但在他们的兴衰成败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他们对市场的关注,对政策的敏感,以及运作手段的大气和高明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的。因为即便在时代和制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并没有改变,国家宏观政策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影响力也没有削弱。在我们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如何争取和运用好国家的宏观政策,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也许,从盐商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依托和遵循国家的宏观政策,也不仅限于要积极地去争取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政策的整体框架内创造政策,大胆尝试,勇于创新,开创性地做好工作。这是说者易而行者难的事情,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注释:
①黄俶成:《论两淮盐业经济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
②自贡市盐务管理局编:《自贡市盐业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倪玉平:《政府、商人与民众——试论陶澍淮北票盐改革》,《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吴泽霖:《百年来引岸制度束缚自贡盐业的史实纪略》,《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⑤⑥自贡市盐务管理局编:《自贡市盐业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⑨吴泽霖:《百年来引岸制度束缚自贡盐业的史实纪略》,《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⑧自贡市盐务管理局编:《自贡市盐业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⑩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九。
(11)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八。
(12)朱宗宙:《“嘉惠士林”的清代扬州盐商》,《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
(13)黄宗凯:《民国时期自贡报业的盐文化特色》,《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
(14)吴泽霖:《百年来引岸制度束缚自贡盐业的史实纪略》,《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15)吴泽霖:《百年来引岸制度束缚自贡盐业的史实纪略》,《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