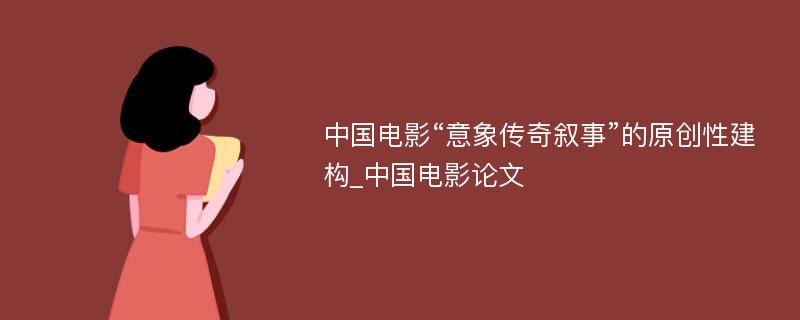
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事”的原初性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影像论文,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1913年“新民公司”以贴附外资制片公司的方式①模仿摄制以“滑稽打闹”为主要内容的短故事片,到20年代前期民族自资的电影制片公司纷纷成立,开始长故事片的拍摄,并逐步形成蔚为大观的态势为止,电影作为舶自西洋的外来之物,在持续了二十余年的“襁褓期”之后,终于迈出了“中国化进程”的第一步。在近期有关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中,这一进程被明确地描述为“中资电影公司的成立,只是从‘地产’和资本来源的意义上界定了‘中国电影’,但文化取向、内容与形式的中国特性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如何从内在层面构建起中国电影的民族身份,成为192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所有的探索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②。应该说,这样的描述是正确的,但也是笼统的,尚不能准确地呈现早期中国电影叙事建构的细密纹理。
早期中国电影叙事的建构是一个涉及中国电影文化传统的基本问题。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这一问题“既老又新”。钟大丰在1984年至2008年的二十余年间,对此曾三度加以重点关注③。1994年,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及其根源——再论“影戏”》一文中,钟大丰提出,十年前以《论影戏》为题所谈起的“对中国初期电影的电影观念及其银幕体现的看法”,“我以为不仅初期中国电影是如此,几十年来在中国电影中占主流地位的电影主张大都是与其一脉相承的”。而他的“试图从‘影戏’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电影的历史,就是企图从中国电影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观和电影观入手,寻找左右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较深层次的根源”④。钟大丰二十余年“不能释怀”的学术努力,显然是富于洞见的,因为“中国电影的民族身份”应该缀接于“深层次根源”的主导性流变。对这一流变,我们主张将探寻的起点和重点,放置于早期中国电影原初性叙事建构的界面上来。
选择原初性叙事建构的描述和阐释,而不是直接对电影观念(艺术观念)加以考察,是因为电影观念的生成是动态的、过程性的,既难以先决性地加以观照,也不能只根据某时期尚未发展成熟的“报刊影评”或“半译半著”的所谓的电影著作(等文字性史料)中的“个人判断”,做出对早期中国电影观念的理论指认。在我们看来,一个民族独特的电影观念的生成,只能在多种因素的参照下,经由主体性选择的多重淘洗,并借助历史契机的推广、扩散而达成群体性的共识,这是一个认知性沉淀的产物。
二
在早期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中,1923年是一个公认的“关键性节点”。无论是1927年刊载于《中华影业年鉴》的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史》,1934年刊载于《中国电影年鉴》的谷剑尘的长文《中国电影发达史》,还是1936年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他们都指认1923年为“开拓民族电影新阶段的重要年份”。这一所谓的“开拓”,在产业界面上是指民族制片业的兴起(仅在几年之间就形成了以“三大四小”为核心的产业格局)⑤,在文本(出品)界面上则是指明星影片公司推出了《孤儿救祖记》这一“电影文化事件”。
称《孤儿救祖记》为“文化事件”,是因为这部影片不仅仅是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初最早的长故事片之一,更为主要的还在于,它“是一个凝聚了巨大昭示性,扭结了众多契机和功能的范本”⑥。按当时的史述记载:1923年底明星影片公司耗时八个月摄制的第二部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完成⑦。12月28日“试映于爱普庐戏院,第二天即有片商登门,以8000元巨资购买南洋地区的放映权,各地片商也纷至沓来”⑧。《孤儿救祖记》于1924年元旦上线映演,“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⑨。社会评论(口碑)与票房的双赢,使其成为中国电影长故事片初兴之际的“范式文本”。
对于“叙事范式”(在民族或国家电影叙事建构中的作用),已有研究者敏锐地加以关注,并将其界定为“在故事讲述(影像叙事)层面上所形成的、对应于一定时期大众观影心理的基本叙事结构(框架)和叙事因素的关系定势”⑩。而所谓的“范式文本”则是指范式的直接承载者(影片),它具有普遍的参照功用、强劲的扩散效力和广泛的影响力(11)。虽然《孤儿救祖记》影片已经散佚无踪,给今天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但基于“本事”和“字幕本”,我们仍然可以对早期中国电影原初性叙事建构的相关指标进行系统的考察。
三
从遗存的完整“本事”可知,《孤儿救祖记》属于典型的“传奇性叙事”。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传奇’一词,含义数变。唐代文言小说称“传奇”,宋元时曾用以指称一些敷演故事的说唱艺术及南戏、杂剧;明代以后则成为以演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的专称”(12)。这即是说,在明代、清代盛极一时的戏曲艺术中,“传奇”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原则和美学特征,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与呈现。承袭唐代文言小说叙事的“新”、“异”、“超”、“卓”,“叙事就得写奇人、奇事、奇情”(13)。在追求曲折变化的叙事传统的基础上,传奇发展出形式特征明晰的两层指涉:
其一是“诗歌音乐形式的原则”。南京大学吕效平在《论“现代戏曲”》一文中指出:“明清传奇也是作家和文学家的戏剧。”“古典诗歌滋养和提携了中国本土戏剧的表演艺术,使它形成了一套表现力极强、形式美资源极其丰富的舞台语言系统”(14)。在此之中,多种传统文化元素以高密度聚合的方式,融会于表演形式(这一形式的电影化转换,所生成的观念性取向,最为直观与直接的例证便是1947年由费穆导演、文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经典名片《小城之春》。更进一步联系于已有论者提出的“影像传奇叙事观”的电影观念(15),它可以被指认为这一观念所内涵的一个层次)。
其二是“关于情节的结构原则”。吕效平认为,“它要求情节的整一性,故事必须有头有尾,追求事件的曲折离奇和缝合照应的构思技巧,讲究叙事的规定程序”(16)。“情节的结构原则”作为传奇的有机内构,对早期中国电影,特别是初创时期的长故事片的叙事建构,有直接而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奇”、“异”内容的叙事选择方面,而且与叙事(情节)推进的动力学模式有深入的关联。正如吕效平所阐释的,“与黑格尔强调‘史诗’的原则和抒情诗的原则经过调解的统一完全不同”,明、清传奇要求“它的人物必须充满情感,但不必具有意志,不必把情感化为动作,它的人物行动可以来自作者的任意安排,而不必出自自觉到的意志;它的情节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作者的意愿,而不是剧中人物的意志。它的情节艺术及其提供的审美资源,主要来自这样一对张力与应力的矛盾;张力的一面是尽可能把故事的曲折离奇推向极限,应力的一面则是通过尽可能巧妙的缝合照应,使这种曲折离奇被信服与被接受”(17)。
当然,在此还需要特别加以说明:就概念而言,明、清传奇虽是“南戏”的特指,但作为叙事传统,又是超越具体戏剧(戏曲)的存在。中国影像传奇叙事承纳的是叙事传统,而非戏曲或戏剧的单一结构,更不是对戏曲的影像化挪用。我曾提出,传奇实际上既是在不同文艺样式中延传流变的民族主导的叙事形式,同时也凝聚为绵延不绝的“形式精神”(18)。因此我们会看到,传奇在明、清时期的“南戏”、“地方戏”中的盛大繁荣(19),同样也可以在明、清长篇小说里目睹它的发展的巅峰状态。以此观之,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早期中国电影研究所归纳和总结的“影戏观”、“影戏美学”,尝试在“电影与戏剧”的关系轴线上把握早期中国电影的电影观念及其美学体系的学理思路,以“影像传奇叙事”进行概括与归纳,显然是全然不同的体认与阐释的路径。
从这一阐释的路径观照《孤儿救祖记》,我们可以看到,《孤儿救祖记》在情节结构及其动力学模式方面有着十分鲜明的传奇(性)特征。
《孤儿救祖记》的完整“本事”由十个自然段落连缀组成,叙述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家庭伦理故事。郑正秋按照“天灾人祸”的传统说法,将情节的捩转拟为“自然事件”与“人物事件”两类。“本事”第一段,“道生坠马身亡”属于天灾,给原本和睦丰实的家庭平添变故。“本事”第二段,“道培承嗣,子敬诬嫂,蔚如见逐”,则是人祸。两类变故让家族陷于危局。而蔚如带孕归依老父,继而父亡、子孤,显然就是“尽其可能把故事的曲折离奇推向极限”的范例。“本事”第三段:“杨翁兴教”是过渡性照应,也是铺垫,为“本事”第四段及后面情节的进展留足榫口。此一段的“十年后祖、孙偶遇,成忘年之交”,开始使用“巧合之法”缝合照应。“本事”第五段至第八段,“孤儿救祖”、“翁媳偶遇”更是频用“巧合”。如“本事”第五段“余璞救祖”一节:
陆以地盘失去,竞以危词,教唆道培,铤而走险,适童过访,奋勇往救。奸谋未逞,守碱继之,又为童机警所阻,误中其侄,于是陆遂捉将官里去,侄亦倒地不省人事。(20)
从此一节可知,孤儿救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复踏再三,一步步将剧情推向高潮,并由此凸显出余璞的“智”、“勇”。而“本事”第七、第八、第九三段,表现“翁媳相见”,仍采用复踏,生出枝节,直至道培临终道出原委,才有“望云亭”上祖、媳、孙一家三口的大团圆结局。
在整体叙事动力方面,《孤儿救祖记》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自作者任意安排”的特色。这种“任意”在《孤儿救祖记》的“字幕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1)。
现存《孤儿救祖记》“字幕本”,以人物对白为主,其间也穿插了近五十处说明性和评述性字幕。“说明性字幕”主要用于交代人物关系或事件原委,如“寒儒余慕陶,为道生之岳父”。“余叟赋性孤僻,生活艰难,所赖者,其婿按月之津贴耳”。“余叟月必临婿家领取津贴”。“族人杨子桓,热心公益,为寿昌所信任者”。“杨道培乃寿昌之侄”。“诡计多端之陆守敬,为道培之密友”等(22)。“评述性字幕”是叙事讲述者对剧情的道德性或抒情性评述,如:“此可怜之少妇,终日悲哀,故常至坟前洒一掬伤心泪焉”。“丧心哉陆贼,不怀杨翁豢养之恩,反敢戏其新寡之媳”。“堕落妇人金媛媛,乃杨道培之外遇”。“亲爱夫婿,人天永诀,所得见者,惟此巍然矗立之墓碑耳”。“道培居然能蛊惑杨翁所信任之族人,以遂基承继之私怀”等(23)。可以见出,对于默片长片而言,这些字幕,特别是评述性字幕,有着强调、引导、指示、烘托的“缝合性效用”,直观地显露出传奇性叙事对故事发展的设置与调控的痕迹。
以《孤儿救祖记》“本事”第二段的剧情设置为例。这一段表现了余蔚如被诬不贞,逐出杨府,带着身孕,归依老父。余蔚如成为影片表现的焦点,而围绕她先后出现的字幕有:“既伤寡苦,犹不得不顾怜贫苦之老父,呜呼蔚如,其苦甚矣。”“悲夫蔚如,意谓哀莫哀于丧斯夫,岂知尤有哀于是者,已在眉睫矣”。“可怜蔚如误会阿翁致怒之由,至于欲辩而心有所不敢”。“薄命蔚如方得遗腹子以稍慰,不图老父竞弃之而长逝矣”。“茫茫神州,何处能容妇女自立,蔚如含冤见逐,舍往依老父将何之”。数条字幕尽是“薄命”、“寡苦”、“可怜”、“悲夫”之类,带有情感和情绪的提示与点染。这既是道德性悲鸣,也是苦情之中对女性美质的玩味。在有关《孤儿救祖记》的既有研究中,已有论者明确指出:“余蔚如的形象本身就是郑正秋着力打造的看点。”“他将余蔚如置于‘被诬—被赶出门—含辛教子—抚育成人—终成正果’的情节过程,在传统‘节烈之妇’的苦戏框架里,完整地体现了‘恭、宽、信、敏、惠,孝、智、礼、勇、忠’的传统儒道美德。于哀、怨、忍、韧之间,达成了饱含中国道德审美内涵与哀情情愫的审美性捏合”(24)。这种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显然有着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双重功效。就策略而言,自《孤儿救祖记》始,这样的原初性叙事已成为中国电影屡试不衰的法宝(25)。
四
早期长故事片中叙事传奇所标示的“形式身份”,是中国影像传奇叙事建构另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有关早期中国电影镜头语言体系的研究中,好莱坞电影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叙事,这已是学界的共识(26)。从目前仍然能够完整观摩的早期中国影片文本看,《一串珍珠》(侯曜编剧,李泽源导演,1925年长城出品)对莫泊桑原著小说的改编所实施的传奇化处置,更多地体现于对情节(及结构)的增删、改换(原小说主人公丢失了借来的珍珠项链,在辛苦劳作多年、终可赔付之时,方知丢失的是一件假货。这一情节被侯曜改换为:马如龙偷盗,为赔项链,王玉生挪用公款入狱。出狱后偶得一字据救了马如龙,最终马如龙愧悔难当,说出了当年真相),而古装片《西厢记》(侯曜编导,1927年民新出品)则更能体现借自好莱坞的叙事蒙太奇手段在细节表现以及新的影像化看点的形成这一方面的效用。
在《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后花园相见一场戏,采用的就是好莱坞常规叙事蒙太奇经典的“三镜式法”。侯曜首先以一个全景镜头介绍人物关系,然后镜头在张生与莺莺之间对切,从中景到近景反复推进(中间还穿插了一个红娘的镜头)。这种“梯级式”推进的用镜方式,将这则人皆熟识的私订终身于后花园的情节以影像化的形式重新演绎,并形成“熟识而又陌生的看点”(27)。总体来看,在《西厢记》并不复杂的(原)情节中,侯曜扣住影像化与传奇叙事双向融通的节点,主要以“滑稽谐谑”和“梦境段落”来增强影像化与可看性。“滑稽谐谑”在传奇发展史上,本来就是特征突出的重要因素。陆炜在《论第四种戏曲美》一文中特别指出:源起于唐代“参军戏”、“歌舞”与“宋代杂剧”的“谐谑滑稽”是“中国戏曲艺术久远的传统”(28)。《西厢记》中,孙飞虎大军围寺,小和尚惊得目瞪口呆,绕着老僧团团转,以木鱼击头的细节;张生梦中以墨狂抹书童之脸,使其满脸皆花的细节,都是以影像化的、滑稽谐谑的方式进行叙事铺展的实例。
“张生笔战孙飞虎”的梦境段落,是《西厢记》至今惹人注目的“亮点”(29)。这个长约四分钟的镜头段落,属于“梦境”性质,本身就具有非现实性的“异”、“奇”成分。而这又与当时已经普遍使用的电影特技相联系,演绎成为电影化和传奇化最为明显、最为引人入胜的奇妙之段。对这一段落,侯曜不惜胶片,大加敷演:从孙飞虎横刀夺爱,张生骑笔追赶(借“神笔马良”之典),到以笔为枪除恶救美。整个段落完整新奇,使《西厢记》这个流传了千古的老故事平添了新意。
从对《一串珍珠》,特别是《西厢记》影片文本镜头段落的分析可见,早期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事的原初性建构,经由《孤儿救祖记》(对叙事范式)的开创,《玉梨魂》、《空谷兰》等后续同类型影片的持续扩散,使其成为早期中国电影(长片创作)共有的叙事范式,而且这种扩散和延展,还伴随1926年勃兴的商业类型电影浪潮,继而也成为中国商业电影原初叙事类型建构的核心范式(30)。
其实,在早期中国电影的人才群落中,侯曜作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参加“文研会”,以拍摄“问题片”著名的编导,比之于群落中的其他一些编导更具“新文化”背景。选择他编剧的《一串珍珠》与编导的《西厢记》来分析考察,确实并非刻意而为,主要是因为现存的早期影片文本已极为稀少,然而这样的偶然与巧合,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影像传奇叙事在早期中国电影(长故事片)创作中已成为共同性定势。而具体到影像叙事手段与传奇叙事的关系,则可以说“早期中国电影是从传奇叙事的需要出发,来认识、选择、掌握和发展电影(技术)手段的可能性的”(31)。
五
早期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事建构是早期中国电影人在历经短故事片阶段的模仿、移植,积累了大量的制片、拍片经验,并较为熟练地掌握了镜语叙事手段的基础上,把握历史发展契机的主体性觉醒的产物。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影像与文字史料来看,主体性觉醒是早期中国电影在20年代快速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因素。觉醒本身不仅体现于早期中国电影自主的叙事选择与叙事建构,而且还广泛涉及到电影生产/消费以及电影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当时,郑正秋在《中国电影的取材问题》等多篇文章中,以中外对比的方式分析和表述了中国电影的取材、剧情表现、演员表演、电影化策略与方法等多方面应有的“原则”(32)。即使像沈钧儒这样的并非真正的“电影中人”,在为洪深创作的中国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所写的“序言”里,也对中国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形象所特有的价值等问题,有着指向清晰的认识。
沈钧儒认为,洪深《申屠氏》的选材极有价值和特色,因为申屠氏“(其一)早慧能文,(其二)安贫,(其三)匿孤赚葬,从容有计谋,(其四)冒险复仇,匪独贞洁亦壮烈焉。此数者皆一般中国女子所难能,而申屠氏具有之,此其所以可称也”。沈钧儒所言显然是以“异”、“奇”作为题材(选材)的衡量标准,而有关“我国女子从来与西洋女子不同。西洋女子,一切行为根据于爱,我国女子则于用爱之间,又另有一种礼的意义,充溢而并行。申屠氏盖即一完全智而明礼之女子也。惟其智,所以能文;惟其智,所以有谋划;惟其智,所以明决而有勇。然而慕孟光,效古男子荆轲,豫让之所为,则贞静而浸淫于书史者也”(33)。这样的议论,分明表现出对中国电影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及其价值判定的传统性理据。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早期中国电影史诸多问题的研究渐趋深入。秦喜清的博士论文《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就对早期阶段上海各大影院上映的外国影片进行了详尽的清理,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实证性地揭示了外国电影,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对早期中国电影的深入影响。梅雯的专题性论著《破碎的影像与失忆的历史——从旧派鸳蝴电影的衰落看中国知识范型的转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借助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研究的大量成果,对早期“鸳蝴派文人”介入电影创作,“文明戏”阵营影响电影创作的历史文化史实,进行了细密的梳理,从人才构成、创作、作品分析、文化阐释几个层次,重现了早期中国电影所围裹的浓重的“鸳蝴文化”气息。
应该说,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早期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侧面,但这些侧面在早期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动力学阐释(范式)中,实际上只能说是重要的“参照性因素”,而非主导性因素。主导性因素只能是与早期中国电影觉醒的主体性相联系,而影像传奇叙事的原初性建构,则是透视这一觉醒的关键性界面。
注释:
①参见虞吉《中国电影史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此一时期,这类公司包括“新民”、“华美”和“幻仙”,被称之为“贴附型企业”。
②秦喜清:《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③参见钟大丰《有没有重谈“影戏”的必要》,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4期。
④钟大丰:《中国电影的历史及其根源——再论‘影戏’》,载《电影艺术》1994年第1期。
⑤参见虞吉《中国电影史纲要》,第9页。
⑥虞吉:《原初探视:影像传奇叙事建构中的女性形象》,载《聚焦女性性别与华语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南京大学2008年,第45页。
⑦明星公司首部长片《张欣生》,因循1920年《阎瑞生》的套路,渲染开棺取证、蒸骨验尸等细节,被上海电检会查禁。
⑧朱剑,汪朝光:《民国影坛纪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⑨⑩陆弘石:《中国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第7页。
(11)(24)虞吉:《中国电影史纲要》,第11页,第10页。
(12)金宁芬:《明代戏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注①。
(13)(28)陆炜:《论第四种戏曲美》,《南大戏剧论丛(二)》,中华书局2006年版。
(14)(16)(17)吕效平:《论现代戏曲》,《南大戏曲论丛(二)》,第128页,第128页,第128页。
(15)(18)(31)虞吉:《早期中国电影:主体性与好莱坞的影响》,载《文艺研究》2006年10期。
(19)解玉峰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一文中指出:“明万历至康熙这一阶段的戏剧无疑代表了中国戏剧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水准……”《南大戏剧论丛(二)》,第372页。
(20)(21)(22)(23)《孤儿救祖记》(本事),《中国新文学大系·电影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5)此一策略在后继者蔡楚生、谢晋的电影中被一再重现。
(26)对此一问题,香港学者林年同、刘成汉,大陆学者倪震、李亦中等均有过专文论述。他们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镜语体系是“属于蒙太奇方法的体系”,“是一种讲故事的蒙太奇,旨在保证让观众通过流畅的镜头组接看完一个故事”。
(27)(30)参见虞吉《原态透视:早期中国类型电影》,载《电影艺术》2005年第6期。
(29)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就称其为“这一成就在1927年前后的中国影坛是极为罕见的”。
(32)这些文章包括:《中国电影的取材问题》(明星公司特刊第2期《小朋友》专号,1925年),《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影戏杂志》1922年1卷3号),《我之编剧经验谈》(《电影杂志》1925年13期),《请为中国影戏留余地》(明星公司特刊第1期《最后之良心》专号,1925年),《导演〈小情人〉之小经验》(明星公司特刊第12期《小情人》专号,1926年)。
(33)沈钧儒:《〈申屠氏〉·序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电影集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