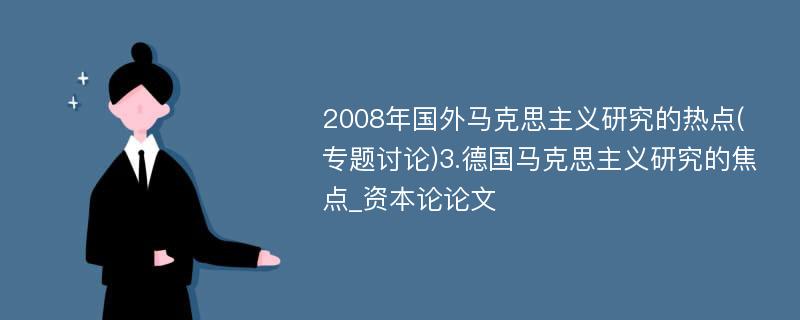
2008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扫描(专题讨论)——3.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关注点论文,热点论文,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有许多问题引起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关注。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成为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的新热点,法国“’68红色五月风暴”(简称“’68运动”)历史作用的不同评判,德国左翼与民族关系以及德国特殊道路问题的论争,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等等。这里只讨论前三个问题。
一、《大纲》成为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新热点
对马克思的手稿或著作进行文献学考证和文本学解读,一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趣所在。2008年,适逢马克思撰写《大纲》150周年,学者纷纷著文对之进行研究。其中,尤以施蒂策勒(I.Stuetzle)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不仅回顾和描述了《大纲》的写作背景、创作史、接受史,还区分了不同的阐释版本,考察了《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确立了《大纲》的历史地位。
关于《大纲》的创作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50年代。1849年,马克思移居伦敦。此时的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英博物馆有研究资本主义的丰富材料。在那里,马克思不仅研究了对他来说的新文献,而且又阅读了在法国流亡期间已经读过的文本,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经济学的理解,这些理解最后积淀在《大纲》中。从1851年起,马克思还为《纽约每日论坛》撰写文章。马克思作为经济记者,主要关注欧洲经济危机、货币金融政策、国际贸易与殖民政策;恩格斯主要关注收入来源问题。应当承认,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学到了很多,尤其是恩格斯对经济关系的阐释,并积累了大量的统计资料。①正是这个记者工作,使得马克思不仅认识到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且促使他深入思考经验现实与理论形式之间的概念再生产。
对于《大纲》的接受来说,阿多拉斯基(Roman Rosdolsky)的工作是奠基性的②。后来,各种修正版本被广泛接受。例如,意大利共产党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反对派特隆蒂(Mario Tronti)、潘兹里(Raniero Panzieri)阐发了《资本论》的独特版本:它是关于——根据自身逻辑而未走向历史终结的,并包含不同阶级力量的——社会关系的动力学阐释。迄今为止,至少出现了四种不同的阐释:(1)《大纲》是通过黑格尔引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批判形式到《资本论》中不再能够看到,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通俗化”并从辩证法中解放出来;(2)《大纲》很少是经济主义的马克思,因为在这里,他还有“火药味”;(3)在《大纲》中找到了理解帝国生产方式与新的物质劳动生产方式的概念工具;(4)《大纲》被解释为从来都不是为出版而思考的、自我理解的重要文本。
至于《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大纲》大致研究了《资本论》第3卷的材料。在其中,马克思突出了货币的必要性及其功能,描述了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与作为价值实现过程的劳动过程,确立了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并使作为生产过程和循环过程统一的资本关系再生产成为主题。不过,马克思既没有阐发抽象劳动的核心概念,也没有澄清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于哪个范畴的问题。因为在《大纲》中,马克思不是开始于商品或商品两种价值形式的分析,而是始于价值和货币。此外,他不仅使用了不同于抽象劳动的语言,即一般劳动,而且从构想上看,也完全不同于1857年理解的内容。在《资本论》第1版中,马克思将构成价值的劳动与简单的、单调的、不熟练的劳动视为统一的,到《资本论》第2版中,马克思彻底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跳跃点”——劳动的二重性。这样,就像亨利希(Mihael Heinrich)所理解的,抽象劳动就成为一个根本的社会范畴,它不再与具体劳动发生关系,而不过是社会抽象的结果,在市场上不同的劳动可以等量齐观。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马克思的进一步研究来说,《大纲》应该是重要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及其他一系列手稿③与《大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可以被视为《资本论》的准备稿。因而,《大纲》的历史地位在于: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里程碑,并且对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来说具有核心意义。
二、“’68运动”历史作用的不同评判
2008年5月是法国“’68运动”40周年。虽然这一运动出现在法国,但德国学者对“’68运动”的起因、过程进行的反思性回顾不亚于法国,并对其历史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评判。
一是持否定态度。德国社会科学家彼得(L.Peter)以“A/R-G”④为例对“’68运动”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们能够从意识形态上以各种不同方式清除’68运动”⑤。在“A/R-G”看来,“’68运动”的真正敌人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后—’68”左派。因此,他们将矛头对准了法国当时两个最大的左翼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于1972年提出的共同治理方案,并对准了密特朗时代(1981-1995)。在“A/R-G”的视野里,左翼的“’68精神”已经转变成为道德相对主义和消极的意识形态。所以,彼得指出,如果将“A/R-G”的《尼古拉·萨科齐阐释的1968年5月》一书⑥与法国历史学家阿吕(G.Aly)的《我们的1968年的斗争》一书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出,尽管这两本书都承认“’68运动”对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创造性意义,但是它们“在意识形态上是根本相同的”⑦:他们都断定,法国的“’68运动”直接地或间接地阻碍了德国改革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
二是持肯定态度。德国政治科学家施佩克曼(G.Speckman)对阿吕的命题进行了批评。在对“’68运动”进行分析时,法国历史学家阿吕提出并阐释了“’68运动与纳粹运动具有相似性”这个命题。在他看来,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把共和制视为历史上过时的,并由此具有掌握国家权力的欲求;两者的差别仅在于:共和制是通过反犹主义、征服战争、大屠杀而获得的统治来代替,还是通过协商民主来代替?对阿吕来说,“’68运动”与纳粹运动之间的差别还是引人注目的:纳粹是通过突然暴乱而获得国家权力;“’68运动”却是突然地失败,至少是分裂⑧。施佩克曼指出,尽管阿吕后来对自己的命题进行了补充,但是,他的命题离对“’68运动”的历史进行清算还差得很远。实际上,运用“’68运动”这个符号,可以证明20世纪的一个历史事实,即:对左翼观念的每一次坚持都必然会导致暴力和恐怖。
三是具体分析态度。如果说,施佩克曼通过对阿吕的批评,肯定了“’68运动”的意义,那么,在柏林召开的纪念“’68运动”的学术会议上,则对“’68运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例如,柯恩(G.Koenen)用自己在德国共产主义联盟和毛主义语境中的个人经历,将“’68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越来越严重的斯大林化主义运动;由此,柯恩抛弃了“’68—代”——因为他们不能被视为“黄金时代的最激进的孩子”。与之相反,德佩(F.Deppe)则对“’68运动”进行了历史分析:这并不涉及对“’68运动”立场的捍卫,而只涉及具体的目标追求。德佩追随德国“左派马克思主义导师”阿本德罗特,要求知识分子拥有某些社会权力,指出为了能够改变社会力量关系,左翼必须定位于此。根据德佩的看法,“’68运动”的作用,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过,他还试图确定当时学生运动的错误。恩格尔斯泰德(H.Engelstaedter)说,“’68运动”并不是政治上暂时胜利的革命或反革命的活动,关键在于它能够使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出保障经济或社会再生产的动能。但无论如何,“对于整个世界的人道主义的进步来说,’68—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⑨。当然,应该进一步讨论的是,各种政治力量、政治运动与社会结构的结盟问题。
除了对“’68运动”的历史作用进行评判之外,德国学者还讨论了“’68运动”前史、原因等问题。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戴纳(Eberhard Daehne)⑩对1959-1962年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与“’68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并着重讨论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高校政策、与SPD的关系。又如,2008年4月18-19日在柏林召开的“’68事件:‘世界革命’的长期影响”学术讨论会,不是讨论具体的人、事件与后果,而是集中关注“’68—代”的活动史、反对美国越战、拒绝斯大林主义暴政、制度民主化与反对“红色军团”(RAF——恐怖主义组织)、民族社会主义的罪责及其在阿登纳体制中的相应后果等问题。
三、德国左翼与民族关系,以及德国特殊道路问题的论争
关于德国左翼与民族关系的讨论,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够正确地处理德意志民族、历史与民族利益问题——一个似乎超越了阶级对抗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民族?斯查迈泰德(M.Szameitat)说,民族就是市民阶层、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广泛的阶级团结。“不仅民族国家,而且民族本身都是资产阶级的创造物……封建社会还没有认识到民族。随着资本主义出现而形成的民族在地缘、语言、文化或特殊历史认同基础上得以发展。”(11)在他看来,德国左翼与德意志民族的关系是“断裂的”。这种断裂关系不仅依赖于德国资产阶级建构民族的特殊方式,也依赖于这个事实:为了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德国大资产阶级将德意志民族带入了侵略战争。就是说,德意志民族在德国资产阶级领导下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即战争罪。当然,“这种与德意志民族的‘断裂’关系是可以理解的甚或是必然的,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上,德意志民族有一个困难的生存状态”(12)。这就是德国左翼难以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因所在。
施密特(W.Schmidt)认为,德国左翼与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困难,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德国历史之中。围绕着德国左翼与民族关系,萨洛蒙(D.Salomon)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德国左翼对民族概念的怀疑;“开放的边界”或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民族国家、文化与霸权;作为公开创伤的“德国问题”。他指出,在德国艺术尤其是德国文学中,“德国问题”总是转向整体矛盾、癫狂、反常性行为等,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如果文学试图在历史中阐释自己的时代,那它就不需要惧怕失败。这个绝对命令又接近葛兰西关于文化与艺术关联的论述。“但是,文化变革意味着什么?这个变化必须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文化变革必须对民族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在变革过程中必须出现变革的艺术吗?”(13)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加以解决的。
2008年,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洛苏尔多(D.Losurdo)《民族问题:为霸权和德国特殊道路的神话而斗争》一文在德国发表,引发了关于德国特殊道路的论争。在该文中,他问道,集中于民族问题会不会有为沙文主义开辟道路的危险?换言之,捍卫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与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有何区别?他回答说,尽管两者表面上相似,但是可以把它们当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来对待:一种是普遍的,另一种不是。况且,“对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或霸权主义的拒绝,根本不是匿名的民族虚无主义。根据黑格尔的提示,我们能够说,民族是一个个体。在民主的世界秩序中,捍卫民族的尊严并不与尊重归属于它的个体的尊严相对立”。(14)那么是否可以说,笼罩着德国的,是永远反革命的特殊道路?洛苏尔多断定,永远反革命的德国特殊道路的说法,适应于协约国的战争意识形态。它是历史上完全未论证的、右翼政治的骗人神话。这意味着,洛苏尔多否认“德国特殊道路”的说法。
针对洛苏尔多的观点,德国学者兰德菲尔特(B.Landfeld)、瓦格纳(K.Wagener)、克诺尔(L.Knorr)等人提出了批评。兰德菲尔特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德国的实际历史进程并没有打上人道主义民主德国的渴望和追求的烙印。对这种情况的痛苦反思,是民主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德国左翼而且是资产阶级的遗产。瓦格纳指出,就“德意志民族”而言,几乎没有一个左翼学者不拒绝洛苏尔多的描述,因为他试图放弃永远反革命的德国特殊道路的“神话结构”。因而,即使对民族问题进行革命回答的尝试有成功的前景,却没有对全球战略的回顾,也几乎不能作出实际评判——这是洛苏尔多分析的真正盲点。(15)克诺尔则认为,洛苏尔多试图清除1789-1945年的德国特殊道路的做法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2008年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状况与往年相比,有着四点突出之处:更加深刻的理论探索,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具针对性的历史反思,更加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文献学研究成为马克思学研究的新热点,但又从过去过分注重“经典”文本走向过分注重“MEGA2”;过分注重经济学维度,哲学维度有所淡化;过分关注现实问题,理论深度有所弱化;理论视野过于宽泛,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左翼思潮研究边界不明;研究队伍严重老化,后继研究人员比较缺乏;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经济状况不佳,社会政治地位堪忧。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注释:
①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克莱特科(Michael Kraetke)说,这些资料被用在了《资本论》加工过程中。
②阿多拉斯基(1878-1945),原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梁赞诺夫的继任者,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48年,他就认识到《大纲》的意义。1968年,他的《关于〈资本论〉的形成史:1857-1858“资本论”的粗略构想》(3卷本)具有奠基意义。
③即《1861-1863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经济学手稿》。
④即:André Glucksmann和Raphaeel Glucksmann,前者作为奥地利犹太流亡者的儿子,生于1937年,法国哲学家;后者生于1979年,法国记者,以下简称“A/R-G”。
⑤Lothar Peter,Die Geburt des Neoliberalismus aus dem Geist von 1968,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 74,Juni 2008,s.93.
⑥在该书中,“A/R-G”抓住了萨科齐的这个断言:“’68运动”遗产必须被清除。
⑦Lothar Peter,Die Geburt des Neoliberalismus aus dem Geist von 1968,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 74,Juni 2008,s.103.
⑧Guido Speckman,Ketzerischer Konformismus.Goetz Aly und der Kampf um 68',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 74,Juni 2008,s.83.
⑨In: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Nr 74,Juni 2008,s.163.
⑩戴纳(Eberhard Daehne),德国社会学家、1961/62年“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两主席之一。
(11)Manfred Szameitat,Globalisierung und Nationalstaat,In:Marxistische Blaetter,01/2008,s.84.
(12)Manfred Szameitat,Globalisierung und Nationalstaat,In:Marxistische Blaetter,01/2008,s.85.
(13)David Salomon,Hegemonie,Staat und Kultur.Gramsci,die Deutsche Linke und das Problem derNation.In:Marxistische Blaetter,01/2008,s.69.
(14)Domenico Losurdo,Nationale Frage,Kampf um Hegemonie und der Mythos vom deutschen Sonderweg. In:Marxistische Blaetter,01/2008,s.51.
(15)Klaus Wagener,Idee und Interesse.In:Marxistische Blaetter,01/2008,s.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