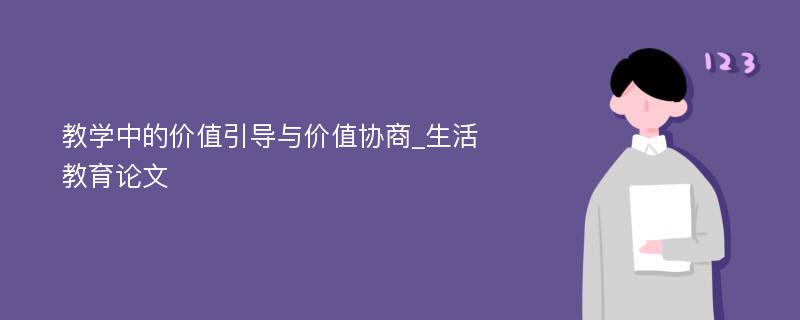
教学中的价值引导与价值商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教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课堂是价值的“富矿”,只要稍加留意,就会看到价值资源的丰富存在。例如,《中国石拱桥》这篇课文,它除了作为语文课文可以发挥的本来价值——启迪学生学会欣赏和写作说明文外,还有多种可能的价值引导功能:可以提升认识能力,如追寻桥的起源,或者从力学角度思考不同的桥的不同构造;可以陶冶审美情操,如将卢浦大桥和赵州桥两幅照片放在一起比较、欣赏,一个现代得炫目,一个古朴得深重,相映成趣;还可以从赞美桥拓展到赞美造桥的人,感受他们的智慧与勤劳……
然而,课堂教学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是间接的、影响方式是渗透式的或者伴随式的;由于课堂生活是学生最基本最日常的学校生活,因而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又是最持久、最“不露声色”的。站在学生是自我发展主体的立场上看,课堂教学无疑是学生道德发展的重要环境。传统上,课堂教学也强调“教书育人”,但实际的理解和做法是:要么将教书与育人割裂,要么把育人标签化,或者是表面上摆脱了道德价值灌输,骨子里却缺少价值多元意识。本文将从学校德育环境重建的角度,探讨课堂教学影响学生价值观念的路径优化问题。
一、趋势:从价值引导走向价值商谈
1.从价值灌输到价值引导的转向
时至今日,大概不会有人公开宣称道德教育就是需要灌输了。在西方,给灌输论以沉重打击的是“价值澄清”学派。他们意识到,在开放的多元社会,丰富多变的社会因素,还有许多成人的行为方式与其行为准则和道德说教的不一致,给儿童价值观念带来混乱。而传统的德育又只注重灌输和劝导,培养出的人往往对权威不加分析地盲从,或是装作相信规范的世故。更有冷漠、轻浮、倦怠等不良心态。价值澄清理论鼓励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与价值有关的问题,帮助他们澄清个人的价值观,以在行动中表现出更少的困惑、冷漠或矛盾,提高他们分析、处理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能力。价值澄清作为一种德育方法,包括四个要素:以生活为中心,关注那些经常使生活复杂化或使价值问题显得扑朔迷离的问题;对现实的认可,即在澄清价值时接受他人的立场,并对他人不作评价地表示理解;鼓励进一步思考,更全面地思考价值问题:培养个人能力,使其能更深思熟虑地看待价值问题,更好地整合其选择、珍视和行动。(注:[美]路易斯·拉思斯著,谭松贤译:《价值与教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2页。)
霍尔和戴维斯提出的关于道德教育的五个命题中,第一个就是“道德教育应避免向个人灌输任何价值体系或信仰”。他们认为,“一个自由社会的教师,不仅应避免教授任何单一的道德原则体系或信仰,而且也应避免反复灌输各种态度、习惯和行为方式”;“道德教育能够而且应该仅仅被理解为试图给予学生做出道德决策的技能和能力”;“人们所采纳的那些原则或观念,最终决定着他们现在是和将来是哪一种人,因此,意识到道德问题是使一个人能更好地支配他自己道德生活的一种方法。”(注:[美]霍尔、戴维斯著,陆有铨、魏贤超译:《道德教育的理想与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85-186页。)他们的锋芒所指,是“灌输”这种方式,正由于方式不对,无论灌输什么,都不能称之为教育。他们说,如果人们反复地灌输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使学生以一种狭隘的思想方式来信奉它们,甚至不去考虑一下其他生活方式所具有的优点,那么这就是灌输而不是教育。(注:[美]霍尔、戴维斯著,陆有铨、魏贤超译:《道德教育的理想与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9页。)
其实,传统的以灌输为特征的道德教育,其行事逻辑包含着两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存在着一套“外在的”、“正确的”乃至“唯一”的价值观体系;可以不考虑教育对象的主观感受、用直接给予的方式让对方接受。我国的不少学者比较赞同用价值引导取代价值灌输,或者将价值引导与学生自主构建相结合。价值引导的道德教育实践,考虑了教育对象的心理感受问题,是值得称道的,但仅仅是采用更为“巧妙”的方式让“受者”接受,而依然保留对灌输式德育的第一个假定,即存在着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且与灌输德育一样,均有意无意将教育“对象”视为被动的接受者。第一个假定体现在学科教学的德育中,还附加了一个假定:教学文本(如语文的课文)所体现的价值取向都是正确的,于是有了如下表现。
2.价值引导在教学实践中的几种表现
以文本作者的价值取向为取向 这一取向也可以叫做“忠实于原著”。尽管有专家提醒,对《落花生》这一文本一定要吃准吃透,不可随意解读,然而,老师往往费尽口舌,努力说明作者的意思是要学花生谦虚朴实,不要像苹果、桃、石榴,把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生羡慕之心。而到了课的后半段让学生开放式地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时,几乎所有学生都不做花生而要做苹果这样的人——既体面又有用。有的还说,如果你去面试时穿戴落伍,人家经理就不会要你。可是老师不予认可,继续寻找符合文本作者心意的答案。我以为,孩子们是对的,至少是合情合理的。《落花生》作者生活的时代状况与今天的确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作为语言学习的文本,以及文本作者的体验,放到今天的课堂对话中也至多只是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而已,老师大可不必强求一律。
以教师自认为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取向 曾听过这样一课——《捡》,作者假设了一个场景:一大学寝室七名女生,围绕“假若你能捡到一个东西就属于你,你最想捡到什么”展开想像,有的说要捡一本大百科全书,这样什么考试都能应付;有的想捡一袋她背得动的金子;有的要捡一个大学校长,还有的要捡个教育部长当当,专管校长;最后一位说,她要捡一对明亮的眼睛,送给邻居小燕子,她是多么可爱的一位盲姑娘啊。在针对这个文本展开的讨论中,捡友谊、捡爱心的都得到了表扬,而赞同或希望捡钱(金子)的却不被老师认可。好几名学生在课后的小作业(这是听课者要求的)中写道:“为什么捡钱不可以,没有钱,什么爱情、友谊、爱心都无法实现。”“她不贪婪,只捡‘一袋她背得动的金子’。”其实,文本作者在后记里说,他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弟弟,因为无法治好,所以写了这篇短文表达自己无法实现的心愿。“捡”在这里是一种寓意,一种寄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愿、不同的抱负,这属于“私德”领域,是完全可以多元取向的,不同取向相互之间是无法也无需分出高下的。
以不由分说的方式强行引导 如有的老师在上《中国石拱桥》一课时,总要多余地问上一句:体现了什么?学生则回答: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在茅以升先生这篇说明文中,重点是介绍中国古代的石拱桥,它们的建成与社会主义制度又有何干?又如上《三棵老槐树》的老师认定作者是因喜欢老槐树而写,也不问学生是否理解、是否赞同,只是一个劲儿地追问“哪些地方体现了作者的喜欢……”布置的课后作业也是“写一件你喜欢的东西”。
看来,如果不加分析、不带条件地奉行课堂提问(或讨论)中的一元价值取向,很难有真正的对话出现。那么,这种从价值灌输转向价值引导,也就只是方法上的“转”而非根本观念上的“转”。
3.价值商谈与价值澄清、价值引导的不同
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呈现于人与宇宙中其他“在者”的关系之中。因而,只有在关系中,尤其是在我们以全身心投入的“我一你”关系之境界中,价值才得以透彻地把握。所以,价值商谈的前提是:态度上相互尊重,认知上存有差异,对各自的观点、立场既坚持,又学会保留或让步,能容忍不同意见、乐意展开讨论、澄清。这是情感上的豁达,也是理智上的宽容。
价值商谈与前述西方的“价值澄清”理论有所不同。(1)对背景的认识不同。价值澄清学派认为当今学生处在一个充满价值冲突的社会环境之中,而笔者认为这个社会中的各种价值观念之间既有相互冲突的,也有相互呼应或补充的,还有并行着、互不“侵犯”的,呈现复杂的关系状态,或者说,是一个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背景。(2)假设前提不同。价值澄清学派认为当代社会根本就没有一套公认的道德原则或价值观,而价值商谈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在不同时代、不同交往层次上都有公认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如自由、正义、民主、法制等这些“普世价值”为几乎所有先进文明所接受;再如文明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取向方面,也不难达成共识,我国学者指出当代中国道德教育内容的基础性构成是: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为人之德”,以责任心为核心的“行事之德”,以爱国为核心的“处世之德”,还有人对待生命和人生的态度,即追求自我表现完善的“立身之德”。(注:详见叶澜:《试析我国当代道德教育内容的基础性构成》,《教育研究》,2000年第9期。)这应该说是反映了价值观共性的。关键在于这些公认原则或观念不是外在于人的,也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需要在反复不断的商谈和体验中、在一个个特定的具体的交往场景中形成认同或自主建构的,并且,建构起来的这些原则、观念及其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生成、改组和改造着的。(3)获得方式不同。价值澄清侧重于价值观念的“选择”、“评价”和“决定行动”,更关注“德能”;价值商谈侧重于“对话”、“互动”和价值讨论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在关注“德识”和“德能”的同时,关注“德情”。
价值商谈与价值引导的区别主要在于:不固守单一的价值体系(这主要是在“私德”领域),不强加某种价值观念或体系于人,而是通过真正的对话、独特体验式的理解,不断地促成学生价值观念及体系的个性化的自我构建。
二、价值商谈的特征:对话、理解、个性化建构
1.真正的对话
课堂上进行价值商谈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话,包括人与文本、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读懂文本中蕴涵的价值观念。“读懂”的意思就是读者作为观照者进入文本,找到“相遇者”。“人观照与他相遇者,相遇者向观照者敞亮其存在,这就是认识。”(注:马丁·布伯著,陈维纲译:《我与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34页。)课堂上人与人的对话,即生生对话和师生对话,既是观照者与观照者的对话,也是相遇者与相遇者的对话,因为人也可作为“文本”被另一个“文本”观照和解读。
对话不仅仅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也不仅仅以语言的方式进行,“人以多种口舌言说:语言之舌、艺术之舌、行动之舌,但精神始终如一……”(注:马丁·布伯著,陈维纲译:《我与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33页。)
对话是直接的、包容的、是不期然而然的“相遇”,是一个关系事件。真正的对话无需刻意“制造”,它的高境界是“无意插柳”式的相遇、相知与相通,是一种“神会”。
2.“设身处地”的理解
其实,对话开始,理解也就开始了。这里所说的理解,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基于观察或推理使主观陈述或描述与“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尽可能“相符”,而是“将心比心”,或是对他人的“设身处地”。理解的过程不止是认知,而是全部人格因素的投入,是“‘你’、‘我’、‘他’作为人之相遇、相知、相通”。(注:鲁洁:《人对人的理解:道德教育的基础》,《教育研究》,2000年第7期。)
课堂上价值商谈过程中的理解是读者基于自己已有的经验和结构(前经验或前结构)而对“相遇者”的一种意义解读,这种解读更多地付诸一种独特的体验或意义阐释。新的《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其实,语文教科书中的每一个文本都是作者独特思想和体验的载体,它的价值和内涵也有发掘的必要。从传统教学中走过来的教师,难免发出“不会教书了”的感叹。杭州市组织一部分小学教师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辩论会,辩论主题是“语文教学首先必须尊重文本的价值取向还是学生的独特体验”。事实上,活动的策划者也清楚,文本作者的取向与学生(读者)的独特体验是互动的、是面对面的、是一种对话,无所谓先后,挑起辩论最终强化了各自的存在价值,引起人们关注课堂阅读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多层次、多维度、多方向的对话与互动。
多主体参与、多场景发生的价值多元取向,无疑向不少习惯了一元价值取向的教师提出了挑战,这样,课堂上发生的对话,就不再是那种表面热热闹闹、七嘴八舌而实际上问者(通常是教师)和答者(通常是学生)都共同期待“最正确的一个答案”闪亮登场的“教案剧”了,全人格投入并始终追求相遇相知的理解也才会在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对话氛围中产生。
3.个性化的价值观念自我建构
传统德育是以外在于个体的价值体系为“蓝图”将下一代型塑为统治者所期望的样子,道德教化的过程是外在的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嵌入”许多个体内部的过程,甚至以消灭个性和个体间差异作为成功有效地实现“社会化”的标志。建国以来的道德教育在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使儿童被动接受道德塑造的观念和模式在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影响,这种状况肯定难以适应价值多元取向的社会发展要求。
适应于今天社会发展的德育,应当以促进儿童个性化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自我建构为宏旨。自我建构并非观念“积木”搭建的游戏,而是基于道德实践的、在多层多向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及人际交往互动中,对意义、价值进行寻找、发现、认同、组合或重组、改建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这一过程渗透在学校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道德教育活动中,课堂教学作为道德教育的间接途径,无疑也要对儿童的价值建构负起责任。
学生作为自身道德价值体系建构的主体,不仅要“知人知己”,而且还要达人体己,学会在各种具体的道德场景中把握好人己关系。课堂可以为儿童的道德成长提供各种场景,相应地可以用渗透方式采取一些教育模式。如运用价值澄清模式,可以帮助儿童去认识自己的价值需要、学会价值选择并据此做出如何行动的决定,这对了解自己是很有帮助的;运用体谅模式(英国人彼得·迈克菲尔德提出),可以帮助个人摆脱那些破坏性的和自我表现损害性的冲动,如自我中心、自我陶醉、自私等等,引导人过利他主义的生活,将人从彼此的不信任和恐惧中解放出来。还有角色扮演模式,让个人通过各种不同角色规范和责任的承担,学习从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了解他人和自己的关系。
尤其要注意儿童价值构建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个性化,一个是建构,因此,课堂上价值商谈要以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价值体验为原则,把每一个生命个体看作是适宜个人道德价值体系自主生长的各具情态的“小生态环境”。
三、教师的责任:引领价值商谈
既然是“商谈”,是不是就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服从谁的问题呢?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商谈可能是这样,但在教育领域,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课堂上的道德生活,毕竟不同于真正的日常道德生活,也不是充满规则的道德“文本世界”,课堂道德生活是“意义层面”而非“事实层面”的生活,它“宛如”日常生活而非“就是”日常生活。教育改革中呼吁“回归生活”,其实是针对儿童失落于抽象道德准则和符号的排列组合“游戏”之中,而这些“游戏”却与儿童现在和未来的“可能生活”无关这种现象提出来的。在课堂道德生活中,教师有职业使命在身,他/她是(也必须是)价值商谈活动中“平等中的首席”。所以要申明的是,这里的“引领”不是引领价值,而是引领商谈,不是“领着”价值走向学生,而是领着学生选择价值、体验价值、澄清价值。换言之,教师以一个类似于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姿态,引领着“价值谈话”。
1.在价值冲突中引导商谈
价值冲突是价值差异、价值分歧的极端表现,也是引起商谈的最佳契机。如前面说到的在《落花生》课上,大多数学生明确表示苹果、桃、石榴既好看又好吃,市场经济时代既要注重内涵又要注意“包装”,做一个“中看又中用”的人有什么不好。在《捡》这一课上,学生说,只要不贪婪,捡钱没有什么不对;没有钱什么美好的愿望也实现不了……这些似乎都与教师的取向或者文本作者的取向相左,显现了两代人之间的价值冲突。教师常常在这些地方敏感度不够,或者虽然意识到了,却回应不当、回应无力或简单地往教师心目中的“正确答案”上引,白白丢失了价值澄清的素材和机会。还有一类价值冲突是文本本身蕴涵着的,如《青蛙与蛇》是一个西方民间故事,讲的是小青蛙和小蛇偶然碰到一起,玩得很开心,成了好朋友,分手时约好第二天再到灌木丛一起玩儿。可是一回到家,各自的妈妈大为震惊,蛇妈妈奇怪小蛇为什么不把小青蛙当晚餐,青蛙妈妈又惊又怕,警告孩子一定要躲开这可怕的天敌……第二天他们见面了没有呢?老师留下悬念,让学生自己去设想。围绕友谊与本能的冲突,孩子们设想了很多种结局,归结起来,这些设想既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又以一颗颗童心,虚拟着它们之间友谊的延续。笔者在评课中把这称之为“悲情友谊”,说的是动物故事,观照的却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是人在其中的尴尬和无奈。
2.在价值质疑中引导商谈
读者不赞同读本的价值观念而提出疑义,是非常正常的,学生的价值质疑也是极好的德育资源,但需要教师敏感地捕捉与恰当地回应。例如,在上《燕子与麻雀》一课时,一名学生提出质疑:“燕子把不做窝的麻雀用泥封死在燕子窝里,不是很不道德吗?”也有其他同学附和,说麻雀再懒,也不至于要把它弄死吧。针对这种情况,老师当机立断,让同学们就此展开讨论,结果想出好几个办法,让燕子既教训麻雀又帮助它学会做窝。面对不同的办法,教师也没有武断地下结论说哪一种最好,而是从不同角度肯定不同的价值取舍,赞赏他们的道德智慧。
提出质疑的学生表现出十分可贵的伦理上的同情与智慧,即:对生命价值的珍爱;反对用不道德的手段去“实现”道德目的。想出解决办法的同学,则表现了一种责任感:帮助麻雀学会做窝。这一事例表明,教师的开放心态,激活了学生中的道德资源,使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涌现”出来,从而使课堂出现了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商谈。
3.在价值混乱与困惑中引领商谈
一位教师组织学生观看影片《白毛女》后,让学生写出自己的观后感。结果,有的学生指责杨白劳欠钱不还,还要债主上门讨还,真不应该;有的说喜儿太傻,黄世仁那么有钱,干吗不肯嫁他;还有的说,那个大春也太不识趣,家里既无权又无钱,还想娶美女……这是由时空错位带来的价值“乱弹”,学生既未读懂文本,又难以理解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境。这位教师意识到在社会背景巨大差异下小学生表现出的价值观混乱,加强了写作前后的价值引导。如写作前让学生讲讲自己的构思,及时发现了学生为让故事精彩而想出的一些捉弄同学的“损招”,引导学生想出不损人、能教育人、使人信服的“高招”;写作后老师以《龟兔赛跑》故事新编为题,规定了“乌龟取胜,但兔子不是因为骄傲而输”这一基本前提。学生又编出了小乌龟“买通评委”、“投机取巧”、“挖坑陷兔”等“缺德”情节,经过教师的点化、引导及师生研讨,学生重编了故事。正所谓“把学生价值取向的车轮,从消极、黑暗、阴冷的车道上引导到健康、积极、有意义的阳关大道上来”。(注:何夏寿:《作文教学要关注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小学教学研究》,2003年第5期。)
价值商谈并不是对价值引导的完全否定,它在超越价值引导的同时,又包容着价值引导的合理成分和有效方式。也就是说,在一次次的价值讨论中,结论可以不给,取向不必归一,但引领依然是必要的。在由价值商谈形成的一个个道德情境中,称职的教师角色应该是道德资源的激活者、发现者,是道德价值信息的重组者,也是新的道德价值澄清、体验及商谈过程/场景的生成者和组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