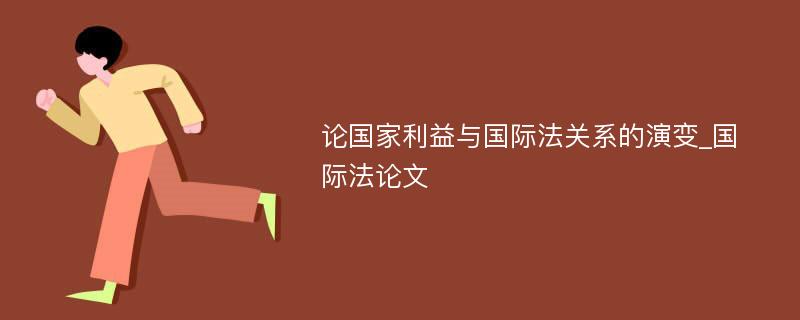
论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国家利益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4-3 [中图分类号]D815 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5-0033-16 一 引言 在实践中,利益与国家结合在一起构成“国家利益”这一词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利益”先与“王朝”、“国王”等先行结合在一起。即在古代时期,人们熟知的是“王朝利益”、“国王利益”等,而不是“国家利益”。同一时期,“国家理性”一词也与王朝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个词语有着更大的迷惑性,容易让人觉得和“国家利益”等同,事实却并非如此。追溯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著作,我们会发现“国家理性”这一词语,实质指的是君主和王室的利益。① 从“国家利益”这一词的使用记录看,早在16世纪的意大利和17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们就曾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发表主张。18世纪是国家利益的概念从理论走向现实,不断成熟,直至百花齐放的时代。②至美国宪法起草以后,“国家利益”一词的使用便已司空见惯。③随着主权的实施主体从个人控制最终转变为广受欢迎的代表机构、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以及国际关系的扩展,这都为现代观念中的“国家利益”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④法国大革命唤醒的“国家”,基本上代表的是社会中最有权力的群体。随着20世纪民主的发展,政治参与逐渐扩展到了所有阶层。在新的工业化社会,国家政策的目标被定义为提高整个国家社会成员的经济和社会福利。⑤但就如“利益”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语一样,“国家利益”这个词语也被赋予了多种含义,并且有时经常相互矛盾。因此,也不存在对国家利益的含义的统一看法,在这里我们只能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即“国家利益”这个词通常被看做“公共利益”的同义词,并且被看做是一个社会所有特殊利益的总和。⑥ 一般来说,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其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及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既包括诸如领土完整、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客观上的利益,也包括形象、自尊等主观上的利益。⑦国家利益作为国家的“利益”,其性质首先是一种“目标”,是对一个国家内群体的“好”,不过国家利益也是一种手段,即其是评价国内外政策的一种价值工具。因此,从性质上来说,国家利益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加权指数。国家利益的决定有内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所有因素既有给定、不会改变的内容,也有不断变化的内涵,后者又分为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所谓内生变量,主要是指广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整体形态;而外生变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各种相关成分。在现代社会,国家利益早已不是由国家内部决定,各种外部因素(包括国际和平与冲突;大国关系与国际组织内的合作氛围;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景气程度;信息的数量、质量以及传递速度;各种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活跃程度以及作用方式等)都是影响国家利益的重要的外生变量。⑧ 今天,虽然对“国家利益”的指责仍然不绝于耳,包括认为“国家利益”这个词是模糊的——很难明确地定义、在特殊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上很不确定以及认为这个概念并没有给外交政策的形成提供清晰的指导——它可能无法反映一个多元社会的各种声音,同时它还可能鼓励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倾向。⑨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种质疑中看出,其实已经很少有人再从性质上质疑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只是从工具上认为理解国家利益还不够,这其实不仅不是一种“否定”,而是“恨铁不成钢”形式的肯定。在实践中,“国家利益”一词已如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所赞:“在一国的国际交往中,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必然,也是一个道德义务,它是国际交往的一盏指路明灯、一则思维标准、一个行动准则。”⑩而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作为影响国家利益外生变量中的重要一环,与国家利益紧密共生在一起。各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外乎一致、互补以及冲突三种。而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正是处理这三种关系的重要工具或手段。因此,对于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辨析,是梳理国家利益研究的基础部分,也构成国际法基础研究的重要方面。当然,这个关系的厘清必须从国际法的产生、发展以及变化的过程入手。 二 国际法的“道德”进化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变迁 回顾国际法的发展史,国际法的“道德”有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古代与近代国际法维系的是极低的“道德标准”,成为大国强国掠夺小国、弱国的工具之一。而民族自决权的产生与发展是国际法变成“国家合意之法”的转折点,也是国际法与国家利益关系变化的转折点。 (一)“道德性”弱的国际法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 古代国际法,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其规则的道德水平是低下的,甚至是“血腥的”。即使到中世纪的欧洲,对城镇和堡垒进行洗劫仍然被视为对参加围攻的士兵的一种必要的奖励,也是对下一个围攻目标诱降的有用警告,这被视为国际习惯规则或习惯法。迟至16世纪,西班牙神学家运用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经院哲学原则辩解说,屠杀和强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对战争中站错位置的人们的惩罚方式。(11) 近代国际法实际上是由欧洲国家之间缔结的国际法外延而成。而在这种外延过程中,“文明国家”与“不文明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际法的缔结与传播,往往是通过坚船利炮而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无论是缔结的内容,还是缔结的方式,都充满了“不合法性”。这段时期所谓的主权原则,或者更具体的主权平等原则,更多只是世俗君王与神权教会争权划界的工具,再晚一点也只适用于欧美的所谓“文明国家”之间。这些“文明国家”与之外的“非文明国家”之间遵循的仍然是弱肉强食法则,国际法成为形式上的“遮羞布”。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即为典型。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至上的迷梦。自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始,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70余年间清政府前后签订了三百多个不平等条约。这些带有特权性质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从一个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的东方大国跌落成为备受列强欺辱的弱国,在实际利益上受到了严重的剥夺。(12)在当时,这些不平等条约仍然是符合国际法的,属于国际法律渊源之一。只是,这种具有严重的“道德问题”或者“不道德”的国际法,对于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来说,确实是在很多方面与其国家利益相抵触。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仅在物质上损害这些小国或弱国的利益,而且因为条约的“丧权辱国”之痛,对国家形象以及国民心态造成很大的矮化或屈辱,从而在精神或文化上也严重损害当事国的国家利益。 至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国际法并不完全是国家之间合意之法。对于列强之间来说,国际法是它们的合意之法,国际法旨在调整它们之间的秩序体系与利益分配;而对于弱小国家来说,在整体上国际法属于一种强国强加于弱小国家的不平等之法,在很多方面可能损害了后者的国家利益,(13)或者国家利益中的某一部分利益。从国际法上讲,根源在于这一时期列强与弱小国家之间并不是主权平等的国家间关系,弱小国家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民族自决权的实践与国际法的“道德性”进化 实际上,要理解国家能否维护共同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必须首先假定国家既是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也是在国际事务中唯一的合法代表。在国际法本身的“道德进化”过程中,民族自决权以及以此为中心的主权法律制度成为国际法“道德性”演进的转折点,也成为国际法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演变的转折点。当许多殖民地地区还不被承认或尚未独立时,国际法在某种意义上自然变成“道德性”较低的法律。当国际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包括帝国、殖民地、半殖民地时,帝国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间自然谈不上能有某种符合现代道德标准的国际法的平等适用。 不过,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自决原则使得一部分人得以通过自身构建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并赋予自身成员许多权利和义务。这种政治单位的形式和范围与现代国家共同体极其相似,即民族已成为国家天然的基础,即使一直存在例外的情形(如多民族国家)。(14)无疑,“民族”和“国家”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在现代社会它们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牢牢地、习惯性地被应用到现代政治话语中。在理论上,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人的权利”学说中最早提出了“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一词,在康德(Imannuel Kant)的永久和平思想中,也论及包括国家的自决权在内的主权问题。(15)“自决权原则是民主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政治自由的表现,即意味着个人拥有就其所属政治单位的组建形式及相关事务被征询意见的权利。自18世纪末以来,自决原则已被普遍解释为‘民族’和‘国家’应当一致,国家应当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而民族则应当形成国家。”(16) 在20世纪前半叶,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得到理想主义者的广泛共鸣,包括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内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中的许多方面都能在这种思想中找到痕迹。这种思想在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1月发表的旨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后来成为战后和平纲领的、题为《十四点》的演讲中得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体现。其中,《十四点》的第五点有关“民族自治”,即“对所有关于殖民地的要求做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此项调整的基础,就是要严格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在决定所有这样的主权问题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受到同等重视”。这是有关“委任制度”与“民族自决权”的早期论述。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民族自决还只是一项政治原则,而不是法律权利。 二战结束后,民族自决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变成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成为主权制度中的核心原则。自决权作为权利的特性,反复地被《联合国宪章》所强调。(17)《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2项明确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由此,“自决权”成为主权制度中的核心部分,并最终使得主权制度成为当代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制度。(18)而一旦“自决权”进入国际法的视野,并得到国际法的不断强化,在许多原来属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不断取得独立解放,并与原来的“文明国家”平等于世界舞台的时候,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基本行为体,国际法本身的“道德性”也不断得到提高。这时,国际法在实质上变成国家之间合意之法,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主权制度成为当代国际法的最核心部分,其不仅使得国家之间在国际法上平等,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也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同时,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主权制度也将原先“不道德”的国际法提升到“相当道德”的状态,取得了其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正当性”。这时,国家利益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转变。除掉特殊的强行法,一般的国际法“只有通过法律条文表达了缔约方间一致或互补的利益的协议才有可能有效并持续,并且只要其中的条款与缔约方的利益相符,该协议就会一直被维持下去,这就是国际间政治的通常规律,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时期”。(19)如今,“互惠主义是国内以及国际法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是国际关系中的规范主题和实践。它被称做外交的灵魂、机构或推动力”;(20)“互惠主义充当了国际条约以及习惯法出现的合理因素。互惠主义作为法律原则的建设性力量和稳定性功能,依赖于国家主权平等及其互动的契约性等价交换(相互利益、给予和取得、权利和义务)。互惠主义可以被视为国际法体系的一项元规则”。(21)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制度本身所包含的许多道德概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二战前很长一段时期,在战争中保持“神圣中立”曾被誉为一种很绅士的国际准则,得到国际法的保护。但“神圣的中立”的道德性在二战后发生质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明显被视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中,没有人再会对仍保持中立的国家保持赞赏。(22)再如,二战以前,一般认为用国际法来限制战败国的权利是后者必须接受的天经地义的“惩罚”。但二战后国际法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即强加给战败国的屈辱条件并不是寻求和平的国际法律制度,只会埋下重新进行战争的火种,这种国际法律制度是不道德的。为了寻求国际和平与发展,包括战胜国在内的各国看待国际生活的视角不能继续从它们自己的利益出发,而必须以一种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利益或者是全球和平的伦理利益的视角,(23)这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正确路径。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在美国霸权下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同以前的历史不一样,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本改变以及对自由与和平的偏爱密不可分。“美国幸运地拥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近一个世纪美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其国家利益已界定为一种愿望,即促进传播自由、繁荣与和平。人民的意愿和现代经济的需求都符合这种对未来的展望。”(24)因此,作为霸权国的美国改变了历史上迷恋于“攻城略地”的帝国扩张模式,而主要借助了国际机构与国际法律制度来实现全球治理,这种治理模式需要和别的国家共存与合作以及共享利益,反过来这种需要改变了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当代国际法律体系的性质,并极大地提升了其“道德性”。 总之,随着以民族自决权为核心的主权制度的建立与稳固,当代国际法已经成为真正的“国家合意之法”,在“道德”上实现了根本性转折。 (三)作为“国家合意之法”的当代国际法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转变 如前所述,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当代国际法从对国家之间利益分配的关注转向对“正义”、“和平”、“发展”、“合作”的追求,原来局限于对国家权利义务的关注也转向对人的权利与国家的责任的关注。最为关键的是,自从《联合国宪章》将“民族自决权”在内的主权制度基本确立下来并得到切实保障后,国际法才成为真正的“国家间合意之法”,国家对于“不合意之法”有了可以选择不加入或者重新谈判或者退出的权利。在执行方面,无论是通过“直接转化”还是“间接转化”之模式,国际法都必须转化成国内法体系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良好执行。这时,在形式上甚至国家是在执行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当国家在除掉少数国际强行法,对一般性国际法律制度的选择已经能够掌握在自身意志中的背景下,当代国际法得到蓬勃发展,大规模违反国际法的现象变得越来越罕见,国家间关系逐渐陷入一个编织得越来越稠密的“法网”之内。此时,当代国际法体系,或者整体上的国际法,与各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为什么在当代国际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具有了认同并愿意接受国际法约束的内在动机呢?分析表明:一方面,对于弱国来讲,成功获取国际社会对其身份的承认以及被这个“国家俱乐部”所接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可能成为它们掌握避免国内战争或分裂的控制能力的关键因素。而且,诸如干涉与武力使用的约束法则为这些弱国提供了外在的保护措施。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支持它们成为“国家”的国际法律秩序,尤其是主权制度,给予了它们认同、接受乃至遵守国际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强国对于国际法的内容与适用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们能够从自己主导下的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现状的稳定对于它们来讲也有着巨大的利益。这样,一旦国家认识到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整体利益,义务的观念与规则的“合法性”便有了具体的形态,对它们的接受可以不过多地考虑短期利益以及国家偏好。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的约束性并不完全依赖于主权国家的需要,它更多的是被看做受约束与自动接受某种义务的象征。具体地讲,国际法的约束性不是依赖于外在的制裁或者威胁,而是依赖于共同的认知、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以及共同的预期。国际法是合作的,而不是依附性质的法律。在一个纯粹的政治体系中,国家将以它们的利益来解释自己的义务;但在一个法律体系中,这种解释将建立在其他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国家必须参照法律来解释它们行为的“合法性”。(25)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国家利益,与当代国际法体系或者整体上的国际法之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宏观的视角,两者在基本关系上已经呈现出共生共长、相互依赖的状态。 三 当代国际法与国家利益的具体关系 “国际法”这一词语既可作集合性概念,也可以作指向概念。作为前者,其指的是整体上的国际法或国际法体系;作为后者,其指的是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由此,探讨当代国际法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时,我们也必须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即宏观角度与微观角度。 (一)从宏观视角看当代国际法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按照属性划分,当代国际法体系主要包括共存国际法、合作国际法与共同体国际法等几个部分。就国际社会法制化进程本身而言,“共存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在共存国际法得到确认与遵守的时候,国家的生存危机才得以化解,多元化的世界才得以稳固。这正是主权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与基本功能之所在。当国家之间共存不成为问题或“严重”问题时,它们之间的外交关系将自然过渡到合作问题领域。这就催生了“合作性国际法”。合作性国际法,诸如WTO所支持的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所支持的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联合国的诸多合作机制等,能够为国家合作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加合作机会等功能。当国家之间达成共存与合作关系后,一些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这时,具有“超国家法”或“世界法”性质的“共同体国际法”成为一种特殊的国际法应运而生。欧盟法就是这种国际法的典型,而在这种“共同体国际法”支撑下的欧盟也具备“超国家国际组织”的性质。 在实践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主要呈现为三种状态:一致性、互补性以及冲突性。当代国际法,无论是共存国际法还是合作国际法,乃至共同体国际法,都作为国家利益的一种外生变量,和国家利益的塑造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三种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存国际法确保了国家的生存权,不仅赋予小国、弱国免于被大国侵吞的风险,从而能与大国并存于当今世界,也使在大国之间对武力竞赛没有决胜的把握之下出现国际系统新的平衡,即让大国之间和平共处,赋予各自所需的安全感。因此,共存国际法在保护国家利益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小国,大国也一样需要共存国际法。例如,经过残酷的一战与二战之后,大国也认识到共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当冷战时期大国纷纷拥有摧毁世界的核武器力量后,大国共存变得至关重要,成为每一个大国的核心利益。“今天,这种系统第一次掌握了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摧毁世界自然基础的能力。因此,国际交往也就要求必须自我克制,而这是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26)由此,《国际联盟盟约》升华为《联合国宪章》,国际联盟也升级成联合国,大国共同治理世界被国际法律制度真正地约束下来。在《联合国宪章》将主权法律制度变得稳固,联合国安理会所承载的集体安全机制开始运转的时候,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共存终于成为现实。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当任何一个大国的核能力能把世界轻易消灭的情势下,没有共存国际法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意义,国家利益甚至整个国家就处于极端不稳定的状态。在“核恐怖平衡”下,冷战终究只能成为冷战,共存国际法基本上得以遵守。这就证明共存与国家利益已经凝结成一体,而国家之间共存国际法的维护与遵守自然也成为当代世界每一个国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合作国际法给予了国家之间增进彼此利益的机会。国家之间合作博弈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囚徒困境”。而要走出“囚徒困境”,就必须实现信息畅通以及搭建一个可持续合作的平台,从而将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合作国际法就扮演了这种角色,一方面,合作国际法本身就是国家之间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合作国际法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让每一个国家取得更多的“绝对利益”。如科斯定理所强调,达成合作必须满足三个关键性条件,包括:“确立行动责任的法律框架”、“完全信息状态”与“零交易成本”。毫无疑问,这三个条件在国际关系中都很难得到满足。这时,作为“沟通”工具的国际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7)因为国际法本身就可以被解释为减少交易成本和以有效方式分配权利与责任的规则体系。(28)实际上,国际法律制度与国际组织存在的首要意义正是承担着减少冲突与促进合作的服务功能,降低了合作中每一个阶段的交易成本。(29)另外,与其他辅助国家合作的规范相比,国际法在“制约作用”、“规范作用”、“惩罚作用”、“示范作用”以及“惯性作用”等方面的效果也更加明显。当然,以功利主义与工具性功能的视角来衡量国际法有效性只是见到“其表”,“整体性”功能与“社会性”功能才揭示了国际法有效性的“其里”。实际上,对于以“软性”见长并且缺乏统一的立法、执法以及司法机构的国际法体系,单凭功利主义所依据的物质权力的解释基点,恐怕难以理解国际法在实践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这时,遵循建构主义的思路,我们却可以看到国际法(包括合作国际法)将国际社会共享的观念与意识具体化、稳定化,塑造着凝聚国际社会的价值支柱并且规范其发展方向。国际法通过构建规范各种行为的具体规则,诱导国际社会不同成员的行动规范化,从而使得国际关系、跨国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得到顺畅的交流与管理,并且将国际社会的共享观念与期待变成现实。当然,这也应验了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塑造的逻辑,“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某种共同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就出现了”。(30)从国际体系迈向国际社会,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共同规则居功至伟。也是由于国际法的存在让国家之间的利益由冲突走向协调,从而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走向“社会化”越来越高的国际共同体。 共同体国际法使得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与一体化进程中其他成员的国家利益紧密凝结在一起。这时,彼此独立的国家利益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辨,一体化利益或有限范围内的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交织在了一起。“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和其超越国家利益的价值正在不断发展。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例如透明国际)带着它们区域或全球宗旨和目标正在测试这种人道主义理念和价值的范围。在作为‘人类共同点’的单边和多边互动中,国家政府和其领导人很多时候都在利用这些普遍接受的规则的结合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知识共享和基本原则的共识作为全球善治理念的一部分,构成了理想的国际标准与共同目标。”(31)也许以上观点还存在争论,但“超越国家利益”却已在区域范围内渐成现实,欧盟的成长以及欧盟法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这种“超越国家利益”即共同体利益的典型生成方式。将最主要的战略物资,即煤与钢由统一的超国家组织来管理筹划从而避免战争正是煤钢共同体建立的初衷。换句话说,避免战争、推动和平是煤钢共同体得以成立并运作的“共同利益”之基础。煤钢共同体的倡导者坚持应从经济方面入手来解决新的战争危险,而把法德等国的煤钢生产置于共同的机构之下管理,正是能让这两个欧洲大陆的宿敌和平共处的绝好方法。同样,推动各国经济合作,使各国获取绝对利益正是建立欧共体的初衷,或者说是欧共体得以建立的“共同利益”基础。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2条规定:“共同体的目标应是,通过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各成员国经济政策的逐步趋同,在整个共同体内促使经济活动的和谐发展,不断地平衡地扩张,日益稳定地增长,生活水平加速提高以及成员国间关系越来越密切。”至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欧洲各国面临着来自欧洲大陆之外的更加激烈的,包括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时,加速建立超国家的欧盟以及实行超国家法的欧盟法符合了欧盟成员国的根本利益:其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从而要求突破国界的限制,实行更高层次的和更大范围的国际调节与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成员国经济的持续与良好发展。其二,欧盟各成员国本身的幅员和力量使它们已无法单独应付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和挑战,因而有形成联合力量的共同需要。(32)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与需要,使得在欧洲建立超国家组织秩序成为现实,也给“共同体法”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同时,“当参与者意识到某些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并采取行动解决‘人类社会’或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时,全球化社会便出现了。为了应对今天或明天的共同挑战,这些基础性的道德价值及责任意图调和个人主义与普世主义。这些‘公共福利’的价值并不是国家特定利益的综合,而是当今人类的共同遗产:民主实践,人权,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类生存”。(33)在这种新形势下,原来立足于自我利益满足的“互惠主义”的内涵也外延到一种加强社会团结及社会利益的全球公共利益领域,许多原属于“合作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法也在向“共同体国际法”过渡,大量有别于“一体化法”的其他“共同体法”也得到不断增长,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全球利益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依据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价值和共同的行动需要而形成的国际法律制度构成了当代国际法体系的“新生力量”。法律主体从国家扩展到个人也是国际法从立足于国家利益基石向人类利益或全球利益升华的一个写照,最鲜明的体现是国际司法干预的内涵从处理国家之间争端的国际法院扩容到赋予国际刑事法庭在个人的四种犯罪上的管辖权,包括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34)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共同体国际法实际上已在促使国家利益向人类利益或全球利益演变,其扮演的是将国家社会往世界社会过渡的推进角色,关注的对象开始从国家逐渐转向组成国家的“个人”,实现国际关系对“人”的权利以及人类利益之关注的本质回归。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当代国际法的属性分析,国际法与国家利益乃至“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利益与人类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今天,英国学派的观点尤其应该得到重视,即国家促进本国利益而不顾全球人类的利益是错误的,这意味着国家利益在任何明显或潜在的意义上都已不再是单纯“国家的”,(35)而是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联。如英国学派认为,国家之间通过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规则、法律和制度形成一个自我调节的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冲突由它们共同的共存需要而得到缓和。国际法、政府间对话和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共同尊重,共同构成了这个由规范、规则、制度以及国际外交文化等组成的制度体系,发挥出协调与促进国家利益的功能。(36)在过去,“道德性”极低的早期国际法代表的更多是所谓“文明国家”,即强国、大国的利益,很多时候变成掠夺“文明国家”之外的后发展国家或地区的工具,从而可能与后一类型国家或地区某些方面的国家利益产生重大冲突。而当代国际法已经具备良好的“道德”基础,无论是共存国际法、合作国际法,还是高层次的共同体国际法,都是维护与促进国家利益的良性外生变量,有助于国家利益的稳固、增进以及升华,乃至“超越国家利益”。 (二)从微观视角看当代国际法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如前所述,国家利益与当代国际法体系或整体上的国际法的关系是一种新的共生共长、相互依赖的关系。当然,我们必须明白,以上描述的只是宏观上或体系层次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在微观层面,即使到今天,某些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或规则在跟国家利益总体协调的同时,仍然有可能与国家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某一部分发生重大的冲突。 在二战结束以前,由于主权制度、集体安全制度等还没有树立真正的权威,当时的国际法比当代国际法更为软弱。当国家利益与具体的国际法义务相冲突时,国际法义务被违反的概率非常频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人道法就得到一定的发展。《日内瓦公约》等改善了对俘虏的人道主义标准,并试图对战争方式进行更广泛的限制,比如限制潜艇击沉商用船只甚至军用船只、减少对平民的伤害、限制战争中某些类型的炮弹和枪弹的使用等。但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这样相互限制的努力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被立即抛弃。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前,国际人道法与战争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相关法律的违反却呈现出更加严重的状态。(37)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霸权体制下,国际法的权威得到更好的维护,但当国家利益与某些国际法律义务相冲突而且该方面的国家利益的诱惑足够大时,包括美国在内的个体国家还是难免会有“铤而走险”的举动。 例如,《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任何集体安全行动都必须由安理会决议同意。但对于当今唯一超级大国即美国及其盟国来说,无论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还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是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而悍然发动了战争。同时,冷战时期苏联入侵阿富汗、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与推翻尼加拉瓜政权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看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约定的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手段的义务。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当代国际法,在触及国家危机或者重大安全利益的时候,也经常发生如古典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在虚弱的国际法与强大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中,法律不得不低头——并且法学家们,要么向天空以及有关国家举起拳头齐唱哀伤的悼歌,要么用一种更为复杂的屈从或奉承姿态结成为国家行为的合理性辩护的团体”。(38) 不过,与二战以前不同的是,一方面,这种事件的发生频率与二战以前相比已经非常低,国际法的权威已经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遵守国际法本身也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同样,与冷战期间相比,冷战结束后国际法的权威也大大增长,公然违反国际法的现象更为减少。如果涉及违反国际法的指责,当事国往往在辩解之余会偷偷地纠正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相关国际法义务。例如,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将大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关押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2006年媒体爆料了关塔那摩监狱发生的一系列的虐囚丑闻,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关塔那摩的法律纠纷最直接的来源是《日内瓦公约》,该公约主要涉及战俘的权利问题。国际红十字会连同国际特赦组织、人权监察组织等坚持这些犯人应该得到《日内瓦公约》关于战犯条款的全面保护。(39)而美国官方认为他们是“非法战斗人员”,不是战俘,因此不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任何战俘待遇。随着美军一系列虐囚事件曝光,关塔那摩监狱的恶劣状况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联合国与多个国家的政府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最后美国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行为进行了“修正”。2011年3月7日,为了加强对美方司法程序的监督以确保恐怖嫌疑人受到人道主义对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重新启动美军关塔那摩监狱军事法庭的起诉程序。在此之前,这一程序已暂停两年。除了重启军事法庭起诉程序,奥巴马还在行政命令中规定,美国政府将定期审核未获起诉、遭无限期关押的囚徒的威胁程度。如果判定他们对美国仍然构成威胁,美国将继续关押他们;但如果判定他们不再具有威胁,美方将寻求合适地点释放他们,但这些囚徒将不会在美国本土被释放。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利益攸关方一般都会运用国际法来为自己的行为做“合法”的辩护,基本没有哪个国家会宣布自己无视国际法。例如,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越来越难以达成目标的情况下,1999年4月25日,北约首脑会议通过了新的《联盟战略概念》。其核心内容为在继续坚持“集体防御”的同时,捍卫所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即为确保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北约可以在其成员国以外地区采取国际干预行动,包括对付恐怖活动、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等一切被认为可能危及北约安全的行为。无疑,实际上北约试图通过新的规章制度来弥补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带来的“合法性”问题。再如,2003年美国及其盟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发动战争的辩解理由是:1991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687号决议规定伊拉克必须解除武装以作为停火的条件,但伊拉克实质上违反联合国决议,推翻了停火协议的基础。根据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不履行规定的义务,授权动武的条款自动生效。虽然美国及其盟国的这种辩护理由有点牵强,甚至有对该决议断章取义之嫌,但至少说明它们对违反国际法还有所顾忌。 因此,即使在当代社会,当某种国家利益与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相冲突时,尤其是西方国家还拥有与国际法相关的主导能力时,国家也会有违反国际法义务的冲动。但随着国际社会与国际法本身的进步,各国越来越克制这种冲动。同时,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它们也可能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制衡西方国家的重要力量,从而让失衡的国际体系走向平衡,大国违反国际法的冲动也能得到更好抑制。而且,我们也不能仅从某些国际法义务被违反就推定国际法的义务形同虚设。其一,对于这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当事国也会从国际法领域寻求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说明其实际上它们还是很关注违反国际法义务的问题。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当代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会公开宣布或承认自己无视国际法义务。其二,某些具体的国际法义务被违反并不是断定国际法无效的理由,因为没有哪个法律不会发生被违反的现象,即使是国内法也不能由于被违反而推断该法律义务无效。但为什么会发生违反现象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某个时间点上某种国家利益的诱惑(这里排除误判的情况)让国家在遵守国际法问题上“铤而走险”。此外,面对着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对相关国际法律制度中不合理的成分进行修改,否则将可能与国家利益产生新的冲突,从而增大被违反的可能。例如,反恐战争的出现实际上对《日内瓦公约》本身的“合法性”构成很大的挑战。因为反恐战争已经不是传统战争,恐怖分子也不是传统上的战俘,如何更好地协调这种新的战争方式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问题,已经提上了《日内瓦公约》的修改日程。 四 结论 无疑,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有一个“道德”的进化过程。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古代与近代国际法往往处于比较低的状态。这种性质的国际法在工具意义上就成为强国掠夺弱国的工具,有利于大国、强国的利益扩张,却和弱小国家的国家利益存在很大的冲突。当《联合国宪章》将主权平等原则确定下来并得到各国遵守之后,国际法才真正变成“国家之间合意之法”。当国际法实现从强国之间的法或强国加于弱国的不平等之法到国家合意之法的转变后,国际法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今,当代国际法体系,或者说整体上的国际法,已经和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基本吻合在一起。它们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本身的建构与维护也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看待国家利益与国际法关系时,一定要放到多元化的角度上看。不仅不同时代的国际法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会有变化,整体上的国际法、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也千差万别。当然,在宏观上,当代国际法在整体上与国家利益是协调的,虽然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与国家利益存在冲突的可能。这种冲突的存在,不仅源于国家对利益需求的多元化,也在于国际法律制度本身必须“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的变化,才能减少与具体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从而提高自身的“合法性”。最为关键的是,当今国际法体系仍然是西方大国主导的,虽然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稳定是这些大国的根本利益,但当某些国际法规则与它们的眼前目标相冲突时,在国际系统结构失衡下这些国际法规则很难抑制它们的冲动。比如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轰炸塞尔维亚而引发的“波黑战争”,苏联为了自身私利而不顾国际法的限制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等。不过,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长期失衡的国际系统将得到更好的均衡,如果世界能够继续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法前景将是更加光明的,遵守国际法与各国国家利益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6-17. ②Rozeta E.Shembilku,The National Interest Traditio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ALBANIA,Master of Arts in Law and Diplomacy Thesis,2004. ③Charles A.Beard,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4,pp.21-26. ④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25. ⑤Edward Hallett Carr,Nationalism and Afte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45,p.20. ⑥David Clinton,ed.,National Interest:Rhetoric,Leadership,and Policy,Bost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8,pp.41-42. ⑦王逸舟:《新视野下的国家利益观》,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代序”,第20-21页。 ⑧王逸舟:《新视野下的国家利益观》,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代序”,第21-24页。 ⑨W.David Clinton,The Two Faces of National Interest,Louisiana: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0-21. ⑩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New York:Alfred A.Knopf,1951,p.242. (11)Jeremy Rabkin,"After Guantanamo:The War over the Geneva Convention," in R.James Woolsey,ed.,The National Interest on International Law & Order,New Brunswick:Transation Publishers,2003,pp.64-65. (12)何志鹏、孙璐:《近代中国条约与文化的互构——建构主义的解读与检验》,载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脚注③。 (13)当然,也不可否定的是,在晚清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有一些条约或其中某些条款具有先进意义,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 (14)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25. (15)参见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8页。 (16)Edward Hallett Carr,Nationalism and After,pp.37-39. (17)Douglas J.Feith,"Law in the Service of Terror," in R.James Woolsey,ed.,The National Interest on International Law & Order,p.180. (18)从实践来看,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地、附属国纷纷宣告独立并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到联合国。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独立的和以前独立的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已在联合国中占压倒多数。在它们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从1958年以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来确认民族自决权。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项宣言确立了民族自决权为一项法律权利,它在“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的标题下,对民族自决权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至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原有的殖民地、附属国已经基本上取得了政治独立,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政治行为体。 (19)Haa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pp.99-100. (20)Wilfried Bolewski,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Berlin:Springer,2007,p.45. (21)Wilfried Bolewski,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p.45. (22)Jeremy Rabkin,"After Guantanamo:The War over the Geneva Convention," p.66. (23)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126. (24)Condoleezza Rice,"Campaign 2000: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Vol.79,No.1,2000,p.62. (25)Andrew Hurrell,"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Study of Regimes:A Reflective Approach," in 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eds.,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3-214. (26)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27)Onuma Yasuaki,"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No.1,2003,p.130. (28)Kenneth W.Abbott,"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 Lawyers,"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4,1989,p.394. (29)Kenneth W.Abbott,"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 Lawyers," p.399. (30)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1977,p.13. (31)Wilfried Bolewski,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pp.25-26. (32)戴炳然:《欧洲一体化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对一个特例的思索》,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第41页。 (33)Wilfried Bolewski,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p.46. (34)国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庭除适用主体区别外,另外的重大区别是前者需要国家自愿接受管辖,也由此导致其运作60多年来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而后者相反,主动管辖权让其能够发挥出更为大的作用。因此,从这个方面讲,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与运作,是国际司法干预的一次升级。可参见John R.Bolton,"Courting Danger:What's Wr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n R.James Woolsey,ed.,The National Interest on International Law & Order,pp.93-108。 (35)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184. (36)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155. (37)Jeremy Rabkin,"After Guantanamo:The War over the Geneva Convention," p.65. (38)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eds.,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7. (39)Jeremy Rabkin,"After Guantanamo:The War over the Geneva Convention," pp.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