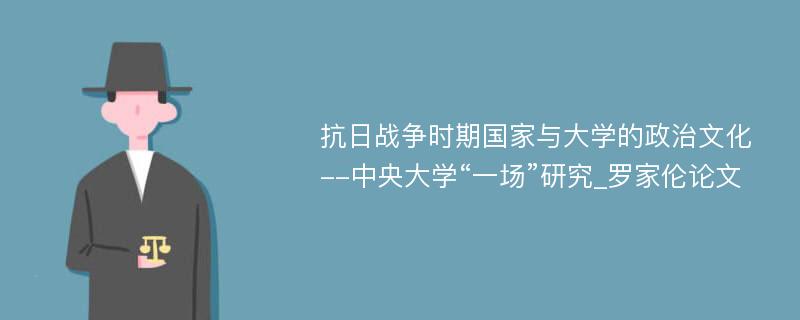
抗战时期的国家与大学政治文化:中央大学“易长”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央大学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3-0089-12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大学校长(特别是国立大学)的人选确定和更迭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或“学术”问题,其中牵扯了许多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近年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大学校长问题已有相当的专题性研究,展现了不同时段中各类大学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多层次面相。①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和江苏医科大学等其他八所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次年2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5月,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从南京内迁重庆,在教育体制上保持了学校的稳定。与清华、北大(包括西南联大)和一些教会大学相比,学界对中央大学史的关注较为“静默”。在既存研究的一般认知中,1927年由东南大学“改造”成的中央大学与国民党(国民政府)关系最紧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党办”大学。②这从“党国”控制与渗透的角度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时代语境中“国立”、“党化”和“中央化”等问题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抗战时期重庆中央大学内部和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其间校长的四次更迭成为学校内最为显著的不稳定表征。其实,校长的频繁更迭一直以来是困扰中央大学的难题,到战时更为凸显。1941年8月,长校十年的罗家伦辞职后,顾孟余、蒋介石和顾毓琇先后担任中大校长,但任期都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内,且校长轮替都与校内外的风潮有很大的关系。而同时期由“易长”引发学校的风潮,实则也是当时存在的普遍现象。本文将细致梳理战时中央大学校长更替的过程,并从中探析“易长”过程中“党国”与校园内部政治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揭示战时后方大学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
一 “经费”、“纪纲”与罗家伦的离职
从1932年直至1941年,罗家伦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长达十年,是民国历史上在同一所国立大学中连续担任校长年份最长的校长之一。然罗家伦晚景颇为“凄凉”,而且当时和后世对他在中大校长任内的评价也一直毁誉参半,久无定论。这或与他施政和辞职过程中的种种“隐情”有关,从中亦透出国民党内政争在国立大学的映射效应。
萧胜文在其论文中称罗家伦在抗战时期曾三次提出辞呈,但没有明确说明罗家伦第一次提出辞呈的时间。③通过对已刊和未刊文集、函札和档案的检视,可以确定,中央大学内迁之后罗家伦向蒋介石第一次提出辞去校长的时间是1939年2月。④
罗家伦于1939年1月29日出席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第七次会议,在讨论教育组审查委员会所提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时,受到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指责。罗家伦称:“我们不怕共产党在陕北办什么抗日大学,只怕我们自己的学校没有科学设备来培养青年,所以充实学校的图书仪器等等的设备,是防止青年走向共产党的好办法。”罗家伦希望将这一点列入报告之中,其中的焦点就是高等教育经费问题。随后,孔祥熙对罗家伦的发言予以反驳:“中央大学每年经费在一百万元以上,现时中大的学生只有三分之一,中央处此财政困难之际,并不核减,这是鉴于中央大学为国家最高学府,担负为国家培育青年的责任,故不惜以巨额经费,以资济困。”发言完毕,吴稚晖立即表示,孔氏所说的恐怕有一些误会,做了些补充解释。孔氏也立即澄清道:“刚才我所说的话,并非有意攻击别人,因自抗战以来,一般人士甚或同志中也有不明真象,以为财政当局剋减教育经费,常有责难,所以顺便说明一下。”⑤虽然吴稚晖试图为罗家伦和孔祥熙在会上的争执打圆场,孔本人最后也转移了话锋,但罗家伦并未因此改变自己对于财政部的态度。三天后,罗氏便因此事直接上书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请辞中大校长。罗家伦在信中对于孔祥熙的指责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深感此后无法负责,敬乞钧座另简贤能,并请派公正人员彻查,以明真相。”⑥
在五中全会上关于高等教育经费争执的两造中,不管谁的“说法”更符情理,至少罗家伦对战时教育经费的论说触及了当时教育发展的症结。抗战时期由于其他经费来源紧缩或停止,相形之下,政府的教育经费对于公私立大专院校的运作就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公立院校更以政府年度预算为唯一可靠的财源。然而,七七事变发生后,高等教育经费立即被删减30%。到了1937年底,经费删减幅度进一步扩大,与战前相比,约删减60%,经费不足的情况极为严重。⑦具体到中央大学,虽然其在全国各国立大学的经费分配上居领先地位,但仍和全国其他的高等院校一样,时时面临着经费危机。
罗家伦在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提案,说明他能凭借在党内的地位为高等教育和中央大学争一个“发言”的机会。但国民党的中央全会最终还是无法解决此类问题,罗家伦本人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个人身上。这种因具体问题而显现的大学与“国家”的微妙关系,恰可反映出当时国民党政治中党政关系及个人权威的一个侧面,即罗家伦深度介入国民党高层政治之中,但也未能真正带给其领导的中央大学以更多的经济利益。
从此之后罗家伦就开始萌生退意。1940年11月13日,罗家伦造访王世杰,谈到意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事情,“然不能决”。⑧1941年1月,罗家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此时罗家伦的心境是“才力已尽,应付已穷”,故而“惟有决心引去”。罗家伦在呈书蒋介石之前已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但更希望蒋“赐予核准”。⑨同年6月23日,罗家伦再次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辞呈。在致陈立夫的信中,罗家伦强调了中央大学存在的两大问题迫使他不得不辞职,即“一为经费,二为纪纲”。⑩
可以说,罗家伦的多次请辞是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说长年累月的经费支绌是主要的外部原因,那么罗氏眼中的“纪纲”紊乱则是造成他处境窘迫的内部因素。内迁之后,由于恶劣的教育生活环境和学校行政出现的某些不当,中央大学的内部一直存在着数股反罗势力。
1939年10月,中央大学100余名学生联名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指控校长罗家伦的种种“恶作”,希望教育部“明察实情,以整法纪”。上书者给罗家伦一共开列了十条“罪状”。这些“罪状”既牵涉到宏观的教育宗旨,又含有具体的贪污问题,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但确实可表明罗家伦在很多学生的心目中观感不佳。如呈文中的第二条中称罗家伦“轻视学校党务”一节,胡思明等学生称“中央一再命令推进学校党务,而罗校长身为党员且负重责,对于命令视若废文。校内党务只有空名而无实际,致使他党活动甚力,而我党无形敛迹”。(11)
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各高校设立党部是应对中共学生运动和加强高校内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手段,中央大学奉令于1939年7月成立直属国立中央大学区党部筹备处,同年12月正式成立了直属区党部。学生指摘身为“党国要员”的中央大学校长竟然轻视党务以致校内“他党活动甚力”,在战时大后方国共党争的语境中极具杀伤力。
学生的反感或许还不能对罗家伦造成很大的压力,更主要的还是学校内部存在派系争执。近代中国大学的派分本十分明显,在时人的认知中便有明显的南北之别。其中北方的北大、清华和南方的南高师(包括后继的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学派对峙是大学派系的重要分野。
从历史上看,中央大学一直存在两个主要的教师群体:一是由中大的前身南高、东大毕业或长期在本校执教的教师构成的“南高东大派”,另一个则是毕业或曾执教于清华、北大的教师形成的“清华北大派”。1927年中央大学改组后,特别是在罗家伦担任校长后,学校引进了一批归国留学生和学界名宿,其中有一大批即有清华和北大的背景。这两派的现实存在是时人的共同认知,但派系的分隔和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是特别强烈。但在遇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时,平日里的宁静往往会被打破,两派的区隔凸显。然中央大学的两大学术派系因为罗家伦有意无意间的偏倚而使得两者间的鸿沟日益加深,(12)而且校长的人选其实更直接关系到教职员的前途甚至是“饭碗”问题,很多大学都有此种情况的存在。
1941年3月,中央大学爆发助教集体罢教事件。起因就是因为生活的困苦和薪津低下,助教向学校要求每人加薪2级,将生活维持费增为40元,并请继续呈部要求发给房贴、膳贴40元。学校于3月3日致函各助教,希望能给予一定的时间予以改进,但助教方面并不赞同,从而引发了一场罢教事件。(13)中大的助教大多为本校毕业生,长期得不到升迁,而且薪金也相当低。(14)况且,在中央大学,助教组织的“助教会”有相当势力,助教会的决议和执行对于整个学校都有影响力。(15)这次助教的集体罢教足以使校长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助教事件的爆发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经费匮乏而致,同时因助教大都为本校毕业生,所以其中也夹杂了学校内部的派系矛盾。
另一方面,罗家伦时期中央大学内部的派系问题中也包含了国民党内的政治因素。郭廷以称当时罗家伦“重用过童冠贤、马洗繁”,使“教育部(部长是陈立夫)不大满意”。(16)童冠贤是中央大学的教务长,马洗繁是中大法学院院长,颇得罗家伦信任,两人在学校内迁的过程中支持罗的决策,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童、马二人是北伐前国民党的“老党务”,均毕业于南开大学。而且童冠贤、马洗繁和何义均(抗战时期长期掌管中大的三青团组织)等则得到朱家骅的维护。(17)可见,童冠贤和马洗繁均是国民党内党务系统中的非主流派,他们和北伐胜利后长期主导国民党党务的CC系关系并不融洽。
陈立夫1938年执掌教育部后,在教育界扩充CC系的势力,对中央大学内非CC系的“当权派”童冠贤和马洗繁等人产生排斥感。朱家骅在抗战时期逐渐与CC系疏离,成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在党务系统内与CC系争夺权势。(18)朱本人在文化教育界有很深的根底,虽在战时主管党务,但也很注重延揽学人。陈立夫和朱家骅对于童冠贤和马洗繁等人的不同态度,明显透出国民党中央派系之争的痕迹。而校长罗家伦虽然没有特别明显的国民党派系归属,但他在个人情感和政治立场上更倾向于朱家骅。(19)对童冠贤和马洗繁等人的排斥,以及CC系与朱家骅的派系矛盾,致使陈立夫迁怒于罗家伦,造成了二者的隔阂。(20)
罗家伦对于陈立夫执掌的教育部也有不满。1941年6月27日,罗家伦在即将离任之际致函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自诚,希望其把信中的意思转陈蒋介石。罗在信中称,学校的经费危机此时已到达“不借垫则学校停顿,借垫则已无可借垫”的境地,学校向教育部“迭经呼吁”,而部中却“不为援助”。而且“中大七、八年间纪律颇好,去年冬起,渐觉败坏,实为部内有人勾结二三别有作用教员之所致,此系最可痛心之事,亦系共见共闻之事”。(21)
其实,罗氏所称的校内“纪纲”的紊乱也与自身的行事风格也有很大的关系。罗家伦生性高傲,对于校务乾纲独断,又身负“党国”的政治责任,因而导致了很多人的不满。时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的金毓黻与罗家伦交厚,他以汉初贾谊自况,曾向校长纳诤臣之谏。受到中央大学校内愈发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的触动,金毓黻主张罗氏处理校政应“提纲挈领,以逸待劳”,主张成立校务会议并采用常委制以分校长之权。(22)
金毓黻提出以校务会议分校长之权的建议很快就成为了现实。1940年3月,中央大学根据教育部的统一规定成立了扩大的校务会议。(23)1940年4月24日,中央大学上呈教育部《修改校务会议规则》,在呈书的最后称:
……其中第十九条修改之文字及精神系指凡任何议案经校长提出后议论一次即须照议决案执行,凡变更与缓办均属不可。是一切校务之最后决定权属于校务会议,在校长本无保持校务最后决定权之成见,惟此后责任所在,不得不事前申明。(24)(文中划线部分由罗家伦亲笔增改)
不知是听取了金毓黻的建议,还是对纷繁的校政已无力独揽,罗家伦向教育部呈请将校务的最后决定权划归校务会议。但教育部在四个多月后给中大下达指令:“查校务会议,依照大学组织法,应为审议机关,该大学校务会议规程第十九条毋庸修改。”(25)一句话驳回了罗家伦的请求,罗家伦所欲放弃的校长决断权,在国家的维持下得以继续实施。但此时,离罗家伦永远放弃校长权力的日子已为时不远。1941年7月15日,行政院第523次院会通过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案,并决议任命顾孟余继任,21日命令公布。(26)罗家伦刚到中大时,“是抱着理想来的”,而离别时“理想并未达到”,只能心存“惭愧”黯然而去。(27)而同时,新校长顾孟余到任,由此全校师生“群情翕然,舆论归依”。(28)
二 国民党派系政治与“学术自由”的诡论性互动:顾孟余的继任与离任
面对罗家伦多次请辞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现实,教育部一方面“劝挽”罗氏继续任职,另一方面也开始多方寻找中大校长的继任人选。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教育部长陈立夫首先想到的中大校长继任人选是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1941年4月,教育部长陈立夫就当面向竺可桢提出,让罗家伦和竺可桢对调,但竺“告以中大更难办,余不能考虑”。(29)同年6月,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致函竺可桢,转达了陈立夫再次要求竺可桢担任中大校长之意,又被他“决然谢绝”。(30)最终,蒋介石亲自介入中大易长问题,任命顾孟余继任。
顾孟余长期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最为重要的成员。1938年底汪精卫离渝赴港,顾未随汪等前往河内从事“和平运动”,而是选择返回重庆,与汪脱离政治关系。汪精卫叛逃重庆政府后,顾便成为蒋极力争取的对象。(31)起初,蒋欲将顾安排为中研院院长候选人,但遭到院内抵制而未果。除了比较反感蒋凭借政治权威推出顾孟余外,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称他个人倒是“觉得顾孟余不错”,但是“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育界多不识”,不过他可以投顾一票;而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则认为顾“只是一个politician(政客——引者注)”,自己“决不投他票”。(32)
1941年7月15日,行政院指定顾孟余为中大继任校长。在此之前,教育部长陈立夫遵奉蒋介石口谕与顾孟余相商,顾“初谦逊不就”,经陈立夫“坚请而后允”。(33)但就在此后不久,当罗家伦前往与顾孟余协商新校长就职日期时,顾“仍以谦逊未得结果”。(34)王世杰也在行政院正式发表顾孟余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第二天(7月16日)见到他,顾氏称对任中大校长之事“有敬畏之意”。(35)
直到1941年8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顾孟余为中央大学校长。8月22日,顾孟余正式视事。(36)8月30日,顾孟余在日本飞机轰炸中央大学之后,于晚上7时在学校教职员集会所招待教授讲师,并即席致辞。(37)顾孟余在致辞中特别指出:“希望本校培养成自由学术空气,并有更优良之纪律。”据当时在场的中大外文系教授徐仲年称,顾的发言“予同仁等以绝大的兴奋”。徐仲年认为顾校长提出的“自由学术空气”就是走向纵的发展的“康庄大道”,而“培养自由学术空气”,是“中央大学全体师生所热烈希望的”。(38)徐仲年在中央大学新旧校长交替之时有如此之论,一方面或许是借顾孟余之“题”来发挥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见解和提升学术的主张;而另一方面,在经历罗家伦长校后期学校校政紊乱和学术发展迟滞的乱局后,徐仲年听到了新校长具有吸引力的谈话,寄希望顾孟余能把中央大学带出困境。
就后一层意思来讲,徐仲年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中大颇具代表性。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和政治学校两边兼课的黄淬伯就认为:“中大易长以来,气象渐好。顾氏提倡学术,冀使国故化为神奇,融洽西学变为国有,此诚通人之见也”。(39)外文系教授柳无忌回忆说:“在(中央大学)这几位校长中间,我们对顾孟余的期望最大。”(40)而从嗣后各方对顾孟余任职期间的评价来看,顾的口碑也甚佳。到1947年时,当中央大学学生谈起早已离职4年多的顾孟余时,还称“由罗家伦先生到顾孟余先生,是中大一个跳跃式的进步”。(41)
昔日的同事和学生对于顾孟余的一致推崇的确是渊源有自。首先是顾孟余的到任使中大经费拮据的困难有所缓解。当时的情况是,罗家伦交卸时,经费仍亏欠27.9万余元。顾孟余上任后立刻得到国家10万元的补拨款,不足之数在1942年中央大学的经费中弥补。(42)1941年8月,顾孟余刚担任中大校长时曾向国家银行透支500万元(由教育部转函四联总处洽商)。(43)顾孟余任职期间,中央大学新建了大礼堂、学生宿舍等多处建筑,经费问题由顾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交涉,获得拨款300万元。(44)此外,顾孟余为了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曾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最终学校500万的亏空由教育部拨款400万元解决。(45)顾孟余是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汪精卫出逃重庆后,留在重庆的原“改组派”成员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更加边缘化,所能掌握的政治资源也较为稀缺。但顾氏凭借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还是能为中央大学的经费问题争取到一些回旋的余地。
在郭廷以的印象中,顾孟余校长“不多管事,不多讲话,讲起来几句话简单明了”。(46)王作荣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念书时,也感觉到“顾校长身居歌乐山,不大到校办公,到校时只与三长接触,连教授晋见都难,不要说学生了”。(47)说顾氏“不多管事,不多讲话”的确道出了他在中央大学的行事风格。顾孟余这种深居简出、“无为”治校的方式与前任罗家伦截然相反,但这不仅没有为人所诟病,反而能得到师生的基本认可。而且顾孟余的“风度”,更令中大师生为之注目。
1940年10月,美国共和党领袖、1940年总统竞选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Wilkie)到重庆访问,其间曾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参观,并和校长顾孟余会面。郭廷以在嗣后回忆起这件在中央大学历史上似乎无关宏旨的“涉外”事件时,所描述的细节还是清晰可见:
威尔基特别到中大参观,学校临时盖起门楼,扩充大门(没有建墙),学生到大门去欢迎威尔基,进了大门,走下坡路,再上松林坡(教室就建在坡上),才转到校长室,一直到门口,才看到顾先生摇摇摆摆出来,够有风度,有派头。(48)
时为中大学生的鲁传鼎在回忆校长顾孟余时,也着重提到了这一段。他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访华,顾校长不惜率同全校有关负责人,以求不卑不亢,不失身份风度,维持中国最高学府校长领导群伦的超然地位。”(49)陶怀仲也曾亲眼目睹了顾孟余迎接威尔基来访的场面:
美国威尔斯副总统来访,……顾校长孟余率领三长和各院院长站在松林坡上,西装笔挺,身裁[材]魁梧,似乎高不可攀。等威氏快到坡上,才降两级握手寒暄。威氏身体高大,面容丰满,有政治家风范气概,而顾校长亦突出挺拔,二人相较,以[已]在伯仲之间。(50)
尽管各人回忆顾孟余迎接威尔基访问中央大学这一事件的具体角度和内容不同,具体的时间也多被遗忘,所提到的人物身份更不一定准确(如陶怀仲将威尔基的身份错记成美国副总统)。但在各种说法中,有一点是相通的,即每个人对顾氏接待外宾时那种不卑不亢和雍容得体的“风度”赞赏不已。这种类同的“历史记忆”,恰是亲历者对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身上所体现的“最高学府”应有的文化与政治象征认同。通过对于以上忆述性史料的比照,威尔基参观中央大学这一事件的本身仍存有一些“迷思”(myth)。但若从类似于“以虚证实”的角度视之,在当时的情境下,校长的一次礼仪性举动能使中央大学的师生们加深对“中央”和“最高学府”现实体认,或可加深我们对此种历史现象的理解。
无疑,身为罗家伦继任者的顾孟余在中央大学师生心目中的形象是较为“完美”的,他在中大的声誉与先前汪敬熙视顾“只是一个politician”的观感也大相径庭。同时,傅斯年称顾孟余“教育界多不识”,这似乎也并没有成为中央大学认同顾孟余的障碍。(51)以上种种,恐怕是中研院同仁所始料不及的。
然而不到一年半,顾孟余便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1943年1月初,舆论已开始传出消息,称顾孟余“于月前提出辞呈,周余未到校办公”。(52)到同年2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指令,准予顾孟余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由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53)
和罗家伦一样,关于顾孟余缘何辞职的“说法”也很多。据档案史料中关于“中大易长”的报告,顾孟余离职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中大饭堂因教育系演剧发生纠纷”。(54)曾由顾孟余聘任至中大任教,又因顾孟余离职而与之共进退的顾颉刚则认为是陈立夫CC系对顾孟余的压迫使他辞职。(55)
顾孟余的辞职消息一经传出,中央大学学生便发起了大规模的挽留请愿运动。1942年11月12日,顾孟余向教育部辞职的消息传出后,中大学生曾发动挽留运动,最后因为顾孟余打消辞意,运动未再继续。1943年2月初,顾孟余辞职的消息再次传出,学生于9日晚再次发动挽留运动。12日,学生自治会拟就上顾校长的呈文,由学生签名挽顾。从13日至16日,中大学生分赴教育部、行政院和顾宅请愿挽留。18日,报纸上有消息传出顾孟余辞职获准,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挽顾运动始告一段落。(56)相比一年半前罗家伦“顺利”地辞职,顾孟余的辞职可以说是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学潮。而从学生对前后两任校长离职截然不同的反应来看,罗、顾二人的“形象”差距亦可高下立判。
三 从“最高领袖”到“知名学者”:蒋介石、顾毓琇和吴有训的先后长校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身份继任中央大学校长,多少使国民党内人士和中大师生都感到意外。陈立夫回忆,蒋介石是主动提出要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而且当时陈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而且还颇不情愿:1943年2月的一天,蒋介石对陈立夫说:“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现在所有的大学我来兼校长好不好?”但陈并未赞同,但蒋介石仍想尝试,最后陈立夫“就答允了他,以中央大学给他试,他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57)
有校友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的消息传到沙坪坝后,“全校师生,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出人意表的事”。(58)当时全校师生是否都“欣喜若狂”,还有待进一步确证,但大家听闻这一消息后大都感到“出人意外”应属实情。
蒋介石兼任中大校长的消息传来后,挽留顾孟余已成泡影,但中大的校园并未因此完全平复,学生开始有了新的“要求”。一些学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热烈欢迎”蒋介石的同时,即意识到“今后必采教育长制”。还有人表示了三点意见:“①院长兼任后,是否行教育长制,②教育长人选我们必须坚决表示意见,③召开全体大会,中大前途在此。”而且,这一消息的传来也没有使所有人都“欣喜若狂”,中大墙壁上即有人贴出壁报:“这是消息不是命令,我们仍可即刻行动挽回残局,不可消沉下去。”(59)
其后中大教育长的人选的问题成为校园内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且由挽顾所引发的风潮又得以延续。据国民党中央大学直属区党部的报告称,1943年2月19日上午九时,《国民公报》寄发到校后,学生看到报上“载有□□□□□□轩(原件文字脱落,应为“复旦校长吴南轩”字样——引者注)为中大教育长之消息,校内空气突形纷乱,部分同学遂不参加考试”。到当天下午一时,学生自动集合大礼堂。到晚上,在校方的维持疏导下,“学生回复理智,秩序得以恢复”。20日报端又传来吴南轩为英士大学校长的消息后,学校秩序才完全恢复,期末考试也得以继续。(60)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与CC系接近,这种过于“党化”的学者在中大师生中名声不佳。从学生对于“传闻吴南轩即将出任教育长”而作出的激烈反应也能印证这一点。当然,关于吴南轩出任中大教育长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在1943年2月12日教育部致行政院的呈文中显示:行政院长蒋介石在此前已发布命令:“中央大学校长由本院长兼任,修改该校组织法,增设教育长一职”。教育部提名中央大学教育长的原文是:“吴南轩原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拟调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但“中央大学教育长”这一段又涂改为“国立英士大学校长”。(61)而且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吴南轩令其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但吴“坚不肯就”。(62)可见,任命吴南轩为中大教育长是一开始就已决定的,而且也极有可能是中大学生的“拒吴风潮”最后导致了当局放弃任命吴南轩为中大教育长的决定。最后,教育部确定由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任命于3月7日才正式发表。(63)
蒋介石在1943年2月19日正式兼任中大校长。(64)3月4日上午,蒋介石偕新任教育长朱经农同赴沙坪坝中央大学视事,在校长室约集学校三长与各院院长和各系主任等50余人谈话。3月7日,蒋介石又赴中央大学对全体同学“训话”,“事前各教职员学生三千余人集合于大礼堂恭候校长之莅临”。训话时间约一个多小时,“全体肃立倾听”。(65)
从蒋介石初任中大校长的两次讲话来看,他视教育学术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并对中央大学的教育直接应用于国家建设和学生毕业后能成为合格的党国干部充满了期望。这也是蒋介石以国家“最高领袖”出任“最高学府”校长后所谋求的中央大学与“党国”最佳的连接方式。但蒋介石的“训话”并没有带给师生们太多好感。尤其令教授们难以忍受的是,他们在聆听蒋的讲话时“都站着,敬礼,他(蒋介石)请教授们一个个报自己的名,大家都以为是点名训话”。(66)且学生们对蒋介石的“训话”内容和方式更不感兴趣,后来干脆一走了之,纷纷“旷会”。
如果说新校长给中央大学带来什么新变化,或许主要还是体现在学校内实施的“军事化管理”。(67)中央大学自1943-1944年上学期起实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蒋介石担任校长期间,学校还驻扎有宪兵,直到1944年8月蒋离职后才撤离。(68)蒋介石在中大施行学生军训和军事化管理,一方面是出于抗战时期调动学生战争精神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蒋将军队和军校的管理经验直接移植到中央大学的教育理念。但中央大学的军事训练不尽人意,1944年7月19日,蒋介石手谕陈立夫:“国立中央大学军事训练总教官及教官等,对于该校学生军训毫无改进,自下学期起,各大学军事训练似均可停办。”(69)
不难想见,蒋介石担任中大校长基本上是象征意义要大于对校务的实际管理。蒋介石长校期间,也经常到校“视察”。他第一次到校便去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各处,并在食堂与各教职员工共同进餐。在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70)此后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视察”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厕所,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71)
作为校长,蒋介石对中大的管理一般来说只是象征性的(当然,作为“最高领袖”,在意识形态上,蒋在中央大学内的影响力还是很强的,但这种影响力和他的校长身份没有直接的关联),同时他对学校具体事务的掌握在很多时候是出于他偶尔视察后的直观感受,目光常聚焦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大的校政全部委之于教育长朱经农。
而在师生的眼中,朱经农在中央大学并未显示出在领袖托付治校权力后所应有的强势;相反,在学校日常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朱经农并没能享有绝对的权威,而且还常常受制于人。由于朱经农在高等教育界的根基并不深,且朱氏的教育背景和仕途履历也与“南高—中大”一系没有丝毫渊源,因此“执行校长”朱经农在声望和权势上的不足使其无法顺利行使职权。
也就在此时,中央大学校内的派系之争也使朱经农的地位更加悬虚。蒋介石兼任校长后不久,在罗家伦和顾孟余时期长期担任教务长的童冠贤被替换,由南京高师出身的胡焕庸接任,总务长也由南高系统的江良规出任。(72)中大校内人事的巨大变动与蒋介石的个人好恶有很深的关联。一方面,蒋介石对原教务长童贯贤极为不满,认为童等人在中大“作梗”。(73)另一方面,经蒋介石同意,朱经农大力执行“校友派路线”,开始延揽中央大学(南京高师、东大)的毕业生返校任教,达到“校友治校”的目的。(74)如胡焕庸即奉蒋介石的手谕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75)
当时在中大校园里流传的一个讽刺笑话中,“校长坐轿四人抬(即教务、总务、训导三长和教育长——引者注)”,教育长是“听由前面三人要怎样走,就怎样走,最没有主意”。(76)当然,这只是个笑话,不必尽以为然,但也的确道出了此时中央大学权力结构中的一些问题。朱经农在校内无权,不仅在师生的眼中如是,而且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得到的情报中也得到印证:“中央大学教务长胡焕庸自任职以来以巩固个人地位,任用东大同学,藉故排挤非东大系之教授,前任教育长朱经农任其操持。”(77)
到1944年夏,蒋介石辞去了中央大学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1944年8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朱经农中央大学教育长之职,改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任命顾毓琇为中央大学校长,免去其教育部政务次长之职。(78)
顾毓琇继任后,即在报章上发表谈话,特别宣布:“学校行政方面,应以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地位及学术上之成就,以避免学术机关变为行政机关。校长院长系主任等,不过民主政治中国家之公仆而已。致教授则为学术权威,享有最高荣誉。”(79)虽然顾毓琇在到任前已做好充分尊重教授的心理准备,但任职刚满一年便挂冠而去,主要缘由恰是在于中大教授掀起强烈的反顾浪潮。
顾毓琇上任后,中大的人事变动很大,教务、训导、总务三长和各院院长大部分都有更动。(80)但学校内部的人事更动并没有使顾毓琇在中央大学内的行政工作如其所愿地顺利进行。从相关史料来看,顾毓琇在中大校长任内卷入了校内的派系之争,这使他疲于应付,最终也因此而辞职。顾由于清华学校的出身和长期在清华执教的经历,他在中大校内的“南高东大派”眼中被视为“北大清华派”。而此时校内的情形是“校友派(即南高东大派——引者注)与清华派势不两立”,此时“中大内情不稳,顾(毓琇)虽多方拉拢,恐将无能为力”。(81)
比起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罗家伦,以及“党国要人”顾孟余和蒋介石,顾毓琇仅以教育部次长的政治身份接任中央大学校长,其所能承载的政治象征实在有限。从学术地位来讲,当时的顾毓琇影响力亦不大。至少在时人眼中,当时顾氏学术地位平平,与他的继任者吴有训相比有很大的差距。(82)因此可以说,中大师生从一开始就对顾产生了政治和学术资历的双重排斥。
1945年6月9日,中央大学沙学浚、戈定邦和潘菽等8名教授于中央大学三十周年校庆时在《大公报》发表长篇感言,其中关于大学校长,他们指出:“大学以研究学术为中心任务,而大学行政是为促进学术研究而存在的,但官僚作风的大学行政把校长私人利益视为最重要,学术研究自然受阻碍。”而且他们还建议,“校长由教授会选出,由政府任命,做道德文章领袖群伦的师表”。(83)不难看出,在本校校庆之际,中央大学八教授在报章上畅论校长问题,其锋芒显然指向本校校长顾毓琇。紧接着,6月13日中大召开的教授会议又对校务“大施抨击”。16日,顾毓琇在学校行政会议上通报,其已向教育部递交辞呈。(84)
此后校内的情形对顾毓琇来说更为严峻。据《新华日报》报导,1945年7月19日中大教授二百余人召开紧急会议,矛头直指顾毓琇,大部分教授认为其滥用职权,无理解聘教授,还指责顾出任校长后学校校务极其混乱。尤其是顾毓琇所办两桩聘用教授的事直接触动了与会者的神经。首先是顾毓琇聘用清华同学梁实秋为中大文学院院长“不符程序”,最后顾毓琇“承认错误并书面道歉”。其次,顾毓琇聘用经济系兼任教授吴干为该系主任也不符合规定。在会上,刘世超教授说:“听说中大有清华派,中大派,互相排挤,实不应该,教授聘用应当以学问道德为标准,不能以朋友、同学、亲戚等等关系来决定”。(85)
刘世超等人的发言锋芒直指教授聘用问题,除了事实上已点明学校内部两大派系的存在之外,言下之意是指责校长顾毓琇在聘人过程中有偏私,再结合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梁实秋聘任事件”,他们实际不满的无疑就是顾校长偏袒“清华派”。
关于这次中央大学教授会议的原委和过程还有另一个叙述版本。这次中央大学内“大规模”的教授集会引起了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别关注,特将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调查报告提供给了教育部:
中大南高系教授集会企图驱逐顾毓琇
据报:中央大学教授中,素有南高与清华两派系,现任校长顾毓琇为清华系统,故自到任以来,南高系教授则尽其排挤外派之能事,极力对顾加以攻击。最近顾毓琇拟聘梁实秋为文学院院长(现为该校教授、顾之同学),并聘吴干为经济系系主任(现为该系兼任教授,亦为顾之同学),而南高系之主要份子,如理学院院长孙光远与体育系系主任江良规等即随时举行秘密集会对顾多方阻挠。本月十九日并联合南高系教授开会,假教授会名义,决议排斥顾毓琇氏及对聘辞教授均应通过教授会等案,并拟向教部提出要求等等。(86)
以上两种叙述虽角度不同,但均直接道出了中大内部的教授派系矛盾和顾毓琇所处之尴尬境地。顾毓琇终于在教授的“倒顾”浪潮中隐退,1945年8月4日,国民政府批准顾毓琇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87)
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夜,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为中央大学校长。(88)任命吴有训为中大校长,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行政当局欲利用知名学者调和校内两派的矛盾。(89)吴有训到任后也确实给中央大学带来了新的风气,在师生两方面中均有很好的印象,深得拥护。(90)吴有训以纯学者的身份执掌“最高学府”,并无太多的政治资源作为依托,也缺少其前任们的“中央”背景,在中央大学的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校长人选的潜规则。但在战后复杂的政局环境之中,吴有训遇到了比他的前任们更为复杂胶着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两年后吴有训也选择主动告别中央大学。
从罗家伦到吴有训,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共更换了五任校长。这四次“易长”的过程中纠缠了许多政治和学术因素。在中大这所与“党国”关系最为密切的高校中,校长人选的确定显然是党国核心层选择的结果,但校长的去留也与校内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后者有时甚至更具关键性作用。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一些认知中,校长的政治身份往往会导致学校教育发展的政治化倾向。考察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易长”问题这一个案,可以发现,中大校长人选的择取无疑体现了“党国”的意志,深深地烙上了政治干预学术的印记。不过,从罗家伦的继任者顾孟余到顾毓琇,不仅他们的任期均只有一年有余,而且由校长所体现出的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党国要员”顾孟余因其“无为”的行事作风和在党内的弱势地位,形成了师生共同认可的象征性“中央化”和实质性“学术自由”的悖论性互动,这恐怕与人们印象中“党人”长校必然会导致学校“党化”的印象有一定差距。而蒋介石任中大校长期间,比起他的前任,他代表的“中央”在中大校园内“在场”(present)的实际政治效能并没有得到空前的强化。校长(特别是处理校政的教育长)在学校权力结构中的实际地位降低,而学校内部某一派系的教授群体则掌握了中大的行政主导权。而这种派系性的“教授治校”现象恐怕与近代以来中国教育文化接受的西方式“大学民主”的理想范型有很大的出入。
从“党国”层面来讲,战时政治权力对教育文化的渗透逐步加强。不过,“学术”一方的话语权应全面考量,而不是仅关注于知识界和大学如何拒斥政治力量。至少可以说,中央大学的师生们普遍希望能够同时拥有政治象征上的“中央化”和实际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从而收“最高学府”的名实双至之效。
注释:
①例如苏云峰:《清华校长人选和继承风波(一九一八~一九三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22期下,1993年6月;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此外,许小青对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去职风潮亦有详细的论述。见氏著《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②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0,pp.119-121.
③萧胜文:《罗家伦与中央大学发展之研究(1932-1941)》,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9年,第195页。
④罗家伦:《上总裁书——简陈七年来在中大经过请派员彻查事实以明真相并另简贤能接替》,1939年2月1日,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157-160页。
⑤刘维开编著《罗家伦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6年版,第155-157页。
⑥罗家伦:《上总裁书——简陈七年来在中大经过请派员彻查事实以明真相并另简贤能接替》,1939年2月1日,《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157页。
⑦参见胡国台:《抗战时期教育经费与高等教育品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9期,1990年6月。
⑧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0年11月13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影印本,第378页。
⑨罗家伦:《上总裁书 恳辞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169页。
⑩罗家伦:《致陈立夫函(一)》,1941年6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3页。按《文存》补编收入该函时未注明年代,萧胜文在其论文中使用了该函的草稿原件(由罗家伦之女罗久芳提供),日期为1941年。
(11)《胡思明等呈教育部》,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56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当时任教于中大史学系的郭廷以就明确表示:“中大同事出身本校的和清华的本有界限”,而且“南高派”一直认为校长罗家伦偏袒“清华派”。(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210页)
(13)详见萧胜文:《罗家伦与中央大学发展之研究(1932-1941)》,第187-189页。
(14)以1938年为例,中央大学专任教授的月薪一般为340-380元,专任讲师的月薪一般为180-240元,文科助教月薪一般在90-140元,而理、工学院的助教只在60-80元。参见《教员一览(二十七年度)》,缩微胶卷,国立中央大学档案648-7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下文引用“国立中央大学档案”时简称“中大档”。
(15)金易:《抗战中的中央大学》,王觉源编《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版,第46页。
(16)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208页。
(17)白瑜:《怀念从政学人朱家骅与王世杰》,《传记文学》(台北)第40卷第1期,1982年1月。
(18)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关于国民党内CC派系的最新研究,亦参见同书第223-242页。
(19)详见罗家伦:《朱骝先先生的事迹和行谊》,《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0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9年版,第170-172页。
(20)据萧胜文的研究显示,中央大学与陈立夫执掌的教育部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而且抗战期间CC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扩充势力也与罗家伦和中大校方产生了很多纠葛。本文不赘。详见萧胜文:《罗家伦与中央大学发展之研究(1932-1941)》,第201-204页。
(21)罗家伦:《致萧自诚函》,1941年6月27日,《罗家伦先生文存》补编,第326页。该函未标明年代,只署月日。据函中内容来看,应为1941年。罗家伦在函中最后称:“今幸告一段落,问心差可上对领袖,下对青年悠悠之口,任之可耳”,应在罗辞去中大校长之时。
(22)金毓黻:《致罗校长志希书》,《静晤室日记》第6册,1940年2月29日,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485-4489页。
(23)《校务会议记录》,1940年3月2日,中大档648-921。
(24)《国立中央大学呈教育部(发文字第603号)》,1940年4月24日,中大档648-909。
(25)《教育部指令(高字第17556号)》,1940年9月6日,中大档648-909。
(26)刘维开编著《罗家伦先生年谱》,第170页。
(27)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民国三十年七月在国立中央大学全体师生初次惜别会中讲》,《罗家伦先生文存》第6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96页。
(28)柳无忌:《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续)》,1941年9月28日《大公报》(重庆),第1张第3版。
(29)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1941年4月14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30)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1941年6月20日,第98页。
(31)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顾孟余自港来渝。蒋先生告我欲其留渝,藉以影响外间对汪之观感。”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39年12月8日,第195页。
(32)傅斯年:《致胡适》,1940年8月14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33)罗家伦:《陈立夫致罗家伦函》,1941年7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附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6年版,第253页。
(34)罗家伦:《致陈立夫函(二)》,1941年7月20日,《罗家伦先生文存》补编,第303页。
(35)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1941年7月16日,第112页。
(36)《顾校长莅校接事》,《中大周刊》第14期,1941年8月24日,第2版。
(37)《顾校长招待各教授,教授会欢迎顾校长》,《中大周刊》第15期,1941年9月14日,第2版。
(38)《论学术自由空气》,《中大周刊》第15期,1941年9月14日,第2版。
(39)黄淬伯先生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此承《黄淬伯先生日记》整理校注者陆远先生提供,并惠允使用,谨致谢忱!该日记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40)柳无忌:《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传记文学》(台北)第32卷第3期,1978年3月。
(41)歌:《从顾孟余校长到吴有训校长》,《中大新闻》1947年7月16日,第3版。
(42)《国立中央大学三十一年度临时经费说明书》,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528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3)《吴世瑞呈》,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528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文件未署年份,由文中“新任校长顾孟余”之语推测,应为1941年。
(44)吴干:《大节无亏恂恂儒者的孟余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9卷第1期,1976年7月。
(45)《中大易长之反应(1943年2月18日)》,《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46)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208-209页。
(47)王作荣:《沙坪之恋(续完)》,《中外杂志》(台北)第19卷第3期,1976年2月。
(48)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209页。
(49)鲁传鼎口述,鲁赵淑敏执笔《三十年前中大学生——沙坪坝上的三抢与站岗》,《中外杂志》(台北)第5卷第15期,1968年5月。
(50)陶怀仲:《沙坪三载见沧桑》,《中外杂志》(台北)第16卷第4期,1974年10月。
(51)中大经济系教授吴道坤称顾孟余在其当政期间采用的是校友派(南高、东大、中大)与非校友派(清华、北大)的平衡政策(Balance policy)。参见《吴道坤致朱家骅函》,1945年6月16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49,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52)《沙磁点滴》,《新华日报》1943年1月4日,第3版。
(53)《蒋委员长兼长中大,国府昨日明令发表》,《大公报》(重庆)1943年2月20日,第1张第3版。
(54)《中大易长之反应(1943年2月18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第436页。
(55)顾颉刚在日记中称:“陈立夫蓄意统制教育界,……所未入侵者,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而已。中大有四千学生、四百教员、七院六十二系,而孟余先生不肯投降,彼遂以经济封锁政策相胁迫”。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1月5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页。
(56)《中大区党部呈组织部(鸿字第十二号)》,1943年2月22日,中大档648(4)-11。
(57)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07-308页。
(58)楚崧秋:《蒋总统兼长中大回忆——为中央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作》,《中外杂志》(台北)第18卷第1期,1975年7月。
(59)《中大易长之反应(1943年2月18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第435页。
(60)《中大区党部呈组织部(鸿字第十二号)》,1943年2月22日,中大档648(4)-11。
(61)《教育部呈行政院(高壹60-5)》,1943年2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25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2)《陈立夫致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函》,1943年2月20日,行政院档案014000005626A,台北“国史馆”藏。
(63)《要闻简报》,《新华日报》(重庆)1943年3月8日,第2版。陈立夫称在中央大学设教育长是他想的一个“办法”,也是他派朱经农去担任中大教育长的。参见氏著《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308页。
(64)《委员长召见中大主脑人员责成各员继续努力》,《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重庆)1943年2月25日,第5版。
(65)《蒋兼校长昨赴中大训话》,《大公报》(重庆)1943年3月8日,第1张第2版。
(66)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209页。
(67)1943年2月11日,蒋介石曾访即将离任中大校长的顾孟余,是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普通大学非实施军事训练不可至”。参见《事略稿本》,1943年2月1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档号060100第173卷编号06—00780,台北“国史馆”藏。
(68)《沙坪坝上》,《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4日,第1张第3版;《沙坪坝上》,《大公报》(重庆)1943年10月8日,第1张第3版;《沙坪坝上》,《大公报》(重庆)1944年8月30日,第1张第3版。
(69)《事略稿本》,1944年7月1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档号060100第190卷,编号06—00855,台北“国史馆”藏。
(70)《事略稿本》,1943年3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档号060100第174卷,编号06—00784,台北“国史馆”藏。
(71)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209页;《学校简讯》,《学生之友》第7卷第5、6合期,1944年2月15日;《学校简讯》,《学生之友》第8卷第4期,1944年6月15日。
(72)《沙坪点滴》,《大公报》(重庆)1943年3月21日,第1张第3版。
(73)《事略稿本》,1943年3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60100第174卷,编号06—00784,蒋中正总统档案。
(74)《吴道坤致朱家骅函》,1945年4月2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49,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75)《胡焕庸致朱家骅函》,1943年3月10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49,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76)丁骕:《松林坡风月录(上)——也是大学传奇》,《中外杂志》(台北)第42卷第2期,1988年8月。
(77)《军委会办公厅函(国壹第22号第49185号)》,1944年8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56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8)《学校近讯》,《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第17、18合期,1944年9月1日。
(79)《顾校长发表教育方针》,《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第17、18合期,1944年9月1日。
(80)《中大小事》,《新华日报》1944年10月13日,第3版。
(81)《吴道坤密函朱家骅》,1944年12月24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49,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82)“萧承龄先生采访记录”,南京秦淮区,2007年1月2日。
(83)沙学浚、戈定邦等:《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中央大学三十周年校庆感言》,《大公报》(重庆)1945年6月9日,第1张第3版。
(84)《吴道坤致朱家骅函》,1945年6月16日;《丁骕致朱家骅函(并附呈)》,1945年6月18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49,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85)《中大教授开紧急会议》,《新华日报》1945年7月22日,第3版。
(86)《中统调查函(国壹第22号第44510号)》,1945年7月3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56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7)《国民政府令 准顾毓琇辞职》,《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第449页。
(88)《新任中大校长吴有训氏定期接事正在昆明候机来渝》,《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23日,第3版。
(89)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213页。据郭廷以回忆,“朱家骅部长(时任教育部长——引者注)听傅斯年的话,请本校出身而又供职外校的人担任校长,最后找到了吴有训当校长,吴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名气大,教育部为了要调他来中大还特地作文章介绍他。中大教授出身本校的最多,清华出身者其次,吴两方面都可以沟通,调他来应该是很合适的”。
(90)中央大学教授会称:“近年以来中大校长屡经更迭,校务上困阻殊多。去秋吴正之先生奉命主持校政,备受全校师生之爱护,校务遂得渐入正轨,力图安定以求进步。”(《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致朱家骅函》,1946年11月19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50,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