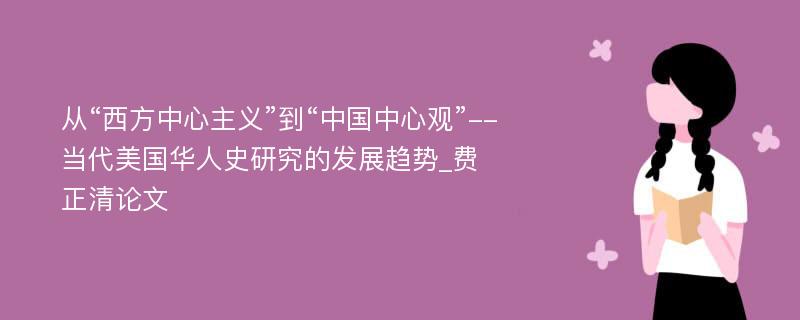
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心论文,美国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反思与批判精神。本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在主要针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以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而开展的批判运动中,美国的中国史学者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跨步,从而实现了美国中国史研究中一次质的飞跃。当前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又在70年代业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为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具有现代的形态而在不断地努力。
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国外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美国中国史学者在广泛吸取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因此我国史学工作者关心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现状是十分自然的。我们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什么是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主流和发展趋势。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一直以明清以来的历史为主,这就决定了我们论述的重点。
(1)费正清与利文森时代的中国史研究
美国史学界一般认为费正清为中国史研究中“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利文森为“传统-近代”模式的一代宗师。这两个学派在50、6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学派。
费正清高度评价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并认为“中国的悠久历史可能代表了有组织人类历史的四分之一”,然而中国文化又是“伟大历史文化中最杰出而又最隔绝的文化”①。根本原因是“钦定的儒家思想的宏伟构思把道德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并且把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融为一体”,由此形成了同心园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中央政权高居地方官僚统治之巅。在基层,靠宗族关系和绅士集团的忠诚来维系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这种忠诚是儒家学说的产物,因此,费正清认为“只有通过儒家学说,才能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②。
儒家学说维护着帝国的秩序,帝国的权力又“包容和利用了文化”。于是国家、社会和文化这三者结为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和平和秩序支持着王朝的统治,但也使中国社会陷于一种长期停滞的状态。
文化传统是抗拒变革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构筑的政治体制非但不能完成社会形态的自我更新,相反地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革命变革有痉孪性,有时在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③。
那么什么力量才能打碎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从而推动中国迈步近代社会呢?那就是“西方的冲击”。根据费正清的观点,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就是西方对中国社会的不断冲击以及中国社会对这些“冲击”所做出的“反应”。这就是“冲击-反应”模式的主要内容。费正清与邓嗣禹发表于1954年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就是用这种模式对中国19世纪的历史作了典型的描述:在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与居于统治地位并处于工业革命推动之下的西方国家的接触中,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诸方面,西方文明“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她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④。
费正清这种用“冲击-反应”的模式来研究和解释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变化历程的方法在美国的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当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执教,所以他和他的追随者被称作“哈佛学派”。
与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遥遥相对的,是以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为核心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形成的另一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利文森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名著《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和《儒教的中国及其近代的命运》(Confucia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I,1958;Vol.,Ⅱ,1964;Vol.,Ⅲ,1968)使他在美国史学界名声大噪。利文森的史学思想既可追溯到“哈佛学派”的渊源,又有他自己的新发展,使他成为“传统-近代”模式的代表人物。
利文森对中国思想史有着精细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对儒家学说的系统观点。他所以用“传统”与“近代”这两个词来区分中国漫长的历史年代,是因为他认为19世纪西方文明影响中国之前与其后,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时代。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19世纪初,以儒家学说为准则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使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和谐、平衡的停滞状态。儒家的人文主义只能造成一种固定的、静态的世界秩序,与为科学理性所支配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根本性的变化不可能从中国社会结构自身中产生,只能源于外界的刺激。所以儒家思想只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利文森的一句名言即是,儒家思想“只有归途而无出路”⑤。
利文森对中国古代文明有种极深的仰慕之情。所以他为中国的衰落感到惋惜。然而中国并非没有前途。利文森认为西方文明在改变中国历史方向上可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西方文明促成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另方面,西方文明又为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楷模。总之,在利文森提出的“传统-近代”模式中,“传统”与“近代”两者之间是绝对对立的。中国要想由传统社会跨步到近代社会,那么只有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
用“冲击-反应”模式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与用“传统-近代”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的美国专家在研究的侧重点上有所区别。前者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制度、本土叛乱、省一级的发展以及中央政府和省一级的统治人物(诸如总督、巡抚和军阀等),并引导人们研究中国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反应。后者侧重研究中国的思想史,即“内在的”世界。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在怎样看待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以及中国人对这类变化的反思。然而两者又有诸多的共同特征:
首先,他们都没有摆脱19世纪业已形成的以“西方中心论”为出发点的中国观的影响,判定中国是个“停滞”社会,只有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改造中国,才能使中国实现近代化。
其次,用“冲击-反应”及“传统-近代”模式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都把“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差异”视作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冲突的根源。所以研究的视角也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上,因而对中国广泛时空内所发生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深刻变化注意不够,这也就是用上述两类模式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视中国为“停滞”社会的重要原因。
其三,无论费正清或者利文森,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区分什么是“停滞”社会与富有生命活力的社会,以及什么是“传统”与“近代”等方面,他们采用的都是西方的尺度,他们都把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当作整个人类的必然发展之途,即西方人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了。这种忽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片面性并带有明显的目的论的倾向。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冲击-反应”模式与“传统-近代”模式虽然各有研究的侧重点,但其基本的历史思维却又是近似的,即,“带有明显的19世纪烙印,而且集中体现了整整一代美国史学家中狭隘主义思想的核心”⑥。
用“冲击-反应”和“传统-近代”模式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所以在50、60年代盛极一时,是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的。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在部分美国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优越感空前膨胀,他们不时想到“白人的责任”。中国革命的成功,无疑地成为美国政府必须正视的新问题。如何使中国重新纳入西方世界的轨道,成为美国统治阶层对华决策的基础。而“冲击-反应”与“传统-近代”模式在客观上恰恰迎合了美国决策者对华战略思想的需要。因此,在60年代末在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象富有批判精神的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已尖锐指出,费正清和利文森等倡导的“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⑦。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以“西方中心论”为出发点构筑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具有一种现代的形态已成为美国中国史学者的普遍要求。
(2)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观”跨步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无论美国国内或是在国际上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导致了世界性的殖民体制的瓦解。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普遍关注。而且越是深入研究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前的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人们越发现每个社会在时空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那种视人类历史进程是有目的、有方向、有目标的思想被认为具有深厚的西方色彩,从而受到怀疑。于是,一些学者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探索前资本主义时代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把研究的重点从集中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上转到研究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上。美国国内的社会震荡也十分有利于上述学术思潮的发展。越南战争的失败、伊朗人质事件,民权运动以及水门事件等等,使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及西方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发生了动摇。年轻一代的美国中国史学者开始反思:能否界定唯有欧洲和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才是理性化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只是接受上述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念影响和改造的“客体”。因此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已成为美国中国史学者所追求的直接目标。美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史学者已开始抛弃他们前辈所持的种族优越感和心理状态,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即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历史首先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规定,所以应当从中国社会内部来寻找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和诸相关因素。这种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趋势就是人们所常说的“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中心取向”⑧。我们认为美国的中国史学者逐步抛弃“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框架,开始用“中国中心观”来研究中国历史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7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以“中国中心观”研究中国历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并集中反应在下面四个论文集中,即约翰·海格尔主编的《中国宋代的危机与繁荣》(John W.Haeger,ed,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1975);魏斐德与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Frederic E.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d,ed,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lmperial China,1975);史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lmperial China,1977)和乔纳森·斯彭斯和约翰·威尔斯合编的《从明到清》(Jonathan D.Spence and John Wills,ed.From Ming to Ching,1979)。
通过上面四个论文集,我们可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中国中心观”为出发点的史学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研究中国历史,他们缩小了研究单位,开始从事地方史的“个案”研究。在地方史的研究中,他们的重点又放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上。⑨由于这些学者已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且采取了动态与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他们看到了与他们前辈学者根本不同的社会图景。在他们的笔下,“给明末到民初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幅充满运动与变化的画面。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的西方进行干预并注入新的生命的这种陈词滥调,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再也不必为他人赐予历史而感恩戴德,它完全可以独立创造自己的历史”⑩。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这种新认识事实上是对中国社会“停滞”论的一种批判。在当代,欧美学者尽管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特点及规律的认识上观点并不一致,但用“停滞”论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的的确确已十分罕见了。
其二,当代美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除十分注重经济与社会因素的作用外,又开始致力于中国社会内部逐步形成的诸多长期发展进程的研究。魏斐德在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概括了美国学者这方面的新见解:“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联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再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他们发现有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垮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这一切在晚明出现的现象又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清朝继续发展,在某些方面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史中才臻于成熟”(11)。《从明到清》一书的前言,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按照传统的史学思想,根据朝代的变化,整个17世纪被分作“明”和“前清”两个阶段,结果造成了一种无法逾越的概念上的障碍。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重视制度的结构胜于长期发展趋势;关注帝国官僚机构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而轻视造成这种紧迫问题的社会环境。然而如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明清时代的历史,那么应当把17世纪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明清两代的内在联系所具有的重要性超过了王朝嬗变本身的重要性,即,王朝虽已转换,然而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趋势并没中断。通过“长时段”的研究发现明清两代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使许多习惯于用王朝划分中国历史的学者感到十分惊讶并被视为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12)。
对中国社会内部长期发展进程的研究导致美国中国史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始于何时的讨论。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海格尔提出的中国近代的开端孕育于8、9、10这三个世纪,即所谓的“唐——宋过渡时期”(13);二是,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前言中提出的,中国近代始于16世纪中叶;最后一种观点,是约瑟夫·弗来彻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二章中提出来的:中国近代肇始于18世纪(15)。当然对于上述观点我国学者自有不同的看法。吴承明先生曾含蓄地指出:“国外有人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提前到18世纪以至16世纪,也许失之偏急”(16)。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长期发展进程或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这一理论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在按着自己的方向和规律向前发展着,尽管王朝在变换,但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却不曾中断。中国历史的内在连续性的揭示,使在西方沿袭已久的所谓中国历史“循环”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为寻找对中国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的长期变化模式开辟了道路。
其三,费正清曾指出:“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来成为风气,今天依然如此”(17)。然而70年代以后,以史坚雅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在中国区域史的研究中,一方面揭示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都是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另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在自然史与经济史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宏观区域系统理论。由于这一理论在美国学术界具有趋向性影响(18),所以我们做一重点论述:
史坚雅认为直到19世纪帝国晚期,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全国性城市系统,而是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和云贵共9个宏观区域。从地缘上来看,重要的河流与盆地的地理特征明显反映在每个宏观区域系统上。在区域系统内部,凡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和人口集中的地方便形成中心地区。从中心地区到边缘地区,交通、资源和人口等条件呈递减的趋势。当中心地区经济发展、人口渐趋饱和状态,人口、资金和技术开始向边缘地区转移,于是边缘地区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甚至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中心地区。但当自然条件的变异以及疫病的肆虐,造成区域系统经济衰退之时,受其冲击最大的又首先是边缘地区: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接着在宏观区域内部的调整时期,经济上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这也可以说是这一区域经济再次“起飞”的准备或孕育时期。但宏观区域经济的兴衰周期,往往是相当漫长的,而且这种区域周期性变化在中心地区的中心城市的兴衰上得到集中的体现。象在华北区域,从8到13世纪就经历了典型的周期性变化。在经济起飞阶段,以开封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系统开始形成,区域市场繁盛,人口激增(从2千万增至3千3百万)。到区域经济衰退时期(蒙古人南下是重要因素),开封市场瓦解,区域城市几乎绝迹,到经济衰退的谷底时期,人口已下降至1千1百万。中心城市开封人口仅及9千人。在其后,以扬州、杭州和苏州为中心的宏观区域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周期性变化(19)。由于各个宏观区域自然条件各异,因此内部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人口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张力”亦不同,从而显示出各宏观区域不同的发展速率,就此形成了中国广大腹地内部不同宏观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史坚雅宏观区域理论非常强调城市的发展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城市发展中,如上所述,他又对中心城市的作用赋予极大的重视。中心城市一般座落在人口与资源得天独厚的地方,以这样的中心城市为中轴发展起来的城市系统与宏观区域的形成及该宏观区域的持征密切相关。根据中心城市的作用方式,史坚雅把中国宏观区域的形成分作两大类:一类是中心城市将它的能量不断向四周扩散直到这一宏观区域的边缘地带。即这种宏观区域是由中心城市辐射而构成的。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域以及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区域都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类,由若干个地区性的自主的经济区聚合成一个宏观区域。而每个自主的经济区又有自己的中心城市。象长江中游区域、东南沿海区域以及云贵区域都属于这一类型(20)。
无论是辐射类型的或是聚合类型的宏观区域,内部都有一个由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直至农村构成的等级空间体系。在这里史坚雅并不把城市当作离散的、孤立的单位来讨论,而是把城市与农村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他的宏观区域理论中,小农的自给自足的“天地”并不是农村,而是基层市场共同体。这里即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向城市流动的起点,也是农村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向下流动的终点,所以小农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活动空间在基层的集市乃至整个宏观区域之中。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所以宏观区域在王朝兴盛时期,社会、经济、政治都处于发展阶段,农村则呈现一种“开放”的态势;当宏观区域由于王朝的衰落,社会、经济、政治都陷入衰退状况,农村则呈现一种“闭锁”的态势。也就是说,农村也随着整个宏观区域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经历着周期性的变化。(21)。
史坚雅宏观区域理论是基于中国广大腹地内部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根本性认识才提出来的。然而中国9个宏观区域之间不仅存在着差异,事实证明,各宏观区域之间又有着联系。这种宏观区域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各宏观区域的城市系统之间的联系体现的。但各宏观区域的城市系统并不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形成的。黄河西部冲积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城市系统历经500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到汉代才形成。华北的城市系统到唐和北宋才建立起来。长江下游城市系统到南宋时才具规模。而其他宏观区域的城市系统直至明清时代才逐步发展成熟。即,各宏观区域的城市系统之间并不存在着共时性。再加上前机械运输时代各宏观区域之间的交往十分困难,因此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并没能形成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全国性的城市系统(22)。然而,发生在中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却在全国性城市系统的形成以及赋予中国城市以近代的意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世纪城市革命”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即城市已不再单纯是政治、军事和行政的中心。官方的市场组织日益衰落;坊市制被取消;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小城市不断衍生,新兴城市的建设格局开始偏离传统的建城宇宙观;税收和贸易货币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商人数量不断增加、财富激增,权力随之扩大,而社会和政府对商人的态度已有所软化;为出口进行的商品生产和宏观区域之间的贸易更成为“中世纪城市革命”的重要内容。上述所有这些变化说明,随着区域城市系统的逐步形成以及各区域城市系统之间联系的加强,中国经济已开始出现朝着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方向上发展的趋势(23)。
史坚雅有关中国宏观区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内部不仅各宏观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即使是在一个宏观区域的内部,其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差异。这种观点与因袭已久的把中国视作一个静态的、均衡的“整体”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次,史坚雅认为中国王朝的兴衰固然对各个宏观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各宏观区域又有自己的周期性变化。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与西方学者习用的以中国王朝的更迭作为判断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依据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其三,史坚雅的理论表述了他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发展脉络以及对中国城市的特征的观点。多年来,马克斯·韦伯依据西方文献和西方城市的发展规律,得出“中国无城市”的结论。此点在西方史学界影响颇深。史坚雅有关中国城市体系以及城乡统一连续体的研究,正如史坚雅自己所说,事实上嘲弄了以往社会科学文献中所表述的那种简单的想像(24)。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70年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最大的收获主要表现为:一、对中国社会充满动态的变化全景的重新认识;二,对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按一定方向发展的长期趋势的发现;三,对于中国广阔空间内存在着差异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的揭示。
(3)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是在70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继续稳步前进。近15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主要著述,我们已列表附于文后,供我国学者参考。笔者个人认为就学术价值而言,应该说那些研究中国地方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著作最值得注意。而且这两者又常常相互结合,使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此外,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区域性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一般都突破了王朝的界线,而以较长的时段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又由于很多著者都曾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广泛地收集了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所以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者的著述较之70年代的那些研究成果,显得更成熟、更深刻、也更具有力度。然而在史学理论上,并无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那种重大树建。80年代以来的著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对70年代中国史研究中已经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论证。至于70年代美国中国史研究中那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在8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并无有效的克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无论在“横向”或“纵向”的“个案”研究中,美国学者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然而对研究的课题也有越分越细的倾向。这自然使人担忧,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今后会不会同样出现史学“碎化”的危险。“区分”(differentiation)不能代替“综合”(integration)。因为整体结构终究规定着各个部分的联系及其性质和意义。所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欲想取得更大的进展,提高中国史研究中的综合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从年鉴派的史学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成分,但年鉴派史学思想中的缺憾处,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同样有所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内部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而轻视政治事件的历史作用。如果说在70年代的美国中国史研究中能打破王朝的界线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从而为突破中国历史“循环”论找到了正确方向,这表明为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那么,反之,如果过份轻视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制约力,那么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同样会出现片面性。三,美国学者在关于中国宏观区域理论的研究中认识到中国广大腹地内部存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各宏观区域和宏观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无论在空间上或时间上也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比之于把中国视作一个停滞的、凝固的“整体”的观点,无疑地是个重大的进展。但上述理论并没能回答各宏观区域之间既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中国历时几千年仍能保持国家的统一。也就是说,对于各宏观区域之间所存在着的内部同一性,尚缺乏深入的探索。此外,宏观区域理论揭示出各宏观区域内部所存在着的周期性变化,但却没能回答更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各宏观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周期性的变化,以及什么因素制约着这些周期性变化。对因果关系的忽视是年鉴派史学思想中的严重缺点,这一缺点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不容轻看。
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自然是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们所普遍关注的。柯文于1984年写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一方面是为了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这一转变历程做出总结;另方面,就是他已经意识到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弱点并希望通过他的这部总结之著,推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能更上一层楼,即,“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25)。
如果说柯文通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在史学思想与方法论方面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建议,那么魏斐德则通过他的《伟大的事业:满洲在17世纪的中国重建帝国秩序》(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l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1985)一书,在如何提高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水平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该书是魏斐德历时15年才完成的一部呕心沥血之著,全书分上下两卷,共1337页。
《伟大的事业》是部叙事史。在书中,魏斐德不仅对明清王朝更迭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而且对这一历史巨变的原因也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以及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诸多方面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该书突出的特点有三方面:一,将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总危机概念引进到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并通过贵金属运动及“路易十四小冰河期”这两个因素对全球的影响,把中国置于统一的、处于激变的世界背景中,来研究和探索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26)。二,把16世纪中叶以来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渐形成的长期发展进程与明清嬗变的历史事件结合到一起,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待明清政权的更迭:王朝有兴有衰,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进程以及中国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并不因此而中断。三,《伟大的事业》一书对明清更迭这段历史并不单纯看成是民族之争或王朝之战,它更强调的是,这是一次以儒家“天下观”和政治理想为出发点,以满汉政治家联盟为核心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运动。就其精神实质来看,它体现的不是北宋那种动态的理想主义,而是南宋那种谨慎的保守主义精神。这一政治改革运动成功地结束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在17世纪的中国重建了帝国秩序,使中国社会内部逐步形成的长期发展进程再度获得活力,同时也使中国较之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地摆脱了17世纪总危机的影响(27),从而保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然而儒家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调控手段是有历史时限性的。当清初,规模令人畏惧的帝国大厦建成之时,社会危机已经潜伏着了。到18世纪中叶以后,帝国的权力虽然仍强而有力地集中着,但行政管理的边缘与权力中心的联系已经削弱,尤有甚者,整个统治系统已失去了前清时代的活力。当19世纪可怕的外部挑战不断出现,帝国解体时刻终于到来。
《伟大的事业》一书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结合,把中国社会内部形成的长期发展进程与急剧变化的历史事件相结合,并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分析了儒家政治学说为基础的专制政体的历史局限性,这些都代表着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新进展。所以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于1987年先后获得“利文森奖”和“伯克利奖”。美国著名学者周锡瑞称该书为一部“博学的巨著”,对中国17世纪危机做出了“具有挑战性的分析”(28)。由于魏斐德勤于笔耕,写出了包括《伟大的事业》在内的众多优秀史著,也由于他在教学和社会活动中的献身精神和组织工作的才能,1992年他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29)。
综上所述,可以说严肃的反思精神是推动美国中国史研究向现代形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美国中国史研究虽然仍以分解性质的“个案”研究为主,但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迎来综合研究的高潮。那时,在一些有关中国历史规律的重大问题上,很可能有所突破。切望我国伏案写作的史学界同仁,勿忘聆听那身后不断逼近的脚步声。
注释:
①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引自《现代史学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②(14)(16)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上卷第27页;第41页;第17页。
③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④⑥⑦⑩(11)(25)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第50页;第84页;第169页;第170页;第1页。
⑤利文森:《儒教的中国及其近代的命运》第一卷第xvi页。
⑧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对这一转变过程有着详尽的论述。该书是我们的主要参考文献。林同奇为该书写的“译者代序”也给我们许多启发。
⑨我们将有另文对此详加论述。
(12)斯彭斯与威尔斯主编:《从明到清》第xi、xvii页
(13)约翰·海格尔:《中国宋代的危机与繁荣》,第4页。
(15)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7)费正清:《中国:一部新历史》(John King Fairbank,China:A New Hisfory),1992年哈佛版,第436页。
(18)(19)(21)(22)(23)史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6-17页;第16页;第249页;第24页;第258页。
(20)有关中国农村与市场的联系问题可参阅史坚雅《中国农民和封闭的共同体;开放与闭合的个案》(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1971年版、第270-281页。
(24)“伟大的事业”实应译为“大业”、“大事”或“洪业”。系指清最初统治者以儒家的“天下观”为出发点,把实现其对全中国的统治,称为他们的“大业”、“大事”或“洪业”。如在天聪五年奴尔哈赤致明朝将士的“劝降书”中即写道:“苦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页四)。
(26)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总危机这一概念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于1954年率先提出的。主要是指地理大发现以后,由于美洲大量贵金属涌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从而导致工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全面衰退。与此同时,欧洲各国连年战争,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欧洲人口锐减,经济萧条。霍氏称17世纪欧洲的现实为一场总危机。魏斐德认为影响欧洲生态环境的“路易十四小冰河期”,也波及到中国,造成自然灾害频发。此外魏斐德还认为中国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洪流。中国的丝绸等产品换回大量白银,从而保证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价格革命”引起国际贸易的衰退,使中国白银入口量锐减,从而加重了明末的财政危机。这两个因素与明清嬗变有关。
(27)魏斐德就中国与主要欧洲国家摆脱17世纪总危机的年代做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走出17世纪总危机的低谷大约在1682或1683年。德国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开始从30年战争(1618-1648年)的创伤中复兴。至于法国和尼德兰迟至1690年代经济才出现转机;而西班牙和英国在1720-1730年代经济才开始回升。详见魏斐德:《伟大的事业》,第20页。
(28)详见周锡瑞《1992年美国历史协合代表大会》一文(Joseph W.Esherick,Gener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 ical Association1992年)。
(29)有鉴于魏斐德个人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优异成就和他在推进美中学术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已另写专文《美国学者魏斐德的中国史研究》,将在《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1期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