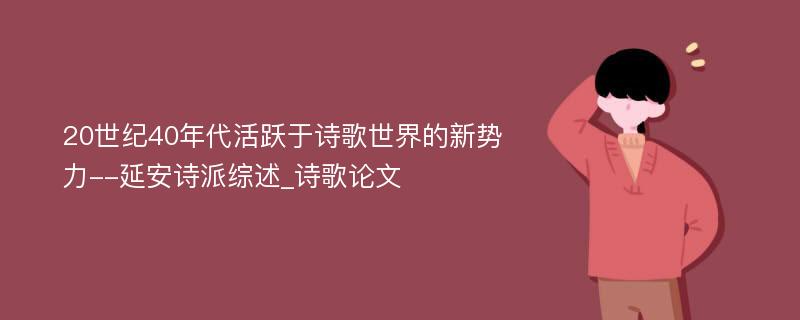
活跃于40年代诗坛的一支生力军——延安诗派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诗坛论文,一支论文,生力军论文,活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并没有把解放区诗歌群体当作诗歌流派看待,虽有人把“晋察冀诗人群”当作一个诗歌流派,但晋察冀诗人群也只是解放区诗歌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它分别出去,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应当说,解放区诗歌群体是一个具有很多内在一致性的整体,可以视为一个诗歌流派——延安诗派。把它视为一个诗歌流派,不但依据了当时的诗坛实际情况,而且从流派整体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利于把握解放区诗歌的总体面貌和本质特征。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出“延安诗派”之说,并为之正名。
一、以政治使命为纽带的诗歌群体
所谓延安诗派,并不是一个纯地域性的诗歌群体,而是一个诗歌流派。它包括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及由此不断向四面推进的解放区的诗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与工农密切结合的新型的诗歌群体。
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解放区的中心,是领导革命斗争的圣地,也是解放区诗歌的根据地,延安诗群的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诗歌队伍,并且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诗歌浪潮。延安诗歌运动的蓬勃开展,推动着整个解放区的诗歌运动的发展。因此可以说,解放区的诗歌运动是从延安起步的,并且一直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所以把解放区诗歌群体称为延安诗派是比较恰当的。
延安诗派是一个开放性的诗歌群体,大家在心灵上息息相通,都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责任感,几乎都是从战斗走向诗坛的。在诗歌目标的追求上基本一致,在美学观点上互相渗透,以及影响较大的代表诗人(如艾青、田间、柯仲平、钱丹辉、曼晴、陈辉、公木、严辰、何其芳、方冰、李季等)在艺术风格上的相似性,从而在解放区形成一条充满战斗力的生气勃勃的诗歌战线,演化出旗展鼓鸣的诗歌大合唱。因此有理由把延安诗群视为一个诗歌整体,一个诗歌流派或准流派。
延安诗派主要集中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太行山区等地,这些地区的诗歌队伍虽有流动,但相对比较稳定,解放区的诗歌运动也主要在这些地区开展得更火热一些。在这些地区,曾建立了延安诗歌总会、战歌社、山脉诗社、铁流社、战地社、晋察冀边区诗会、太行诗歌社、潮海诗歌社等诗歌团体,先后出版了《诗建设》、《新诗歌》、《山脉诗歌》、《诗战线》、《诗刊》、《街头诗》、《诗》、《太行诗歌》、《诗风》、《新世纪诗歌》、《边区诗歌》等油印或铅印的纯诗歌刊物。活跃于陕甘宁边区的诗人主要有:艾青、柯仲平、光未然、何其芳、萧三、严辰、鲁藜、严文井、公木、刘御、林山、吕剑、贺敬之、郭小川、朱子奇、李季、闻捷、戈壁舟、李冰等;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诗人主要有:田间、李雷、钱丹辉、曼晴、邵子南、方冰、史轮、魏巍、陈辉、林采、孙犁等;活跃于太行山区的诗人主要有:高鲁、叶枫、冈夫、袁勃、高咏、柯岗、阮章竞等。这些诗人大都工作在解放区各级党政、文化、教育、宣传部门,其中又以报刊编辑记者为最多,成绩最为突出,他们长期活跃在对敌斗争的前线,生活在乡村中,既熟悉具体的战地生活,又了解整个民族的以及国际上的反法西斯进程,既有丰富的生活感受和积累,又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还有活跃于八路军、解放军中的一批诗人,他们熟悉军队、熟悉战士,虽然很多人写诗是偶尔为之,但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活的熏陶,也有不少人的创作量大、质高,成为著名的诗人,如流笳、陈陇、雷烨、商展思、胡可、天蓝等。延安诗人当时的写诗热情是十分高昂的。魏巍后来回忆说:“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抒情诗、长诗、小叙事诗、街头诗,都是大量产生。尽管战争频繁,生活艰苦苦,有时连桌子、凳子都没有,肚子也不太饱,可是写诗的劲头倒足得很,简直是充满了诗的灵感,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使人精神振奋。”(注:魏巍:《晋察冀诗抄·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这可说道出了当时延安诗人的创作景况。他们“当时都有军事、行政、文化方面的本职工作,又在艰苦而快乐的本职工作中激发着诗的灵感,写下数不清的异彩纷呈的诗作,组成边区革命战争的气势磅礴的交响诗”(注:王剑青、冯健男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4-115、83页。),由此支撑起一个独特的光辉灿烂的诗歌空间。
延安诗人努力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自觉地服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明确为根据地人民而创作。他们个个既是战斗者,又是诗人,诗,是他们的生命,也是他们服务人民的工具。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魏巍回忆当时的创作心态时说:“愈是政治热情饱满的时期,也愈是生活美丽的时期,也就愈是诗的时期。”(注:魏巍:《黎明风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诗人既是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战士,那么诗人所创作的诗就应是战斗的武器,这种观念成为延安诗人诗歌美学思想的核心。正因为这样,延安诗人的创作,一般来说,政治意义是大于艺术意义的,或者说,在这短兵相接的时刻,诗人的创作并不是纯艺术的,而是同他的政治信念和政治选择联系在一起的,陈辉可说是延安诗人的典型代表。为了斗争的需要,他写过简短有力的“墙头诗”和“传单诗”,他把对敌人饱含仇恨的诗篇油印成传单,散发到与敌人厮杀着的战场上。其实,延安诗派的诗人都同陈辉一样,始终是以完成政治使命为目标的,他们的诗歌创作,始终是与革命武装斗争结合着的,与群众结合着的,与革命的政治任务结合着的,它是作为革命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延安诗人都心向革命,心向党,团结一致,朝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前进。诗人之间、社团之间,没有门户之见,相互关怀,相互支持,坦诚磋商诗艺,那真是一种可称之为战友的情谊。柯仲平有一首诗正表达了这一意向:“啊同志们!我们有/一致的方向,/一致的主张/我们的团结,/像五个指头,/共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每一个同志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个个同志的岗位都朝中央。”(《告同志》)这一批诗人大多是与解放区的新政权一起诞生、成长的,其诗歌的总体美学特征,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的。他们与现实和新政权处于协调一致的状态中,他们以一个战斗者、建设者、主人翁的态度主动参与生活,以新的世界观去面对世界,从而在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现实、诗人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关系。中国40年代的延安时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歌时代,活跃的诗坛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凭其强大的群体创作实力向社会塑造了一个无可争辩的“诗坛生力军”的光辉形象,并由此孕生了一大批影响当世乃至以后的杰出青年诗人。
二、诗的主旋律:英雄的诗与人民的诗
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诗魂和内在节奏,可以说是延安诗派的共同的、也是最为显著的流派特色。
当着祖国和人民正蒙受着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极大灾难和屈辱,当着一场生与死、荣与辱、铁与血的殊死大搏斗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与人民一道投入斗争,“把新的血的战争的现实写进诗里”。所以在开展于敌人后方的中国解放区诗歌中,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主题,这其中包括反对日本侵略者,宣传歌颂救亡图存,反对国内反动派的投降罪行,揭露、打击黑暗,以及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思考等。正如当时诗人魏巍所写的:“在这苦战的年代,你应把智慧也用于战争,/把战争也当成诗。”(《诗,游击去吧》)
延安诗歌的战争图景既是具象的,又是全景式的;既是纵向的,又是多方位的。诗人们从现实中观察、体验、咀嚼、提炼,灵动地浸润于历史长卷之中。诗人们描写敌人的凶顽、抗日勇士浴血奋战的诗篇,记载下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欠下的血债,更记载了讨还血债付出的昂贵代价。如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方冰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曼晴的《打灯笼的老人》、孙犁的《儿童团长》、商展思的《不准挂个“小”》、蔡其矫的《雁翎队》、魏巍的《蝈蝈,你喊起他们吧》、丹辉的《红羊角》、流笳的《哨》、袁勃的《不死的枪》、夏川的《血战苏付》、贾芝的《牺牲》、胡征的《我回来了》、侯唯动的《将军的马》、朱子奇的《民兵从前线回来了》、公木的《八路军进行曲》、冈夫的《敌人来了困死他》、田兵的《我们的女战士》、陈登科的《老虎不要再凶》、苗得雨的《我送哥哥上战场》、鲁琪的《英勇的爆炸手》等等,数不胜数,它们浮雕似地显现了战争的多侧面,绚丽夺目地反映了战争中的各种人物、各种情景,真可谓风起云蒸、摇荡性情、惊心动魄!
诗人们抒写的战争题材的诗歌,充分抒发了对祖国的爱与对敌人的恨,正如茅盾所指出的,“诗人们所咏叹者,是全民族的悲壮斗争,诗人们个人的情感已溶化于民族的伟大斗争情感之中。”(注:茅盾:《这时代的诗歌》,《救亡日报》1938年1月26日。)冈夫的《我喊叫》是抗战初期创作的一首有影响的力作,作品充满了对侵略者的愤怒,充满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昂扬着抗战必胜的信念。诗篇开头发出了悲愤的呐喊:“祖国!让我喊出/你的愤怒吧!/喊出你的苦!/沉重的苦痛/你的/风信旗似地飘扬的/战斗的光辉!/喊出啊/向全世界!/……/在全世界面前,/(啊,全世界!)/你高高地昂着/那不屈的头颅!”产生于这时期的延安诗歌,大都像这首诗一样,以磅礴之气唱出了高度的爱国之情,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针对日寇的侵略罪行,面对严酷的现实,季纯的街头诗《给我一支枪》作了坚决的回答:“给我一枝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椿,/那个能够再忍让!”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对正义和真理的严正呼唤,响彻在延安诗人的诗作中,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和鼓动性。
为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延安诗派的创作,理所当然要不断激励军民,同仇敌忾,藐视敌人;要描述正义战争的雄威,歌唱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方冰在《我亲眼看见》这首诗里,摄下了日寇惨无人道地烧死一个小小的孩子的镜头,并怒不可遏地呼喊:“我们要复仇!”在《过平阳镇》一诗的开头,诗人就用富于哲理性的诗句写道:“仇恨的血迹,/是很难消灭的;/它永远鲜红,/在复仇者的心里。”读着这样的诗句,人们无不感受到一种仇恨在汹涌,无不感受到一种复仇的战斗精神在燃烧。陈辉那最受人称道的《为祖国而歌》写战士要以血肉和生命来为祖国唱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即使牺牲了,“在埋着我的骨骼的黄土堆上,/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延安诗派那众多的街头诗、抒情诗、叙事诗,乃至千行长诗,哪一首不回响前人民战斗行动的足音,哪一首不是为了鼓起人民战斗的情绪呢?不但他们的诗歌为战斗、牺牲、胜利而歌唱,而且在血与火的搏斗中,他们中一些人也以血肉之躯殉了革命事业,殉了他们所热爱的诗。
除了写人民反抗日寇侵略,保家卫国的英勇斗争外,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土改运动以及解放区人民命运的变化和解放区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与富于诗意的生活情景,是延安诗派创作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它仍然与战争紧密相关。诗人长期生活在新生的土地和人民的战斗行列之中,生活本身所蕴含的浓烈诗意激发着诗人创作出一首首好诗。柯岗写于1940年的太行小景之一《采椒》、太行小景之二《月夜牧歌》,以色彩鲜明的笔触描绘着太行根据地人民当家做主后的劳动场面,热情地赞美根据地人民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风貌。诗中写道:“她们笑了/他们笑红了花椒//我在漳河岸上走/她们在花椒树下笑/她们一声笑/剪落了一串玛瑙”(《采椒》)。诗人善于从生活中捕捉那些富有浓烈诗意的生活场景,采取抒情与叙事相融合的手法把它生动地描绘出来。高咏的《麦收季》是一组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表现根据地军民满怀喜悦心情武装抢收小麦的欢快情景:“吹绿了山岗,/吹熟了农民的希望,/风,/吹着麦浪,/麦浪像夏天的漳河呀,/在悄悄地长。//洗清了磨刀石,/动员了一家老小,/拿了镰刀的月牙儿,/收一年的欢笑。”延安诗坛大量的诗作是歌唱解放区和根据地人民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的,从中可以照见那个大时代风华正茂的身影:在那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人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解放的喜悦心情,人民表现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新生活的巨大热情。
延安诗派的作品,都是植根在解放区和根据地人民战争的沃土上的奇葩,是延安诗人在“刀枪并举”的特殊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诗章。正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编》的“后记”所言,“这种新诗歌具有时代的先锋意识,明确把歌颂抗战救国作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它无愧于那个时代对诗文学的嘱托与期望。”
三、诗体建设:街头诗与民歌体叙事诗的繁盛
在以政治任务为责任承诺的延安诗歌中,对文体的要求呈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大众化的即时性文体的倡兴。在当时那民族的与阶级的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中,那些短小精悍、直接诉诸民众的诗歌形式,如街头诗、朗诵诗、合唱诗、剧诗等格外受到重视。第二,史诗风格的长诗和叙事诗的兴起。为适应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全面、深刻反映的需要,延安诗歌呈现出了叙事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从延安十多年的诗歌历史来看,多种诗体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街头诗和民歌体叙事诗在延安诗坛中占的比重最大,成就也最好,它们是延安诗坛上最具现实性和时代特色的诗歌形式。
街头诗古已有之,而且一直在民间流传。但街头诗的真正崛起,并且成为群众性诗歌运动,则是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在诗人田间、柯仲平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延安发起了街头诗运动。这种传播迅捷、思想指向性鲜明而又带有新闻特征的街头诗便成为40年代解放区和根据地诗歌的新形式、新事物。街头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不仅指题写在街头或墙头上的诗歌,还包括派生出的岩壁诗、传单诗、路边诗、战壕诗、枪杆诗、地雷诗、手榴弹诗、背包诗等。街头诗具有短小通俗的形式,富于宣传鼓动性的内容,大众化的艺术取向。它从生活出发,反映现实,通过生活来体现政治或感染读者。街头诗也运用典型化手法,通过具体形象化的人物事件来反映时代的一般要求。当时的街头诗基本上都是抒情短诗和小叙事诗。小叙事诗也是一种创造,它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丰满的人物形象,只是截取战争生活的某个片断,某种场景,用白描手法勾勒人物性格和表现特定环境下人们的思绪;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人物集中,富于直观性,使读者能从具体场景或一刹那的人物活动中,把握住作者要表现的思想情感。这实际是运用的生活浓缩或剪裁的方法来传达思想情感的诗歌形式,街头诗受小诗影响,重在说理,因为宣传鼓动群众,得以理服人;若没有有力的理论或哲理,是不足以打动人心的,所以寓理于情,或理中含情,是街头诗的重要特点。
街头诗是承应大时代的感召而起的,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宣传性鼓动性极强。它一出世就与标语口号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它被称为“政治号筒”、“时代鼓角”。但它并不等于标语口号,标语口号是直白式政治宣传,而街头诗是艺术化形象化的政治宣传,“它比标语丰富、具体、复杂,有大体可念的音韵,有情感。”(注:《关于街头诗运动》,《新中华报》1938年8月15日。)当时一首街头诗《送郎当兵》这样写道:“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不是好铁不打钉。”这样的街头诗,比起那种号召广大青年当兵的标语口号的宣传效果,明显要高出一筹。这也说明,街头诗需要高度艺术化,它必须要将政治口号通过艺术形象深刻地表现出来,才能发挥政治的功效。当然,标语口号嵌入或融合进街头诗中,处理得好,也可以起到“政治号角”的作用。正如田间后来所说的:“街头诗中,有的难免有‘口号’,但这‘口号’要和全诗融为一体,好像宫殿的一根柱子,不是装饰,不是附属品,不是节外生枝,更不是炫耀自己的那些废话。”(注:《田间自述》(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例如田间的《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我们应该跟着——/边区的旗帜,/首长的/指挥,/站在大队里头,/照毛主席所说:/‘坚持持久战斗!’”以“假使”句开头,43个字一气呵成,形象而生动地道出了边区军民按照毛主席的持久战指导思想,坚持神圣的民族战争。他的著名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采取同样的结构、格式和节奏,道出不抗战的严重后果。当时延安诗派的许多优秀的街头诗都是这样,充满了直截了当的呼唤,具有政治术语、标语口号的引用,但由于诗人把标语口号的内容形象化了,诗化了,因而其街头诗的艺术效果胜过了“坚持持久战”和“不抗战就要灭亡”等同义的标语口号。当时有人对诗与标语口号的结合提出责难,田间则写诗回答:“依我看来,口号和诗,如同云彩和风景,云彩是风景的前奏,风景是云彩的呼啸。”(《我的回答·二》)即是说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尽管当时有不少人不能处理好标语口号与诗的关系,使街头诗缺乏诗情诗意,但相当多的诗人则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从事街头诗创作,探索街头诗艺术,使街头诗创作取得了辉煌的实绩。
在40年代延安诗坛,如果说街头诗昌盛于前,那么民歌体叙事诗则繁盛于后。民歌体叙事诗是随着40年代中后期整个叙事诗繁盛而繁盛,它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超过了其他类型的诗体。
在抗战开始以后,现代叙事诗具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达到了高峰。当时诗人除了写街头诗、抒情诗外,大都重视叙事诗的创作,形成了叙事诗的竞写热潮,这是因为,现实生活和战斗的热情,本身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人们普遍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审视的目光观察过去,以满腔的热情表现现实,以热烈的理想憧憬未来,渴望整体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于是诗歌创作出现了追求史诗风格的倾向,长诗创作也就多起来了。在长诗的总的发展趋势中,民歌体叙事长诗逐渐突现出来,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创作倾向。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抗战时期,出于配合抗线,组织民众投入抗战的需要,鼓词等俗曲形式得到新文学作家的大力推崇。它们不仅被称之为“是一种可以弦歌的叙事诗”,而且还进而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发展为新时代的史诗”的一种民族形式。(注:茅盾:《关于鼓词》,《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8期。)于是,不只是赵景深、穆木天等人直接采用鼓词形式的“旧瓶”,来表现新的时代现实,写出了一批通俗的“鼓词叙事诗”更有柯仲平为首的一些诗人,采用唱本俗曲的句式和章法结构,来叙述抗战的故事,因而受到诗歌界的广泛注意,甚至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冯雷峰当时就肯定了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是“可以称得诗”的长篇叙事诗,是“在创造着新的形式”。其中的《边区自卫军》,“在全体的基本的构成和谐和上说,这几乎是一篇民众自己天然地产生的民歌。”(注:孟辛(冯雪峰):《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文艺阵地》第4卷第10期。)茅盾也认为柯仲平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值得继续去试探的”。(注:茅盾:《文艺杂谈》,《文艺先锋》第2卷第2期。)可以说,这种企图从多种表现形式中,获得一个更为人民大众所欢迎,同时提高了艺术水平的形式的努力,在40年代中后期的解放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的一批诗人,注重从民歌的形式中探寻叙事诗创作的路径,他们看到了民歌具有浓厚的叙事因素,运用它来创作叙事诗,必有其优势。李季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功,在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给广大诗人以极大鼓舞。于是民歌体叙事诗创作形成空前未有的热潮。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也与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40年代中后期,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从概括生活的广度,反映现实的深度以及塑造人物的力度来看,都需要发挥叙事文学的功能,选择叙事诗的品种,可以说,民歌体叙事诗的发达,既是诗人积极投入战斗生活、深入群众的结果,是诗歌为现实服务、为群众服务,不但要求内容大众化,形式大众化,就是作者本人的生活响应大众化的结果。
在40年代中后期,民歌体叙事长诗成为诗坛的潮头,涌现出了大批作品,这些叙事长诗是民歌体的新诗,它们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秀传统,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更为深刻和广阔,同人民群众和革命斗争的结合更为密切,表现出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些民歌体叙事长诗不仅内容新、人物新,而且形式、语言和风格都是新的。它在艺术上走的不是“采取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而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的道路。它的艺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与方法同新诗结合能够开创出新的艺术前景的可能性。其艺术特征主要有这样几点:一、向民歌学习,从民歌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经过“推陈出新”,从而创造出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乡土风味的新的叙事长诗体式。二、叙事和抒情的紧密结合。三、语言的口语化和大众化。总之,延安诗派所开拓的民歌体叙事长诗,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以新鲜活泼的民族形式和刚健明朗的艺术风格为群众所善闻乐见。这些民歌体叙事长诗为实现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工农兵方向,开拓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道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是在人民生活和民族艺术土壤上结出的诗艺之果。
延安民族体叙事长诗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不少叙事长诗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洋洋洒洒的诗行中,往往都是具体战斗过程或生产过程的复制,而没有与人物形象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联系起来,并且实事实景束缚了诗人激情的翅膀,不能使诗产生更感人的力量。不少叙事长诗或采用平铺直叙的写法,缺少重点的描写,或者受真人真事的限制,缺乏内容的提炼;有的诗人强调诗歌的“叙事性”而相对地压抑个人的抒情,忽略诗人内心的感受。不少叙事长诗表现手法单调,感觉不到灵感、思想和对新的表现形式的探求。当时不少诗人探索用民歌体叙事诗创作,并未成功,艾青就是其中之一,他精干自由体,尝试民歌体未获成功。虽然一些优秀的诗人能够用长诗这样的大型体裁来装载他的丰富的生活阅历,但仍觉力不从心,最突出的一点是这些长诗“还没有把民间歌谣形式与所应反映的强烈、浑融、阔大、深沉的历史变动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当时长篇叙事诗作者所要反映的对象,原本是充满艰苦的历程,充满血与火的斗争,充满痛苦与喜悦的心灵挣扎,而作为大多数的诗体形式,带来的却更多的是轻松、愉快、和乐、静美的风格,因而作者们追求着革命史诗的内容,却没有带来应有的革命史诗的气度。”(注:王富仁:《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版,第231页。)其实,当时茅盾、王亚平、戈茅等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用民歌格式写抒情小诗可以,而用它来写长篇叙事诗是不妥当的,因为现代叙事诗的内容决定了它非有庄严与雄伟的风格和雍容的风度、浩荡的气势不可,而现有的民歌形式,都是谈不上庄严与雄伟的。正因为这样,延安民歌体叙事长诗没有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而当这类叙事长诗一度繁荣之后,就再也没有在诗坛重现兴盛的局面。
四、开一代诗风:战斗的现实主义
战斗的现实主义在延安诗派中占了上风。这是因为延安诗派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诗人,这其中不仅活跃着一批传统的现实主义诗人,而且从解放区乡村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农民诗人和从部队的战斗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战士诗人,都自觉地站到了现实主义的旗帜下。对于他们来说,现实主义不仅是诗歌创作方法,同时也是世界观的原则。所以,延安诗人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是最清醒、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这种现实主义把战斗性,群众化、刚健美合为一体。而其中战斗性又是最突出最根本的特征。尽管延安诗人也各有自己不同的风格,但这内在的一致性特征却是比较明显的。
延安诗人为时代而歌的自觉精神,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战斗品格,这种品格体现在诗的内容上,就是与现实保持一致,“把新的血的战争现实写入诗里”,强调出色的表现现实并充满火辣辣的热情;体现在美学观点上,就是理直气壮地张扬诗歌的功利目的,把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紧密地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都是以笔作刀枪同敌人殊死搏斗的时代战士,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们作纯艺术的追求,他们摒弃了那种写自我、写生活琐事、抒发个人感情的诗风,而以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斗争生活为根本题材,表现人民的喜乐和愤怒,反映人民所关心的现实,并鼓励和帮助人民前进。他们是乘风破浪、尽阅沧桑的人,忠于理想、富于感情、懂得爱与恨的人。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都有个人感情,有私人生活,在战斗的人生路上,时时存在生离死别,无处不有悲欢离合,但他们抒发爱情和个人生活情趣之类的诗作甚少。那不但是因为战争的环境不允许,更是因为他们把一己之爱扩展为爱人民、爱国家、爱同志和战友,把个人的苦乐融入人民的悲欢之中,把一切个人的幸福憧憬、痛苦,强制冻结在深深的心底。
群众化的增强是延安诗歌的鲜明特色,这不仅表现为诗歌读者圈的不断扩大,还表现为诗人力图让诗歌更强烈地表现读者的心声。因为,欲使诗歌在战争中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就必须让它更接近人民群众,更易为读者所接受,因此战时的延安诗歌就形成了鲜明的趋众模式,这种趋众模式以人民大众为中心,把“让诗和人民在一起”作为诗的最基本的发展方向,要求在诗歌创作中选择大众感兴趣的题材,表现大众的思想意绪,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传达形式,运用大众晓畅明白的语言,趋向大众的接受习惯和欣赏的口味,以赢得大众的真正喜爱。正因为这样,延安诗歌不再是少数人的消遣品,而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诗的神秘面纱在这里被彻底撕破了。无数劳动群众也拿起了笔,加入了诗歌创作队伍。延安诗歌在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上的这些变化,改变了中国诗歌的性质,使中国新诗以空前有力的步伐走向了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这真是一个诗与时代、与人民紧密结合,空前普及的时期。
延安诗歌的刚健美,则是指它在作品的风格上所体现出来的力度美。战斗的生活,不但武装了诗人,也武装了诗。延安诗歌作为民族解放的号角,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延安诗歌“走出了缪司的宝殿,以投枪匕首般的锋利,号角鼓点般的响亮,阳光火焰般的赤热,晓露春芽般的清新,走向战争,走向人民,再无那种灰暗的自遣,风花雪月的泛呤”。(注:王剑青、冯健男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版,第114-115、83页。)延安诗歌力求在表现形式上“明快晓畅而不艰涩朦胧,朗朗上口而不诘屈聱牙,简洁生动而不雕琢铺陈,质朴充实而不华丽空洞,通俗易懂而不生僻难解”。(注:杨忠:《陇东革命根据地诗歌漫评》,《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尤其是那些街头诗,通俗而又富于鼓动性,精悍而又不失激越与豪放;那些政治抒情诗,旋律一般都比较急促,语言铿锵有力,情绪饱满激昂;那些民歌体诗歌,常常在明快朴实中带着一般清新活泼的气息。那些战争的诗,大都写得慷慨悲壮,铮铮有音,读起来令人神情鼓舞;那些反映农民翻身解放的诗,欢乐、激昂的主人公和明朗的节奏感很强的语言,构成了诗的主色调。这些诗歌在显得个性有些不足,技巧有些粗糙的同时,也体现了延安诗人独特的精神风采和美学风貌。
延安诗派承继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诗风,较之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派,以蒋光慈、殷夫为代表的普罗诗派,以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和“密密期”新诗人,它更为持久更为有效地深入和强化了革命诗歌的优秀传统,并为新中国诞生以后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范型,指定了路标,这其中虽有利有弊,有着深刻的经验与教训,但它的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则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