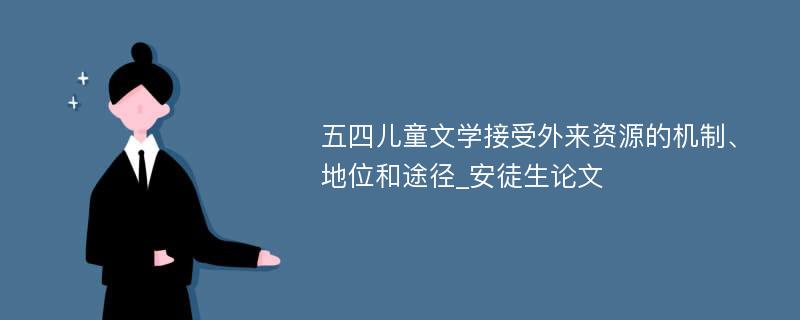
“五四”儿童文学接受外国资源的机制、立场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文学论文,路径论文,立场论文,机制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儿童文学是在中国转型的特定语境中发生的,其观念范式所依托的语言形态和美学构架,绝非随意、偶然的拼合,而是凝聚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他者的现代沉思,也勾连了本民族的深层心理,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审美范式。借助中西文化的互视与交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纳入中国新文学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之中,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范式的生成与创构。 一、“为儿童”还是“为成人”:接受机制的两歧诉求 要探究“五四”儿童文学接受外国资源的问题,有必要廓清现代知识分子的“儿童文学”观,因为这直接关涉他们的接受机制。“五四”之前,儿童文学混杂于教育学、民俗学、儿童学等学科门类之中。为了确立儿童文学独立的学科价值,儿童文学先驱试图将儿童文学从成人文学的话语体系中析离出来。戴渭清曾用绝对化的立场来阐明其与成人文学的差异:“成人有成人的文学,儿童有儿童的文学。成人文学,是成人真情之流;儿童文学,是儿童真情之流。成人喜欢欣赏成人的文学,不喜欢欣赏儿童的文学;儿童喜欢欣赏儿童的文学,不喜欢欣赏成人的文学。”①凭借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殊异的价值认定,儿童文学的学科性质被确立下来了。周作人早期的童话研究始终围绕着“童话”与“原人文学”的关系展开,其目的也是为了创生出具有独立归属的学科门类。②“五四”时期创构的儿童文学表征了一种全新的、现代的文学范式,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儿童”这一主体的想象和建构问题上。应该说,“儿童的发现”是一种崭新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建构。“儿童”这一独立的“人”的主体,是通过成人的现代知识生产构筑生成的。正是基于儿童的真正被发现,儿童文学才得以产生,“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适合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③在“五四”启蒙思潮的推动之下,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自觉地汇入了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变革和演进的大潮之中,儿童文学因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在“儿童的发现”归并于“人的文学”的主潮的同时,也亟待将“儿童文学的发现”纳入中国现代文学体系之中予以观照和审思,以彰明其本有的价值。以往研究中对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存在着曲解、误读,主要表现为:一是将儿童文学视为成人文学的附属形态。这种观念的逻辑基础是“五四”儿童文学的生产者、批评家以及优先接受者是成人而非儿童,儿童只是成人作家话语实践的符码,儿童文学所持立场、标准依然掌控在具有知识话语权的成人手中。成人话语的泛化使得“五四”时期“儿童的文学”与“儿童视角的文学”概念混杂难辨,这无疑弱化了儿童文学的学科性质,也模糊了儿童文学的边界壁垒。二是将儿童文学理解为与成人文学完全相异的形态。这一思维的逻辑动因是为了儿童的发现与解放,为了从传统的家庭秩序中拯救新人群体,以此撼动成人的神话。因为“只有成人相信儿童在某些方面与成人不一样,需要一种属于他们的文学,儿童文学才能够存在”。④其结果却切断了两者的共同性和深刻关联。 上述误读的症结在于未能辩证地融通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联,“泛化”或“窄化”了两种文学形态的学科壁垒。故此,若要真正理顺两者的关系,绝不能简单地以“为儿童”或“为成人”的差异为尺规去判定两者的区别,而必须将两者置于“五四”中国的历史现场,在动态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审思。在笔者看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能建立关联的逻辑起点是文化的同一性命题和文化的时代性命题。“五四”儿童文学接受西方资源的主旨是用西方现代儿童文学资源来对抗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儿童的桎梏,这种接受方式,实际上承担着儿童教育及文化启蒙的使命,它包含了一种以儿童为杠杆、开掘主体价值的现代性实践,创造了一个跨越旧时代、向着新的话语关系迈进的想象空间。成人作家将国家“种性”和“族性”的提升寄望于儿童弱者身份的现代变革。基于此,儿童“可塑”的精神品格拒绝社会对其“弱性群体”的套话定性,儿童转型的书写与中国新生的建构有机地连接起来。这表明了儿童文学先驱是以中国本土立场来认同和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并且在中西文化间的对接中延展了“五四”儿童文学的内在精神结构。 事实上,“五四”儿童文学对外国资源的接受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儿童文学“为儿童”与“为成人”的现代性的转换与融合。⑤儿童文学“为儿童”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尊重儿童“新人”的精神品格,将儿童现代精神的铸造视为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特征。而儿童文学“为成人”的现代性则是将成人化的现代理想及价值取向作为是非标准付诸现代儿童的文化结构中。其实,两种现代性共构了儿童文学内在结构的多维向度,但也因主体文化诉求、思维形态及精神指向的差异而衍生了诸多矛盾。“五四”儿童文学始终无法回避的悖论是:一方面为了凸显“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思想,作家必须拉开儿童与成人的距离、强化儿童与成人的差异,这样才能挣脱儿童归属于成人的宿命;另一方面,为儿童的真正解放考虑,作家又不得已要用成人一套话语系统来启蒙或书写儿童,这势必又要拉近儿童和成人的距离。就接受实践而论,“为儿童”主要表现为译介以“儿童为中心”的符合儿童阅读习惯的文学作品。这要求淡化成人话语的引导和渗透,真正回到儿童本身。然而,这势必又弱化了“五四”现代性的知识逻辑,将儿童文学置于狭小的精神天地;“为成人”则主要基于儿童启蒙、儿童教育的现代性诉求,而接受那些凝聚成人话语的儿童文学作品,显然,这又偏离了“儿童本位”的初衷,进而导入了成人所设置的话语体系中,难以彰显以儿童的主体价值。于是,接受的过程与目的失序难以豁免,由此产生的对于外国资源的差异选择、中国化误读等接受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之所以存在“为儿童”与“为成人”的两歧性,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五四”儿童文学译介者,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茅盾、叶圣陶等人,均身兼儿童文学创作与成人文学创作,很难用两套标准和立场来区分“为儿童”和“为成人”的内在关联。与成人文学相异的是,儿童文学拥有双重读者:一个是作为接受主体的儿童,另一个则是作为“隐含读者”的成人。在译介安徒生的童话时,赵景深有意识地强调安徒生童话预设双重读者的特点:安徒生题名“说给孩子们的故事”,但其童话“要写给小孩看,又要写给大人看”,因为“小孩们可以看那里面的事实,大人还可以领略那里面所含的深意”。⑥郑振铎也认识到了安徒生这一特点,“童话有专为儿童写的,也有不专为儿童写的。最有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所做便有一部分不适合儿童的”。⑦周作人则赞赏安徒生“能够造出‘儿童的世界’或‘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⑧肯定其催发儿童想象力的文学要素。正是这种双重读者结构,使得儿童文学在思想阐发上不可能那么纯粹。 往深处研究,儿童文学自身结构性的缺陷也是生成上述两歧诉求的重要根由。与同为弱性群体的妇女不同的是,“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儿童却始终要依赖成人间接地表达自己,“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造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⑨因而,“当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欣喜地获得了对世界对自我描述的话语”时,儿童“依然要通过成人的话语系统来传达自己的声音,儿童的特殊点就在于成人与儿童的双逻辑支撑点”。⑩在此“双逻辑支撑点”的逻辑之中,儿童文学陷入了借助成人话语来反成人话语操控的尴尬境地。遗憾的是,尽管通过“自身童年”的唤醒,成人可以与儿童进行对话,但成人被唤醒的“观念性童年”与儿童“实体性童年”之间依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于是,在成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儿童被列为启蒙的对象,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郑振铎曾提出儿童文学的“工具主义”,在他看来,成人文学没有传达理性知识的义务,都是无所为而为的作品,而儿童文学则不然,可以对其实施工具主义的启蒙。(11)但是,在“五四”文化语境中,这种实用的启蒙意识被转换为成人话语实践的另一形态。换言之,“为儿童”的启蒙被变换为“为成人”的话语需要,“儿童本位”的观念也因成人话语的渗透而合理延伸。基于此,在接受外来资源时,成人作家往往以成人先入为主的意识来选择资源,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诸多与儿童本体有偏差的儿童想象。这种译介与接受间的“不对位”现象使得“五四”儿童文学接受外国资源时实际上是由两个价值主体共同完成的。 因而,如何处理好“为儿童”与“为成人”的关系就变得相当关键:如果过多地考虑成人读者,有可能会导向成人之于儿童的教化或训诫;如果过多地倚重儿童读者,有可能会归于游戏或娱乐的套路。当然,只预设成人或儿童为单一的“受述者”,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深度和厚度也会受限,因为它失去了儿童接受者与成人接受者冲突与互动反向的推力。从这种意义上说,“为儿童”与“为成人”的两歧诉求扩容了“五四”知识分子接受外来资源的思维视野,但也使其陷入了表述自我与表述他人的话语焦虑之中。 二、“自然性”与“社会性”失衡:译介过程的容受困境 翻译这一语言实践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不同的传统相遇将某一文化、语言语境的文本的意义导入另一语境,并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隙中找到可以兼容与观照的立足点。可以这样理解,翻译本身蕴含着比较的视野和观念,它让他者与自我直接对话,并迫使两者都要经历多重转换。“五四”儿童文学译介外国资源的过程就并非易途,此间的文化“习语”与文化“失语”并存。概言之,儿童“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矛盾是困扰儿童文学理论界接受西方资源的一个难题。从本源上考究,两者的冲突问题是前述“为儿童”与“为成人”难题的衍生物,这种结构关系体现了现代性叙述中各种普世化抽象范畴所包含不了的越界、滑落与矛盾,它们如影随形地同构了“五四”儿童文学翻译大潮中译介者的精神困境。 英国学者戴维·拉德认为儿童必然是既被建构的也能建构的,因而在生物本质论和文化决定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话语裂隙。(12)换言之,儿童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成人操控儿童话语的前提条件,儿童可以被建构为国家未来的符号,也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原初精神的表征。这样一来,成人作家就既要弥合儿童“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裂隙,又不得不拆解两者顺应时代的默契,其陷入话语撕裂的焦虑之中就是必然的事情了。上述的话语裂隙潜存于“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内核之中,直接影响着译介选择的立场、技巧和主题。在“五四”儿童文学翻译大潮中,译介哪些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作品成了当时争论不休的话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种观点主张以儿童的自然属性为出发点,译介契合儿童精神世界的文学资源。他们认为,厚积成人功利思想的儿童文学作品容易扼杀儿童的自然天性,因而不宜被儿童接受。许多知识分子对接受外国资源的实用主义倾向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周作人就曾指出中国翻译界的一个弊病是“‘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融通: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13)他不主张儿童过早地介入现实的成人政治,认为这可以在长大以后自己去选择。郭沫若也曾指出,强调翻译功利性的行为是“阻遏人的自由”,是“专擅君主的态度”。(14)在他看来,“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儿童文学中的教化应寓于文本之内,“像藏在白雪里面的一些刺手的草芽,决不能像一些张牙舞爪的狮子”。(15)与此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则是主张重视儿童的社会属性,强调儿童文学对儿童的教育与启蒙效应。在他们看来,儿童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不可能隔绝与社会的关系。倘若儿童接受的内容仅局限于诸如猫狗之类的知识与游戏,那么儿童就“不配做世界上的人,更不配做中国的国民”,其结果会培养出“变成猫化狗化畜生化的国民”。(16)上述分歧涉及“五四”儿童文学译介者如何看待儿童文学“自然性”与“社会性”关联的根本问题。倘若孤立地坚守其中任意一方而不加以融通,那么,必然会导致儿童价值的文化失衡,不利于外国资源在中国的内化与吸收。 应当承认,“自然性”与“社会性”原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确有相互融通的基础。但问题是在“五四”中国现代转型的文化语境中两者统一的条件尚不具备。梳理“五四”儿童文学的接受史,不难发现多元的外国儿童文学资源以及中国本土文化的过滤机制,是造成“五四”儿童文学“错位”或“变异”地接受外国资源的深刻根源。这样一来,当译介者接触到混杂着儿童“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西方资源时,难以制衡两者的矛盾,产生了关于儿童本位的“童心崇拜”与儿童本位的“民族隐喻”的论争。其实,在“五四”中国的情境下,要融通两者的关系并非易事:一味强调儿童自然性,就容易将其孤立于社会之外;而一味强调其社会性,又容易扼杀其自然天性。那么,是否可以用先“自然性”传入再“社会性”启蒙的方式避开两者紧张而衍生的难题呢?表面上这也许是一种可能性的实践路向,但实际上与“五四”中国迫切的现代性困境却是相悖的。这其中隐含了启蒙动机的急迫性与启蒙过程的缓慢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单方面强调儿童文学的“自然性”或“社会性”都很难契合儿童的成长需要。也许可以期待随着教育的慢慢普及、民众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最终能够实现儿童与未来中国并举的理想。可是中国社会处于相互牵扯的悖论当中:儿童的觉悟依赖于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普及依赖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而社会公正的实现又依赖于儿童的普遍觉悟。这种互为条件的悖论,预示了儿童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命运。总之,“自然性”与“社会性”的非同一性遭遇“五四”中国动态的文化语境,将知识分子带入了确认和传播外国资源的困境,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撕裂着他们的内心。以郑振铎为例,他非常肯定儿童的自然属性:“凡是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本位。要顺应了儿童的智慧和情绪的发展的程序而给他以最适当的读物。这个原则恐怕是打不破的。”(17)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绝对的‘儿童本位’教育的提倡,当然尽有可资讨论的余地。”(18)郑氏的接受与创作经验表明,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不在于儿童拥有自然性而成人拥有社会性,而在于自然性与社会性在儿童、成人那里分别拥有怎样的配比方式和组合规则。显然,“五四”儿童文学先驱尚不具备自觉调节“自然性”与“社会性”互融互动的心理机制,无法调适文化选择的不平衡所带来的话语错位,进而陷入了精神困境之中。 西方童话的翻译实践,更鲜明地体现出了因观念不同而引起的译介选择的差异。童话是“五四”知识分子译介最多的文学样式。究其因,童话强调儿童生命力和想象力的催发,不附加过于沉重的社会内涵,不渗透太多的现实教训。周作人高举童心崇拜的旗帜,译介了大量“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童话作品。(19)在他的引领下,很多译介者从儿童“自然性”的角度来接受外国资源,成为“五四”儿童文学翻译大潮的重要支脉。然而,在“五四”启蒙的文化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不止于儿童自然性的褒扬,而是从儿童社会性与中国想象的契合上大做文章。基于儿童启蒙、儿童救国的时代诉求,译介者对童话的选择与过滤,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意识。至少有三种路向值得关注:一是翻译儿童科幻作品,寄予“科学救国”的理想。二是译介英雄色彩浓厚的儿童文本,彰明“人”的主体价值。三是引入弱小民族的文学,积聚启蒙弱者的精神气度。与其说上述迥异的译介选择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差异造成的,不如说是其对于儿童“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不同偏好使然。事实上,“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儿童本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区别与融通。但是,“五四”中国的特殊情境使得两者无法有序地组合在一起,由此出现的“童心主义”就是片面强调某一方而割裂两者精神关联的极端倾向,值得反思。(20) 要洞悉“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必须找到勾连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节点。周作人非常认同日本作家柳泽健原提出的“第三之世界”的概念。(21)这个“第三之世界”是一种中间状态,是连接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桥梁。在他看来,立于“第三之世界”能跳出其他两个世界孤立自足的偏见和短视,洞见两者之间的差异与统一。这一观念经由“五四”知识分子的译介传入中国后,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围绕此论题展开的讨论深化了这一思想的内涵。我们可以通过赵景深与周作人讨论安徒生和王尔德童话区别来析之。赵景深认为,安徒生的大部分童话是“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而王尔德的童话“内中很多深奥的语句”。在他看来,童话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性逐渐强化,但“就儿童的眼光去看,总要觉得一个不如一个……离儿童又觉得远了”。(22)赵景深的此番评论道出了童话发展过程中“社会性”逐渐强化,而适合儿童的“自然性”却日趋消逝。在他看来,这种倾向对童话的发展是不利的。赵景深理解的童话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是一种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形态,也是儿童文学无法兼容的文化结构,因而他认定充当“第三之世界”的童话也难以融通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毕竟“小儿般的成人”与“儿童”的出发点、心态及价值取向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周作人的回信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赵景深的观点,他认为安徒生的童话是“超过”和“融和”成人与儿童世界的,所以属于“第三之世界”,而王尔德的童话“有苦的回味”,是现实上覆了一层极薄的膜,所以其创作的童话世界并非“第三之世界”而是成人的世界。王尔德童话中社会性对自然性的挤压和占领恰是周作人、赵景深诟病的地方。然而,王尔德童话包纳儿童自然属性的艺术性始终很突出,当时批评家对其“艺术至上主义”“个人主义”“唯美主义”等倾向进行过犀利的批评。基于“为人生”的观念,沈泽民就曾指出,“他在文字中所表现的享乐主义的倾向和艺术无上主义的僻见,对于世道人心及文学本质上的影响却很有讨论的余地”。(23)对此,赵景深一改上述批评王尔德的态度,转而为其辩护,他认为,唯美主义的美学追求恰恰成就了王尔德的童话,“他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注重空想,不重现实,要把世界造成一个美的世界”,在他看来,这种唯美主义的文艺主张却与生活中的假恶丑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使其不得不对受欺凌的弱者表现出深切的同情,歌颂他们善良的心灵。于是,他得出结论:“唯美主义并不是厌世主义。写实主义主张艺术要人生化,他却主张人生要艺术化,虽是立论不同,究竟都是离不开人生的。”(24)事实上,赵景深已经站在“社会性”与“社会性”区别、融通的基础上来深思王尔德的童话了。基于此,王尔德童话内蕴的现实与童话被理解为一种显隐共在的话语转换关系,它不会导向虚无,而是在艺术之中渗透了作家观照现实人生的思想内核。阅读的效果必然是“读去极为愉快,但是有苦的回味”。(25) 要言之,该运用哪种观念来接受西方资源是由接受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以及所秉承的文学观念等要素决定的。在容受过程中,接受者对于西方资源各种各样的阐释及运作方式,尽管因所持立场而不乏误读与偏见,但也表明,多元性西方资源业已成为“五四”儿童文学发生、发展进程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其内蕴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错位与混杂皆本源于文化间转换生成的困境所致。 三、双重他者互动:“传统资源”与“西方资源”的整合 “西方儿童文学资源”和“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是“五四”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两个“他者”,世界性与民族性已经内化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两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互相关联的辩证主体。它们的碰撞与冲突,制导着“五四”儿童文学接受西方儿童文学资源的出发点、方式及策略,也影响着“五四”儿童文学化用中国古典儿童文化遗产所持的标准、尺度和原则。 在理解跨文化交流的问题上,萨义德曾提出过著名的“文化旅行图示”,他认为,文化能够传播与交流首先需要有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其次则需要有一段横向距离,再次需要具备一系列接受条件,最后才能实现文化间的容纳与融合。(26)实际上,文化间的这种流通远非萨义德上述的线状传播那么简单,两者的连接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就“五四”儿童文学而言,如果简单地套用萨义德的理论,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看法:西方儿童资源作为一种强势“源传统”,它支配着中国作家儿童文学的话语实践。而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则将被弃置,成为“沉默”的他者,其结果必将降格中国文化的自我传统及价值。显然,文化间的交流不存在这样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流动态势。异质文化只要一接触,彼此之间的互渗就不可避免,而这种互渗是用“起点-终点”这样的图示无法准确予以概括的。因此,我们可以将“互渗”行为产生后的诸多问题进行梳理,反思其错综复杂的张力关联。 循此理路,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来梳理两种资源互为他者的对话体系,着力于“以西审中”与“以中审西”的双向互动的话语实践。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将中西资源的整合内化为儿童文学发生、演进的现代框架内。他们采用先“器识”后“灵魂”的策略,从浅入深地融通中西资源。具体路径主要有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西方资源之于中国传统资源的参照价值主要在于现代性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在《童话研究》中,周作人陈述了俄国、日本、爱尔兰等国的童话的不同,有的美艳幽怪,有的奇俗骇人,有的洒脱清丽,有的浓郁夸诞,唯独中国乏善可陈。(27)他曾将中国古典志怪小说所辑录的民间童话与西方童话进行比较,深有感慨,“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据此,他提出了收集古代童话的方法,“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然而非所可望于并代矣”。(28)从国内外“异文”中寻漏补缺的收集方法,体现了周作人立足中西融通的背景打捞中国古代童话的视野及思维。通过中西资源的比照,冯飞认识到了西方童话中的巨人是养成少年勇武之心和不屈个性的空想,“巨人的空想,骤视似无甚道理,其实是伟大民族性的表象……童话上的空想,与其民族性有密切关系”。相反,中国传统儿童读物缺乏那种响彻天宇、横空出世的巨人形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性中对于强权只有“躲避”“防卫”以及“恐怖心”。正因为如此,他充分肯定外国童话中的“菲丽”形象,主张利用“菲丽”超自然的视觉去改造儿童的心灵世界,创构现代中国的新童话。(29)在阅读大量西方寓言的基础上,茅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儿童文学的质素予以重新认定,对其中如“孔子劝学”“学以砺身”等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古典资源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造,期冀儿童能养成好的习惯和品格,承担起社会及国家的使命。他力求“把儿童文学古籍里的人物移到近代的背景前”(30),这种古为今用的思维是茅盾儿童文学创造及改编的重要维度,自觉地将古与今两个视域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资源之于西方资源的参照价值则主要体现在民族风貌和本土立场上。正是这种中国立场,使得“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31)“五四”知识分子主张从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和民间信仰中来考量中国国民的精神,这种眼光深深地吸附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流脉,本源于民族文化现代转换的精神冲动,扩充了“五四”儿童文学的民族含量和中国元气。驻足于安徒生童话的中国传播方式、路径、过程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安徒生童话对于“中国”的想象与言说。童话《夜莺》《没有画的画册》《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在养鸭场里》等童话均以“中国”为背景,建构了诸多中国人的形象。在这里,安徒生借“异域”想象来建构其自我想象,其中所展开的对于中国人物、事件、情境的论述与讨论,均以西方文化“在场”对于中国文化“缺席”的言说,这些是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32)的理论假设上。换言之,安徒生深层的精神指向是“中国”之外的“自我”,其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中国”这一他者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中国儿童还是外国儿童,阅读安徒生的上述童话都会产生一种文化“交往”的陌生化困境,丑化或美化表述中都存在着某种跨文化审视的偏见,影响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可为西方自我批判和自我扩张提供条件。在深入研究了外国童话家所编的中国童话后,赵景深撰写了系列文章《费尔德的〈中国童话集〉》《皮特曼的〈中国童话集〉》《马旦氏的〈中国童话集〉》《亚当氏的〈中国童话集〉》《白朗的〈中国童话集〉》,批判了西方搜集中国童话漠视中国本土文化精神、仅从想象文学的现成书本里去搜求的偏狭倾向。在他看来,这“只是用西洋民间故事乔装中国童话,将对风俗人情的描写点缀文中,几乎全是杜撰改作,骨子里仍是西洋童话”。(33)同时,他也指出,“西洋搜集中国童话的人不从我们老百姓和孩子口头采集《蛇郎》《老虎外婆》一类的童话,而从想象文学的现成书本里去搜求,可谓失策”。(34)换言之,没有考究中国语境,简单地用西方本土文化“装点”和“套用”中国童话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童话精髓的。为了抚平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想象的变异现象,必须加入中国的视角,变缺席的、沉默的他者为主动的在场言说者。赵景深极力强调“民间的童话”本土化的重要性,他深信,民间童话“要想发扬我国民族的精神”,这种铭刻了民族印记的童话才是中国童话发展的方向。(35)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重新发掘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扩大的心胸和宏大的视野,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弥补了文化危机所带来的认同缺失,也提升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新文学的民族品格。 “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立关系上,而这种差异对立关系,又被结构到一种整体性想象的互动机制中。可以说,“五四”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资源的目的并非是其对于异域文明的钦羡,而是借西方他者的功能来检视本土文化的内在肌体。沈从文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体现了其融合中西资源的跨文化实践,值得深入研究。在仿写过程中,沈从文用中国人的方式来构思和撰写,将这一个童话原型嫁接于中国的土壤上,开出了融合中西的全新花朵。在这里,沈从文将中国的书写镶嵌于外来者认识中国知识、风景的现代性装置中。在漫游路上,阿丽思与傩喜看到了诸多残忍的现实内容,如连自杀都需要求助于人的难民;毫无操持、为了虚名竞相倾轧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的文化官员,以及表征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种种弊病均被外来人所发现。无奈,她们来到了远离都市的边缘之所——湘西苗部,然而,这里也远非所期待的真正“自然”,在亲历了原始而残忍的奴隶买卖后,她们决定结束漫游回到英国去。显然,这其中有用外国他者言说中国的“借镜”功能的征用。“外国孩子”这一独特的他者身份,为阿丽思提供了观照中国的很多便利。对她而言,中国的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儿童的天性让她不会像成人外来者那样理性地思考异域风景。然而,现实的生活彻底击溃了她稚嫩的幻想,现实的发现让她变得沉重,童话本身的趣味性自然退场。沈从文“天真打量沉重”的改编策略彰明其秉持的中国立场,也体现了其跨文化实践的现代认知。沈氏强调,“把阿丽思写错了”,“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不少”。(36)道出了他改写西方童话时错位的文化心理,其实质依然是内涵的中国情结。加入“社会沉痛情形”的色调后,该童话的主旨不再止于纯粹的“逗小孩子笑”的趣味上,而有了更多想象中国的话语实践了。 如上基于中国本土立场的接受实践表征了“五四”儿童文学从吸纳借鉴西方话语到逐渐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其价值至少有两方面:一是“五四”儿童文学并非被动地接受西方资源,而是基于“五四”中国的文化语境有选择性地辨析中外资源,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二是“五四”知识分子整合中西儿童文学资源的话语实践介入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进程之中,其融通中西资源的“现代”立场确证了“五四”儿童文学的现代品质。当然,在接受的过程中,误读和曲解的现象始终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其吸纳外来资源为己所用的价值取向。然而,这一时期也存在着过分强调外来资源与历史价值同构的接受理念,致使这种思想显效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五四”儿童文学的审美意蕴的彰显,进而这种受限的艺术形式反过来制约了思想文化的传达。 ①戴渭清:《儿童文学的哲学观》,见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3页。 ②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先驱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为基石,找到了儿童与原始人、原始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由于成人与原始人殊异,原始人的文学自然就与成人文学有差异。这样一来,儿童文学的存在就有了合法性依据。 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儿童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794页。 ④[加]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⑤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6页。 ⑥[丹麦]安徒生:《我作童话的来源和经过》,赵景深译,《小说月报》第16卷8号,1925年8月10日。 ⑦郑振铎:《儿童读物问题》,《大公报》1934年5月20日。 ⑧仲密(周作人):《王尔德童话》,《晨报副镌》1922年4月2日。 ⑨周作人:《儿童的书》,《晨报副镌》1923年6月21日。 ⑩唐兵:《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1)郑振铎:《儿童文学的教授法》,《时事公报》1922年8月10日。 (12)[英]戴维·拉德:《理论的建立与理论:儿童文学该如何生存》,[英]彼得·亨特主编:《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13)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 (14)郭沫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7月27日。 (15)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第2卷第4期,1921年1月11日。 (16)荆生(周作人):《童话与伦常》,《晨报副镌》1924年2月28日。 (17)郑振铎:《〈稻草人〉序》,《文学周报》第92期,1923年10月15日。 (18)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文学》第7卷第1号,1936年7月1日。 (19)仲密(周作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晨报副镌》1922年3月12日。 (20)对于五四时期的“童心主义”倾向,很多研究者意识到了其成人主导的“非儿童本体”的实质。王泉根认为,“童心主义”立足点是成年人,“成年人通过观照童心进而观照人生的一种自慰、怀旧与排遣,是成年人看取人生的一种哲学态度”。(参见王泉根:《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朱自强则指出,“童心主义是从成人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而非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参见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21)[日]柳泽健原:《儿童的世界——论童谣》,周作人译,《诗》第1卷第1号,1922年1月1日。 (22)周作人、赵景深:《童话的讨论(四)》,《晨报副镌》1922年4月9日。 (23)沈泽民:《王尔德评传》,《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1921年5月10日。 (24)赵景深:《童话家之王尔德》,《晨报副刊》1922年7月16日。 (25)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晨报副刊》1922年4月6日。 (26)[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01页。 (27)周作人:《童话研究》,《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期,1913年8月。 (28)周作人:《古童话释义》,《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7号,1914年4月。 (29)冯飞:《童话与空想》,《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8号。 (30)茅盾:《最近的儿童文学》,《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31)仲密(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镌》1922年2月12日。 (32)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 (33)赵景深:《童话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第36页。 (34)赵景深:《白朗的〈中国童话集〉》,《文学周报》第196期,1929年7月。 (35)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文学周报》第105期,1924年2月5日。 (36)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沈从文全集》3,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4页。标签:安徒生论文; 文学论文; 儿童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周作人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赵景深论文; 他者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