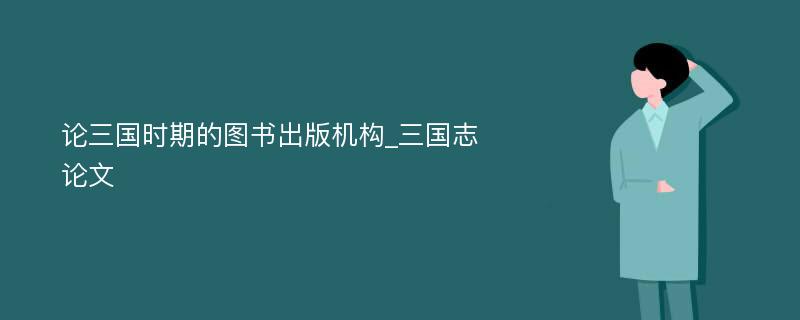
试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三国时期论文,机构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4)01-0032-06
秘书监与著作郎,是中国古代职官体系中同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的职官,三国时期则是它们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对于二者的研究,传统都是从职官制度本身或史官制度的角度进行。如各相关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百官志》或《职官志》、《通典》、《历代职官表》等,均是从职官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考述;而刘知几的《史通》等著作,则是以史官制度为切入点展开讨论。牛润珍的《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是近几年研究汉至唐初史官制度发展演变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就从三国时期史官制度发展的角度,对这个时期秘书监、著作郎等职的职掌、作用、隶属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制度研究,贡献颇多。
然而,从图书出版的角度对秘书监、著作郎等职的研讨,力度明显不够,将它们当成图书出版机构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章或著作,迄今无见。2000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瑞良的《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一书,其中也涉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官机构,并对它们在这个时期国家图书流通中的作用有所讨论,但主要是从“藏书管理机构”,而不是从“图书出版机构”的角度展开,且内容过于简略,实不足以说明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本文试图从图书出版机构的角度,将秘书监、著作郎等职,作为图书出版专职机构进行分析探讨,并通过从这个角度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三国时期图书出版发行的情况,及当时图书出版趋于活跃的原因。
一、曹魏的秘书、著作官
秘书监一职的设置,始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设有秘书监一人,职掌图书保管及古今文字,并负责考订古今图书在文字方面的异同。因其所典掌的图书文字都具有一定的保密性,故而称为“秘书”。其时之秘书监,还不是独立机构,其上级领导机关为太常,职能与东汉时期的东观类似,相当于皇家图书馆,主要是收藏东汉国家的藏书,与现实政治之间似无直接关系。其后,秘书监一职曾一度废罢,大概是由于桓灵时期政治腐败,国家政局动荡不宁,已无暇于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秘书监的再次恢复设置,则已经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其时三国鼎立已初现端倪。是年,曹操任魏王,在王府内设置秘书监一职,以原魏公府赞令刘颁、孙资为秘书郎,负责机要命令的撰拟。曹操恢复秘书监一职,主要目的当然不在于收集整理或保管图书典籍,而是以秘书监“典尚书奏事”,即由秘书监典掌尚书府文书,并撰拟机要命令,夺取了尚书的出令权,从而控制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的秘书监职能相当于后世的中书机构,是以杜佑认为此时之秘书监,“即中书令之任”[1](卷26,P732)。因此,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所恢复的秘书监,其功能主要是通过秘书监“典尚书奏事”的方式,控制政治决策中枢。当然秘书监也典掌图书典籍,但那只是其附带职掌。很明显,这时候的秘书监仍不是专职的图书编撰出版机构。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秘书监的名称、职掌一仍其旧,只是将刘颁、孙资所任之秘书郎改名为秘书左丞、右丞。同年十月,曹丕代汉建魏,改元黄初(220年)。魏朝建立后,曹丕下令改秘书为中书监,以刘颁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二人各加给事中。这样,刘、孙二人正式成为中书机构的首长,职掌中央中枢决策文书。中书监已成为曹魏中枢决策机构。这时候如果仍由它承担图书典籍的管理收藏,显然已经不太合适。因为就重要性来讲,后者显然不及前者重要、机密。因此,成立新的机构负责图书、秘记的保管,已成为现实的问题。
在改秘书监为中书监的同时,曹丕还成立秘书监“掌艺文图籍之事”[1](卷26,P733),专职负责典籍的收集保管工作。由于新置秘书监,与政治决策基本无涉而专职负责图书典籍,因此,可以认为曹丕新设之秘书监,才基本算得上专职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不过,这时候的秘书监,还未成为独立职官机构,而文属少府。其脱离少府成为独立机构,大约在魏明帝景初(237-239年)前后,时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2](卷13,P416)。王肃认为魏秘书之职,即东汉时期的东观,不宜仍隶属少府,此事载《初学记》卷十二秘书监条:“及王肃为监,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之职,安可复属少府,自此不复焉。”从此秘书监就脱离少府,成为独立机构。
以上只是对曹魏秘书监设置、变化等情况的大致概述。欲明了其具体职掌,还必须对其组织机构、组成人员稍作详述。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初置秘书监时,置令丞各一人,主要职掌为“典尚书奏事”,其中秘书令当为秘书长官,丞为长官助手。有迹象表明,起先可能只有一丞,直到魏文帝黄初年间才有左、右丞之分。据《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秘书丞条注:“文帝(曹丕)徵何祯,至为秘书郎,月余,祯因事,帝令向外曰:‘吾本用祯为丞,何故为郎?’按主者罪,遂改为丞。时秘书监尚未转,乃以祯为右丞。”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秘书丞原本只有一人,魏文帝曹丕本来欲用何祯为丞,“主者”却用为郎,文帝认为未尽其才,故而治“主者”罪后,将何祯由秘书郎改为秘书丞。由于原秘书丞并未迁转,故而只好任命何祯为右丞。又《三国志》卷二一《刘劭传》注引《庐江何氏家传》,明帝时有谯人胡康,号为神童,诏付秘书,使博览典籍,帝以问秘书丞何祯“康才如何?”则何祯所任为秘书丞,或者即秘书右丞的省称。这样,秘书监就由一丞,增加为左、右二丞。秘书监除令、丞为长官、副贰之外,尚有秘书郎、秘书校书郎等职。秘书郎一职,在东汉时,主要是在东观典校图书。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设秘书监时,即有秘书郎一职,时刘颁为郎。据《通典》,西晋时秘书郎的职掌为“掌中外三阁经书,校阅脱误”[1](卷26,P734)知曹操所设秘书郎及曹魏秘书郎职掌与此类似,由于秘书监长官主要参与中枢决策,故而其附带管理图书典籍的任务,具体就由秘书郎负责。至于秘书郎员数,《宋书·百官志》云:“郎四人,”《南齐书·百官志》则云“不著员数”,《通典》云“(晋)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看来,秘书郎有定员四人,在西晋时是不成问题的。《宋志》言有郎四人,说的可能是晋定员以后,《南齐书》言“不著员数”,则未敢肯定。如所周知,任何职官机构从产生到成熟都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三国时期的秘书郎,起初极有可能并无固定员数,但随着其职能的发展,秘书郎员数逐步相对固定。到晋武帝时,终于定员四人,此后南朝也基本以此为准。秘书校书郎一职,两汉均有设置,属兰台、东观属官,西汉兰台及东汉东观,既是藏书地方,也是著述的场所。校书郎一职,主要就是在兰台或东观负责校雠图书。两汉校书郎,人员组成似也不确定,如“后于兰台置令使十八人(注:秩百石,属御史中丞)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可见组成人员并不固定,他官亦可临时充任。正由于此,两汉校书郎名称似不确定,即“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中”。曹魏时正式定名为秘书校书郎,职掌当与两汉时类似,主要负责图籍的整理校订。附带指出一下,两汉时人多看重秘书校书郎一职,主要是由于它的荣誉性。该职晋、宋时似无设置。
曹魏时秘书监,主要是负责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及保管,作用性质与西汉兰台、东汉东观基本相同,属于国家文化事业机关,可以视为曹魏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由于秘书监所从事的职业对文化素养要求较高,因此能够到秘书监任职者,多为博学多识之士。如曾任职于秘书监的王肃、刘颁、杜挚、薛夏等人,均为饱学宿儒。是以,任职于秘书监所代表的崇高荣誉,仍为世人所瞩目。
尽管由于中书的崛起,使得秘书监远离了权力中枢,但仍无法完全脱离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据《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三年十月,魏文帝曹丕表首阳山为寿陵,作诏书、令曰:“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这表明曹魏秘书监仍负有保管国家诏敕政令副本的职责。在这一点上,它与尚书府、三公府的政治职能是一样的。再则,秘书监所负责的修撰、校正图书的职能,正是先秦时代史官政治职能的演变,与国家政治本来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注:参见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意义》等文。见氏著《乐师与史官 传统政治文化与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1版。)也正因为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故而才有王肃上表论争秘书监官员的政治待遇(地位),《通典》卷二六“秘书郎”条注引王肃表曰:“臣以为秘书职与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此陛下崇儒术之盛旨也。尚书郎、侍御史皆乘犊车,而秘书丞、郎独乘鹿车,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转台郎以为秘书丞、郎之本意也。”王肃上表认为应提高秘书监的地位,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即秘书监官员政治地位的的高低,是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重视与否的一个体现,可以反映“陛下崇儒术之盛旨”。
曹魏国家编撰出版机构,除秘书监外,还要提到著作郎。作为专职的著作官员,著作朗、佐著作郎(刘宋以后改为著作佐郎)也是国家出版编撰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郎一职,东汉时已有设置,其时国家图书尽在东观,故而使名儒硕学入直其中,撰述国史,称为著作东观。当时入东观著作者,都是以他官兼领。如班固、傅毅著作东观时的职官为兰台令史,陈宗则以睢阳令,尹敏以长陵令,孟异、杨彪以司隶校尉的身份,入东观著作。可见,这时的著作官还未成为专门的职官,专职的著作机构尚未成立。曹魏初年仍未见专职的著作机构出现,其国家编撰机构一直由秘书监独力承担。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始置著作郎官一人,负责国史修撰,其上级领导机构则为中书省。从现有史料来看,这时的著作郎官仍是由他官兼领,如卫觊以侍中尚书之职受诏典掌著作。这种他官兼领著作官的做法,甚至一直延续到曹魏末年。如应璩在曹爽秉政期间,也是以侍中典掌著作。[2[(卷21,P604)那么,曹魏时期的著作官员与东汉时是否完全相同呢?我们认为,在以他官兼领而无独立职官机构这一点上,曹魏与东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曹魏的著作郎官职掌更为明确,即专门负责国史的修撰,这是著作郎官走向专职机构的一个重要步骤。
除著作郎以外,曹魏还设置佐著作郎,以副贰著作郎,协助著作郎工作。据《初学记》卷十二“著作郎”条云:“著作佐郎,魏置,常贰著作,佐郎修国史,(与著作郎)初俱隶中书,谓之中书著作佐郎。”可见,著作郎与佐著作郎为曹魏时著作郎官,由于隶属中书省,故而又称中书著作郎、中书著作佐郎。虽同为著作官员,著作郎与佐著作郎的工作却各有侧重。据《通典·史官建置》,著作郎主要负责撰写,而佐郎则“主广采博访”,主要负责收集史料,提供给著作郎作为撰写依据。著作郎与佐郎之间的这种分工合作,协调行动,有效地保证了修撰工作的质量。佐著作郎员数,西晋时八人,估计曹魏时也有八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曹魏已设有秘书监典掌图书文籍,为何又要设置著作官员?据《初学记》卷十二“著作郎”条:“魏晋之际,中书兼国史之职,史官在焉。故魏代王沉为中书著作郎。”因此我们认为,虽然秘书监与著作官所掌之事均与著作图籍有关,但侧重点不同,中书兼修国史,具体承办人就是它属下的著作郎官,由于它专修国史,故而朝着专职史官的方向发展。而秘书监则重在典掌其他图书及诏敕政令等副本的收藏保管诸事宜,因此,与著作郎相比,其与现实政治依然保持着更多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强证。据《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注引《别传》:任嘏,字昭先,“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书怀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同书卷一五《司马朗传》载:司马朗曾上复五等爵等建议,裴注引《魏书》曰:“文帝善朗论,命秘书录其文。”凡此均可见,臣下行状及奏书文集等,秘书监均有收藏保管之责,而且常常是奉君主诏令行事。
尽管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旋涡,但秘书监、著作郎还是朝着日益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而文化色彩渐趋浓厚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包括图书编撰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做出较大贡献。曹魏时期在图书整理出版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秘书、著作官的相对独立是分不开的。据《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参诸同书卷二一《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可知《皇览》乃是儒家经典著作的汇编,其修撰乃是曹魏图书编撰出版业所取得一项重大成就,是一部能够反映曹魏图书出版水平的国家级项目。其具体修撰事宜,即由秘书监负责,据《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注引《魏略》:“魏有天下,拜(王)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220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八百多万字,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煌煌巨制,由此可见曹魏图书出版业盛况之一斑。如此巨著,若非有秘书监这样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组织协调实施,要在短短数年之间完成,是很难想象的。曹魏在图书编撰出版方面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中经》的修撰,《中经》即由秘书监完成。据《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又《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引王隐《晋书》云:“郑默,字思元,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郑默所修《中经》,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成书为了解当时图书存佚状况有很大帮助。另外,荀勖于西晋时在此书基础上编《中经新簿》,在《新簿》中,荀勖使用的四部分类法也很有可能就是对《中经》分类法的沿袭。另外,大凡在著述方面作出突出成就者,几乎都有任职秘书监或著作郎的经历。如卫觊曾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2](卷21,P612)。再如刘劭,除主修过《皇览》外,在法律、考课、音乐、辞赋等方面,均有大量著述,“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2](卷21,P620),刘劭也曾担任过秘书郎。
二、孙吴与蜀汉的著作官
同时期的吴、蜀两国,由于相关的史料较少,情况不甚明了。但根据情理推测,也应该有类似职官设置,特别是孙吴,职官设置与曹魏存在更多的相似性。
先说蜀汉,蜀先主刘备,从小“不甚乐读书”[2](卷32,P871),彭漾也曾讥骂其为“老革”[2](卷40,P995)。然实际刘备对于经学还是知其一二,如他早年曾追随名儒卢植,在徐州时也曾向郑玄问学。而在入蜀以后,更是表现出对儒学的重视。对于“耆宿学士”备加礼敬,并设儒林、典学校尉及劝学从事、典学从事等官,职掌文化教育。有记载表明,刘备对于图书文籍的收集整理也颇为重视。据《三国志》卷四二《许慈传》:“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据同卷诸传,时来敏为典学校尉,孟光为议郎。另外,谯周在诸葛亮时曾任劝学从事,“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学》之属百余篇”。因此,我们认为,蜀国的图书编撰可能就由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劝学(典学)从事等文化教育机构承担。
另外,有记载表明,蜀汉也设有秘书监之类机构,《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有云“后进文士秘书郎邵正数从(孟)光谘访,光问正太子所习读并性情好尚……”同卷《郤正传》“博览坟籍。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性澹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杨、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幅,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郤正传》所载,不但有秘书机构,而且职官设置次序井然,有秘书吏、秘书令史、秘书郎、秘书令四个级别,从郤正所习均与图书有关,似可推知,蜀汉的秘书机构也参与了图书文籍的管理收集等工作。因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蜀汉的著作官员包括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典学从事等文化教育官员及以秘书令为首长的秘书诸职,如果从不太苛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机构同时就是蜀汉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
东吴在图书编撰出版方面,也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这首先与孙吴统治者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图书典籍的编撰整理收集有很大关系。如孙权就非常重视史学,他除了注重对吴国国史的编撰外,对于继承人和部属臣僚读书学史,也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再如孙休,少年时代即从射慈、盛冲等人受学,即位之后不久即下诏兴学,史言孙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2](卷48,P1159)。除了统治者重视这一因素外,孙吴能在图书编撰出版方面取得较大成就,还与孙吴的图书编撰机构设置比较完备有一定关系。综考诸书,东吴职官设置,其中与图书典籍编撰出版有关者,有秘府中书郎、太史令、东观令、左右国史等。下面就依据相关史料,对这些职官略加分析。
(一)秘府郎、秘府中书郎:据《三国志》卷六五《华覈传》载,华覈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这是秘府郎。同书卷五三《薛综传附薛莹传》,莹“初为秘府中书郎,孙休即位,为散骑中常侍。……孙皓……建衡三年,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综合二传,秘府郎人选以“文学”充当,因此当与图书文籍有关,秘府郎有可能就是秘府中书郎的简称。(二)太史令、太史郎中:《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附莹传》,载右国史华覈上疏,其中有云“大皇帝(孙权)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同书卷六五《韦曜传》(即韦昭):“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覈、薛莹等皆与参同。孙休践祚,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综合二传,太史令之外,可能还有太史郎中,其职掌则是修撰国史。(三)东观令、丞:《三国志》卷六五《华覈传》,“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覈上疏辞让,孙皓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宜勉修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又同书卷六。《周鲂传》:鲂子处,“亦有文武材干,天纪中为东观令、无难督”。据《晋书》卷五八《周处传》:周处“仕吴为东观左丞。孙皓末。为无难督”。从孙皓所言及人职东观的要求可知东观令一职的设置,明显是沿袭东汉的做法,不但名称未作改变,就连职掌也基本相同。《晋书·周处传》言周处为东观左丞,与《三国志·吴志·周鲂传》所载为东观令略有不同,虽难以判定孰是孰非,但却透露出孙吴的东观不仅有东观令,而且有东观左丞一职,而根据其时职官设置一般规律,既有左丞,也应当设有右丞一职,至于令、丞之间,则有可能是长贰的关系。又据《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曰:“牧之在濡须,深以进取可图,而不敢陈其策,与侍中东观令朱育宴,慨然叹息。……”朱育官职是“侍中东观令”,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的特点,“侍中”为加官,看来孙吴的东观令有时还可以加侍中参与中枢决策,这说明东观令一职在政治上也相当有地位。(四)左右国史:此职主要是为修撰吴国国史《吴书》而设置。从孙权末年至孙皓时,先后参与《吴书》修撰者有丁孚、项峻、韦昭(即韦嚯,陈寿修《三国志》时,为避司马昭讳,而改为曜)、华覈、薛莹、周昭、粱广等人。[2](卷53,P1256)以上诸人或亡或黜,历久未成,最后实际由韦昭独自完成,但仍剩下述、赞等部分未就,韦昭即因事下狱被杀。其中韦昭、华覈、薛莹诸人,曾任左、右国史之职,有材料表明,左、右国史似不能独立成职,而一般用作加官,如韦昭在孙亮统治时期奉命修撰《吴书》,官太史令;孙休即位后,“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时昭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孙皓即位后,“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2](卷65,P1462)华覈,“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其余诸人,在参与修《吴书》时,也都有不同官职。因此,左、右国史之职,当是领官或兼官,另外也有迹象表明,并非每个参与者都有这个加官或兼官。
三、三国秘书著作官在图书出版史上的意义与局限
以上是对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有关图书编撰出版机构的简略考述,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宁,三国之间军事斗争连绵不断,三国国内的政治风波也是不时或起,但三国的统治者并未因政治的动荡,就完全漠视礼乐教化,他们充分认识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2](卷48,P1159)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对于包括图书编撰、收集、整理在内的文化教育事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三国都设置有相对专业化的职官机构,如曹魏的秘书监、著作郎;蜀汉的儒林校尉、劝学从事等;孙吴的东观令、太史令、左右国史等,对各自国家图书文籍的收集整理、编撰出版,都程度不同的做出了贡献,象曹魏修撰的《皇览》、《中经》,孙吴的国史《吴书》等,都是较大部头的图书著作,它们的修撰完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修撰者个人努力的结果,但与秘书监、著作郎等图书编撰出版机构的组织协调也有关系。如孙吴史学家韦曙,修撰有《吴书》、《国语解》等史学名著,固然体现了他突出的史学才华,但他任职于东观,领左国史的经历,也是他完成这些著作的重要条件。因为韦氏修史所引据的大量文献典籍,并不是仅凭个人力量所能收集到的,而必然要参考东观、太史、秘府等国家藏书机构所收之典籍。
当然,我们也承认,无论是曹魏的秘书监、著作郎,还是蜀汉、孙吴的儒林校尉、东观令、太史令等官职,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编撰出版机构,它们还承担文化典籍事业之外的其它政治职能,有些机构、职官在某些特定时候,政治职能还远大于它在文教方面的职能。它们所负责保管、收集或整理的图书秘籍,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国家发布的诏敕政令,从而与现实政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从职官隶属关系来看,这些机构也很难完全摆脱与现实政治的干系。如著作郎一职,就隶属于中书省,中书机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中央政治决策的核心所在。至于以秘书著作官员带侍中之类的加官,以参与政治决策的情况,也可表明这些官员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另外,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包括图书编撰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本身也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教化从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施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正是基于这一种认识,统治者对于图书的编撰出版传播,始终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和兴趣,这样就必然考虑设置相关的官僚机构进行管理。三国时期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尽管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职编撰出版机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分工的日趋细致化、专职化,三国时期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也必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两晋时期国家编撰出版机构较之三国时期更为完备、成熟,正是这个发展的必然结果。
收稿日期:2003-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