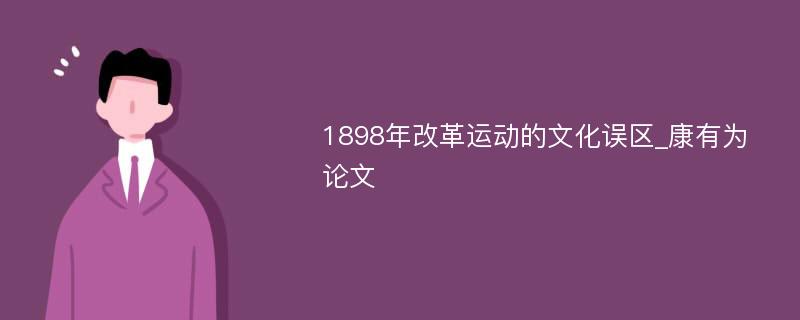
戊戌变法的文化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误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其结局是悲壮而耐人寻味的。由于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办报刊、立学会、开学校,充满了近代文化气息,因而被后人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可以说,向西方学习是戊戌维新的主题。然而,由于戊戌维新没有经过如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沉思和文化兴盛,难免出现囫囵吞枣的现象,甚至走进了文化追寻的误区,这是值得深思而未引起注意的文化研究课题。
“不中不西”:西学中化的急就之章
比照当前成功进行着的改革,返观戊戌变法,不难看出改革的成功要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正确的文化理论导向。成功的改革运动的领袖总是那些杰出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以创造性的理论教育群众,使群众围绕改革产生强固的凝聚力;并能以自己的洞察力烛照改革前途,带领群众前进。而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理论并不成熟,导致他们所能影响的群众层面狭小,在政治舞台上很难起扭转乾坤的作用。
当时的中国,内有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以及与此基础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文化心理,外有列强的鲸吞蚕食与经济倾销。戊戌维新派没有时间对当时的内外情况作深观细察,便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提出了自己的变革理论,这就注定了维新派不可能有完整、先进的思想体系,而是呈现出新旧交替、斑驳杂糅的特点。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思想界“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灭裂,固宜然矣。”维新派急不饥食,对新学还来不及加以认真消化,对旧学更无暇甄别筛选,就谈不上居高临下,取精用宏了。维新派从功利主义出发,古今杂糅,造成了一个“不中不西”或曰“即中即西”的思想庞杂体系,造成了西学中化急就之章的致命弱点。
这种“不中不西”理论运用起来,总不免苍白无力,流弊丛生。梁启超承认这种理论最易产生两种流弊:其一,以新学新理缘附古义,必有牵强附会之处,最易导致国民产生不正确的观念。例如,以古代经典中的某些词句相附会立宪共和,认为这种制度是我国所固有的国粹,其实这种制度在欧美也只不过起于数百年前,这种附会将使人的思想局限于所附会的文句,混淆了诸如“周召共和”与资产阶级共和的本质不同。其二,凡所倡导的新学新制,都托为古人已有,“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若诸经皆无可比附,则明知为真理也不敢服膺了。所以梁启超宣称:“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这个认识是有深度的,可以说是揭出了维新派文化误区的疮疤。
维新派所杂糅的“不中不西”文化理论,在表述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量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及西方自然科学的名词和概念,尤其是袭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名词、概念,往往给人带来文化困惑:是按这一名词概念的愿意,还是按它所比附的事物的性质去说明这些概念的涵义,使人难以认定作者的原意和确定它们的范畴,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偷换概念的误区。“不中不西”理论的另一表现就是在维新派的理论系统中,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相调和。维新派用自然科学名词(如以太、电等)解释“仁”和“不忍之心”,产生了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哲学基础的芜杂导致理论的贫乏,从而使得理论没有起到团结更多要求改革人士的作用。
维新派这种“不中不西”的理论表明,他们并未处理好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是半生不熟的。首先,维新派的中西结合模式在整体上始终没有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维新派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以自身的文化基因为核心和立足点来吸收西方文化,力图在吸收西学的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去过滤西学的内容,他们始终没有在整体上超越传统意识。这种中西结合模式的后果并不美妙,因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取决于西学的渗透度和冲击度。中国近代维新派不仅面临西学在观念价值方面的冲撞,而且在引进过程中起码面临东西方文化4 种强硬的挑战:一是面临西方文化基因的挑战,即如何从思维方式本身改造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取其皮毛,构成思想意识中的表层结构。不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基因成份,而仅仅用中学思维方式的旧模式去包装西学的新理论,其结果是“旧瓶装新酒”。二是面临自身传统文化基因的挑战,无法突破儒佛道三教所构成的意识深层网络,因而不可能形成类似西方的非人格化法律运作体系,而这套理性机制恰恰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三是西学所孕育出来的制度的挑战,没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做后盾,只是形式上引进新名词,结果必然不对号。四是面临本身文化传统源流中产生出来的制度挑战,深层观念难变,由观念引申出来的制度更难变,两者互相牵制,导致近代中国制度变化的幅度甚小。
其次,维新派“旧瓶装新酒”式的中西文化结合,注定了这种“四不象”文化失败的命运。近代西方文化是大工业文明的产物,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与儒学、道学及佛学是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化现象,因而无法组装到与传统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以儒学为主的文化之中,如果硬性安装,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如此,近代化的变革要逐步淡化对孔子和儒学的信仰,康有为等维新派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不仅使维新志士陷入困惑之中,而且也限制了自己思想的发展。
“托古改制”: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
戊戌维新志士深感中国改革的艰巨以及传统儒学的潜移默化作用,于是他们便以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的“托古改制”方式,来进行维新变法的理论建构。“托古改制”既反映了维新志士在思想上对旧势力的抗争,也表明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的妥协。“改制”是斗争,也是追求的政治目标;“托古”是妥协,又是调和手段,并以“托古”为手段达到“改制”的目的。戊戌维新派思想上的妥协色彩,虽然使维新运动减少了一些反对派,增加了一些支持者。好像达到了预期要求,所以梁启超在评价《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影响时,形象地将它们分别比作“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与“火山大喷火”。
自然,康有为等维新派有关“托古改制”的理论确曾吹皱清末思想界一池春水,给变法维新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并成为团结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士人的旗帜。但严格审视“托古改制”理论,就会发现维新派并没有真正做到区分儒学中的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而是怀着一种对儒学在西学冲击下陷入困境的忧虑与依恋。这样,他们就不可避免地祭起了同样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同一儒学体系中的今文经学,去反对古文经学,力图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然而,食古不化,浓重的封建气息最终窒息了革新精神的生长点。在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两部重新解释儒学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他为了达到“托古改制”的目的,不惜采用曲解、牵强附会、比附,甚至捕风捉影等种种武断方法打破古文经学的统治地位,树立今文经学的理论权威。从形式上看今文经学取得了胜利,而在方法上却走进了强史就我的文化误区,犯了科学家之大忌。
在中国,自古以来儒学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是门户相望、流派纷呈,但总体上仍然沿着封建主义文化轨道运行。纵观清朝期,读书人都通过学习古文经学而得到高官厚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出版,正是为了发古文经学之伪,明今文经学之正,猛攻刘歆所倡导的古文经学,其目的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不在于探讨“经学”,而在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即为了扫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在破除顽固派保守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能变”等观念,为改革运动开辟道路时,所使用的武器,也是从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武库中找出了“三统”、“三世”说。“三统”“三世”说合起来,即证明社会是循环往复不断向前发展的。他在号召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训诂考据之学和扼杀人们灵性的宋明理学中解放出来时,不是用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启迪大家,而是耗费心血,用牵强附会的手法,编撰一本《新学伪经考》,用以证明千百年来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古文经,原来是汉儒为了讨好王莽而伪造的假经,不是孔夫子的真经,因而应屏弃这种“灭人灵性,空疏无用”的“正宗”儒学。他在给人们树立勇于改革、弃旧图新的权威楷模时,一不举华盛顿,二不举拿破仑,却抬出人们心目的圣人——孔子,说孔子是积极主张改革的祖师。所以,康有为还是从传统儒学中吸取力量反对传统儒学中某一派别或集团,以儒经反对儒经,尽管他讲的今文经学和西汉的今文经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而不可能彻底地反对传统儒学。这使得被严密包裹在传统文化符号之中的近代化主体意识,在当时甚至不易为人们所觉察。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开宗明义,说明先秦各家学派为了宣传自己所向往的社会制度,都托为古代所曾实行过,假借古已有之来加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例如墨子假托夏禹,老子假托黄帝,许行假托神农,而后方能入说。春秋战国,各派学者纷纷起来创教立义,改制立度,百家争呜,思易天下。先秦诸子热烈宣传自己的主张,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社会。但是当时的社会流俗是“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一味迷信古代,颂古非今,所以诸子百家只有假托古代,才能推演自己的论点,争取人们的信服。康有为托古的目的,也无非是发挥今文经学“绌周王鲁”的论点,以大量的古代史料证明这种“尊古贱今”思潮在战国时曾风行一时,在后来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因而“托古改制”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从而为他的托古变法提供了远溯洪荒的历史根据。
康有为之所以到了中国近代还要采用“托古改制”这种手法,乃因当时中国仍是一个传统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尊古贱今”这种封建社会的思潮在晚清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康有为根据民族的世俗心理,认为只有托古才能取得人们的敬重与信服。康有为还认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说明他既想效法诸如王安石依托《周礼》而变法,也用附会经义的办法封住反对者的嘴巴。
康有为通过考辨,认为中国古代改革思想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一反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周公旧作的说法,确认“六经”都是孔子亲手所作。他认定孔子为了创立儒教,提出了一整套所谓尧、舜、文武等政教礼法范式,并且亲自作了“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典章,而自居为“改制之王”的地位。这样,孔子在康有为的笔下就成了“托古改制”的维新主义者,而不是古文经学家所说的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者。既然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孔子的“六经”又是托古改制的范本,那么,康有为就似乎顺理成章地证明了他本人主张维新变法,正是对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其实,考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际状况,可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不管是顽固派、洋务派、文人学士、平民百姓,还是维新派,“六经”与孔子的形象都是不可动摇的,是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沉淀形成的。因此,“六经”与孔子的形象理所当然是封建主义的文化象征。
康有为曾经在其“托古改制”理论中注入了西方进化论的清流,但由于其理论本身固有的封建主义的浊流,早已稀释和吞没了这涓涓细流,这样就不可能把当时的中国引向维新变革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轨道,从而导致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在当时根本无法形成共识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解释的“正邪”之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仍在封建儒学的范围里打转,并不能起到团结维新派变革人士从事革新运动的作用,反而使维新派陷入上有反对派(顽固派、洋务派)剑拔弩张的敌视,中有文人学士的诽谤,下有平民百姓的误解,几至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说明,“托古改制”理论—没有统一维新派的思想,二没有达到避免顽固派冲击变法的目的,三没有起到动员青年士子投身变法事业的作用。因为康有为学习西方,倡导改革,捧出的还是儒家经典,而不敢理直气壮地为新思想呐喊,因而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那艰涩的文字,隐晦曲折的寓意方式,就难于吸引那些急于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的那样,“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
中国历来搞“托古改制”的人虽然动机不是复古,但由于托古的内容如儒家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也无非是原始社会遗留的史影,所以改制的人愈是把这种理论推向极致,却往往反而将社会退回到历史的起点。同时,康有为借用孔子亡灵的办法,给他自身也带来了严重后果。这就是他对中国封建传统也无法进一步批判,以致他在即将突破传统又未突破传统的门口止步不前,加上他那过于自负的性格,终于没有迈出这最后的一步。马克思曾经对搞“托古改制”的人有过深刻的评判:“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康有为正是穿着孔圣人的服装,打着孔圣人的旗号,借用孔圣人的语言和战斗口号,演出戊戌变法的新场面。
“西学中源”:近代文化源流的错位
维新派为了变法维新,就必须借助具有近代化意识的西学,但在如何认识和向国人宣传西学这个问题上,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所谓的“西学中源”说。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一样,“西学中源”说也是19世纪中后期的时代思潮。“西学中源”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初的黄宗羲和康熙皇帝。鸦片战争以后,邹伯奇、冯桂芬倡导在前,洋务派呼应于后,70年代、80年代大行其道,90年代盛极一时。郭嵩焘、曾纪泽、张自牧、郑观应、陈炽、薛福成等大抵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无不持“西学中源”说。而且,这种思想不仅没有因戊戌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决裂而受到批判,反而倍受维新派的青睐。
维新派说西方许多事物如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平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而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是源于中国。如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的:“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所创”;“选举者,孔子之制也”;“儒是以教任职,如外国教士之入议院者”。“凡西人所号奇技者,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泰西各艺,皆起于百余年来,其不及我中人明矣”。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声称,中国文化传统早就提出了许多现代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有些东西甚至比西方还要发达。梁启超作这样的断言,虽说有可能是为了便于文化的引进和说教的便利,但细考当时的社会思潮,便可知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文化传统作这种肯定,梁启超当然也不能例外。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所强调的内容,最能说明他在对西学的广泛接受中,看到了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威胁,因而产生了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心的需求。
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看,“西学中源”说是华夏中心主义的变态,是一种错误观念。在华夏中心主义这个顽固的民族心理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摧毁之前,它是引进西方文化的必要的阶梯;在复古守旧的保守心态没有受到彻底清算之前,它又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巧妙策略。但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引进的西方文化,却往往受到严重的扭曲,甚至面目全非。戊戌维新派鼓吹“西学中源”说的目的,是为了“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亦即所谓“新学”。但是,维新派建立的“新学”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美好预想。他们所成就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新旧杂糅、中西牵合、不中不西的怪胎。在这个所谓的“新学”系统中,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化和西化了,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原则则被儒学化和古董化了,它们与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地主阶级“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之间的尖锐对立被填平了。
维新派构筑“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思想体系的计划之所以造成他们汗颜的结果,除了阶级的局限性及梁启超后来所指出的对西学知识贫乏等原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既不承认文化的时代差别,也不承认文化的民族差异。不承认文化的时代差别,就不可能真正分清何为旧,何为新,当然更谈不上会通古今;不承认文化的民族差异,就不可能真正分清何为中,何为外,当然更谈不上包罗中外。勉强为之,其结果只能是新旧杂糅、中西牵合。而这一切,又都可归结为“西学中源”说的谬误。
综上所述证明,在社会改革的关键时刻,一方面要使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启蒙同步进行;另一方面,文化变迁必须追求时代新潮流。如果单纯局限于从传统文化中寻章摘句,那么,这样的变革只能是失败的结局。
标签:康有为论文; 梁启超论文; 儒家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孔子改制考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学伪经考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