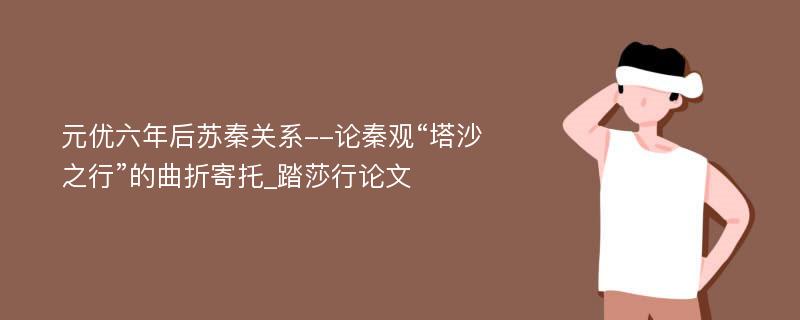
元祐六年后的苏、秦关系及其他——试论秦观《踏莎行》的曲折寄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年论文,曲折论文,试论论文,寄托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3)06-0103-08
绍圣四年(1097),被贬郴州的秦观作《踏莎行》,哀莫大焉: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1](p.848)
黄庭坚跋此词说秦观当时是“多顾有所属而作”。(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卷十二,《山谷集》。)有所属的意思是有所寄托。这首词中的寄托是什么呢?纵观全篇,上阕的意思颇为直白,但抒其寂寞失意而已;而下阕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历来被看作是“淡语之有情者”,[3](p.388)是全词最动人的地方。《冷斋夜话》云:“少游到郴州作此词,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3](p.206)王国维却认为:“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3](p.4245)显然不认为这两句有什么深意。
《蓼园词评》按曰:“次阕言书难达意,自己同郴水自绕郴山,不能下潇湘以向北流也。语意凄切,亦自蕴藉,玩味不尽。”[3](p.3048)北流当然意味着重新回到京都官场,秦观向往“北流”而不能,故戚戚;今人胡云翼说苏轼之所以喜爱这两句,是因为苏轼自身的贬谪经历,使他“有足够的经验来体会秦观这种失望和希望交织的心情。”[4](p.103)胡先生只是笼统地将这两句的意思表述为:原本绕着郴山的“郴江也不耐山城的寂寞,流到远方去了”[4](p.103)而秦观自己却不得不留在这片黄昏的春寒之中。以上说解在郴江到底是否北流下潇湘这一点上,是矛盾的。但我想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以为更重要是,如此这般的“戚戚之语”,苏轼怎么会“绝爱”之呢(注:苏轼以为“不应戚戚徇无己之悲”([5]卷七十五《答刘巨济书》。他曾在给钱穆父的信中说:“愁人泪眼”之句,读之惘然。公达者,何用久尔戚戚”([5]补遗《与钱穆父五十上》之三十四);他多次在自己的诗文中表示自己虽历经坎坷而“未尝戚戚”。他在给王定国的信中说:“定国必不以流落为戚戚,仆不复忧此”。[6](p.1513)。)!
苏轼一生坎坷,受他牵连的朋友,何止秦观!苏轼却认为“定国为某所累尤深”[6](p.1513),他在“王定国诗集序”中写道:“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幽忧愤叹之作盖亦有之矣,特恐死岭外,而天子之思不及报,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平!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其人之浅也。”[6](p.318)当苏轼“自恨其人之浅”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王定国的人格怀有真挚的敬意,对王定国的友情充满了感激。据说苏轼读《踏莎行》后,曾说“吾负斯人”。[3](p.2530)以苏轼对友情如此深刻的理解,秦观若只是悲悲戚戚,就不太可能令苏轼感喟如此!
秦观与苏轼的交往,始于熙宁七年(注:当时二十七岁的秦观“闻嵋山苏公轼为时文宗,欲往游其门。未果。会苏公自杭倅徙知密州,道经维扬便“预作公笔语,题于一寺中”。据说当时苏轼“见之大惊,及晤孙莘老,出先生(指秦观)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必此郎也。’遂结神交”。《秦谱》中的这段记载,无从证实。[7](p.1640)熙宁七年甲寅条下引《秦谱》)。)。苏轼有一段文字说明自己认识、赏识秦观,是在秦观尚未发达之时。“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总集类,第二百二十七,《文章辨体汇选》,《答李昭玘书》。)。元丰元年,三十岁的秦观入京应试不第,退居高邮,杜门却扫,颇为惆怅。苏轼有《和参寥寄秦观失解诗》一首,叹“回看世上无伯乐”[8](p.904)云云,并给秦观写了一封信,说:“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耳。”[6](p.1534)这是苏轼给秦观的第一封信,此前秦观已给过苏轼好几封信,但苏轼因“既冗懒且无便,不一裁答”。[6](p.1534)而在秦观落第,情绪最坏的时候,苏轼却给了他真诚的关怀。当时的苏轼在秦观的心目中,绝不仅仅是一个长自己十三岁的朋友,“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7](p.135)对秦观说来,苏东坡就是晦暗生活里的一束光啊!来自苏轼的安慰,使颇感沦落的秦观感激涕零。第二年,“乌台诗案”事起,苏轼九死一生。在苏轼被贬黄州的这段时期,秦观又有过一次落第的经历。
元丰七年秋,自黄州量移汝州的苏轼[7](p.596),在真州给王安石写信推荐秦观:“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其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一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6](p.1444)。”当时苏轼自己尚处于“盘桓江北,俯仰逾月”(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七十三《回苏子瞻简》。),立足未稳的境地,却已经在关照秦观了。他希望借重王安石的人望、及其在朝的故旧僚属,使秦观得显于世。秦观中进士是元丰八年春天的事[7](p.1673),而苏轼在给王安石的这封信中,却已经称其为进士,未免“虚美”之嫌。北宋对进士殿试后的等第有严格的五等之分,进士及第与同进士出身犹判然有别(注:《宋史》选举二:是秋,四方士集行在,帝亲策于集英殿,第为五等,赐正奏名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同出身。第一人为左宣教郎,第二、第三人左宣义郎,第四、第五人左儒林郎。第一甲第六名以下并左文林郎,第二甲并左从事郎,第三甲以下并左迪功郎。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第三人赐同进士出身,余赐同学究出身。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入伍等者,亦与调官。),何况是对一个已数番落进士第的人呢!苏轼在当时已经远离权力核心的王安石面前称秦观为高邮进士,与官场的俗套不能说完全无关,但更能说明的倒是苏轼“爱才”而不遗余力的风格。
元丰八年六月戊子(26日)司马光、范纯仁等力荐二苏。[10](p.677)十月,苏轼被从登州召还京师,任礼部郎中,弟弟苏辙也于此时升任右司谏。第二年(元祐元年),苏轼在“免试为中书舍人,仍赐金紫”[10](p.711)之后,又入翰林。这一年秋,司马光去世,朝廷命程颐主司马光丧事,苏轼对程颐泥行古礼的作法颇不以为然,就公然嘲弄程颐与其门生。程颐要以素馔供奉,苏轼偏要准备肉食供品。于是乎程颐及其门下范祖禹等食素,而苏轼及秦观、黄庭坚等食肉。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与程颐为首的洛党,从此结怨立敌。程颐的门下朱公掞为御史,“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苏子瞻语人曰:何时打破这敬字?”[10](p.736-736)苏东坡的口莫遮拦,深深地得罪了洛党。
尽管政见上的干戈最初表现在上述互不相容的个性冲突中,但洛党却认为,苏轼之所以要与程颐唇枪舌剑,是因为当时的宰相吕公著“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口诋之云。”[10](p.734)不管这是他们以己度人,还是胡乱推测,“进退人才”,恰恰是这一变革时期最重大的政治问题。
元祐二年,苏轼在试馆职策问命题时,被洛、朔两党的朱光庭、王岩叟等罗织了讥讽祖宗的罪名而数遭弹劾(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四,12条。是日,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策题不当,累有章疏……”。),更有曾被苏轼斥为“聚敛小人,学行无取”[6](p.828)的监察御史赵挺之奏曰:“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薄之甚者,力加论焉。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定国);取其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其比。……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紧接着赵挺之又攻击苏轼的学问类战国纵横揣摩之术,又说苏轼专门喜欢讨论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的篡逆之举云云。赵挺之颇为耸人听闻地说:“今二圣在上,轼代王言,专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国迟速之术,此何议也!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设心,罪不可赦。轼设心不忠不正,辜负圣恩,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11](p.9915)
此后,侍御史王觌也上了差不多意思的奏折,他说:“轼自立朝以来,疚愆不少,……若使量狭识暗、喜怒任情如轼者,预闻政事,则岂不为圣政之累耶!”他认为,对苏轼这样的人“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意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并建议把苏轼调离京城。[11](p.9866)
但太皇太后高氏在苏轼本人坚乞“补外”的情况下,依然对弹劾苏轼的傅尧俞、王岩叟等说:“此小事,不消得如此。”王岩叟坚持指陈苏轼的策问选题,太皇太后竟在帘中厉声说:“更不须看文字也”!甚至说要将弹劾苏轼的人和苏轼一起外放。于是执政的范纯仁等出来为苏轼说话,太皇太后才消了气。[10](p.790-791,763-764)
苏东坡的喜怒任情,他的文采,他对长于辞华的人的偏爱,以及太皇太后高氏对他的偏爱,使他在身边聚集了许多才子(注: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团》:绘苏轼等有姓名者十七人雅集西园之状,米黼为之记。[10](p.852))的同时,成为元祐党争的焦点人物。
由于同处京城的时间很少,苏轼与秦观在这一时期的交往并不多。秦观于元祐三年九月到京城应孙觉、苏辙等主持的制科考试,被人在“了无事实”的情况下“诬以过恶”,[7](p.1690)只好非常失意地回到了蔡州,继续当他的蔡州教授。元祐五年五月,秦观又一次赴京,让他去当太学博士,但不久,又因为洛党右谏议大夫朱光庭的劾奏,被免去了这一任命。六月,秦观终于被命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心境为之一畅[7](p.1700-1701),而苏轼此时正在杭州任上。元祐六年三月苏轼被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这一年的七月,秦观由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迁为正字。此时洛党的朱光庭、贾易等因为朔党的刘挚当了宰相便都归附了朔党。贾易是个自以为是的偏执狂,[11](p.11062)元祐二年八月,他就在试馆职策问命题上攻击苏氏兄弟,并将矛头指向反对如此罗织文字狱的文彦博与范纯仁,触怒了太皇太后高氏。在宰相吕公著极力捍卫其发言权的情况下,他才未被高氏“峻责”。[11](p.9928)此番再用贾易为侍御史,无疑给羽翼正丰的朔党领袖刘挚提供了对付苏氏兄弟的枪手。(注:《淮海集笺注》附录一,秦观年谱,元祐六年七月纪事引苏诗总案卷三三云。)。
贾易此番对苏轼兄弟的攻讦连刘挚都觉得可骇。[11](p.11062)苏辙被他说成是“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被言殄行,甚于蛇豕”,“挟私怨,蔑公义”等等,又说苏轼“趋向狭促……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真倾危之士也!”还攻击道:“轼、辙不仁,善谋奸利,交接左右,百巧多门”。[11](p.11054-11056)大有睚眦必报、磨牙吮血之势。贾易还附带弹劾秦观,以加重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11](p.9915)的罪名。
秦观为正字,是赵君锡举荐,而贾易弹劾秦观时,赵君锡却附和贾易曰:“臣前荐观,以其有文学。今始知其薄于行,愿寝前荐,罢观新命。臣妄荐观罪,不敢逃也。”不久赵君锡又上一疏,说:“二十七日,观来见臣,言贾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党类’,此意是倾中丞也。今贾之遗行如观者甚多,中丞何不急作一章论贾,则事可解。观之倾险如此。乞下观吏究治之!缘臣与贾易二十六日弹观,才一夕而观尽得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密如此!观访臣既去,是日晚有王遹来,苏轼之亲也。自言轼遣见臣有二事:其一则言观者公之所荐也,今反如此;其二则两浙灾伤如此……臣以为观与遹,皆挟轼之威势,逼臣言事,欲离间风宪臣僚,皆云奸恶。乞属吏施行。”[11](p.11050)贾易弹劾苏氏兄弟的疏奏虽然被太皇太后高氏“封付吕大防、刘挚,且谕令未得遍示三省官”,[11](p.11058)而时任尚书右丞的苏辙却不知通过何种途径知道了疏奏的内容。他意识到贾易来者不善,便要屡遭暗箭的兄长有所防范;但苏轼却在“一夕”[11](p.11050)之中,把弟弟透露给他的不该外传的信息又传给了秦观。对秦观来说,知道这一内幕后如何举措,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自卫的问题了。按说,为了不至于给苏氏兄弟惹麻烦,他应该装作毫不知情才对;而他,居然马上就去找不久前还推荐过他的赵君锡,以为自己可以说服赵君锡,让赵君锡反过来弹劾贾易。这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天真,还不如说他是一下子乱了方寸。当时秦观已年过不惑,眼看着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正字之职又要保不住,他沉不住气了,竟没有想到,自己找台谏官员疏通,对正处于朔党睽睽冷眼之中的苏氏兄弟来说,等于是授人以柄。
早在元祐二年,贾易就曾利用言官可“以风闻言事”[12](p.49)的条则,攻击“苏辙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当时,深谙官场守则的苏辙,立刻反击说:“臣非台谏,凡易所言,不敢条析论奏,唯有言臣一节,理当辩明。易虽顷为谏官,今出守郡,于条不当复以风闻言事。”结果是“御史交章论易‘人才庸下……附下罔上,背公死党……,意欲盗敢言之名以欺中外。奸险之心,欲盖弥彰’,”贾易被看作是一个“谄事程颐”的小人。[11](p.9878)这一次,贾易卷土重来,本想以元丰八年五月苏轼题诗扬州僧寺的事情,再搞一次“乌台诗案”式的文字狱。但他的疏奏却使“太皇太后不悦”。太皇太后发话后,首鼠两端的刘挚说:“轼虽无事,然却有赵君锡所陈王遹云云乃实迹,故两罢之。”[11](p.11060)党争到了此时,即使君子亦难免小人之举了。
被太皇太后封付刘、吕的疏奏的内容,因二苏而外传,当然会使得苏氏兄弟的政治品格受到反对派的强烈质疑。二苏的对手很多都是那些出自理学家门下的、以品节高尚自我标榜的政客,朝廷在他们眼中不过“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13](p.141)其中有不少人将“视二苏如深仇”的贾易,看作是“刚果敢言”的“直臣”,[11](p.11060)而苏轼即便有太皇太后护着,副相刘挚依然敢说:“轼高才,使少循步骤,谁能过之者?夫知自贵,盖有道者之事,古人所难也。”刘挚用的是虚拟语气,言下之意当然是说苏轼不守官场的规矩(步骤),而且不自重,所以称不上是“有道者”;刘挚说那些支持贾易的人“各自伸其私耳”,[11](p.11060)他自己又何尝不如此呢?苏辙、苏轼在为自己辩白的奏折中,不能不承担“朝廷文字”外泄的罪责。但是同时,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用当时官场的道德标准审视自己,为的是能给自己的不“循步骤”辩护。比如苏轼对自己要王遹去找赵君锡的事情是这样解释的:“臣与赵君锡,以道义交游,每相见论天下事,初无疑间。近日臣召赴阙,见君锡崇政殿门,即与臣言老缪非才,当此言责,切望朋友教诲。臣自后两次见君锡,凡所与言,皆忧国爱民之事。……臣既见君锡,从来倾心,以忠义相许,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义,尽言无隐。”苏轼还说:“臣知遹与君锡亲,自来密熟,因令传语君锡,大略云:‘台谏、给事中互论灾伤,公为中丞,坐视一方生灵,陷于沟壑,略无一言乎?’臣又语遹说与君锡,公所举秦观,已为贾易言了。此人文学议论过人,宜为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遹与赵君锡言事,及与秦观所言,止于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苏轼的自劾状说自己之所以把贾易弹劾秦观的事情告诉秦观,是希望他能够“力辞恩命,以全进退”,但根本不知道秦观跑到赵君锡那儿去说了些什么。我想这是事实。如果他知道秦观会跑去找赵君锡,怎么会把弟弟向他透露的消息告诉秦观呢?这不是要让自己的兄弟担一个泄露朝中机密的恶名吗?苏轼为弟弟辩解说:“臣本为见上件事,皆非国家机密,不过行出数日,无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议论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锡,欲其一言以救两浙亿万生齿,不为触忤。”他还解释说:“右臣既备位从官,弟辙以臣是亲兄,又忝论思之地,不免时时语及国事。”总之,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苏轼也只能承认自己“不合辄与人言”[6](p.935-936)。苏辙尽管从来就知道哥哥难免“祸从口出”(注:孔凡礼《苏轼年谱》:“辙以慎于口舌相戒”。并引涵芬楼《说郛》卷十二所引文字曰:“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子由晦默少许可,常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好人,此乃一病。’”),但出了官场,两兄弟之间无话不谈的亲情,毕竟是他看得最重的东西。一向谨慎的他,在这一风波之后,也在奏折中说:“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实缘臣退朝多与兄因语次遂及朝政。臣非久,亦当引咎请外。”[11](p.11059)
值得注意的是,假如没有秦观的失态,苏氏兄弟真不至于如此尴尬。王遹去找赵君锡,虽然也会引起赵君锡对二苏的猜测,但猜测毕竟不能作为苏辙一夕之间泄露朝廷文字的凿凿证据。秦观跑去游说赵君锡,等于将苏轼的软肋暴露在他的对手出拳之际,苏轼挨了狠狠的一拳,却怨不得别人,还要承担过错以保护弟弟苏辙,而苏辙也尽力担当以淡化哥哥所犯的低级错误。本来,秦观在整个事件中,不过是一块强加于苏轼莫须有罪责之上的小小砝码,但最后,他却成了二苏犯规的直接证据,成了贾易们落败之际堂皇退场的台阶。他在苏轼和苏辙心目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风波过后,秦观罢正字,[11](p.11073)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苏轼在给他和秦观共同的朋友参寥子的信中说:“少游近致一场闹,皆群小忌其超拔也。”[10](p.988)苏轼没有跟他的朋友们说自己此番外放,罪在莫须有。更没有在朋友们面前埋怨秦观给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麻烦。但显然,秦观成为事件以如此方式结束的主要原因,他的节外生枝,在苏轼心灵深处引起的波动,远远超过了贾、赵凶狠的弹劾。苏轼重情,对秦观即使心存芥蒂,也不会形于辞色,何况这番风波的由头是他自己的不谨慎呢!东坡和秦观之间,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朋友间的沉默,有时确实是因为对友情的失望。
以秦观的敏感,不会觉察不到苏轼的疏远。当时未被放逐的他,回顾上述风波时,忿忿然写道:“而今世荐绅之士,闲居负道德、矜仁义、羞汉唐而不谈、真若无循于世者。一旦爵位显于朝,名声彰于时,稍迫利害,则释易而趋险,叛友而诬亲,挤人而售己,更相伺候,若弈棋然。”[1](p.525)对于贾、赵的痛恨,使他忽略了对自己行为的反省。但对苏轼,他却依然是充满了感情。元祐七年的春天,他的《金明池词》曰:“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纵宝马嘶风,红尘拂面,也则寻芳归去”(注:《淮海集笺注》此词也有人认为不是秦观所作。徐培均将其系于元祐七年春三月,徐说是。)。李商隐的“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注: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457-458页,上海古籍1979年版。),和刘禹锡被贬十年重回长安所发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注: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中册702页,《元和十一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上海古籍1989版。)的感慨,被他用来表达再次得到重用的希冀。“寻芳归去”,唱出的是他怀旧的心声,而“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曲折地道出了他对往昔的留恋。这首词中的“怎得东君长为主“把绿鬓朱颜,一时留住”云云,也或许有所寄托?
外放颍州一年后,苏轼又被召回京城,元祐七年的十一月迁“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15](p.644)。这一次他和秦观同处京城近一载,彼此却几乎不往来(注:秦观的年谱上,记载他当时与苏轼交往的材料,包括非直接接触且无旁证材料者,也不过两条(参阅《淮海集笺注》元祐七年至元祐八年事页。而苏轼年谱上只载有元祐八年五月十一日秦观与多人一起造访一笔。见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188页。)。元祐官场人心险恶,苏轼、秦观屡遭弹劾,上一场风波的阴影还在,他们自会处处小心。这期间又有人弹劾苏轼并秦观,但未得逞。[14](p.502)元祐八年七月,由宰相吕大防推荐,秦观“由正字迁国史院编修,授左宣德郎。”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卒。在她垂帘听政期间倍感压抑的哲宗,亲政以后,很快就起用元祐元年被罢政出朝的章惇为相。章惇的做法很简单:恢复已废新法,放逐元祐旧臣。[16](p.251-253)苏轼被驱逐得更早,他的保护人太皇太后一死,他就被外放“知定州”,[10](p.1101-1102)绍圣元年四月,又以讥刺先朝(神宗朝)的罪名贬知英州,八月再贬惠州,十月到达惠州贬所。[15](p.644)而秦观则于绍圣元年的春天离开京城,“蒙恩除馆阁校勘,通判杭州”。不久又被刘拯弹劾,贬到处州监酒税。秦观在处州“管库三年”,又被劾“败坏场务”、“以谒告写佛书”等等,“削秩徙郴州”。[14](p.521-526,539)这些年来的遭遇,使他在“自警”之时,对元祐旧臣间的纷争作出了如下总结:“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心多偏窄。争鸣竞利走如狂,复被利名生怨隙。”[7](p.1389)当初那些自以为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不断对苏轼以及门下横行攻讦的人,如今也全部被放逐。秦观在远离朝廷的同时,也远离了朋友和敌人,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面对往事,面对孤独的自我。绍圣元年春天,他写过一首《望海潮》,这首也题作“洛阳怀古”的词,确实多委曲、婉转的寄托。[1](p.837)其中“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句,尤为引人注目。“误随车”用的是韩愈《嘲少年》诗的典,韩愈嘲笑那些京城的轻狂少年“只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注:参阅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36-37页该词的注6。),跟错了别家女眷的车。一般注家都认为秦观这是在回忆自己往年春游中发生的趣事,我却不敢苟同。当时正是哲宗亲政改元之初,秦观的亲家范祖禹等也在这“东风暗换年华”之际被罢官放逐[4](p.520)。秦观那么多年被政敌攻击为轻薄无行,却在党祸黑云压城之际,念念不忘自己的“轻狂”,怎么可能呢!如果说,“误随车”指的是自己曾把赵君锡当朋友,稀里糊涂找上门去游说,结果让自己与二苏陷于窘困难言的境地,倒是完全讲得通。这样一来,后面那句“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就很有意思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然是喻苏门,然而苏轼对赵君锡是否一度“乱分春色”,把他说得很好呢?按照苏轼的天性,我想是可能的。秦观也许就因此把赵君锡看成可信赖的人,以至于造成了自己对苏轼终身都讲不清楚的愧疚。这首作品和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出讨论的《踏莎行》一样,都是向朋友表白心迹的佳作。《白雨斋词话》论秦词深厚沉着时说:“如‘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绝,其妙令人不能思议。较‘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之语,尤为入妙。”[3](p.3785)也拈出了这两篇作品共通的心绪。
黄庭坚在绍圣三年收到过秦观的一封信,他的回信措辞客气但语气颇不亲切,大意是这样的:我现在简直就是个不中用的老农了,你给我写信,高谈阔论,但就好象庄子《逍遥游》中接舆给肩吾所讲的道理一样“河汉而无极”,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好使。……欧公有“老去自怜心尚在”之句,我却已经是枯木寒灰,心也不在了。你学富五车,那么有才,假如碰到一个有实权的大人物提拔你,那你将来的通达,恐怕就不止是我们这么说说的了。……希望你能把平时写的文字,寄给我,我在浇灌了我的菜园子之后,很想有些东西念念,老朽也可以从中得到些安慰[14](p.547)
秦观写给黄庭坚的信已经丢了,我想他当时一定是非常怀念老朋友,而黄庭坚的自嘲语气,会不会让秦观感到被朋友冷落呢?元祐六年秦观“致一场闹”的时候,黄庭坚已经回家“丁母安康太君忧”(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卷十二,《山谷集》所附《山谷年谱》载元祐六年事。),直到元祐八年才回到京城,七月“除编修官”。据“秦谱”说,这时并列史馆的有黄鲁直、张文潜与晁无咎[14](p.509)。九月黄庭坚辞职,而苏轼是在这时出知定州的。绍圣元年底,黄庭坚即被贬黔州。第二年春天到黔州时,苏轼马上自惠州去信慰问。[10](p.1198)以苏、黄之间的交情,他多少会知道秦观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在感情上他当然是更多地偏向苏轼。因而他在给秦观回信的时候,真有点绵里藏针的意思。《踏莎行》中的“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说的是远方朋友带给秦观的音信,象沉重的砖头一样,重重叠叠砌在一起,压在他的心头。秦观这辈子在京城的最高职务就是国史院编、修,他自比《后汉书》的作者范晔,[4](p.102)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那么,这里所说的朋友的来信,会不会就是曾经与之同列史局的黄庭坚的回信呢?根据上述黄庭坚的信与秦观这首词写作的时间以及黄庭坚为之作跋的史实,我认为我的推测是有道理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很可能是向朋友表示:尽管我被看作是苏轼的朋党而流放潇湘,但我觉得,就象郴江本来就绕着郴山一样,我之所以会成为苏轼的朋党,全然是因为我不可移易的天性。很多年以后,张耒“闻苏轼讣,为举哀行服”[9](p.13114),都免不了被责罚,足见秦观在绍圣四年这样表达自己的心迹,需要下多大的决心了!而同被看作苏轼一党的黄庭坚,即使明白秦观之“所属”为何,也不会公之于世。由于后世解人对苏、秦之间这一段曲折不甚了了,对这两句词的含义也就难免误解了。
绍圣四年的四月,苏东坡又从惠州被谪海南,六月渡海,七月到贬所。直到元符三年五月大赦,量移廉州,才离开海南。[15](p.645)秦观于元符二年编管雷州,与苏轼的流放地“隔海而实近”。《秦谱》说:“先生至是,复得与苏公通问,不至寂寂如横州时矣。”[14](p.566)苏谱在该年条下,系有“秦观自雷州惠诗书累幅”事,[10](p.1318)但根据苏轼给秦观的最后两封信来看,两人之间恢复书信来往是在元符三年苏轼移廉之前不久。苏轼文集中一共有七封给秦观的信,其中五封都是在元丰八年以前写的。而排序第六、第七的两封信,应该是第七在前,第六在后。先是秦观听说了苏轼将移廉州的消息,故给苏轼一信。苏轼的回信说:“近累得书教,海外孤老,志节朽败,何意复接平生钦友。”[6](p.1538)“何意复接”云云,显然是说他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苏轼在信中问秦观听到的消息是否确切,说如果消息确切的话,自己也需要打点半个月,过海之后,不知能否见上一面。此信尚未发出,大赦移廉的告命下来了,[10](p.1327)所以苏轼又写道:“某书已封讫,乃得移廉之命,故复作此纸。”[6](p.1537)然后苏轼告诉秦观,十余日之后可出发,已经托人安排渡海的船只并雇了脚夫等等。并表示:“若得及见少游,即大幸也。”六月二十五日,历尽沧桑的苏轼与秦观相会于雷州的海康。[14](p.576)秦观的一首《江城子》写道:“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14](p.577)读来令人怆然。见面时秦观还把自作挽词给苏轼看,苏轼抚其背曰:“某长忧少游未尽此理,今复何言!”[10](p.1342)他没有想到,此后不到两个月,秦观就死在北归的途中。
我们无从知道苏轼是什么时候读到秦观的《踏莎行》的,但《苏轼年谱》将苏轼书扇的事情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也就是苏轼生命的最后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他为秦观的《好事近》作跋,赠送湖南的供奉官侬沔。也许就在此刻,想到已经阴阳睽隔的老友,想到自己坎坷一生的人与事,他在自己的扇子上书写了《踏莎行》的末二句,[10](p.1382)可以想见这首词在他心中的位置。忧患余生中与秦观的重逢竟成了永诀,这使苏轼深为内疚,元祐六年七月以后对秦观的有意疏远,成了生者与死者之间永远的遗憾。“少游已矣,虽万人莫赎”,秦观留在苏轼生命中的,除了他堪称一流(注: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318页,六日条下引文集卷五八《与欧阳元老》简,称观:“乃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的辞章外,还有那令苏轼心痛的真诚的表白。
收稿日期:2003-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