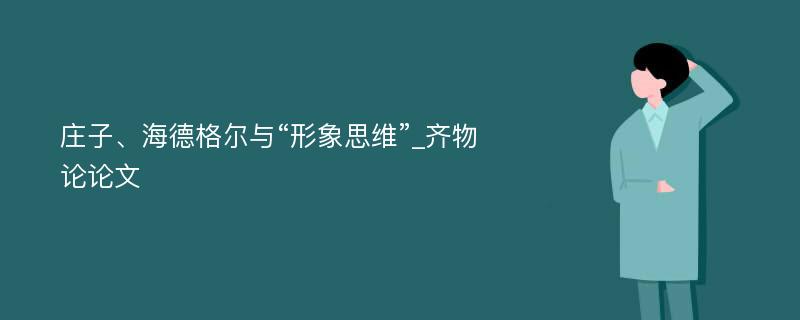
庄子、海德格尔与“象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庄子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6)03-0005-07
笔者在研究庄子过程中,经过对比庄子与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发现两者有值得注意的共同点。特别是后期海德格尔,趋向中国道家“象思维”的特点比较突出。下面试将庄子与海德格尔在“象思维”上的特征分别论述之,并欢迎有兴趣的研究者一起讨论。
一、“说不完的庄子”
自《庄子》成书以来,解庄之书之文就未尝断过。由此,流行一种“说不完的庄子”之说。《庄子》何以“说不完”呢?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回答,而是有其需要探索的深意。所谓“说”,有口头语言之说,又有文字语言之说。就是说,其说总要诉诸语言或文字。但是,用语言文字表意,一般而言,就要进入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这是语言之为语言、文字之为文字的一种本性。因为,语言文字产生的初始,就是为事物命名,或形成事物的概念。这样,一般使用语言文字,就自动进入了概念思维。实际上,语言文字与逻辑几乎是并生的。语言文字这种命名的意味,使得中国相当于西方逻辑学的学问,被称为“名学”,研究这种学问的古代学者被称为“名家”。
就概念思维的自觉和成为思想主导而言,乃是产生于自古希腊的西方并流传至今。与此不同,中国虽然在先秦墨家那里也产生了《墨经》逻辑,其水准并不亚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逻辑,但是,后来不仅没有达到在社会文化界的自觉使用和成为主导,而且到汉代就中断了。在中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概念思维,但近代以前占主导的,一直是悟性的具有诗意的“象思维”。可以说,中国先贤的经典,主要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创造出来的。应当说,概念思维与“象思维”,各有长短。可以互补,却不能取代。从现今西方概念思维的特点来看,它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的思维。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尽管能抽象出事物的本质性规定,但就其用语言文字对于事物的把握和表意来看,无论是对于大宇宙整体和具体事物的小宇宙整体,都是“言不尽意”的。
那么,中国先贤又是怎样使用语言文字的呢?就《庄子》之文而言,公认其文体可分为寓言、卮言、重言。虽然庄子之文有这种形式的区别,但我们认为,实质上三者一也。何以这样说?因为卮言的支离,并不离开寓言之旨,也是言外之意的表达。至于所谓重言,所引史实,也并非如历史学家那样澄清事实真相或讨论历史问题,而是服从其文整体的寓旨性。而所谓寓言的寓旨虽说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的,不如概念规定那样确定和明晰,但却具有概念所不能比拟的深邃意蕴。如上所述,庄子的寓旨,同概念思维清楚确定之所指相比,乃是一种不确定的能指。也就是说,《庄子》既然给予读者一个大方向的能指,那么读者接着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在这个大方向下作出可能的所指(包括回归文本和发挥文本)。就此而言,在《庄子》寓旨的不确定性中,又包含有确定性。这里的确定性,是由解庄者自己作出的。由此可知,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筑象的语言文字都大于概念的语言文字,甚至具有无限的可解性和启迪性,如同“诗无达诂”一样。这样一来,对于“象以筑境”和借境象以尽意的《庄子》,就确实是说不完了。
二、庄子以言筑象
也许有人会问:《庄子》之文不也是用文字语言所写的吗?那么,按照前面的说法,《庄子》的文字语言岂不也可能进入了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吗?毫无疑问,对于解《庄》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1](第1章)。但是,老子不也是用文字语言写了五千言吗?还有禅宗,虽然指出“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但是在参禅活动中,不也是不能完全避开语言并且留下了典籍吗?显然,人类既然发明了语言文字,那么,在人事活动中,完全不用语言文字,已属不可能。然而,语言文字既为人所发明所使用,也就可以有不同的使用。
特别是对于汉语言文字来说,从其创造的源头看,乃是以“象形性”为根基的语言文字。所谓汉字造字法的“六书”,其实只有前四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属于造字法。后两书的“假借”、“转注”则是用字法。其中,“象形”自不必说。所谓“指事”、“形声”,本质上不过是“象事”、“象声”,而“会意”也不过是“象意”之会。由此可知,汉语言文字比西方拼音的语言文字在根基上更富于“象”之性,或“象以尽意”之性。尽管中西语言文字有如此不同,但在使用上,两者各自都可分为两种不同的使用:其一是用于抽象的、规定性的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其二是用于“筑象”以把握动态整体的“象思维”或悟性思维。例如,前一种语言文字的使用,主要是用于理性分析论理上,属于科学思维理性领域。后一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则主要用于悟性或与动态整体作直觉式的一体相通上,属于体道的诗、艺术、宗教信仰等领域。概括地说,前一种语言文字使用,归结为科学性语言文字之用,后一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则归结为诗艺性语言文字之用。
可知,庄、老、禅的语言文字使用,显然主要不是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使用,而主要是作为诗艺性语言文字来使用的。对于庄子来说,主要是“文以筑象”和“象以筑境”,最终是以情境之象来尽其意的。无论其文中的鲲与鹏,也无论神人、圣人、至人、真人,以及朝菌、斥鹌、彭祖、山木、秋水、无何有之乡等等,所有这些天地人间之象、联想创造之象、虚幻之象,可以说,都是“象以筑境”、“境以蓄意”和“境以扬神”。不难理解,正是这里所说的“象”、“境”、“意”、“神”,才是真正进入《庄子》文本和领会其本真意蕴的思想通道。显然,这个通道,不是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通道,而是悟性的“象思维”的通道。这个悟性的“象思维”通道,不是从定义的概念出发,而只能是从体悟“象”与“境”出发。这是解庄也包括解易、老、禅等中国古代经典,必须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
三、庄子的“象思维”
对于道家来说,从老子到庄子,他们的“象思维”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们在把握“道”这个大小宇宙之魂时,是诉诸悟性,而不是理性,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去体悟。这种体悟的结果,表现在联想或想象这种体验意识流的“中断”。如庄子所描述的“心斋”、“坐忘”。亦如禅宗所说“识心见性”的顿悟。也如老子所表述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2](第16章)。这种通于整体的体验意识流的中断,实质上,乃是道家体道而得道,或禅宗参禅而“见性成佛”。这是在精神境界上所实现的一种关键性的飞跃,即飞跃到“道通为一”的境界,或禅宗“即心即佛”的境界。所谓体悟至“道通为一”的境界,或“即心即佛”的境界,不过是使有限的人能与永恒、无限的道或佛在精神上一体相通,从而使人在精神上能得到“无待”或“无执”的自由自在。实质上,禅宗所说的“心性”与道家所说的“道”,不仅是相通的,而且几乎就是一种东西。人一旦与道通,一旦悟而成佛,不仅能进入精神自由无碍的大境界,而且还可能原发地创生出大智慧。当然,这里所说的智慧,不是老子批判的“智慧出,有大伪”那种智慧,而是能摆脱“大伪”的智慧,能超凡脱俗而进入与造物者游的“逍遥游”之大智慧,或者说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大智慧。
另一方面,庄子“象思维”的语言文字表达,则主要是借用语言文字的诗艺的表现形式。以庄子的寓言、卮言、重言来看,如前面指出的,三者在本质上都属于诗艺的表现形式。与概念思维的语言文字表达相比,这种富于诗艺性的语言文字表达,无疑是更需要作者的天才之才性和在创造中的神来之笔。理性的概念思维下的语言文字表达,是一般人经过努力都可以作到的。但是,悟性的“象思维”的诗艺性语言文字表达,则惟有天才甚至大天才方可为之。
当然,从形式上看,《庄子》之文也不乏概念的分析和论理内容。例如在《齐物论》中关于“是与非”、关于惠施、公孙龙的“指非指”和“白马非马”等辨析。但是,即使这些概念的分析和论理,也不是游离于《庄子》之文的整体“象思维”之外。相反,它们也都服从于《庄子》之文“象思维”的寓旨。这种寓旨,大不同于西方语言中心论的概念思维之“能指”和“所指”。就是说,概念的分析和论理,在西方语言中心论那里,是主客二元的、对象化的,也即对有限物所作的规定性的把握。但是,在《庄子》那里,这些概念分析和论理,都服从于庄子的寓旨,最终归结为“道通为一”。或者说,《庄子》之文的立场或主要倾向,对于那种执著于事物有限性和对之加以规定性把握的态度,是予以批判和超越的。在这里,如何看待庄子的概念分析与论理问题,可以说是解《庄》研究的又一个关键问题,但却为许多解《庄》者所忽视。
在《庄子》内篇七篇中,涉及概念分析论理内容比较多者,当属《齐物论》。但是,在《齐物论》中,庄子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可以说都是“道”,或“道通为一”。在此篇开始提出“天籁”、“地籁”、“人籁”之声时,其所描述的南郭子綦就自称:“今者吾丧我”,并批评颜成子游:“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这段话明确地指出,能体悟天、地、人一体相通之道,乃在于“吾丧我”。所谓“吾丧我”,就是《逍遥游》篇中庄子曾经描述神人、圣人、至人的精神境界,表现为“无功”、“无名”、“无己”而“道通为一”的境界。《齐物论》篇一开始,借子綦之口说出的“吾丧我”这个体道而“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就是《齐物论》全篇的出发点。从此出发,庄子在展开“人籁”的描述中,提出“人籁”的具体内容包括“知与言”、“是与非”以及惠施、公孙龙等名家所提出的“指非指”、“白马非马”等认识和逻辑问题。不难看出,在对这些逻辑问题的具体辨析中,庄子在语言、逻辑等名辩的知识修养上,不仅不亚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而且由于庄子还具有“道通为一”的高境界和大视野,从而又使庄子能超越惠施、公孙龙等执著于名辩逻辑不能自拔的思想局限。庄子在讨论“是与非”、“知与言”等问题时,他的寓旨乃是指向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问题。他洞察到,正是“知与言”的分辨能力的出现,使人陷入“是与非”无穷争斗的严重异化境地。这种异化境地,对于人乃是与生俱来,严重到甚至生不如死。如庄子所描述的:“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终身役役,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2](齐物论)。为什么会这样?庄子对此的回答与老子一样,认为这是人和社会在文明中“损道”或失道所造成的结果。如老子所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1](第18章)。庄子也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2](齐物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文明的负面效应批判上,庄子比老子更加深化了。就是说,庄子在批判中已经深入到与人们思考须臾离不开的“知与言”这个领域。的确,人间的一切“是与非”的争斗,都首先表现于这个“知与言”。或者说,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一切异化现象,也都首先表现在人借“知与言”所陷入的文明牢笼之中。庄子所要解构的,正是文明为人所造的这种牢笼。“齐物”就是他所用的非常厉害的解构方法。以往,对于庄子齐是非之论,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等等,都简单地给扣上“相对主义”帽子加以抛弃。今天看来,这种简单的抛弃,实质上是把庄子在揭露和批判文明负面效应上的深刻思想简单地抛弃了。如果我们注意到前面所指出的《齐物论》高境界和大视野的出发点,就不难看出,加给庄子的所谓“相对主义”帽子,不过是就“是非”论“是非”,眼界狭窄,境界低下,甚至是完全不解庄子的本真之意。
实质上,庄子齐是非之论,乃是从道出发又回归于道,使一切是非都在道中化解而“道通为一”。如他所说:“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2](齐物论)就是说,“知与言”、“是与非”,在人的不同境界和视野中,是不同的。在世俗的低境界中,在异化中的“是与非”,不仅存在,而且可以无穷地争斗下去。相反,如果能超越世俗之境界和视野,而入庄子这里所说的“道枢”之境界,人们就可以在眼前展开一个超越异化的新境界和新视野,并进而有可能走入化干戈为玉帛的“道通为一”之大同世界。在这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西方世界宣称“上帝死了”之后,东方的整体思维,特别是中国之“道”,乃是必须特别加以珍视的一种救世之思。这一点,在西方的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那里,如丹麦物理学家波尔(1885-1962)、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1901- 1976)、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和法国大思想家梅洛-庞蒂(1908-1961)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走入“道通为一”的境界。所谓物理学的“测不准定理”的发现,不过是宣布实体论形而上学的破产,而承认非实体性也即“道”的存在,并且这个道才是更加本真的存在。而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位一体”论,不过是“道通为一”的西方现代版。
关于名家的“指非指”论和“白马非马”论,庄子根据他的“齐物”之说,认为亦可提出反题而加以解构。如他所指出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2](齐物论)我们知道,名家之论在立论上,不过是就名与所名之物的区别,以及名之为共相如“马”与殊相如“白马”之区别,并加以辨析和争论,其眼界局限于道外之思,是不言而喻的。庄子提出反题,并不是陷入与名家的无穷争论,而是认为在“齐物”的“道通为一”之视野下,就可以把名家的正题与庄子的反题加以解构。如他所说:“道行而成之,物谓之而然。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2](齐物论)。就是说,既然是为物命名,这种所指,乃是无可无不可的。或者说,事物都可以用指、马称谓。甚至极而言之,“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这充分表明,如果能站在“道通为一”的高度,世间的一切差别和对立,皆可融于大道而被化解和超越。
四、“道通为一”之思
我们对于前述庄子的“道”或“道通为一”之思,还必须加以进一步诠释。那么,如何领会“道”或“道通为一”之思呢?首先,与概念思维不同,这不仅是一种动态整体之思,而且是一种整体直观之思。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直观之“观”,包括眼见之观,但不归结为眼见之观,而有更深刻的体悟之意。如老子所谓“观其妙”、“观其徼”、“观其复”之观,亦如庄子“外物”、“外生”、“朝彻”、“见独”之观,即超越于眼见之观的体悟之观,或内视之观。还必须强调,这种整体直观之思,乃是动态的,即作为“象的流动与转化”的“象思维”。再说,这里所谓的“象思维”之“象”,包括眼见之象,但不仅仅是眼见之象,而是具有“象”的众多层次。其最终的“原象”,乃是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之“象”,或“无物之象”。“象思维”之思,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就是在思的不断超越中能回归这种“原象”或“道”之境域。如前所述,这种“原象”或“道”作为道家的最高理念,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最高理念,而是非实体性的、非对象性的、非现成性的,从而具有原发创生性。在庄子那里,这种“象思维”,其动态整体性及其悟性,表现为“物我两忘”的境域,或超越主客二元的思之境域。如他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齐物论)可以说,这是中国道家特有的精神大视野和高境界,也是最具原发创生价值的大视野和高境界。
但是,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降,道家这种大视野和高境界却逐渐被淡忘,或被逐渐强化的西方中心论所遮蔽。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源于中国的这种悟性的“象思维”的大视野和高境界,在中国人淡忘之时,在西方一些思想家那里却成为启迪他们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与中国的学人的淡忘不同,这些西方思想家特别重视这种中国传统的思想境域并向之趋近。西方思想家的这种表现,在海德格尔那里最为典型。由于他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特别是批判其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中,很注意吸取与融合中国道家的思想。所以,在他后期思想里,倾向动态的整体直观之思这个特点很突出。甚至可以说,源于中国传统的悟性的“象思维”,在海德格尔那里出现了西方的现代版。当然,这个西方现代版在向中国道家思想趋近中,还有其自己的特点,或者说有他的发挥。
五、海德格尔与“象思维”
正因为海德格尔有了新的思想视野和境界,所以才能重新发现“存在”(einai,sein,to be)范畴之被西方形而上学所遮蔽的本真意义,即“存在”作为最高理念的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之意义。其中,“存在”的思想境域,它的动态整体性和非逻辑性、原发构成(Ereignis),都接近于中国传统悟性的“象思维”的思想境域。也正是这种思想境域,使海德格尔在他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和开拓。下面试举两例,侧重说明他的动态整体直观的大视野和高境界。
例一,海德格尔在论述“艺术作品的本源”时,以凡高名画《一双农妇鞋子》为例,具体展现了他的“象思维”的思想境域。他所作的描述是:
……只是一双农鞋,再无别的。然而——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
……夜阑人静,农妇在滞重而又健康的疲惫中脱下它;朝霞初泛,她又把手伸向它;在节日里才把它置于一旁。这一切对农妇来说是太寻常了,她从不留心,从不思量。虽说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之中,但有用性本身又植根于器具之本质存在的充实之中。我们称之为可靠性(Verlasslichkeit)。凭借可靠性,这器具把农妇置入大地的无声召唤之中,凭借可靠性,农妇才把握了她的世界。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存在,为伴随着她的存在方式的一切而存在……[3](PP253-254)
上面海德格尔的描述性述说,常见于哲学、艺术、美学的论文和著述的引文中,但是能从“象思维”视角领会海氏这段描述的价值和意义者则罕有。的确,如果从逻辑的概念思维视角去解释和领会海氏这段描述,几乎是难以下手的。即使归纳出命题加以分析,也是南辕北辙的。因为,他的思考和表达方式,都属于逻辑的概念思维之外的另一路。在这里海德格尔所显示的思路,就是上述所谓悟性的“象思维”之西方现代版。首先,我们在海氏生动的诗意描述中,能清楚地感受到“象思维”的动态性,即一系列“象的流动与转化”。从鞋的黑洞之象的联想,过渡到“劳动步履艰辛”之象;由鞋的“硬邦邦”之象的联想,过渡到“寒风料峭中”田野上步履的单调、“坚韧和滞缓”之象,以及暮色中“踽踽而行”之象。进而又由鞋具在田野上种种象的联想,过渡到秋日丰收之象,作为大地馈赠之象,冬闲之象,对面包的焦虑和战胜贫困的喜悦之象,以及农妇分娩时的阵痛之象,死亡逼近时的战栗之象……这种种由鞋具联想而生出“象的流动与转化”之思,最后归结为鞋具属于大地,归结作为农妇生活世界本质的“存在”这个动态整体。
显然,这个动态整体的“存在”,不是实体,不是现成的对象,所以不能用逻辑的概念思维把握。对之,只能诉诸悟性的“象思维”加以体会和领悟。因此,对之表达也只能诉诸诗意的描述。当然,这种描述,不是概念思维的规定,可以给人提供一种确定的知识,而是只给出一种需要人自己发挥联想力去领悟的方向指引。正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附录中对他的描述和叙述所说的:“艺术归属于本有(Ereignis)(张祥龙译为‘原构发生’),而‘存在的意义’(参看《存在与时间》)唯从本有而来才能得到规定。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是本文中没有给出答案的诸种问题之一。其中仿佛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而其实乃是对追问的指示”[3](PP306-307)。海德格尔作出这种不确定的、看似无可奈何的答复,恰恰说明进入艺术和一切精神底蕴之难。只有悟性的“象思维”,才有可能对其有所体悟并经过体悟作出诗意描述的表达。而这种表达,不是规定的知识,而是启发性的指引,即海氏这里所说“对追问的指示”。
例二,海德格尔在《物》这篇文章中,以壶为例,在“象思维”的联想或“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揭示出壶的“存在”之本质,乃在于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统一。他指出,壶的虚空具有容纳作用或“承受和保持”作用。但是,这种容纳还不构成壶的存在之本质。壶的“存在”之本质,乃在于把壶倾倒时使所容纳的东西倒出来的这种动态。海德格尔把壶倾倒出来的东西,称之为“馈赠”。正是在“倾倒”、“馈赠”的联想或“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海氏把壶的“存在”之本质展现为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统一。他这样描写道:
在赠品之水中有泉,在泉中有岩石,在岩石中有大地的浑然蛰伏。这大地又承受着天空的雨露。在泉水中,天空与大地联姻。在酒中也有这种联姻。酒由葡萄的果实酿成。果实由大地的滋养与天空的阳光所玉成。在水之赠品中,在酒之赠品中,总是栖留着天空与大地。但是,倾注之赠品乃是壶之壶性。故在壶之本质中,总是栖留着天空与大地。
倾注之赠品乃是总有一死的人的饮料。它解人之渴,提神解乏,活跃交游。但是,壶之赠品时而用于敬神献祭。如若倾注是为了敬神,那它就不是止渴的东西了。它满足盛大庆典的欢庆。这时候,倾注之赠品既不是酒店里被赠予的,也不是终有一死的人的一种饮料,倾注是奉献给不朽诸神的祭酒。作为祭酒的倾注之赠品乃是真正的赠品。在奉献的祭酒的馈赠中,倾注的壶才作为馈赠的赠品而成其本质。奉献的祭酒乃是“倾注” (Guss)一词的本意,即:捐赠(Spende)和牺牲(Opfen)……
……在倾注之赠品中,各各不同地逗留着终有一死的人和诸神。在倾注之赠品中逗留着大地和天空。在倾注之赠品中,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这四方(Vier)是共属一体的,本就是统一的。它们先于一切在场者而出现,被卷入一个统一的四重整体(Geviert)中了[4](PP1172-1173)。
在海德格尔充满诗意的描述中,由“象的流动与转化”所展现的画面,使人感受到,由壶倾倒所“倾注的馈赠”不仅不是孤立的现成物,而且在本性上是与大地、天空、终有一死的人和诸神联系一起的整体。“馈赠”的泉水来自土地岩石之间,而这泉水又为天空的雨露润泽所成,并成为人的一种饮品。同时,泉水又为酿酒所不可缺少。至于酒,其原料葡萄等,乃生长于大地,亦为大地和天空的土肥、阳光、雨露所滋养。至于酒,不仅是人的饮品,而且是祭祀神灵的祭品。在泉水、岩石、葡萄、饮品、祭品诸象的“流动与转化”中,作为壶性或其本质的“存在”,就在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动态整体中跃动着。由此可知,“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概念思维意义下的实体性范畴,而是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最高范畴,其意义趋向中国道家的“道”、“无”。这种非实体性范畴,其动态的“惚兮恍兮”之特征,决非概念思维的定义、判断、推理所能把握和表达的,而只可体悟并借诗意的描述加以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作为祭品的“馈赠”,对于领会壶性或壶之本质“存在”的重要意义。但是既然祭酒的奉献,是献给“诸神”的,所以海氏毋宁说是强调“诸神”在四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和本质性。那么,又怎样领会“诸神”在四位一体中这种重要意义呢?海德格尔借此所暗含的指引又如何呢?对此,似乎可以从海氏阐发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的意蕴去领会。直接地说,在天、地、人、神四位一体中,神无疑是最隐晦的“黑”,也就是最应当加以守护的。海氏这里所说的“神”,是否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呢?我们的领会,可以说又是又不是。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明镜》周刊采访海氏时,他曾说过“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但是联系到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透露出的立场,既非无神论也非有神论,那么海氏对神的态度,也许更接近于康德。[3](394)、[4](PP1305-1307)就是说,对于科学所不能涉足的宗教信仰领域,海氏不仅不否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试图从哲学家的立场就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
在海德格尔的描述中,他所用的“馈赠”、“捐赠”、“牺牲”、“奉献”等词语,都具有神学意味。但是,海氏借以发挥的,显然不是引入神学,而是引入他的哲学境域。就这些词语的神秘和神圣指向而言,最典型的要属于:耶稣降世为世人赎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奉献。海德格尔主要不是讲这种神秘和神圣,而是讲潜藏于天、地、人中的神秘和神圣。对于天、地、人中的神秘和神圣,就是指应当“守其黑”的“黑”。为什么把这种“黑”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是天、地、人的生命之根。现在世界文化学术界都在警惕和批判的“现代性”,就因为这种“现代性”以其“科技失控”的发展,正在毁坏天、地、人这种生命之根。[5]
前面指出,海德格尔在思维方式上所表现的“象思维”的西方现代版,在“象思维”上还有他所作的丰富和发展。这涉及到海氏整个思想的一个大问题,不能展开。这里只想略谈一个问题,即如何领会语言文字与文化的问题。从“象思维”视角看语言文字,则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文化的文化,是最根本的文化或称文化的根。这一点,海德格尔在以言筑象中和对词语意义内在关联的分析上,都见出他关于“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一深刻洞见。例如,海氏所说奉献的祭酒的意义,就是“倾注”,而“倾注”就是“捐赠”和“牺牲”。我们在这种语言筑象和意义的内在关联上,确实能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链条,乃是文化的血脉流淌。作为“生存”的存在(海氏的Dasein),确实就生存在这类奉献祭酒的“倾注”等等语言文字的文化血脉中。由此对我们的启发是,中国汉语言文字作为“存在的家”之内涵,不是很值得我们去发掘吗?
收稿日期:2006-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