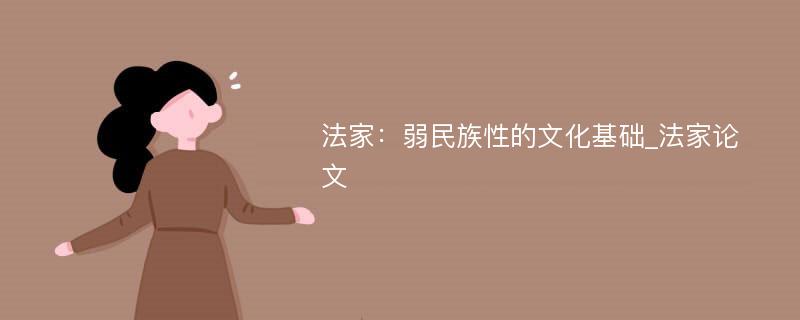
法家:弱国民性的文化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弱国论文,法家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时下鲜有听见人们议论国民性问题之际,《探索与争鸣》1997年12期发表的《陈独秀“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是正确的》一文,打破了许多年的沉寂,重新提起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旧话题。
法家理论融铸了国民劣根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民性问题。什么是国民性?最权威的《辞海》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均未收入这个词条,这使我们难以凭籍精英们的智慧对国民性作最直观的理解和认识。笔者认为,国民性就是国民的普遍性格或社会性格。国民的社会性格具有二重性,国民性中的闪光点我们常称之为优秀品质或传统美德,不良国民性我们常称之为弱国民性或劣根性。闪光点和劣根性共存于国民的社会性格中,这是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的。国民的社会性格是受这个国家的文化涵养培育生成的,民言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以最通俗的语言说明国民性是一种文化积淀的深刻道理,并非形成于朝夕之间。国民性一经形成就较难更易,并且融入国民的血脉代代承传。因此,改造国民性也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文化的概念十分宽泛,几乎是人言人殊,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认定在历史上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儒家。确切地说,应是“内法外儒”的文化格局,这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所谓“内”,当是指内在的、隐蔽的、处在核心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所谓“外”,当是指外在的、装饰性的、处在表形的起辅助作用的文化。笔者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用儒家包装法家的文化,支配中国文化的核心力量是法家文化,而非儒家文化。
二千多年前的西周王朝瓦解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裂土纷争的无序局面,秦国顺应历史潮流,从诸子百家中挑选了法家学说作为建立新秩序的理论武器,扫六合,平四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法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中首次获得成功,秦始皇也被后世尊为“祖龙”。然天不佑秦,汉代秦兴。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大抵汉武帝认为始皇帝不善包装,所以秦祚不永,于是信誓旦旦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主张。然而学者们另有说法。从本质上看,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汉兴以来,承用秦法”(顾炎武《日知碌·会稽山刻石》),即便是汉武帝首创“独尊儒术”,儒学也未处独尊地位,如胡寅论道:“武帝虽曰崇儒,实则好以刑法寓下”(《读史管见》卷二)。事实上,二千余年来并未脱秦汉窠臼,这也是史家的共识。
汉武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的帝王之一,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懂得用儒家的“人情味”掩饰法家的“血腥味”。如果说秦始皇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那么汉武帝则开创了“内法外儒”的历史新纪元。这是“秦皇汉武”能并列于史的原因。正是这种内法外儒的文化,涵养培育了中国国民的社会性格。因此,“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鲁迅先生讴歌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即便是帝王家谱的“正史”,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辉。这是中国国民性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部分,他们那以身践道、殉道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然而,我们从古以来,也有谄谀取容的人,也有攀龙附凤的人,也有任意作奸的人,更有崇尚卑鄙的人……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所凸显的大抵都是国民劣根性,他们的恶行,即便是帝王家谱的“正史”也难以掩饰,而不得不将其归于“奸佞”之属。这类人在历史上绝非少数,他们蠹国害民为祸之烈,决东海之波也难尽其毒。
综上所述,如果说以法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国的脊梁”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铸炼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主要承当者。
《韩非子》是国民劣根性的经典
法家最后一位理论大师是韩非,他的大著《韩非子》人称是集法家之大成者,被奉为帝王之学、御下之术。这部帝王经典洋洋大观,不过法、术、势而已。这里需特别提出的是,法家的全部理论是以“性本恶”为立论的逻辑起点,而儒家学说是以“性本善”为立论的逻辑起点,由此推导出的许多理论也是大相异趣的,即是同一种观点,其内涵也各不相同。例如,儒法两家都主张尊崇君权,儒家持有限君权论,法家则持无限君权论;儒法两家都主张人治,儒家倾向于德刑并用,而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轻罪重罚,等等。
什么是法?韩非没有直接解释,但也说过“君之立法”(《饰邪》);“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上》);“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利,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独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主道》)。韩非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法”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归一的专制独裁,韩非教导帝王们要牢牢抓住,不可假手于人。韩非也没有解释什么是势,但势是与权威、权势同层次的概念,可理解为是帝王的无尚权力和崇高地位。“势足以行法”(《八经》),“威者足以行令也”(《诡使》),失势就意味着丧权,因而韩非教导帝王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势。然而帝王的权势是“人设之势”(《难势》),为了强化帝王的权势,韩非教导帝王们要以术保势。什么是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术者,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人所执也”(《定法》)。可见术就是权术,是帝王独操、深藏不露、驾驭群臣的阴谋韬略。郭沫若曾作过统计,韩非在“他的书中关于术的陈述在60%以上”(《十批判书》),可见术在法家学说中的地位之尊。
帝王该怎样玩权术耍阴谋呢?韩非如是说:不要相信任何人。只能“恃势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不然“信人则制于人”(《备内》)。“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主道》)。要装聋作哑,然后挟知而问,显得高深莫测,使臣下常存惕怵畏惧之心。密设暗探、广布耳目,实行特务政治,以达到“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奸劫弑臣》)的独裁统治。实行愚民政策,“圣人之道,去智去巧;巧智不去,难以为常”(《扬权》)。禁锢思想,限制自由,服从驯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行,其次禁其事”(《说疑》),等等。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韩非子》无异于是一本玩弄阴谋诡计的教科书。
以法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等级关系,具有模式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超稳定性的特性。二千余年来,无论是皇冠易主还是山河变色,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等级关系基本不变。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专制主义统治手段——“术”不断在变,但方法论已被技巧化了。例如,国民,尤其是跻身官僚行列的国民们,或为了自身免祸,或为了既得利益,或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特权,他们必须学会明争暗斗、钩心斗角,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卑身贱体、屈邀恩宠,朝秦暮楚、韬光养晦,巧媚阿谀、伪恭伪敬……这林林总总、花样翻新的技巧,无不是卑劣的臣民心态、权力欲与服从欲的分裂人格和奴才品格的反映。祖上留下的这份遗产,是心理定势的产物,实利主义的需要,使其成为一门显学,以致今天的国民对什么欺、瞒、哄、骗,什么厚黑学、钻营术、窝里斗,什么东方式妒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这些玩艺儿岂只是毫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无师自通。某些国民玩起这些技巧,娴熟得令人叹为观止,游刃有余,毫不比古人逊色。这说明国民对劣根性有某种亲和感和认同感。
当然,侈谈弱国民性可能是个犯忌的话题,因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民有太多的美德。然而,为何每到改革的关键时刻,就会听到人们无奈而委婉地说:国民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阻力!并何以会听到人们痛心疾首地议论:腐败严重、道德滑坡、内耗很多……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十分艰巨的。朱熹说过:“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法,所以后世不肯变”(《朱子语类》卷134)。 这说明法家学说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清除这个基础是十分困难的,这里不妨举二例说明。朱元璋删《孟子》是历史上有名的《孟子节文》事件,所删除文字为“民为贵”之类。这位开国皇帝为何不删出一本《韩非子节文》来?这足以说明后世人君绝不可能变更尊君卑臣的专制制度,那怕是撕破遮羞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专制主义的思想并未清算。即使是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五四”运动,仅是打倒了孔家店,并未彻底摧毁以法家学说为理论基础的“阎王殿”。专制主义的遗毒被历史带到了新中国,成为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这就是“文革”中张春桥提出的“臭豆腐理论”。“臭豆腐理论”时至今日是否还在起作用呢?当然,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我们甚至可以遥想当年汉武帝如转而实行“外法内儒”的文化政策,中国的历史又该是何种景观呢?这些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