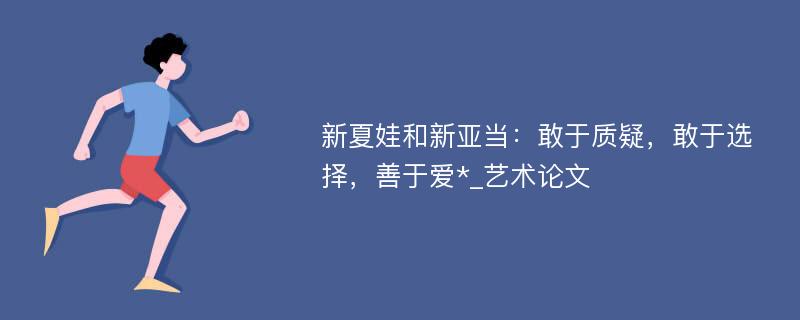
新的夏娃和新的亚当:勇于质疑,敢于选择,善于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夏娃论文,善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期学术人物R.艾斯勒
〔编者按〕今年6月,杰出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具有文艺复兴勇敢精神的女学者理安·艾斯勒将庆祝自己65岁生日。我们特此编辑专栏,介绍她的学术成就和新作,以示同庆。
艾斯勒在我国知识界已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她提出的“男女伙伴关系”概念已逐渐为我们理解和接受,因为她的名作《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1993年在我国翻译出版,接着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又在1995年集体创作了《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这两本书在我国的妇女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艾斯勒的丈夫和最亲密的事业伙伴大卫·罗依撰写的《理安·艾斯勒——她的著作及她的影响》一文,全面介绍了她在十几个领域的学术成就。我们从中获悉,艾斯勒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围绕三个东西在进化:权、性和钱。《圣杯与剑》写“权”,她刚发表的一部新作《神圣的欢爱——性、神话和肉体的政治》写“性”,显然下一步还要写一部关于“钱”的书。
由黄纪苏撰写的《评介〈神圣的欢爱〉》一文全面介绍了她新发表的巨著《神圣的欢爱》的内容。此书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外出版的学术水准较高、较严肃的性学著作。在古代男女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里,女人的肉体受到崇拜,男女的性爱是神圣的。在男性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里,女人的肉体成了罪恶的渊薮,男女的作爱变成了男人寻欢作乐和女人为男人生儿育女的手段。
由黄觉翻译的《神圣的欢爱》的最后一章,对此书的主题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艾斯勒在此书中采用的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重构”的方法。
我们希望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能尽快翻译出版《神圣的欢爱》一书,也祝愿艾斯勒女士健康长寿,能将第三本书,即论钱同社会模式的关系的书早日写出,使我们能全面了解这位有独创性的女学者对人类社会进化的独特看法。
我们都喜欢听故事。故事里有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目标。故事教我们判断身边一切事物的是非——从我们自己的身体到一切宗教的或世俗的、好的或坏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和故事里的人物比试,向他们学习,崇拜他们,或是鄙视他们。我们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按着故事里的样子塑造我们的生活。
随手翻翻历史书,我们会看到,正是由于为数不多的勇敢女子和男子敢于描绘新的政治、经济和两性关系——敢于向那些由来已久的制度挑战,比如奴隶制,比如神授君权,比如“如果强奸挣不脱,不如放开来享受”和“不打不成器”之类的说法——我们才能一点一点地改变着现实中许多的痛苦和不人道。
我们已经看到,这便是当代意识革命的主要目的:逐步解构和重构神话故事,它们长期钳制我们的思想、身体和灵魂,使之顺应一个由惩罚、恐惧和痛苦驱动的制度。我们还看到,今日的意识革命已进入第二阶段,我们日益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能够作出选择,我们能够改变世界。在当今这个受着核弹和生态灾害威胁的高科技时代,这样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一定成功,不一定能摆脱那些至今束缚着我们,使我们生生死死都那么痛苦、不平、不得和谐的神话故事和结构。然而,这种努力本身就是一次不寻常的探险:这是一次既向内心又向外界的旅行,它带领我们进入意识的更深层次,同时也引导我们走上更宽更美的生活之路。因为在塑造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愈趋于完整,就愈能更多感受到意识的变化。就象处女地上的探险者,我们愈是敢于闯新路,就愈能开辟更新的道路,愈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体验生活。
我们的创造历程
目前所谓的创造力仍是统治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产物。首先,创造力被定义为高于“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能力,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少数奇才才能获得,而他们创造出来的也只是些摆在博物馆或别的什么特别场合供人观赏的稀罕物,或者是些用来革新生产技术或破坏技术的玩艺儿。没人区分那些能扩大人们的生活空间、提高生活质量的发明,和那些限制人们的生活空间甚至更迅速地杀人的发明(比如纳粹发明的屠杀营)。也没人注意创造力的社会环境(大卫·罗依称之为社会制度中哺育创造力的“女性”基质)或协作的创造力。
这样一种处处受阻而又处处阻碍他人的定义在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少数男人高踞于所有人之上的社会中是合理的。但在一个以伙伴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中就行不通了。因此,人们对创造力有了新理解,那些着力培养创造力的研究者、艺术家和管理人员如此,千千万万的“普通”女子和男子亦如此。
这种新观念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创造力,只是每个人的创造力各有不同(和人类的其他能力,如提举和奔跑一样),人们可以发展它,也可以扼杀它。此外,正如阿尔封斯·蒙突利和依莎蓓拉·龚迪在其著作中所说,创造力可以体现在各行各业中,不仅仅限于艺术家的工作室或火箭科学家的实验室。这样一来,什么是“创造力的产物”,什么不是,就有了新的划分标准——当代艺术中已体现了这样的新标准——“普通”的创造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发明,才是最伟大的创造力,因为它能够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更多的意义,甚至使我们的生活更神圣。创造力一词也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于一切发明,人们不再用创造力来称呼那些以加强统治帮助屠杀为目的的发明。创造力专指那些具有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发明。
但是这种新观念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强调创造力的社会环境,强调帮助或妨碍我们发挥创造力的因素,不仅如此,它还强调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创造力:对于社会制度、信仰制度和神话故事的创造。换言之,这种新观念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探险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共同创造者。这种观点为我们的研究和实践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无论是在我们祖先的生态意识中,还是在他们更加以自然和肉体为中心的爱情中,西方史前社会似乎早已有过我们现在为之奋斗的以伙伴关系为中心的世界。然而,古时对于女性身体的崇拜并非凭空而生,同样,今天新的更符合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社会结构的信仰、偶像和神话故事也是在我们耳闻目睹的个人、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中产生的。
在过去3个世纪中, 世界上至少一部分地区的人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主流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和偶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统治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这一部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新思想和新发现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已存的知识和真理所接收。但更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旧的统治关系模式的神话故事和偶像牢牢地箍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尤其是箍制了众多文化守门人——学术、宗教、经济和教育机构,特别是书籍、杂志、报纸的出版商以及电视和电台的新闻、娱乐节目及电影的制作人——的想象力。
结果是,我们的主流文化中大多数偶像和神话故事仍以维系统治关系社会结构的因素为中心:身体的痛苦或这种痛苦的威胁。不幸的是,在一个由男性统治的时代,一个视暴力为天命的时代,我们的宗教偶像也无一例外地是这样。
因此,我们的宗教偶像很少让人觉得平易可爱,这实在不足为奇——尽管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便会大惊失色。在我们的神像中找不到性爱或性的快乐,因为只有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才勉强得到神父们的宽恕。基督教的许多宗教形象所表达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的残忍,理想化的甚至是被神化的磨难(基督教里有无数殉难的先知,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宣扬的也是这种磨难)。在我们的宗教里,即使亲子关系和兄弟之情也不免染上暴力的色彩(比如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或是机械地服从父母的至上权力(耶稣顺从地引颈就死,亚伯拉罕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上帝,这常常成为画家的题材)。不仅如此,我把从中世纪早期到当代的圣母与圣婴画像仔细地看了又看,却发现从许多画中丝毫看不出母子之间的温情。
由此看来,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创造更符合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社会结构的神话故事和偶像,在这些神话故事和偶像中,唱主角的应该是给予和接受快乐和仁爱,而不是制造痛苦,也不是忍受痛苦——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统治和征服的旧传统已经越来越功能失调,甚至即将自取灭亡,如果我们想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将人类的探险继续下去,这便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重写神圣
维护不公和痛苦的宗教神话故事受到挑战,这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举。早在19世纪,伊利莎白·凯蒂·斯汤顿就编写了《妇女圣经》,把那些说妇女堕落,是附属品,无足轻重的段落从《圣经》中挑出来,进行了尖刻的批评。然而,那时人们仅仅反对现有的神话故事,因为它们将我们束缚在统治关系的生活方式上,他们呼吁“进行比世界上一切宗教书籍都更感人更崇高的教育”,也就是说,现代意识革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批判现存神话故事——或者说,是解构。只有到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意识革命的第二阶段,革命重心才逐步转向重构。
今天,有些人在旧传统中工作,一砖一石地为伙伴关系的社会和两性关系打基础。他们说我们犯不着扔掉所有的宗教神话故事和偶像,他们认为我们的宗教中有许多不同的因素,我们可以保留并加强那些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公正、更和平、更完美的东西。不错,在我们的犹太——基督教神话故事和传说中,确实有很强的伙伴关系因素,比如,有许多神话故事讲述耶稣的善良和仁爱,还有的讲述他如何蔑视那个时代的道德,自由地和女性(包括近来发现的一些女门徒)交往。不仅如此,有些神话故事和仪式在其统治关系外表下还有早期伙伴关系传统的痕迹。
我相信还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亲昵关系以神圣是建造新的伙伴关系爱情的重要环节,这种新爱情既是内化也是超越:它将是至上的欢乐而不是赎罪的痛苦理想化。我还相信,创造一个新的神话故事体系,使性爱神圣化,使我们改变自己和社会,这将给我们带来新的神话故事,包括适应更公正更民主的新世界的圣家族的神话故事。这又一次有悖于我们从古老的统治关系社会继承下来的遗产,然而,变化还是一点一滴地发生了——各路专家、艺术家和小说家纷纷以神性重写圣母,这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要抛弃那种以父子为中心的家庭模式,这显然使重申玛利亚的神性变得格外重要。当然,在圣家族的宝殿里还应加上圣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所有家庭成员得到同样的重视,受到同样的尊重。
有些故事经过改造可以适应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社会结构,有些神话故事却应该彻底抛弃。比如印度教里有一个故事,讲伟大的神毗湿奴如何被他父亲赐死,又如何由一个女婴替死而得以存活。犹太—基督教里的一个故事讲述洛特为了保护他的天使客人,把他的女儿送给一群强盗,供他们奸淫。还有神学家沃尔特·温克称之为救赎暴力的神话故事——上帝让他的儿子耶稣以死替人类赎罪的故事,基督教士兵列队厮杀的寓言,还有“英勇的”骑士、牛仔、警察杀人如麻的故事,以及最新的宇宙小子为保卫他们的国家、社团或星球用他们的“超人”能力大开杀戒的故事。
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扔掉这些神话故事是不对的,甚至是渎神,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伙伴关系社会里的神圣和道德与统治关系社会里的神圣和道德是不一样的——这就象这两种社会对于正常和不正常有不同的标准一样。我也知道有人会说,不管多么需要,宗教神话故事是不可能改变的。然而改写宗教神话的先例在历史上不一而足。肯定会有人说,我们的宗教和世俗神话中关于英雄暴力的故事不过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宇宙间善与恶、上帝与魔鬼、光明与黑暗,或者,用荣简斯的说法,“人与他的影子”之间的搏斗——这些神话故事只是反映了人类的现实。
然而,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邪恶的现实。犹太神秘学者巴姆·闪姆·托夫说,就全宇宙来看,最好把恶视为缺乏善,而不是反过来看。我要补充一点,就全人类来看,最好把恶视为缺乏那些使人之为人的品质:我们拥有的意识、选择,更重要的是,同情和爱的巨大能力。
爱是人性和神性的精华,伟大的精神导师如耶稣和佛陀的一切教诲都是围绕这一点进行的。但是,尽管耶稣和佛陀言传身教,宣扬同情和爱,(耶稣给病者以治疗,给哀者以慰藉,给饥者以面包,他将被指控为通奸的女人从乱石砸身中解救出来,他号召我们远离暴力,教我们以待己之道待人),这种爱的教导却在统治关系社会里被歪曲和遗忘了,甚至经常被用来充当最野蛮行径的借口。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摘除过去几千年的统治关系历史挂在爱这个字眼上的所有残酷意义。这件事已经开始了,这真让人激动不已。
重新学习爱的艺术
我们常说我们爱父母,爱子女,爱同伴,爱朋友,我们说我们爱莫扎特,爱玫瑰,爱落日,爱跳舞,爱唱歌,爱烹饪,爱园艺,我们还说我们爱吃巧克力,或者爱看富于刺激的书。我们用爱来涵盖一切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物,尤其是那些使我们感到与同类息息相通的事物。
的确,在进化的过程中,大自然通过脑啡肽和其他神经肽(科学家们不久前才开始研究它们)等化学物质,使我们这个物种具有巨大的能力从性爱、仁爱和被爱中获得快乐。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关心,人类便无法生存。科学家最近证明,我们不仅在儿时而且在整个一生中都是如此。
我们从昏睡中醒来,逐渐认识到几千年来我们建立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阻碍、歪曲和遗忘了人类对于爱的渴望。如今,我们从世界上的大屠杀中意识到这一点,这心狠手辣的屠杀持续了近5000年。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电影和电视屏幕上的野蛮和恐怖中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从挥之不去的统治关系、经济制度和行为中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变得麻木不仁,互相伤害,这样的行为,如耶稣预言的那样,使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们从那些残忍的、麻木的家庭关系中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家庭关系遏制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爱的能力。我们也从大众传媒、甚至我们最推崇的某些爱情经典里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尽管性爱被描写成面目可憎的样子,尽管那么多不健康的暴力行为纷纷打着爱的幌子——也许正因为这样——今天成千上万的女性和男性不再买旧文化传统的帐了。不过,对于传统文化定义的浪漫爱情的批评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人做改变两性和家庭关系的尝试。直到今天,我们已从当代意识和两性革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焦点才转移到统治关系或是伙伴关系的亲昵关系的行为模式上来。因为只有现在,人们才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尺度重新衡量并试图改变社会制度和我们的日常个人行为。
新闻媒介所报道的仍是解构——比如随科技和社会的迅速变化而来的离婚率迅速提高。显然,个人和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对许多人来说,旧制度形式的瓦解所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新的创造机会——一个展望和创造更健康更令人满意的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机会。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称之为性关系转型——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众多的男女被我们这个时代所未有的现象,众多的男女被我们这个时代席卷社会的运动激发着,自觉地抛弃旧的方式,重新学习爱的艺术。
由此看来,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习爱的艺术是从怎样作对子女更有爱心的父母开始的,这并不是在基础课程资金剩余时随手加上的花边。如果我们真的想建设一个更民主、更少暴力、更加文明的社会,这便是一门必修的基础课。在经过许多世纪的统治关系社会化之后,任何人如果想要解放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神经和组织,彻底地体验和表达人类渴望互相勾通的强烈愿望,都需要学习这门课。因为根据对爱的心理学研究,我们与我们的养育者之间的关系将严重影响我们今后的亲昵关系,它甚至会影响我们与自身的沟通。新的教育方式教会我们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亲昵关系,这种新的教育方式现在已经开始有了立足之地,它会帮助我们接受并爱我们的身体——莉塔·福雷曼在她的《身体之爱》中说,这是我们对爱的新理解的另一个方面。
挑战,创造的机会和真正的文化战争
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新文化,把它带入主流文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制度——使它融入我们的家庭、政治、经济、宗教和教育制度,这样我们的下一辈就不用再从头摸索——这个任务具有历史意义。我们不仅要推翻几千年的统治关系的神话故事和偶像,还要抵制象癌细胞一样挤入伙伴关系的神话故事和偶像中的新的统治关系的神话故事和偶像,因此我们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还要有坚强的意志抵制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仍在鼓励违背人道的行为,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真正仁爱的行为不仅能使我们感到幸福,还能帮助我们战胜疾病,延长我们的寿命,然而在现行的经济制度中,这样的行为换来的往往是最少的回报。我们甚至需要提一些闻所未闻的问题,比如,当我们从心底感觉到我们的某些想法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意识形态制度的产物时,我们就应该扪心自问,这到底是谁的想象力?简言之,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选择异说而不是随声附合——现代意识革命第一阶段的急先锋们也是势单力薄,但他们不畏权势,迈出了通向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制度的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在现代意识革命的第二阶段所具备的也正是这种异说的力量——科学实验表明,这种力量远远大于随声附合的力量。我们处在一个文化进化的关键转折点上,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制度极不平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文化转型理论指出,变化有可能发生——甚至有可能在短期内发生。
对我们最为有利的,是一个物种正在觉醒地为生存而奋斗的意识,以及我们人类巨大的创造力:唯有这种能力能使一个物种实现其最高的愿望,尤其是我们人类爱的愿望,以及创造新制度、新的神话故事形式的愿望。
我们已经看到,神话故事的变化是携手并进的。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导致了故事和偶像的变化,而故事和偶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形式,新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形式会产生意识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神话故事和偶像——这又会刺激我们人类独有的创造力,激发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进行变革。
忒修斯和其他的亚尔古英雄是史前人类的佼佼者,他们将世界推入了一个暴力和强人统治的阶段——在这个世界里,就象忒修斯的故事里讲的那样,男人最理想的性关系是与爱情无关的。同样,我们这个时代奋力将世界推向一个新阶段的佼佼者们也将被明天的人们传颂,成为明天的故事的原型。而这些真事和故事又会激励我们改变思维、生活和相爱的方式,这种改变又会产生更多更新的神话故事和偶像。我们从古老的统治关系社会继承下来的许多神话故事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手法对待统治关系的神话故事,为自己扫清道路。
我们也可以改造统治关系社会的经典著作,从《驯悍记》到《蓝勃》,剔除其中的糟粕。比如,我们可以重写“灰姑娘”,灰姑娘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把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争取了一个过来,共同教育那位又自私又麻木的继母和那位迟钝不称职的父亲(在旧故事里他根本没有出现,好象这事儿与他无关),教他们怎样作体面的父母——既不娇惯子女(象旧故事里的继母对她那两个倒霉女儿那样),也不剥削和虐待她们(象他们对灰姑娘那样)。当然,新故事里三个女孩儿谁也不会去试穿那著名的水晶鞋,他们会让王子的信使给王子捎个信,告诉他说,他如此看重女子的身体,竟觉得她们的某一部位一定要符合某种既定的规格,这样的男人永远不会得到任何女子的青睐。
另一个可以加以改造、创造出有趣又有新意的故事的领域,是性神话故事。过时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当代色情小说都在对我们说:男人要通过污辱、折磨、漫骂、贬抑或以其他方式践踏女人才能得到性快感。弗洛伊德的观点就是一个例证,他认为男人只对比他们弱的女人感兴趣——然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夫妻双方都有职业的家庭中,阳痿的发病率要少些,而在这样的家庭中,女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地位更平等些。不仅如此,这样的夫妻据说有更频繁更和谐的性生活。
当然,那些打着上帝的旗号竭力维护统治关系传统的人会跳出来大喊大叫。然而我要提醒大家,仅仅在几个世纪以前,针对独裁王权的政治讽刺也同样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民主世界里,即使是宗教领袖也应该允许批评;再说,小小的不敬总是强于利用宗教权力煽动和激发暴力,目前就有人利用宗教权力在西方发动了一场所谓“文化战争”,他们以一个打着宗教的幌子实施最大的野蛮和残暴的时代所产生的神话故事为遮掩,进行反民主宣传。
一些社会评论家说得好,冒犯原教旨主义的最主要原因——美国的基督教也好,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或印度教也好——是他们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所以产生了恐慌。通过痛苦或痛苦的威胁植入统治关系心理的僵化使具有这种心理结构的人难以适应任何变化。从这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原教旨主义者为了重新控制一切,必然对女性施加更严厉的束缚——尤其会更严格地束缚妇女的性爱。因为这种束缚是维系统治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关键之所在。
由于这样的原因,西方当代“文化战争”的领头人和经济上的支援者无疑是危险人物。他们企图退回“过去的好时光”,那个时代所有女人和大多数男人都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一个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男人凌驾于男人之上,国家凌驾于国家之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制度下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一旦得逞,我们就将进入一个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的时代,因为那些人将要控制一切,这是“天命”。因此我们要更积极更直率地自卫,反对这种宗教法西斯主义,要警惕他们的静悄悄的战术,要调动法律、经济和媒介等各种手段来阻止它。但我们并非要用同样的漫骂和暴力来迎战那些带着一群教徒进行挑衅的人。我们的目标是那些追随者,他们来自恐惧和痛苦之乡,因此我们要以同情待他们——要揭露原教旨主义极右领袖的文化阴谋和他们造成的巨大破坏,使人们不再相信他们,要让那些追随者知道,他们完全可以以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方式对急剧变化着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作出反应。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战争”其实并非宗教价值观与“异教”价值观的战争,而是企图把我们彻底毁灭的不协调不人道的制度与正在破土而出的新的伙伴关系制度之间的战争——这全仰仗于千千万万人的英勇奋斗,他们已不再接受《创世纪》里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不再相信我们人类注定要永远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永远没有爱。
重新定义勇气,再造我们的生活
提到勇气,我们不禁要谈谈意识中的另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同样没有在主流文化的故事和偶像中反映出来,主流文化倒更象一面反光镜,它反映着我们的统治关系的过去,却无法精确地反映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旧模式里,勇气产生于愤怒、恐惧和仇恨。我们更意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勇气,那种勇气源于仁爱——不论对我们所爱的人,还是对萍水相逢的陌路人:那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里总爱说,勇敢就是杀死毒龙和怪兽,然而我们现在意识到,以非暴力的手段与不公正的权势抗争比杀死所有毒龙和怪兽需要更大的勇气。
统治关系传统如今也受到其他行业的挑战——比如,心理学家亚瑟和艾莲·阿仑夫妇,他们的著作把我们带入爱的新天地;社会学家罗伯·高吉尔,他正在编写一套伙伴关系教育丛书;哲学家闵家胤,他是北京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的组织人;还有经济学家迪华基·杰恩、尼尔马拉·马纳吉,和其他数不胜数的人,他们在为消除南北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以及各民族男女之间的分配不均而不懈工作着。
在以精神力量挑战统治关系道德标准的人中不乏知名人士。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默默无闻。不象那些动辄惊动新闻媒介的政治家、将军、摇滚明星、社交明星、体育明星和其他显赫人物,这些人不寻常的社会创造力毫不引人注目。所以,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艰巨任务,那就是要让人们更广泛地注意他们。
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女子和男子努力创造着新的神话故事、新的制度和新的信仰,他们也在创造着新的生活和交往方式,正是他们为我们时代的个人、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变提供了迫切需要的角色模式。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痛苦,他们所经历的磨难和所取得的胜利,将成为新故事的素材,在那些新故事里面,新的亚当和夏娃们将在我们的地球上孕育出一个新的伙伴关系文化。
未来的性爱、情爱和快乐
本书已将近尾声,我却自始至终苦于没有足够的篇幅容纳这众多的个人和团体,他们为我们的未来创造着新的伙伴关系文化。能够通过我的工作看到这么多的进步和希望,我不禁感到无上的荣幸。我也不禁回想起,在我的生命中曾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我对发生着的转变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30年来我自己生活中的深刻变化。然而当我亲身经历了这种变化,而且目睹这么多人正在努力地改变着他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我觉得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能够为我们和我们的后辈开辟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尽管这绝非易事。
如果在成功之时回顾我们现在的科学和宗教神话故事,我们会感到吃惊的。我们会惊问,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人类大脑的潜能只有一小部分被开发出来,我们的许多社会生物学故事却大讲特讲那些远不如我们的生命形式——让我们觉得我们人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无能,因为我们是进化过程中的迟到者,这是为什么?最著名的讲述人类起源的故事,《创世纪》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对性爱、爱情和快乐没有一句赞美之辞,人类对于更高意识的追求成了诅咒而不是幸福,对我们人类拥抱或触摸我们所爱的人时油然而生的那种战栗和玄妙的感觉,它居然只字不提,我们会觉得这简直无法想象。
世界上仍然会有神化磨难的故事,因为痛苦和死亡也是自然和生命的循环。但是更多的故事将表达我们的敬佩、惊叹和狂喜,包括我们从性爱中得到的欢乐、敬佩、惊叹和狂欢。
我们的故事将描述欢天喜地的人类,而不是罪孽深重的人类。我们的偶像将赋予性爱以灵性,而不是一味追求暴力和统治。我们会有救赎的故事,但是通过仁爱与快乐,而不是通过暴力与痛苦。
世界上仍然会有关于神圣的造物主的故事,甚至比以前还多——圣母与她神界的情人结合,繁衍了所有的生命。我们的故事会昭示隐含在几尔加美什史诗里的观点,我们的性爱是使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甚至会讲述女人和男人天各一方的故事,就象雅各布·波伊姆写的《圣经》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不过在我们的故事里,伤口已经愈合。
在我们的故事里不会出现要求奴性、受难和自卑的神灵。掌管宇宙的力量将以人的形象出现,它既是慈母也是严父,它将欢乐赐予我们,而不会嫉妒我们的快乐——它是慈爱的长辈,从我们的快乐中得到欣慰。这神圣的父母不会独占知识,而是鼓励我们去追求。他们会为我们生命中的喜悦欢呼,而不是去刈剪它。他们会教导我们珍视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这样做。
由于精神和物质不再分离,在我们的经济神话中,我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我们对于意义、公正以及从互相关心中得到巨大乐趣的需求——都将得到考虑。儿童真正被视为珍宝,所以在我们的故事里,儿童比现在要少一些,家里除了生身父母之外,还有许多充满爱心的人照料他们。这些故事在孩子们的婴儿时期就会讲给他们听。
这个世界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富有意义,在这些仪式里有鲜花、烛光、音乐和美酒。这些仪式赞美我们的精神和肉体的结合,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某些仪式是庆祝男女之间的结合,这将是神奇和狂欢的盛典。然而我们祖先的性仪式一定是从人们的性经验中发展而来的,这种性经验是另一种形式的意识,我们的这些仪式也应该来自于这种亲身的经历——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套用瑜珈密宗仪式,或者我们今天从书本上读来的方法——一个人的身体只会成为另一个爱情的寓所。
在这些仪式里,最神圣的接触应该是那些给人以快乐的接触。所以某些仪式应该专为我们接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的身体而设。这些仪式不应用可怕的惩罚吓唬我们,而应让我们自由地流露出我们的同情和仁爱的自然能力,使我们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看到神圣。
我们面前的道路漫漫无涯,但我们终将进入一个世界,在那里,情爱可以化为性爱,性爱也可以化为情爱,在那里,性可以升华为神圣,而我们的身体便成为圣殿,在那里,我们从每一天的生活中,而不是从片刻的精神幻觉中得知,通过爱,我们能把自己扩大成六合八方。当我们拥抱的时候,我们便融为一体,进入一个神秘的境界,共同体验恋人们常说的那种至柔的激情和至美的宁静。
通往那个世界的道路是全世界众多女子和男子的选择:那是一条情爱、性爱和社会的愈伤之路。也许我们这一代有许多人永远看不到这个世界,然而那希望支撑着我们在生活中创造我们人类未完成的故事,向着未知的王国进发。
黄觉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英文版编辑部
注释:
*这里理安·艾斯勒继《圣杯与剑》一书之后刚刚发表的新著《神圣的欢爱》最后一章的节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