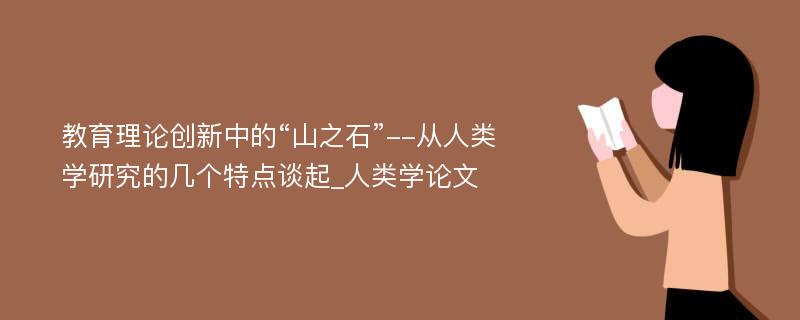
教育理论创新的“他山之石”——从人类学研究的几个特征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他山之石论文,人类学论文,特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4-0095-05
一
按照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罗杰·基辛(Roger M.Keesing)的观点,人类学的学科领域包括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四个部分。前三部分内容构成广义的文化人类学[1],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西方人类学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实际上已经走出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原始民族研究的局限,进一步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现状放到了人类学研究的主导位置;人类学研究积极参与社会决策,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并且与其他学科形成了新的更加密切的联系,推动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化。
然而关于人和人类文化的研究,并非人类学一家,实际上涉及多种多样的学科。这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的。因此,学科交叉在所难免,学科之间的相互启发和借鉴也成为必然。例如,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作为关于培养人类未来一代的研究活动,也一定像人类学一样涉及到文化遗产问题——如教育内容的选择及传承方式等问题的研究。这样,教育理论研究与人类学的研究就可以通过相互借鉴,实现共同繁荣。实际上,早在19世纪后期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就写出了副标题为“教育人类学初探”的教育名著《人是教育的对象》,此后这样的教育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前期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国内外一批人类学家也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触角延伸到教育领域。时至今日,人类学研究一百多年以来所铸就的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仍然可以赋予我们的教育研究以更新的视野、更高的理论起点和更为切实的实践指导和历史借鉴,可以成为我们教育理论创新的“他山之石”。
二
人类学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其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性视角”(the holisticperspective)。人类学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其他研究人类文明的学科,它不仅仅研究人类生活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而是要将人类及其社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试图给出一个全貌性的观察和整体性的结论。因此,人类学对某一区域的人类生活研究不仅包括这一区域的政治组织、经济状况,还包括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习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遗存、婚姻及继嗣制度、个体生理特征、儿童养育、社会历史变迁、科技发明等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学研究尤其强调各种社会事象之间的关联,强调文化的背景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从而将社会事象与各种各样其他方面的因素联系起来,进而获得对于该区域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入理解。
在教育理论研究的领域中,过去那种单纯的阶级分析的不足,已经为教育研究者所认识;但是仅仅强调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的分析仍然是不够的——虽然它们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性的东西。对于许多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如果能从一种多维的视角、整体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比如不仅注意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而且能从宗教传统、文化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加以综合研究,以整体性视角进行观察,那么将会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或者获得更好的应用效果。对于中国教育的一些问题,则应当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对教育理念和人性形成的巨大作用,并结合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展开研究。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20世纪初西方教育被引入中国所产生的作用的分析。传统的读经及科举教育,从那时起被引进的西方学校教育逐步取代,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可惜的是,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目标的对外学习和引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强民富的初衷。我们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诚然要分析当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国情,但也必须指出那时的改革未能顾及中国的民族性、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层的教育需求、承受能力的实情,以为不触及中国文化传统而简单轻易地搬用外来的教育就可以发挥效用。当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这种观点的集中反映。这是一个相对自我封闭的民族在追赶世界潮流时,产生的对异文化的理想化观察所导致的盲目的、浪漫的和生硬的嫁接过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教育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不仅不能停留在单纯性的译介上,而且也不能停留在仅仅对国外教育的经济、政治及历史的分析上。众所周知,宗教渊源和个人主义哲学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忽视了这两个重要方面,西方文化就失去了灵魂,西方教育思想或制度的核心或特征也就无从谈起。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对西方宗教理念与教育理论的关系和对西方个人主义与教育关系的研究都极为薄弱。此外,在我国加入WTO后,西方各国学校将直接抢滩中国,教育竞争在所难免,同时也将具有各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更为直接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这就需要我们切实把握我们自身的文化教育基础和特色,也需要我们清楚地了解国外文化教育的历史传统特征,方可从中提取为我所学所用的内容,并避免在引进外国教育理念或方法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优秀教育传统造成损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一些教育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同时,也进行较为深入和广泛的东西方人类文化研究,以便从宏观的角度同时把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用以指导相关的教育研究。
再如关于“应试教育”特征及其根源的理论分析。按照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视角”和“背景分析”的要求,这一问题必须置于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中国儒家传统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后来又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和“教,政之本也”(《春秋繁露》)的观点,显示了中国传统教育极为显著的政治性和伦理性特色;同时,儒家礼仪的政治和伦理观念特别是其中的等级规定,已经先行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单向性和依附性,以及在教育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加以强调的集体意识等。教育中渗透的这些传统文化成分,使得在中国的教育和教学过程中,教育对象总是表现出被动的受教特征,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族群性的约束性文化表现。[2]时至今日,这种约束性文化依然在教育上延续,仍然作为一种文化滞后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教育意识。“应试教育”就是这种约束性文化在现代中国教育现实中的表现之一。这就是应试教育的根本特征和终极性的根源所在,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根源于“家长的功利心态”“考试制度的不配套”、“社会流动制度”和“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等等。总之,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看待中国教育问题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深入关注儒学理念长期以来对教育理念和人性形成的历史作用,并结合经济及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给予整体性的关注。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其研究过程中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即田野工作、田野调查)。所谓“田野作业”,是指人类学家为了深入而真实地了解某一研究区域中人类的行为和文化特征,而将自己融入该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包括与调查对象至少有一年时间的共同生活,学习和使用他们的语言,亲身参与他们的社会文化及生活活动,同时实施多种调查方式,并据此作出详细的文字、语音或图像的记录,从而获得研究对象的各种真实的文化材料,进而依据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在人类学界,这种“田野作业”已经被看成人类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研究技能和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实践基础。它反映了人类学研究者极为注重对基层民众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并要求在此之后才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研究。所谓理论来源于实践,本是众所周知的原则,而人类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就是将这种对于基层民众社会文化生活活动的关怀常规化,进而将这一工作变成了研究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和一种可操作的研究方式。可见,人类学的知识建构过程“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经过田野工作回到书斋,再把得自生活的新知写进书本”[3]。
与人类学的这种极强的实践性研究相比,当今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就显示出了较为严重的远离社区和农村等基层教育的偏向。例如上百种在书房中、从书本到书本而写就的“教育学”等其他形式的“专著”,内容大同小异,难以见到创新的理论成果;一些在中小学进行的教育实验,在相当程度上远离基层民众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需求和教育的文化底蕴;一些教育专家常常只是站在指导的位置上,只求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研究或进行实验,并最终验证自己所设想的“教育理论体系”。在这类教育研究过程中,极少存在研究者以平等的身份较长时间实地亲身参与并多处观察社区及农村基层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究方式。又例如,以“减负”和批判“应试教育”为开端和特征的“素质教育”运动及其理论研究,最早不过是基于媒体对学生“离家出走”、暴力行为以及所谓“高分低能”等方面数量不多的极端事件的报道,引发高层和专家的注意,从而自上而下地推行开来——也就是说,素质教育运动的基础并不包含教育研究者对于全国大量基层学校的较为广泛和长期深入的实践调查。“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主流,此后逐渐变成了对教育政策的阐释、补充说明和再论证,包括形势的分析、素质教育的含义以及将若干地方看成素质教育的“试点”等,找到一两个开展素质教育的“成功”事例,从而证明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树立起实施素质教育的“样板”,告诉人们应当如何贯彻。这大概也是造成“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现象至今仍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说到教育研究中像样的实际调查,反而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专家们做了更多的工作,例子之一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加拿大有关学者对中国农村地区教育作的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该项调查的成果《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24县调查》以及该所其他涉及教育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可以说为教育研究者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值得学习的研究榜样。
毋庸讳言,人类学研究者中也不乏弗雷泽(J.G.Frazer)那样的所谓“安乐椅上的书斋学者”,他们不屑于跋山涉水进入另一种文化之中自行观察和记录,却也取得了惊人的研究成果。然而这类人类学家并不是人类学研究者的主体,而且他们的研究方式也并没有改变人类学研究中“田野工作”的重要地位。因为实际上这些人类学家仍然需要利用已有的田野调查的丰富成果,或者集他人调查资料之大成展开工作。“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学科的一种基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其过程本身也是人类学家的文化探索过程。只有田野工作的实践活动,才能给人类学研究提供宽广的基础,提供取之不尽的动力。总之,一切学科理论研究的创新,最终都要基于长期而认真的实践活动;只有深入细致的实践研究,才有理论创新的可能。教育理论创新也不例外。
人类学研究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跨文化研究视角”(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或“交叉文化分析”(cross cultural analysis)。人类学的这种比较和交叉性的文化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按照尤金·科恩(和爱德华·埃姆斯)的分类[4],人类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可分为“有限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和“统计比较”(statisticalcomparison)两种。“有限比较”通常是比较处于同一地区不多的几个文化群体,它们有许多相同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便于进行背景分析,但它们之间的少量的差异却是比较分析的主要对象或关键。这种比较方式寻求的是对少量相似社会的微小差异的理解,但却难以说明更广大范围内人类文化的差异和变迁。“统计比较”则缩小了这种缺陷。摩尔根(和爱德华·泰勒)的进化论人类学研究,就是建立在三百多个社会样本之上的。及至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耶鲁大学开始分类编辑《文化材料概览》,形成了一个包括一千多个社会单位的调查资料的人类学资料库,即所谓“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the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并输入了计算机,为人类学研究复杂的大型社会创造了条件。
第二,从上述比较方法的含义可知,人类学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建立在大量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的,是对大量田野工作记录的分析和抽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家可以控制一些可变因素,建立假说,然后检验假设和决定是否修改或抛弃原有假设;其他人类学家也能够对已有的假设或结论再度进行调查研究,再度加以检验。因此,“交叉文化分析达到了科学的方法的基本标准之一——能够检验和再检验假说。”[5]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使用的实验技术相似。
第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跨文化视角”所依据的指导思想,即所谓“文化普同论”(culturaluniversalism)和“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这一理论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是生物学上的同一个种属,任何一个人群都不比其他人群进化得更多;任何地方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人都应当是平等的;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的价值,无优劣之分。因此,各种人群之间应当采取宽容的态度,互相理解和尊重,应当反对民族中心主义或文化沙文主义。许多人类学家都认为,基于这种多元文化观点的人类学研究,可以保证其科学性和正确性,因为如果认为某一种文化高于另一种文化,必然会造成理解上的偏颇,既不会获得真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也将达不到预期的理论研究成果。
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统计和比较的方法,这是教育研究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我们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缺少长期深入的基层社会调查,缺少具体、实际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就教育统计来看,其结果的真实性往往就要大打折扣。例如涉及国内某一地区教育的一些基本数据,就只能够依靠当地行政机构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由此也会受到某些行政官员的影响,服务于一些行政长官的需要,从而失去学术性和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另外在教育的“比较研究”方面,建立在教育研究者长期亲身参与、观察和调查基础上的国内民族教育的比较研究成果可以说还比较少见。同时,对于国外教育经验的不适当的观察和运用,至今并没有在我国教育界内外销声匿迹。例如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之时,便有一系列介绍各国“实施素质教育”的书籍和文章的问世,似乎国外早就在推行“素质教育”,而且做得如何如何的好。那种将国外教育理想化并作为我们素质教育理论的注脚的倾向,那些照搬外国以至有损我国基础教育“双基”质量的主张的出现,都是由于缺乏文化分析的态度而造成的,实质上也是不尊重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异文化盲目推崇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能注意借助文化人类学“文化普同论”和“文化相对论”的理论视角看待异国的教育问题,或许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一些人的这种不良倾向。
近二三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进程加快,造就了人类学研究的全球化背景。此后人类学界关于“文化全球化”的解说与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学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视角”和“交叉文化分析”理论,显示了人类学学科对人类现实的密切关注和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人类学界对“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可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参考。例如,以福斯特(Robert J.Foster)、费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一种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也不是文化的同一化,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文化”或者“图像、人民、货币、技术等各种主体和客体”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的流动;流动不是单向度的;面对这种流动,不同文化的接触所引起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反应和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必然的现象;对本土化和传统复兴现象的研究是人类学“全球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随着人类学关于全球性文化交流和互动研究的兴起,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也更加丰富,并与各种新的跨学科研究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6]。人类学关于“全球化”理论的这些进展,对于我们处理国际教育交流与弘扬优秀教育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有有益的借鉴意义。
三
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文化人类学都是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人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大约80年,可能比西方教育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还要短一些,但却取得了更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英文化人类学和德国的哲学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包括教育人类学方面的成果)被介绍到国内,老一辈人类学家的重要著作也得以再版或重印,新一代学者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不断面世,从而开创了国内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和教学的新特征。人类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也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以深入的实际调查为基础,同时注意加深对现代人性、现代社会的根本需要的理解,加快对现代社会及生活转型的反应速度,从而取得对各种教育问题的深层认识,获得教育理论创新的灵感,不至于在教育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闭门造车,将过多的精力用在主观地构建各种各样的“教育××学”或“××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方面。
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赫伯特·茨达齐尔(HerbertZdarzil)曾经指出:人类学“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人的行为动力和目的以及人的发展规律等见解从一开始就对教育思想有着重要作用”[7]。西方“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B.Tylor)也曾指出:人类学在教育研究中的加盟,将“快捷地促使研究负担的减轻,而不会加重……它把日常教育的零散科目合为一个便于掌握的整体”[8]。的确,尽管人类学的观点及方法并非十全十美,尽管人类学研究不能替代具体的教育研究和成为整个教育科学的全部基础,但人类学研究所包含的对人的各个方面的全面性的研究,它的一系列研究特点,对于我们教育理论的创新仍然有着多方面的启示。除了上述几方面之外,人类学研究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关于文化适应(濡化)的观点、两代人之间三种文化传承模式的划分(所谓“三喻文化”)等等,都对教育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学这个“多面孔”的学科对于教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影响和贡献也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切实加强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力度,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将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