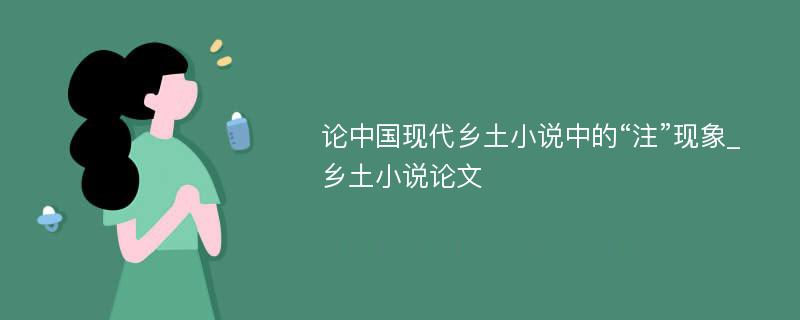
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加“注”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中国论文,现象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附以注释是学术性论文的基本范式和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乡土小说也时常出现加“注”的现象。其实这并不奇怪。文艺性作品的加注并非自现代小说始,古代诗文中早已出现过这种情况。迄今为止,有关小说注释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版本的差异,小说文本的注释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家创作时所加的“原注”,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创作的一部分。另一种则是编者所加的“编注”。在一般人眼里,不论是原注还是编注,其目的都是为了便于读者的文本阅读。当然,这种说法并不错。然而,“原注”同作家的知识结构、叙事修辞、文艺思潮乃至创作生态的关系常为人所忽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更是编注较为单一的解读功能所无法替代的。这里,我们拟就作家的“原注”为对象,探讨与此相关的问题。
一
就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而言,小说“原注”的内容大都与民俗学方面的知识有关①。“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域的民俗,在给异域读者带来审美享受的同时,客观上也给阅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作家主观上也不是要把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写成一个谁都不懂的东西。“原注”显然是作家针对文本解读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一种有别于主体叙事的文字。某些情况下,没有文本注释可能会影响读者的理解和阅读兴趣。
可以看出,阐释、说明和补充是作家注释的基本目的,但并不是惟一的意义功能。这是因为,有些文本注释在解读的同时,因其修辞性的意义而具备了一定的审美功能,体现出作家多样化的艺术构思和叙事技巧。例如,茅盾对乌镇蚕事“禁忌”(《春蚕》)的注解,反映出祈求祥瑞的民间心态,小说文本显然不适宜安排这种非叙事性的成分。当然,最典型的要算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作家别具匠心地将民间“求雨”习俗中有关“癞痢头孩子”的民间故事置于“原注”中进行叙述:
这位脾气好的菩萨,叫做“西风癞痢”。据说玉皇大帝是他的外公。外公派他一件有趣的差使:职司山乡地方的晴雨。每逢六月,也不知他是孩子气玩乱了心,还是其实做不得主,天老是一晴就晴上十天半个月,让太阳把田里土壤晒开裂,河水干涸到露出滩石;正要飞速地发长的稻稞,都变得垂头丧气,一天天萎黄。大家一看这情形急得要不得,照例先禁三天屠,表示向这位癞痢头孩子以及他的上司下属忏悔求情。还不下雨,村上人把锣一敲,邀上一百二百人,戴起杨柳圈,赤着脚,排成行列,火把,龙旗,香案,鸣锣放鳅,星夜跋涉三四十里乱石荆棘路,到承流峰顶的龙王潭里捉起一条雨鳅,虾,四脚蛇……或者什么的,总之是条“真龙”,供到这里龙王台山来。这是瞒住癞痢头孩子,贿赂恐吓他的下属的办法,如果仍然不下雨,那可不客气了:选几个粗壮汉跑到斗南山西风庙里由神座上把癞痢头孩子绑押到这里来,叫猛毒的太阳把他一头癞痢晒得出汗冒油。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人物小说、性格小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正格和路子。这一时期,作家对“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也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如果作家将“求雨”的介绍置于小说“环境描写”中,那么叙述视点、叙述时间极易造成叙事结构的混乱。而取消这一段文字,文本相应的关涉和乡土情调似乎又不能得到很好的表现。作家巧妙地采用注释的方式,既解决了小说整体结构的协调性问题,也为文本的阅读做了必要的补充。可见,小说注释并不仅仅局限于读者对小说文本的理解,也同作家的艺术构思与小说叙事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属于叙事修辞和技巧层面的问题。注释理应成为小说文本的有机部分。
作为环境的重要构成,中国现代小说的风俗画、风情画与风景画的描写,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审美维度之一,构成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作为文化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化,民俗是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最为感性的一面。因此,民俗描写体现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现代化、民族化的重要特征。注释对民俗事象的补充和说明,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
其次,“原注”为考察作家、文本和创作提供了可行性的研究视角,从中可以发现现代作家与中国民俗学的深刻结缘和良性互动。与编者添加的编注不同,“原注”大都产生于作家艺术构思和创作实践的过程之中,包含着丰富的创作意念和精神发现。因此,作家的创作视阈、创作心态、思维结构等等都可以从“原注”中寻出蛛丝马迹。第一,“原注”基本能够体现现代作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注释的作品就没有写实的精神)。作家对乡土社会原生态的客观再现,必然涉及到乡风民俗,并对某些独特的民俗加以注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茅盾之于浙江,蹇先艾之于贵州,王实味之于河南,台静农、吴组缃之于安徽,罗淑、李劼人之于四川,萧军、端木蕻良之于东北,叶紫之于洞庭湖流域,周文之于川藏边地等等,作家对不同地域的民俗注解,直接反映出作家创作题材的广阔性,绘制了一幅完整而真实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全景图。第二,“原注”可以洞见作家民俗学知识结构与创作之间所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作家从民俗生活汲取创作养料的同时,民俗文化也制约着作家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以方言为例,作家采用特定地域的方言作为小说语言材料,有助于营造特定的情境、氛围和艺术典型。同时,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有机部分,方言习俗也体现出不同地域民俗群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观念。
最后,“原注”与小说涉及的民俗事象一同构成了民俗文献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文学家“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分历史,就是说风俗史”②,茅盾也认定“文学家是保存古代神话的功臣”③。虽然这是针对神话而言,但对作家在保存民俗文献方面的贡献具有普泛性意义。郭沫若将李劼人小说比作“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④,明确析示出作家创作的“风俗志”倾向。既然是针对作家作品而言的,那么小说“原注”无疑强化了这种创作风格。另外,“原注”相当大的部分是有关方言的注释。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语言符号系统和制约语言符号系统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给不同文化地域语言信息的交流、传播带来了实际困难。而对方言注释的研究,既可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心理,同时也丰富了民俗学、语言学研究的资源。
二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注释的大量出现,首先与作家民俗学意识的高度自觉有着极大关系。从民俗学方面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与民俗学存在着极为深刻的关联。它们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阐扬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不仅在发展阶段上十分切近,而且相当多的现代作家都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俗学活动,成为中国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力量。尽管中国现代作家对民俗学的倡导偏重于文艺审美,但民俗学语境和学科知识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杨义曾就许地山民俗学、宗教学背景与创作的关系指出:“这种潜心研究之所得,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谋篇立意和艺术想象。”⑤ 作家民俗学意识不仅表现在构建主题、提炼情节、塑造人物,自觉地展开民俗风情的描写,而且也体现在对作品的民俗注释上。鲁迅是现代最早具有民俗学意识的作家,1913年,他就呼吁:“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⑥ 不过有意思的是,鲁迅第一个短篇集《呐喊》并未出现民俗方面的注释。直到1925年,《彷徨》小说集里的《长明灯》、《离婚》才有了浙东方言俗语的注解。据现代作家苏雪林的回忆:“胡适常惜《阿Q正传》没有用绍兴土白写,以为若如此则当更出色。”⑦ 乡土作家台静农亦曾参与当时的民俗学活动,并在家乡淮南搜集民谣。民俗学活动对他后来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小说《拜堂》有六处皖西方言的注解。由于独特的地域性和文化差异性,蹇先艾的部分小说(如《在贵州道上》、《到镇溪去》等)对贵州边地民俗的注释也相当普遍。
茅盾鲜明的民俗学意识与当初新文学对于神话审美价值的探讨有着直接关系。“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因而也给我一个机会对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这就是我当时从事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⑧ 1928年,茅盾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把神话的地位提升到民族文学源泉的高度。他说:“就文学的立点而言,神话实在即是原始人民的文学。迨及渐进于文明,一民族的神话即成为一民族的文学的源泉:此在世界各文明民族,大抵皆然,并没有例外。”⑨ 茅盾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十分重视民俗审美功能的构建,《春蚕》不仅对乌镇“蚕事”习俗进行艺术化再现,而且对其中独特的民俗事象进行了注解。吴组缃在清华学习期间得到朱自清和郑振铎这两位文学兼民俗学的名家指导,对他民俗学意识形成以及乡土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前所述,《一千八百担》有关“癞痢头孩子”的注释具有一定的叙事学价值。李劼人对四川成都的乡风民俗有着特殊情结,曾写下《说成都》、《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和《旧账》等一系列民俗学文章。作家民俗学功底和求实科学的精神成就了他的小说创作。另外,萧军、端木蕻良、周文等30年代乡土作家的小说注释,都显示出相当厚实的民俗学修养。
除了中国现代乡土作家民俗学意识的自觉外,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对作家小说的加“注”行为也构成了实际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创作思潮呈现出一种大众化、通俗化、民间化的发展态势。“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取代“文言”而起的白话文学思潮,要求作家采用明白晓畅、富有活力的民间白话从事创作。不同地域的方言虽不可能统统写进小说,但是,即使少量的方言语汇有时也会给异域读者的阅读带来麻烦,创作话语的两难为现代作家加注提供了可能。例如,鲁迅的《离婚》就“对对”、“逃生子”等浙东方言进行了注解。这些注解对于异文化区域的读者来说非常必要,不至于引起文本的误读。“何况两岸多老二,这些柳叶恶又恶,不若就地齐下灰”是高世华《沉自己的船》中的民歌。没有注释,读者似乎很难将“老二”、“柳叶”与匪、兵联系在一起。王实味的《杨五奶奶》所提及的“秧大麦”习俗,也只有看过注释才知道那是“一种极野蛮之风俗,皆施之于泼毒之恶女人。闻系以小锥刺下体,就每创口填入大麦一粒。主其事者皆壮妇”⑩ 可以看出,白话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民间方言进行加注现象的出现。
“‘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初的倾向和意义。”(11)“主张白话者,从语言依附于生活出发,更看重表达的内容,在表达的形式方面,他们更多地考虑大众接受的可能。”(12) 30年代,左翼大众化运动中这股民间化创作思潮更为强烈和显著。1929—1935年,几次“文学大众化”的论争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把“必须具有比较通俗的形式和为工农容易了解的语言”作为文艺大众化的起点。甚至有的作家如欧阳山、草明等开始创作“方言小说”。所有这些对“新文艺腔”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在30年代的接续和发展,文学与民俗学特别是与民间文艺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作家的民间意识和本土化意识,加上当时民俗学活动的蓬勃开展,使得30年代作家在他们乡土作品中加以注释的情况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作家有茅盾、吴组缃、叶紫、萧军、李劼人等等。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讨论以及解放区工农兵创作的兴起,文学创作的大众化、通俗化、民间化更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原注”并不多见。当然,这一现象与文学所处的特定文化语境有密切关系(后面将进行具体分析)。总之,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通俗化、民间化的创作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家的注释行为。
除了现代作家民俗学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创作思潮外,是不是还存在别的原因影响作家在创作中的注释行为?严家炎认为:“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13) 这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作家走出故乡偏僻的一隅,侨寓在现代都市,由此获得了观照乡土的审美视角。第二,在现代都市,绝大多数作家都以写作为生,所以离不开出版商和书店的商业化运作。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使得出版商特别关心作品的出版发行和销量。从作家方面来看,一方面,受制于书店与出版商,他们不得不考虑创作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作品被接受的程度;另一方面,作家乡土题材的创作对现代都市和异域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新奇和富有吸引力的,但作品涉及的独特风俗,特别是方言民俗给阅读带来了困难。从语言学角度看,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语言,方言有着相对稳定的自足自律的系统。它的“所指”(概念)、“能指”(音响形象)及其关系,都是异文化区域的读者不易理解的。因此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便是对这类民俗加以注释,才不至于妨碍读者阅读和小说发行。例如,蹇先艾的乡土小说大都取材于偏远的贵州乡村。当地特殊的民俗风情给读者带来了新奇感和审美餍足,然而小说众多的生产、生活和方言民俗无疑又给读者的阅读制造了障碍。此外,周文对川康边地的民俗描写,萧军、端木蕻良对东北黑土地的描绘,李劼人对成都日常生活的描摹等,都采用“原注”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作家写作与受众阅读的矛盾。拿李劼人来说,其“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两百多条“原注”绝大部分都是有关方言的,具有较高的民俗学和语言学价值。可以看出,依靠书店发行、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作家,必须充分考虑到受众的阅读需求和审美期待,这是作家在小说中加注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
三
毋庸讳言,在对“原注”功能及其相关分析的同时也存在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中,对小说进行加注主要集中在有数的一些作家身上,而多数作家并未对其描写的民俗进行注释。第二,“解放区”小说、“京派”小说和“七月派”小说没有注释的现象如何解释?
解释这种现象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如前文所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客观事实的存在,那就是现代作家的民俗学学殖背景并不一致,民俗学意识的自觉程度也各有高下。因此出现上述情况在所难免。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民俗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求雨”为例,不同地域的作家如王任叔、王统照、吴组缃、李劼人、王西彦、叶紫、韦君宜等人都描写过此类民俗(14)。随着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虽然民俗在具体形态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其内核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类民俗对于异域的读者来说也不算太陌生。三、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广大区域基本可划分为儒文化区域和非儒文化区域两大板块。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与对话,非儒家文化区域的民俗往往保存了比较完备的原生形态。相对于异文化区域的读者来说,这些民俗往往就不是很好理解。特别是那些不同方言区的语言民俗尤为如此。客观地说,小说文本出现的方言成为了异域读者阅读最主要的障碍。这或许是蹇先艾小说出现大量“原注”的缘故。
解放区小说创作的主体是乡土小说,并涌现出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这两个成熟的乡土小说流派。解放区小说虽然描写了众多民俗,但文本并未出现注释。需要指出的是,解放区作家的民俗学意识是非常自觉的。他们在创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民俗学研究成果。他们的民俗学研究带有明确的文学功利目的,即运用民间文化资源服务于当前的文学创作。当然,除了上述分析以外,似乎更应该从解放区的文化生态和文艺的独特性方面去考虑。第一,解放区地域环境的封闭性。作为红色政权的根据地,延安等解放区一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重重封锁围剿之中,形成了相当恶劣和封闭的文化生态。第二,解放区文学活动的独特性。严酷的战争环境改变了作家创作心态,解放区文艺因此而有着比较实际的功利性目的,即注重发挥文艺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特别是在毛泽东的“讲话”指引下,解放区作家以根据地现实生活为题材,自觉表现解放区军民火热的战斗生活。第三,根据地文艺出版发行的单一性。在与外界阻隔的情况下,解放区文艺的发行渠道受到严重限制,文艺作品的出版和发行主要是面向根据地的广大工农兵读者。另外,解放区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民间化倾向,也为广大根据地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便利。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生态中,受众并不存在多少阅读的隔阂和障碍,加注显然是多余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解放区作家在创作时所设想的读者与半个多世纪后今天的读者在文本接受方面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见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15) 解放区小说中那些独特的民俗事象,对于当下的读者或许有些陌生。这可能是今天的编者需要设以“编注”的原因,自然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京派”作家描写了大量的民俗事象,尤其是废名、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他们的小说按理说会有不少关于独特地域民俗的注解。然而恰恰相反,他们的小说文本注释极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原注”与作家的文体意识有关。众所周知,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小说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散文化叙事体征。周作人曾对废名“随笔化”、“散文化”小说体式作过这样精彩的描述:“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萦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16) 对“京派”散文化叙事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与周作人的看法不一样,苏雪林对小说散文化、随笔化的叙事风格并不是十分认同。例如,她在肯定沈从文小说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正是“过于随笔化”,“好像是专门拿Essay的笔法来写小说”。“作者写文字时信笔挥洒不着意”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17) 当然,沈从文也是个明白人。在《〈石子船〉后记》中他说:“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全到。也像是有意这样作,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18) 虽然周作人和苏雪林对小说叙事的理解和态度有很大出入,但是他们都抓住了小说叙事的随笔化、散文化的文体特征。客观说来,小说散文化对文本结构的忽视和从容书写的追求,使得作家有足够的叙述时间和空间来阐释民俗事象的种种。不妨看看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第八章对故乡“放猖”风俗的描写。小说不仅具体叙述黄梅的“五猖庙”,装扮“猖神”孩子的“许愿”,以及“打脸”、“练猖”、午后的“放猖”、夜间的“游猖”和“收猖”等一整套民俗活动的程式,而且还穿插“莫须有”先生(作家)孩提时代对于这一习俗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感受。极为细腻的民俗描写既体现了作家自觉的小说文体意识,也与其对“注解”独到的看法不无关系:“作文是不应该要人作注解的,如果需要注解那就非自己注解不可,到得要旁人注解便不成其为文章了。”作家所说的“注解”当然不是指文中加注,而是对相关内容进行文本叙述。废名还以小说主人公的口吻表达了对小说散文化叙事的认可:“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必于人情风俗方面有所记录乃多有教育的意义。最要紧的是写得自然,不在乎结构,此莫须有先生之所以喜欢散文。”(19) 正因为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独特的小说文体意识,文本无须注释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与废名在民俗叙述中掺杂着主体审美感受不同,沈从文则偏重于对民俗事象的客观描述。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小说加注的情况并不多见。不过,作家采用另一种特殊方式对小说民俗进行更为集中的注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似乎是惟一一位对小说进行真正民俗学意义上批注的作家。1936年3月,沈从文对《边城》所涉及的部分民俗事象加以注释。1944年12月间,他又对《长河》进行更为系统的民俗学注释。虽然这两篇小说的注释都是在小说发表后才做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们视为“原注”。这是因为,两篇“注释”折射出沈从文一贯“抑郁”的创作心态。忧郁正代表了作家整体性的审美风格和美学特征。我们从作家对《边城》的“批注”中不难发现,那些与注释无关,但又反复出现的“无聊”、“凄凉”、“难受”、“不幸”等语汇,恰恰反映出当时作家的忧郁情绪(20)。不妨再看看沈从文在《长河》批注后留下的文字:“十二月十五日校毕,去《边城》完成刚满十年……长荣、子和、老三等战死已二年。陈敬摔车死去已一年。得余离开军职已三年,季韬、君健两师部队在湘中被击溃亦已四个月。重读本文序言,‘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高尚的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热忱与虔敬态度,惟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写它,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逝者如斯,人生可悯。”(21) 《长河》通篇散发出的抑郁伤感的气息,与小说“序言”那种乐观进取的心态相去甚远,倒与“批注”时流露的心境颇为协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青年军官的命运似乎改变了作家对战争的看法。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内战使得沈从文的忧郁表现得尤为深切。此时作家的忧郁不再是早期个人生活的忧悒,也不是在文学论争的漩涡中左右不讨好的抑郁,而是站在民族、人类、人性的高度,以悲悯的眼光和情怀审视这场战争。一方面,作家超越战争的具体形骸,看到战争罪恶丑陋的一面,提出了战争是非理性的产物的见解。战争在他的眼里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露出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22)。另一方面,沈从文凭借“个人独自为战精神”(23),试图用理想的“抽象”重塑现实的希望彻底落空,以致沉湎于忧郁的心绪中难以自拔。这个时期,作家文章中最常见到的是“崩毁”、“疯狂”、“发疯”等一些字样。1948年底,沈从文在完成《传不传奇》后,因极度的忧郁,不得不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
当然,话也得这么说,文学作品中的忧郁和作家的忧郁,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忧郁似乎还不完全是一码事。“人的忧郁以及文学作品中所描述、渲染的忧郁并不一定是消极的东西。事实上,忧郁可使人深思,唤醒人的良知,继而改变人类的困境。理解欣赏文艺作品中的忧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排遣个人的忧郁,起到‘净化’(catharsis)作用,使个人的忧郁融入人类整体的忧患之中,从而唤起对同类的同情,对万物的爱惜,使个人的心灵升华并靠近崇高(sublime)的理想境界。”(24)
“七月派”乡土小说没有加注的现象,与这一流派所倡导的“主观现实主义”理论有着直接关系。主观现实主义创作强调突进小说人物内在丰富的精神世界,凸显“主观”把握现实世界的审美方式。胡风认为:“客观对象没有进入人的意识以前,是‘不受作家主观影响的客观存在’,但成了所谓‘创作对象’的时候,就一定要受‘作家主观影响’的。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创作’。”(25) 在这一理论倡导下,作为客体的风俗、风景和风情的描写,成为作家主体乃至小说人物精神发展的对象化存在,普遍呈现出一种高度写意化的美学特征,显然与客观现实主义创作带有根本性的区别。正是这种将“主观战斗精神”的因素导入现实主义创作之中,使得“七月派”小说对民俗事象的客观描写极为有限,自然也就谈不上给民俗加“注”了。
注释:
① 对《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49)所涉及的乡土小说进行分析后发现,小说“原注”绝大部分都是有关民俗方面的内容。其中以不同地域的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以及民间会社的行话、术语、俚语等语言民俗最为普遍。
②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陈占元译,载《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茅盾说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④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载《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
⑤ 杨义:《许地山:由传奇到写实》,《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⑥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76页。
⑦ 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⑧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载《中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⑨ 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茅盾说神话》,第158页。
⑩ 王实味:《杨五奶奶》,《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
(11)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12) 庄锡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8页。
(1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14) 张永:《从一民俗个案看中国现代作家审美取向》,载《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15)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16) 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17) 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页。
(18) 沈从文:《〈石子船〉后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19)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倪伟编《纺纸纪》,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17页。
(20) 沈从文:《〈边城〉题识五种》,《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443页。
(21) 沈从文:《〈长河〉自注》,《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82页。
(22) 徐庆全:《陈沂关于沈从文致周扬的信》,载《黄河》2003年第6期。
(23) 《沈从文致张以瑛的信》,参见徐庆全:《陈沂关于沈从文致周扬的信》。
(24) 汪榕培、王晓娜:《忧郁的沉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8页。
(25)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
标签:乡土小说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沈从文论文; 边城论文; 散文论文; 作家论文; 民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