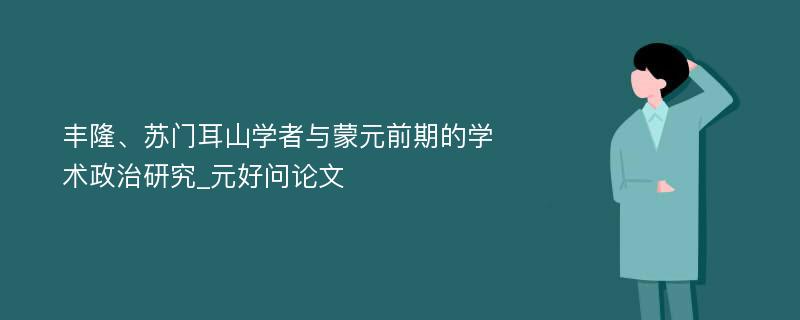
封龙、苏门二山学者与蒙元初期的学术和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学者论文,学术论文,政治论文,苏门二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封龙山和苏门山都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东麓。封龙山位于河北省鹿泉市与元氏县的交界处,东北距石家庄市区22公里。苏门山则位于河南省辉县市的西北,距市区2.5公里。从全国范围来讲,这两座山虽不算特别有名,却也以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享有一定的声誉。历史上有众多名人与它们结缘,留下的文化遗迹也相当可观。在蒙元初期,封龙、苏门二山与当时的学术和政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封龙山与“龙山三老”
金元之际,广大华北地区先后崛起了众多的汉人武装。这些武装集结起来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兵自保和抗击蒙古。后来迫于蒙古军的强大压力,纷纷接受蒙古统治者收编,其首领成为雄霸一方的汉人世侯。一些汉人世侯常有宽纵俘虏、救济贫民的行为,而且兴学养士,对于维护一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乃至保护和发展汉族文明,有一定的功绩。其中,最强大的集团有东平严实、益都李全、顺天张柔、真定史天泽。封龙山,正处于真定路的辖区之内。
封龙山原名飞龙山,因山势如伏龙欲飞而得名。此山有着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山中的汉碑、书院、禅林、道观在我国文化史上居重要地位。蒙元初期的封龙山,活跃着“龙山三老”。《元史·张德辉传》:“与元裕、李冶游封龙山,时人号为‘龙山三老’云。”张德辉(1195-1274)为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裕即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1190-1257),为忻州秀容(今属山西)人;李冶即大数学家李治(1192-1279)(注:“黄丕烈、施国祁据元遗山所撰李氏碑,称其兄名澈、弟名滋考定,其名实作‘治’而非‘冶’;又有人谓‘冶’是他后来的改名。”(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p8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近人陈叔陶曾作《李冶李治辨》(《史学集刊》三期,1937年4月)进行辨析,今人刘德权点校《敬斋古今黊》“前言”亦曾涉及(中华书局1995年版),可参看。),为真定栾城(今属河北)人,金朝灭亡前后曾流落山西的忻州、崞县之间。三人中,元好问年最长,也最为今人所熟知。他不仅是冠盖金、元两代的大文豪,而且是于乱世中致力于保存文化的有心人。金亡之前,他上书耶律楚材,请求保护大批著名的文人学士;金亡之后,他编辑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保存了251位金代诗人的2062首作品(注:统计数字引自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p122(天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家乡构筑野史亭,苦心搜寻金朝史料,编成《壬辰杂编》、《金源君臣言行录》等史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他还经常来往于华北各地,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到真定路、东平府等处讲学等等,为挽救和复兴文化教育事业而四处奔波。他为中原传统文化在乱世中存一命脉,真可谓呕心沥血(注:有关金元之际元好问的文化活动及其意义,已有程千帆、姚从吾、黄时鉴、李正民、降大任、刘泽等等先生进行过探讨,可参看相关论文、著作。)。
封龙山是河北地区书院的发祥地。北宋时,河北见诸记载的书院仅有三所,全在封龙山中。据《元氏县志》(注:清光绪元年刻本。)卷七:封龙山的三所书院分别为封龙书院、中溪书院、西溪书院。李治晚年迁至元氏,在封龙山下买了田地,又应邀在封龙书院(或中溪书院)讲学(注:方志中的相关记载有些混乱。也可能李治在两所书院都讲过学。)。在讲学的同时,他潜心钻研数学理论,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的名著《测圆海镜》,由此,他被誉为宋元四大数学家之一。《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天元术”的著作(注:莫绍揆先生《对李治〈测圆海镜〉的新认识》(《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与通行看法不同的意见,认为《测圆海镜》不是讨论天元术的著作,而是一部几何学著作。卷一《识别杂记》纯粹是几何理论,卷二以下运用天元术来解勾股形,实际上是几何学的应用部分。可参看。),而所谓“天元术”即运用代数并通过列方程、解方程而求出未知数的方法。李治的“天元术”是世界上最早的半符号代数学,代表了当时世界上高次方程数学的最高成就。此外,李治还著有多种著作,如《敬斋文集》、《壁书丛削》、《泛说》、《益古演段》及《敬斋古今黈》。前三种已亡佚,仅有极少部分的内容零散保存在其他文献中。《益古演段》是一部根据前人《益古集》增衍而成、旨在普及“天元术”的数学入门书。《敬斋古今黈》是一部笔记类著作,内容遍及哲学、历史、文学、天文、数学及医学,显示了李治多方面的才学。然而,据王德渊《敬斋先生测圆海镜后序》记载:李治临终前嘱咐儿子说,平生其余著述死后可以全部烧掉,惟有《测圆海镜》一书是心血凝聚而成,希望能够得到广泛传布,永垂不朽(注:《测圆海镜细草》卷末,《丛书集成初编》本。)。可见其真正志趣所在。在与蒙元关系方面,李治虽然前后三次受忽必烈征召,却只在至元二年(1265)短暂地任过一年的闲职,次年即告老病而返回封龙山,直至去世。与张、元相比,可以说,李治与封龙山关系最为密切。
三老中,张德辉是惟一长期仕于蒙元者。张德辉虽然不以学术、文章闻名,但颇有治才,且刚直敢言。他先后受到史天泽、忽必烈的赏识,在历任官职上都有良好甚至优异的表现。在文化救亡方面,他所做的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件事:1.减轻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据《元史·张德辉传》,蒙古定宗二年(1247),忽必烈曾问张德辉:“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以亲身体会作出了恳切的回答,使忽必烈相信金朝灭亡的责任根本不应由儒者来承担。2.荐举有才德的儒士。定宗二年,张德辉向忽必烈荐举魏璠、元好问、李治等二十多人;第二年,又荐举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槃等人。当然,这些人不见得全都愿意为蒙古人所用,但他们利用被征召的机会向忽必烈宣扬儒家文化,无疑使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在蒙古统治者那里不断得到增强。3.请忽必烈当“儒教大宗师”。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和元好问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奉请忽必烈充当“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张德辉还趁机请求蠲免儒户兵赋,得到批准。这是张德辉所做的最常为人提起的一件事。虽说,请不大懂得儒学是怎么回事的人充当“儒教大宗师”,张、元此举多少有点滑稽,然而,忽必烈无疑是当时蒙古统治集团中最有雄才大略也最倾向于行汉法的人,他从中看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企求;而张德辉、元好问呢,也为经受冲击的汉文化和朝不保夕的儒士们找到了有力的支持。显然,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此外,张德辉对重振真定地区教育事业也颇有贡献。张德辉提调真定学校时,曾倡导并主持重修了元氏县的庙学(注:李治《真定府元氏县重修庙学记》,《全元文》第2册p26-2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李治在封龙书院的教育活动无疑也会得到张德辉的大力支持。
“龙山三老”在封龙山的活动究竟是在哪一段时间?据《元朝名臣事略》和《元史·张德辉传》记载,张德辉在金朝灭亡(1234)之后至忽必烈即位(1260)之前,一直是真定府史天泽的幕僚。《元史·李冶(治)传》则说李治“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根据其本传文意,此时应在忽必烈即位的前些年。再据缪钺《元遗山年谱》,元好问生命中的最后八九年(1249-1257)主要是在真定、东平两地度过的,最后还把家安在获鹿(今鹿泉市),并卒于获鹿。因此,“龙山三老”一起在封龙山活动的时期应该就是在1249年至1257年之间。
封龙山北的获鹿一带地处晋、冀的交通咽喉,是太行山中部通道之一,在历史上,战乱时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平时则是河北、山西的商品集散地,有“旱码头”之称。今天,这一带仍是连接石家庄与太原的交通要道。金元之际,元好问从家乡外出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或由外地回家乡,就经常穿越太行山,走井陉、获鹿一线。封龙山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决定了它在宗教、教育、旅游等方面的优越地位,而且,伴随庙会而来的各种娱乐活动也相当丰富多彩。因此,“龙山三老”的文化活动显然会因封龙山的强大辐射能力而产生较大的影响。真定地区之所以成为蒙元初期的人文荟萃之地,出了不少在文学创作、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人才,其中既有汉人世侯史天泽的功劳,也有“龙山三老”的功劳。
二、苏门山与蒙元初期的理学名家
苏门山海拔仅有184米,比812米的封龙山矮了许多。然而,山南麓有著名的百泉湖,仁山智水,交相辉映,动静阴阳,颇具玄机。历代众多名人曾与之结缘。单就理学名家来说,宋代的邵雍、清代的孙奇逢都曾在此隐居和讲学,而蒙元初期更是三星辉映,有姚枢(1201-1278)、许衡(1209-1281)、窦默(1196-1280)在此切磋理学并大力加以传播(注:姚枢为营州柳城(今河南西华)人,许衡为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窦默为广平肥乡(今属河北))。
作为北方学者,窦默、姚枢接受理学的机缘,都是由于战争。据《元朝名臣事略》记载,窦默在蒙、金战争中,一再南下避兵,甚至逃到了南宋的德安府孝感县。在那里,他接受了孝感令谢宪子的理学启蒙。蒙古太宗七年(1235),杨惟中、姚枢奉诏随进攻南宋的蒙古军南下,招致儒释道医卜等各类人。在德安(今湖北安陆)之役中,姚枢救出了后来成为元代理学开山祖的名儒赵复。窦默和宋儒砚弥坚,金儒杨弘道、王磐、王粹等也同时被俘送北方。窦默北归后,即隐居在大名,钻研理学。后来又回到肥乡,一边治学授徒,一边用医术治病救人。
赵复将自己所有的程朱理学书籍都送给了姚枢。太宗十二年(1240),杨惟中、姚枢等在燕京筹建太极书院,请赵复在书院中讲授理学。次年十月,当时任燕京行台郎中的姚枢因不满顶头上司牙鲁瓦赤的腐败行为,弃官而去,带着全家来到辉州,隐居在苏门山(注:在姚枢到来之前,已有一位受理学影响的学者王磐在此讲学。姚枢到来后,王磐因为要到燕地,就将讲堂交给姚枢使用,让所有学生跟随姚枢学习(姚燧《三贤堂记》,《牧庵集》卷七,《四部丛刊》本)。)。他筑室奉祀孔子、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等圣贤,自己刊刻朱熹的《小学》、《论语或问》、《孟子或问》、《朱子家礼》等书,请杨惟中刊刻《四书》,田和卿刊刻《尚书折衷》、《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让弟子杨古用活版印刷《小学》、《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使理学著作广为流传(注:《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续资治通鉴》卷170。)。
许衡则是通过姚枢而接触到理学的。金朝灭亡的前一年(1233),许衡北渡黄河,逃难到泰安东南的岨崃山,三年后,转到大名隐居。在大名,许衡结识了窦默,“每相遇,则危坐终日,出入经传,泛滥释老,下至医药、卜筮、诸子百家、兵刑、货殖、水利、算数之类,靡不研究”(注:《鲁斋遗书·考岁略》,《四库全书》本;《许文正公遗书·考岁略·续》,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姚枢隐居苏门山之后,听说许衡的学行,特意到大名和许衡、窦默一起探讨学问。许衡听到姚枢的纯正精粹的理学言论,很受触动,于是也特意到苏门山回访姚枢。在苏门山,许衡读到程颐的《易传》,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感到耳目一新,有契于心,便一一亲手抄录,带回大名。他向学生们检讨自己从前只知传授汉儒章句之学,没有领悟治学和修身的途径,要求学生放弃章句之学,转而学习程朱理学。学生们都听从了。从此,许衡精研理学,几乎达到入迷的程度。海迷失后称制二年(1250)春,许衡全家搬到苏门山,与姚枢家相邻,二人往返探讨学问。窦默也曾前来,三人伴着苏门山、百泉湖的湖光山色,探寻着当时在北方还属于新生事物的理学的真谛。三人中,许衡接触理学最晚,却后来居上,成为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之一,与后来被征北上的南方学者吴澄并称“北许南吴”。
姚枢、许衡、窦默三人在辉县苏门山和大名切磋理学的活动,随着宪宗元年(1251)姚枢应征出山而告结束。此时,窦默已先行被征至忽必烈潜邸,姚枢被召用,正是窦默推荐的结果(注:后来窦默又荐举许衡、史天泽。)。只有许衡继续留在苏门山,独自钻研。宪宗四年(1254),许衡被征为京兆教授。苏门山的理学家们就全部出山行道了(注:后来在大都,姚枢、许衡、窦默还时常聚集一起切磋学问、分析时政,交谊始终如一(《鲁斋遗书·考岁略》)。)。
三、封龙、苏门二山学者的学术旨趣及政治态度之比较
同在金代传统儒学的学术背景下成长,同处于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一样怀着在铁蹄下扶危济困、延续汉文化的愿望,几乎都曾有过隐居治学、讲学的经历,蒙元初期封龙、苏门二山的学者们有不少的共同之处。不过,这两个小小的群体在学术旨趣以及后来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颇有意味的差异。
1.旧儒学与新儒学
金元之际的北方学术,正处于旧儒学尚有较强势力和新儒学逐渐抬头的新旧交替时期。有金一代,传统的注疏章句之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虽然北宋理学的余脉一直残存着,南宋理学也于金中期开始逐渐北上,但对它抱有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金朝学者仍然占据了绝大多数(注:可参看拙文《金代理学发展初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金朝灭亡后,南宋理学北上的规模和影响都要更大一些,但短时期内也很难改变北方的学术品格。北方的乡间老儒还是“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注:《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滋溪文稿》卷八。),旧金习气很浓。赵复北上的意义,在于他给北方学界带来了系统的程朱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直接、间接影响了蒙元初期的著名理学家如姚枢、许衡、郝经等,奠定了元代理学发展的基础,因此,《元史·儒学传》将他列在首位可谓实至名归。然而,他一度载书南游,途经保定、真定、大名、东平、济南等地,并未取得多大效果。这固然与北方传统学风有关,但恐怕与元好问也不无关系。
蒙古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元好问在燕京与赵复有交往,二人虽相互钦敬,但在重道还是重文方面的意见明显不投合(注:《元史·赵复传》。)。而赵复后来南游所经各地,正是元好问常来常往、影响力巨大的地方,结果可想而知。龙山三老中,元好问主要是文学家和史家,张德辉则主要以治才闻名。李治于宪宗七年(1257)在忽必烈潜邸荐举了赵复,显然对赵复及其学术有所了解。而且,从李治现存的文章和其他所交往的人(如醉心理学的曹之谦等)来看,李治确实是接触过理学的。然而,李治虽然“经为通儒,文为名家”(注:《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内翰李文正公”。),他的主要兴趣却在数学。他在《〈测圆海镜〉序》(注:《全元文》第2册p18-1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自己从小就喜欢数学,虽然人们都认为那是“贱技”,自己也知道醉心于“技”而不去钻研“道”有些不好,但自己毕竟不仅仅在考究自然之数,而且是在推究自然之理,何况由“技”也可进于“道”,因此,即使被人可怜、遭人笑话都不在乎了。由此可见,封龙山的学者们虽都具有传统儒学的底色,但成就却主要不在儒学上。
苏门山的学者们当然也具有传统儒学的底色,但在接触理学之后,学术旨趣却产生了明显的转向。与不热衷理学的龙山三老不同,相对年轻的苏门学者却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徒。姚枢在刊布理学书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许衡无论在出仕前和出仕后,在开展理学教育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许衡的理学研究虽然比不上后来北上的南方学者吴澄,却也是蒙元初期卓有成就的学者。窦默在理学研究和传播方面的贡献相对逊色,但他显然在理学思想的践履上有更突出的表现,以致忽必烈有这样的评价:“朕访求贤士几三十年,惟得李状元、窦汉卿二人。”又说:“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始成完人矣。”(注:《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按:李状元指李俊民。窦默字汉卿,姚枢字公茂。忽必烈这样的评价透露出他对汉人的要求是忠心超过才干,才干必须在忠诚不二的基础上发挥才可靠、才有价值。不知这种评价是何时作出的,但联系他在李璮之叛后对汉人儒臣的疏远,可见其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同为儒士,封龙、苏门二山学者在儒学上既有群体差异,也有个体差异。而且,由于这些学者的涉猎面较广,并未把自己完全局限在儒学上,比如李治的数学、窦默的医学、许衡的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素养和成就,说明了这些学者们在学术上是丰富多样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们不能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2.合作与不合作
在论学二山期间,这六个人的身份有点多样化:既有隐士(李治、窦默、姚枢),也有文化活动家(元好问)和地方官员(张德辉),还有当时名声还不是很响的儒户之人(许衡)。相比较而言,封龙山学者在金朝都有当官作吏的经历,而苏门山学者中许、窦二人未曾在金朝任职。原先职位相对高一点的元好问、李治二人较为倾向于不合作(注:虽然元好问曾与张德辉去见忽必烈,奉请其为“儒教大宗师”,但主要是为了保护儒士和儒学。李治在流落太原时曾多次推辞藩府的征辟。忽必烈曾多次征召,他也只是勉强出任翰林学士一年就辞归封龙山。),职位更低的张德辉、姚枢则在鼎革之际就已出任蒙古官职。未有仕宦经历的窦默、许衡的态度则相当有意思:初闻征召,窦默改了姓名,许衡则从苏门山逃到大名。而出仕后,二人却与姚枢一起仕至高位,在政坛上颇有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封龙山学者较为倾向于不合作,而苏门山学者是较为倾向于合作的。
由于政治态度及学术旨趣上的不同,造成了封龙山学者后来在政治上的影响不如苏门山学者,儒学上的影响也要逊色于苏门山学者。
封龙山学者中,只有张德辉在元朝曾仕至东平路宣慰使。张德辉虽也曾为朝官,但只是参议中书省事(正四品),品秩不如姚枢、许衡的中书左丞(正二品),既没有姚、许、窦三人在朝为官的时间长,也不如三人常备咨访。姚枢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出色的军事韬略,他审时度势,劝诫宪宗时期的忽必烈韬光养晦、为忽必烈建言图宋战略、助忽必烈征服大理、制定礼仪等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许衡虽时进时退,但他先后担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等要职,在制定朝仪和官制、培养人才、制订新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姚、许二人所献的施政纲领,对忽必烈的政权建设有重要影响。窦默的才干虽比姚枢、许衡略逊一筹,但却最受忽必烈敬爱,谏言常被采纳。姚枢、窦默先后担任过太子真金的老师,许衡辅导过世祖朝年轻的中书右丞相安童,所培养的学生中如宗王孛怜吉歹、野先铁木儿以及成宗朝的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上都留守贺仁杰等等,都是足以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此外,姚、许、窦三人和权臣王文统有过正面交锋,许衡与权奸阿合马也进行了斗争。因此,单就二山学者本身来说,苏门山学者在政治上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至于儒学方面,苏门山学者比封龙山学者也更有影响。一来理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自然要超越传统儒学而成为时代主潮;二来苏门山学者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其学术思想的号召力颇有后来居上之势;三来许衡及其学生耶律有尚等长期掌握着国子监和一些地方教育机构的行政大权,对元朝的教育方针、政策、内容、方法等等都有深刻的影响,在推行理学思想上有便利条件;等等。我们可以看到,理学的影响后来也渗入了封龙山。在李治之后,主封龙书院讲席的安熙是理学家刘因的私淑弟子,正是他使封龙山的学术趋向发生了转变。
然而,传统儒学并未就此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它顽强地融入北方的新儒学之中,并因此形成了蒙元初期北方理学的特质。元好问的文学影响也持久而深入。封龙山学者的后学们(如郝经、王恽等)受到了理学的熏染,而苏门山学者的后学们(如姚燧等)也出现“流而为文”的现象,在“文道合一”的旨趣中,二山学者的后学们走向趋同,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标签:元好问论文; 封龙山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元朝名臣事略论文; 测圆海镜论文; 理学论文; 国学论文; 张德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