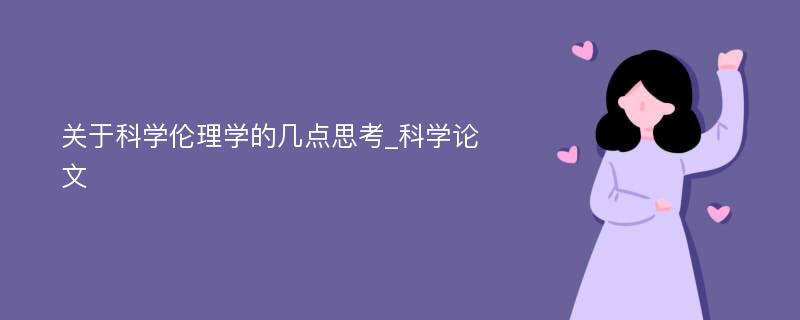
关于科学伦理学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几点思考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国内关于科学伦理学的研究,已获得了一定的进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以及知识经济的异军突起,科学伦理的问题日益凸现,因而有必要对科学伦理学及其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
一、科学范畴的界定
科学,这里是指包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科学。从科学的伦理问题引发来看,它是在当代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中凸现出来的,而不是仅由自然科学所引起或仅由技术科学所引起。因而科学伦理学仅探讨自然科学的伦理问题或仅探寻技术科学的伦理问题都会有失偏颇。只有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引起的伦理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探讨,才有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实际上,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边界日趋模糊。一方面,由于应用科学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科学已向着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和开发研究三个方向发展。而在以信息和通讯技术的研究开发为中心的知识经济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别,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更模糊化了。例如,几乎所有的软件开发,既是立足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上的开发,同时又是面向市场、面向用户的产品生产。软件的研制与生产,不但把科学与技术的各环节打通,而且把科技与生产融为一体。另一方面,由于科学运用于技术的周期不断缩短,使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相互渗透性不断加强。技术科学尤其高技术是基于科学的技术。这正如舒尔曼所概括的:“现代技术的基本结构是由技术活动者、科学基础以及技术—科学方法构成其特性的。”(注:(荷兰)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8页。)同时,自然科学从研究课题,到研究手段,直至成果鉴定,都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及其手段。因而,海德格尔认为,科学理性的实质是技术理性,科学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控制论的亦即技术的。而在科学学的创始人之一贝尔纳看来,“科学是一种研究描述的过程,是一种人类活动。这一活动又和人类其他种种活动相联系,并且不断地和它们相互作用。”(注: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序言),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684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墨顿则主张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建立综合的、含义广泛的现代科学概念,他不仅把科学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而且也看作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就科学的内涵而言,它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是创造知识的社会活动,又是一种社会建制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创造知识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具有核心的地位。因为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的科学是其主体科学活动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是科学活动发展的内在要求——组织化的要求。就科学的外延来看,它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开发研究的统一体,其中既含科学,又含技术。
二、科学伦理学建立的可能性
首先,从科学活动的发展看科学伦理学建立的可能性。科学伦理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实践理性,主要是在科学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近代科学经过多年的发展运作,其显性特征逐渐为人们尤其是科学活动主体所认同,即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定律等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因而,科学活动就是科学活动主体运用思维或有关仪器,通过观察、实验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现象并揭示其内在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活动。在科学活动中生成的科学精神便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求真精神,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一种以物为尺度的客观性原则。这种思维定势又经过休谟、康德等近代著名思想家的理论强化,便逐渐地积淀于人们思想的深层。科学(活动)“价值中立说”便是其较为典型的表征。持这种观点者以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为划界基础,进而指出,科学(活动)是关于事实的,价值是关于目的的;科学是追求真理,价值是追求功利;科学是理性的,价值是非理性的;科学是可以进行逻辑分析的,价值则不能进行逻辑分析。但从1945年以来,在社会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科学活动的规模迅速扩展,即从原来以基础研究(包括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的工作)为主,迅速向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发展,科学活动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运用的周期在不断地加快,科学对自然——人——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科学活动主体的伦理意识日益觉醒。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使许多科学家感到震惊:“一个在哲学摇篮中哺育、在纸上涂涂写写的科学理论,最终竟能顷刻间毁灭数万人的生命。”(注:参见邱仁宗:《科学技术伦理》,《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期。)1945年在纽伦堡对纳粹战犯医生的审判表明,过去一直被认为不依赖人的感情与好恶等主观因素,只注重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可用如此惨无人道的方式进行,不但破坏了基本人权,而且残害了许多无辜人的生命。”(注:参见邱仁宗:《科学技术伦理》,《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期。)因而,莫泽克在《论科学》一书中认为,科学伦理学问题往往不是经典认识论性质的问题,而是良心问题、态度问题。在人们考虑科学伦理学问题时,更须关注日常的科学工作。在他看来,“在我的专业领域里,我思考的结果究竟属于谁所有?”这一问题是科学伦理学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注:参见邱仁宗:《科学技术伦理》,《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期。)。现在的科学活动正越来越使这一问题凸现出来。1997 年2月23日,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其利用基因转移技术,以无性繁殖复制首只克隆羊“多莉”诞生已有7个月。同年3月2日, 美国俄勒冈地区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也报告以克隆技术繁殖成功与人类最接近的动物两只恒河猴。这两条消息向人们展示了当今基因工程的突破性的创举,并宣告:人类离可能复制自己的日子已经不远。人类复制自己尽管只是一项科学活动,但它却将涉及到社会、家庭、人自身等诸多伦理方面,也将涉及到自然、人、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运作。因而,克隆羊在成为全球头号热点新闻的同时,也迫使科学活动主体在进行人类复制自己的研究前,对这项研究将对自然、人、社会系统以及对社会、家庭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这不仅促使与人直接相关的科学活动主体人文意识的觉醒,而且触发了过去被认为与人无关的、研究自然的科学活动主体的良心危机。
其次,从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出现看科学伦理学建立的可能性。从50年代起,世界范围的环境污染威胁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态危机,其中又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为表征,这是威胁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的最严重的问题。从环境退化的性质来看,它不是一个单项的问题,而是众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空气和水污染、表土流失,土地破坏、森林锐减、沙漠扩大、物种灭绝的过程加速等,从而,致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四大生命系统森林、草原、渔场和农田面临危机形势,而这些问题又同人类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科学发展紧密相关。此外,生态问题的发生具有普遍性,从天空到地下、从海洋到大陆都发生了环境退化现象并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二是能源危机、粮食短缺。这是同地球上人口猛增相联系的。由于科学的发展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预计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会增加到63亿,这样会使耕地面积与人口比率继续下降,粮食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人类,自然资源也将有枯竭之虞。拉兹洛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一种决定命运的选择;是进化和灭亡之间的选择。”“这种挑战是史无前例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与生物圈的承载能力相接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注: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1997年第159页。 )各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科学活动不再是一种仅仅作用于自然的研究活动,而是对社会、自然和人自身都有深刻影响的社会活动。因为当代科学活动在其活动的规模、范围和内容上都较近代发生了质的飞跃,它“已不再局限于个别科学家自发的认识过程,而表现为一种精神生产形态,表现为科学家、科学工作者的共同活动。”(注: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而科学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对社会生产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教育模式。
再者,从数字化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看科学伦理学建立的可能性。当代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正在形成全球规模的人体外的神经系统,它储存、加工、传输信息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这场革命含有五大核心技术:半导体技术、信息传输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数字压缩技术,此外还辅之以现代生物技术、纳米制造技术和能源技术等。这场信息革命促使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知识经济与以广大的耕地和众多人口劳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不同;与以大量的自然能源和矿藏原料冶炼、加工、制造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也不同;它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主要基础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经济是依靠新的发展、发明、研究和创新,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智慧型的经济。这种经济以不断创新为特色,而这种创新是急速旋转、迅猛异常、没有终止和无限的。这里,也提出了科学伦理问题——科学活动主体的道德素质培养。因为在当代知识经济爆发和迅速扩张的背后,是人,是掌握了具有相当丰富知识的人,是敢于和善于应用新的知识并将其物化为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的人,是善于将分散存在的知识融会贯通、组合凝练成新知识,又进一步将其付诸应用的人。因而,知识经济在这一意义上,又是人才经济,同时也是科学活动主体活动的新形式。我们在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中,不仅要注重科学活动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更要注重其道德素质的培养。一是就科学活动主体个体而言,他只有具备了优良的道德品性,才能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把准服务的方向,把握发展的机遇,积极地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二是从科学活动主体群体来说,优良的道德品性又表现为群体成员之间的协作、团队意识和拼搏精神。此外,科学活动主体的道德直接关系到知识的应用、传播和开发程度,同时也关系到国家、企、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前景。总之,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不再被排斥在经济系统之外,而是系统内的关键生产要素;同时科学活动内蕴的伦理本性已由近代的潜在状态通过现代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活动日益显现出来。这便昭示了科学伦理学建立的可能性。
三、科学伦理学建构的几点思考
关于科学伦理学的建构,不仅涉及现代科学活动的“形而上”的伦理意义,而且也涉及科学活动“形而上”的伦理功能。下面仅就现代科学活动的“形而上”的伦理意义:“科学活动是什么”和“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谈一点浅见。
首先,“科学活动是什么”,这是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对科学活动的本质进行的思考。尽管从近代科学产生之日起,人们就在思考“科学活动是什么”,但由于科学活动范围、规模和内容的局限,而未能揭示科学活动内蕴的伦理本质,更多描述的是科学活动外显的非伦理本质,如,科学活动的求真性和探索性。人们在科学活动中主要关注的是人对自然的作用。随着科学活动规模的扩大、活动范围扩展和内容的丰富,科学活动内蕴的伦理本质越来越显现出来。正如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所说:“科学不能仅被看作是一组技术性的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时还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献身于既定精神价值和受伦理标准约束的活动。”(注: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1991年第100页。 )科学活动的这种伦理本质不但从其整体的宏观层面上显现出来,而且还从其微观层面上显现出来,即表现为一种科学活动主体与其对象相互作用的统一性(如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揭示了科学活动中主体与对象、主体与客体不可分离)。它揭示科学活动主体的本质与自然本质的统一,即对于自然规律、自然本质的揭示与科学活动主体的当前的认知水平(如理解能力和颖悟力以及理论阐释系统)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活动实际上是科学活动主体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它既是科学活动主体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的体现,又是科学活动主体与自然、科学活动主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运作形式,同时还是科学活动主体履行对自然、社会、科学共同体及其自身的义务与责任的过程。
其次,“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科学活动的本质所进行的思考。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从其显层次上来看,是以对真理的探求为其价值目标。然而,科学活动主体为什么要探求真理?探求真理的目的是什么?前者是科学活动主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初始动机,后者则是其进行科学活动的价值指向。两者都深深地打上了科学活动主体所处的时代、所在社会的价值目标取向的印记及其自身需要的印记。因而,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是一定社会价值目标在科学活动中的体现,同时也是科学活动主体的自身价值目标实现的动态表征。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这时的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从根本上来看是当时社会价值目标的表征和实现方式,“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6页。)
如果说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形成和发展时期,其社会价值目标的指向偏重于物的方面,显现为一种功利价值,进而使这一时期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更偏重于人对自然的控制,以满足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单一的求真特性,在成果形式上显现出工具性的特征,在科学活动方面,已形成了被科学活动主体公认的规范,如普遍性、诚实性、无偏见性和合理性等;那么当代随着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社会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更趋一体化,社会的价值目标便由偏重于物的方面向精神、物质并重的多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加之,现代科学对自然——社会——人这一超大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尖锐化,一方面,这一现状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原有的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的局限性,即仅以控制自然、向自然索取,抑或以求真为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不但没能促使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却很大程度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进而影响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如上所述,当代,科学活动已由近代以基础研究为主扩展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并重,而且科学活动成果由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其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代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作用更大。然而,知识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即科学活动主体既可以用它造福于人类及社会,也可能使它产生不利于人类及社会的负效应。正如爱因斯坦所强调的:“在我们这些把惊人力量释放出来的科学家身上,有一个重大责任,有为人类福利而不用于破坏的责任。”(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8页。)因而,现在科学活动主体的价值目标取向不仅仅作用于科学活动的领域,而且已经扩展至整个社会,其道德责任就不仅是坚持真理、发展科学,还要注重科学活动的社会道德责任即对科学活动的社会后果的关注。贝尔纳指出:“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注: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37页,第478页。)因此,作为科学活动主体“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页。)由此, 当代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就由偏重于人对自然的控制转为注重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在表现形式上由原来单一的求真型向求真、臻善、达美的三维的立体型结构转化,即形成以求真为动力,以臻善为目标,以达美为指向的三维价值目标体系。在科学活动的成果形式上既体现了其特有的工具性,又表现出科学活动主体对促进人社会自然协同发展的目的性。在科学活动的规范方面,既弘扬近代以来的科学道德规范,又增加了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活动成果合理应用的义务性与责任性。
简言之,现代科学活动价值目标的转化,一方面是社会价值目标在科学活动中的具体展现,另一方面也是科学活动主体对于科学活动在人、社会、自然系统中所产生的正负两极效应的意识自觉,亦是科学活动主体对自身所担负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意志自律,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社会价值目标与科学活动价值目标相统一,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目标的自觉意向。而这正表明科学伦理学建立既有内在的可能性,又有客观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