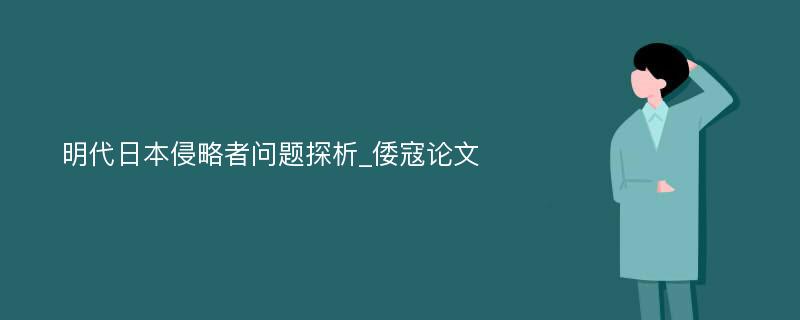
明代倭寇問題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倭寇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對于明代東南沿海的倭寇問題,歷來討論甚多。較早的如1930年代,因抗戰而使倭寇研究文章激增①1950年代,因爲農民起義成爲了正面形象,嘉靖倭患也具有了反壓迫的標識。②1980年代,學術氣息漸趨輕鬆,嘉靖“倭患”被部份學者定義爲是一場反海禁的鬥争;③類似的判斷在當下也頗爲盛行。④當然也有學者對此不予認同,認爲嘉靖倭寇是倭人與中國海盗的勾結。⑤實際上,早在嘉靖年間的當時及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有關倭寇的構成問題,就有許多不同的判斷,嘉靖時人鄭曉說:“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略可用者,往往爲賊”。又說:“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踪迹”。⑥鄭曉的觀點也代表了當時相當部份人對倭寇的看法。一般認爲,明代早期或中期的倭寇多由日本海盗組成,而嘉靖時期的倭寇則“類多中國之人”。⑦實際上以筆者看來,有明一代倭寇,不論是明初,還是中期、晚期,始終都有中國的流寇參與,只是嘉靖時期的倭寇,“編戶之齊民”參與的更多一些,且一部份還作爲主導地位,“華人藉倭奴爲爪牙”了。但需要强調的是,明代的“倭寇”,始終以倭人爲主,以倭人爲主的倭寇劫掠沿海的性質是難以否認的。⑧筆者一段時間以來曾對明代海防史料做過一些整理,對明代倭寇問題也有一些看法,整理出來與諸位學者討論,也就教于相關識者。
一、各時期倭寇
據史料記載,早在元代時倭寇已經開始在大陸沿岸進行劫掠活動了,如武宗至大元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⑨,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倭人寇蓬州……倭人連寇瀕海郡縣”⑩,等等。進入明代,由于政權初定,國內形勢不穩,倭寇因此乘機在沿海一帶劫掠作案,“中原擾擾,彼倭來寇”。明明代初期記録倭寇侵擾,最早的數洪武二年一月:“倭人入寇山東海濱郡縣,掠民男女而去”(11),這似乎是明初最早有關倭人入寇的記録。但實際上,隨後的洪武二年二月即有“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12)的記載,這裏的“辛卯”,可能指的是元至正十一年(1341年),說明洪武二年以前,倭寇已經幾度侵擾山東。此後的幾年間,倭寇侵擾逐漸頻繁,《明實録》記載:
(洪武二年四月)先是,倭寇出没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財貨。沿海之地皆患之。(13)
(洪武二年八月)倭人寇淮安,鎮撫吳佑等擊敗其衆于天麻山,擒五十七人。(14)
(洪武三年六月)倭夷寇山東,轉掠温、臺、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縣。福州衛出軍捕之,獲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餘人。(15)
自此而後,倭寇劫掠海邊的記録幾乎每年都有,從《太祖實録》與《太宗實録》的記載來看,發生在洪武、永樂年間的倭患事件中,涉及浙江的最多,爲十六起,其次山東九起,廣東六起,南直隸六起、福建五起。其中的大部份事件應是倭寇所爲,如温州下湖山一役,“獲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餘人,及倭弓等器”(16),還從倭寇手中救出了被其擄掠的高麗人三人。又如洪武“六年,舟師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殺戮甚衆,獲其弓刀”。(17)又有倭船,又有倭刀,顯然這些倭寇是“真倭”無疑。實際上日本海盗在侵擾明朝邊海之前,已經多次在朝鮮一帶進行劫掠了。《朝鮮史略》就記録了早在宋元時期倭寇即劫掠朝鮮沿海一帶:
康宗元孝王十四年(1226年,南宋寶慶二年)“時倭賊侵掠州縣”;(18)
忠烈王二年(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倭寇固城巨濟等處,合洽萬戶崔禪等擊卻之。倭寇始此,此後年年寇竊不絶”;(19)
恭湣王九年“倭寇全羅道沃溝等處及楊廣道平澤等十餘縣”;(20)
恭湣王二十年(1371年,明洪武四年)“倭船二十七艘入揚州,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大敗……至是,倭勢大熾,西北東南諸道畿甸郡縣無處不發,國之兵備疏虞,又不習水戰,兵出輒敗”;(21)
辛禑二年(1376年,明洪武九年)“倭寇扶餘至公州元帥朴仁桂戰死”。(22)
如上所述,可見日本海盗劫掠周邊沿海之事不僅僅發生在明朝疆域,也同時發生在鄰近的朝鮮。(23)故倭人在周邊沿海進行劫掠是當時的常態。但倭寇團夥一般人數較少,而遼東的望海堝一役,是早期倭寇入犯人數最多的一例,被殲滅的都是真倭,歷來都是没有争議的。
但即使在明代初期,也已經有冒充倭寇的現象出現,如洪武二十六年十月即記載了朝鮮沿海居民假借倭寇之名而到中國沿海劫掠的事例:“有寇百餘人,入金州新市屯劫掠。獲其一人張葛買者,乃朝鮮國海州民,詐爲倭國人服。遼東都司遣人械至京,上命宥之,遣還其國。”(24)可見至少在洪武晚期,由于倭寇惡名遠播,于是借倭寇之名而進行劫掠的事例也逐漸開始出現。
此外,倭寇犯邊的事例中,恐怕也有一些是國人所爲,一些沿海流民可能參與了其中的入寇事例,據說方國珍、張士誠在元末明初戰争落敗以後,他們的一些殘餘勢力隨即遁入沿海島嶼,與倭寇相互聲援,劫掠沿海一帶。明代後期的文獻中多處提到過這一點:
《皇明四夷考》:“初,方國珍據温、臺、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松、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强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25)
嘉靖時人茅坤:“國初時,由方谷珍、張士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煽誘倭奴,相與爲亂”。(26)
這些記述雖然多爲晚期追述,但也反映了明初時“倭寇”構成的部份情况。除此之外,當時一些沿海邊民也違禁下海,“糾島倭入寇”:臺州黄岩縣海盗張阿馬,經常“潜入倭國”,引導倭寇到臺州沿海一帶劫掠,“邊海之人甚患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張阿馬又引導倭夷入寇,“自水桶澳登岸,欲劫掠居人”,被官軍追擊而“擊斬之”。(27)同樣的事例還發生在海鹽縣:洪武四年“有海民沈保童用竹筏載倭,登略海鹽”。(28)可見即便是明代初期,以倭人爲主的寇邊事例中,也多有沿海“編戶”的參與。
明代中期(嘉靖以前)的海防形勢比較穩定,這時期倭寇犯邊的事例就相對較少,據《明實録》,這時期倭寇劫掠的事件中,涉及浙江的有六起,福建三起、廣東一起。在這些爲數不多的事例中,以正統年間倭寇進犯浙東影響最大,因爲這是連續有衛城、所城被倭寇攻陷:
(正統四年)五月初一日,倭賊登岸犯桃渚千戶所,殺虜人民。(29)
正統四年五月,夷船四十餘隻,夜入大嵩港,襲破所城,轉寇昌國,亦陷其城……惟爵溪所官兵擒獲賊首一名畢善慶,誅之。(30)
(正統七年五月)倭寇二千餘徒犯大嵩城,殺官軍百人,虜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筭。(六月)倭寇二千餘人臨爵溪千戶所城,雖被官軍擊卻,尚潜海島。(31)
其中,倭寇攻陷桃渚城後,大肆殺戮,當時人記載:
倭奴入桃渚,犯大嵩,劫倉庫,焚室廬,驅掠蒸庶,積骸如陵,流血成穀。嬰兒縛之竿柱,沃以沸湯,視其啼號爲笑樂。捕得孕婦,與其儕忖度男女,剔視之以中否爲勝負,負者飲酒。荒淫穢惡,至不可言。民之少壯與粟帛,席捲歸巢。城野蕭條,過者隕涕。(32)
倭寇之所以屢屢攻破衛所城堡,往往先以入貢爲名,然後再伺機進行劫掠,“倭之來也,輒矯云求貢,苟或海防弛備,即肆劫掠”。(33)《英宗實録》說:“倭夷奸譎,時來剽掠海邊。見官軍追捕,乃陽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34)因爲對中國的地形情况不熟悉,所以倭寇常劫持沿海邊民作爲向導,如正統八年七月,“浙江黄岩縣民周來保、福建龍溪縣民鍾普福,洪熙間俱困徭稅,叛入倭。倭每來寇,輒爲鄉導”。(35)《英宗實録》說:“近年逃軍、逃民與倭寇交通,或被其劫制,詢我虛實,然後乃敢捨舟登岸,殺虜軍民。”(36)有的被倭寇劫掠後做了翻譯、通事,如争貢事件中的宋素卿,即是自小被日本貢使帶走的。《憲宗實録》也記載了類似的事例:寧波人林從杰,因幼時被倭寇劫走,長大後作爲通事隨使臣入貢。(37)
這時期也有一些誤捕誤抓的事件,很多是朝鮮人出海遇風,漂流到中國沿海,由于語言不通,被當作倭寇。如正統八年六月浙江海門衛擒獲“倭寇”七名,解京審問,自稱是朝鮮國“臘州官莫連公木判官下部屬,駕船下海捕魚,遇大風雨,漂至海門桃渚千戶所長跳沙灣地方”。(38)景泰四年八月浙江備倭都指揮僉事馬良等擒獲文吞只等五人,送部審查,自稱是“朝鮮國漁戶,入海捕魚,遭風壞舡,漂流海島”(39),等等。
當然也有一些是邊民因爲“困徭稅”等因素,入海爲盗的。弘治年間朝鮮人崔溥所寫《漂海録》,記録了其在浙江沿海二次遇“海賊”的情况,“十二日,遇賊于寧波府……望有中船二艘,皆帶懸居舠,直指臣船而來……其党二十餘人,或執搶,或帶斫刀,而無弓箭,秉炬擁至,闌入臣船,賊魁書曰:我是觀音佛,洞見你心,你有金銀便覓看……賊魁即叫其党窮搜包中衣物、舟人糧食,輸載其船”。第二次是在臺州桃渚沿海一带,“十六日,到泊牛頭洋……俄而,所謂六船棹圍臣船,一船可八九人,其衣服語音與下山所遇海賊一般”。(40)崔溥兩次靠岸都遇到了“海賊”,一次是在寧波沿海,第二次是在臺州桃渚千戶所附近的“牛頭洋”,可見沿海“海賊”還不少。這些“海賊”與倭寇不盡相同,没有殺人如麻的殘酷,記載中並没有對崔溥等大開殺戒,只是搶討一些財物。但一旦倭來,這些海盗就會勾引倭寇。正是這些入海爲盗的邊民與倭寇沆瀣一氣,使得倭寇的聲勢逐漸壯大。
從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争貢之役(41)開始,朝廷罷市舶,“濱海奸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爲之”(42),違禁下海的邊民與倭人開始在舟山雙嶼一帶結集交易,日本五島的倭人因爲利益誘惑而結隊而來,而浙閩粵沿海的通番商人也接踵而至,形成了很大的離島市場。這些且商且盗的倭人和海盗還時不時地對沿海一帶進行“分迹剽掠”,朝廷爲此加强了沿海的管理,“嚴通番之禁”,于是,鋌而走險的劫掠事件開始增加,尤其是嘉靖二十年以後,李光頭、許棟等從福建獄中逃脫,盤踞舟山雙嶼,勾結倭寇、佛郎機等,使得劫掠活動愈來愈猖獗。(43)
對此,朝廷命朱紈巡撫浙江主持海防,朱紈于是嚴海禁、革渡船,並指揮官軍剿滅雙嶼倭寇,一時倭寇遠遁而去。但不久朱紈被革職,並憤而自殺。朝廷不再設浙江巡視,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海防由此廢弛,倭寇也轉而猖獗。從史料記載看,大批倭寇深入內地劫掠、攻陷府縣城池,繼而在大陸安營扎寨,還是要從朱紈被罷以後開始,嘉靖《永嘉縣志》說:“正德以來時有漳寇在海洋打劫,鮮登岸者;嘉靖初徽、鄞奸商勾引島夷入擾,二十三、四年以來登劫……猶未敢深入;至三十一年破黄岩縣治,而勢日熾。”(44)此論述基本能反映朱紈以後倭寇爆發的情况。
二、倭寇成分分析
對于嘉靖中後期倭寇的成分,自明嘉靖以來就討論甚多。有認爲國人居多的,也有認爲國人僅爲勾引作用而倭人爲主導的,此試做一些分析。
1.倭寇“類多中國之人”
當時的許多記載認爲,嘉靖倭寇成分中,中國人占很大比例,東南倭患“類多中國之人”,這樣的觀點在當時著述中可以說並不少見:
《世宗實録》:“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45)
鄭若曾《籌海圖編》:“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托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間有之,夫豈盡爲倭也。”(46)
胡宗憲《題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疏》:“至于柘林等處之賊,名雖倭夷,而沿海奸民寔居其半。”(47)
趙炳然《與張半洲書》:“此賊(指倭寇)狡悍,半爲吾人。”(48)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如宋素卿起釁于前,王直、徐海、陳東等作孽于後,皆以倭人爲名,實則真倭頗少也。”(49)
嘉靖《太平縣志》:“昔之爲寇,一謂倭也。今之爲寇,二謂漳賊也、與導漳之賊也,而倭不與焉。凡漳賊與導漳之賊,率閩浙賈人耳。”(50)
鄭茂《靖海紀略》:“倭人禿頭鳥音,不滿二三百,餘皆寧、紹、漳、廣諸不逞之徒。”(51)
歸有光《震川集》:“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52)
屠仲律《禦倭五事疏》:“夫海賊稱亂,起于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九,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53)
《虔臺倭纂》:“倭夷……其爲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其人衆,其地不足以供,勢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爲利,寧紹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戶爲利。”(54)
《皇明四夷考》:“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55)
除此之外,《明史》、《明史紀事本末》等也有類似記載。各家記載中還有一些生動的例子,說明倭寇中“中國叛逆”的存在:采九德《倭變事略》記載,小股倭寇被官軍圍困于海鹽小營盤巡檢司,“自分必死”,由于倭寇中多有漳州人,于是官軍中“四漳兵入與打話,遂私與賊約,佯爲潰走,縱之出。”(56)《鄭開陽雜著》記載了寧波人駕駛的蒼山船與倭寇交通之事:“賊中多有水手,親識前日蒼山船爲前鋒,遇賊交語而走。”(57)歸有光、茅坤也記録有類似事例:“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异。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58)“近聞里中一男子,自昆山爲海寇所獲,凡没于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大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並閩及吾温臺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謂倭而椎髻者,特丁數人焉。而巳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爲號而巳,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59)上述記述中都記載了倭寇團夥中多有國人參與的情况,而且其中多數爲“閩及吾温臺寧波人,間亦有徽人”。
但恐怕,爲了强調國人的參與度,相關記述中難免有過度描述之嫌。有些可能僅僅是孤立的事件,卻也把它視作普遍現象了。上述這些記載、闡述中,以《世宗實録》的記載爲最典型:“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但其原來的記述反映的並不是這樣的事實:
時海洋並岸諸島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風泛不獲歸者、有沿海奸民搶江南旋侯來歲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有三舟登岸,(張)棟、(董)士弘擊之,引去,擒賊數人,皆真倭。比泉州州兵巡海,攻賊于石圳澳深泥灣處等處,凡再戰,擒賊四十餘人,則皆浙江臨海、福建漳浦、廣泉揭揚等縣人。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60)
從此條記載中,需要大家重視的有幾點:首先,指出“並岸諸島”的“栖寇”中,既有“真倭”,也有“沿海奸民”,但相當數量的“真倭”已經回日本,留下的僅是少數“阻風泛不獲歸者”的“真倭”。其次,指出這些“栖寇”是爲了“侯來歲倭至”,自然這些“來歲倭”應多屬“真倭”,因爲“真倭”纔需要“泛歸”。其三,首次擒獲的都爲“真倭”,第二次抓獲的“則皆浙江臨海、福建漳浦、廣泉揭揚等縣人”,可見即使是許多“真倭”“泛歸”以後,入犯福建南日寨的海盗中仍舊有許多“真倭”存在。其四,“蓋江南海警……”云云,應該是作者針對“倭寇”團夥中大量存在的“沿海奸民”而做出的感慨,並不是嚴謹的統計,這樣的感慨與籠統判斷並不能說明真的就是“倭居十三”,因爲大量真倭已經乘風歸去。而相關的類似“夷人十一、流人十九,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的說法,可能也有“好發新論”的傾向,並不全是真實的記録。(61)至于有些更加偏激的說法,如認爲徐海等入寇浙西時僅有“真倭一十八人”(62),以及把倭寇直接歸接爲“漳賊”所爲,認爲嘉靖倭寇没有倭人參與:“昔之爲寇一:爲倭也;今之爲倭二:爲漳賊也,與道漳之賊也。倭不與也”(63),這種偏激的說法就更不可信了。
2.真倭大量存在
歷次禦倭戰役中,實際上多有斬獲真倭者,如嘉靖三十八年三爿沙大捷,“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三顆”(64),“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真倭,無從者”(65),等等。當時有關倭寇的著述中,有許多史書明確記載倭寇的來源,並把倭寇來源指向爲日本諸島:
前之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築前、築後、博德、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等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66)
審得入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野島小夷,被中國逋逃之徒糾同打劫。(67)
竊意此賊,恐多各島小夷……私出買賣,國主不知。(68)
倭人還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殺,至其本國,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歆慕之心。(69)
徽歙奸民王直、徐惟學……竄身倭國,招集夷商,栖泊島嶼。(70)
審擒獲賊首李哪噠亦稱:渠魁沈南山等,安住倭國,分遣其黨,同倭入寇。(71)
《明史》也明確指出:“(王)直初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由此日至。既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72)這些被王直等“誘之入寇”、與中國逋逃“同倭入寇”的“島夷”,由于“譯言莫通”,很少有知道其姓甚名誰的,即使“全島無一歸者”,中國史籍也較少對這些“各島小夷”有所記載,倒是王直、徐海、陳東一類華人多被史書屢屢提及,原因即是國人的姓名容易記住,而倭寇由于語言不通,較少被記録在案。采九德《倭變事略》記載倭寇初犯海鹽的事件,基本反映了有真倭但不易確認的情况: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二日,一海船長八九丈餘,泊鹽邑演武場北新塘嘴,約賊六十餘,皆髡頭鳥音,有槍刀弓矢而無火器。時備倭把總指揮王應麟率本衛驍兵數百而出,賊見我兵不敢動。王遣陸路指揮王彥忠率兵百餘,至船詢所以來,而譯言莫通。惟以小木櫃置書,其中曰:“吾日本人也,來自吾地,以失舵,願假糧食,修吾舵,即返。幸無吾逼,逼則我爾死生未判也”。時承平久,邑人相携往觀,嘻然莫爲虞。日甫西,彥忠率衆逼船,倭盡起立,以燕尾利鏃射數軍,皆立死。諸觀者始知懼,奔入城,遂塞門爲拒守計矣。會雨,夜昏黑,防少懈。漏四鼓,賊留半在船,其半登陸路而遁,次日侵晨,軍人胡士澄持火藥數斗,奮身上船焚之,火發,賊突起,胡遂被殺。酋長有八大王者,從火中奮躍,眉毛盡焦,獨舉二刀拂火飛斫我軍,跳擲數四而倒。焚死者十餘賊,生擒被傷者六賊。縛置北城闉內。刀瘡傷處,見其痕多無血,人咸异之。
文中提到了“八大王”、“髡頭鳥音”、“刀瘡傷處,見其痕多無血”等描述符合當時國人對于倭寇的概念。這些倭寇最初用“以失舵,願假糧食,修吾舵,即返”等謊言做試探,一旦探明官軍防守情况,認爲有機可乘,即“倭盡起立,以燕尾利鏃射數軍”——這種犯邊的情形也是倭寇屢試不爽的招式,但是否真倭卻很難確定。周召《雙橋隨筆》記述了發生在昆山的故事:“明嘉靖間倭亂江南,昆山夏生爲倭所獲,自稱能詩,倭將以竹輿乘之,令從行,日與倡和,竟免害。久之,夏生乞歸,厚贈而返”。(73)夏生“乞歸”後没有講到國人多于倭人的情况,可能這夥倭寇多爲“真倭”;而“倭將”的表現也活脫一個既羡慕中土文化、又以淩辱華人爲樂趣的倭寇小頭目的面目。可見這些小股作亂的倭寇應該多爲倭人或多有倭人參與,而那些“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的則亦多爲倭人,但因爲不知其姓名而難辨其究竟。
其實徐海倡亂時,其有一重要的合作者辛五郎,“大隅島主弟也”,是徐海在日本的“少東家”,“同巢柘林,攻乍浦、圍桐鄉、毒螫吳諸州郡,其志欲吞全浙、窺留都,勢甚猛也”(74),在作亂浙西一帶的倭患中辛五郎等真倭的作用不亞于徐海,但中國史書少有提及之,原因即是在當時信息不够發達的背景下,是很難瞭解真倭的情况的。至于其它倭寇,往往只有簡單的名字,其作惡的事實都很少有記録,更不用說把這些倭寇與其作惡的事件串聯起來了。如與辛五郎一起被俘的密之摩多、許公四飛、過柴由門,僅見于趙文華的奏疏中,其他史書幾乎不載(75),其他如朱紈清剿舟山雙嶼時與許棟一起被擒的倭人頭目稽天(76),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在餘姚鳴鶴場被斬的“白眉倭帥”、生擒的“望斗帥”(77),嘉靖三十四年在臺州大陳島與林碧川一起被擒的烏魯美他郎(78),嘉靖三十五年四月進攻觀海衛慈溪,五月又進攻餘杭縣並被官軍擒獲的“豐洲酋”周乙(79),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副使許東望在馬墓福山洋擒獲的二曪表、柘林一帶“生擒倭賊助四郎等”(80),嘉靖四十年戚繼光臺州長沙之捷生擒的“倭酋五郎、如郎、健如郎前後數十輩”(81),等等。上述這些倭寇由于屬倭人頭目,所以被記録下來,更多的倭寇因爲並不著名而不見記載。當時的刑部主事郭仁講到其在刑部時遇到朝鮮國解來的倭寇望古、三甫羅等,在其的贓物中有“火銃木牌,刻有軍門及松江府字號”,因此判斷“則倭奴之流劫江南也無疑”(82),但相關史書並没有“望古、三甫羅”劫掠松江的記載,或雖然記載了卻不知是“望古、三甫羅”等所爲。(83)采九德《倭變事略》記載數十起倭寇侵犯事件,但倭寇有名姓者卻僅有“二大王”、“八大王”之稱謂(84),其它如“衣紅衣渠魁二人”(85)、“倭酋一人”等等不記其名姓者更多,可見要明確倭寇之真僞並進而記録其身份情况確實是不那麽容易的。嘉靖三十六年隨王直一起來的倭寇頭目有四十多人,但也只記下了善妙一人(86),而倭寇嘍羅更無從記載。實際上嘉靖倭患初起時,當時國人對倭寇的成分、倭寇的起因曾經一度很不瞭解,更不用說記録倭人的名姓了;當時還曾把佛朗哥等認作“老回回”,以爲所謂的“倭寇”可能是“老回回”作案,並不像後來對王直徐海輩携倭作亂有所瞭解:
近年黄岩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近者流寇亦不知何賊首亂,何事兆隙,所云老回回等名目,亦未嘗知回回何姓名也,其作賊之繇,或云逃兵,或云饑民,亦不確也(87)。
顯然,倭患最初爆發時,並不像後來許多史書記載的那樣明確,黄岩縣被攻陷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這是首次有縣城被倭寇攻陷。此後倭患大爆發,倭寇萬餘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流劫臺州、温州、寧波、紹興等地,當時對“何賊首亂,何事兆隙”等問題一度還很有疑問。况且倭寇一旦被俘,“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88),難以辨其倭人身份。即使開口,“言如鳥語”,也不辨真僞。(89)因爲倭人與國人長相差別不大,“言如鳥語”,很難區分是真倭、或是國人作僞,更談不上記録這些倭寇姓甚名誰了。
王世貞《倭志》說:“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築前、築後、博德、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90),顯然大批倭人的入寇在當時是明顯存在的事實。這些入寇的倭人一旦劫掠得手,即滿載而歸,“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91)可見倭人大批的來中國劫掠、經常地來“做客”也是當時普遍存在的事實;“做客回”後鄰家還來“稱賀”,類似于遠道經商返家,對倭人而言也算是尋常事。胡宗憲“譯審”倭寇“助四郎”時,該倭寇即稱“彼國荒旱,私出買賣,國主不知”。(92)鄭曉記載說:倭人“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唤,而不知其已爲俘鬼”。(93)到中國來大肆劫掠卻與做“買賣”“交易”“做客”是同一意思,可見倭人視劫掠大陸沿海爲平常事。這些以交易爲名、行劫掠之實的真倭顯然是大量存在的。《明史》指出:“(王)直初誘倭入犯……既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94),倭寇來犯後“有全島無一歸者”,可見來“買賣”“交易”的倭寇並不在少數,籠統地把倭人倭寇視爲“主要成分是中國沿海居民”(95),顯然是有所偏頗的。《嘉靖平倭祗役紀略》記載一被劫平民講述倭人駐地的情况,就很能說明問題:
逃回民人倪淮供: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內被倭賊攔搶上船,跟到彼處,只見漳、温兩處人無數在彼,衣帽言語一般。說這裏是日本國所管,地名五斗山,種植稻米、緑豆、大小二麥、菜蒜等物。但來打劫,俱是漳州人指引,船中俱有倭子做主;如要來者,先送一千文與船主。今年(96)四月二十一日,賊衆合伴共有七百餘船開洋,大者每船二三百人,小者三四十人,各自備飯米。(97)
此段文字雖然有誇張的部份(98),但也透露下述一些信息:1、來犯倭船都由倭人主導,“船中俱有倭子做主”;2、每次來犯,都有國人帶路,“俱是漳州人指引”;3、當地倭人只要交出乘船費用,“先送一千文與船主”,就可以上船到明朝“交易”、“打劫”了,但船主不管餐食,需“各自備飯米”;4、倭船“大者每船二三百人,小者三四十人”;5、當地倭人中混雜有許多中國人,這些違禁通番的國人以漳州、温州人居多,“漳、温兩處人無數在彼”。
由此可見,嘉靖倭寇的組成實際上是一種比較鬆散的組合體,其中以倭人爲主體,部份流竄到彼的國人參與、引導。一旦到大陸土地,由于關係到各自的“買賣”利益,于是争相竟進。而各地官軍畏懼作戰,遇倭即潰,由此,倭人“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歆慕之心”,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嘉靖大倭患。
俞大猷在《議處日本貢》中講到的事例也能說明倭寇的來源主要在日本各島:
賫去浙江布政司宣諭明文,轉行各島,禁戢過海爲盗之倭,亦甚嚴切,今歲入寇之賊數較少,是其驗也……今源議鎮(99)……能禁衆倭之侵,今歲揚州之賊雖有數千,又直、浙沈家門等處屢有小警,要之比諸前歲江北、江南共有數萬之賊,似亦小綏,而源議鎮輸款效勞之功、誠有不可掩者。(100)
上述文字記載,由于浙江布政司代表朝廷向日本島主發出“明文”,要求約束倭寇海盗,于是“山口、豐後等島主源義鎮”對過海而來的倭寇嚴加禁止,“禁戢過海爲盗之倭,亦甚嚴切”,使得第二年兩浙一帶入犯倭寇明顯减少,“今歲入寇之賊數較少,是其驗也”,可見倭寇中的大部份是來源于日本諸島,當然,其中可能也包括居住在五島一帶的王直團夥等。
另一個現象也可以說明真倭是造成嘉靖倭患的主因:自從嘉靖二十七年日本貢使周良入貢以後,在嘉靖倭患最劇的一段時間內,即再也没有派遣使者來貢(101),這與此前日本頻繁入貢、“多有先期入貢”的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原因即是日本也自知“嘉靖大倭患”對中國挑釁太過、造成禍害太深,因此也不再覥顔入貢。徐光啓在《海防迂說》中說:“自時厥後,倭自知釁重,無由得言貢市”(102),即說明了問題。
3.國人接濟參與
但不可否認的是,倭寇中多有國人參與,也是嘉靖倭寇的不争事實。大凡倭寇團夥人數上萬,其中“出于日本者不下數千”(103),而更多的可能都是一些在籍編戶、沿海流寇,畢竟倭寇多以小股爲主。尤其是在王直、徐海等的團夥中,國人數量多于倭人,也是當時一段時期內的客觀事實。其實,從相關資料來看,不僅僅是嘉靖年間,即便是正統前後的倭寇,數量達到數千的,其中也往往多有沿海居民參與其中。所謂“國初倭患,雖遍于沿海一帶,然止倭耳”(104),這樣的判斷恐怕不全是事實。正統時黄淮記載桃渚所被陷事件時說:“狐鼠之輩睨鼎垂涎,心萌覬覦;外侮乘隙作釁,桃渚、大嵩先後爲賊鋒所襲”(105),所述即是指沿海居民與外來倭寇相互呼應、聯合作亂的情况。而洪武初期,史書也記載張士誠、方國珍餘部入海島引倭入寇的情况(106),顯然即使是明代早期,也有部份國人參與倭寇劫掠的情况。實際上有明一代的真倭,多是以小股的倭衆爲主的,“皆三、四十人作一夥”(107),“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108)除了永樂時期的望海堝之役外,其餘時期的倭寇主體還是以小股的“專業海盗”爲主,也包括“莊官、地頭、武裝商人的團夥、沿海地方的農民、漁民”(109),組成爲數不多的倭人團夥。人數衆多的倭寇入犯事例,則往往有國人參與。
倭寇主體是日本人,而“中國叛逆”往往做接引、糾合之事。浙江提督王忬說:“閩廣徽浙無賴亡命,潜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者則聯夷肆劫。”(110)實際上,“倭之能賊害我中國者,皆我中國人媒之也”。(111)因爲有內地叛逆接引,所以倭寇纔敢成群結夥而來,“且如閩廣群不逞之徒、明越諸得利之家,外交內詗,爲彼耳目。”(112)都御史章焕說:“倭患之熾,其原不在于外,中原之雄咸爲之謀主也。土著之奸人爲之向導也,窮民爲之役使也,有是三者,然後能深入長驅。”(113)而徐海、陳東之輩也是因爲熟悉內地情况,而成爲倭寇幫凶,“看得陳東等本以華民,背逆天道,勾引倭奴辛五郎等,侵擾內地,流毒三省。”(114)因爲華人諳熟國內情勢,許多時候華人就成爲倭寇的頭目,“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其魁,則皆閩浙人”。因爲倭人“勇而戇”,所以許多中國亡命之徒招徠倭人以爲用,“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舶主……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115)
三、倭寇類別
從相關資料來看,嘉靖年間的倭亂,大致可以分爲三種類型:一類是貢船倭商違規滋事造成倭亂;其次是一些没有勘合的日本私商船隊亦商亦盗;其三是專業日本海盗結合“中國叛逆”,劫掠沿海各地。
1.倭使作亂
倭寇爲患中,貢船倭商違規滋事、滯留不歸造成的倭患,事例雖然不多,但影響卻很惡劣,由此造成的後果也很嚴重。早一些的如景泰年間倭使在臨清“擾害軍民、歐打職官”(116),成化年間倭使“淩轢館僕,殘殺市人”(117),弘治年間倭使在濟寧州“持刃殺人”(118)等,都對市舶的管理問題提出了挑戰。嘉靖二年瑞佐、宋素卿與宗設等的“争貢之役”,一般認爲是嘉靖倭患的肇因,“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圍城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兵,占據門禁”。(119)其造成的直接後果,使得朝廷關閉了市舶司(120),海禁政策也再度收緊,使當時海上貿易比較活躍的局面突然停頓。而沿海私商爲了既得利益,必然要尋求其它途徑,“市禁則商轉而爲寇”,導致違禁下海者鋌而走險。
另一方面,每次倭使作亂,朝廷都以“懷柔之意”而不加懲治,使得倭使越來越無所顧忌,以致屢屢在明朝地方犯下殺人違法之事。宋素卿、宗設“争貢之役”後,朝廷依舊把滋事生非的瑞佐等輕易放回,也再一次讓倭人以及日本國內滋生輕視明朝的傾向,“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121),而瑞佐等百餘人大鬧寧紹,“圍城劫庫”,官軍竟不能制止,也使得日人對明朝沿海防衛的鬆懈有了直接感受,這與之後大倭患的發生不能說没有相當關係。時人李承勛即指出:“其後瑞佐竟釋還該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遺禍無窮。”(122)此後倭人視明廷禁海政策爲無物,五島居民結夥而至,舟山雙嶼一帶隨之形成了離島貿易的集散地,“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123),沿海的劫掠事件隨之也越來越頻繁,並進而引發嘉靖大倭患。
2.走私商船“亦商亦寇”
没有勘合的日本走私商船也是倭患事例的主要肇事者。這些商船爲了自衛也裝備有武器,既作爲自衛,也尋機劫掠,有亦商亦盗的性質。由于日本對中國的貨物有所必需,使得這些亦商亦盗的倭寇有了生存空間,“其嗜中國物猶西番之嗜茶也,西番不得茶必寇掠,倭奴必假寇通商始得所欲”。(124)當時日本商人通過與明朝交易,據說可以獲得數十倍的利潤,一斤生絲運到日本可獲利二十倍,因此雖然風險很大,但冒險者仍舊前赴後繼:“對明貿易利潤是很豐厚的,因而很具有誘惑力”(125),除了持有勘合的官方入貢船隊“十年一貢”,其它的私人貿易船隊也加入到這一利益豐厚的活動中。這些船隊都裝備有武器。爲了應對明朝官軍的圍剿,這些船隊携帶的武器可能還不少。而一旦遇到沿海防衛鬆懈,這些武裝船隊就會趁機劫掠,“倭奴奸詭,載其方物,出没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奮戎器,肆剽掠;不得間則陳方物,稱朝貢”。(126)由于劫掠容易且屢屢得手,這些隨著商船而來的倭人的狡黠本性也隨之膨脹,劫掠也就無所忌憚了,“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127)
3.日本專業海盗與“中國叛逆”合夥爲寇
倭人聯合“中國叛逆”組成的倭寇,是嘉靖大倭寇的主要現象。這些專業的海盗,可能最初會借著經商的名義(128),但其主要目的卻是劫掠。這些專門到周邊沿海進行劫掠的倭寇中,“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築前、築後、博德、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而“中國叛逆”中,嘉靖以前的多不知名,嘉靖時期則以許棟、王直、徐海爲最出名。其中略早些的爲許棟、李光頭等,“黎光頭數爲倭主,已,復引佛郎機行劫”。(129)後來的如王直、徐海等“傾資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130),王直並“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131)
據明成化、正德年間出使日本的朝鮮使者估計,對馬、壹岐、北九州島及瀨戶內海的倭寇海盗,大者數百股,小者數十股,總數約有數萬。(132)這些數量衆多的小股倭寇一旦與沿海的“中國叛逆”結合,就會形成很大的勢力,畢竟倭寇主要以小股的海盗爲主。據說朱元璋曾經對劉基談起倭寇爲患之事:“東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亦猶蚊蟲警寤,自覺不寧。”(133)可見倭的盗寇性質從來是比較明顯的,但嘉靖時期因爲“編戶之齊民”參與多了,僞倭寇人數多了,倭寇的構成也有了變化,由此形成了倭寇盡爲國人的錯覺。但倭寇造成的禍患,倭寇掠奪的性質並没有改變,某些階段國人參與人數的多寡也並不能改變倭寇寇邊的本質。
四、倭寇禍害
倭寇入犯,在明初主要是沿海劫掠,當時武備强勁,故没有造成大的侵害。明代中期由于承平日久,沿海軍衛涣散,倭寇開始攻城掠寨,其凶殘本性也逐漸暴露,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如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餘艘攻陷浙江臺州桃渚千戶所,大肆殺掠:
劫倉庫,焚室廬,驅掠蒸庶,積骸如陵,流血成穀。嬰兒縛之竿柱,沃以沸湯,視其啼號爲笑樂。捕得孕婦,與其儕忖度男女,剔視之以中否爲勝負,負者飲酒。荒淫穢惡,至不可言。民之少壯與粟帛,席捲歸巢。城野蕭條,過者隕涕。(134)
到了嘉靖中期以後,倭患爆發。倭寇長期盤踞浙西一帶,給兩浙一帶造成嚴重創害。東南兩浙一帶,自兩宋以降,人口繁盛,財賦集中,村鎮聚落多不設防,倭寇衝突其中,造成的禍害也最爲慘烈。(135)且兩浙一帶素無戰事,民不知兵,一旦戰亂發生,容易形成大的禍害。時人評論,認爲倭患之害,其慘烈程度,爲兩漢以來之未有。“吾浙、直數十州郡,所橫罹倭夷之慘,漢以來西北所當虜患、雲中上党漁陽之變、蓋未有並之者”。(136)可見民生受害之深,非史書可以盡言。在倭寇爲患的幾年裏,燒殺擄掠,慘劇連連,使得素稱繁華之所的浙西,千里成墟。采九德《倭變事略》記載倭寇劫掠事例頗多,茲試舉幾例:
癸丑年……吾鹽被寇者四,死者約三千七百有奇;平湖、乍浦各三被寇;澉浦、海寧各一被寇。(倭寇攻陷乍浦所城)屠戮淫劫,不勝其慘。
越數日,黄灣賊千餘,掠袁花鎮,焚劫甚慘。……所過數十里無人烟,海寧大姓多罹其害。
廟灣周氏有二庠生,執之,令負擔,不勝,釘手足于樹,殺之。
隨處掠劫人口,男則導行,戰則令先驅。婦人晝則繰繭,夜則聚而淫之。
石墩賊攻澉浦城……不得志,殺男婦千餘以泄怒,見者悲痛。
(倭寇)居吾土凡四旬有三日,殺害數千人,蕩民産數萬家。
(倭寇)退就石條街,毁劫一夜,焰燼亘數百里焉。
有避寇村婦數百,繈負幼小,齊渡西浦橋,值天雨橋滑,皆弃兒匍匐以渡。河畔積孩尸甚多,悲號震野。
(倭寇)抵長安鎮……遂分入客店擊殺,鎮民騷動出避,傷者死者塞途,樂土一旦丘墟矣
犯湖州市,大肆毁掠……殺人無算,城邊流血數十里,河內積滿千船。
賊遇鄉官侍御錢鯨送家衆,抵家,殺侍御並家衆。
所掠蠶繭,令婦女在寺繰絲,裸形戲辱之狀,慘不可言。(137)
鄭茂《靖海紀略》記載:
(倭寇)毁民房三百餘,自天寧寺而止,皆鞠爲煨燼。烟塵蔽空。(138)
《全城記》記載:
城外焚廬舍、伐林翳,繫虜男婦,殺溺死者無算,金帛財物捆載。百里而內,村落爲墟。(139)
《金山倭變小志》記載:
(倭寇)分劫追趕,男婦溺死大橫潦涇者六百餘人,泖東西如張莊、楊扇、高滸、呂巷等鎮,無一免者。(140)
徐宗魯《松寇紀略》記載:
(倭寇攻)青村,軍民死者幾二千餘。劫財擄婦女,即歸巢。
賊攻蘇郡,至西關,大肆焚掠,大家小戶盡遭殘破,烟火七晝夜不絶。(141)
天啓《平湖縣志》:
(倭寇攻陷乍浦城)屠戮淫劫,不勝其慘。(142)
嚴從簡《殊域周諮録》:
三四年間,吏民死鋒鏑、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143)
當時的奏疏、筆記等也多有倭寇爲患、殘害生民的記載:
倭賊犯境,百姓被殺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至村落爲之一空。迄今逾月,其勢益橫。(144)
(倭寇)大肆侵掠,傷殘人命有如草菅。自有郡邑以來所未經見。
自甲寅乙卯纔兩歲耳,賊凡三至……男女死者無筭。小民瓶罌之儲、茅茨之蓋,鮮一存者。危堞孤懸,兀然江滸,處處烟生,夜光盡赤,皆爲賊火。(145)
彼倭奴突入中壤……殺人如麻,流血積骸動若川阜;焚劫室廬,半爲懸磬焦土。(146)
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鏑,積尸高者丘陵,卑者溪澗爲之不流。(147)
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錢薇《血泪歌》描述當時海鹽縣被倭寇劫掠後的慘狀:
端陽五日與六日,四郊烟焰運雲高。紅巾填塞秦溪野,勁槍毒矢殺氣豪。此時哭聲動天地,橫山積血成波濤。少婦污蔑觸白刃,嬰兒中塑娘同刀。(148)
倭寇爲患兩浙多年,燒殺劫掠、無惡不作,諸如“河畔積孩尸甚多,悲號震野”“此時哭聲動天地,橫山積血成波濤”等現象,可謂不一而足。但上述記載僅僅是倭寇劫掠造成的一小部份事例,更多的慘案早已被時間所淹没,不爲人知。那些認爲嘉靖倭患是“轟轟烈烈的反海禁鬥争”(149),要“爲王直記一大功”(150)的看法,或許並不是恰如其分的判斷。嘉靖年間的倭患,就是國家之灾禍、民生之苦難。而對于那些塗炭之生靈而言,更是滅頂之灾。對造成這些禍害的倭寇,需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判斷,這也是撰寫本文的初衷。
①相關論著有鄭振鐸《明代倭冠侵略江浙考略》(《七種聯刊》1937年第1—4期)、剪伯贊《論明代倭寇及禦倭戰争》(《中蘇文化》1940年第6期)、李晋華《三百年前倭寇考》(上海國民外交委員會,1933年)、陳懋恒《明代禦倭考略》(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孟錦華《明代兩浙倭寇》(國民出版社,1940年)等文。
②許多學者認爲,所謂的“倭寇”國人數量遠多倭人,這些國人是反壓迫、反腐朽朝廷。如陳鳴鐘認爲“‘小民’的從倭,或是困于徭役,或是迫于饑餓”,並且認爲“通倭、從倭的華人,遠多于所謂的‘真倭’”,(《嘉靖時期東南沿海的倭寇》,《新史學通訊》1955年2期);云川在《明代東南沿海的倭亂》也持類似判斷,見《新史學通訊》1956年2期。
③見陳抗生:《嘉靖“倭寇”探實》,《江漢論壇》1980年第3期;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戴裔煊:《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盗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蔭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日本學者也有類似觀點:“倭寇的本質,並不在于中國人、朝鮮人、或日本人中參與行寇人數的多或少,而在于……它承擔著環中國海地域國際通商交流的重任”。村井章介:《亞洲中的中世日本》“倭人海商的國際位置”,東京:校倉書房,1988年。
④如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爲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等等。
⑤陳學文《論嘉靖時的倭寇問題》說:“倭患是日本海盗勾結喪失民族立場的中國奸商侵擾中國的侵略行爲。”見《文史哲》1983年第5期;陳學文:《明代倭寇事件性質的探討》《江海學刊》1958年第4期;張聲振:《論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質》,《學術研究》1991年第4期;張聲振:《再論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質——兼與〈嘉隆倭寇芻議〉一文商榷》,《社會科學戰綫》2008年第1期。等等。
⑥鄭曉:《今言》卷三“二百三十九”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⑦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認爲“元末明初的倭患,主要是日本海盗剽掠中國沿海,嘉靖以後……倭寇隊伍的成分發生了變化”。詳見《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⑧王儀《明代平倭史實》說:“在明世宗嘉靖間,是倭寇最爲猖獗的一段時期,但日本人在比例上反占少數,其中多爲閩、浙、粵沿海之地的海盗,與貪圖暴利的奸民,以及被威迫落寇的良民。這個時期所謂的倭寇,可視爲中、日匪類的大結合……不過日本人成爲倭寇的主角,則是鐵的事實,已不容否認的了”。筆者基本認同這樣的判斷。
⑨《元史》卷九九、志四七《兵二·鎮戍》。
⑩同上,卷四六、本紀四六《順帝九》。
(11)《太祖實録》洪武二年一月乙丑。
(12)同上,洪武元年年二月乙丑。
(13)同上,洪武二年四月戊子。
(14)同上,洪武二年八月乙亥
(15)同上,洪武三年六月乙酉。
(16)同上,洪武五年六月癸卯。
(17)同上,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甲子。
(18)《朝鮮史略》卷八《髙麗紀·康宗元孝王十四年》。臺灣文淵閣《四庫全書》版,《史部·載記類》。
(19)同上,卷九《髙麗紀·忠烈王五年》。
(20)《朝鮮史略》卷十一《髙麗紀·恭湣王九年》。
(21)同上,《髙麗紀·恭湣王二十年》。
(22)同上,《髙麗紀·辛禑二年》。
(23)“朝鮮”之稱謂始于洪武二十五年,此前應稱作“高麗”。見《太祖實録》洪武二十五年閏十二月,“乙酉,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號曰朝鮮”。
(24)《太祖實録》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丙戌。
(25)鄭曉:《皇明四夷考》,《國學文庫第一編》,1933年。
(26)茅坤:《條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宜》,《明經世文編》卷二五六《茅鹿門文集》。
(27)《太祖實録》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癸酉。
(28)天啓《海鹽縣圖經》卷七《兵衛》。
(29)《英宗實録》正統四年五月庚午。
(30)嘉靖《寧波府志》卷二二《海防書》。
(31)《英宗實録》正統七年五月丁亥、六月壬子。
(32)錢薇:《與當道處倭議》,《海石先生文集》卷十《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7册,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33)錢薇:《處倭議》,《海石先生文集》卷十《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7册。
(34)《憲宗實録》成化五年五月辛丑。
(35)《英宗實録》正統八年七月庚申。
(36)同上,正統七年六月辛卯。
(37)《憲宗實録》成化四年六月戊戌:“日本國通事林從杰等三奏:原係浙江寧波等府衛人,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
(38)《英宗實録》正統八年六月戊申。
(39)同上,景泰四年八月丁亥。
(40)崔溥:《漂海録》卷一。
(41)嘉靖二年六月“日本國夷人宗設、謙導等賫方物來,已而,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俱泊浙之寧波,互争真僞,佐被設等殺死,素卿竄慈溪,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袁璡,蹂躪寧紹間,遂奪舡出海去”(《世宗實録》嘉靖二年六月甲寅),是爲“争貢之役”。
(42)《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三、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倭寇浙東”。
(43)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五《浙江倭變紀》載:“嘉靖十九年……福人李七、(歙人)許棟……皆以罪繫福建獄,逸入海,勾引倭奴,結巢于霩衢之雙嶼港,其党有王直、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出没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
(44)嘉靖《永嘉縣志》卷五《兵衛》。
(45)《世宗實録》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46)《籌海圖編》卷十一《經略一·叙冦原》。
(47)胡宗憲:《題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疏》,《明經世文編》卷二六六《胡少保奏疏》。
(48)趙炳然:《與張半洲書》,《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三《趙恭襄文集》。
(49)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九《命將下》。
(50)嘉靖《太平縣志》卷五《職官下·兵防》。
(51)鄭茂:《靖海紀略》,《叢書集成初編》第3226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52)歸有光:《備倭事略》,《歸先生文集》卷二《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8册。
(53)屠仲律:《禦倭五事疏》,《明經世文編》卷二八二《屠侍御奏疏》。
(54)謝杰:《虔臺倭纂》上卷《倭原二》。
(55)《皇明四夷考》。
(56)采九德:《倭變事略》,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第88頁。
(57)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卷二《論福蒼船之弊》。
(58)《備倭事略》,《歸先生文集》卷二《議》。
(59)《條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宜》,《明經世文編》卷二五六《茅鹿門文集》。
(60)《世宗實録》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61)本地盗寇一段時間內多于外來倭寇的情况應該也是客觀存在,即便是同樣遭受倭寇困擾的朝鮮,當時也有類似情况:“倭寇興行,民不聊生,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見《朝鮮王朝世宗實録》二十八年十月壬戌。
(62)陸葇:《通洋宜防倭患議》,康熙《平湖縣志》卷八《藝文》。
(63)嘉靖《太平縣志》卷五《職官下·兵防》。
(64)唐順之:《三沙報捷疏》,《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九《唐荆川家藏集》。
(65)唐順之:《與胡默林一》,《明經世文編》卷二六○《唐荆川家藏文集》。
(66)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四《四裔考·東夷》,並見《鄭開陽雜著》卷二《日本入寇論》,及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選》卷六《倭志》。
(67)《籌海圖編》卷十二《經略二·在京各衙門會議云》。
(68)《題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疏》,《明經世文編》卷二六六《胡少保奏疏》。“私出買賣”,即指到明朝沿海劫掠。
(69)《籌海圖編》卷十一《經略一·叙述寇原》。
(70)嘉靖《寧波府志》卷二二《海防書》。
(71)王忬:《條處海防事宜仰祈速賜施行疏》,《明經世文編》卷二八三《王司馬奏疏》。
(72)《明史》卷二○五、列傳第九三《胡宗憲》。
(73)周召:《雙橋隨筆》卷二。
(74)《籌海圖編》卷九《大捷考·金塘之捷》。
(75)趙文華:《嘉靖平倭祗役紀略》卷五《獻俘疏》。
(76)《明史》卷二○五、列傳九三《朱紈》。
(77)《世宗實録》嘉靖三十五年十月癸巳。
(78)同上,嘉靖三十四年九月戊申。
(79)《籌海圖編》卷五《浙江倭變紀》。
(80)《題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疏》,《明經世文編》卷二六六胡少保奏疏》。
(81)《籌海圖編》卷九《大捷考·長沙之捷》。
(82)同上,卷十二《經略二·在京各衙門會議云》。
(83)尤其典型的是,上述同樣記載朝鮮解來的倭寇,刑部主事郭仁記録有“望古、三甫羅”,南京工部尚書馬坤記録有“林望、古多羅”(《籌海圖編》卷十二《經略二·在京各衙門會議云》),《世宗實録》也記有“謀叛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世宗實録》嘉靖四年四月癸卯),看似名姓差不多,初以爲是一回事。實際上“林望、古多羅”是指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争貢之役”時在寧紹一帶作亂的倭寇,後逃歸時被朝鮮國截獲,並遣送回明朝;而“望古、三甫羅”是刑部主事郭仁“承乏刑曹”即在刑部任職時遇到的事情。郭仁是“長洲人”,嘉靖十六年中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可見其在刑部任職是在二十六年以後,其所述“望古、三甫羅”顯然與嘉靖初年的“林望、古多羅”不是同一夥倭寇,此事也見于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歐陽德所撰《朝鮮擒獲倭犯疏》,其中也提到“望古三夫羅等犯、並銅銃木牌等器”(歐陽德:《朝鮮擒獲倭犯疏》),由此可見,倭寇姓名對國人來說非常容易混淆、不易區分,要記録“某某倭寇劫掠”也是比較難的事情,况且“望古、三甫羅”與“林望、古多羅”,以及“五郎、如郎、健如郎”的確實難以區分,不如許棟、徐海輩容易記住。
(84)《倭變事略》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二日、五月初六日。
(85)《籌海圖編》卷九《大捷考·寧臺温之捷》:“兵分三路進剿,殺死三百餘人、衣紅衣渠魁二人”。
(86)《世宗實録》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乙卯:“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王)直等來”。
(87)《條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宜》,《明經世文編》卷二五六《茅鹿門文集》。
(88)《鄭開陽雜著》卷四《寇術》。
(89)《倭變事略》三十三年十月初八日:“生擒十三賊,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
(90)王世貞:《倭志》,《弇州山人四部稿選》卷六《文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5册。
(91)《鄭開陽雜著》卷四《寇術》。
(92)《題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疏》,《明經世文編》卷二六六《胡少保奏疏》。
(93)鄭曉:《答荆川唐銀臺》,《明經世文編》卷二一八《鄭端簡公文集》。
(94)《明史》卷二○五、列傳第九三《胡宗憲》。
(95)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95~97頁。
(96)即嘉靖三十四年。
(97)《嘉靖平倭祗役紀略》卷二《賊情疏》。
(98)“共有七百餘船開洋,大者每船二三百人,小者三四十人”云云,或有誇大描述的成分。
(99)俞大猷:《議處日本貢》載:據出使日本諸島的蔣洲等口述,“山口島太守源議長……即豐後州太守源議鎮之親弟也,此兄弟二人近歲以來聲勢相倚,令行諸島,源議鎮見管之州六,源議長見管之州十有二”。《世宗實録》“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乙卯”稱爲“山口、豐後等島主源義鎮”。
(100)俞大猷:《議處日本貢》,《明文海》卷八一。
(101)查閱:《明實録》,《世宗實録》有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使臣周良等入貢事例,此後的嘉靖年間没有日本入貢記載;隆慶、萬曆年間,《穆宗實録》《神宗實録》等也没有日本入貢的記録,這與明代早、中期日本頻繁入貢形成强烈反差。
(102)徐光啓:《海防迂說》,《明經世文編》卷四九一《徐文定公集》。
(103)《籌海圖編》卷十一《經略一·叙冦原》。
(104)《與當道處倭議》,《海石先生文集》卷十《議》。
(105)黄淮:《桃渚千戶所遷城記》,見《介庵集》卷九。
(106)《皇明四夷考》:“初,方國珍據温、臺、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松、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强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
(107)徐宗魯:《松寇紀略》,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1955年。
(108)《虔臺倭纂》上卷《倭巧》。
(109)山根幸夫:《明代倭寇問題研究》,《江淮學刊》(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1期,第78頁。
(110)王忬:《倭夷容留叛逆糾結入寇疏》,《明經世文編》卷二八三《王司馬奏疏》。
(111)《虔臺倭纂》上卷《倭媒》。
(112)《與當道處倭議》,《海石先生文集》卷十《議》。
(113)章焕:《南方兵事疏》,《明經世文編》卷二七二《章中丞奏疏》。
(114)俞汝楫:《禮部志稿》卷六八《征倭獻俘》。
(115)《倭志》,《弇州山人四部稿選》卷六《文部》。
(116)《英宗實録》景泰五年二月乙巳。
(117)見《憲宗實録》成化四年十一月壬午、成化五年五月辛丑。
(118)《孝宗實録》弘治九年八月庚辰。
(119)夏良勝:《勘處倭冦事情以伸國威以弭後患疏》,《名臣經濟録》卷四二。
(120)“争貢之役”後,“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鄭曉:《吾學編》)。《明史》也說:“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
(121)《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亂》。
(122)李承勛:《勘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疏》,《李康惠公奏疏》,《明經世文編》卷一○一。
(123)《倭志》,《弇州山人四部稿選》卷六《文部》。
(124)錢薇:《海上事宜議》,《海石先生文集》卷十《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7册。
(125)《明代倭寇問題研究》,《江淮學刊》(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1期,第79頁。
(126)《與當道處倭議》,《海石先生文集》卷十《議》。
(127)《皇明四夷考》上卷《日本》。
(128)如前引倭寇“助四郎”所稱“彼國荒旱,私出買賣,國主不知”,即以買賣之名義行劫掠之實。見《題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疏》,《明經世文編》卷二六六《胡少保奏疏》。
(129)《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九《明世宗皇帝》
(130)佚名《王直傳》。
(131)《籌海圖編》卷九《大捷考》。
(132)《李朝世宗實録》世宗十一年十二月乙亥。轉引自張聲振《論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質》,《學術研究》1991年第4期,第69頁。
(133)嘉靖《寧波府志》卷二二《海防書》。亦見王士騏《皇明禦倭録》“卷之一”引《日本國略》。
(134)《與當道處倭議》,《海石先生文集》卷十《議》。
(135)康太和《擬應詔陳言以備安攘大計疏》:“今江南財賦淵藪,民多散居田里,如直之羅店閔行、淅之塘西硤石等處,廛宅連雲,可當近邊二三縣,緣無藩垣屏翰之備。以故賊一突至,長驅深入,如履無人之境”見《皇明經世文編》卷213《留省稿》。
(136)茅坤:《與趙方厓中丞書》,《明經世文編》卷二五六《茅鹿門文集》。
(137)《倭變事略》。
(138)《靖海紀略》,《叢書集成初編》第3226册。
(139)《倭變事略》所附《全城記》。
(140)玉壘山人:《金山倭變小志》,見《倭變事略》。
(141)《松寇紀略》。
(142)天啓《平湖縣志》卷六《倭變》。
(143)嚴從簡:《殊域周諮録》卷三《東夷·日本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144)《備倭事略》,《歸先生文集》卷二《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8册。
(145)張袞:《題爲獻末議靖丑夷疏》,《張水南文集》卷三《奏疏》。
(146)同上。
(147)王維楨:《答姜以正僉憲書》,《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二四《文部·書》。《續修四庫全書》第13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48)嚴從簡:《殊域周諮録》卷三《東夷·日本國》引。
(149)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50)陳抗生:《嘉靖“倭患”探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