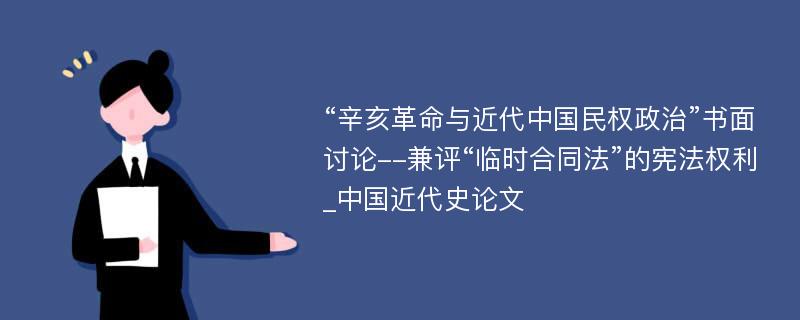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权政治”笔谈——《临时约法》制宪权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约法论文,笔谈论文,民权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宪法是国家与人民的契约,也是不同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书。可以说,谁掌握制宪权,谁就在权力分配书的设定上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1912年年初,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对制宪权的争取或者争夺,就成为新政权宪争的最初波澜。
1912年1月30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派员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送到参议院,请各位议员参考。孙中山说:“查临时政府现已成立,而民国组织之法尚未制定,应请贵院迅为编定颁布,以固民国之基。并据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呈拟《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五十五条前来,合并咨送贵院,以资参叙。”但是,孙中山递送组织法草案的举动,遭到参议院的拒绝。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孙中山送来组织法草案之前,参议院的前身代理参议院就已经开始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逐步演化为临时约法。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在参议院正式成立之前,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职权,从1912年1月2日起。1月5日湖北、江西、福建、云南、广东、广西六省代表提出,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人民权利义务”一章,公决前先付审查员景耀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君武拟具修正案。当人权条款订出时,议员们觉得放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不合适,故拟将文本改名为临时约法。1月25日,景耀月等5人向代理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并进入审读阶段。可见,在孙中山派员送呈《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之前,参议院就已拟好临时约法草案。
1月31日,参议院议定:不接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草案,为郑重计,委专人起草否决书,该书称:“宪法发案权应归国会独有,而国会未召集以前,本院为唯一立法机关。故临时组织法应由本院编订。今遽由法制局纂拟,未免逾越权限。故虽称为参考之资,而实非本院之必要。”
为探究参议院否决孙中山提议和垄断制宪权的原因,实有必要了解参议院参会人员构成。
广东:赵士北(同盟会员,留学美国);湖南:欧阳振声(同盟会员,留学日本)、彭允彝、刘彦(留学日本);湖北:时功玖(同盟会员,留学日本);江西:汤漪(同盟会员,留学美国);广西:邓家彦(同盟会员,留学日本);浙江:王正廷(同盟会员,留学日本)、陈毓川、殷汝骊(同盟会员,留学日本);福建:潘祖彝(同盟会员,留学日本);江苏:陈陶怡(副议长);安徽:常恒芳(留学日本)、凌毅(同盟会员);山西:李素、刘懋赏(留学日本);贵州:平刚(同盟会员)、文崇高;云南:段宇清(同盟会员);陕西:赵世钰;四川:吴永珊(留学日本)、周代本(留学日本);奉天:吴景濂;河南:李鎜。
请假参议员:福建:陈承泽、林森(议长);四川:张懋隆;江苏:凌文渊;江西:王有兰、文群;湖北:张伯烈、刘成禺。
在以上22名参会人员中,同盟会员占到12名,正好一半(非同盟会又非整体),所以当天的参议院实以同盟会成员居主。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同盟会总理兼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提议,尚需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其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融洽。当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过渡成代理参议院之后,各省就委派了各省参议员组成参议院,议员们是受各省都督的委托或旧咨议局的委派来南京的,他们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各省尤其是各省都督的受托人,这就难以罔顾委托方的意志和利益。当时,各省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并不理想,用孙中山的话说是“各省联合互谋自治”(《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相当有限,胡汉民称之为“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既然地方政府强悍,各省参议员代表地方前来,就不必事事听命于中央行政。
其二,同盟会外部受压,内部分派。从内部来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倒孙人士颇有离心力,即使是追随孙中山的少壮派,也存在胡汉民为首的“左派”和宋教仁为首的“右派”的分野。从外部来看,同盟会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以黎元洪、蔡锷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都在分散同盟会的影响力,对同盟会成员进行合纵连横。由此,同盟会会籍的众多参议员们就无法做到行动一致,共进共退,并服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意志和规划。
其三,参议员具有共同体意识。各省的参议员绝非随意选取,而注重其学历、专业背景和经验,如蔡锷《致杨毅廷张耀曾电》中所言,参议员“其职权在参与立法,监督政府,关系甚巨,应选精通法律、文言并妙之人”。这些成员,大多具有留日背景,少数则有留学欧美背景,有的研析法科,有的是旧咨议局的成员,都有较强的自主性与判断力。参议院既已成立,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机构,参议员们都不难明白权力分立的法理精神,从前是纸上谈兵,如今实际运作的契机来临,岂愿轻易糟蹋?还在参议院正式成立之前,代理参议院就已行使参议院权力,针对孙中山关于继续停战的决定,认为这不仅没得到代理参议院的同意,也没有通知本院,有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尤为骇异”。由此可见,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立法为己任的参议院一旦形成,就表现出参议员们的共同体意识,这恐怕不是革命领袖孙中山始料所及的。
因此,具有法政素养的参议员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间形成一种宪争态势,参议院将立法权扩大为制宪权与立法权并举,试图垄断制宪权。按照法理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享有立法权。但是,行使立法权并不意味着立法机构要负责所有法律的起草,临时政府中的法制局的职能是起草法律。1月12日,孙中山就派总统府秘书李肇甫送来请求代理参议院审议法制局职制的函件,孙中山表示:“临时政府成立,所有一切法律命令,在在须行编订,法制局之设,刻不容缓。应将法制局职制提出贵院议决,以便施行。”在当时的代理参议院审议通过的法制局职能中,该院认可法制局的职能是:“一、承大总统之命,草订法律命令案;二、对于法律命令有应修改及增订者,得具案呈报大总统;三、考核各部所定法律命令案。”一部分法律而不是全部法律,由法制局起草,参议院审查,应属于各司其职。由此,法制局草拟草案供参议院参考,不属于参议院所说的“逾越权限”,而在参议院议定的职责范围内。进一步说,制宪权与立法权还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未确定制宪权的主体是哪个机构,没有明确规定。但严格来说,如果没有法律文本上的依据,那么制宪权的主体是谁,并不能简单由立法权推理出来。以此来看,参议院拒绝了孙中山,是基于对立法权的双重扩大解释,一者,扩大解释为垄断立法的全过程,连政府方面提供的草案都不接受;二者,扩大解释为立法权包含制宪权。此后,在其制定的临时约法条文中,规定两条,一是临时约法的效力等于宪法,二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权属于国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两条进一步明确了制宪权的归属问题。要知道,早于《临时约法》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没有自称为宪法,这表明在宪法制定之前,民国没有正式意义上的宪法。而《临时约法》作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替代者,将自己等同于宪法,无疑抬高了自己的地位,意味着对国家有了实际的约束能力,并牢牢确认了参议院的宪法修改权和解释权。至于国会享有制宪权的条款,更是以宪法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为国会扩权。这就将制宪权是否属于立法机构的模糊状态,一举说明。
同样是革命之后的制宪,1887年美国制宪与民初的《临时约法》和其后的“天坛宪草”模式不同,美国有专门的制宪会议机构。对比《临时约法》和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到异同。
二者相同之处是:制宪的主体——1912年中国南京参议院和18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都有争夺制宪权、垄断制宪权的行为。南京参议院驳回孙中山提交参考的草案,可以说是垄断制宪权的极端行为,即便没有这个极端的偶然事件,该院垄断制宪权也一定会呈现必然性。费城制宪会议的行为则表现为布鲁斯·阿克曼所讲的:“1787年宪法忽视了《邦联条例》授予大陆会议的修正宪法的权力……制宪会议不顾《邦联条例》的规定,把制定宪法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者不同之处是:参议院是准立法机构,美国制宪会议是专门制宪机构。对南京参议院来说,制宪,既然与普通立法不同。那么,从立法权推导出制宪权,并非顺理成章的逻辑。制宪涉及权力分配,如果总统连一点提交草案以供参考的权利都没有,那就很可能造成机构之间权力的冲突。此次《临时约法》之制定,连时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都不能染指,更不用说远在北京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了,前者和后者都只能完全听命于《临时约法》给自己设定限制。除了总统角色之外,孙中山和袁世凯还在建国和统一过程中有相当贡献。辛亥革命,首先是以革命方式建国,其次又以南北和谈统一,宪法或宪法性法律制定过程中,似不应完全排除在革命建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孙中山和在南北和谈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袁世凯,使其被彻底摒弃在制宪之外。合理的做法,还是在强调分权的前提下,在制宪分配权力过程中谋求最大共识,顾及各方利益,以避免在行宪过程中遭遇冲突。事实证明,当临时约法明确了国会的制宪权之后,袁世凯和国会之间果然就制宪问题发生了巨大分歧,这虽然是后话,却也不能不说是参议院及其替代者国会对《临时约法》的制定产生路径依赖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说,参议院在制定《临时约法》过程中,过于强调了权力的分立,而忽视了权力分立造成的不信任,也忽略了妥协和折中的智慧。美国宪法不同,作为专门的制宪机构,能够超然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上来分配机构权力。尤其重要的是,在立法过程中,制宪者们重视妥协,正如阿克顿在对比法国和美国革命时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建设时期,人们作出一切努力、设计出种种方案来阻止不受约束的民主制度……(制宪者们)不属于那种好走极端的人,他们最令人难忘的发明创造不是出自机巧的设计,而纯粹是不彻底的折衷办法和互相妥协的产物。”观之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亦证阿克顿之说。
民初参议院退回孙中山提交参考草案的史事,看似一个细节,实为大细节。制宪权问题,实为大问题。《临时约法》本属临时性的宪法性法律,而在历史的“花车效应”中成为一部大宪法。回顾《临时约法》的制宪权问题,我们无意责备那些优秀的法政前贤,而有心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宪法或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制定之前和制定之后,有政争和宪争乃属正常之事。宪法作为国家契约,本身就是通过赋予政府和人民、中央和地方、各权力机构权力,进而主张和平行宪、和平宪争而排除暴力冲突的最高法律文本。但是,行宪过程中,尤其是制宪过程中,不应因分权而忽略妥协和共识。如果说,制宪的主体问题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立法机构制宪或者制宪会议制宪,那么,尤其在选择前一种模式的时候,适度强调妥协而不是过度扩大自己机构的权力,就成为制宪机构应当自我约束、自我提醒之事。纵览中国民权政治的建设过程,我们总能看到,试图垄断权力,而不是寻求妥协、构建共识,成为一种惯性的思路和做法。辛亥革命百年之时,我们瞻望未来,期待一种在分权前提下倡导温和、中和、共和气质的民权政治思维和民权政治框架。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美国参议院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孙中山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