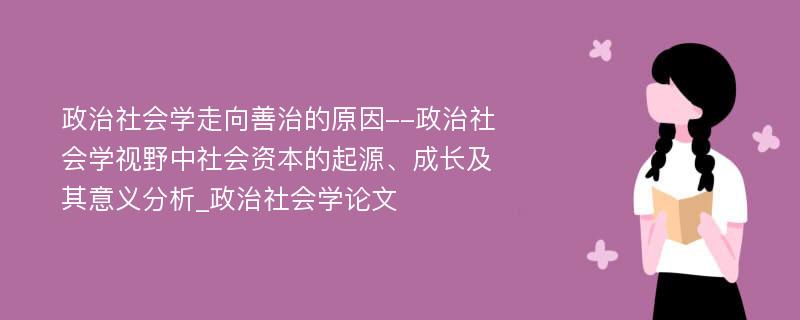
政治社会学走向善治的理由——社会资本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渊源、成长及意义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政治论文,探析论文,渊源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167-12
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当前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理论被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广泛推广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学科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而自罗伯特·D·帕特南于1993年发表其著名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以来,社会资本理论日益成为当代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尽管如帕特南自己所言,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他的独特发明,但是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把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提升为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进而发展成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宏观政治民主方面,这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由于它强调集体行动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重要性,因而这本身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结社传统、信任和合作组成的社会资本促进了善治和民主机制的有效运转。社会资本理论对于研究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政治社会学渊源
政治社会学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是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着重研究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等。①早在古希腊时期,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已为先哲们采用了,只不过那个时代尚缺乏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自觉而已。而社会资本理论的政治社会学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重视民情、民智、民族性格、风俗、习俗等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影响的传统在思想史中古来有之。构成社会资本组成成分的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等因素,都可以在古典政治哲学家的鸿篇巨著中找到其源流。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提出:城邦居民性情的不同,造成了政府的不同。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建立理想社会,并塑造出具有善的心灵和美德的人,因而他以大量的篇幅详尽地讨论了教育问题。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认为对男女都应该进行教育,但教育应当从小开始实行,“真正的爱知者应该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是追求全部真理的。”②在柏拉图看来,教育的作用就是要培养具有一定公共精神和美德的人,从而有利于理想国家的建立。柏拉图对居民性情、公共精神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资本有着某种渊源。
亚里士多德曾认为,人类的目的是实现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其中,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才是最本质的。人只有实现了灵魂的善,才真正有别于动物,才实现了人的本性。在论及公民的本质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有权参加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的人们才是真正的公民,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全体公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他说政治不同于技术,日常所谓的技术,自然应以坚守本业为贵,如鞋匠终身应不离线革,木匠应终身不离斧斤,政治却不应成为统治者终身不离的职业。“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政治上这种恒业就不可能施行,而且根据公正的原则——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正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③他主张公民不仅应当参与政治,而且应当轮流掌权,即公民应当“轮番为治”。他说:“当城邦根据平等原则,由相同身份的人组成政治体系时,公民(城邦组成分子)们自然认为他们大家应该轮流执掌治理的职司主要是致力于被统治者的利益,所以这些义务应该由大家轮流分担,而统治者作为公民团体中的一员,也附带地获得共同的利益。”④在此,他把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资格看作公民的本质。此外,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城邦的讨论涉及城邦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生育、教育等。而良好的公民道德、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和资格、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就很明显与社会资本有着某种模糊的联系。
近代西方国家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基雅弗利则对比了历史上罗马共和国的强盛与当时意大利的衰落,认识到政治——文化变量、伦理价值以及认同和承诺的情感,对政治上的威名与虚弱,对于国家的强盛和衰落是极其重要的。马基雅维利通过对罗马历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罗马共和国崛起并上升到统治地位,其原因就在于罗马拥有“这么多的美德”。⑤而当代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帕特南也是对比了意大利南北两部分公民信任与公民参与传统的不同,得出其社会资本存量存在差异的结论;随后帕特南又对美国各州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了测量,并对其差异进行了详尽地阐释。⑥
较早系统地用社会的观点研究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分析政治现象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用这一方法写出了《论法的精神》一书,在该书中,他描绘和分析了政治现象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孟德斯鸠是近代政治社会学的开创者。孟德斯鸠以亚里士多德的地理环境论为思维素材,认为各个国家中人们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情感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所差异,法律应建立与这种感情与气质的差别之间的相关性。反过来,一个民族因其气候而形成的性格特征,也会影响到它的政治行为。如英国人由于气候的缘故获得了一种不耐烦的脾气,但这种性格极适宜挫败有计划的暴政。孟德斯鸠提出,《论法的精神》这部著作要讨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构成孟德斯鸠全部政治理论的核心与出发点。在孟德斯鸠看来,存在着某些包括自然的、政治的、精神的因素在内的一般原因,在每一个国家中发挥作用。他就是要从自然的、社会的事物中寻求大量的例证,联系当时当地的法律,说明古往今来就存在某些必然决定或者影响法律内容和性质的多种因素,并力图从这些因素的联系中得出一些规定性的原则来。孟德斯鸠认为,法的精神就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他指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治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之间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建立法律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⑦毫无疑问的是,孟德斯鸠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本身具有某种唯物主义因素,对于什么是政治公正的纯抽象解释或先验的解释提出了纠正,他指出了风俗、习惯这些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这对以非正式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理论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而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思想或许与社会资本理论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性。托克维尔是最早将民主理解为社会民主的思想家之一。1831年对美国的考察,使他强烈地意识到美国民主的社会前提是身份和风俗习惯的社会平等,它完全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的贵族统治。托克维尔所理解的美国民主不仅仅是政治形态的民主,而且是遍及整个社会的民主。托克维尔对美国民情与民主的关系进行了详尽地阐述。托克维尔指出,“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做我全部想法的终点。”⑧就民情而言,在托克维尔那里,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⑨概而言之,民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或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在民情当中,宗教和教育、习惯以及实践经验等等都很重要。托克维尔对美国民情与民主关系的考察,与帕特南对于公民传统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探讨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地方政府改革绩效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造成意大利南北不同改革效果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形成的公民传统,这些公民传统延续下来形成了今天不同的地区公共生活,从而带来了民主政治的不同绩效。
托克维尔还指出,在民主国家,在他看来,现代性带给人类的是分裂、孤独、软弱的原子地位,彼此除了利益和权利的纠结和冲突外,并无更深层次的关联。如何修正这种破损?托克维尔认为要恢复人的社会性及“公共精神”,他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部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⑩托克维尔认为,结社就是在公民和政权之间人为地仿造出一种中间权力,“只要美国的居民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识,他就立即会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会倾听他的意见。”(11)“这些社团”就是一个个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迫害的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它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无理由要求的时候,也保护了公民全体的自由,恢复了公共精神。托克维尔认为自由最重要的保证就是把从各种自治团体或贵族收回的管理权不完全交给主权者,而部分地分给由普通公民临时组成的次级团体。这样个人的平等也不会削弱。托克维尔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信仰的衰弱,人们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向现世的幸福,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在这时,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依赖政府当局的援助,托克维尔认为公民就越有被奴役的危险。“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12)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的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的学问。人类如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成比例的发展和完善。托克维尔对结社的重视思想也被帕特南继承了下来。帕特南格外强调民间横向社团的重要性,认为这些组织具有潜在的政治功能。他指出,在那些公共精神水平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如地方乐团、足球队、扶轮社,甚至是狩猎俱乐部、鸟类观察俱乐部等等,那里人民关心公共事务,相互信任,社会组织和参与方式是横向的、水平的。相反,在公共精神水平低的地区,人们极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他们眼里,公共事务就是别人的事务,他们互不信任,社会生活就是按照垂直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由此观之,托克维尔关于民情、公共精神与公民结社等思想与观点可以说是当代社会资本理论的萌芽和发展基础。
概而言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等诸位思想家的著作中均有一些部分涉及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民情、风俗习惯等概念,他们分别考察了文化习性、习惯、性格、公共精神、传统和期望等“非正式制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而这些早期的政治社会学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与当代社会资本的含义与理论相融通。
二、当代政治社会学形成以来社会资本理论的成长
当代政治社会学的形成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帕累托、莫斯卡、李普塞特、达尔、伊斯顿、迪韦尔热、阿尔蒙德、米歇尔斯、曼海姆和迪尔凯姆等。他们均从社会这个广阔的角度来描绘和分析政治现象,并提出了一些政治社会学的理论。20世纪以后,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迅速地发展起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使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张,当代政治学者都注意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盛行的时代,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如阿尔蒙德所言,“近来社会科学中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就是数据收集和数据评估领域里的革命。这场革命依赖于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的发展:即抽样调查理论和方法与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用来处理大量数据的机械装备的发展。但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依靠研究工具的有效性,它更多的是依靠对数据使用的一种新态度。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系统和比较可靠的。”(13)当代社会资本研究中注重定量测量和实证分析,即是深受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布伦和奥妮克丝、安妮鲁德·克里希娜、C·格鲁特尔特与T·范·贝斯特钠尔以及安尼·斯佩尔伯格等学者均从不同的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和研究。(14)
而20世纪社会资本概念从提出到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盛行,则是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运动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性。1968年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伊斯顿在年会上发表了《政治科学的新革命》一文,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状况进行反思与批判。他呼吁政治学家要负有政治的责任,要把研究重心从方法和事实转到“价值”中来,这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开端。正是这场革命,在重新重视对价值的研究中,发现西方社会存在严重的社会信任问题。正如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复兴和衰落》一文中所指出,当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正是美国人对公民结社运动的热衷使这个国家的民主具有空前的运转能力,而罗珀组织的调查表明,现在美国自愿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与公民社团的人数显著减少,美国人开始从精神上远离政治和政府。(15)正是在政治社会学界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和政治学中理性主义范式的复兴之中,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长起来。
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产生出了西方政治学所说的“后行为主义”,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对制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马奇和奥尔森提出,当代政治科学的主流学派——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共同特点在于:其一是背景论,倾向于把政治看做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而不太愿意将政治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区分开来。其二是化约论,倾向于把政治现象当作是个体行为聚集的结果,而不太愿意把政治的结局归因于来自组织的结构和适宜的行为规则。其三为功利主义,倾向于把行动看成是来自于自我利益的筹算,而不愿把它看做是政治行动者对责任与义务的回应。其四是功能主义,倾向于把历史看成是达到唯一的适宜均衡的有效机制,而较少关注历史发展中的适应性欠佳和多种可能性。最后是工具主义,倾向于把决策和资源分配看做是政治生活关注的中心,而较少关注到政治生活围绕着意义而展开的通过符号、仪式、典礼组织起来的一面。(16)而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以及行为主义主要的区别之一,即在于将制度的内涵延展到“文化”、“社会规范”这些非正式制度中。新制度主义在对正式制度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那些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又处于非正式地位的一些不成文规则的重要作用,将一些非正式制度也纳入自己的研究框架。行为主义时代过于强调正式制度而忽略了社会信任,那么在新制度主义盛行的时代非正式制度能否弥补这种信任危机呢?关注非正式制度空间的社会资本伴随着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成长,逐渐适应了这种需要,它是恢复公民对国家、政府与社会信任的一种尝试。而帕特南正是将新制度主义与社会资本成功地结合了起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拓展。
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相呼应的是对社群的重视。虽然政治哲学战胜了政治科学,但其内部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80年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则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而在90年代,“社会正义”和“社群”则同时成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发展所促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衰退已经到了必须加以纠正的地步。过分的自由导致了社会分裂,就如泰勒指出的,“一个分裂的社会就是其成员愈来愈难以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相认同。这种认同的缺乏反映了原子主义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人们总是纯工具性地看社会。而且这也有助于巩固原子主义,因为有效的共同行动的缺少把人们推回到他们自身。”(17)针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社群主义认为,个人权利既不能离开群体自发地实现,也不会自动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纯粹孤立的、不属于任何社群的原子式的超验自我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不具任何必然社会内容和任何社会身份的民主化的自我能够是任何东西,能够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他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也没有。”(18)反之,只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充分的实现,所以,只有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才是人类最高的价值。由此观之,社群主义者一直坚持把追逐公共利益看做是公民的一种美德,并把积极的实践当作实现公民美德的基本途径。在他们看来,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丹尼尔·贝尔说:没有人怀疑国家都有其自己的政治目的,国家有权要求公民服从其政治目的,公民则有义务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每个公民都应当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甚至不惜去冒牺牲生命的危险。(19)社群主义者认为,这种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奉献显然是最高尚的美德,应当受到最高的褒扬。社群主义所倡导的公共利益是一种非排他性的相容性利益,它意味着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而当一个人增强了他人自助的能力时,也就增强了他人帮助他的能力。
社群主义遵循自由主义的传统,在重视个人价值的基础上,主张建立共同体意识,要求个人要积极参与社群的公共生活,为其服务的同时享受着公共利益。而另一方面,社群主义则强调自我的构成性,即自我对社会现实的依赖性,强调成员资格是个人权利的前提条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欣迪·斯凯克特使用“新公民资格”、“积极的公民资格”和“公民所有者”等概念,来分析现代国家的民主治理状况。他们指出:“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界定公民的作用了。他们已经从政府服务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了创造社区特定性格的积极的活动者。这说明公民已经成为其社区管理的一部分,他们承担着社区责任,而不是把自己要么看做是孤立的地方政府服务的消费者,要么看做是政府对立或反对的力量。”(20)华尔采和米勒也强调指出,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是别的,而正是个人的成员资格和公民资格,没有积极的政治参与,这种成员资格或公民资格就不能真正实现,从而个人也就无法享受到充分的权利。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社群主义无疑对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以公益为取向的价值观有助于推动社会资本强调互助与公共精神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社群主义理念从本质上讲,就是重视公民共同体的作用,尤其是信任、参与和合作的公共精神,这需要借助一种新的概念和理论,社会资本正好满足这种需要,同时这个概念和理论有力的修正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行动逻辑,也从某些方面解决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下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
由于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推崇,一些西方学者还把社会资本理论看成是为“第三条道路”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正如吉登斯所言,“‘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21)“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会关系,通过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重构个人生活和集体社会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私有化、削减福利)虽提高了经济效率,但扭曲的“个人主义”使社会过度原子化、福利的大幅度削减将大量城市贫民和外来移民推到贫困线以下,这既加剧了社会暴力与社会对抗,破坏了社会团结,又增加了对集体和政府的敌意,降低了社会共同体和政府的合法性。针对这些问题,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合作包容型的社会关系。……“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22)为此,它主张:在肯定个人自主性和保护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倡在政府机构、社区乃至家庭等各个领域,培养基于协调和相互依赖的积极信任关系;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提倡公民价值、社群、公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意义,鼓励个人、团体和社群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培养共同体意识;通过“利权人”公司理论,发展“利权人”经济,协调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提倡双方建立共担风险与利益分享的关系;协调国内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关系,帮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中,重塑具有包容精神的共同体意识和国家意识。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中,社会资本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被用来论证理论的实践性和政策的合理性。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共和主义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逐渐受到关注,对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的挖掘促成了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而新共和主义也与社会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面兴起,加之卢梭的激进民主共和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古典共和主义自19世纪中叶起逐渐式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社群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不断吸取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资源,共和主义思想逐渐复兴,并在90年代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包含了自主性、政治自由、平等、公民权、自治、共善、参与、爱国情操、公民德行以及克服腐化等。(23)迈克尔·H·莱斯诺夫认为,古典共和主义直到20世纪才在汉娜·阿伦特身上得到了最为出色的表达。(24)确实,此后共和主义思想在欧美的复兴很大程度上与阿伦特的思想的激发有直接联系。虽然阿伦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共和主义的名称,但现在人们已经公认首先是阿伦特复兴了共和主义的政治观。共和主义在现当代的思想家除了阿伦特外,还包括波考克(J.A.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佩迪特(Philip Pettit)、森斯坦(Cass Sunstein)等人。新共和主义希望通过对公民社会的讨论,努力重塑公民德性,恢复现代社会对政治价值的关注。
当代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认为,西方社会在90年代对公民身份问题的关注既是西方政治思想自然演进的产物,也存在深刻的现实基础。就理论层面而言,公民身份概念似乎要整合制度正义与共同体成员资格两方面的需要。公民身份一方面与公民权利观念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与对特定共同体的隶属观念密切相关。就实践层面而言,则包括在美国逐渐增加的对投票选举的日益冷漠和对福利的长期依赖:东欧民族主义运动的复苏;逐渐增加的文化多元和种族多元对西欧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撒切尔领导下的英格兰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反击;依赖于公民自愿合作的环境政策的失败,如此等等。(25)共和主义对现代公民身份的关注试图表明,现代民主政治的健全与稳定不能仅仅依赖于其“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且还依赖于其公民的素质与态度。金里卡提出:他们的身份感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潜在竞争的其他民族、地区、种族或宗教的身份;他们对不同于自己的他人予以宽容和共事的能力;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他们在自己的经济需求上以及影响他们健康的环境的其他个人选择上表现自我约束和实施个人责任的愿望。如果没有具有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步履维艰甚至遭到动摇。(26)金里卡认为,帕特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关注公民美德与公民精神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公民的美德与公民精神是对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补充。社会资本与新共和主义理论均表明,自我利益原则不再具有最根本的合法性,现代民主制度所陷入的一些困境说明自我利益应该接受公共合理性的考察。而社会资本与新共和主义关于现代民主与公民德性关系的论述确实提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症结所在。
90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也与社会资本理论有密切的关联性。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和参与政治的复兴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然而只是80年代协商民主的概念才开始逐渐具备明确的形态。“协商民主”一词好像是约瑟夫·毕塞特最先提出的,他反对宪政的精英主义解释。毕塞特的挑战与要求参与性民主政治的各种观念交织一起,这些理论家怀疑早期经济学和多元主义模式的主要假设:政治应该主要根据竞争性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根据讨价还价而不是公共理性来理解;理性选择框架为理性决策提供了唯一的模式;合法政府是最低纲领主义的,致力于保护原子式个体的消极自由;民主参与可以归结为投票等等。从积极的角度看,他们倾向源自各种协商背景和主旨:直接民主、市政会议、小规模组织、工厂民主、具有不同道德背景的公民之间公共理性的中介形式、志愿协会,以及将社会作为整体来调控的协商宪政和司法实践。从广义上讲,协商民主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合法的立法必须源自公民的公共协商。作为对民主的规范描述,协商民主唤起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与公民自治的理想。(27)
协商民主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当代民主的转向: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转向“以对话为中心的民主”。它在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中得到了回应,也在共和主义的复兴对公共利益和公民品德的关注中得到了认同。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面临的诸多困难,特别是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认知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协商民主重新强调公民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强调对民意的质的提升,即通过不断地对话和协商,使各方都能了解彼此的立场,扩宽彼此的心胸,进而把私利提升为公利,以弥补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缺陷。从某种意义而言,在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中成长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似乎也可以为社会资本的发展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协商民主倾向于建立较为包容、平等、自由的讨论沟通机制,以求达致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共识,如古特曼和汤姆森所指出的,基于互惠概念,协商民主因为相互认可,所以不仅是民主的决策程序,更具有丰富的实质性内涵,可以避免暴力。(28)古特曼和汤姆森将协商民主的原则确定为三项:互惠性、公开性和问责制。在这三项原则中,又以互惠性为首要原则。“因为它型塑着公共性和问责制的意义,而且也影响着对自由和机会的解释。”(29)由此观之,协商民主可以培育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保护公民权利,激发民间组织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尤其可以促进互利互惠的规范社会资本的成长与发展。
而新共和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均是当代参与式民主的理论的衍生。“参与式民主”源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因为城邦的地域范围、人口数量有限,所以由公民大会共同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政治形式能够得以实行。古希腊雅典的参与式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这只有在小国寡民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近代以来,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西方启蒙学者基本上沿袭了古希腊的民主观念,将民主看做是人民大众的权力,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在近代社会契约论者眼里便成了共识。但是近代民族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属于代议民主类型,从霍布斯的学说、功利主义的民主观到今天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都没有超出代议制民主的框架。20世纪以来民主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不断涌现,如精英民主、程序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以及社会民主论等。
虽然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民主思潮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并没有日趋式微,而是在70年代开始逐步复兴。20世纪上半期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后期代表道格拉斯·柯尔,继承了直接民主制的某些思想,否定了代议制民主论,提出了体现参与式民主的职能民主制。共和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则将政治理解为平等公民的自由交流、对话,反对各种极权主义的政府,针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弊端,主张用一种参与式民主制度来取而代之,这种制度即联邦制的人民委员会制度。卡罗尔·佩特曼是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1970年,她的《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被视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兴起的标志。佩特曼对以精英民主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进行批判,认为真正的民主是所有公民直接充分参与的民主。巴伯1984年出版的《强势民主》一书则区分了弱势民主和强势民主,指出了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并提出实现参与式民主的创新制度。80-90年代以来威尔·金里卡等学者的新共和主义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博曼等学者的协商民主理论等都积极倡导参与式民主,从而呈现出参与式民主理论与实践成长的新景象。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公民参与,强调公民的直接参与,主张通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解决共同体的公共问题;这是参与式民主的本质特征,它区别于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的参与。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认可宏观层次的政治参与,但是更推崇诸如校园、社区、工厂等非政治社会以及经济领域的微观层面的参与。这种思想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成长影响很大。帕特南在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中发展了“公民参与网络”理论,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的网络分两种:一是横向的平等关系网络,二是垂直的等级关系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则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公民参与网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和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密不可分的。
概而言之,20世纪社会资本概念从提出到盛行,是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以及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密不可分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当代社会资本研究中注重定量测量和实证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20世纪80-90年代逐渐兴起的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第三条道路”、协商民主、善治以及参与式民主理论等思想潮流,则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拓展提供了空间,导致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等非制度因素的社会资本理论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同时,社会资本强调草根民主与集体行为的重要性,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个人自由主义国家恢复中间组织,进而实现其全球政治价值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也为西方国家加强社会资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选择现代化的同时,必须重视制度建设,但更要加强传统的非制度因素研究,实现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的契合,这应该就是社会资本对当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三、政治社会学走向善治的理由:社会资本在政治社会学领域成长之意义探析
从古希腊开始,政治社会学的萌芽思想就以倡导政治生活的价值与理想为自己的宗旨,对理想政治状态的追求,既是对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批判,对现实政治社会制度的鞭策,更是对美好政治社会生活的一种设计。即使是在“价值中立”原则盛行的行为主义时期,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明确的价值观取向,正如奇尔科特所言,“行为主义者依靠自身的方法论与定量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种社会的推力是专家治国和失去了个性的。与此相对照,对国际事务的解释却奉行一套冷战的两分法:一边是民主和仁慈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边是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国家。”(30)这说明,行为主义在号称价值中立的同时,它实际所持的立场仍然是美国制度所倡导的一套价值观体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政治社会学研究必须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正如伊斯顿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31)帮助人们做出价值判断,在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规则中进行取舍,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目的,而理想的选择和取舍,正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愿望,使得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需要有根据的想象,需要受知识引导、超越已经获得的真理的思辨,需要乌托邦的设计和冥思,需要愿意面对太容易设想的解决办法而为不可设想的选择作艰苦的思考”,(32)离开了政治理想或者政治价值,政治社会学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从政治行动的目的与政治事物的本质来看,政治研究者不下价值判断,就无从研究政治现象”。(33)政治社会学研究必须介入政治,脱离社会实际,妄谈政治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必然会使政治社会学研究只剩下一些技术和工具理性。
而就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引入与拓展而言,其意义首先在于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政治社会学领域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融合。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拓展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密切相关,帕特南等学者对传统政治科学中的“价值中立”理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公民美德、公共精神、合作、参与和社会责任感等,而这些价值观也正是社会资本理论所推崇的。另一方面,帕特南继承了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优秀遗产,在20年来对意大利地方政治调查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资料,并进行了娴熟的分析处理。为了搜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数据资料以便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帕特南等人对6个精心挑选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分别研究,然后又扩展到20个地方政府。其中,在1968年至1988年进行了6次特别委托的全国调查和其它几十次选民调查。帕特南将20个地区的数据资料通过多种角度进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等,百分比、分布率以及各种精心整理的图表将分析结果清晰地展现给读者。但是,帕特南并没有局限于上述数据分析,他能够从经验研究上升到一般理论,进行富有哲理的定性分析。从他提出的基本问题,即“造成各地区制度绩效上出现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到他最后的基本结论,即“积累社会资本是使民主运转的关键”,始终都贯穿着当代政治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帕特南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形成新颖独特的、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政治理论,成为他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而在帕特南之外,AJ·道格拉斯·威廉斯、安尼·斯佩尔伯格等学者也采用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社会学领域拓展中更为深远而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其对民主政治的强大的解释作用,对于政治社会学的成长和发展而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也为其找到了一条“走向善治”的理由。当代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学者们就其标准、原则、程序、效果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由洛克奠基,尔后经孟德斯鸠、卢梭以及密尔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丰富和完善古典民主理论,在20世纪初期受到了精英民主论者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等学者的挑战,20世纪中叶又受到了熊彼特、米尔斯等学者的严厉批判和大量修正,从而形成了当代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马基雅维利主义学派的精英民主论者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把社会划分为少数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被统治者,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应由少数精英人物控制。这些学者强调精英主宰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为少数精英的寡头统治辩护,认为社会分为全能的掌权的精英和从属于他们支配的群众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而熊彼特则认为,并不存在古典民主理论所说的人民的共同幸福和要求实现这种幸福的共同意志,这主要是因为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幸福的意义千差万别。即使共同的幸福确实存在,且被全体所接受,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共同的幸福能够得到,因为这里仍然会出现许多争论和分歧。传统的民主观念认为,“民主”(democracy)由“人民”(demos)和“统治”(cracy)两个词合成,它的规范意义就是人民统治。“人民统治”在制度意义上指主权不可分割,它只能由人民本身或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机构代表。而熊彼特认为,“按照我们的观点,民主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上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34)熊彼特直言不讳地说:“人民从来没有统治过,但是他们总是可以被定义弄得他们像是在统治。”(35)在批判了古典民主理论之后,熊彼特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民主理论。古典民主理论认为“主权在民”的实现乃民主之本质所在,代表的选择则是辅助性的。现在既然否定了传统民主的定义,否定了“人民的统治”,熊彼特就很自然地把人民选择代表视为民主最本质的特征,人民的作用就是产生政府。因此,熊彼特指出,“我们决心强调一种程序方法”,民主就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36)这种新的民主理论强调了一种可以验证的程序方法,深深地留下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烙印。
施米特和卡尔也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公民的行为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的竞争与合作来完成。”“民主政治最一般的界定是把它等同于公正、可靠、定期举行的选举”。“它另一被普遍接受的形象是,把它等同于多数派统治(majority rule)。无论是在全体选民、议会、委员会、城市委员会,还是正常的秘密会议里出现的多数派,只要它联合了超过半数以上的合法选票,那么任何这样的支配实体的决策就可以说成是‘民主’的。”(37)沿着这条民主理论的修正路线,罗伯特·达尔提出了更为精致的程序民主理论,对比较政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他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进行比较研究时,也毫不犹豫地沿用了这种程序民主概念。他说:“遵循熊彼特的传统,这项研究在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38)选举式民主的缺陷就在于:首先,公民被认为拥有一系列偏好,这些偏好的确定先于和独立于政治过程;而投票的作用就只是在于提供一种公平的决策程序或合计机制,以把这些事先存在的偏好转换成公共决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合计的”或“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观不能履行民主合法性的规范要求。其次,投票民主无法把基于自利、偏见、无知或情绪冲动的要求与那些基于正义原则或基本需求的要求区分开来。事实上,这种政治过程根本就没有包含公共维度。投票民主提供了确定输赢的机制,但却没有提供旨在发展共识、塑造公共舆论甚或形成值得尊重的妥协的机制。(39)很明显,在这里,选举被当作民主的本质。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无足轻重;公民的才能和美德也被置之不理。
然而,经历了最近几十年的民主化之后,人们发现了选举民主与真正的自由民主之间的分歧。就连程序民主论者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种现象,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假设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用民主的方式迫害基督教徒、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屠杀犹太人。那么,即使这些行为是由民主程序所决定的,我们也不一定赞同这么做。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并不能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经济、保障公民权利和扩大社会福利,从而形成所谓的“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阱”。(40)事实也证明,在有些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常常以专断的方式行事,无视立法机关,通过宪法修正强行延长自己的任期,漠视个人权利,歧视少数民族,遏制新闻自由,甚至鼓励警察滥施暴力。
这些问题的出现就向人们昭示:民主并不等同于定期选举和多党竞争,民主的改革必须从基层开始,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和参与。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而言,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而这一观点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来说才是最根本和至关重要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及其运行必须得到长期的历史孕育和丰富的社会资本的支持。民主制度并不能简单移植,即便移植了,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资本的支持,也很难有效运作。关于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历史背景、社会基础和文化内涵等问题,正是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中心论题。
帕特南从自己对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了“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而乌斯拉纳教授也从理论分析上得出了“民主和社会资本似乎是共生关系”的结论。他们二人的共同结论都佐证并支持了“社会资本”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论断。人们普遍相信,政治价值观的三驾马车——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民主之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每一个都很重要,但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平等、博爱恰与信任、互惠合作等社会资本的价值规范在内涵上相一致,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它们是“在功能上的等价物。”(41)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指出,正是由结社传统、信任和合作组成的社会资本促进了善治和民主机制的有效运转。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作,必须得到丰富的社会资本的强大支持。概而言之,民主政治必须在作为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之逐步发育完善中成长,离开了公民间信任、互惠与合作性态度和价值观的生成,民主政治的构建就失去了文化根基。这一结论与修正民主理论大相径庭,但与古典的民主理论却有某些不谋而合之处。在古希腊、雅典的城邦,崇尚一种公民积极参与和自我管理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治人者也会受治于人。全体公民聚集一处,讨论、决定和制定法律。因而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体制,它力图使不同背景和属性的人们,能够“通过政治的互动作用来表达和交流他们对善的理解”。(42)但是帕特南对民主政治运作的社会资本的强调并非是向古典民主的简单复归,而是运用严格规范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所得出结论,因而这一结论不是假设,而是民主政治逐步走向善治真实的图景。
对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的估价离不开特定国度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议题。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分析社会资本与政治体系的关系,从理论上阐明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对于本土化的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也不无积极意义。因而社会资本这种理论框架,也是对我国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必要补充,是开展中国政治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基础。假如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政治社会生活,中国的某些政治和社会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比如社会资本分析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所谓“超稳定结构”的性质和形成,有助于解释中国高度集权模式的形成,有助于将中国政治的“关系”研究纳入政治社会学主流研究领域,有助于解释和评价近年来中国社会普遍推行的村民自治和自治组织的发展,也有助于形成解释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更为完整的模式。鉴于国内政治社会学界目前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国内政治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仍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尤其是从实证研究和深层理论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问题,并以此来解释政治社会学中的各种理论、现象与问题,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民主治理与善治的实现将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张友渔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02页。
②[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1页。
③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6、132页。
⑤Mae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Trans.by Allan Gilbert,vol 2,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p.192.
⑥Robert D.Putnam: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onsequences,Volume 2 No.l,Spring 2001.
⑦[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页。
⑧⑨(12)[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58、332页\第217页。
⑩(11)[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37、639页。
(1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7-48页。
(14)see,Pual Bullen,Jenny Onyx,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in NSW:An Analysis,CACOM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1),1990; Anirudh Krishna (Duke University),Active Social Capital: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Christiaan Grootaert & Thierry van Bastelaer,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Assessment,College Park,2002; Anne Spellerberg,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in New Zealand,published by Statistics New Zealand Te Tari Tatau Wellington,New Zealand.2001.
(15)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a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
(16)James G.March,John P.Olso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8,1984,pp.734-749.
(17)Charles Taylor,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17.
(18)[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19)[美]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36页。
(20)Ostrom,E.,A Communitarian Approach to Local Governance.National Civil Review (Summer).1993,pp.226-233.
(21)(22)[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107页。
(23)萧高彦:《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转自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知识分析子论丛》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24)[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4页。
(25)(26)[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11、512页。
(27)[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协商民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导言。
(28)Amy Gutman and Thompson Dennes:Deliberative Democracy beyond Proces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10.2.2002,pp153-174.
(29)[美]阿米·古特曼,[美]丹尼斯·汤普森:《民主与分歧》,杨立峰、葛水林、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30)[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铦、潘世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31)[美]戴维·伊斯顿著:《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0页。
(32)[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33)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Glencoe:The Free Press,1959,pp.18-20.
(34)(35)(36)[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5、308、337页。
(37)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页。
(38)[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6页。
(39)[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22-523页。
(40)[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转自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24-425页。
(41)Kenneth Newton & Paul Whiteley (eds.),Social.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9.p.61.
(42)[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标签:政治社会学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社群主义论文; 行为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学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