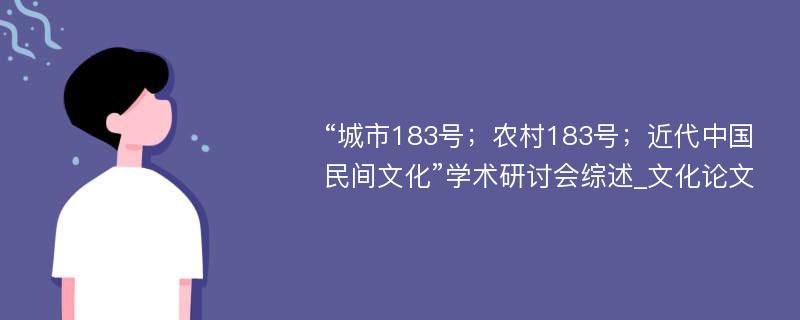
“近代中国的城市#183;乡村#183;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民间文化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9—11日在青岛举行。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岛大学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山西大学、苏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单位协办,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港澳台与内地的100余名学者参会,提交论文90余篇。
这是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中国内地举办的首次比较全面涵盖近代社会史领域的学术研讨会。社会史复兴20年来,在中国社会史学会举办的10届学术年会上,近代社会史的比重不断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进来。近年来以区域社会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中有不少侧重于近代社会史,如山西大学和中山大学分别举办的一系列研讨会。目前将国内外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力量聚集起来,集中进行学术研讨,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次研讨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举办的。研讨会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比较宽泛,意在容纳较多领域的学者参与,比较全面地检阅目前国内外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实绩。会议论文佳作甚多,因篇幅限制,会后已经发表的部分论文,这里不再评述。
一、近代乡村社会史研究
在过去数十年里,华北、江南和华南三大区域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积累
已经相当丰厚,近年来的近代乡村社会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而至今一些社会史论文还具有比较浓的“社会经济史”味道,这次研讨会上的部分论文依然延续了这一特征。从时段来看,这次会上的乡村社会史论文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时期;从地域上看,华北与华南研究在数量上平分秋色,江南研究较少。在新资料的发掘和新视角的开拓上,以下几篇论文值得注意。
我国东南地区素以宗族组织发达著称,历朝历代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都离不开利用宗族组织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清代在推行保甲制的同时,又在聚族而居的地区设立族正制,负责举报族内的不法分子,治理宗族械斗。乾隆时期闽台的族正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近代的族正制还没有人研究。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近代闽台族正制考述》一文中,利用大量官方文献、档案与民间契约资料,勾勒出近代闽台地区族正制的一般情形。作者认为,19世纪闽台地区宗族械斗问题严重,社会秩序不够稳定,清政府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族正制,对于当地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一定作用。从清前期到近代,族正制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成熟的做法,既监控宗族又防止族正借官府权威而控制宗族,并使宗族进一步组织化。由于清朝的宗族政策比较得当,基本上将宗族纳入了政府的社会控制范围。19世纪宗族的发展虽然带来一定的社会危机,但未能逸出、更不能威胁政府的统治。
陈支平(厦门大学历史系)在阅读一批清末闽南地区地方公牍和民间文书的基础上,写成《清末闽南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一文。他试图透过抗粮事件来透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认为把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抵制反抗行为局限在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关系上,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清代赋役制度的维持与破败,更多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相互消长的各方面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而不是以简单机械的所谓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的关系所能涵盖说明的。
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绅权借举办团练而有所伸张,以及清末士绅投身近代实业和教育事业等课题,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一文中着力讨论了在清末至北洋时期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士绅如何经由参与地方自治组织的途径实现了绅权的组织化,他们攫取了地方公共权力,从而改变了以往处于分散状态,仅以私人身份倡办公共事务的局面。作者指出,绅权的膨胀,虽然有抵制国家、官吏压榨地方社会的一面,而削弱具有法制意义的“官治”行政,侵害、吞噬普通民众权益的一面更令人瞩目。清末民初绅权膨胀的实际结果是土豪劣绅社会政治权力的恶性膨胀,与清末维新派倡导的“兴绅权”的初衷严重背离。其原因在于,作为在国家体制之外充当制衡因素的“绅权”本身具有局限性——它极富宗法性,允许它普遍而合法地组织地方公共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劣绅活跃,“绅权”恶性膨胀。此文与罗志田提交的《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一文入手处有所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试图在对学界讨论甚多的“民国年间乡村社会何以多土豪劣绅”的现象做出解释。魏文将基层政治制度史的因素引入到士绅社会史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
与魏文相类似,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公务人员——见之于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一文,也是一篇政治—社会史论文。作者考察在清末以来实施地方自治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公务人员的类别、出身背景、产生途径、主要职责、经济收入、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理解乡村政治变革广度和深度的意义。她利用1933年7—9月初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主持的河南、陕西、浙江、江苏四省农村调查中的有关资料,试图通过这四省部分地区的调查来察知当时全国乡村政治状况的一般情形。她所描述的乡村政治景象是:乡村政治的实际与国家规制的差异引人注目,这种差异存在着明显的由东部政治中心区到外缘和边远地区的梯度递增现象;地方自治恶性变质;国民党基层组织薄弱。这种政治状况当然会影响到乡村的社会面貌。事实上,在这篇论文里也不乏乡村社会状况的连带描述,这对于我们理解民国乡村衰败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另外,此文运用现代社会调查资料对乡村公务人员类别、出身背景、产生途径、主要职责、经济收入、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等方面进行归纳概括,从方法论上来说,是运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基层政治史,令人耳目一新。
土地改革无疑是20世纪影响乡村政治社会面貌的重要因素。19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意识领域的解冻,学界对土改的研究尤其是对左倾错误的认识远较以往实事求是。但李金铮(河北大学历史系)认为迄今在理论方法上仍然存在着简单化倾向,最为典型的就是“政策—效果”模式,即共产党的政策演变、农民获得利益以及革命斗争积极性提高的三部曲。土改的主体——农民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参与进来,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伦理规范是什么,共产党是以什么办法突破了传统社会伦理规范的限制,从而使这场运动按照自己设定的道路发展下去,这些既有延续又有变异的传统伦理规范怎样影响着土改进程和乡村社会面貌?这些问题在社会学界已经受到重视,产生了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如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一文,收入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但还有待于更加系统的研究。李金铮的《土地改革与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一文除利用了传统的史料以外,还运用了部分社会调查资料(包括他本人近年来在华北农村所做的调查)以及当时与现在的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的观察与分析。他指出,农民在土改之初认同既存体制,对地主、高利贷者具有依赖甚至“感恩戴德”的心理,共产党实施新政策、新措施时,他们往往胆小怯懦,顾虑重重,不敢响应和执行。鉴于农民的这一心态对土改构成巨大障碍,共产党从改造乡村社会的传统伦理体系入手,通过“访贫问苦”、“倒苦水”、“斗争大会”等办法,挖掘农民生活困苦的根源,使其产生被地主阶级剥削的感觉和阶级意识,认识到对地主、高利贷者的斗争非常必要,从而缓解了农民在土改之初的心理矛盾,对土改政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土改政策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遇到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其被剥削感、阶级意识、阶级复仇、侵夺中农利益以及不敢生产、惧怕冒尖的心态,都是前所未有或甚为少见的。但又要注意,其中的复仇心态和绝对平均主义是以土改为媒介的农民传统心态的延续和放大,表明民间传统会以变异的形式展现出来。本文将农民在土改中的心态变化生动地描画出来,且给予历史的纵深感,克服了以往土改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农民“缺席”现象,为更加深刻地认识20世纪乡村社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李云峰和袁文伟(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在《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与乡村社会危机》一文中,对以往研究甚少涉及的西北土匪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作者运用了以前学界较少注意到的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的《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和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等一手文献,这是这篇论文在资料发掘上最有价值的部分。作者在“概述”的基础上,还试图探讨土匪与乡村社会危机之间的关联。他们指出,土匪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主要影响有:加速了西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逆向变动,导致了民国基层权势更迭的短暂性和残暴性;阻碍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乡村社会的贫困化程度;冲击了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恶化了社会风气。
二、近代城市社会史研究
与近代乡村社会史相比,近代城市社会史起步较晚,资料积累与水准较高的研究成果都还不多。但正如新时期在文学领域出现从乡村题材向城市题材“转向”一样,城市社会史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从这次研讨会来看,资料的发掘、视角的拓展与若干较成熟研究领域的综合提高并行,呈现出一种放射状的缤纷色彩。从地域上来看,北京、上海及周边的江南地区、成都等仍然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
长期以来,对近代报刊中的城市社会生活史资料注意的人较多,而对于个人文集、日记、信函等文献中更为分散的史料则缺乏系统的发掘、整理。透过个人经历、眼光能够过滤到多少有价值的社会生活事实?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最近出版的《恽毓鼎澄斋日记》里面读出了清末10年北京居民生活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他在《从恽毓鼎日记看晚清北京城》一文指出,恽毓鼎日记的“记载虽不够系统、不够完整,没有统计数字,但极为生动、形象,读来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北京的立体图”。他所摘录的“沙尘暴肆虐”、“对外交通”、“市政建设”、“市内交通”、“休闲与社会生活”、“报刊及新媒体”、“慈善事业”等7 方面的事实虽然不系统、不全面,但确是当时生活在北京城一个普通居民最真切的感受。这样的史料挖掘得多了,相互参照着看,我们才有可能拼接出一幅更加完整的社会生活画卷,也可以由此解释一些范围较宽的社会变动现象。
同样是对北京城的研究,李少兵(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则把眼光拉到民国初年至抗战开始前发生在北京城墙上的一段故事。在《1912——1937年官方市政规划与北京城墙的变迁》一文中,他运用现存的民国档案、文书资料追溯1949年后北京城墙遭到大规模拆毁之前的一段历史,重现了民国前20余年间官方市政观念施之于城墙后所产生的后果。作者指出,“1912—1937年间,北京城墙的变迁确实与官方市政规划有密切的联系。市政当局的城墙政策,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缺乏宏观计划、拆改城墙为主到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并行的过程。京都市政公所时期,市政建设指导思想不明晰不科学,缺乏长远、整体的规划,有临时抱佛脚的特点。这就导致城墙保护与临时市政建设出现矛盾时,市政公所往往迁就后者。1928年后,北平特别市政府吸取前届政府的教训,有了比较科学、全面的城市规划。由于卸去了首都这一繁重的中央级政治城市的重担,它把目标放在了发挥地方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上。人们有了比较清晰的文物保护意识和规划,北平的城墙保护因之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内、外城墙的暂时保存,使北京至少在1937年时还是一座保留了中国传统城市设计规制,具有都市系统布局结构的建筑艺术品。”此文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市政建设与历史遗迹保护之间的关系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朴赫淳(韩国木浦大学校史学科)在《近代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演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用于概括近代国家权力侵入之前的“自律性体制”下的北京下层社会面貌的概念——“北京胡同社会”(北京老城区由于胡同的纵横交错,使之形成了如迷宫般的独特城市空间,以胡同这个社会空间特征可以来指代社会群体)。此文旨在探寻这个地区的居民生活从近代以前到近代是如何演变的,以及所谓老北京人的北京地方社会独特的自我意识与这种变化有何种关系。作者认为,从义和团运动以来,一直没有停止的行政体制近代化破坏了“北京胡同社会”的“非正式统治”,使之变为“正式性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老北京人”的自我意识自然而然地应时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1930年代老舍等一群京味小说家对北京十足京味的刻画是对这一扭曲现实的折射。
近几年来运用报纸广告资料,尤其是《申报》广告资料来研究近代社会史蔚然成风。这次研讨会就有多篇论文是这一风气的产物。高岛航(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在《1920年代的征婚广告》一文中,以1920年代《申报》的征婚广告为主要资料,详细地分析了161则征婚广告中男女双方自我介绍中的各个变量(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籍贯/居住地)和配偶条件(学历、年龄、品性/性情、职业/财产、容貌)。在分析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回答当时知识界关注的问题:征婚与自由恋爱、社交公开这些新潮的思想主张有什么关系?他的结论是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征婚广告未必能够反映新的婚姻观。征婚可以没有恋爱,或许没有恋爱的征婚占多数。总之,不同立场的人怀有不同的目的来征婚。征婚既可以体现新婚姻观的理想,又可以促进旧式婚姻的完成。”日本学者对资料的精细处理在此文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结论既出人意料,细细揣摩,又似在情理之中。池子华和朱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在《三雅园的经营策略与昆剧的命运——以〈申报〉广告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广泛搜集晚清上海著名的昆剧戏园三雅园在《申报》上刊登的戏曲广告,从经营策略的角度来分析广告与这家戏园的兴衰之间颇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戏曲的命运打开了一条前人很少注意的通道。
在20世纪初现代警察制度建立之前,中国的城市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是什么关系?以前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城市被国家权力紧密控制,市民“自由”很少,成熟的城市共同体意识也未能发展起来。王笛(美国得克萨斯A&M 大学历史系)在《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与节日庆典——清末民初成都的街道、邻里和社区自治》一文从这个问题切入,以生活史的手法详细地描绘了清末民初成都街头的商业空间、日常空间和庆典空间,分析了体现在社区自治里面的共同体意识。他认为,20世纪初缺乏市政管理,中国城市日常生活受国家权力影响很小,拥有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市民的自主权相当大,也拥有成熟的城市共同体意识。他以成都的个案研究印证了罗威廉在关于汉口的杰出研究里对马克斯·韦伯的批评。
闵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苏杭甬拒款运动中的民众集会》一文中,研究了发生于1907年秋至1908年冬江浙一带的大规模民众集会——苏杭甬拒款运动。他以翔实的资料分析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发生地区,并将运动的过程做了仔细的梳理。作者的视角不是以往学界熟知的政治史眼光,而是以社会史的眼光来分析一场社会运动。他认为,苏杭甬拒款运动主要不是一场排拒外国人掠夺路权而是激烈反抗清政府的运动,它的主要组织者绅商阶层和学校师生在保卫江浙民营铁路的过程中要求人民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不许政府独断专行。作为一场由经济事件引发的城市民众反抗政府专权的示威运动,苏杭甬拒款运动是清末民权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前导,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场运动说明,在清末的上海及其周边的苏南和浙北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与清政府对立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具有独立的意志、强大的经济实力、足以号召的社会威望以及各种通畅的联络渠道,由此得以在清末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主角。此文对于研究清末城市的民众集会,以及清末绅商与学生等新兴社会阶层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近年倡导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史”。他的论文《文化交往网络中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看作是这一研究思路的“论纲”。他认为,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现代城市知识分子具有归属感的空间关系主要有三层: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虽然不起主导功能,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发挥着其潜在的影响,宗亲关系、同乡关系,深刻地镶嵌在现代都市的人际交往中,与现代的文凭身份等级、意识形态认同和都市地域文化交织成一个非常复杂、相互缠绕的交往关系网络。在这个迷宫一般的彼此重叠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认同、交往空间和身份归属不是单一的,而是呈复数状态,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价值和身份取向,有多种团体认同和身份归属,这形成了知识分子个体身份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把知识分子置于城市社会空间网络中,由此来把握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市场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许纪霖试图对以往注重单个或群体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心灵史研究有所超越。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不满足于前人仅仅对晚清上海城市文化的次级领域进行分别研究。在《晚清上海的新知识空间》一文中,她认为,在晚清上海存在着一个与西学、西方文化相关而产生的新的知识生态空间,它由以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以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以社会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以及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这种‘知识空间’的概念虽然不像‘西学’或新文化事业那样边界清晰、可触可辨,而是隐于人们社会生活之中的‘潜形态’,但它却是连接各种相关元素的粘合剂,是揭示有关知识的各个层面与社会文化元素互动关系的立体结构,反映了由知识诸元素构成的文化生态,因而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晚清上海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形态,应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晚清上海“新知识空间”概念的提出,表明作者试图综合近年来上海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诸多成果,将文化史与社会史打通,实现她“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学术追求。
三、近代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研究
按照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民间文化与思想史研究》一文中的看法,“大众文化不同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都市中的流行文化,它通过模式化制作,广告式的宣传,倾销式的发行,推向广大民众。它有消费性,满足民众的休闲、娱乐的需求;它有时尚性,此唱彼随,变动不居;它有商业性,以获利为目的,以市场导向而制作的文化产业。”“民间文化是非模式化的,它起自民众自发的创作,缘情而发,因地制宜,有乡土性,民族性,千里不同俗,各有千秋,这些都不是集约化的制作,因而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从会议论文来看,属于“民间文化”者有之,属于“大众文化”者亦有之。所以,在这部分概述里,笔者将主题归结为近代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研究。会议论文的题目主要集中在庙会、民间信仰、都市大众娱乐方式等方面,以下论文较值得注意。
谢国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田野考察、拍摄录像的方式记录下了从清代流传至今的台湾庙会中的“宋江阵”习俗。在《宋江阵与台湾的庙会文化》一文中,作者认为,“宋江阵在泉州地区的戏剧表演成分较浓厚,跟宗教的关系似乎不那么密切。传到台湾之后,由于移垦社会的特性,使宋江阵一方面依附于庙宇与民间信仰发展,增加其宗教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移垦社区的治安问题与草莽特质,也使宋江阵的操练不只是为了强身,确也有社区防卫的作用。因此清代及日治时期,台湾乡间组织宋江阵或狮阵的风气极盛,而且显然朝激烈的武打技艺发展,因此化妆式宋江阵流传甚少,多以劲装为主,拳术、兵器、阵法排练均极讲究。”此文意义在于揭示台湾今日政治生态的历史因缘。
吉泽诚一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在《近代天津的庙会与民间文化》一文中认为,虽然19世纪后半期天津的“皇会”(天后宫庙会)最负盛名,但是民国以后却屡遭停办。他讨论了停办“皇会”的原因——除了军阀内战造成的社会不安以外,也受到新知识分子主张破除迷信的影响。1936年在振兴工商业的新时代政治护符下,“皇会”又开了一次。“对于天津人来讲,皇会就是值得自豪的传统活动,跟崇拜妈祖的心情分不开。可是,总的来说,民众对皇会的态度可能有所变迁,商业化、观光化的因素越来越大了。”
刘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信仰·仪式·禁忌——近代娼妓文化漫谈(上篇)》一文中,借鉴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的视角, 认为以往的娼妓史都是站在娼妓与社会或娼妓与他人的关系上来论述,惟独没有把娼妓视为一个人,视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站在娼妓的立场上看问题。此文主要研究娼妓文化中的信仰史与民俗史,重现娼妓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角落。
姜生和于志(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依据该所师生调查小组在山东省沂源县栖真观、神清宫、织女洞、牛郎庙、迎仙观、唐山、荆山等7处佛道教遗址的调查资料,写成《近代沂源的宗教生活——山东沂河流域佛道遗迹考古调查与研究》一文。作者在考察中发现,近代沂源的道教规模要远盛于佛教,而且曾有过一时的辉煌,道教是近代沂源民众宗教生活的主题。
对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学界研究成果很多。郝平(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传说、信仰与洪洞乡村社会——兼及大槐树移民的文化认同》一文中探讨了何以惟独洪洞大槐树会产生一种“根祖”认同。作者认为,要解答这个疑问,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洪洞本身具备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二是有什么样的深厚地方文化促成其独特性的形成。就洪洞而言,就是下面两点:一是明代洪洞是北中国最大的移民集散地这一客观因素;二是汉民族发祥地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之大槐树移民的空前规模和影响,促成千百万移民把洪洞作为他们魂牵梦绕的“想象家园”。把洪洞而不是其他地方作为“想象家园”,最根本的因素,恐怕就在于洪同本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作者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在洪洞民众精神世界中占据“神圣”地位的“唐尧虞舜及娥皇女英”、“女娲”、“玄帝”信仰及迎神赛社活动为主线,透视这三种类型的民间信仰是如何影响民众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如何塑造洪洞乡村独特的地域文化的。这些远古传说和信仰的存在和延续,赋予了该地域“正统”与“根”的文化象征,恰恰暗合了洪洞作为汉民族发祥地的“根祖”意义,可能与移民后裔的“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说法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最近赵世瑜在《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里探讨了明清至民初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何塑造了大槐树移民这一神圣象征,但并未解释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而不是别的地方承载了这样的“根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郝文恰好可以填补赵文的论证缺环。
顾德曼(Byran Goodman,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系)在《不道德的交易:民国初年妇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腐败》一文中,使用民初出版的有关交易所的小说、档案、证券交易所相关法令与手册、报纸报道、读者投诗,以及知识分子对1922年发生在上海交易所的一桩真实的女性投资人自杀案件的讨论等资料,将虚构的与真实的事件并置处理,试图揭示蕴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女性之间的复杂的道德意蕴。此文对于揭示中国现代都市经济生活里面所蕴涵的文化象征意义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1927年夏,天津社会名流借助官府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禁舞风波,引发了一场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争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大公报》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对跳舞与禁舞、跳舞与社会风化、跳舞的性质、跳舞与男女社交公开诸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依据《大公报》上的材料对这场禁舞风波做了详细的叙述与分析。作者在《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评析》一文中认为,天津禁舞风波是西舞传入后第一次民众观念的集中反映。它所展现出来的观念是复杂的。跳舞是都市繁荣和发展的象征,也是都市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跳舞是现代文明的新式娱乐,是社会新思潮的体现,但也是有产子弟的消费场,对于社会风气未尝无害。跳舞与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女子剪发一起,被视为新思潮和都市新式生活的体现,是社会趋新的反映,但在革命、外患、灾荒、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跳舞也同样与社会风化、破坏旧礼教相联系,从而被视为青年社会堕落的象征。因此,1927年的天津禁舞风波,不仅表明了名流禁舞的力量是何等的软弱无力,其禁舞的理由又是何等的苍白乏力,而且也同样反映出跳舞与禁舞问题体现出的民众思想是何等的复杂,而其后上海、北平禁舞之声的不绝于耳,说明跳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在中国的流行,又是何等的曲折和坎坷。
认同与社会记忆是近年来社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来解构一种我们长期以来视作“客观真实”的文化现象的“不真实性”,重建这种“不真实”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的过程,帮助我们解开了不少重大的历史疑团。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论文就是一例。他在《地域认同与族群分类——1640—1940年韩江流域“客家观念”的演变》一文中,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检视近代学术史上流传甚广的说法——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支派,既是外来人的他称,也是自称——是如何在客家人聚居核心区韩江流域通过漫长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的。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客家“族群”意识的自觉,与西方近代“种族”观念的传入和近代城市生活引发的族群隔阂直接相关,20世纪初年的《岭东日报》以及关于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对于“客家”意识的塑造与传播起到很大作用。
结语
从这次研讨会来看,经过20年来学术界的努力,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新史料的发掘上,学者们普遍重视报刊、方志、档案、文集、日记等传统文献,除此之外,民国社会调查资料、当代学者的田野考察资料、报刊中的广告资料、图像资料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对于民国社会调查资料的生产史,这次研讨会上有两篇论文进行研究[欧阳恩良(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抗战时期的贵州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研究》,赵丽和朱浒(北京市北海公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在理论方法上,重视社会学、人类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并加以改造,使其适合历史学的特点,已经在许多学者中达成共识。从会议论文看,借鉴民国与当代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的著述并与其展开对话,已不鲜见。突破政治史设定的时代划分界限,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面探讨某一社会事实或文化事象的演变趋势,在许多论文里面有所体现,甚至有人提出打通明清史与近代史的主张。近代史的下限已经被一些学者延伸到了1949年以后,他们认为现在不抓紧时间抢救一批口述文献和民间文书,将来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山西大学行龙教授主持的集体化时期研究和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主持的建国后30年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理研究这两个研究项目就是突出的例子。这表明社会史学界突破传统史学条条框框的限制,正在大胆地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而这些努力,最终将会融入新的史学主流。
近代社会史的魅力还表现在它对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的辐射力。如专长于学术文化史的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嘉道年间京师士人修禊雅集活动与经世意识的觉醒》一文中,在学术史本身的讨论之外,增加了士人社交活动与思想潮流关系的环节。再如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研究著名的学者许纪霖把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定位在“知识分子的社会史研究”。他在会上提出“有社会的思想史”和“有思想的社会史”,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在巨大的成绩背后,我们也要认识到,近代社会史研究在史学研究的园地里还只是一株幼苗。系统性资料丛书的缺乏,使得社会史学者长期以来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有不少人呼吁在这方面加强资金、人力投入。在理论方法的训练上,史学学者往往有所欠缺,亟待更加良好的“科际整合”。目前的社会史论文,论题还比较细碎,往往是“各自为战”,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讲述一个小小的故事。所发掘的事实具有多大范围的解释力,不同论文之间往往差异很大。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邱捷教授在《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一文的结尾处说,他常用“瞎子摸象”的故事比喻自己对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与邱教授抱有同样感受的学者可能为数不会太少,读到此处,不禁要叹一声:于我心有戚戚焉。
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申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