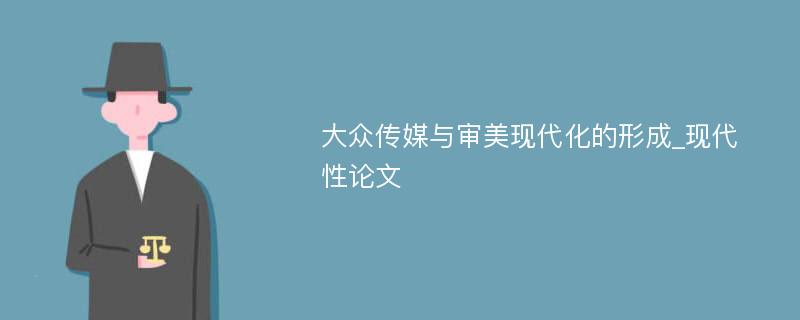
大众媒介与审美现代性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大众论文,媒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4)02-0121-05
审美现代性,在这里是审美—艺术现代性的简称,即它既代表审美体验上的现代性,也代表艺术表现上的现代性。在文化现代性的诸方面中,审美现代性是看来非实用或非功利的方面,但这种非实用性属于“不用之用”,恰恰指向了文化现代性的核心——现代中国人对世界与自身的感性体验及其艺术表现。谈论中国审美现代性,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这种审美现代性是怎样生成的?人们常常从西方的主动冲击与中国的被迫回应去说明,或是尽力伸张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严复、胡适、陈独秀等的文化启蒙活动。这些诚然都有其合理处,不过,大众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继续忽略的了。
一、大众媒介及其革命性力量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译媒体),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按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见解,“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1](P144)在现代传播学里,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而大众媒介作为媒介的现代形态,则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六类以及目前新兴的国际互联网等。
应当看到,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是与媒介的现代性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审美现代性依赖于传播方式的现代性即大众媒介的发达,因为正是大众媒介的发达为审美现代性提供得以展开的现实传播网络和社会动员场域;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发达本身并非外在于审美现代性,而是构成它的一个基本层面。小说中的审美信息需要由特定媒介传递给受众。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媒介便没有文学审美;同理,没有现代媒介便没有现代文学审美或审美的现代性。而审美现代性及更根本的文化现代性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的现代性变革。审美现代性是在相应的传播媒介中萌发和生长的。具体地说,正是现代大众媒介取代古典媒介这一必然进程,使审美现代性成为可能。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晚清时期,是什么使中国人感受到新的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现代性审美体验?新生的大众媒介正在其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大众媒介(mass media)与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紧密相关。大众传播主要指职业传播者使用现代大众媒介(包括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在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传播对象中广泛、迅速和连续地传播信息,以便施加影响的过程。相应地,大众媒介是指大众传播得以进行的专业机构和技术。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传播历史,并且是世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史却是短暂的。即便是在明清时代,中国也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专靠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群。作家们的创作往往是属于“业余”性质的,而且主要靠手抄本在友人中流传,有时自己出钱刻印也只在小范围内散发。这表明,单就文学的传播方式来说,古代中国还主要处在以手抄为主的文字媒介时代。手抄本固然有其审美价值,如书法的美,但手抄容易出错,更重要的是所得册数极为有限,而且只有少数富人才买得起,这些必然限制了它的传播。
而现代大众传播的引进终于导致了重要的变化。在中国,大众传播是与鸦片战争以来大众媒介的引进和运用相伴随的。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如报刊、书籍)和电子媒介(如广播、电影和电视)。而就中国晚清情形来说,大众传播首先是与新的印刷媒介取代旧的文字媒介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西式印刷机器的引进,逐渐地铅字排版取代了木刻活字排版,机器印刷代替了手工印刷,而铅印洋装书也替换了木刻线装书,报刊则成了拥有惊人传播能力的新媒介。
这种新的大众媒介对于大众传播的意义是深远的。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雷在1909年指出,新媒介在四个方面更为有效:“表达性,它们能传送范围广泛的思想和感情;记录永久性,即超越时间;迅速性,即超越空间;分布性,即能达到所有各阶级的人们……新的大众传播体现了生活各方面的变革,包括商业,政治,教育以至单纯社交行为和闲谈……”[2](P27)到了1935年,本雅明清晰地论述了以平版印刷、摄影和电影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技术对现代艺术的巨大而深远影响。机械复制“不仅能够复制所有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从而导致它们对公众的冲击力的最深刻的变化,并且还在艺术的制作程序中为自己占据了一个位置”。而这种新的复制技术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通过成批的机械复制而把传统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的审美特质——“灵韵”(aura,或译光环、光晕、韵味等)“排挤”掉了。“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正是艺术作品的灵韵。这是一个具有征候意义的进程,它的深远影响超出了艺术的范围。我们可以总结道: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的领域。通过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它以一种摹本的众多性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复制品能在持有者或听众的特殊环境中供人欣赏,在此,它复活了被复制出来的对象。这两种进程导致了一场传统的分崩离析,而这正与当代的危机和人类的更新相对应。这两种进程都与当前的种种大众运动密切相关。”[3](P60-63)本雅明清楚地看到,现代机械复制技术能够给传播带来革命性变化:有力地冲击以维护独特“灵韵”为宗旨的“传统”传播方式,而开创以大量“复制”为标志的新的大众传播方式。
其实,大众传播不仅在文学活动中、而且也在整个社会变革或转型过程中都起着“革命”性作用。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美国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就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信息增殖、控制、扩散及社会变革力量:“在一个传统的村庄,像其它地方一样,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在有媒介之前的文化中,力量的形式往往存在于能记住过去的智慧、神圣的文字、法律、习俗和各家族史的老人的记忆之中。”而在大众媒介伸展到“一个传统的村庄”后,“惊人的”变化发生了:“可以得到的信息的数量大大增加。传播来自更远的地方。地平线几乎一夜之间向远处退去。世界越过最近的山头或看得见的地平线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村民们关心别人是怎样生活的。力量从那些能记住很久以前的事的人那里,传到了那些掌握遥远地方有关信息的人那里。把过去的事写下来就成了共同的财产。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而不是维持一成不变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想象在传播渠道中流通……于是,正如哈罗德·英尼斯精辟地指出的,村庄的生活从口传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之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实践、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变更的轮子从此转起来。”大众媒介把变化的契机带到了以往封闭的地域,社会“变更的轮子从此转起来”。他据此归纳说:“大众媒介既是了不起的信息的增殖者,也是信息的很长的输送管……传播机器能够收集大量信息,能很快增殖和被极其广泛地利用,以致使控制和扩散信息的能力出现了量变,聚集了人数的注意力。”[1](P16-17)大众传播不仅具有这些信息革命功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在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时有力地促成或导致社会“革命”。正如施拉姆指出的那样,“书籍和报纸同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的分配感到普遍不满的时候,先是新闻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1](P18)这一点只要回顾《文明小史》中的《芜湖日报》事件就会清楚了。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官方,都力图以报纸为社会权力斗争的重要工具,力图通过办报而在社会权力冲突中赢得话语控制权。施拉姆断言说:“要是没有大众传播的渠道,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就不大可能像它已经做到的那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大众传播对于西方人来说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而对发展中地区来说,则使得整个社会革命的过程大大缩短:“信息媒介促进了一场雄心勃勃的革命,而信息媒介自身也在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中。”这正有力地证明了大众媒介及大众传播的强大的变革力量:“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这些革命教会我们一条基本格言:由于传播是根本的社会过程,由于人类首先是处理信息的动物,因此,信息状况的重大变化,传播的重大牵连,总是伴随着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1](P18-19)
二、大众媒介与中国审美现代性
如果上述有关大众媒介及大众传播的革命性力量的论述是成立的,那么,回头审视中国的情形,能得出怎样的观察呢?可以说,大众媒介的发达必然与文学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的进程相伴随。有理由这样说:正是发生在晚清的以现代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革命,在传播方式方面有力地参与并促成了文学现代性和整个审美现代性进程。这一点单从文学革命角度看就已经十分清楚了:从西方输入的机械媒介使得现代报刊印刷成为可能,而现代报刊的创办和发行为文学提供了大众传播条件。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学的传播媒介主要还是手工印刷媒介,如以手工抄写,以雕版、木活字或铜活字排版而以手工印刷,其主要形式是手抄本和线装本。诗和散文通常以手工抄写或手工印刷方式去复制和传播,由作者分送亲朋好友;即便是用于“买卖”的通俗小说,也多是以雕版刻印的。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雕版刻印《全唐诗》,收2000多位诗人的48900余首诗,分400卷,用去一年半时间。小说《红楼梦》一书于1791年首次问世,是用木活字印行的[4](P145)。这种手工印刷媒介方式决定了古代文学生产的手工传播性质:它的复制规模有限,产品数量有限,传播距离也有限。而从鸦片战争以后,来自西方的机械复制媒介逐渐进入中国,铅字排版和机器印刷取代过去的手工抄写和雕版印刷而占据主流地位。这导致现代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业迅速发生和发展,为文学提供了崭新的强有力的大众传播方式,从而使文学传播从手工传播演变成为大众传播。也就是说,由于机械印刷媒介的运用,文学得以从少量的“手工业”生产,变成了大量的“工业”生产。在上海,印刷工业与报业和文学之间,迅速形成了互动关系。“上海的工商业能力为近代印刷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促进了报刊和书籍出版的繁荣,也大大推动了印刷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到1884年,上海的全部外资工业中印刷业要占9.6%,拥有资本93.6万元,高于上海制药业、卷烟业和饮食业加在一起的总和。”[5](P42-43)
确实,现代报纸由于其出版周期短和发行量大,在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使文学迅速地走向了工业化规模。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担任主笔,得以较早体察到现代报纸的巨大威力。1872年2月,他在题为《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的社论中,归纳出报刊的如下作用:其一,“知地方之机宜”;其二,“知讼狱之曲直”;其三,“辅教化之不足”;其四,“指陈时事无所忌讳”[6](P146)。总起来看,他结合自己的办报经历,在大量政论中对报纸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阐发:一是“政事上行而下达”,即上情下达;二是“民隐得以上达”;三是“通外情于内”,使人民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也是“开民智”的重要途径;四是“达内情于外”,即发挥报纸“达内事于外”的作用,以事实之真相破除西方报纸的“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之论;五是控制舆论,感化人心,扬善贬恶。他因此不无道理地被誉为“我国近代专文表达报刊思想的第一人”、“我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6](P149)。从维新运动以来,由于政治变革的需要,政治精英大力提倡办报,如康有为大力著书立说以宣传维新主张,梁启超等于1895年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创办《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严复和夏曾佑在天津办《国闻报》,梁启超1896年主持《时务报》等。谭嗣同把兴办报纸、学校与学会并列为维新变法的三个重要手段,认为“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7](P418)。他充分认识到了报纸这种新兴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大众的启蒙与解放作用。洋务派的张之洞在《时务报》创办后即大为赞赏:“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于是他通知属下官员订阅:“照得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8](P152)
由于认识到现代报刊的巨大传播作用,文学以报纸副刊的形式陆续问世。当时著名大报纷纷开辟文艺副刊,如《申报》有《自由谈》,《新闻报》有《快活林》,《时报》有《余兴》等。由于文学报纸、小说杂志和小说书籍借助印刷媒介的威力迅速拓展其商业市场,需要一批专门人才从事文学职业性写作,于是,第一代职业作家群终于出现。他们往往居住在大都市如上海,既专事商业性写作,也同时兼任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如吴沃尧、李宝嘉、曾朴、黄小配、徐念慈、包天笑、周瘦鹃和徐枕亚等[5](P38-45)。
正是借助现代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威力,小说得到迅速发展。据阿英估计,在1898至1911年间,“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9](P1)。另一种统计则说,“短短十余年时间,成册的小说译著梓行一千数百种;从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小说》,到徐枕亚1918年创办《小说季报》,先后发行的小说期刊在五十种以上”[10](P1-2)。还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在1898~1911年间,中国出版的小说种类竟比此前250年间的总和还要多[11](P89-90)。13年胜过250年,足见新媒介的能量!按阿英的分析,晚清小说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机械印刷媒介的发达,即“印刷事业的发达”造成“刻书”的方便和“新闻事业的发达”导致“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则是知识分子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而“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是他们以小说“抨击”时政并提倡“维新与革命”[9](P1-2)。这里把机械印刷媒介列为晚清小说繁荣原因的第一条,是有眼光的。如果无视传播媒介的转换在小说繁荣中的基本的作用,是无法弄清现代小说生长的奥秘的。
小说传播媒介的这一转换是意义重大的:它代表了现代工业化的机械印刷媒介对于中国古代人工印刷媒介的胜利征服。同时表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传播媒介的现代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尤其是精英人物,可以在外来西方政治制度、思维方式、学术体制、法律制度等面前表示出种种怀疑、反对、拒绝等姿态,但在机械传播媒介的引进上,却似乎显得毫不犹豫和十分大胆。在机械传媒面前,矜持和犹豫都是多余的了。无论上层官吏还是下层民众、知识精英或普通公众,谁都想通过报刊而夺得话语控制权。《文明小史》里围绕《芜湖日报》而展开的知识精英与黄抚台之间的较量,以及李宝嘉本人出任《绣像小说》主编并任作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科学》杂志由任鸿隽于1915年创办,它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和“德先生”角色准备了充足了社会动员基础。尤其是陈独秀创办的《青年》和《新青年》杂志,更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试想,如果没有大众媒介的发达,中国的“小说界革命”乃至整个文学革命就必然缺少合适的传播媒介、传播信息、传播受众等,因而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思议的。报纸的发行和阅读,既为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维度,并且更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必要的传播媒介,从而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当然,广播、摄影、电影和电视等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限于篇幅,这里暂不一一论及。
三、大众媒介与审美现代性的生成
如何认识大众媒介在审美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对此,观点很多,这里可以举出其中三种:(1)“传播的偏斜”(bias of communication)论。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认为,一种传播媒介对于知识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传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对这种时间或空间因素的相对注重,将意味着被植入其中的文化出现一种意义的偏斜[12](P33)。例如,“偏于时间”的社会往往由简单的口头文化统治,或者其中通行的媒介是沉重的、难以移动和复制的,如石头和粘土,这类社会强调习惯、连续体、神圣知识等,是偏重于传统的社会。与此相对,偏于空间的社会则以更易移动、携带和复制的媒介取代,如古埃及以纸莎草取代石头,欧洲以纸张和印刷取代羊皮纸等。这种社会会产生偏于空间的文化,如领土扩张、世俗制度、专门技术等[12](P42)。他甚至主张:“一种新媒介的优势将成为导致一种新文明诞生的力量。”[12](P34)(2)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论。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主张媒介是人的延伸,即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媒介的发达使得全地球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正是据此观点,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媒介即讯息”的主张。与以往把媒介仅仅视为传播的工具或渠道不同,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从而总会带来传播内容(讯息)的变化。“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引起的,这种新尺度是被我们的每一次延伸或每一种新技术引导进我们的事务中的。”[13](P23)新媒介的产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或新技术,而是一种社会“新尺度”的创造。这种观点富于启发性地揭示了媒介的重要作用,但又将这种作用作了过分渲染。(3)媒介即情境论。美国传播学者麦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把麦克卢汉的理论与戈夫曼(Goffman)的“面对面互动”(face-to-face interaction)论结合起来思考,提出“信息情境”论:不应把媒介的作用仅仅理解为技术本身的决定性作用,而应理解为由媒介所造成的信息情境(situation)的作用。媒介的作用取决于媒介所造成的信息情境,这种信息情境犹如谈话的地点场所一样,可以影响到信息的传播,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他明确提出如下主张:“新媒介,新情境”(new media,new situations),“新情境,新行为”(new situations,new behavior)[4](P38-40)。显然,比较起来,麦罗维茨的理论较为契合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实际作用。从以上三种各有其得失的理论可见,媒介在审美中的作用既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轻视,而是需要正视,予以充分合理的关注。
大众媒介在审美现代性中的作用表现在:它不只是审美现代性的外在物质传输渠道,而就是它本身的重要构成维度之一;它不仅具体地实现审美现代性信息的物质传输,而且给予审美现代性的意义及其修辞效果以微妙而又重要的影响。这具体地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从社会情境看,大众媒介有力地参与营造了审美现代性得以生成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可以突破官方的话语霸权垄断而实现自由信息的传输与制造;第二,从发送者看,正是在这个由大众媒介建构起来的教育与舆论情境中,一批批痛感文化危机而渴望寻求出路的文化青年承受到强烈的现代性冲击,毅然决然地从传统文人变成了现代艺术家;第三,从接受者看,同样是在上述社会情境中,公众获得了崭新的现代性启蒙,成为熟悉并喜爱现代艺术如白话小说、话剧、油画、摄影、广播、电影等的“大众”。第四,从传播方式看,大众媒介构成审美现代性及其现代艺术样式得以传播的物质传输渠道。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大众媒介便没有审美现代性以及现代艺术样式。第五,从修辞效果看,大众媒介关乎现代艺术文本的意义,从而关乎审美现代性的意义构成。大众媒介并不只是影响现代艺术文本的外在剩余装饰因素,而是它的意义及修辞效果的重要构型因素。由于不同的大众媒介在社会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这种媒介对于具体艺术文本的意义及修辞效果会发生某种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影响。例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单从艺术标准来看很不成熟,但由于在《新小说》杂志连载,借助这种现代大众媒介而对知识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并由此对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竟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这些表明,大众媒介直接关乎艺术文本的意义及社会修辞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