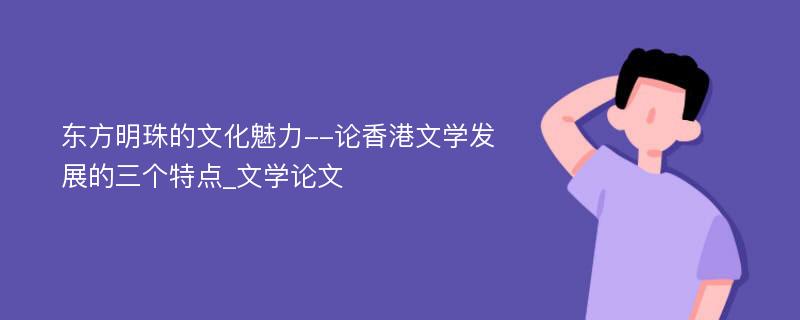
东方之珠的文化神韵——论香港文学发展的三个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神韵论文,之珠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美丽的东方之珠。独特的地理位置,流动而密集的人口,高度发达的都市工商经济,几十年沿袭英国殖民地组织形式的行政体制,香港人民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使香港流形成了“港派风味”浓郁的文学,表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文学队伍的多元构成
香港文学圈具有世界上同等规模的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多样性。这首先是由香港人口的多元性和流动性造成的。由于香港当局对移民的流入和流出持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所以自20年代以来,每当香港人口出现流动高潮时,往往是香港文化人聚散最频繁之时。以作家为例,出版过文学作品或主持过报刊文艺专栏,并在港居住7年以上的香港作家,自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总共有360多位。如果按各自的文学经历,大致可分成五大类:第一类,香港生香港长,在香港写作并且成名,如舒巷城等;第二类,外地出生,移居香港后开始写作,并且走向成熟,如西西等;第三类,外地出生并开始写作,甚至已有相当成就,移居香港后继续写作,如倪匡、戴天、杨明显等;第四类,外地出生成长,旅居香港写作一段时间,又移居外地继续写作,如“一脚踏在台湾,一脚跨在香港”的余光中、高旅、施叔青等;第五类,在香港出生,离开香港后在外地工作成名,又经常在香港发表文学作品,如刘绍铭等。
上述作家,按进入香港文坛的早晚,又可分为“本土作家”和“南迁作家”两大类。
第一代本土作家是在20年代至40年代崭露于香港文坛的。1929年,年轻的侣伦在寂寞的港岛上首先与一批文学朋友组织“岛上社”,被称为香港文坛的第一只春燕。此间,又有谢晨光,刘火子、张吻冰、黄天石、黄谷柳、舒巷城、夏易等脱颖而出。由于在此之前尚无完全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所以他们的创作多带有拓荒性质,而且常常会遇到许多叉道。这一阶段的香港文学以充满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穷巷》和《虾球传》等,树起了香港早期文学的丰碑,同时又有许多人迅速地从文学圈中分化出去。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香港作为贸易中转港的地位日趋重要,开始进入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繁荣期。这刺激了香港人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刺激了第二代本土作家的文学追求。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西西、亦舒、梁锡华、也斯、钟晓阳、小思、温健骝等。他们大多毕业于高等院校,部分人还留学欧美,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正因如此,他们身居港岛,在文学视野和感情天地上,却和世界文坛各种新潮流相通。如西西等人,很早就接受了存在主义,后来又走出了存在主义的阴影,以惊喜的目光关注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历程(《我城》等);而诗人温健骝等,则多角度地抒写香港社会的光与影、曲与直、火与冰,体现着一种比较自觉的香港人意识,要“为中国人的未来做点有意义的事。”
由海峡两岸移居香港的作家,被称为南迁作家。其中50年代前后赴港的为第一代,包括刘以鬯、徐讦、唐人、李辉英、徐速、司马长风等。他们把回五十年代政治大风暴的涛声带进港岛,拓宽了香港文学的视野。70年代前后,是第二代南迁作家赴港的一个高潮。其中由大陆移居香港的作家群体就个人素质而言,基本上与大陆作家相通。他们在大陆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初来香港又尝尽了世态的炎凉,浮沉在茫茫人海中。由于亲自体会到反人道主义的社会丑恶,他们很注意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种种丑恶现象,对跑马赌场、选美丑闻、商场奸诈、少女堕落、黑道猖獗、道德沦丧等都给予鞭挞和嘲讽。另一个特殊现象是香港聚集了一批“亦港亦台”的作家。由于独特的政治和人文条件,港台之间可以自由来去,其民俗风情和文学环境又有很大的区别。这对穿梭两地、眼光敏锐的作家常常构成新的刺激和挑战,出现了一批既有香港都市味又有台湾乡土情的“混装型”作家。如施叔青,生于台湾,学于美国,1979年受聘于香港艺术中心,5年后离职在港专门从事写作。她认为“全世界找不到第二”香港不像台湾那么封闭,“美到几乎不够真实的程度”反而能激发许多遐想,使她以外来客的眼光写下《香港的故事》。
90年代初以来,以程乃珊、吴正为代表,又有一批青年作家南下香港。作为“老三届”的一代人,他们深埋着历史的创痛,对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有较深的体验,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中国的巨大变化有过亲身的参与,所以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有文化自信心。如吴正赴港后,从事过多种职业,直到创下自己的产业,在沪港等地进行跨区域的发展。他从不简单地认同香港的商业环境和社会风习,而以大陆积淀深厚的人文传统与香港开放喧嚣的竞争氛围相互对照,既用现代的商战心态来反观内陆文化的沉重缓慢,又以长江子民的苍凉来映衬港岛风气的浅薄浮躁。他们既在商业场上拼杀,又在香港报刊上发表创作,还与自己出生地的上海、北京、江苏、广东等地文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二、创作趋向的自由冲撞
如果说如此多样化的来源,构成了香港作家特有的流动性和素质多元化,那么,这个“自由港”的氛围和社会结构,更给作家开辟了自由表达的空间。
在这里,有政治风浪激起的回声,5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60年代近在咫尺的印度支那战争,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腾飞,80年代以后香港回归祖国的冲击波等,无不像台风季节气象台挂起的信号气球,震荡着香港文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50年代围绕“绿背文化”的冲突。所谓“绿背”是美元的别称,因为美钞都以绿色的墨印刷。50年代前期,为了宣传“美式民主”,美国的亚洲基金会在香港一方面资助出版机构,另一方面又广泛延揽内地迁港的文化人,掀起了一股“绿背文化”的浪潮。这批文化人大多是被大陆刚解放的国内形势所迫,带着“逃难”的心境来港岛避祸的,来港后凄凄惶惶,生活无着,精神苦闷,正好在美援的庇护下借助文笔发泄怨恨。如端木青的长篇小说《阿巴哈哈草原》就抒写了一种“天堂失落,魂归何处”的深深悲衰。
有矛必有盾,有投靠“绿背文化”的文人,必然会有“反绿背文化”的文学。以表现蒋家王朝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而名噪一时的香港作家唐人,以一支辛辣尖刻的文笔,讽刺了这群失落民族气节的社会弃儿。他的《某公馆散记》(又名《人渣》)就描写了一群国民党军政人员来港后走投无路,终于沦为“人渣”的下场;又在《混血女郎》等中短篇小说中,揭示着香港社会的生命悲剧,斥责“香港这个地方,教人学坏的地方太多了!”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少有社会大变动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相反,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最大的自由港,它充满了激烈的商业竞争、险恶的人世倾轧、多变的流行时尚和残酷的市场厮杀。一方面,香港居民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但香港人不能持香港护照自由出入英国本土,与英国人可以自由来去香港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香港又与当年同属英联邦范围的印度、巴基斯坦大不相同,它处在几大文明板块的边缘,既不属于英联邦的文化氛围,也与大陆的本土文化圈保持着相当距离。香港作家在这座“水泥森林”中蠕动挣扎,在“空气都有价目表”的商业都市中竞争求生。他们从切身的体验出发,长于展示都市众生相,褒贬商业化氛围,但每个人的着眼点和开掘角度又不尽相同。舒巷城、王一桃等诗人善于捕捉都市心态的各个侧面。他们徘徊在中环的高楼脚下、旺角的红灯区、尖沙嘴的长堤边,既赞叹这座城市的金融奇迹,又为香港在人性伦理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扼腕叹息:“无数人的破产/堆积成一个人的腾达/然后再由那个人出面/普济众生!”难能可贵的是,在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不少诗人作家仍然保持着平民意识,对于艰难求生的普通劳动者保持着深深的同情。
正因为香港是激烈的竞争社会,作家们创作中也爱走极端,以此来吸引社会注目。因此,香港文学园地中经常出现畸变景观,各执一端,推向极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构成另一道文化风景线。如乡土文学和诡异小说就是两股反向而行的快车道。乡土文学最早兴起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代表作《太阳上山了》真实地展现了香港下层社会的风情。那筲箕湾里轻轻晃动的破渔船,那一毫两件的卤水档,那弥漫着水烟味的低档茶馆,悠然响起贫家女儿哼唱的粤语小调。许多当时的下层方言,经过作家提炼,成为俗不伤雅的“粤味风”,如“冷巷”、“大头彭”、“咸肉庄”等等无不响脆流畅,亲切宜人。而徐讦等人的创作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吸收中国古典志怪故事的基础上,熔入西方传奇因素和宗教因素,还融入了好莱坞电影的悬念手法。
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则是香港文坛上另一对欢喜冤家。本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香港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生态和社会结构大踏步走向现代化,陈旧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和道德观念已经与现代步履不相适应,与此同时,香港民众的视野也越来越趋向国际化,这就迫使香港作家们打破常规,用新的手法来形成新的阅读热点。在这方面,刘以鬯的“实验小说”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技巧,在主题和情感上都有浓郁的“港味”。如《天堂与地狱》就把苍蝇拟人化,它在咖啡馆里看到了由3000元港币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深感这“天堂”里的人“外表干净,心里比垃圾还龌龊”,苍蝇愤愤不平地下定决心,“宁愿回到拉圾桶里过地狱般的日子,而不愿在这人的世界里过天堂的生活”。刘以鬯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酒徒》,则被誉为中国最早采用意识流手法的长篇之一。它以现代香港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的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
三、爱国之心的延伸折射
几十年来,香港作家从各个角度刻划了英籍殖民官员、驻港英军官兵、香港本土企业家、各地来港移民、商海弄潮儿、受过国际化教育又返回香港发展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为命运而拼搏的扛工仔和港女等多种人物,在一片斑驳的色彩中,见出殖民地心态的光影。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就是典型一例。第一部《她名叫蝴蝶》写东莞少女黄得云落难到香港被卖为妓女的4年经历。作者先此发表的另一部《维多利亚俱乐部》,主人公黄威廉是黄得云的孙子,已经发迹当了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正在受理1987年前后香港维多利亚俱乐部的一桩受贿案。通过黄得云一家的挣扎沉浮,作者写出了香港殖民史上几个典型历史事件:1892年香港的鼠疫和政府洁净局放火焚烧华人疫区,瘟疫过后死里逃生的华人演戏酬神;1895年香港政府颁发新住宅条例,倍受压迫的华人大量迁回内地;20世纪初叶香港取缔中医案几经争取,祖传的中医终于在香港有了一席之地……。在作者笔下,殖民主义的手掌玩弄着香港的命运,千百个象黄得云这样的小人物在他们的手掌中无奈地挣扎着,受够了殖民主义制度对华人的奴役和欺侮。
在许多小说家和诗人的笔下,香港又是香港人创造的一个奇迹。随着70年代以来,华人经济的迅速发展,香港人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伴随着民族自信心的不断增强。英国报纸悲哀地宣称:到2000年,香港人的平均收入要超过他们原来的宗主国英国人,香港人在各个领域都表现着对殖民主义者的不满和愤怒。如果说海辛在1988年完成的《塘西三代名花》以30—50年代的香港欢场塘西为背景,展示了三代烟花女子的跌宕变化,透露着香港人作为“二等公民”的无奈和愤怒。第一代名妓花如锦,虽然年轻时“出道较早”,但流落风尘,屡遭磨难,舔尽了遍体的伤痕;第二代女性花影湘,沉浮于上流社会,痛恨殖民官员的少廉寡耻,钟情于有正义感的司机兼保镖;第三代影星钟月湘毅然告别早年恋人,只身踏上畏途。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则是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从1892年到1987年,以三代人将近100年的时空跨度,概括了香港从初建时的贫寒到现今的繁华过程。这既是殖民官员“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过程,也是港人的奋发有为获得世界承认的过程,从而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小说的文字图绘香港,为历史留纪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老牌殖民主义者逐渐衰落,遍布亚、非、拉、美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每一个殖民地的独立过程都伴随着眼泪、屈辱和奋斗。而香港的归宿是独一无二的。它将以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九七”到来之前,香港人的心态成为作家们感兴趣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作家们怎样表现这一历史转折本身,也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梁锡华的小说《头上一片云》以香港某大学教师卓博耀为中心,把他一家及亲朋好友面对“九七”回归的多种心态描绘出来,他们长期生活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已经成为一种定势。
在更多香港作家笔下,更有一条从省港工人大罢工开始,直到“九七”回归的壮丽红线。香港不是超然世外的桃源,从20年代反抗列强的大罢工斗争,到抗日战争中配合东江纵队的英勇战斗,香港人民血管中也流淌着爱国主义的热血。不少诗人和小说家形象地描绘了香港人民盼望“九七”的心情,在诗人李平笔下,“那是象维多利亚海湾的波涛一样震荡的心潮,是象阴沉了多日的梅雨季节之后海平线上展开的一片亮色”。而梁凤仪的小说《大家族》则描绘了几个香港豪门大族荣氏、庄氏等,在跨入90年代后所面临的历史选择。商海交兵,惊心动魄,境外势力,竭力拉拢。然而,荣心聪等人历经惊涛骇浪,终于顺应大趋势,作了向祖国大陆追加投资的重大决策。主人公摒弃了奴颜婢膝的殖民地心态,向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升起竞争的风帆,并且相约:“度密月,最好的地点应该是北京!”
这犹如宣告灰色调的殖民地心态即将成为历史。香港文学伴随着百年沧桑,录下了港人的心史。随着“九七”回归的到来,它必将在南中国海的春风中,掀开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