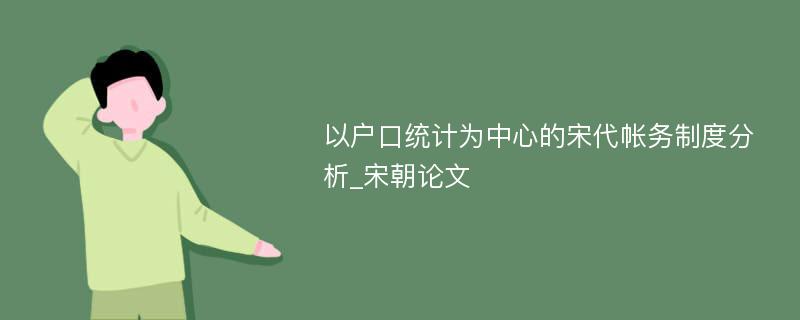
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宋代论文,户口论文,制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籍帐制度源远流长,是历代王朝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之一。在经历安史之乱的重创后,唐代租庸调制迅速瓦解,中国古代的籍帐制度发生重要变化。随着以土地财产税为中心的两税法的实施,“以丁中男为对象的,均一的租调役来征税的理念下的计帐,完全转变为异质而复杂化的帐簿体制”,① 从而开启了唐后期至宋新的籍帐制度。
长期以来,围绕宋代户口统计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户口研究的推动下,宋代籍帐制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②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然而,由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加之宋代制度的复杂多变,以至有学者认为,宋代户籍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明确、一贯的官方规定和缺乏统一性。③ 迄今为止,宋代户口统计籍帐制度仍有一些问题未能搞清,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宋代的户口统计籍帐,主要涉及五等丁产簿、丁帐、税租簿帐、保甲簿和赈济户口统计帐五种,其中又以五等丁产簿、丁帐和税帐最具代表性。本文试以这三种籍帐为主要对象,围绕户口统计,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宋代籍帐制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便正确认识唐中叶以降中国古代籍帐制度的变化。一管之见,有待方家指正。
一 五等丁产簿始设年代考辨
宋五等丁产簿又称五等版簿。论述五等丁产簿,不能不涉及五等户籍制。关于宋代五等户籍制的确立时间,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然分歧较大。日本学者柳田节子认为明道二年(1033)的仁宗诏书始确立五等户籍制度。④ 中国学者梁太济则认为五等户籍制的颁行时间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至乾兴元年(1022)这9年间,明道二年诏书规定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1034)为首次执行撰造五等丁产簿的年份。⑤ 这一问题牵涉到宋代五等丁产簿的始设年代,不可不辨。
在探讨宋代五等户籍制时,首先应该考虑户籍制的历史继承性问题,关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制度对宋代户籍制度的影响。其次应当重视当时的法律规定。法典文献是籍帐制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法律有时不一定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它毕竟是社会活动的基本规范。
在入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唐律、令、格、式仍是当时有效的法律形式。《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1载:“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格]后敕》、《开成详定刑法总要格敕》、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天福编敕》、周《广顺续编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⑥ 上述众多法典都在宋初行用之列。建隆四年(963)修成《宋刑统》后,仍然参用唐式、令。窦仪在《进〈宋刑统〉表》中云:“请与式、令及新编敕兼行。”⑦ 其所云式、令,就是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所订。即使到了天圣时期,“令文尚依唐制”。⑧ 既然北宋前期用唐令唐制,我们在研究北宋户口统计制度时不应忽略唐令唐制的参考价值。1998年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原以为失传的修撰于天圣七年(1029)的宋代令典《天圣令》。《天圣令》今存后十卷,其记载户口统计制度的《户令》已佚缺。然而存世的《田令》、《赋役令》、《杂令》有关条文却给我们以重要启迪,如《天圣令》卷22《赋役令》载宋令第9条:
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外(升)降户口,即作五等定簿,连署印记。若遭灾蝗旱涝之处,任随贫富为等级。差科、赋役,皆据此簿。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凡丁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者要月;家贫单身者闲月)。其赋役轻重、送纳远近,皆以此为等差,豫为次第,务令均济。簿定以后,依此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豫差科。若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⑨这条令文为我们了解宋初五等户籍制提供了重要信息。关于《天圣令》的编撰,“凡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⑩ 换言之,在修订《天圣令》时,将业已行用的五等户籍制修人新令文中。因此可以断定,五等户籍制并不始于天圣七年。《天圣令》卷21《田令》载宋令第2条曰:
诸每年课种桑枣树木,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第二等八十根,第三等六十根,
第四等四十根,第五等二十根,各以桑枣杂木相半,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此条田令所规定的以五等分户课种树木制,也并非是天圣七年新定,乃是承袭了建隆二年诏书的规定。早在建隆二年春,太祖曾“诏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植,每县定民籍为五等”,(11)开宝五年(972)《沿河州县课民种榆柳及所宜之木诏》又日“仍按户籍高卑,定为五等”,(12)从中可以看出宋五等分户制是一以贯之的。早有学者指出,户分五等五代后晋时就已出现。(13) 晋高祖天福七年(942)十一月,“以所在禁法,抵犯者众,逐开盐禁,许通商,令州郡配征人户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14) 后周也曾实施户分五等制。作为新建立的政权,宋代的户籍制不可能完全摆脱前朝的影响。
《长编》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条载:“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仍请三年一责户口之籍,别定升降。从之。”“仍请三年一责户口之籍”,显然是承袭了五代的户籍旧制。问题是究竟用唐九等制还是后周五等制,必须做出选择。宋太祖采用了五等制,户籍仍定为五等,以家资财产多寡分高下。《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庚辰”条载:“诏诸州版簿、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此诏规定诸州的版簿等文书由判官和录事参军掌管,如果原无版簿等文书,则造之。“版,户籍也者,汉之户籍,皆以版书之。”(15) 可知“版簿”乃沿旧称,实即户籍簿。综上所述,宋初沿用唐制,三年一造户籍,户籍簿制度早已存在,有些州可能由于五代战乱等原因致户籍簿散失亡佚。五等分户制从建隆元年起就作为宋代主户的户籍制度而存在。建隆二年太祖诏令课民种植,不过是重申了后周显德时期的定制。
虽然宋最初五等分户的目的主要是课民种树,但是户分等级高下有着多种作用,差科征税仅是其中部分功能。宋初五等分户制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16) 当时唐九等制还有一定的影响,在差科方面,尚未完全按五等制分差徭役。太平兴国五年(980)程能建议以九等分户来行徭役,(17) 正是唐九等制影响在宋初的反映,同时也表明当时五等分户制尚未能渗入徭役这一领域。宋五等户制的功能是从课民种树逐渐延伸到其他方面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五等户籍簿的撰造和存在。
《天圣令》卷30《杂令》载宋令第40条云:“诸道士、女冠、僧尼,州县三年一造籍,具言出家年月、夏腊、学业,随处印署。案留州县,帐申尚书祠部。其身死及数有增减者,每年录名及增减因由,状申祠部,具入帐。”此杂令乃是在唐令基础上修改而成。《唐六典》卷4“祠部郎中员外郎”条所载唐令作“诸道士、女冠、僧尼之簿籍,亦三年一造(原注: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鸿胪,一本留州县)”。以唐令为蓝本的日本《养老令·杂令》亦有与此相似的规定:“凡僧尼、京国官司,每六年造籍三通,各显出家年月、夏腊、德业,依式印之。一通留职国,此外申送太政官,一通送中书,一通送治部。所须调度,并令寺准人数出物。”(18) 参考《唐六典》及《养老令》,可知《天圣令》基本保留了唐令的内容,承袭了唐制三年一造籍的规定,只是增加了每年报僧、道增减统计数至祠部的内容。至道二年(996),祠部员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
盖自唐末以来,乱离相继,急于经营,不遑治教。故金谷之政,主于三司,尚书六曹,名虽存而其实亡矣……今职司久废,载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诸州僧道文帐,职方有诸州闰年图经,刑部有详覆诸州已决大辟案牍及旬禁奏状,此外多无旧式。(19)
北宋前期三司主财政,户口帐籍归三司之户部掌管,尚书省户部职掌被削夺。尚书职司由此多废,档案载籍散失不存。然而祠部却存有诸州上报的僧道文帐,职方存有诸州上贡的闰年图经。这表明《唐令》规定的僧道籍帐三年一造并报祠部的制度北宋初期是实行的。由此联想到《唐令·户令》所定户籍制度,在宋代也应留有其痕迹。
唐均田制崩溃后,赋役制也发生很大变化,这必然引起籍帐制度的变化,不过有些基本制度不会变动太大。张泽咸先生指出:“编制户籍和三年一定户等的原则,在两税法时期是大体上沿袭了下来。”(20) 这一看法对于我们研究实施两税法的宋代户籍编撰制度不无参考价值。前文曾提到唐僧道三年一造帐并报祠部的制度,仍为宋代所沿用,而唐户籍制“天下户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本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21) 应当说,宋政权建立之初,除户分九等制被五等制替代外,唐三年一造簿的制度仍在沿用,后来才改为逢闰年造五等丁产簿。三年一造与闰年一造仅是撰造时间上的区别,但五等户制本身却并没有变。笔者以为五等丁产簿由三年一造改为逢闰年一造,与宋代闰年造闰年图有关。《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丁巳”条载:“有司上诸州所贡闰年图。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贡地图,与版籍皆上尚书省。国初以闰为限,所以周知山川之险易,户口之众寡也。”“故事”者,乃指前朝之制。唐制:“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偕上省。”(22) 为节约成本,宋代五等丁产簿的撰造时间此后逐渐与闰年造闰年图的时间同步。
明道二年,诏“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簿,自今先录户产、丁推及所更色役榜示之,不实者听民自言。”(23) 这是我们见到的宋代文献中关于闰年造五等丁产簿的最早记载。有学者据此认为五等户籍制确立于明道二年。然而正如前面所论,闰年造五等丁产簿并不自明道二年始。我们不能因明道二年诏书首次出现“闰年造五等丁产簿”,就断定五等制确立于明道二年。《作邑自箴》载:“造五等簿,将乡书手、耆户长隔在三处,不得相见,各给印由子,逐户开坐家业……仍须一年前出榜约束人户各推,令名下税数着脚。次年正月已后更不得旋来推割。”(24)“着脚”即著脚,是指在户籍上注录有关数据。(25) 据此段史料,知各县在正式造簿的前一年,须出榜告示民众,令民户将该推割税产的手续办定,并于各自旧籍下注明税产。来年正式造簿时不得再办理推割事宜。换言之,户籍登记的家业财产乃是造籍前一年的财产状况。并以此为准确定户等级别,张榜公布。这一做法是为正式造户籍做准备,涉及造籍之程序。
《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定户以仲年(原注: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原注:丑、辰、未、戌)。”唐规定每三年一造户籍,造籍的第二年即为下一轮的造籍定户之年。登录田产户口,是一项琐碎而繁杂的工作。笔者以为宋造五等户籍亦沿用此制,三年一造(后定为闰年一造)。仁宗景祐元年为闰年,在此前一年的明道二年下诏书,实际上是要求做好闰年造籍前一年的“定户”准备工作,以便来年正式造籍。此诏书所言与《作邑自箴》记载的造五等丁产簿前出榜约束人户的规定可以互证,证明宋代闰年造五等户籍,亦仿唐制;定户在闰年前一年,待各户户口财产数据登记公示无误后,至来年(闰年)才正式造户籍。
二丁帐、丁籍考辨
宋代丁帐又称丁口帐。景祐元年中书门下言:“《编敕》节文:诸州县造五等丁产簿并丁口帐,勒村耆大户就门抄上人丁。”(26) 关于丁帐,学界有不同看法,主要为丁帐的始设年代,客户与丁籍的关系,上报户部的丁帐统计对象,非闰年期间朝廷公布的主客户数据来源,丁帐与升降帐、桑功帐的关系等问题。以下分别作一辨析。
在探讨丁帐诸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丁籍。在宋代的文献记载中,除丁帐外,还有丁籍,丁帐和丁籍有何区别?学术界对此尚未予以注意。
在宋代,丁帐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丁帐包括丁籍在内;狭义之丁帐,则单指申报朝廷的丁口数据汇总文书。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帐与籍(簿)是有区别的,是不同类型的文书。丁籍专指用于征役催税的簿籍而言,又称丁簿。但学者往往用丁帐取代丁籍,或将丁籍视作丁帐,(27) 也有学者把丁籍混同于五等户籍,(28) 从而影响了对宋代户口统计制度的正确理解。地方基层登录每家每户原始材料的文书,通常称簿或籍,如五等丁产簿、丁簿、纳税租簿等。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曰:“诸州专令知、通取索逐县丁簿,稽考岁数,依年格收附销落。”(29) 乾道二年(1166)五月,有臣僚奏言:“两浙路去年百姓以疾疫死亡,以饥饿流移者至多,州县丁籍自应亏减,窃闻州县按籍而催,尚仍故目。”(30) 这两条材料中的丁簿(籍)是指保存在州县,作为催科征税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不能换称为丁帐。除丁簿外,五等丁产簿也属此类簿书。《天圣令》卷22《赋役令》载:“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升降户口,即作五等定簿,连署印记。若遭灾蝗旱涝之处,任随贫富为等级,差科赋役,皆据此簿。”这表明五等丁产簿是基层征税差科的依据,留县并不上缴,而是仅录副本送州存档。“应诸县造乡村、坊郭丁产等第簿,并录副本送州印缝,于州县(院)架阁。”(31) 即使是副本也是存档备查的,不是上报朝廷的统计汇总文书。前引《天圣令》卷30《杂令》载宋令第40条的史料也说明所造僧道籍,经审核后留存州县,另外再造帐申报中央。籍和帐的使用区分得很清楚。《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戊戌”条载,睦州通判张方平奏言,当时睦州管内主户户籍“有升降帐,有桑功帐,并岁上于户部”,“州县赋役,各有五等户版簿,常所据用”。这些户籍各自户口统计数据不一,作用不尽相同。其中只有五等版簿是主户最基本的户口统计依据。然各州县官员在点差由主户承担的弓手时,拘泥于敕文规定的“须见管帐籍”之“帐籍”二字,以致舍五等版簿不用,而造成“点差异同”。可见帐与簿不能混为一谈。
《作邑自箴》卷5《规矩》记载有县级政府奏帐制度:“年终帐状限次年正月二十日,半年帐状限次半年孟月十五日,每季帐状限次季孟月初十日,月帐状限次月初五日,旬申帐状限次旬二日,夏秋税管额帐当年五月一日,纳毕、单状税满限四十日:并要申发讫呈检。”可知县每年上报的帐有年终帐、半年帐、季帐、月帐、旬帐、管额帐、纳毕帐等,但却未提到上报的有簿、籍。《宋史》载,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婺州实施经界法,丈量清理土地,重定税额,“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灿然可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创库匮以藏之”。(32) 所云各类簿册,皆为与土地、赋税相关的重要文书,其中也不见有以“帐”为名的文书。上述例证说明簿与帐性质不同。
综上所论,丁籍是地方州县催科征税的依据簿书,保留在州县,并不上缴朝廷;丁帐则是指依据丁籍制成的报呈上级的丁口统计文书。开宝五年,“罢两京缘河诸州每岁春秋丁帐,止令夏以六月、冬以十二月申”。(33) 从这一史料来看,当时两京及黄河沿边诸州夫役繁重,需征发大量劳动力,朝廷为了掌握丁口总数,统筹调配,以至于一年要两次申报丁帐。我们只有把丁籍和丁帐统计的对象和范围区分开来,才能进一步了解宋代的籍帐统计制度。
(一)丁帐始设年代及太祖乾德诏书的史料意义
关于丁帐的始设年代,学者们大都以《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庚辰”条所载“始令诸州岁所奏户帐,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作为宋代丁帐制度始设时间的证据。然而细细推敲,其中并没有说自乾德元年(963)始奏户帐,而是说从这年开始,规定成丁的年龄界限为20岁至59岁。“始令诸州岁所奏户帐”中的“所”字,是一个助词,用在本句中,表示中心词是“户帐”,而不是“奏”这一动词。“始”字是针对下文丁口的年龄规定而言的,意思是从今开始,诸州每年所奏报的户帐,其统计的丁口的成丁年龄为20岁,60岁入老,女子不计人内。关于此条文献记载,《文献通考》作:“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34) 根本没有提及始令诸州岁奏户帐之事。马端临将此理解为乾德元年规定诸州岁奏(帐)的对象以20岁至59岁的成丁为限,妇女不计,也表明岁奏户帐制不始于乾德元年。后梁开平三年(909)三月户部奏云:“请诏天下州府,准旧章申送户口帐籍。”(35)可见五代时申报户口帐籍已成为一种制度,宋只是承袭了这一定制。
关于乾德元年诏书中“户帐”所指,学者们看法不一,以日本加藤繁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是指丁帐,(36) 苏基朗却认为是指升降帐和桑功帐,不是三年一造的户籍。(37) 此诏书所载内容,《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亦作:“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宋史·食货志》本于宋之国史。(38) 可见“户帐”二字,并非李焘随意之笔,也非古书传刻之误。笔者以为“户帐”乃“户口帐籍”之省称,用以泛指地方每年所奏的所有户口帐籍,其中既有苏基朗认定的升降帐、桑功帐,同时也包括了丁帐。乾德诏书的旨意是,这些帐籍中的丁口年龄,不管是主户,还是客户,统一规定为男口以20岁至59岁为成丁,女口不计。如果仅云丁帐,则升降帐、桑功帐中的丁口将会排除在外,这显然不是太祖乾德颁诏的本意。
关于乾德元年诏书的颁布,学者们作了不同的解释。袁祖亮认为“是针对徭役而发,是划分应役年龄的诏令”。穆朝庆认为“其实质是明确了赋役对象和国家的重点控制对象”。(39) 笔者以为,乾德元年始规定成丁的年龄界限,旨在更改《宋刑统》的相关法律条款。在此之前,宋代是以25岁成丁,55岁入老。乾德元年七月颁布的第一部法典《宋刑统》,其卷12《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门”规定:
准户令:诸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其男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准唐天宝十三载十二月二十五日制节文:自今以后,天下百姓宜以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
准唐广德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敕:天下男子宜令二十五成丁,五十五入老。(40)
《宋刑统》记载了三种唐不同时期规定的不同的成丁年龄界限,其中“户令”是指开元二十五年所修令。这三条法令规定的年龄界限各不相同,究竟以哪条为准?考《宋刑统》卷30《断狱律》断罪引律令格式:“准唐长庆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敕节文,御史台奏,伏缘后敕,合破前格。自今以后,两司检详文法,一切取最向后敕为定。敕旨宜依。”依据此法律规定的从新不从旧的适用原则,宋在乾德元年十月之前应是沿用唐广德元年(763)规定,男子25岁成丁,55岁入老。(41) 然而宋建立之初,积极准备统一全国的战争,急需劳动力,广德元年规定成丁年龄在时限上偏晚,不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宋太祖在乾德元年十月颁布诏令,更改《宋刑统》的规定,调整成丁的年龄界限。由于女子不在夫役征发之列,故不用统计。因此,乾德元年诏书“始令”成丁以20岁至59岁为限,应是针对《宋刑统》的规定而作的修改。
必须指出,乾德元年的规定最初适用范围在于岁所奏户帐统计,以便征发徭役。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成丁以下的中、小男以及女口不再纳入宋代其他簿籍的统计范围。《天圣令》卷22《赋役令》宋令第9条载:“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升降户口,即作五等定簿,连署印记。”其中明确说到县令的职责包括须掌知丁、中数额,并据此制定五等版簿。又熙宁三年(1070)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制,“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十五以上皆充。”(42) 15岁以上皆充,显然是包括中男在内。(43) 而中男无论主客户,都必须登录于簿籍。又宋赋役令规定:“诸女户寡居,第三等以上,虽有男子,年十五以下,其税租应支移者,免全户之半。”(44) 宋名例敕曰:“诸缘坐应编管而年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并免。”(45) 这些法令规定年十五以下男子可享有一定的赋税及司法减免权。换言之,15岁以上至19岁(南宋至20岁)的男子与成年男丁一样,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他们在户籍簿上当然也应有登录。
上述材料都说明乾德元年诏书规定的男夫20岁为丁,60岁为老,适用于岁所奏户帐统计。在其他场合,仍然须统计成丁以下的男口。乾德元年诏书规定的原则,是我们正确认识宋代户部户口统计制度的关键所在。
(二)客户与丁籍的关系
宋朝将全国人口依据土地财产的有无划分为主户和客户。(46) “天下户籍,均为五等”,(47) 此乃指拥有土地的主户而言。主户之外,尚有大量的客户存在。客户也应有自己的户籍。但是宋代有多种帐籍涉及客户统计,如丁帐、税帐、保甲簿。(48) 其中究竟哪一种帐籍是登录管理客户的基本帐籍?换言之,即客户归属于哪种籍帐管理?他们又是如何编籍的?对此,传世文献所言不明,学术界尚缺乏足够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客户没有独立户籍,而是登记在五等丁产簿的主户之下,是附籍于五等丁产簿。(49) 但证据并不充分,似乎未被学界所接受。吴松弟在《宋代户口调查统计制度问题答客问》一文中就“客户应入五等丁产簿”观点提出了否定意见,(50) 所论是正确的,但没有就客户的户籍归属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由于没有土地等固定财产,“客户往来不常”,(51) “转徙不定”,(52) 流动性较大。给户口登记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但这不等于客户没有户籍管理。《宋刑统》卷12《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载曰:“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若一户之内,尽脱漏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纵一身亦为一户,不附即依脱户,合徒三年。”这虽然是唐制,亦为宋所沿袭。按此法律规定,每一个人都应登录于一定的籍书,即使是孤身一人,在户口籍上亦应为一户。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宋代丁籍、丁帐撰造申报制度十分重要。
景德四年(1007)真宗诏“诸路所供降升户口,自今招到及创居户委的开落得帐上荒税,合该升降,即拨入主户供申,内分烟析生不增税赋,及新收不纳税浮居客户,不得虚计在内”。(53) 既云“新收”客户,那一定是已登录在某种帐籍中,只不过不能算作主户而已。熙宁三年考课院奏言:“准诏定到知县、县令考课法……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54) 考课法将客户数是否增长也纳入县官的考课范围。如果客户没有户籍予以登录,如何考知他们是否增长呢?
早在唐代,就有收客户编籍的记载。唐柳芳云:“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55) 开元九年(721),唐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获巧伪甚众”。唐规定“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赋调”。(56) 《唐会要》卷85《逃户》载:“天下所检客户,除两州计会归本贯已外,便令所在编附。”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有一条检括出的浮客蒋化明籍为百姓的史料:
102化明辩:被问先是何州县人,得共郭林驱驴?仰答。但化明
103先是京兆府云阳县嵯峨乡人,从凉府与郭元味驱驮至北庭。括
104客,乃附户为金满县百姓。为饥贫,与郭林驱驴伊州纳和籴。
108 开元廿一年正月 日(57)
蒋化明是没有土地的浮客,附户后成为有独立户籍的百姓。玄宗天宝敕有“客户终年者编籍”的规定,(58) 客户因无田土而常流移不定,故天宝敕要求客户于当地居住满一年者置籍加以管理,纳入差科范围。
唐制,“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59) 唐所谓计帐,是关于下一年度课役征调的预算文书,由户口统计和课役预算两部分组成。(60) 自唐后期行两税法后,原先的计帐制度发生变化,原租庸调并入两税,“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61) 力役据丁征调。唐建中元年(780),京兆府“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62) 入宋以后,旧之计帐制度虽已不存,但却制定有丁籍、丁帐制,宋据丁籍征夫役。编制丁籍成为宋实施赋役制度的重要内容。
北宋法律规定,即使是被强制执行流徙于他乡并服苦役的流刑罪犯,“居作一年,即听附籍”。(63) 又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75《编配流役·户令》规定:“诸缘坐编管、羁管人永不放还者,编管、羁管处及六年,给公凭,从户口例附籍,愿于他州附籍者,许牒送。”关于“附籍”,有学者认为是附于主户之下。(64) 其实“附籍”,即登录于户籍之意,不作“依附”解。前引《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所载浮客蒋化明附户成为有独立户籍的百姓即是一佐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立继有据不为户绝》载:“准法,异姓三岁以下,并听收养,即从其姓,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虽不经除附,而官司勘验得实者,依法。”所谓“除附”,乃是宋代户口管理制度。宋人云:“此谓人家养同宗子,两户各有人户,甲户无子,养乙户之子以为子,则除乙户子名籍,而附之于甲户,所以谓之除附。”(65) 可见“附籍”,是相对于“除籍”(注销户籍)而言的登录户籍之制。法律规定犯人服役刑满或流徙远地六年后,可以在当地落户入籍。这些罪犯被强制流徙他乡,刑满后附籍,如果没有土地财产,身份当属客户,所入户籍不可能是五等户籍,应为丁籍无疑。
论者常引《作邑自箴》中“如系客户,即去(云)系某人客户”,(66) 来强调客户依附于主户之籍,附载于五等丁产簿。然而宋代客户除了租种地主的土地外,还广泛租种官田。(67) 按照前述客户租种地主的地,即附籍于地主之户的说法,那么租种官田的客户又如何依附编籍?也有学者以唐代奴婢部曲依附于主人户籍为例,认为宋代客户也是附籍于主户的。(68) 然而宋之于唐,时代毕竟不同了,宋代客户虽然没有土地财产,但他们不是地主的私属。北宋人此山贳冶子《唐律释文》就部曲、奴婢释日:“此等并同畜产,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以奴畜之。及其长成,因娶妻。此等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类,名为部曲。婢经放为良,并出妻者,名为客女。二面断约年月,赁人指使为随身。”(69) 此山贳冶子谈到了部曲、奴婢依附其主生活,籍随主人,其主以奴畜之。然奴婢经放良,成为雇佣劳动者,与雇主签订契约,身份上是良人。笔者认为应自有户籍。宋人胡宏曰“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70) 即客户和主户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客户与地主以契约为纽带,结成租佃关系。客户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良人身份,在户籍管理上有自己的专属户籍。因此,那种客户依附于主户之籍的观点不具说服力。
北宋仁宗时,滁州遭旱灾发生饥荒,朝廷命开官仓赈灾,而当地主管官吏未能及时照办,新任通判姚仲孙“既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尽给之”。(7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州县丁籍登录了主客户人口资料,故赈灾之粮可依据丁籍来发放。如果五等丁产簿确如有些学者所说附载有客户的话,姚仲孙为何不直接取五等丁产簿赈灾呢?原因很简单,五等丁产簿并没有登录客户。
《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辛卯”条载司马光赈济之奏,建议“据乡村五等人户,逐户计口出给历头”,实施救济,而不是要求据丁籍救济。据五等户籍救济,则显然排除了客户。难道客户不需救济了么?抑或客户是附于主户之籍?然而细细解读司马光整篇奏文,不难发现司马光此奏是要求朝廷重视主户,认为他们“比于余民,尤宜存恤”,希望宋政府在各地未发生民众流移之前,做好主户的安抚存恤事宜,使他们不至失业。故建议朝廷据五等户籍赈济。其赈济的对象原本就不包括客户。皇祐三年(1051),仁宗曾诏:“漳州、泉[州]、兴化军,自伪命以来,计丁出米甚重,贫者或不能输,朕甚悯之。自今泉州、兴化军旧纳七斗五升者,主户予减二斗五升,客户减四斗五升。”(72) 据皇祐诏书,身丁税的豁减应是按照户籍区分主客户来实施的。五等丁产簿只登录主户数据,因此客户另有自己的户籍。
北宋毕仲游在《耀州理会赈济奏状》中云:“勘会本州七县,据籍,主客户共十一万三干五十户,计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口。据诸县元抄录末等无营运阙食之人,共四万六千三百三十八户,计一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四口。”(73) 此奏中提到的两种数据来自不同的统计系统,后一种是赈济系统,统计的对象是全体男女人口。(74) 这里,后一种数据暂且不论,单看前一种包含主客户在内的户口数据。毕仲游所云“据籍”当是据户口系统之籍,而载有客户统计资料的户口系统之籍,除赈济统计帐籍外,有丁籍、保甲簿。保甲簿乃神宗熙宁年间才出现,(75) 时距宋政权建立已有一百多年。如果说只有保甲簿才是唯一登录客户的基本户籍,那就意味着,在熙宁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客户一直没有自己的归口户籍,这显然说不通。因此,从宋初以来制度的连贯性来看,毕仲游所言之籍应该就是丁籍。
综上所述,宋代客户有自己独立的户籍,那就是丁籍。如果说唐代的户籍以人丁为主兼及土地,那么宋代的五等户籍则是以土地财产为主兼及人丁。这从客户不人五等户籍制之规定反映出来。丁籍是脱离了地籍的独立的户口籍。五等户籍制尚没有做到户口统计的单一化,宋代只有丁籍才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户口籍。
(三)上报户部的丁帐统计对象是否包括所有男口和户数
宋初编制丁籍、丁帐,主要是为了征发夫役,只统计户口,不计财产。《长编》卷12“开宝四年七月己酉”条载:“令河南府及京东、河北四十七军州,各委本州判官互往别部同令佐点阅丁口,具列于籍,以备明年河堤之役。如敢隐落,许民以实告,坐官吏罪。先是诏京畿十六县重括丁籍,独开封所上增倍旧额,它悉不如诏。上疑官吏失职,使豪猾蒙幸,贫弱重困,故申警之。”关于此次清点丁口对象,《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1记载说是“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差遣之时,所贵共分力役”。牛客、小客属客户。(76) 客户也是宋代夫役的承担者,故清点不分主户、客户,俱登录于丁籍,目的是为第二年的河堤之役做准备。所造丁籍,明显具有差科簿书的性质,夫役也并不局限于修浚河道,《天圣令》卷22《赋役令》共计23条宋令,其中有10条是关于丁匠役使管理制度的。(77) 例如宋令第10条云:“诸丁匠上役,除程外,各准役日,给公粮赴作。”丁匠属承担夫役的劳动者。这些令文反映出北宋前期大量役使丁夫,其中自然包括客户在内。又如乾道二年五月臣僚言:“两浙路去年百姓以疾疫死亡,以饥饿流移者至多,州县丁籍自应亏减,窃闻州县按籍而催,尚仍故目。”(78) 孝宗时蔡洸奏言:“镇江共管三邑,而输丁各异。有所谓税户,有所谓客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税户、客户,惟丹徒并输丁,而丹阳、金坛二邑有税则无丁,其输丁者,客户而已。”(79) 这些都说明当时丁籍是用来催科征税的,不分主、客户。
丁籍登录对象是主、客户,以全体男性为统计范围,登记每户男口姓名、年龄。不少学者认为,县和州两级的丁帐都以全体男性为统计范围,登记每户男口姓名、年龄。(80) 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将丁籍统计的对象误认为丁帐统计的对象。事实上,只是丁籍才登记全体男性数据。关于这个问题再补充几条相关资料:
其一,淳熙二年(1175)孝宗庆寿大赦云:“应人户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与免户下一名身丁钱物。”(81) 这一政策对客户来说,也应有效。减身丁钱物,是以户为基本单位来计算的,8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没有登记人丁籍,便无法计算豁减。
其二,淳熙八年有臣僚奏言:“饥馑之时,遗弃小儿为人收养者,于法不在取认之限,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82)
其三,《事物纪原》载:“《周礼》: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已上皆书于版,太宰听间以版图,今州县有丁口版簿即此,盖始于周也。”(83)
其四,宋封赠令规定:“诸士庶遇恩应官封者……下厢耆邻保次第勘验,本处取丁籍,再行审验年甲。”(84)
这些史料都证明丁籍不分老小登录全体男口。州县丁籍登录有全体男口的资料,那么每年上报户部的丁帐,是否也将所有男口资料一并供上,或只报成丁数?对此学术界有争论。(85) 这一问题可以在乾德元年诏书里找到答案。诏书规定诸州所奏户帐,“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86) 其中仅规定成丁的年龄,这就意味着包括丁帐在内的户帐只报成丁数。如果说另外还包括中、小丁,那理应将中小丁的年龄界限一并作规定。据前引《宋刑统》卷12《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门”载唐以来丁、中、小、老年龄界限的沿革,唐开元令规定中的年龄界限为16—20岁,其中有5年的跨度;天宝制规定中为18—22岁,其中也有5年的跨度;广德敕规定中为18—24岁,其中有7年的跨度。依据法律从新适用之原则,宋初期中的年龄界限为18—24岁。我们假定乾德诏书只更改成丁年龄,中、小丁年龄不变,依然有效,然而由于乾德诏书更订了成丁的年龄结构,上限从25岁降至20岁,这就使得中的年龄跨度减小到18—19岁,只有两年。与以往制度相比,显得非常不协调。因此,笔者以为乾德诏书只规定成丁年龄,表明中、小等幼丁并不在州每年申报的丁帐、升降帐等户籍统计申报范围之内。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诏曰:
诸州专令知、通取索逐县丁簿,稽考岁数,依年格收附销落。如辄敢将未成丁之人先次拘催,及老丁不为即时销落,许经本州申诉,依条根治施行。(87)
诏书所谓“年格”之“格”是一种法律规范,宋代的法律形式有敕、律、令、格、式,年格的法律规定就是“民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88) 知州、通判取索的县丁簿,应是上一年县制作的旧丁簿。这与州稽考县税租簿的方式相同。宋法:“诸县税租夏秋造簿,于起纳百日前,通旧簿并干照文书,送州申磨点检。”(89) 丁簿上因注有每户主户和客户的所有男口状况、年龄,知县、通判将新旧簿籍予以对照,可稽考年龄,凡达到成丁年龄,或入老者,皆应予以收附或注销。淳熙十二年刑部尚书萧燧奏曰:“在法,民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官司按籍计年,将进丁或入老、疾,应收免课役者,皆县令亲貌颜状注籍。通、知取索丁簿,稽考岁数,收附销落。”(90) 这些材料都强调州长官亲自审核丁籍,稽考丁口岁数,保证成丁的实际年龄,严禁用未成丁及已入老之人充数。淳熙五年有臣僚奏言:“今欲县委县丞,如均税事体,置丁税一司……每岁入务限前,以籍实丁名数关报本县催理。”(91) 宋代丁之称谓,通常专指成年男子。南宋户令云:“诸男年二十一为丁。”(92) 如是别指老人或未成年人,则在丁之前冠以“老”或“幼”字。如成年男子与老丁、幼丁并称时,则云“成丁”,以示区别。(93) 上述例证表明,只有成丁才是州县丁籍最终要稽考的对象,总计成丁实数,据以征收身丁税。丁籍的基本作用就是用来催税和征役。
笔者以为,州上报朝廷的丁口统计文书,只是根据丁籍编制成的丁帐,而不是丁籍本身。而丁帐统计的对象只是户数与成丁数,不包括其他男口。高宗绍兴七年,比部员外郎薛徽言:“欲望明饬有司,稽考州县丁帐,核正文籍,死亡生长,以时书落。岁终县以丁之数上州,州以县之数上漕,漕以州之数上之户部,户部合天下之数上之朝廷。”(94) 所谓“死亡生长,以时书落”,笔者以为是针对成丁的登录而言的,即成丁中死亡的和入老的人,都应从丁籍中及时予以注销,以便把准确的成丁统计数呈报给上级部门。丁帐是逐级上报给上级部门的统计文书,应将其与“关报本县催理”丁税的丁籍区分开来。
我们知道,申报丁帐的目的最初是为了征发力役,宋“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95)承担力役的人应是成丁之人。北宋统一南方后,丁籍又成为科派身丁钱的依据,但依然以成丁为科派对象,“年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其未成丁、已人老者,及身有废疾并与放免”。(96) 南宋承袭这一定制,“二十岁以上则输,六十则止,残疾者以疾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97) 宋代的中男和小男,已不再承担徭役。《天圣令·杂令》所附不用之唐令,其中有许多由中男、小男充任役使的规定。《天圣令》弃之不用,至少表明宋代的夫役实行成丁充任制。因此,尽管县级丁籍统计所有男口资料,但是上报户部的丁帐只统计户数及成丁数。
既然只报成丁数到户部,那么为何县级丁籍还要统计所有男口资料呢?丁籍登录主客户所有男口,是为了便于稽考岁数,正确实施进丁入老的措施,防止作弊。以便做到合理承担力役和摊派身丁钱,减少社会不均现象,缓和阶级矛盾。
吴松弟认为“丁帐上报到户部的只是丁口,没有户数”。(98) 然考《景德农田敕》:“诸州每年申奏丁口文帐,仰旨挥诸县差本村三大户长就门通抄。每年造帐,本县据户数收落,仍春季终闻奏。”(99) 丁帐以丁籍为基础制定而成。敕文所云“据户数收落”,就是说据户别一户一户登记成丁,以户为基本单位统计丁数,造丁帐报户部。既然以户为单位登录丁口,上报户部的丁帐,也就不可能省略户数不报。这一点,从宋政府公布的户口数据也可得到验证。宋政府公布的户口数据,通常丁(口)数和户数是对应的,有丁(口)数,一般就有户数。因此,上报户部的丁帐应该统计有户数。
(四)非闰年期间朝廷公布的主客户数据来源
由于宋五等丁产簿只登录主户资料,客户不在统计之列,吴松弟指出,宋政府公布的全国户口数字并不是来自地方上报的五等户籍资料,而州县丁帐统计有全部主客户男口资料,“北宋初期闰年图的户口只能得自丁帐”,从而构成北宋初期地方闰年所贡闰年图的资料来源。他认为全国性户口数“并非直接来自户部的数据,而是主要来自保存在兵部职方的闰年图”。(100) 然而闰年图为闰年上贡,在非闰年期间,宋政府公布的包括客户在内的户口数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呢?例如开宝九年并非闰年,宋政府公布的这年的数据包含有客户在内,“太祖开宝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万五百四”。(101) 虽然在两个造置闰年图的间隔期,各地每年申报有丁帐和户口增减帐(户口升降帐),但据文献记载,无论是丁帐还是升降帐,每年申报到户部而非掌图经的兵部职方。(102) 而升降帐记载的仅是主户户口的变动数;税租帐虽载有客户的数据,且定有每年申报制度,但税租帐制度的建立是在后来的太宗至道元年。因此这些都不是解开开宝九年户口数据来源之谜的答案。
由于州掌握有主客户数和全体男口的数据,宋地方每逢闰年申报闰年图时,这些数据也一并予以供报。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云:“臣文观《西京图经》,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置二十县。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一十九县(主户五万七百,客户二万五千二百)。”(103) 范仲淹所言《西京图经》,当是西京河南府闰年所贡闰年图经。《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载:“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又诏重修定大小图经,令职方牒诸州谨其藏,每闰依本录进。”《西京图经》中的客户数据显然是来源于地方的丁籍统计系统。除此之外,州每年还以丁帐形式向户部申报户口统计数据,其中除了成丁数(不包括成丁以外的男口数)外,还包括了主、客户数。然后由“户部合天下之数上之朝廷”,(104) 朝廷最后予以公布。搞清了这一点,才能解开非闰年时期,朝廷公布的主客户数据来源之谜。这个问题,是我们研究宋代户口统计制度时不应忽视的。
宋代统计主客户数据的有税帐、保甲簿。然而税帐制度的设立是在太宗至道元年,时距宋政权的建立已有35年。保甲簿的出现则更晚。从文献记载来看,在这段时期内,宋代事实上早已存在一个全国户口统计制度。而州上报到户部的丁帐则是这户口统计数据的最基本的来源。当然,诚如吴松弟指出的,“宋代在户口调查统计各系统之外还存在着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105)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
(五)丁帐与升降帐、桑功帐的关系
北宋仁宗时,据睦州通判张方平言,当时州县主户户籍有升降帐、桑功帐和五等丁产簿,作用不尽相同:
敕文,其弓手须见管帐籍主户差点者。只如臣州管内户籍,有升降帐,有桑功帐,并岁上于户部。升降帐所管主户二万二千三百有余,此盖官吏受俸约此户口数也。桑功帐所管主户三万七千六百有余,此乃州县户口岁有增益之数也。州县赋役,各有五等户版簿,常所据用,窃虑逐处拘于“帐籍”二字,致有点差异同,欲乞明降处分,州县止以见用五等版簿见管主户数为准,则天下之役均焉。(106)
张方平云五等版簿与升降帐、桑功帐所登记的户口数各有差异,故奏请以五等版簿为准。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差异?这里以升降帐为例做一比较。升降帐全称为“户口升降管额文帐”,每年一报户部。(107) 景德四年九月真宗诏曰:“诸路所供升降户口,自今招到及创居户,委的开落得帐上荒、税,合该升降,即拨入主户供申。内分烟析生,不增税赋,及新收不纳税浮居客户,并不得虚计在内。”(108) 根据诏书的意思,升降帐所统计的主户是以能增纳赋税为原则的。以此推论,即使是主户分家,由一户析为二户或三户,但因其原承担的税赋总量没有增加,不符合奖励原则,故不能计入升降帐的主户数申报。此外,倘若有客户因购买土地而成为新主户,但从升降户口制的原则来看,从某人手里购得土地,仅仅是从某税户手里分摊到一部分纳税义务,从宋政府角度来看,并没有增加新的税赋,故也不能计人升降帐。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诏曰:“诸州县自今招来户口,及创居人中开垦荒田者,许依格式申入户籍,无得以客户增数。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县即申等,乃加其俸缗,至有析客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入,故条约之。”(109)然而揆之常理,那些因分家或购买土地而增加的主户户数在闰年制定五等丁产簿时却是不能不统计的。于是就造成了升降帐的现管户数和五等版簿现管户数的差异。
升降帐是以在一个规定时段内能增加赋税的主户为统计对象的。此帐主要起激励县官的作用,是地方官吏加俸升等的主要依据。而五等版簿只要是主户一概予以登记,主要是用来征税差科。然而上述每年新增加而不能入升降帐的新主户,要等到下一轮五等丁产簿写造时,才能纳入簿册。至于桑功帐的户数,按照张方平的说法,乃“州县户口岁有增益之数也”,是基于升降帐统计出来的,与五等丁产簿的户数差异亦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宋代每年的户口统计就产生了一个缺口。这一缺口如果没有其他相应的户口统计予以弥补,势必影响宋代户部统计的准确性。丁帐则起了填补这一统计缺口的作用。无论主客户或新旧户,“就门通抄”,全部予以登记上报。从这点来看,宋代只有丁籍才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户口籍。
三税租簿帐考辨
税租簿帐,又称二税版籍,包括税租簿和税租帐。关于宋代的税租簿帐,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苏基朗认为税帐有两种形式,“一种叫管额帐或空行簿,另一种叫纳毕帐”,税帐每年分夏、秋两造之。(110) 吴松弟认为,“税租簿又称实行簿,由各县每三年(逢闰年)造一次,上报到州复核后留州存档”。(111) 此外,对于监司申报户部的《夏秋税管额帐》是否列有所有男口资料,学界亦有不同观点。以下就这些问题试作分析探讨。
(一)税租簿与空行簿、实行簿的关系
宋代税帐制度正式形成于太宗至道元年(995),《长编》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条载:
诏重造州县二税版籍,颁其式于天下。凡一县所管几户、夏秋二税、苗亩桑功正税及缘科物,用大纸作长卷,排行实写,为帐一本,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缝,于长吏厅侧置库,作版柜藏贮封锁。自今每岁二税将起纳前,并令本县先如式造帐一本送州,本县纳税版簿,亦以州印印缝,给付令佐。
这一诏令分前后两个部分,分别就税租帐和纳税版簿的申造作了规定。纳税版簿即税租簿,其撰造之规定,诏令所言过略。《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2对此记载较为详细,为便于说明问题。一并抄录如下:
(天圣)三年七月京西路劝农使言: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今乞候每年写造夏秋税簿之时,置木条印,一雕年分、典押、书手姓名,令、佐押字。候写毕,勒典押将版簿及归逃簿,典卖、析居、割移税簿逐一勘同。即令、佐亲写押字,用印记讫,当面毁弃木印。其版簿以青布或油纸亲背津般,上州请印。本州干系官吏,更切勘会,委判、勾官点检,每十户一计处,亲书勘同押字讫,封付本县勾销……事下三司,三司检会《农田敕》:“应逐县夏秋税版簿,并先桩本县元额管纳户口、税物都数,次开说见纳、见逃数,及逐村甲名税数。官典勘对,送本州请印讫,更令本州官勘对,朱凿勘同官典姓名,书字结罪,勒勾院点勘。如无差伪,使州印讫,付本县收掌勾销。”今请依所乞造置簿印施行。从之。
所谓《农田敕》应是景德三年所修《景德农田编敕》。敕文所云经州审定后由本县收掌的夏秋税簿,即至道元年诏书规定的请州印印讫,给付本县令、佐的纳税版簿。关于县造夏秋税租簿,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47《税租簿·赋役令》亦有法律规定:“诸县税租,夏秋造簿,于起纳百日前同旧簿并干照文书送州申磨点检,书印讫,起纳前四十日付县。”这一规定应该说是承袭了北宋《景德农田编敕》的规定。关于木条印,是用于各纳税户之税簿的印记,以防作假。自天圣三年下令置造后,遂成为定制。(112) 县税租簿应是在户纳税簿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庆元条法事类》卷47《税租簿·赋役式》载县《夏秋税租簿》格式如下:
某县某乡,某年夏或秋税租,元管户若干……新收:户若干;正税……开阁减免……见纳:正税……某人(原注:谓见纳或新收人户姓名,仍于逐色并纸末量留空纸,以待折变、割移):正税……
余户依此开
以上三十户计(原注:每三十户依此计):正税……
簿后年月、官吏系书依常式(113)
税租簿以乡为单位,首载原管户数,次列祖额税收数、新收户及税租额、开阁减免户及税租额、现纳数额,并开列了现纳每一户户主姓名、应纳税租额。税租簿以三十户为一统计单位,开列总纳税租额。据此不难判断,《夏秋税租簿》乃合若干纳税统计单位为一乡税租簿,合若干乡税租簿为一县税租簿。此税租簿以三十户为一统计单位,与上述天圣三年规定的“每十户一计”的统计方式是一致的。(114)
至此,县造税租簿的作用和功能应该比较清楚,它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纳税统计簿,与唐代县级计帐颇为相似。(115) 所不同的是唐代县级计帐是预计下一年赋税征纳的帐簿,而宋税租簿乃预计当年税收,登载一县应纳赋税数额。它是宋代赋税帐籍系统中最原始的赋税征收记录簿,经州府审核认定后,成为向民户征收赋税的凭据。税租簿就其预算性质而言,不属于上报上级机构的汇总帐。例如在前述《夏秋税租簿》格式末尾,没有“谨具申州”的结款。而这样的结款,在宋代呈送上级籍帐格式中通常是必具的。绍兴十六年规定:“诸典卖田宅,应推收税租,乡书手于人户契书、户帖及税租簿内并亲书推收税租数目、并乡书手姓名,税租簿以朱书,令佐书押。”(116) 可见税租簿作为乡里推收税租和差科的依据是不上缴州的。道理很简单,民间百姓典卖田宅的时间并不固定,税租簿上报,如何登记税租的推收手续呢?
有关税租簿就是实行簿并三年(闰年)一造的看法,可能源于天圣元年的一项规定:“凡赋入,州县有籍,岁一置,谓之空行簿,以待岁中催科。闰年别置,谓之实行簿,以藏有司。”(117)何谓空行簿?欧阳修在《论按察官吏札子》中曰:“今请令进奏院,各录一州官吏姓名,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才干,明著实状,及老病不材,显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书于姓名之下。”(118) 据此,空行簿是一种为落实某项政策措施而预制的簿书。而实行簿,顾名思义,当是与之对应的一种簿书,记录政策措施实际落实完成情况。例如,欧阳修所言进奏院所执空行簿,等到记满了按察信息后,自然成为实行簿。
置空行簿,乃“以待岁中催科”,“待”者,有尚未完成之意。换言之,空行簿是用以催征税收的凭据。县每年于夏秋纳税之前所造税租簿,是一种预制性质的簿书,应是“以待岁中催科”的空行簿。《夏秋税租簿》于“某人”一栏注云“仍与逐色并纸末量留空纸,以待折变、割移”。据此注文,可知在征税过程中,税租簿随时记注上实际纳税状况,已纳者则勾销,未纳或未完纳者亦于注录。待夏秋税征收完毕,原先的空行簿因就簿记录或增添了实际征收数据,自然变成了实行簿。县造税租簿事实上承担了两种功能,只因税前税后不同而分称空行簿和实行簿。
但是仅有一种簿书,一旦毁失,就会造成很大混乱,所以景祜二年侍御史韩渎奏言:“天下赋役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则登耗之数无从钩考。”要求恢复被中止的别置实行簿制度。仁宗采纳了韩渎建议,诏每两闰一造之。(119) 笔者以为闰年别置的税租实行簿,实际上是县赋税征收情况的原始记录簿的副本。宋在州存放重要文件的架阁库中,就有此税租实行簿副本,其全称为“实行丁产等第税租簿副本”,属于宋《文书令》规定的“重害文书”。(120) 实行簿在景韦占以后又进一步恢复了一闰一造制。南宋时赋役令载:“诸税租簿,每三年别录实行副本,保明送州。”(121)
综上所述,县每年于二税起纳前造送州审核的税租簿,带有预算性质,以待征税,故又称空行簿。等到征税后,因其登录了征税的实况,便成为实行簿。而县造税租簿应是一年分夏、秋两次撰造。天圣三年京西路劝农使奏言云“每年写造夏秋税租簿”,(122) 以及《赋役令》规定“诸县岁造税簿”,(123) 都是确凿的佐证。至于管额帐即空行簿的观点,显然是把宋代簿与帐这两种不同作用的文书混淆起来了。
宋代二税征收完成后,依法必须申报《夏秋税纳毕帐》,纳毕帐与税租实行簿有何区别?《庆元条法事类》卷48《税租帐》载有州、漕《夏秋税纳毕帐》,其栏目有“见催”、“新收”、“开阁检放”、“实纳”。可知纳毕帐是一种汇总帐,而税租实行簿只是征税实况的原始记录簿。两者登录的对象、范围也不尽相同,如税租簿登载有户口情况,纳毕帐则无户口数据。
(二)税租帐的申报制度
至道元年诏书规定县每岁造帐一本送州。此帐为税租帐,性质与交付县使用的税租簿性质不同。在《庆元条法事类》里,税租帐与税租簿分列于两个不同的类别,这也表明二者是有区别的。
至道诏书所云“颁其式于天下”,所谓“式”,是一种法律形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样式。宋初期用唐律令格式,式“以轨物程事”。(124) 换言之,宋至道所颁两税帐式是一种必须遵行的法律规范。神宗元丰改革法制,始规定“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125) 所定式与唐式不同。至道诏书所颁式的具体文字内容,传世文献已无可考,但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48《赋役门·税租帐》载有《诸州申夏秋税管额帐》,其以县为统计单位,统计栏目有“某县主客户丁”、“税租”、“新收”、“开阁”、“应管”、“今帐实催”等。此《管额帐》,是否即宋至道所颁两税帐式?《作邑自箴》卷5《规矩》记云:“年终帐状,限次年正月二十日;半年帐状,限次半年孟月十五日……《夏秋税管额帐》,当年五月一日;《纳毕》、《单状》,税满限四十日,并要申发讫呈检。”《作邑自箴》是一部县级官员理政须知,其中所言“《夏秋税管额帐》”,即为县报州之税帐。由此可以断定,至道元年诏书规定的县每岁上奏给州的税帐,实际上就是这种《夏秋税管额帐》,是一种汇总性质的统计帐。
县造税帐,每年一报州,这一制度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然《庆元条法事类》卷48《赋役门·税租帐》载仓库令云:“诸《夏秋税管额帐》,每三年一供全帐,余年有收支或开阁者,供刺帐,无,即供单状。”关于这条法律规定,学者尚未注意。据此规定,《夏秋税管额帐》主要有全帐和刺帐两种形式(单状因不登录数据,可以忽略)。全帐,应是一种内容详备的帐,《庆元条法事类》卷48所载《夏秋税管额帐》即其样式。而刺帐,据该书同卷所载,为某单项数据统计表,内容较为单一简练。刺帐可能是南宋时形成的称谓。《庆元条法事类》卷51《道释门·供帐》载道释令:“诸僧道及童行帐三年一供,每一供全帐,三供刺帐,周而复始。”换言之,三年供一次详细的全帐,其余时间每年供报一次较为简单的刺帐。这表明全帐与刺帐相结合的供报制是宋代普遍适用的制度。关于《僧道帐》,北宋《天圣令·杂令》亦有规定日:“诸道士、女冠、僧尼,州县三年一造籍……案留州县,帐申尚书祠部。其身死及数有增减者,每年录名及增减因由,状申祠部,具入帐。”《天圣令》云三年申报一次《僧道帐》,此外每年还得申报增减数,却没有提到刺帐。北宋虽不用刺帐之名,但类似帐早已出现。开宝五年宋规定“诸州科纳,止令县具单帐供州,不得令逐乡造夹细帐,以致烦扰”。(126) 细审其意,所谓单帐实即后来之刺帐,而夹细帐即后来之全帐。
税帐可细分为夏税帐和秋税帐,皆一年一申。太宗至道元年诏书规定县造税帐每年一报州,说得比较笼统。事实上每年一报州的只是单帐(刺帐),此外尚有三年一报全帐的制度。南宋赋役令规定:“《诸州夏秋税管额帐》,夏自正月一日,秋自四月一日,各限四十五日(原注:刺帐、单状同)……造申转运司。”(127) 赋役令规定了《管额帐》、刺帐、单状相同的申报时间与时限,说明刺帐、单状与《管额帐》的申报是交叉进行的,报了全帐,不报刺帐。至道元年所颁帐式是全帐形式还是单帐形式,缺乏记载。笔者以为其制也应是遵循三年一供全帐,每年~供单帐(刺帐)的原则,可能既有全帐格式,也有单帐格式,以便各地依式造帐。这与《僧道帐》三年一供全帐,余年供刺帐的原则是一致的。
(三)转运司供报的《夏秋税管额计帐》是否统计全体男口
《庆元条法事类》卷48收录有州、漕两级《夏秋税管额帐》式样,这两件帐式有繁简之别。在州向转运司供申的《管额帐》“主客户丁”一栏的注文里,详细开列有包括丁、中、小、老、残疾人数在内的所有男口的分类统计项目。然在转运司向尚书省供申的《管额计帐》“主客户丁”一栏里,却没有中、小、老、残疾人的分类统计项目。究竟是转运司《管额计帐》因州税帐格式已有详注故而无须再作说明,予以省略了呢?还是本身就不统计这些成丁之外的男口?这一问题牵涉到宋代户口统计制度。对此,学者们看法不一。(128)
关于《夏秋税管额帐》,转运司的那份称《夏秋税管额计帐》,州的那份则无“计”字,另《庆元条法事类》同卷所载《夏秋税纳毕帐》,以及卷37《给纳》所载《钱帛帐》、《粮草帐》亦莫不如是。这反映出漕、州管额帐统计的范围、对象有所不同,有着繁简之别。何谓“计帐”,苏辙曾上奏称:元丰三年朝廷规定,“使州郡应申省帐,皆申转运司。内钱帛,粮草,酒曲,商税,房园,夏秋税管额、纳毕、盐帐,水脚,铸钱物料,稻糯帐,本司别造计帐申省……盖谓钱帛等帐,三司总领国计,须知其多少虚实,故帐虽归转运司,而又令别造计帐申省”。(129) 据此可知,计帐是转运司“别造的”不同于州帐的特有文帐。
再从转运司《夏秋税管额计帐》格式看,只有“实催”和“户口人丁”两大栏目,省去了“旧管”、“新收”、“开阁”及“田产”等诸多栏项,且把“户口人丁”改置于“实催”栏之后。这也与《诸州夏秋税管额帐》的排列次序不同。宋代转运司负有监管一路财政的重任,代表朝廷对州申报的帐籍进行稽考磨勘。宋规定,“县、镇、仓场、库务帐,本州勘勾;诸州帐,转运司勘勾”。(130) 因此,州上报的《夏秋税管额帐》数据自然繁杂详备,有“旧管”、“新收”、“开阁”等详细数据,以供转运司比对稽考。而转运司上报的《夏秋税管额计帐》,只是使户部“知其多少虚实”,所以无需统计“旧管”、“新收”、“开阁”等项目数据。如果说州、转运司申报的《夏秋税管额帐》内容是相同的,那么,《庆元条法事类》就没有必要分别详细规定两种《夏秋税管额帐》的格式内容。因此,诸州申报的《夏秋税管额帐》所载中、小、老、残疾人的分类统计数据,主要是供转运司稽考磨勘之用,而不上报尚书省。
关于下级申报上级的税帐,《庆元条法事类》卷48载,除了《夏秋税管额帐》外,尚有《比较税租帐》、《夏秋税纳毕帐》,通过其他税帐之间的差异比勘,或许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宋州、漕都有《比较税租帐》,在《诸州比较税租帐》内,开列了一州当年与上一年的税收数额,以此来比较当年实际征收数额。其中“析生、归业、请典等”一栏下,列有“以下项逃绝析[生]外,实收若干”文字。在《转运司比较税租帐》内,同样的“析生、归业、请典等”栏目下,“以下项逃绝析[生]外,实收若干”的文字被省略了,却有注文日“准州式”。也就是说,此栏目须按《诸州比较税租帐》格式填写。又如在同样的“某年应管”栏目下,州、漕两帐都注云“谓前一年”,漕帐并不因州帐已有细注而予省略。这些说明,转运司和州的帐式,彼此都有严格的规定。转运司的奏帐与州的同类奏帐,不存在因精简文字而相承简化格式的问题。
综上所述,转运司申报尚书省的《夏秋税管额计帐》并非因格式简化而省略了主客户丁中、小、老及残疾人等统计项的注释文字,应该是这一《夏秋税管额计帐》原本就不上报这些统计内容。换言之,上报到户部的户口数据只统计主、客户数和成丁数。
注释:
①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注释2。
② 参见苏基朗:《宋代的户多口少现象》、《宋代一户两口之谜》,载《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穆朝庆:《两宋户籍制度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47—157页;何忠礼:《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83—98页;吴松弟:《宋代户口调查统计制度史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5—327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吴松弟的成果最为完备,代表了目前最高研究水平。吴松弟经过充分详尽的论证,提出宋代在户口调查统计各系统之外还存在着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对我们正确认识宋代户口籍帐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③ 何炳棣:《宋金时代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5期,第26页。
④ 柳田节子:《宋代乡村的户等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五册,第196页。
⑤ 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46页。
⑥ 《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462页。
⑦ 窦仪等:《宋刑统》,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页。
⑧ 王应麟:《玉海》卷66《天圣新修令》,光绪浙江书局本,第28页;《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4,第6463页。
⑨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下册,第390页。本文以下所引《天圣令》录文皆本此。“每因外降户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条所载当作“升降户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页)。宋制,三年一推排户口财产,升降等第。
⑩ 《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4,第6463页。
(11) 《长编》卷2“建隆二年春”条,第43页。
(12) 《宋大诏令集》卷182《政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58页。
(13) 参见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14) 《旧五代史》卷81《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73页。
(15)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06《周礼折衷》,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67册,第905页。
(16) 参见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49—63页。
(17) 《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午”条,第472页。
(18)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令义解》,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年,第341页。
(19) 《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二月壬申”条,第829页,据《历代名臣奏议》卷159《建官》补正(四库全书本,第437册,第391页)。
(20)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2页。
(21) 杜佑:《通典》卷3《食货·乡党》,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4页。
(22) 《唐六典》卷5“职方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页。
(23) 《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月庚子”条,第2637页。
(24) 李元弼:《作邑自箴》卷4《处事》,四部丛刊续编本,第18页。
(25) 其法源于唐户籍制度。王溥:《唐会要》卷85《籍帐》载开元十八年敕:“其户每以造籍年预定为九等,便注籍脚,有析生新附者,于旧户后以次编附。”(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59页)
(26) 《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3,第4999页。
(27) 穆朝庆:《两宋户籍制度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4页;王育民:《宋代户口稽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110页。
(28) 李宝柱:《宋代人口统计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69页。
(29) 《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11,第5013页。
(30) 《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16,第5015页。
(31) 《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4,第4999页。
(32)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79页。
(33) 《长编》卷13“开宝五年三月乙酉”条,第282页。
(34)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1《户口考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3页。
(35) 王溥:《五代会要》卷25《帐籍》,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09页。
(36) 参见加藤繁:《宋代的人口统计》,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60页;李宝柱:《宋代人口统计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69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26页。
(37) 参见苏基朗:《宋代的户多口少现象》,《唐宋法制史研究》,第100页。
(38) 参见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9) 袁祖亮:《宋代户口之我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113—115页。穆朝庆:《两宋户籍制度与人口再探讨》,《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第103页。
(40) 天宝十三载为天宝三载之误。详见《旧唐书》卷9《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页;《通典》卷7《食货》,第155页;《唐会要》卷85《团貌》,第1555页。
(41) 既然以广德元年规定为准,《宋刑统》为何还要收载开元户令和天宝三载制节文呢?这牵涉到宋代法典的编纂体例,这样做是为便于今后立法官修改法律时作参考。例如天一阁藏宋《天圣令》,其编纂体例亦是如此“凡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4,第6463页)不用的唐令即附录于后。参见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71—86页。
(42)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1《保甲》,光绪十九年(1893)广雅书局本,第1页。“十五以上皆充”,《长编》卷218作“推以上皆充”,“推”为“稚”的避讳字。
(43) 唐宋法律在计算“以上”、“以下”时,是包括本数在内的。如《唐律》卷17《贼盗律》:“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原注: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其中16岁以上与15岁下是可以上下衔接的。据建隆四年制定的《宋刑统》卷12《户婚律》规定,宋以18岁以上为中,亦即17岁以下为小。至天圣七年制定《天圣令·户令》,可能对宋代的中的年龄时限作过调整,以15岁以上为中。到了南宋,以21岁成丁,相应的,中的年龄也顺延一年,以16岁以上为中。《庆元条法事类》卷75《侍丁·户令》条仅规定成丁年龄,省略了老和中的年龄内容,这是由于宋代条法事类体法典编纂体例所决定的,并非没有对老和中的年龄作规定。
(44)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48《赋役门·支移折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58页。
(45) 《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门·侍丁》,第790页。
(46)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47) 《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条,第5446页。
(48) 参见苏基朗:《宋代的户多口少现象》,《唐宋法制史研究》,第102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13~52页。苏基朗和吴松弟都曾正确指出客户纳入丁帐统计范围。不过丁帐与本文讨论的作为客户基本户籍的丁籍,具体说来还是有所区别的。
(49) 陈乐素:《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求是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葛金芳、顾蓉:《北宋五等版簿考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52页;王育民:《宋代户口稽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108页。
(50) 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63—70页。
(51) 洪迈:《盘州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249册,第328页。
(52) 吕祖谦:《宋文鉴》卷106《民议》,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418册,第1091页。
(53) 《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2,第5008页。
(54) 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15《官制门·考课类》,四库全书本,第937册,第207页。
(55) 李肪等:《文苑英华》卷747《食货论》,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册,第3907页。
(56) 《资治通鉴》卷212“开元九年正月丁亥”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44页。
(57)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1—62页。关于蒋化明的身份,唐长孺先生指出是浮游在外以驱驮为业的客户,括附为百姓后,并未受田,依然为驱驮。见唐长孺:《唐代的客户》,朱雷、唐刚卯选编:《唐长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29—530页。
(58) 《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56《赋役门·役类》,第784页。
(59) 《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第74页。
(60) 参见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13—28页。
(61) 《唐会要》卷83《租税上》,第1535页。
(62)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六月辛丑”条,第7282页。
(63) 《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戊寅”条。关于此条材料所言“居作”,从上下文意看,乃专指法律之服刑役而言,关于刑罚之居作,详见《通典》卷165《刑制下》及《宋刑统》卷2《名例》、卷30《断狱》缘坐应没官不没官门。不少学者未能细审,误认为是定居营作。
(64) 参见王育民:《宋代户口稽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108页。
(65)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夫亡而有子不得谓之户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3页。
(66) 《作邑自箴》卷6《劝谕民庶榜·状式》,第34页。
(67) 曾琼碧:《宋代佃耕官田的农民及其地位》,邓广铭、徐规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68) 参见高桥芳郎:《宋代中国的法制与社会》第1章第2部分“五等簿上的主户客户”,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16—18页。关于宋代客户属籍问题,还有一些日本学者的成果亦涉及之。然限于条件,未能寓目。
(69) 此山贳冶子撰、王元亮重编:《唐律释文》卷22,日本文化三年东京御书物所刻本,校以丛书集成本《唐律疏议》所附释文。关于此释文,通常认为是元朝人王元亮所作。实际上是北宋人此山贳冶子为《宋刑统》所作,后来王元亮将其编入《唐律疏议》。详见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61页。
(70) 胡宏:《五峰集》卷2《与刘信叔书五首》,四库全书本,第1137册,第128页。参见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1页。
(71) 《宋史》卷300《姚仲孙传》,第9971页。
(72) 《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66,第6453页。
(73) 毕仲游:《西台集》卷1,四库全书本,第1122册,第10页。
(74) 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54页。
(75) 参见穆朝庆:《两宋户籍制度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47—157页。
(76) 关于牛客、小客的客户身份,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31页;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116—117页。
(77) 参见戴建国:《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文史》第53辑,2000年,第143—153页。
(78) 《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16,第5015页。
(79) 《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19—20,第5017页。
(80) 详见前引穆朝庆、苏基朗、吴松弟等论著。
(81) 《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15,第6215页。
(82) 《文献通考》卷11《户口考二》,第116页。
(83) 高承:《事物纪原》卷1《版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页。
(84) 《庆元条法事类》卷12《封赠》,第253页。
(85) 穆朝庆认为丁帐统计的是全部男口(《两宋户籍制度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4页);苏基朗则认为丁帐报男丁总数给朝廷,所谓男丁是指成丁(《宋代的户多口少现象》,《唐宋法制史研究》,第103、104页);吴松弟也认为上报到户部的只是成丁(《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33页)。
(86) 《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庚辰”条,第106—107页。
(87) 《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11,第5013页。
(88) 《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16,第6215页。北宋则为20岁成丁。
(89) 《庆元条法事类》卷48《簿帐欺弊·赋役令》,第652页。
(90)《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16,第6215页。
(91) 《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31—32,第6345页。
(92) 《庆元条法事类》卷75《侍丁》,第790页。
(93) 例如陈襄《州县提纲》卷2《户口保伍》载:“县道,户口保伍最为要急……如一甲五家,必载其家老丁几人,名某,年若干;成丁几人,名某,年若干;幼丁几人,名某,年若干。”(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32册,第23页)又如洪迈《盘州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载:“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其丁多及老小者,以次增减。”其所云丁即指成丁。
(94) 《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7,第5001页。
(95) 《长编》卷277“熙宁九年九月辛巳”条,第6787页。
(96)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31“太平兴国九年十一月丁卯”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97) 《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31,第6345页。
(98)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71页。
(99)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类·户口》,四库全书本,第484册,第211页。
(100)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85、72页。
(101)《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26,第5005页。
(102) 张方平:《乐全集》卷21《论天下州县新添弓手事宜》,四库全书本,第1104册,第204页;《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7,第5001页。
(103)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177册,第181页。
(104) 《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7,第5001页。
(105) 吴松弟:《宋代户口调查统计制度史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第317页。
(106)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戊戌”条,第3105页。
(107) 《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6,第5000页。
(108) 《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2,第5008页。
(109) 《宋会要辑稿·食货》12之2,第5008页。
(110) 苏基朗:《宋代的户多口少现象》,《唐宋法制史研究》,第101页。
(111)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44页。
(112) 《庆元条法事类》卷47《税租簿·赋役令》云:“诸税租等第产业簿,以木长印每页横印,印讫,当职官躬临毁之。”木长印应是钤于户纳税簿之上的。因每户纳税额据户等高下而定,故户纳税簿又称“税租等第产业簿”。
(113) 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诸本所载税租簿格式,因错简而存讹误,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点校本已纠正。又,为行文方便,对原税租簿排版格式作了调整。
(114) 天圣三年规定的“每十户一计”,似为“每三十户一计”之讹。《作邑自箴》卷4《处事》:“逐一户长各具所管户口及都催税赋数,须先开户头、所纳大数(原注:谓三十户为计者)。”其中即云三十户为一统计单位。
(115) 参见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13~28页。
(116) 《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8,第5001页。
(117) 《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申”条,第2342页。
(118)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98《奏议》,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506页。
(119) 《长编》卷116“景祐二年正月丙午”条,第2719页。
(120) 详见《庆元条法事类》卷17《文书门·架阁》,第357页。
(121) 《庆元条法事类》卷47《税租簿》,第635页。
(122) 《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2,第4998页。
(123) 《庆元条法事类》卷47《税租簿》,第634页。
(124) 《唐六典》卷6“刑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85页。
(125) 《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乙巳”条注,第8254页。
(126) 《长编》卷13“开宝五年三月乙酉”条,第282页。
(127) 《庆元条法事类》卷48《税租帐》,第643页。
(128) 如何忠礼认为不报全体男口,穆朝庆、吴松弟则认为报全体男口。参见何忠礼:《宋代户部人口统计问题的再探讨》,《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50页;穆朝庆:《两宋户籍制度与人口再探讨》,《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第106—107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第45—46页。
(129) 苏辙:《栾城集》卷40《论户部乞收诸路帐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4页。
(130) 《长编》卷309“元丰三年闰九月庚子”条,第74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