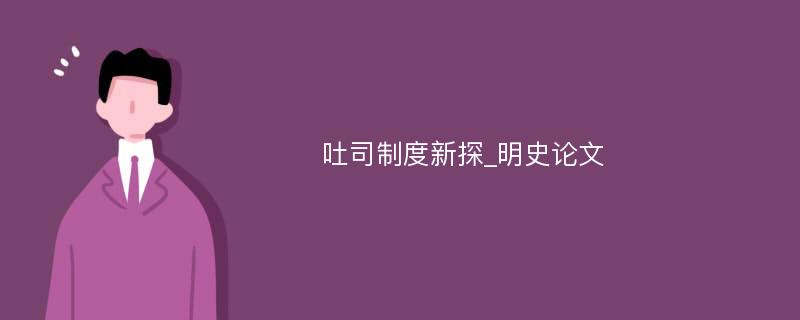
土司制度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司论文,新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土司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是地方行政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王朝对境内的一些特殊区域,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虽和前一时期在同一区域内实行的有关制度如唐宋时期羁縻府州制有着某种联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但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土司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使元明清时期的国家结构和前代相比也有了根本改变。本文拟就上述几方面问题对土司制度作一粗浅的探讨。
1
名目纷繁的南方少数民族被中原王朝势力不断向南挤压,分散在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中央王朝对他们的统治经历了一个从羁縻、有限“自治”到直接治理的过程。
在土司制度实施以前,中央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是羁縻政治。羁縻政策乃是中央王朝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对南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行笼络和怀柔,以换取他们对中央王朝形式上的臣服。如广西左右江地区唐时称太平羁縻州,宋平岭南分为五寨,各领州、县、峒,至明太祖遣使赍诏晓谕其地官民,说该地:“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1]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唐、宋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府州制是一种间接统治。中央王朝承认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为世袭的刺史,县令,但却既无意,也难以干预这些民族地区的内部事务。中央王朝并不将中原地区的法律制度推行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而是由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完全依其本民族的习惯法治理其各自的辖区。对南方各族间的矛盾,即羁縻府州之间的利益冲突,唐宋王朝采取的是一种晓谕、调解的做法,而不直接卷入双方的冲突。由此可见,中央王朝所扮演的仅仅是一个调停和斡旋的角色,连一个仲裁人的地位也不想去达到。总之,唐宋时期羁縻府州制度下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虽有某王朝的州县之名,实际上却形同许许多多“独立王国”,和内地州县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联系方面看,唐宋时期的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贡赐制度,即南方诸族首领依例按期遣使入京进贡本地区的土特产品,中央王朝则在他们朝贡后对其进行丰厚的回赐。朝贡和回赐虽然构成中原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往来,但更重要的则是政治上的意义。南方诸族首领以朝贡这种形式对中央王朝表示臣服,而中央政府则以相当数量的经济付出为代价,装扮出太平盛世的宏大气象。
综上所述,羁縻构成了土司制度实施之前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总的思想和总的原则,在这种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原本被分割的一块块南方民族地区实际上形同一个个“独立王国”就不足为怪了。
自南宋开始,除经济重心南移而外,政治中心也一度移到东南,这自然就产生了强化管理南方的要求。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统治力量的强化和南方各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加强,羁縻这种管理思想和原则已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土司制度应运而生。
在土司制度下,中央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就不再限于羁縻了,而是逐步适时地对其重大事务实行干预。如在土司地区官员的任命上,开始实行土流兼用的政策,“大率宣慰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县佐贰多流官”,[2]各级武职土司也各设流官经历、知事和吏目。[3]就是在鄂西南万山丛中,明初所设施州宣慰司及金洞、隆奉、忠孝、世德、平溪、东乡等五路长官司,皆“以流官、土官参用。”[4]至明成祖广设鄂西土司衙门之时,几乎没有一处不同时设流官经历或吏目。[5]就是万历年间修《湖广通志》和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时还“山水无考”的容美(今湖北鹤峰、五峰境),也设置了流官经历和吏目。[6]参用流官的目的虽主要是为了贯彻“用夏变夷”的企图,但中央王朝通过这些流官也达到了更有效地管理土司地区事务的目的。
在土司承袭制度上,明代土官虽可世袭,但如何承袭本身就有一个不断准确和详细化的过程。成化年间以前,土官袭职通过“本部移文、三司核实、定名会奏”[7]的程序即可。后由于云南土官因嫡庶之争而影响了该地区的统治秩序,朝廷令布政司牵头,“公核在职土官宗派嫡庶始末,详具谱图,岁造册籍,遇有土官事故,借此定之”[8]并将此制推广到南方其它民族地区。这实际上是以修谱牒为手段,全面向土司地区推行嫡长承袭制,以稳定各民族地区的统治秩序。明世宗对土司承袭问题十分重视,常就此问题举行廷议,并责成吏部和兵部会同商讨,终于制订出一个“画一之法”的“土官袭职条例”,并将其载入《明会典》。[9]从此,土官承袭完全走向了制度化和法典化,这些制度和法典使土司承袭完全掌握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
自元朝开始的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普遍地实行的赋税征收政策,标志着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强化了其统治,赋税和贡赐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赋税是封建国家组织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即强制征收,不存在返还的问题。贡赐制则完全不同,贡更多地表现为南方各族土官的一种自觉行为,赐则表现为较贡范围和价值大得多的返还,对南方各族土官而言,赐甚至可以说是贡的目的。正是由于贡赐制度对贡的一方十分有利,面对“朝贡人数日增,岁造衣币赏赉不敷”[10]的局面,中央王朝只得采用“减各夷入贡之数”的硬性规定,使入贡人数和频率被限制在一个既减轻自己财政负担,又能维护羁縻统治的恰到好处的水平上。明代来朝贡方物虽仍很盛,但对土官也“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使之“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11]
土司制度实施后,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赋税制度对强化中央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至少有两点意义值得肯定:一是户籍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是赋税征收的依据,这一工作使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人口和物产等资源信息有了初步的掌握,为日后的直接统治提供了前提;二是赋税征收的强制性,虽然其消极作用很大,体现了封建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盘剥,但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统治较前深化了一大步。
土司制度建立后,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地方武装力量土兵的征调成为中央在土司地区直接行使权力的一个明显标志。唐宋时期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虽也有土兵,但多用于守土,其功能主要是保境安民。到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已开始大量征调土兵参加各种与土司地区无直接关系的军事行动。元朝末年,苗帅杨完者统军前往江浙一带围剿张士诚。明代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几乎都与土兵有关,嘉靖年间的征倭和明末的援辽都投入了大量的土兵。在王江泾一役中,“保靖掎之,永顺角之,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东南战功第一云”[12]。抗倭的征调十分广泛,据《明世宗实录》湖广的容美、麻寮、桑植,四川的酉阳、平茶、邑梅和广西的田州、归顺州、东兰、那地、南丹的土兵,狼兵都曾参与抗倭,可称得上是“奔走惟命”,“每遇征伐……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13]。可见土兵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方面看,土司制度实施后,中原地区文化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的力度大大加强。在物质文化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直接统治成分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双方大规模的人员往来,汉族地区先进的物质文明随之加速流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从制度文化方面看,土司制度本身就是中央王朝结合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参用汉族地区官制的产物。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武职土司名称早已在内地出现过,至于土府、土州、土县等文职土官名称更是对汉族地区行政系列的直接改造。因此,土司制度本身就是中原制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司制度的顺利实施实际上是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制度文化的接受。随着土司制度的实行,其它中原制度文化也相继输入,如官员的考核、升迁等,虽其具体执行时的细节与中原地区有异,但已贯穿了其最基本的原则。
综上所述,土司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央王朝在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原则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时的中央王朝已不再满足于羁縻,而是加大了直接统治的成分,即由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单纯的羁縻,发展成为允许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在不违背中央王朝基本政策和法律的基础上实行有相当大程度的内部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土司制度“其道在于羁縻”的说法是欠准确和不全面的,反映出撰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的眼光的狭隘和思维上的因循。
2
从国家结构上看,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个王朝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复合制的国家结构,即一种邦国间的联盟。这主要表现在承认地方诸侯国的相对独立性。夏、商、西周王朝的天子实际上只是邦国联盟的盟主,他们在本邦国可以管辖本邦国的人民,却无权管辖别的邦国的公民。战国时期郡县地方行政体制出现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郡县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其特点是郡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而不是由世袭产生,国君通过郡县长官可将自己的权力一直延伸到社会最底层。秦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将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但应看到那时郡县制度的实施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主要局限于汉族地区,对于幅员辽阔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秦、汉、唐、宋诸王朝均无法实行郡县制度这种直接统治。如前所述,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虽以郡县命名,实际上仍是一个个独立的“邦国”,直到元代实施土司制度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土司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是继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度以后的又一次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上的重大举措。从此,郡县体制开始推广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从政治方面看,土司制度实施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唐宋羁縻州制下,中央王朝虽也任命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担任刺史、郡守、县令等一类地方行政职务,但更重要的是对他们颁与王、公、侯等爵位。这种王、公、侯等爵位在汉族地区大多仅仅是一些与具体职务完全无关的荣誉虚衔而已,但对尚未实施直接统治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这类称号使得这些地区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意味,而不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土司制度实施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后代土司虽也被封以各种虚衔,但仅包括勋阶、文、武散官了,也就是说,已和汉族地区官员的虚衔趋于一致。到明代,文武两系列土官都被纳入九品十八级的官阶之中,所不同的就是不给俸禄,但仍有实惠,官品高下决定入贡次数与来贡人员的多少和获得回赐的等第。除一般纳入九品十八级之外,文武两系土官还按兵部和吏部规定的散阶进级,土司之妻也得以封赠命妇。可见,在土司制度下,明代土官从官职,官阶、服色,乃至妻子的封赠命妇等第等都已被纳入朝廷命官的同一轨道。从行政序列上看,土司制度下武职土司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文职土官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的系列已整齐划一,并和内地地方行政系列基本趋于一致。因此,可以这样说,自从南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接受中央王朝授予的土司职务时起,他们双方已在统一的国家观念上完全取得了认同,土司地区已不再是独立的“邦国”,各级土司实际上已成为中央王朝任命的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了。
从经济角度看,赋税制度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王朝在土司地区征收赋税,尽管实行的是征收额很低的轻赋税政策,用明太祖的话说,广西全省甚至包括桂林、平乐等大片流官地区的财政收入尚不及江浙地区一个富庶的县,又如整个贵州地区,“赋不敌东南小郡焉”[14],但赋税征收本身的意义则十分重大。南方各少数民族人民通过赋税的征收所体验的是一种国民的义务,这对土司地区人民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反映出土司地区的地位已发生重大变化,土司统治下的土民已成为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土司地区地方武装力量的归属看,在土司制度实施后,大量土兵被频繁调出土司地区,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这说明土司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已成为当时全国统一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土司制度不仅和作为其渊源的羁縻府州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它还与同时期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统治方式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如当时在北方地区设置的一些卫、所、都司等,虽也可称得上是一种特殊行政区域,但其制度化程度较低。一旦中央王朝力量削弱,这些地区往往又很快恢复到往昔状态。而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中,各级土司作为中央王朝任命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官吏的地位并不随着中央王朝力量的盛衰而变化,甚至在元明,明清两度改朝换代之际依然未脱离土司制度的控辖,这说明土司制度作为一种地方行政体制已高度制度化。土司制度作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其基本精神即由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担任土司职务、实行有限度的内部自治这一原则,在其存在的四百年时间里保持着稳定性和延续性,得到了中央王朝和各级土司的共同遵循。
3
尽管土司制度的实施使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应该看到土司地区仍有其特殊性,和内地州县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这种行政区域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性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途径,即经中央王朝认可后由南方诸族上层人物世袭;二是其在经济上享受一系列的优惠,表现为贡赐制度中丰厚的回报和赋税制度中较低的赋税征收额。但也应当看到,从元代确立土司制度到清初实行改土归流,四百年的时间里土司地区的这些特殊性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其发展的总趋势和主流是随着土司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特殊性逐渐地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司制度实施的过程正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郡县体制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土司制度的实施标志着郡县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确立,但一个新制度的发展成熟则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而且在新制度实施的初始阶段必然遗留有大量旧制度的残余。就是在汉族地区,郡县制度的完善和成熟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其初始阶段,中央对地方的控驭也不是那样紧密。隋朝以前,地方长官拥有自辟属吏的权力,而且一旦中央力量被削弱,地方行政长官便乘势割据,甚至将地方官职作为世袭的对象,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和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中的情形正是如此。汉族地区尚且如此,地处偏远闭塞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在实施郡县体制时自然要经过一个更为长期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间保留许多旧制度的痕迹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土司制度中包含了大量的旧制度的残余,但应看到在其实行的四百年时期里,旧的羁縻性质的残余在逐渐减少,新的郡县性质的直接管理因素却在茁壮成长。
从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控制程度看,土司制度实施后,中央王朝不断扩大自己在土司承袭这一最关键问题上的权力,从制度和法律上加强控制的力度。明朝颁布了有关土司承袭的一系列制度和法典,到清初,中央王朝对土司承袭的管理更为严格,并在法律上禁止犯罪土司的继承人世袭继承土司职位,“土官受贿,隐慝凶犯逃入者,革职提问,不准亲子承袭,择本支叔伯兄弟之子继之;若有大罪被戮,即立夷众素所推服者,以继其职。”[15]
随着内地和土司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日益缩小,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经济优惠也处于不断地调整之中,其发展的总趋势是优惠的范围和程度在日益缩小和减弱。就贡赐制度而言,从唐宋时期单纯的贡赐制度发展为元明时期贡赐制度与赋税制度并存,到清朝初年事实上取消贡赐制度。贡赐制度的削弱乃至取消是和赋税制度的成长并行的,反映出土司地区和内地的差别的逐渐缩小乃至最后完全泯灭。贡赐制度的消失意味着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经济上的优惠仅仅局限于较低的赋税征收上了。
从上述也可以看出,土司制度的实施过程正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特殊行政区域逐渐丧失其特殊性的过程,即土司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换句话说,是土司地区郡县行政体制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清朝初年的改土归流正是土司制度的必然归宿,标志着土司地区郡县行政体制的最终发展成熟。改土归流之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除在赋税征收上享有一定优惠外,与内地已无差别和特殊之处了,土司地区这个特殊行政区域终于演变为大清王朝的一个正常行政区域。
综上所述,土司制度的实施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其意义是巨大的。这一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土司地区和内地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推动了土司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注释:
[1]《明史》卷318《广西土司二》。
[2][11]《明史》卷76《职官五》。
[3][5][6]《明太宗实录》卷55,88、266。
[4]《明太祖实录》卷70。
[7][8][10]《明宪宗实录》卷69、180、78。
[9]《明世宗实录》卷110,112。
[12]《明史·湖广土司传序》。
[13]《明史》卷310《土司传序》。
[14]《黔书》卷1。
[15]《大清会典事例·吏部一百二十九》。
标签:明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