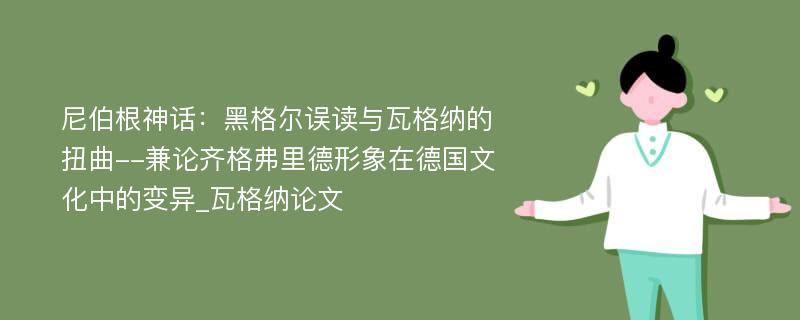
尼伯龙根神话:黑格尔的误读与瓦格纳的扭曲——兼论西格弗里的形象在德国文化中的异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格纳论文,黑格尔论文,误读论文,神话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4)04-0130-07
一、关于黑格尔对史诗背景的误读及其对西格弗里的反感
黑格尔也许是最不喜欢《尼伯龙根之歌》的德国人之一。黑格尔认为这部史诗不符合 自己的史诗理念;他也不喜欢史诗中的英雄西格弗里,这显然是由于西格弗里的形象有 悖于黑格尔的审美观念。但无可否认的是这部史诗里存留着顽强的日耳曼民族的基因, 它一次次地激发起这个民族雄起于欧洲民族之林的信心,当然也一次次受到这个民族伟 大思想家的批判与修正。它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是强大的,这是我们不得不重视这部史诗 及其文化蕴含的理由。
黑格尔似乎从本质上就没有把尼伯龙根的故事看作神话,他说在这部史诗中“看不出 一个明确的实在的形象鲜明的背景场所……我们感觉不到所描述的事迹如在目前,只感 觉到诗人的无能和使劲卖力。”[1](p121)
黑格尔在这里提出了《尼伯龙根之歌》缺乏“一个明确的实在的形象鲜明的背景场所 ”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对《尼伯龙根之歌》的否定性评价的主要原由。他认为这部 史诗没有能展示一个真实可感的社会生活环境,为此他把荷马史诗拿来比较,说:“《 尼伯龙根歌》在地理上是和我们德国人接近的,但是其中的布尔根德人和国王艾茨尔却 和我们现代文化的一切关系和爱国情绪都割断因缘了,乃至我们读起《尼伯龙根歌》还 不如读荷马史诗那么亲切,尽管我们对荷马史诗没有什么学问。”[2](p346)可以看出 ,黑格尔心目中显然有一个《尼伯龙根之歌》应该有的环境背景,这个环境应该与黑格 尔时代的德国社会显示出某种联系,正如他在论述“史诗的一般世界情况”时所做的更 详细的说明:
《尼布龙根歌》…其中所写的布根第人,克里姆希尔达的报仇,西格弗里特的事迹, 全部生活情况,全族覆灭的命运,北欧的人情风俗,厄泽尔王等等,都和我们现在家庭 、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生活以及规章制度没有任何活的联系。比起《尼布龙根歌》中的 事迹来,基督的传记,耶露撒冷,伯利恒,罗马法乃至特洛伊战争,对我们都还有较多 的现实联系。在德意志民族意识中,尼布龙根之类传说事迹都已一去不复返了[1](p124 )。
对史诗内容做那样机械地理解使得黑格尔丢掉了文学欣赏的态度,因而也无法接受史 诗的神话内容。我们可以把雅格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对同一个 问题的观点与黑格尔上述的话摆放在一起,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瑞士文化史学家实际 上是针对性地批判了黑格尔的观点:
如果要问在这些作品里是不是体现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从荷马和《尼伯龙根之歌》所 形成的关于史诗的理想,那是无聊的;它们自然是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理想[3](p321) 。
布克哈特显然认为史诗只能反映它自身形成时代的生活观念,而拿我们自己这个时代 关于这些史诗的观念去硬套原来的史诗,是不合理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黑格尔似乎 徒劳地在一部史诗中寻找一个民族残存下来的某些硬件的东西,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文化 人类学上的考古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阅读《尼伯龙根之歌》时的心态与阅读 荷马史诗时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注意到,当黑格尔说“尽管我们对荷马史诗没有 什么学问”的时候,他仍对史诗反映的生活表现出那样的亲切感,那才是文学欣赏的正 常心态。
但黑格尔在现今德意志民族和古代日耳曼民族间根本找不到这种联系上的硬件东西, 我们称之为社会生活的有形现象。《尼伯龙根之歌》出现于1200年,但史诗早在公元五 世纪就已形成,正是日耳曼民族由蛮族社会向封建时代急速过渡时期。自公元5世纪初 ,处于氏族公社晚期的日耳曼人就开始由西欧洲的北部不断向整个欧洲扩张,这一扩张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主要分化出三个主要分支:东日耳曼语,后来逐渐消亡,它包括 哥特语、汪达尔语、勃艮第语;北日耳曼语发展成为斯堪的那维亚各语种;而西日耳曼 语则衍化为后来的英语、法语、荷兰语、低地德语和高地德语[4](p68)。《尼伯龙根之 歌》中的西格弗里是尼德兰王子,显然属于这一族群分化的西支,而史诗的主要背景是 处在莱茵河一带的勃艮第王国,属于东支;换言之,《尼伯龙根之歌》的原创族属群已 经消亡。稍晚于黑格尔的尼采对此持同样看法,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指出:“ 所有的古代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更不要说血缘上的 联系了。”[5](p170)
黑格尔对《尼伯龙根之歌》感到隔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基督教文明和封建 文化的注入,这种新兴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因素迅速渗透到各新生民族的社会生 活中,将原来的蛮族文化内容迅速瓦解。
我们只能在与《尼伯龙根之歌》的产生相距不远的同一族群中找到黑格尔所期待的这 种认同。我们把《尼伯龙根之歌》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对照起来阅读,便可清 楚地看到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对日耳曼民族的生活实际上做出了非常生动的描写。塔 西佗生活于公元1世纪至2世纪之间,正值日耳曼民族发展壮大的时期,此时《尼伯龙根 之歌》尚未形成,因此,他对日耳曼民族的描述有利于我们了解《尼伯龙根之歌》产生 前的日耳曼社会生活。我们看到他在书中对日耳曼民族的描述与后来的《尼伯龙根之歌 》中的社会生活形象有一种惊人的契合,例如,他较为详细地描写了这个民族的地理位 置、民族来历和人情风俗:
……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他们只有突然冲动的勇 猛而不耐心于操劳和艰苦的工作,也决不习惯于忍受燥渴和炎热;由于气候和土壤的缘 故,他们对于寒冷和饥饿倒能安之若泰[6](p57)。
塔西佗所介绍的日耳曼民族尚处于原始的军事公社时期,大事由酋帅首先商议,然后 由全部落共同决议。书中以说明文的语气介绍了日耳曼民族简朴、尚武的民族性格,和 他们重视卜筮、尊重女性的习俗,这些民族传统的确深深渗入在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所描绘的生活画面中,例如哈根等武士对莱茵国王求婚冰岛和探亲匈奴等重大决策方面 实际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王本人的意志却显得暗淡。又如塔西佗在书中描述 了日耳曼人的婚姻制度,说日耳曼人的婚姻制度是非常严密的,“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中 没有比这个更值得赞扬的了。他们大概是野蛮人中惟一以一个妻子为满足的一种人”[6 ](p64),这甚至使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理解了《尼伯龙根之歌》中哈根对西格弗里的愤怒 ,因为那位大英雄的不良行为玷污了王后布伦希德贞洁的名声。实际上,与阿喀琉斯类 似“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行为方式相比,哈根的愤怒则含有更多的民族因素,他维护了 日耳曼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
黑格尔虽然承认《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人物形象有一定的成功之处,但在总体上对他 们却持否定态度,他的评价主要集中于史诗英雄西格弗里,他说:“皮上起茧的什格弗 里特,特洛伊的哈根甚至于音乐家浮尔考,尽管也是些强有力的个性,都显得黯淡无光 。”[2](p303)当我们仔细观察黑格尔对西格弗里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西格弗 里的反感主要在形式上,在他眼里这位史诗英雄已完全失掉了古代英雄的神话色彩。西 格弗里早年曾杀了一条毒龙,浴龙血而使浑身皮肤刀枪不入,这原本是一种原始神话中 的英雄特征,但这一特征在黑格尔眼中却变成了“茧”,一种粗糙物的象征。黑格尔还 用了一种令人不快的口吻说,“希格弗里德身上长了一层象牛角那样硬的皮”[7](p245 ),使人感到这位英雄身上仿佛有一些怪诞之处,像是某种妖兽。黑格尔是理性主义者 ,他对违反常识的怪诞描述当然决不欣赏。
但黑格尔在同一部书中对荷马史诗中具有同样特征的阿喀琉斯却赞不绝口。他认为, 相比之下,阿喀琉斯也是刀枪不入,但他仍算是勇敢的,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早死,却从 不避艰险。黑格尔欣赏阿喀琉斯,认为高贵的人格的多面性在这个人物身上显示出它的 全部丰富性。黑格尔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把阿喀琉斯与西格弗里相比,会发现阿喀 琉斯其实并不依靠或实际上根本没有利用他那刀枪不入的皮肤,他全仗自己的力量和勇 敢。而西格弗里虽然也有勇力,并且也未见其真正利用他的“硬皮”,他却实实在在地 利用了自己的隐形衣。并且,他的勇敢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对自己“不会被武器伤害 ”的倚仗。对于隐形衣,黑格尔也认为是这位史诗英雄身上的违反逻辑的做作的东西( 黑格尔说是魔帽):
希格弗里德身上长了一层象牛角那样硬的皮,也是不可损伤的,但此外他还有一顶魔 帽,戴起来就没有人能看见他。在隐形中他帮助耿特王和布伦希尔德作战,这就是只凭 野蛮的魔术,不能替耿特王和希格弗里德的勇敢增加多大光彩[7](p245)。
二、关于史诗中的封建主义原则与日耳曼民族精神
黑格尔对西格弗里的反感应当有其内容方面的原因,只是他并没有谈到这一点。但如 果我们重新观察一下这位西格弗里的形象,我们便会承认这位英雄实际上是令人失望的 。西格弗里的时代特点,在于他是一个封建制度确立时的臣子形象,而封建制度的最大 的特征就是渗透到人们灵魂中的等级观念。作为臣子,他必须忠诚主子。西格弗里最初 是尼德兰王子,他第一次来到勃艮第宫中时曾是一派王者风度:
我要把你所有的一切夺取过来,你的土地和城池,全都要听我主宰[8](p25)。
但他既然决定为恭太王效力,便只能以一个臣子的形象要求自己。西格弗里自愿扮作 家臣,竭尽全力包办了恭太王的整个婚姻过程——在恭太王求婚时为他牵马,穿起隐形 衣帮他比武,甚至帮他在洞房里制服勇武暴烈的冰岛女王布伦希德。从这个意义上,我 们可以从西格弗里的隐形衣上发现一种象征,它隐去了他作为尼德兰王子或尼德兰国王 的身份,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家臣;他的行为绝无原始英雄如阿喀琉斯的光 荣,有的只是封建家臣乃至东方皇宫太监的卑琐与忠顺。
而当我们把西格弗里定位为封建时代的武士,我们又发现他身上其实还有许多与封建 武士格格不入的东西,其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他在洞房里制服了布伦希德后,顺手 牵羊,偷了她的戒指和腰带;而他的妻子克琳希德便以此羞辱布伦希德,硬说这位尊贵 的王后被西格弗里破了身。西格弗里这一毫无意义的行为揭示了他性格的另一侧面:这 位英勇无敌的武士、谦恭的臣子同时还是一个心眼儿狭小或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儿童, 他根本不曾想到他的行为实际上对布伦希德已构成了死一般的威胁,因为日耳曼人有着 重视婚姻、禁绝私通的传统。塔西佗这样描述:“通奸的案件算是极少的了。他们对于 奸淫的处罚是毫不容缓的……有些部落的风俗尤其可嘉,在那儿只有处女可以结婚;当 一个女人作了新娘以后,她便不得再有任何其他妄想了。她们只能有一个丈夫,犹如只 有一个身体、只有一次生命一样,因此她们不会三心二意。她们不是为了寻找丈夫,而 是为了结一次婚。”[6](p64-65)可见,西格弗里在儿戏之间便毁掉了一个民族最尊贵 的女人的最受关注的贞洁声誉;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毫无意义的恶作剧把自己摆在了一 个民族的敌对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格弗里虽然进入了封建时代,接受了这个时代 的观念,却仍不免时时回归于一种童稚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他陶醉于自己膂力与魔 力的无敌,却将封建原则与日耳曼传统精神一并丢掉。以这种观点,我们便可以认为, 史诗对西格弗里的表现实际上是赞美与批评并重的。
而当我们用同样的观点观察哈根全部的行为,我们便可以看出哈根是这部史诗歌颂的 真正英雄。哈根其人,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野心家的形象,是恶人,是正面英雄西格弗里 的对立面。但哈根与西格弗里的冲突并不能构成哲学上的善恶二元对立,因为他们原本 是相容的,一致的,而西格弗里只是由于自己的行为低级而远逊于哈根。
根据史诗中的情形来看,哈根并不是道德上的坏人。按史诗的描写,特别是后一部分 写莱茵勇士与匈奴人的冲突中,哈根其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英雄,他不知失败,不怕死 亡,即使在极度绝望的环境中也保持着乐观精神。史诗对这个人物也充满了歌颂,表现 他在渡过莱茵河后悲壮的誓言,在匈奴国中英雄的气概和勇敢的战斗,以及在失败被俘 后宁死不屈的高贵气节。
当然哈根的行为也确实存在道德问题,最明显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背后行刺西 格弗里,这种自古以来被人痛恨的懦夫行为使他很难被文学欣赏者所认同;二是杀死了 匈奴王艾柴尔托付给他的儿子奥特利布,这种杀死无辜的行为违反了人类依循的道德观 念。在后一种行为中的道德色彩也许不那么严重,因为在古代的政治活动中处死人质更 可能是一种常规的操作:匈奴王艾柴尔将儿子奥特利布托付给哈根实际上是古代政治活 动中的一种人质行为,他以此向已经产生了危机感的尊贵客人承诺他们的安全,而克琳 希德既然已破坏了艾柴尔的承诺,杀死人质在哈根一方不存在道德问题。当然,哈根还 有一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例如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用人血解渴,不过这种“渴饮匈 奴血”的行为毋宁被看作一种壮举:当克琳希德极尽卑鄙地纵火、莱茵勇士全部陷于火 海而万般无奈时,哈根带头喝敌人尸体里的血,并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的勇士们坚持到 胜利。
这样看来,哈根的污点实际上只在上述第一种败德行为,即背后行刺,但即使这样, 史诗仍然赋予哈根某些正义性。西格弗里偷走了王后的戒指与腰带,还不顾尊严地将此 事讲给了自己的妻子克琳希德,这使西格弗里的精神在哈根眼里严重下降:他既不是忠 臣,也够不上男子汉,实际上已经为族群所不齿,因而哈根选择那种阴险的行为方式时 自己却并不觉得堕落可耻。另外,可以推知,哈根选择那种不义的方式杀死西格弗里, 于他自己也有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哈根论勇力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逊于西格 弗里,但西格弗里胜过哈根的地方乃是外力:他浑身刀枪不入,他穿上隐形衣时便增加 十二倍的力气;而哈根则除了自己的勇气、膂力、意志与心智以外全无外力可借,于是 他用了背后行刺的方式把西格弗里拉回到同一个对话平台上,用心智抵御了西格弗里超 自然的能力部分。
史诗实际上把哈根写成了一个真正的日耳曼英雄。哈根的英雄气质首先表现为他的成 熟,他具有那种识大体、讲原则、服从理性的英雄性格。当西格弗里来到莱茵国,哈根 立刻判断出这就是那位杀了毒龙、取了尼伯龙根宝物的大英雄,并且从莱茵国的利益出 发从内心里接纳了这位英雄,因此他劝阻了恭太王迎战西格弗里的决定;哈根还推荐西 格弗里前往迎战入侵的萨克森人,推荐西格弗里随往冰岛陪同求婚,实际上是把这些重 要的荣誉都安排给了这位英雄。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哈根的良苦用心:当恭太王决意前 往冰岛求婚时,他原本是想让母亲乌台来准备求婚的服装,但哈根却建议由恭太王之妹 克琳希德来做;在恭太王求婚成功、一行人胜利返乡时,哈根又一次推荐西格弗里,让 他先行回去报喜。哈根这些建议和推荐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是在促成让西格弗里与 克琳希德的爱情并使他们终成眷属。这说明哈根对待西格弗里的初衷是想接纳他。这样 看来,在哈根与西格弗里的冲突中,责任的一方在西格弗里而不在哈根。哈根对西格弗 里与克琳希德的婚事的热心往往被阐释为一种阴谋行为:根据神话,西格弗里与冰岛女 王布伦希德曾有婚约,只是他完全将婚约从记忆中忘却(瓦格纳在《尼伯龙根的指环》 中将其表现为哈根用魔力的作弄)才转而向恭太王之妹克琳希德求婚。但根据史诗中的 情形来看,哈根这样做至少是没有包藏祸心的,因为西格弗里的悲剧原本产生于他扮家 奴、偷腰带等一系列行为,而对于这些行为,哈根在当初既不能预料又不能操纵。所以 ,哈根促成西格弗里与克琳希德婚事的行为只能解释为他对国王利益的忠诚。
而史诗中哈根形象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深重的义气,这是封建时代英雄的最高境界— —关云长义释曹操,依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等级观念,而是封建精神的最高原则 ——义气,那种生死相托的信任与视死如归的气概。他挑战神明,毁弃船只自绝后路, 用必死的预兆向武士们做了悲壮的战前动员,并且在战斗最激烈、几乎面临死地时也坚 信英雄们一定能安然回到勃艮第,这说明他根本否定了神谕,而只相信自己的意志和力 量。哈根并不回避自己背后行刺的羞耻,他大义凛然承担罪责,“我就是哈根,是我杀 死了西格弗里”,声称这是西格弗里必须为自己的过错付出的代价;这也说明哈根心中 有着更强大的精神支撑:那就是坚决承担一个臣子应尽的责任,而完全忽略事件是否将 给他个人带来的羞耻。哈根的封建义气最光彩照人的地方,表现为他与匈奴的一个方伯 路狄格的不幸冲突,其慷慨豪壮竟不逊于中国的关云长:他原本与路狄格相互有恩义, 不得不厮杀时,却是英雄惜英雄。他从路狄格手中接过了盾牌,替下手中被打烂的那块 (原本也是路狄格所赠),发誓说厮杀中决不碰路狄格一下,他们的义气让参战的勇士们 血红的眼中热泪涟涟;而他在被俘后也是慷慨斥敌,拒降而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哈根用生命完成的是一个封建时代精神与一个日耳曼精神统一的 英雄形象。哈根和西格弗里一样进入了这个时代,并且接受了这个时代严格的等级观念 ,只是,在哈根的潜意识之中尚涌动着日耳曼人的血液,那个暴烈的日耳曼之魂在哈根 生命的最后时刻转变到了哈根心中的另一层面上,那便是铅一般灰冷的毁灭情结。
然而哈根背后行刺的恶劣行为终于使他无法成为德国文化中的正面英雄;德国文化只 能将这个民族的英雄形象寄托在一个性格单纯、勇往直前的西格弗里身上,但这就使人 面临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一个童子军式的少年英雄无法体现出一个民族对成熟的英 雄性格的自我认同。这个矛盾在渴望英雄的浪漫主义时代终于被解决了,德国音乐家瓦 格纳根据尼伯龙根神话创作了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剧重塑了西格弗里的形 象,他仍是那样无敌无畏,他拯救布伦希德的行为使他成了德国青年心目中完美的英雄 ,他的形象因此而完整地代表了德国文化的英雄认同。
但从另一方面看,瓦格纳音乐剧中的西格弗里的死而不已的毁灭行为实际上已溶进了 哈根那铁血般的性格。
三、关于瓦格纳对尼伯龙根神话的重新建构
瓦格纳结合北欧神话对尼伯龙根神话做了全新的处理,创作了四部曲歌剧《尼伯龙根 的指环》。与史诗相比,瓦格纳的这部歌剧是全然浪漫主义的,剧中建构了一个类似古 希腊俄林波斯神系的神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于大神沃旦的弄巧成拙而演化出人间的恩怨 与悲剧冲突,最后是天国里火光熊熊,诸神与天国宫殿同归于尽,因而该剧表现出强烈 的浪漫主义反叛精神。
瓦格纳按照德国民族对英雄西格弗里的热爱之情塑造了这位古代英雄的形象:他力大 无比,从不知何为恐惧;他奋杀巨龙,染其血而懂鸟语;他爱情炽烈,冲入火焰解救了 被困的布伦希德。至于西格弗里背叛布伦希德转而追求国王之妹的事,瓦格纳用了类似 迦梨陀娑开脱豆扇陀的方法,让他中计饮下了哈根的药酒,失去了记忆。在瓦格纳的剧 中的西格弗里是极其辉煌与伟大的,他的死是全剧的高潮,这时布伦希德骑马跃入大火 ,为他殉情而死。
《尼伯龙根的指环》在神学层面上又高扬了欧洲浪漫主义时代的反宗教精神。首先, 它展示的神的世界是一个原始多神教的世界,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一神教思想形 成鲜明对照。进而,在这个北欧神话的神灵世界中,神的形象是虚弱的、愚笨的,这一 点尤其值得注意。歌剧中大神沃旦全无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伟力和魅力,他以女爱神弗里 雅为报酬请巨人法索尔特与法夫内为他建造瓦尔哈拉宫;之后悔约,又改许以尼伯龙根 指环,而所有灾祸皆因此而起;另外,他虽然不及宙斯的伟力,却也像宙斯一样惧内, 一样为命运女神所摆布。
《尼伯龙根的指环》正是在这两个形象间展开了冲突。大神沃旦是正统社会理性的象 征,它因自身虚弱无奈而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它实际上象征着已经堕落的封建德 意志既有的秩序;冲突的另一方是西格弗里,他则是浪漫主义的革命意识的象征,体现 着瓦格纳的革命主张,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反抗——他来自血缘的婚配,他从不知恐惧为 何物,这些形象化的语言都是这一非理性反抗精神的阐释。
因此同史诗中的西格弗里相比,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西格弗里形象已被重新 建构:瓦格纳删除了西格弗里扮家奴、偷腰带等不光彩的行为,而从出身开始便赋予他 以神话英雄的了不起的特征。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西格弗里的父母成了大神沃旦 的一对孪生儿女,西格弗里于是成了真正意义上乱伦的产物(尼采指出,这一激烈特征 的创造者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瓦格纳[10](p28)),但这却使他与古希腊的传说英雄有了 同样的出身特征。不过,实际上西格弗里的反抗者形象与十八、十九世纪之间的欧洲浪 漫主义文学运动中其他的反抗者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例如英国诗人雪莱的《解放 了的普罗米修斯》,其中反抗神王朱庇特的赫拉克勒斯。雪莱的这部长诗的主题不仅在 于反抗,而且在于建设,他的思想远远地延伸到未来的时代,那里美好的人间共和国已 经实现。但瓦格纳的反抗者却毁灭了一切:他毁灭了邪恶也毁灭了英雄。在这全然毁灭 的悲剧中,瓦格纳高扬了浪漫主义的最神圣的旗帜——爱情,它不是爱情的相悦与心心 相印的甜蜜,而是对非凡情感的无限渴望。当爱情因受阻而无限郁积时,它就变成了这 样一种渴望,它所要求的不再是获得与占有,而恰恰是爱情惊天地泣鬼神的精彩展现, 在那样一种意志的实现中获得情感的满足。
瓦格纳这种很“另类”的爱情至上论触怒了一位大思想家,这就是尼采。尼采曾是瓦 格纳音乐的崇拜者,但终于与瓦格纳决裂,为此写了小册子《尼采反对瓦格纳》和《瓦 格纳事件》等,而尼采与瓦格纳的决裂恰发生在瓦格纳即将完成《尼伯龙根的指环》谱 写的时刻:
随着《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谱曲工作的即将完成,特里布申的田园生活也到了尾声。1 872年4月24日瓦格纳、科西玛和孩子们动身离开特里布申前往拜鲁伊特,尼采赶来作他 的第23次探访。他似乎已预感到随着特里布申的移主,他与瓦格纳的友谊也到了破裂的 边缘,他不由悲伤地写道:“特里布申已经不复存在”[9](p135)
从《瓦格纳事件》中可以看到尼采对《尼伯龙根之歌》极为不满。尼采把这部作品的 主题解释为拯救,而且是内涵极狭窄的拯救。他指出,西格弗里的主要事业是解放妇女 ——拯救布仑希德,他说:“无疑瓦格纳一直沿着这条航线寻找他的最高目标。”[10] (p28)但他认为瓦格纳的拯救主题并不成功:“轮船撞上了暗礁,瓦格纳搁浅了。这暗 礁便是叔本华哲学。”[10](p28)抱着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却诉诸道德,去完 成对一个堕落的旧世界的拯救,这是艺术在思想内容上的症结所在,而这在尼采看来是 极端可笑的,他把这种精神状态看作是一种颓废,因为它是“贫困的生活,求虚无的意 志,极度的疲惫,”是“道德否定生命”[10](p16)。
尼采准确地把握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在主题上的谬误之处。首先是英雄的出身与行 为方式:
他[即西格弗里—引者]的出生就是对道德的宣战——他是通奸和乱伦的结果。但中世 纪和北欧的传说里并没有这样说,是瓦格纳自己创造出了这一疯狂的人物,由此他修正 了传说。…齐格弗里德自出生后就继续革命:他只遵从他的第一本能,他将传统、敬畏 、恐惧全都掷于风中,所有不中他意的东西他都要将之打倒。他肆无忌惮地攻击神祗[1 0](p27)。
尼采的这一阐释让我们看到瓦格纳的西格弗里作为浪漫主义反抗者的形象具有非凡的 原动力和盲目性,并且他的反抗将导致全然地同归于尽。从这一点出发,尼采甚至完全 否定了瓦格纳的歌剧创作,认为其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都是极有害的:其艺术风格只是 一系列无序的震撼,用文章来比喻,就是“词语受到重视,从它们所从属的句子中跳出 来;句子也非法越出边境,模糊了整个段落的内容,而整个段落又顺次以牺牲全文为代 价取得优势地位,从而整体不再是整体”[10](p36)。其思想内容极为颓废。尼采还说 :“我和瓦格纳一样是时代的孩子——即我是一名颓废者。惟一的区别在于我正视这个 事实,并与之相抗争。”[10](p15)
尼采把瓦格纳的西格弗里一下子扔到了半空,让他无足轻重地漂浮在那里。如果我们 把尼采的批判与尼伯龙根史诗中那个隐起形来专干些丢英雄身份的勾当的西格弗里联系 在一起,我们差不多要对西格弗里嗤之以鼻了。
我们又想起史诗中的哈根。瓦格纳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改造了哈根的形象,他着 力表现了哈根的卑鄙:哈根受其父阿尔伯里希的指使,要夺取指环,进而控制整个世界 包括天国;为此他配药酒改变了西格弗里对布伦希德的爱情,他诱使恭太王之妹克琳希 德对西格弗里产生爱情,并使用奸计弄成了恭太王与布伦希德的婚姻,最后,他还亲手 刺死了恭太王。
《尼伯龙根之歌》中不共戴天的“双雄”终于被改造为《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一正 一反两个形象:最大的英雄和最阴毒的小人。可怜的哈根实际上成了一个小丑,他原本 所具有的那深重的义气、无敌的气概和坚忍的性格完全被删除了。
然而哈根精神不死。史诗中的哈根就是一种无可阻挡的意志,这种精神恰恰适应了十 九世纪德国民族的精神;这个民族在法英等先进文化的压抑下正以一种高度自尊的心态 骤然崛起,因此相对于这个民族而言,哈根的精神最为符合这种民族精神。可惜,这个 形象致命的负面因素——背后行刺,一种与英雄主义决然无缘的行为——使他无法成为 一个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代表形象。
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恰恰完成了这种精神协调,被删除的哈根的精神被附加 在西格弗里身上。这是一个超级英雄,他因被删除了那些不光彩的行为而变成了一个重 新诞生的德意志宁馨儿,他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冲破德意志陈腐的空气的一切阻碍,去追 寻爱情或拯救事业的精彩展现;与这一崇高目标相伴的,正是《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西 格弗里或《尼伯龙根之歌》中哈根的激烈心态:要求自己意志的全然顺畅或毁灭一切。
于是我们联想起塔西佗对日耳曼民族凶暴好战性格的描述,联想起纳粹对欧洲毁灭性 的打击。我们试图思考,德意志民族何以生长出纳粹精神,那样一种以毁灭为喜悦、以 意志的顺畅为最终目的的铁血性格呢?我们眼前便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德国青年隆隆踏 响的脚步伴随着瓦格纳狂暴的音乐,直令大地发出颤抖,激情的青年甚至把尼采的警告 抛到半空,他们冰冷的目光中已透射出哈根式的死亡阴影。
我们至今可以从二战文学的德军将领乃至希特勒本人的形象中看到《尼伯龙根之歌》 中哈根的这一毁灭情结的阴影,特别是当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些狂热于毁灭的法西 斯党徒为何狂热地崇拜瓦格纳的音乐?这使我们联想到尼采的说法,他认为:“瓦格纳 征服这些孩子用的并不是音乐而是那个‘意念’,是他的艺术的迷幻和朦胧,一百个扑 朔迷离的象征意义,多色画法彩饰起来的梦想。瓦格纳就是用这些诱骗误导了青少年们 。”[10](p48)瓦格纳对《尼伯龙根之歌》的重新建构从深处唤起了一代德国青年的英 雄认同感,因为“德国的年轻人——长角的齐格弗里德和其他瓦格纳的追随者——要求 宏大的、深厚的、势不可当的东西”[10](p32),而瓦格纳则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自己与 生俱来的崇高、深刻和伟大;一代德国青年显然是在这样的狂热的鼓动之中接受了那个 “欧洲新秩序”的观念,并以那种毁灭一切的行为方式去建设那个新秩序。
他们本来要崇拜的是豪勇多情的骑士西格弗里,但瓦格纳的音乐刺激早已轰毁了他们 的理性,让他们实际上是对着《尼伯龙根之歌》中铁血的哈根顶礼膜拜;他们全然忘却 了哲人尼采的批判。尼采说:“追随瓦格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0](p56)
收稿日期:2004-03-08
标签:瓦格纳论文; 尼伯龙根之歌论文; 西格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神话论文; 布伦希尔德论文; 德国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