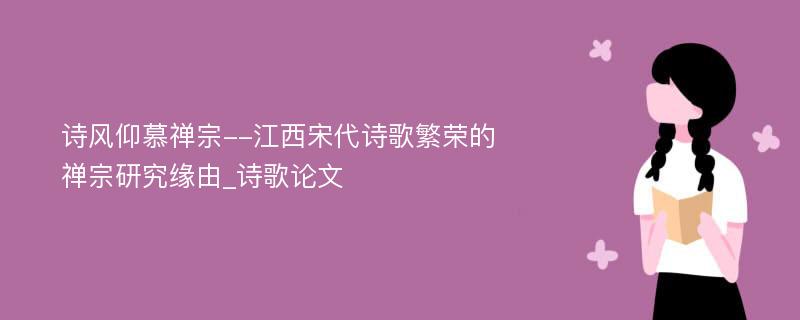
诗风慕禅——江西宋代诗歌繁荣的禅学因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江西论文,因缘论文,宋代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1)02-0037-07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曾经说过:“要知诗客参江西,正似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1](《送分宁主簿罗宏才秩满入京》)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看出当时江西诗坛在全国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这首诗也透露出江西诗派与禅宗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江西诗派的得名固然与其领袖人物黄庭坚的籍贯有关,但同时也与江西是南宗禅滋长繁衍的基地,诗派中成员大多是南宗禅的忠实信徒分不开。南宋时期,继江西诗派而起的是杨万里。他不但跻身“四大中兴诗人”,而且享有“四海诚斋独霸诗”的盛誉。尽管杨万里完全摒弃了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旧路,而将目光投向了活泼的现实生活,但其“诚斋体”中同样可以找到禅宗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整个宋代江西诗坛的繁荣,都是与禅宗的沾溉之功分不开的。其中“诗风慕禅”,则可以视为这种沾溉之功的具体表现之一。所谓“诗风慕禅”,无非是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禅学化的审美意趣。在笔者看来,这种禅学化的审美意趣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闲适淡泊的超然心态
众所周知,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一个最基本的禅学观点便是“即心即佛”。禅宗大师神会在滑台论辩大会上回答什么是“僧家自然”这一问题时就认为:“僧家自然,众生本性也。”这就是说,只要依本性行动,即可以成祖成佛。这是南宗禅的佛性论,更是他们所推崇的至高无上的人生哲学。正是依据这一禅学观点,所以百丈怀海才得出了修禅的过程为:既不求佛,也不求理智;既不怕地狱苦难的威胁,也不必羡慕天堂乐趣的诱惑,一切都不必拘泥,这就叫解脱无碍。葛兆光先生在谈到南宗禅的这一特点时曾作过如下分析:“我心是佛——我心清净——依心行动——适意自然,这种宇宙观、时空观、人生哲学、生活情趣极为精致的结合,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顺序十分自然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慧能、神会之后,几乎每一个禅宗大师都要大讲这种适意的生活情趣与现世自我精神解脱的人生哲学。”[2](P106)笔者认为,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言,禅宗最吸引他们的或许正是这种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淡泊超然的人生哲学。表现在诗歌创作当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作者在对自然物的观照中,往往显露出一种禅意盎然的闲适心境。在宋代江西诗人中,开这种风气之先的是著名诗人王安石。
王安石晚居钟山,读经参禅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据说他对禅宗经典《楞严经》特别倾心,曾撰写《楞严经》疏解,颇多心得体会。正是在这种参禅活动中,王安石的诗歌摆脱了早、中期作品通常具有的那种功利和实用色彩,转而在诗中表达出对闲适淡泊的生活情趣的向往和追求。如: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得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1](《游钟山四首》之一)
山花如水净,山鸟与云闲。我欲抛山去,山仍劝我还。[1](《两山间》)
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艇倚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1](《定林所居》)
在诗人的笔下,山、水、风、云、花、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禅宗闲适淡泊的人生意趣。毫无疑问,只有在退隐钟山、服膺禅宗的人生哲学之后,王安石才可能用这种不经意的“平常心”去看待自然万物;而自然万物也只有在这种充满着“平常心”的观照中,才可能显现出那种舒卷自如的恬淡之美。用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1](《赠僧》)。
到了“江西诗派”诗人的手中,闲适淡泊的心态更成了他们诗歌吟咏的重要主题。如:
已透云庵向上关,熏炉茗碗且开颜。头颅无意扫残雪,毳衲从来著坏山。瘦节直疑青嶂立,道心长与白鸥闲。归来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峰烟霭间。[1](李彭《寄希广禅师》)
倚空栏楯一禅关,衲子幽人得往还。樵径盘纡秋草里,僧堂结构野云间。旧穿虎落婵娟净,晚泊龙沙舴艋闲。如许澄江写寒鉴,明朝乘兴上西天。[1](洪朋《晚登大梵院小阁》)
晚辞富贵功名士,竟作东西南北人。早岁衣冠如昨梦,平生笔墨累闲身。时情尺水翻千丈,世故秋毫寓一尘。自有使君天下士,新诗挥扫唤人频。[1](饶节《次韵赵承之殿撰二首》之一)
本不因循老镜春,江湖归去作闲人。天于万物定贫我,智效一官全为亲。布袋形骸增碨磊,锦囊诗句愧清新。杜门绝俗无形迹,相忆犹当遗化身。[1](黄庭坚《次韵戏答彦和》)
在上述诗篇中,闲适淡泊的心态随处可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宋神宗之后,新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残酷的官场倾轧,文网森严、仕途险恶迫使士大夫不得不暂时压抑自己“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1](欧阳修《镇阳读书》)的政治热情,以便全身远祸。在这种情况下,禅宗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和旷达清静的生活情趣自然最合他们的口味,所谓“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2](P163),其实并非黄庭坚个人的自赞,而是江西派诗人的共生相。有的江西派诗人走得比这更远,像饶节干脆在39岁时削发出家,摇身一变,成了云门宗的香岩如璧禅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接受禅宗的人生哲学是江西派诗人最合乎情理的历史选择。既然禅宗的人生哲学已经被江西派诗人所接纳,那么在诗歌中表现闲适淡泊的情趣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除了江西派诗人之外,江西宋代其他的一些重要诗人也大多在诗作中表现出类似的情趣。像著名的诗僧慧洪就曾经反复吟唱:“花枝重少人甘老,燕子空忙春自闲”[1](《晚步归西崦》),“野僧自是闲,不复知闲味”[1](《次韵曾侯庵僧》);杨万里的《诚斋集》中,也不难找到“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1](《闲居初夏午睡起》)之类的诗句。总之,我们认为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加上禅悦之风的炽盛,已经铸就了宋代江西诗人内向谨慎、淡泊闲适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表现在诗中自然不再是火热情感的宣泄,而是一种精致的充满着禅学智慧的人生情趣的流露。这样,也就无形中拉近了诗人与禅宗之间的心理距离。
二、平淡简放的艺术风格
与闲适淡泊的生活情趣相联系,受到禅风熏染的宋代江西诗人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平淡简放的艺术风格。葛兆光先生在谈到禅宗的人生哲学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时,曾精辟地分析说:“在这些禅诗中,感情总是平静恬淡的,节奏总是闲适舒缓的,色彩总是淡淡的,意象的选择总是大自然中最能表现清旷闲适的那一部分。如幽谷、荒寺、白云、月夜、寒松,而不是暴风雨、阳光、桃花、骏马。……他们崇尚清静的本心,信仰这颗本心的自然流露,因此,诗画常常挥手而出,不加雕饰,显得天真、自然而又有些草率。”[2](P123)我们认为葛兆光先生对禅诗审美情趣的总体评价同样适合于宋代江西诗歌的艺术风格。以王安石为例,他前期的诗风直露、雄奇、劲峭,后期的诗风则深婉清新,自然平易。试看其《示董伯懿》一诗:
穿桥度堑只闲行,咏石嘲花亦漫成。嚼蜡已能忘世味,画脂那更惜时名。长干里北寒山紫,白下门西野水明。此地一廛须十筑,故人他日访柴荆。[1]
在这首诗中,我们再也看不到王安石早年那种火热的政治激情,流露出来的只有淡泊功名和向往归隐的出世之情。这种思想情感上的变化,无疑是与他晚年热衷参禅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伴随着思想情感的变化,王安石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于是出现在诗中的自然是平易简放的艺术风格。这种平易简放的诗风在王安石晚年所作的一些绝句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如: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红,两山排闼送青来。[1](《书湖阴先生壁》)
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无。[1](《慎真院》)
这些充满自然天趣的小诗,风格平易简放,丝毫找不到斧凿之痕。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只有这种风格的诗歌出现,才真正确立了王安石在宋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荆公之诗,实遵西江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中,其绩尤伟且大,是不可不尸祝也。”[3](《王安石评传》)就诗风而言,我们认为梁启超先生所说的“荆公诗”,主要是指王安石晚年创作的那些风格平易简放的绝句小诗。这种推论绝非臆测。早在宋代,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黄庭坚就说过:“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4](P234)
或许正是由于受到过王安石的影响,所以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也走过了一条与王安石极为相似的道路。黄庭坚早年的诗歌风貌以新奇拗峭为主,晚年的诗风则趋向平淡简放。这种平淡简放既表现为意象的平淡而意蕴深远,又体现为语言的简易而意味无穷。就意象而言,黄庭坚前期的诗歌以刻意求奇、求新为最大特点。据《王直方诗话》记载,黄庭坚早年自认为最得意的诗句不外乎“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1](《题落星寺》)和“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1](《汴岸置酒赠黄十七》)之类的“奇句”。这类诗作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在意象的奇特上下功夫。后期的诗歌则体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如《新喻道中别元明用觞字韵》:
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获稻午风凉。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1]
在这首诗中,黄庭坚完全是以一种充满生活情调的笔墨,抒写出了自己内心复杂的人生感慨,并将这种复杂的人生感慨寓于平淡的意象之中。这种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无疑是诗人晚年“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见解的一种具体实践。黄庭坚在《梦中和觞字韵》的小序中就曾经说过:“崇宁二年正月己丑,梦东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间,予谓寄元明觞字韵诗数篇。东坡笑曰:‘公诗更进于曩时。’”[1]这实际上从侧面证实,黄庭坚晚年诗歌意象由新奇转为平淡,乃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与追求诗歌意象平淡相一致,黄庭坚晚年诗歌的语言也一改早年的瘦硬而变得貌似简易,实则意味深长。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跋子瞻和陶诗》: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1]
这首诗作于1101年,当时黄庭坚在荆州读到了苏东坡的《和陶诗》,不由感慨万千,于是当即写下了这首和诗。诗中的情感极为深沉,而用语却十分平淡,甚至连“饱吃饭”、“细和诗”之类的口语都出现在诗作之中。这种情况与山谷早年造语新奇、典故繁富的创作风格简直判若两人。类似的例子在山谷后期的诗作中可谓俯拾即是。诸如“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1](《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兄弟”[1](《竹枝词》)之类的诗句,无不具备简易平淡、明白流畅的语言特色。
继黄庭坚之后,在宋代诗坛上影响最大的大概莫过于杨万里的“诚斋体”。尽管杨万里宣称“诚斋体”是对江西诗派的反动,他在《荆溪集序》中曾经表白说:“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安石)、陈(师道)、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但杨万里摒弃的主要是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弊端,相反对于黄庭坚等人诗作中平淡简放的风格不但未予抛弃,而是把它发展到了极端。杨万里诗歌的意象以日常生活和山川风物为主,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1](《小池》)、“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1](《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语言则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入诗,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1](《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前者使得杨万里的诗歌富有生活情趣与美感,后者则使他的诗歌显得轻松活泼、新颖风趣。
从北宋中期的王安石,一直到南宋中期杨万里的出现,这是江西诗坛“云蒸霞蔚”的黄金时代。在这长达2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江西诗坛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但对于诗歌风格的平淡简放则一直是江西诗人不懈的追求。即便是在素以“资书以为诗”著称的江西诗派雄霸诗坛时期,这种追求也未停止过。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禅宗影响的结果。从理论上看,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首倡的“平常心是道”,一直是江西禅宗信奉的佛性论。在这种佛性论影响下,“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业已成为当时江西禅门士子共同遵奉的人生信条。以黄庭坚为例,他就十分向往“无山而隐,不褐而禅,听松风以度曲,按舞鹤而忘年”[5](《赵景仁弹琴舞鹤图赞》)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充满禅意的人生态度,促成了黄庭坚晚年诗风趋向平淡简放。山谷贬居戎州时说:“但观子美到夔州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5](《与王观复书》)这既可看作是对杜诗的评价,也可视为山谷晚年诗歌风格的“自白”。黄庭坚如此,杨万里也不例外。尽管杨万里自称“平生学仙不学禅”,但其诗论和创作同样无不深受禅学影响。其“诚斋体”诗所强调的通俗化的特点,完全可以看作是禅宗“平常心是道”的佛性理论在诗歌领域的集中体现。而事实上,杨万里所写的那些通俗诗篇中的语言,有的还直接从禅宗语录中借用而来。比如杨万里《竹枝歌》中“须遣拖泥带水行”一句中的“拖泥带水”四字,便是禅宗语录中常见的话头。承天惟简禅师就说过:“师子翻身,拖泥带水。”[6](P1009)
三、审美意象的哲理化
倘若说唐诗的特点重在神韵,那么宋诗的特色则重在理趣。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审美风尚在江西宋代诗歌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理学的兴起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从本质上探根究源的话,人们还得承认禅宗的兴起才是这种审美风尚形成的内在动因。大致从中唐时期开始,士大夫禅悦之风鼎盛和诗僧队伍崛起构成了江西这片土地上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宋代江西诗坛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便是参禅的士大夫和习诗的僧人长期双向交流的必然结果。从习诗的僧人来说,他们必然会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的引导下,逐渐养成以形象化的手段来表达他们对禅理的感悟。这种情况发展到禅宗演变为五宗七派之后,无不竞相以诗偈来说明各家禅理。杨岐派著名禅师白云守端就在一首诗偈中写道:“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7](《林间录》卷下)诗歌完全借用形象的语言来阐明诗人关于佛理不在佛经而在对“本心”顿悟的见解。从习禅的诗人来说,参禅的经历必然使他们的诗作无形中充满一种禅意盎然的理趣。王安石晚年所作的《记梦》诗写道:“月入千江体不分,道人非复世间人。钟山南北安禅地,香火他日供两身。”[1]诗歌阐释的无非是玄觉禅师《证道歌》中“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的禅理。上述情况足以表明,江西宋代诗歌繁荣是与禅宗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伴随着诗、僧双向交流进程的加快,禅理、禅趣开始在诗中大量出现,并最终导致了江西宋代诗歌审美意象哲理化特征的形成。动态地考察江西宋代诗歌审美意象哲理化特征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其间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用诗歌的形式直接阐释禅理
尽管从总体上看,宋代诗歌、包括江西宋代诗歌在内,审美意象哲理化的发展水平已远远高于唐代而渐趋成熟,但就江西宋代诗人的具体情况而言,他们诗歌的审美意象还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以王安石、黄庭坚、慧洪等著名诗人为例,他们的诗集中就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直接用诗歌形式阐释禅理的作品。如:
本来无物使人疑,却为参禅买得痴。闻道无情能说法,面墙终日妄寻思。[1](王安石《寓言三首》)
骑驴觅驴但可笑,非马喻马亦成痴。一天月色为谁好,二老风流只自知。[1](黄庭坚《寄黄龙清老》)
眼不自见宁见物,去来不见宁见今。万物只今全体露,镜里有空无路寻。[1](慧洪《读大智度论》)
上述诗作中,王安石的作品指责了面壁坐禅的修行方式而肯定了自性清净的禅法,黄庭坚和慧洪的诗作则从不同侧面肯定了南宗禅自身即佛、无需外求的佛性论。其中“骑驴觅驴”还是禅宗最常用的“话头”之一。如《景德传灯录》卷28《神会大师》:“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更觅驴。”同书卷9《大安禅师》:“即造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骑牛觅牛。’”[7]此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采用诗歌的形式直接阐释禅理,它们与禅师惯用的偈颂并无本质区别。就诗的审美特征来说,这些作品由于过多地采用了充满宗教意味的意象而缺乏必要的审美观照,因而显得理胜于辞、诗味索然。不过,此类作品虽然艺术价值不高,但它们在诗歌审美意象哲理化进程中的作用却不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对禅偈禅理的心慕手追,造就了诗人看待世界的哲理眼光,从而形成一种以诗明理的时代风气。
(二)寓禅理于诗歌的审美意象之中
毫无疑问,就一首优秀的禅诗而言,它必然是将抽象的禅理与具体的意象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成功之作。沈德潜所谓“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8](P259),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王维《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向来就被称为这类诗歌的典范之作。陶文鹏先生对此曾精辟地分析说:“这两句之妙,还在于深蕴禅机、理趣。在佛家眼里,白云的无心无意,舒卷自如,悠悠自在,无所窒碍,正是所谓‘不住心’、‘无常心’、淡泊闲趣、安详自足等禅意的象征。”[9](P144)考察文学史可以发现,虽然唐诗中出现了上述类型的诗作,但远未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只是到了宋代,特别是江西诗派的出现之后,伴随着文字禅的流行和诗人禅悦之风的盛行,融禅理、禅趣于诗歌的审美意象之中的做法才真正发展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试举数例分析如下:
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觅,莫觅无心处。[1](王安石《即事三首》)
王安石晚年在参禅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将有限的个体自觉地融入到无限的自然当中去,才可能使心灵得到净化,而且融入并非刻意追求,而是一种不经意的“无心”之作。不难理解,这种“无心”的闲适实际上完全可以视为禅家适意自然、任运随缘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诗性显现。在这种诗性显现中,作者所体悟到的禅理、禅趣已与诗歌的审美意象“钟山之云”完全融为一体,以至于使得“无心”这一禅语也完全成为诗中审美意象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再给人以“隔”的感觉。
风生高竹凉,雨送新荷气。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一挥四百病,智刃有余地。病来每厌客,今乃思客至。[1](黄庭坚《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
这首诗非常生动地写出了黄庭坚病愈后的禅悟体验。黄庭坚之所以在病后能进入这种“风生高竹凉,雨送新荷气”的清净境界,原因就在于他病中参禅时有了深刻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驱使黄庭坚用一种充满禅意的眼光去观照世间万物,于是自然界中的“鱼游”和“鸟语”也显得那么禅趣盎然。特别是诗歌尾联“病来每厌客,今乃思客至”二句,更是深蕴禅机。按照禅宗的观点,悟道后若能以一种“平常心”入世,则生活中将会无时无处而不自适。这两句诗实际上正象征悟道后的诗人由超凡脱俗转入一种任运随缘的境界。可见在这首诗中,黄庭坚所要表现的禅意、禅趣同样是熔铸在诗歌的审美意象当中的。
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西。[1](杨万里《桑茶坑道中》其七)
杨万里这首充满生活情趣的小诗,乍一看来,似乎与禅理、禅趣无关,实则不然。正像王琦珍先生在《中国禅诗鉴赏辞典》中所分析的那样:“在禅门中,‘牧牛’原指养心。”[1](P848)《五灯会元》卷3《南泉普愿禅师》载:“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拟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1](P137)杨万里这首小诗,显然是从上述禅典中受到过启发,只不过将禅意盎然的人生体验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充满生活情趣的审美意象当中,显得了无痕迹而已。
从以上数例诗作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将禅理融入诗歌的审美意象当中,到宋代确实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宋诗审美意象的哲理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角度说,此类诗作的蔚为大观完全可以视为以表现宗教教义为主旨的偈颂诗与表现审美情趣为旨归的禅意诗的正式分野。由此再向前迈进一步,那种超越宗教意味而带有更普遍人生体验的哲理诗也就呱呱坠地了。
(三)人生哲理与诗歌审美意象浑然一体
相对于芸芸众生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所体悟到的人生哲理来说,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禅理毕竟显得过于单一而且缺乏生气和活力。江西宋代诗歌审美意象的哲理化作为一种主要立足于世俗生活的文学现象,它必然要从较为狭窄的表现禅理、禅趣走向表现人生哲理这个更广阔的空间。事实上,江西宋代诗歌中那些在文学史上久盛不衰、生命力极强的作品,往往正是那种人生哲理与诗歌审美意象浑然一体的诗篇。试看几首这方面的名篇佳作: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1](王安石《登飞来峰》)
人事好乖当语离,龙眼貌出断肠诗。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诗悲。[1](黄庭坚《题阳关图》之二)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1](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王安石在千寻高塔上体悟到的是人生只有放眼高处,才能不为浮名所累;黄庭坚面对龙眼居士所作《阳关图》中的渭城柳色,所想到的是别离之情与关情之物的内在联系;杨万里身临崇山峻岭,感受最深的则是人生道路多险阻。毫无疑问,无论是千寻高塔、渭城柳色,抑或崇山峻岭,诗中出现的这些客观物象,都绝非纯属作者偶然捕捉到的事物的表象,也并非作者主观情感瞬时观照外物而产生的意象,而是经过诗人长期的人生体验和理性思考后所感悟到的人生哲理与客观物象之间的一次契合。由于这种契合带有浓郁的审美色彩,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契合着人生哲理的物象是一种哲理化了的审美意象。宋诗的理趣,很大程度上就存在于此类审美意象当中。这也就是说,凡是称得上富有理趣的诗,都必然是人生哲理与审美意象浑然一体的佳作,或者说是人生哲理的诗性显现。此类诗歌,虽是用诗说理,但又不乏生动感性的形象。人们在品读这类作品时,不但不会感到乏味,相反还会产生出一种如食橄榄般的无穷回味。
收稿日期:2000-12-22
标签:诗歌论文; 王安石论文; 杨万里论文; 黄庭坚论文; 宋朝论文; 江西诗派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禅宗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