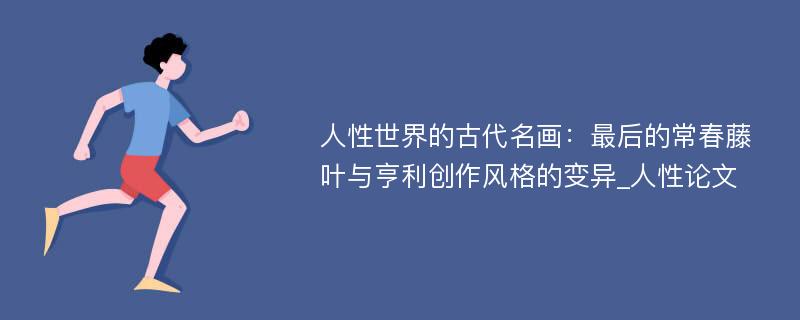
人性世界的千古名画——《最后的常春藤叶》与欧#183;亨利创作风格的变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常春藤论文,名画论文,千古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表于1905年10月15日纽约《世界报》星期日版的《最后的常春藤叶》,是欧·亨利人性基督小说的代表作。它问世近一个世纪来,一直为历代读者所津津乐道,已经成了脍灸人口的世界名著。
歌颂人性美的小说,是欧·亨利文学创作的主流,其中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基督式人物,表现了作家对人性理想的执著追求。而这种理想追求,则是跟欧·亨利从小在文学艺术的熏陶中接受人道主义和宗教意识的影响,以及在此后所经历的基督式的人生苦难分不开的。因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在揭露社会生活的不公平、不合理、不正常和同情下层社会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着力挖掘和赞美小人物的伟大人格和高尚品德,塑造个性鲜明的人性基督形象,展示他们向往人性世界的美好愿望,以耶稣基督的博爱之本,万善之源,献身之体,建构人间地狱的神圣的人性天堂。《最后的常春藤叶》里的贝尔曼,就是这样的一位人性基督。他是一位老画家,一生穷愁潦倒,郁郁不得志,却能爱护、关怀青年画家的成长而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最后的常春藤叶”救活了危在旦夕的女画家的年轻生命,为人性世界留下了一幅千古名画。
小说故事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离奇的情节,用来描写的语言也十分质朴,洗练,篇幅极为简短,但它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原因何在?即在于内容主旨所蕴涵的人情味与人性美,在于“欧·亨利手法”所常用的白描语言和杠铃结构——以白描语言绘写千古名画,用杠铃结构展示人间的苦难和人性的温暖,让千古名画在人性世界散发人性美与人情味的芳香,小说因而充溢着一种动人的凝炼美,蕴蓄美。
小说开篇,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贫病交加的生活场景:在纽约的华盛顿广场西区,连街道都“发了狂似地”相互交叉弯折成许多小胡同,形成无数的角度和曲线,以致使得前往收讨颜料、纸张和画布欠款的商人“转弯抹角”、“大兜圈子”误入歧途而一无所获,因而吸引了大批发现此中“可贵之处”的穷艺术家。他们“逛来逛去”,在古色古香的格林威治村寻找“低廉的房租”,由此而组成了一个“艺术区”,一个底层社会小人物的世界。小说中的老画家贝尔曼就租住在“楼下底层”,已经落拓到给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以糊口度日的地步。而两个少女画家则“联合租下”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屋的顶楼——她们一个来自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一个来自遥远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为了生活背井离乡而萍水相逢,艺途相投而相依为命,不得不靠替杂志社画短篇小说的插图来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就像这些小说是青年作家为了铺平文学的道路而创作的一样。穷愁潦倒,更有病魔肆虐。萧瑟悲秋,冷酷无情的不速之客“肺炎先生”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这是一幅典型的欧·亨利式的背景素描:“凄风”,“苦雨”,“枯萎”,“虚弱”,“困倦”,“飘落”,“黯淡”,“惨白”,“寂寞”,“狭窄”,“残缺”,“倒塌”,“光秃秃”,“空荡荡”,“阴沉沉”……这些景象,意象,虽然没有工笔画的具体描述,但唯其如此,那一笔一画,有比喻,有拟人,有议论,有抒情,简约而含蓄,所勾勒的虚幻迷离的纽约大都市底层社会的轮廓,则更具概括力和象征性,因而才由这些零散的意象情景组成一个魔幻世界的象征体,构成了欧·亨利式的“地狱”。
“地狱”里有琼珊痛苦的呻吟。一个弱小的女孩子,本来“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当然经不起那“有着红拳头,气吁吁”的肺炎病魔的致命一击。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脸色惨白”、“活像一尊倒塌下来的塑像”,望着荷兰式小窗外对面砖屋的墙壁,断断续续倒数着被秋风吹落的的藤叶……她要看那“最后的藤叶飘落下来”,好让自己也随着最后一片叶子飘然而逝:“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悠悠地往下飘,往下飘。”这里喊出的是人生的哀鸣,虽然微弱,虚幻,但它却是对现实不满、失望而从内心迸发出来的一声强有力的控诉!琼珊是一个为老画家所称赞所疼爱的好姑娘。她有理想,总想有一天能够去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海湾;又很纯洁,连一点有关男人的心事都没有。但是,眼前“空荡荡、阴沉沉的院子”,恰如她伤感情怀的写照,是这样的失落,空虚,灰暗;那一株纠结的根“已经枯萎”得只有“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残缺的砖墙上”的“极老极老”的常春藤,正是她病态心理的对应物,是这样的衰秃,悲凉,绝望。她好比秋风中的枯叶一片,正飘向神秘遥远的终极世界,那悲观厌世的玄想正使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关系“一片片地脱离”,因而人世间没有比她的心灵更沉寂更荒凉的了。这是魔幻世界的受难者,正是她,象征着千千万万底层社会小人物不幸的命运。这是小说情节的发源地,正是她,引来了医生而从“地狱”带出了一个人性世界,一个人性基督。
情节带引的过程,就是杠铃结构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的过程,就是杠铃上的“横杠”。而“那一头”就是意想不到的起死回生——它来自人性基督“最后的常春藤叶”。因而反复渲染琼珊病势的危急,无望,想死,以及苏艾的关切,焦虑,照料,是欧·亨利所运用的“蓄势”手法,以给“最后的常春藤叶”作好铺垫,让“横杠”把杠铃的“两头”接连起来。在小说开头就正式登场的医生,虽是一个仅出现两次的跑龙套角色,但在结构上却举足轻重,杠铃的两头都有他特殊的作用。铺垫的第一块基石,就是他安放的——他“扬扬”“蓬松的灰眉毛”,告以琼珊的病“只有一成的希望”,作了一通病情分析就走。此后即有苏艾侍候“病孩”的无微不至和“病孩”一心想死两者矛盾纠葛的情节,在铺垫中拓展。但又于曲处暗伏一笔:“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这一伏笔很重要,有了它,铺垫才有方位,蓄势才有动力,“最后的常春藤叶”的起死回生才有照应,杠铃结构的两头才有呼应。“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但确切地说,是身处“地狱”的琼珊不想活下去。她一无所有,连去画那不勒斯海湾的心愿都无法实现,空荡荡得没有任何感情牵挂,没有一点生活留恋,就连想活下去的那一成希望也是没有的。医生尽管表示要“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他”,却还是担心每逢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殡的时候”,就得把医药的治疗效果“减去百分之五十”。因而强调要让她对生活有所依恋,比如说“使她对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提出一个问题”,这样就可以保证她康复的机会“提高到五分之一”。由此即成蓄势,推动铺垫的步步进展。铺垫的第一块基石,有着医生人品的闪映:医道精明而心地善良,诊断恳切而富于哲事。虽只有一两笔的勾画,却跃然纸上,引人注目。
医生离去,铺垫即由苏艾和琼珊承接。苏艾先是哭了一场,“把一张日本纸餐巾擦得一团糟”;又抑制和掩饰自己的悲伤,“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音乐调子。昂首阔步地走进琼珊的房间”;以为她睡着了,又“赶坚不吹口哨”,悄悄架好画板作画;发现有想死的念头,又编了一套“好的希望”的假话来安慰她。在这里,苏艾所能给的,除了体贴、温暖、照顾、还有“红葡萄酒”,“猪排”……但一心想死的琼珊对苏艾的一片真心,苦心,却无动于衷。她只管躺着“凝望”窗外,倒数着掉落的藤叶:“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等最后一片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又掉了一片。不,我不要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落下来。那时候我也该去了。”……在寒秋风雨中,藤叶越掉越多,琼珊越数越少,这时候读者的心也就越揪越紧,因为无论如何,常春藤叶是敌不过“秋风扫落叶”的命运的,迟早是要掉光的,这样,琼珊也将随之而逝,而她正青春年华,怀有美好理想!由此也牵动了苏艾无限悲痛的心情,发出“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我可怎么办”的呼唤。这一呼唤,又使读者心里为之一震——为即将“撒手人寰”的琼珊痛惜,为患难之中见真情的苏艾感动。一个是万念俱灰而一心想死,一个是精心护理而提心吊胆,两个人物性格相互对比映衬,于双向铺垫中又互为交缠,几笔白描勾勒而神态尽出,得到相得益彰的刻划。就像是苏艾为短篇小说画钢笔插图是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一样,这两幅人物素描也完成了向杠铃结构“另一头”的铺垫——出现了“最后的常春藤叶”;
……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叶了。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这简直是奇迹,不可思议!原来,琼珊从“差不多有一百片”叶子开始倒数到“只剩四片”,数了三天,等了一天,就只等“最后的藤叶飘落下来”,却想不到这“最后的常春藤叶”竟能战胜“秋风扫落叶”的命运,而且历经了一天一夜秋风秋雨秋雪的侵袭而顽强地“依附在茎上”!这一突然出现的奇景奇观,从欧·亨利的蓄势中崛起,是欧·亨利出人意外的“结尾”,它给苏艾、琼珊以至读者带来的,又何啻是绝处逢生的惊喜!就在“结尾”之处,埋藏于前的“一成希望”,如伏兵出击——永不凋谢的“最后的常春藤叶”,给琼珊死寂悲凉的心境射进了一线阳光,为她垂危绝望的病体灌注了新生的活力:她,“要活下去”!从此,她走出了魔幻世界,迎来了启示世界——她悔疚地对苏艾说:“冥冥中有什么使那最后的一片叶子不掉下来,启示了我过去是多么邪恶。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于是,医生的治疗有了效果,“好的希望有了五成”。你看,她多么兴奋,对苏艾如孩子般撒娇:“现在请你拿些汤来,再弄一点掺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用枕头替我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煮东西。”一小时后,竟又重提她隐藏已久的心愿:“苏艾,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这是琼珊生活中唯一“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是她一种强烈的艺术追求,看似顺带一笔,却表达了“要活下去”的信念与决心,同那“一成希望”正是相映成趣的照应。而这种照应,却又是为了渲染与烘托“最后的常春藤叶”的奇迹,以此形成新的“蓄势”,继续新的铺垫,把突然弯曲的情节,拐进奇迹奥秘的深处——但奇迹奥秘的深处,又打下一个埋伏:当医生抓住苏艾高兴得“颤抖的手”肯定了琼珊“好的希望”之后,却又说:“现在我得去楼下看看另一个病人。他姓贝尔曼——据我所知,也是搞艺术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病势来得很猛。他可没有希望了……”这里埋伏了一个悬念:怎么青年画家琼珊的肺炎刚有“好的希望”,老画家贝尔曼又突然“也是肺炎”而“没有了希望了”呢?这就是杠铃“横杠”所要连接的“另一头”,也正是小说情节所要到达的另一个“结尾”。医生在这里发表的病情报告,跟在开头发表的病情报告,刚好在杠铃的“两头”,一“开”一“合”,前呼后应。至此,一个人性世界,已经由一片“最后的常春藤叶”一托而起,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当大悬念中谜底一旦揭开,则如太阳冲出了迷雾,照耀了人性基督形象,让人性世界大放光明。
谜底,是主题所在,它是由苏艾揭示出来的;贝尔曼,是主题的寄托,他又是苏艾牵引出来的。这好比是大杠铃结构中的小杠铃结构,苏艾又如医生一样在“两头”一“开”一“合”;而其中由贝尔曼谱成的人性基督的赞歌,又好比是短篇小说中的“小小说”,在结尾处汇合,重叠。“小杠铃”出现在“大杠铃”的“后头”,“小小说”诞生于短篇小说“人性世界”之中,贝尔曼的行动又为琼珊病危想死所触引,这就使“小杠铃”的“前头”跟“大杠铃”的“前头”在两相呼应中彼此关联;而“小杠铃”的“后头”与“大杠铃”的“后头”则由苏艾于结尾处的“转述”而合二为一。这种欧·亨利式的情节走向,时空处理,画面组合,节奏变化,同中有异,直中见曲,平中出奇,别出心裁,新意独创,颇有审美意趣和诗学特征,直接作用于小说结构的架设而富于魅力。然而这一切都是为贝尔曼的出场而惨淡经营,都是为“最后的常春藤叶”而背面敷粉,都是为人性基督的施爱,行善,献身而创造的典型环境。
因而贝尔曼虽是寄托主题的主要人物,却露面很迟,是在其他人物都登场表演,作了充分的“铺垫”活动、有了足够的“蓄势”力量之后,才告以琼珊“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而被苏艾“叫”上来的。欧·亨利不惜用了小说的过半篇幅,以准备我们的人性基督出场。而对他的形象绘写,也只有寥寥几笔的白描速写。从“肖像”速写中,我们看到他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上的胡子,从那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萨蒂尔似的头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形体怪诞而带神秘色彩,生活困顿却整天借酒浇愁,性情古怪,脾气暴躁,火气十足。这是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了一辈子的饱经风霜的小人物,也许他有着琼珊类似的境遇,也是从外地流浪而来,在纽约举目无亲,过着逃亡一般的生活,只能以格林威治村作一生的坟墓而把自己扭曲成这幅怪模怪样。从“心理”速写中,我们看到他极端瞧不起人家的温情,却把自己当作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凶狗”——虽对琼珊“满脑袋都是稀奇古怪的念头”发出“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的咆哮,但他那“充血的眼睛”却在“迎风流泪”;虽对苏艾嚷着“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可怜的小琼珊……”但还是替苏艾当了模特儿,“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口翻转过来的权充岩石的铁锅上,扮作隐居的矿工”。原来,这个瞧不起人家温情的怪老头,内心却充满了温情!——在他的“咆哮”里,有爱的爆发;在他的“流泪”里,有善的流露。也许,他的“最后的常春藤叶”的构思,就是在这爱与善的交流中涌现的;而到了跟着苏艾“上楼”,望着窗外雨雪交加中的常春藤,那“担心地”一“瞥”里,也许,他的“最后的常春藤叶”就已经成竹在胸了。从“事业”速写中,我们看到他在艺术界是一个失意的老画家:“他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是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他虽“老是说就要画一幅杰作”,但由于现实的无情,生活的嘲弄,命运的不公,却使他始终无法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外,别无成就。因而在他楼下那间“酒气扑人”而又“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的“一幅空白的画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了二十五年”!除了贫穷,不幸,还有一生中艺术与生活的距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苦苦地折磨着他,狠狠地打击着他,这是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所难以忍受的,而他却一直忍受着,等待着。他毕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希望。他热爱绘画艺术,爱护青年画家,有助人之善,有伟大抱负,仍然坚信“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他虽是艺术上的失败者,却是生活中的强者,最富生命力的画家,所以最终才有不朽的“最后的常春藤叶”的杰作问世……构成小说中的“小小说”的这几幅白描速写,虽用的是简单的笔墨,却勾画得相当精美,传神,带有强烈的肖像性与个性化的特征。这里同样也运用了“蓄势”的手法——极力渲染贝尔曼一生中的潦倒、落魄和艺术上的失意、失败、突出描述贝尔曼对青年画家的爱心与善举,以及为人的怪僻与顽强,也正是为“最后的常春藤叶”奇迹的出现作好铺垫,而让“小小说”的“小铺垫”与前面的“大铺垫”接轨,“小蓄势”与前面的“大蓄势”汇合,归结为最后的“献身”速写——苏艾向琼珊转告老贝尔曼的死讯而最后完成了欧·亨利式结尾:
“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里,他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地方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支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这是“最后的常春藤叶”的配画诗,是欧·亨利为贝尔曼描绘的人性画,是另一幅不朽的杰作!它又是一个照应,如电光一闪,把医生在前埋伏的的悬念谜语点明,把小说主题照亮。因而我们和两个青年画家一样,直到最后才明白,原来,永不掉落的那一片“最后的常春藤叶”是画上去的,是老贝尔曼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和一生的艺术创作出来的千古名画!
奄奄一息、一心想死的肺炎患者琼珊,从“最后的常春藤叶”汲取了生命的活力,赢得了新生,而对生活有着坚定的信念、对艺术有着执著追求的“看家凶狗”老贝尔曼,却因不愿琼珊听凭“可恶的藤叶掉落而想死”,在雨雪之夜被肺炎夺走了生命,无声无息“撒手人寰”!一生一死,其契机全在于一片神奇的“最后的常春藤叶”!这“最后的常春藤叶”,是欧·亨利的“意料之外”,又在欧·亨利的“情理之中”,既有突变逆转的心理震撼,也有奇峰突起的艺术感染。罗丹说过:“要点是感动,是爱,是希望,战栗,生活。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作一个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创作出“最后的常春藤叶”这样的不朽杰作,在世态炎凉、充满铜臭的魔幻世界为人消灾化难而自我牺牲,成了“失意的人”“耍了四十年的画笔”的艺术结晶,是贝尔曼落笔在静候“二十五年”的“空白的画布”上真善美的丹青,是老画家走向艺术女神而为之奉献的无与伦比的珍品!它融进了老画家的博爱之本,万善之源,献身之体,因而才涵蓄着无穷诗美的动情力,闪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辉,使人性基督辉映人间,千古名画永世留芳!
名著以小人物的命运去表现人性的重大主题,篇幅简短紧凑而容量博大精深,写得平易亲切而感人肺腑,充分发挥了短篇小说以小见大的艺术优势,显示了欧·亨利作为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的文学天才。契诃夫说“写得有才华就是写得简短”。高尔基认为“最大的智慧在于字句的简洁”。还说:“要写得简练,紧凑,写最主要的东西,而且要写得像钉子进木头那样,一切都钻入读者的心中”。杀尔尼雪夫斯基也说:“紧凑——是作品美学价值的第一个条件,一切其他优点都是由它表现出来的。”这里说的,就是短篇小说要求更高的艺术概括,也就是鲁迅所强调的“蕴蓄”二字。伟大作家的艺术见解和艺术实践都是相通的,他们所指出的也正是欧·亨利的创作风格。欧·亨利就主张创作要“简单、明白和不加修饰”。这也正是鲁迅的白描观:“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这篇小说堪称典范。它简洁到还不上五千字,却能涵纳生动而又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而显示出内在的意蕴和诗的神韵;又能把小说的灵魂和艺术的重心安排在结尾部分,在突出形象和点明题旨之后戛然而止,让人内心猛受震荡而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欧·亨利创作风格给我们带来的强烈的审美感受和莫大的艺术享受。然而,在欧·亨利小说中,这却是一篇很有独特性的名著,艺术手法有别于其他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它是欧·亨利创作风格的一种变异。这里,欧·亨利固有的俏皮、风趣、逗乐和嘲讽,都不见了,有的只是严肃的文字,感伤的情调,沉郁的氛围,表现了欧·亨利小说中所鲜见的一种悲怆的风格。这都是为了映衬人物,烘染主题。因而虽是一篇哀伤的小说,却能令人从哀伤中奋起,从悲秋中见到阳春,从黑夜中见到光明,产生了悲怆美,成为欧·亨利一篇最带变异性的最优美的小说。这里虽也不例外地选取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但对三个穷苦画家人物关系和生活片断的处理,却更见结构功力,更具艺术匠心,更有巧妙的变异。在大杠铃结构套小杠铃结构的框架中,作为歌颂对象的人性基督,贝尔曼并不是一名来往奔驰呼号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退居于关系人物之后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画过一片叶子的老画家。也并不用从头到尾的细描详写,而是让他在靠近小说结尾的地方出场,而且着笔处仅有约八百字,只占小说字数的六分之一。这又都是为了凝炼,为了蕴蓄。而老画家画那舍己救人的“最后的常春藤叶”,是小说中塑造人性基督形象至为重要的笔墨,本应作正面浓墨重彩的铺写,但这里却又隐入暗中的虚拟,侧面的描绘,而且竟然吝惜到只有约二百字的几笔素描,有意留下广阔的艺术空间,让读者通过“画什么”去作“怎样画”的想象和补充:漫漫长夜,凄风苦雨,老画家如何吃力地“挪动”梯子,如何艰难地爬上高梯,如何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高处,依傍在“一根藤枝”之旁,细心调配“绿色和黄色的颜料”,如何一手高举“燃着的灯笼”,一手专注地把“最后一片叶子”补“画在墙上”……就用这种“不写之写”,让读者从有限的几笔速写中,看到小说无限广阔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生活图景。这种艺术填补空间,也都是为了凝炼,为了蕴蓄。而凝炼,蕴蓄,则又更多地表现在对人物的映衬,对主题的烘染,更得力于白描语言与杠铃结构的运用。因而在这里,凝炼多含韵味,蕴蓄透出神采,别具一番迷人的魔力。这种变异,也是发自“欧·亨利手法”同中见异的变奏而从欧·亨利小说中脱颖而出,使欧·亨利的创作风格更加奇特,更加典型。正因如此,《最后的常春藤叶》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才高出其他小说而成了人性作家欧·亨利的千古名著,值得我国小说界、学术界深入探赏、研究,并从中加以借鉴。
1994年11月中旬写于华侨大学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