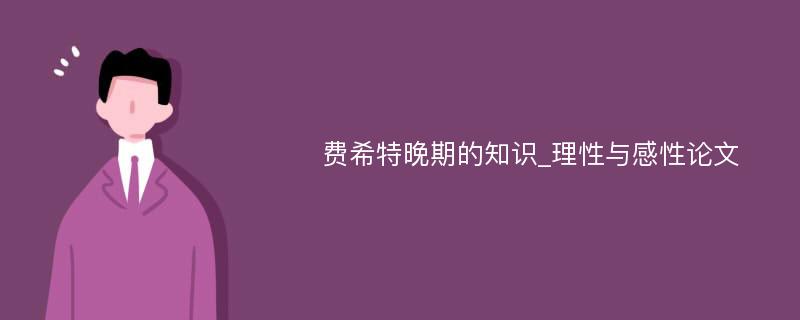
费希特晚期的知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希特论文,晚期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3)06-0026-09
黑格尔说过,费希特哲学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早期的思辨哲学,这是经过严格一贯的论证的;一是他晚期的通俗哲学,他在柏林时期对各色听众的演讲和发表的著作都属于这个方面。“它们的内容虽然有很大的价值,但在哲学史里却不能予以重视。哲学的内容必须得到思辨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只有在他早期的哲学著作里才有”。[1](P309)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梅狄寇斯版《费希特著作集》的出版,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业已演变的知识学日益受到了重视,黑格尔的这种评价已经发生动摇(注: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首先当推格扎维埃·莱昂著《费希特和他的时代》(三卷本,巴黎1922~1927年)和马夏尔·盖鲁著《费希特知识学的演变和结构》(两卷本,巴黎1930年)。)。尤其是,自从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于1962年开始问世以来,德国哲学家大力研究了费希特柏林时期的知识学,彻底推翻了黑格尔的这种评价。慕尼黑学派的代表赖因哈德·劳特根据建立严密体系所要求的公理化原则,认为费希特不仅在耶拿时期建立了一个以自我为最高原理的知识学体系,而且在柏林时期把这个体系提高为一个以绝对为最高原理的知识学体系;尽管费希特没有把这项成果以专著公之于众,但从他1804年以来所作的演讲和发表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业已演变的知识学是一个不仅把本体论与认识论,而且把现象论和真理论统一起来的严密体系,并且他以这门第一哲学为依据,在建立各个哲学学科的工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注:赖·劳特:《费希特的全部哲学观念》,入《先验哲学观念》,慕尼黑1965年;《费希特的知识学——对费希特的看法的改变》,入《从笛卡尔到马克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验发展线索》,汉堡1989年;《费希特在哲学史中的贡献》,入《理性在现实中的渗透》,诺里德1994年。)。这个基于研究详尽占有的资料而得出的看法,现在已经在国际费希特研究中得到了确认,而黑格尔那种长期流行的评价再也无法成立了。
一
知识学的演变是由多种因素逐渐促成的。从费希特的著述情况看,1800年1月问世的《人的使命》可以说是这一演变的转折点。在这本书里,上帝既不像在《试评一切天启》(1792年)里那样,是人的主观东西的外化,也不像在《我们信仰上帝统治世界的根据》(1798年)里那样,是生动的和发挥作用的道德秩序,而是这样一个不可名状的无限者,这个无限者有他自己的知识和希求、生命和行动,他与人息息相关、人的知识和希求、生命和行动是从他那里来的,因此,人应该坚信他的天意,尊重他的安排,因为这个无所不知、永恒不灭的无限者最了解人的所作所为和人的全部计划。这样,费希特就从哲学开始过渡到宗教,为他的知识学的演变开辟了前景。同时,我们在这本书里也看到,他在如何对待当时那种以极权整体论为基础的国家制度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宁愿与现存的状态妥协的倾向,说他自己为了现状所准备的更好的事物,甘愿在这现状下尽自己的一份责任[2](P267)。这样,他在自己的国家学说发生变化时就必须回答,一种不以社会契约论,而以极权整体论为基础的国家学说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最高哲学原理为其最终的根据的。
当然,直接促成知识学发生演变的还是费希特与谢林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起源于谢林1800年5月发表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他在这本著作里认为,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分别属于两个可能的方向,前者的课题是使客观东西成为第一位东西,从中引出主观东西来,后者的课题是使主观东西成为第一位东西,从中引出客观东西来,而整个哲学的开端和终点就是一个既不主观也不客观,因而只能加以理智直观的绝对同一体。[3](P274)费希特看过此书以后于11月15日给谢林写信说:“关于您讲的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对立,我与您的看法不一致。一切问题看来都是由混淆观念活动和实在活动而引起的,我们两人有时造成了这种混淆,我希望用新的阐述完全消除它。在我看来,既不是事实要归附于意识,也不是意识要归附于事实,而是这两者在自我这个具有观念的实在性和实在的观念性的东西中直接统一起来的”。[4](P360)谢林在11月19日给费希特写信回答说,“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对立是主要之点。我只能向您作这样的保证:我作出这种对立的根据并不在于观念活动与实在活动的区分,而在于某种更高的东西”,即主观东西与客观东西的绝对同一。[4](P362)
显然,争论的要点是最高哲学原理,争论的结果则是知识学作为惟一的哲学体系是否能够成立。尽管谢林向费希特多次写信作出解释,费希特依然认为谢林是错误的,并在1801年3月发表的《明如白昼的报导》中公开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把谢林讲的同一哲学称为“另一种与知识学对立的理智直观体系”。[5](P239)于是,谢林也在他同年5月发表的《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里说明,“费希特可以把唯心论看成是完全主观的,而我则相反,把唯心论看成是客观意义上的;费希特可以站在反思立场上坚持唯心论,而我却站在创造性立场上制定唯心论原则”。[6](P5)费希特看到了谢林对知识学的这种误解,在5月31日至8月7日时断时续地写成的一封很长的回信中指出:“关于知识学把知识看作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它是唯心论还是实在论,这类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只有一种科学,而这就是知识学;所有其他的科学都仅仅是知识学的分支,它们只有以知识学为依据,才是真实的和明白的”;“知识学完全不缺少原则,但知识学缺少完备的阐述,因为最高的综合、即精神世界的综合尚未作出”;在阐述知识学时,“决不能从一种存在出发,而是必须从一种观照出发;也必须把观念根据和实在根据的同一性作为直观与思维的同一性建立起来”。[7](P45~46)
费希特拒绝的这种存在就是谢林所主张的主观东西与客观东西的绝对同一性。谢林在10月3日给费希特写的信里说,“既然思维与直观的这种绝对同一性是最高的原则,那么,它实际上就被设想为绝对的无差别性,必然同时是最高的存在”。[7](P81)对于这种客观唯心论意义上的存在,费希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但他所主张的那种应该作为出发点的观照,则反映了他的知识学在这场争论中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他当时写出而未发表的《知识学阐述(1801~1802年)》里,他一方面坚持这种观照就像耶拿前期知识学中的本原行动和耶拿后期知识学中的理智直观那样,具有创造万物的含意,说“理智直观自为地是一种绝对的自我创造,完全不是出自任何东西”,但“这种创造不是作为自在的事实存在的,相反的,观照作为绝对的活动恰恰就是这种创造”;[8](169~170)另一方面,他克服了耶拿知识学的出发点只表示创造万物,而没有直理之光的含意的缺陷(注:关于这个缺陷,谢林在争论结束以后,还在他的《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图宾根1803年)里提到,“‘行动,行动’这个呼声虽然响彻许多方面,但也只有那些不想继续从事认识活动的人喊得最响亮。”(《谢林全集》第3卷,第240页。)),时而认为观照作为知识是这样一种自为的存在,“这种自为的存在恰恰是活生生的光明状态,是一切现象在光明中的源泉,是<绝对的>实质性的内在观照”。[8](P149)在这里,把这样的观照假定为重新阐述知识学的出发点,虽然表示费希特已经不再在实在性的意义上,而是在观念性的意义上理解存在,但也不是没有问题。谢林在1801年10月3日写给费希特的那封信里就已经指明,“从观照出发,即意味着从主观性出发。”[7](P82)费希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02年1月15日给谢林写的最后一封信里说明,“我在前一封信里说过,哲学中的绝对当然永远是一种观照。您回答说,这不可能是对于某种东西的观照,这完全正确,我也没有否认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不谈这件事情”;为了避免误解,费希特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作为绝对的观照正是绝对知识。[7](P112~113)
关于这种绝对知识,费希特在《知识学阐述(1801~1802年)》里作过两方面的描述。否定性的描述是要说明“绝对知识不是任何关于什么的知识,不是一种(量的和相对的)知识,而是(绝对质的)知识”,以纠正谢林那种把知识学的出发点视为相对知识的观点;肯定性的描述是要说明存在与自由在绝对知识中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构成一个直观的统一体,“就这里本来要追问一个能动的东西而言,存在与自由都是能动的东西”。[8](P145、149)由此可见,在费希特的这本遗著里,存在已经不再具有受动的意义,而是具有能动的意义;它已经不再是派生的东西,而是原始的东西。因此,作为存在与自由的相互融合的绝对知识也就不再是自我的本原行动,而是知识学的一个更高的出发点了。
二
在用三年时间对知识学进行过修订以后,费希特觉得它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外在形态,因而在1804年这一年,他满怀信心地先后作过三轮知识学演讲,使他在这个领域里迸发出来的火花形成了一道绚丽的火焰,宣告了他柏林时期的新的第一哲学。
在1804年第一轮知识学演讲里,费希特虽然把绝对称为绝对知识,但已经把绝对假定为知识学的最高原理。他在紧接着作的第二轮知识学演讲里,则再也没有把这个最高原理称为绝对知识,而是很正规地界定了绝对的含意。他在回答什么是知识学的问题时写道:“如果说一切先验哲学——康德哲学也是如此,并且就此而言,知识学也与它没有差别——都既不把绝对设定为存在,也不把绝对设定为意识,而是把绝对设定为两者的联结,设定为自在自为的真理性和确实性 = A,那么我说,可以由此得知,在这样一种哲学里,自在地有效的存在与思维的差别就完全消失了”,“既没有无思维的存在,也没有无存在的思维,而是完全同时有存在与思维”。[9](P24)这个作为最高原理的绝对如果与1801至1802年的知识学阐述加以对比,则不难看出,它具有那里讲的观照的两重含义,即创造万物与真理之光,因为费希特在这里所讲的绝对是作为“内在创化”与“光明”的绝对,[10](P152、181)并且它也具有那里讲的绝对知识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存在和思维(或自由,或意识),因为费希特在这里同样强调这种存在不是僵死的,而是活生生的和原始的。[10](P153、216)因此,如果把这里的绝对与耶拿知识学里的本原行动加以比较,则可以断言,那里的最高原理是主观的主客同一体,这里的最高原理是客观的主客同一体(注:谢林在《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中挑明了他与费希特之争是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之争以后,黑格尔紧接着在其《费希特与谢林的哲学体系的差异》(1801年7月)中解释说,费希特体系的原则是主观的主客同一体,还需要补充以客观的主客同一体。(《黑格尔全集》,理论版,第3卷第94页以下)这本来是维护谢林的同一哲学的,但就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取向来说,也同样道出了晚期知识学发展的途径。)。费希特1804年作出的这个选择为他柏林后期的知识学奠定了基础,而不管他随后又把绝对称为什么。这样,他就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一,从他与谢林的争论来说,把绝对设定为最高原理就保证了知识学作为惟一的哲学体系所占有的地位,而不再会被贬低为同一哲学体系中的一个与自然哲学并列的分支。其二,从唯心论与实在论的对立在知识学之内得到解决来看,费希特在耶拿知识学里曾经将从自我到物的路线与从物到自我的路线对立起来,以肯定前者和否定后者的方式解决了这一矛盾,而现在,他在1840年知识学里则依靠绝对这个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体解决了这一矛盾,也就是说,以客观唯心论扬弃了主观唯心论与实在论的矛盾。
随着最高原理的改变,知识学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改变。费希特在1802年1月15日写给谢林的信里就已经指出,“斯宾诺莎说明了问题。太一必定是万物(更确切地说,是无限的东西,因为在这里还谈不上总体)皆有的,反之亦然,这完全正确。然而太一怎样成为万物,万物怎样成为太一,即过渡点、转折点和真实的同一点是什么,他却未能向我们说明。因此,他从万物出发时,就丧失了太一,而在把握太一时,又丧失了万物。所以,斯宾诺莎设定的绝对的两个基本形式——存在和思维——也和您所做的一样,没有进一步的证明,因此不能为知识学所接受”,[7](P112)而这就是要解决一本万殊和万殊归一的问题。在耶拿知识学里,这个问题是通过从客观到主观的理论理性和从主观到客观的实践理性的统一去解决的,但这种方法并未显示出最高原理的真理性,因而在以绝对为最高原理的知识学里就不充分了。正因为如此,费希特就把他的1804年第二轮知识学演讲分为两个部分,详细地研讨了这个问题。第一部分谈的是从现象到绝对、从杂多到太一的过程,第二部分为的是从绝对到现象,从太一到杂多的过程,前者称为真理论,后者称为现象论,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客观意义上的先验唯心论的内部结构。
真理论的目的是纯粹显示作为真理的绝对,只让真理得到承认,或者说,是达到对于这样的绝对的洞见;但这种洞见不是立刻直接达到的,而是必须经历一个从现象到绝对、从杂多到太一的还原过程,也就是说,必须经历一个应用综合方法,逐步克服实在论与主观唯心论的片面性的上升过程。这种上升开始于杂多的现象,因而是以纯属事实的东西为前提的,而这类东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反思对象的僵死存在,实在论者用概念把它设定为绝对的东西;另一类是作为陈述对象的直接意识,主观唯心论者用直观把它设定为绝对的东西。这两类东西都是与纯粹理性对立的。因此,知识学必须逐步排除这类纯属事实的东西,但又必须同时把概念和直观中包含的真理成分及其显现综合起来。知识学纠正了实在论的片面性,说明那种僵死的东西只是属于现象的,真正的存在则是纯粹的、自身封闭的和活生生的存在,而这就是绝对;同时也纠正了主观唯心论的片面性,说明那种直接的意识正是属于有待剥离的现象的,关于直接意识的陈述根本无效,真正有效的是完全需要加以理智化的东西,即纯粹理性。针对主观唯心论,知识学表示自己必将让纯粹理性完全呈现出来;针对实在论,知识学表示自己必将显示那种真正的、活生生的存在。知识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那种上升要达到的是一种更高的存在与思维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在其内在本质中是构造出来的,因而是原创性的综合。所以,尽管这种上升在经历的各个阶段所达到的洞见既有原创性成分,又有事实成分,但它最后还是从自身消除了一切纯属事实的东西,而显现出了作为真理的绝对。[9](204-206)
在这种从现象到绝对的还原过程达到对于真理的原初内容的洞见以后,就开始了现象论的那个从绝对到现象的下降过程。现象论的课题就是要把在真理论的上升过程中作为纯属事实的东西予以放弃的形式,作为绝对的现象或显现演绎出来。这种演绎涉及的问题是要证实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真的,以及它何以是真的。这种演绎标志着现象的不断分化或分裂,导致认识的日益明朗的理智化。具体地说,在现象的分裂达到最高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转化点,一个表现真理的存在与思维的统一点,它既是最明晰的,同时也是最隐蔽的,或者说,它是人们想要理解的不可理解的东西。因此,这时知识学又重新踏上了上升的路程,其出发点为:纯粹的、活生生的存在不能从外部加以构造,而必须自己构造自己。过去在还原的道路上借以达到真理的外在形式不应该由真理论的内容直接加以毁灭,而应该在内部由自身加以解释和纠正。这样,知识学的这种上升就绝不是重复同样的东西,而是一方面达到在形式上具有质的同一性的知识,另一方面达到作为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的知识,从而根据最高原理先验地解释了杂多的现象的起源;当然,知识学之所以能洞见到现象出自绝对,可以理解的东西出自不可理解的东西,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分清了以纯属事实的东西为本原的通常知识和对绝对具有原创性洞见的先验知识。用费希特的话来说,“既然现象、从而杂多的本原已经a priori[先验地]从[最高]原理得到了解释,那么,一切诉诸经验的做法就都废除了,而那种在以前[仅仅]从纯粹事实方面获得的东西也就被察觉是有起源的。”[9](P300)
关于这种以绝对为最高原理的知识学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关系,费希特在1804年6月23日给他的友人(注:可能是法国新教布道士鲍·约·阿皮亚(P.J.Appia 1783~1849)。)写信时附寄的箴言里说,一切哲学的对象都是存在和意识“这两者在它们的分离状态的彼岸的绝对统一。正是康德作出了这项伟大发现,因而成了先验哲学的首创者”。但是,康德“把某些仅仅在经验的自我观察中能够发现的根本不同的东西假定为不能进一步统一的,并且把需要相应地加以推演的东西还原为这些分离的根本统一体中的任何一个”,因此他的先验哲学“一方面是不完备的,自身不彻底的,即未达到绝对统一的,另一方面是部分地基于经验材料的,因而并不是严格科学的”。与此不同,知识学则“真正表达出了这种统一”,因为“洞见到它分裂为存在与意识的根据,并且进一步洞见到在这种分裂状态下的东西以特定的方式继续分裂的根据”。所以,知识学会“完全不求助于经验知觉,而出于对那种统一的洞见,全然a priori[先验地]理解这一切”,“真正理解太一中的万物和万物中的太一。[7](246~247)虽然这篇箴言很简略,但它足以表明:费希特已经把康德的先验哲学发展为一种以存在与意识的绝对统一为最高原理,以真理论和现象论为组成部分,因而具有客观唯心论形态的先验哲学。当代费希特研究专家沃尔夫冈·杨克曾经就此指出,“费希特对于反思、存在和真理的仔细思考完成了批判理性的工作。它构成了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独特的完成形态”。(注:沃·杨克:《费希特·存在与反思》,柏林1970年,第15页。)
三
费希特在结束1804年知识学演讲以后,立即就去解决另一项艰巨的课题,即以这种新型的知识学为基础,重新阐述和建立各门应用哲学。初步的尝试是在他于1805年2月至3月所作的《神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原理》中进行的。他在1804年知识学里已经把这个课题称为“推导显现的实在的一切可能的变化形态”。[9](P132)在他看来,在业已被理解为统一体的存在与意识的继续分裂中,存在是在它与意识的结合中分裂的,所以,当意识首先分裂为感性意识与超感性意识,这种分裂被应用于存在时,则必定提供感性存在与超感性存在;当超感性意识又分裂为宗教意识与道德意识,这种分裂被应用于存在时,则必定提供一位上帝和一种道德规律;当感性意识又分裂为社会意识和自然意识,这种分裂被应用于存在时,则必定提供法权规律和自然界。[7](P247)按照这样的哲学学科分类方法,费希特经过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作过下列演讲:体现他的历史哲学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4年11月至1805年3月);修订他的道德哲学的《关于学者的本质》(1805年5月至8月)和《伦理学体系》(1812年6月至8月);修订他的宗教哲学的《极乐生活指南》(1806年1月至3月);修订他的法权哲学的《法学》(1812年4月至6月)和《国家学说》(1813年4月至8月)。虽然此中的《法学》《国家学说》和《伦理学体系》演讲在他1814年逝世前未曾出版,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他在柏林时期已经建立了一个以客观唯心论的知识学为基础的思想体系。
这些演讲一方面阐述了他在柏林时期建立的应用哲学,另一方面也与他1804年以后的其他知识学演讲一起,深化了他业已定型的晚期知识学。就后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关于知识学的最高原理。费希特在论证他的知识学阐明了基督教文明的真谛时,总是把绝对称为上帝。例如,他在《神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原理》中就明确地表示,“绝对 = 上帝”。[10](P380)又如,他在《极乐生活指南》里反复说明“上帝本身就是太一”,[11](P94)是“纯粹的和实在的绝对”,[11](P167)同时在把绝对解释为逻各斯或道的意义上,论证了《约翰福音》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上帝本身就是道”是跟知识学完全一致的。[11](P118)并且,他在论证他的知识学起源于古代希腊哲学时,总是把绝对称为理论。例如,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里他就把理念视为像绝对那样的世界本原,他写道,“理念是一种独立的、在自身有生命的和赋予物质以生气的思想”,而“赋予物质以生气”就意味着,“所有物质中的生命都是理念的表现,因为物质本身在其具体存在中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理念的映现,由此产生了寓于物质本身的活跃性和生动性”。[12](P235)
第二,关于从绝对到现象。这个分裂过程的前提在于,作为绝对的内在存在的东西必然表现于外,表现于外的东西必然存在于作为绝对的内在存在的东西中。所以,费希特在《神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原理》中就阐明了绝对的外在表现是知识,上帝的外在表现是上帝的具体存在,(注:在原文中,具体存在(Dasein)是一种有空间性而无时间性的存在,亦可说是在场。)因此“知识 = 上帝的具体存在”。[10](P380)而这种分裂过程是发生在作为绝对的显现的知识里的,或者说,是发生在作为上帝的显现的具体存在里的。在《极乐生活指南》里他很详细地论述了绝对之分裂为超感性东西与感性东西。在他看来,绝对是生动有力地具体存在的,因此,作为具体存在的知识必然在其自身有区别,要用其拥有的概念设定一个作为知识对象的世界;所以,概念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使感性东西从超感性东西分离出来。费希特就此写道,“概念或道是整个世界惟一的创造者,由于其本质中包含的分裂而成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创造者”。[11](P119)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里他进而很详细地论述了感性东西之分裂为自然界与社会历史。在他看来,知识本身要靠一个由它设定的和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对象,不断地发展自身;它虽然靠概念能理解这个对象,却不能理解这个对象的原始根据,因此,它仍然要靠这个对象,去理解没有被理解的东西。费希特就此写道,“这个对象是在知识的已经预先设定的存在之内出现的,所以它是纯粹知觉的对象,只能从经验上加以认识。我说,这是惟一的、永远依然如故的对象”,“它以这种持久的客观性被称为自然界”;但“知识是在持续不断的时间中靠这个对象发展自身的”,这样就出现了“知识靠不被理解的东西进行的永远不被理解的发展过程”,即作为历史学的对象的人类社会史。[12](P297)
第三,关于从现象到绝对。这个还原过程的目的在于,把全部分裂的东西都还原为绝对统一的绝对。在《极乐生活指南》里,费希特在阐明了真理之光从绝对、上帝外化出来,分裂成无限的杂多的光芒以后,又从真理论的角度阐明了我们昔日以为自为独立的现象其实是隐藏于自身的神圣本质在知识中的显现,而不是任何本身实在的东西。他就这个还原过程写道,“这种光也能够依靠自己,从这种分散状态重聚起来,把自己作为单一的东西来把握,将自己理解为自为存在的东西,理解为上帝的具体存在和显示”。[11](P103)而这就给人们从感性世界观出发,将物质的东西、法律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相继综合于自身,达到直接洞见和直观绝对、上帝的宗教世界观,开辟了上升的途径。当然在费希特看来,最后上升到对绝对的把握,还得由具有透彻的明晰性的哲学世界观来完成。
从费希特1804年以后制定的各门应用哲学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知识学的演变,它们已经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不同于他在耶拿时期制定的应用哲学。
第一,关于宗教哲学。他修订了在《人的使命》中把上帝视为不可名状的无限者的概念,认为“上帝在自身中是统一的,而没有变化和改变”,“上帝绝对地和直接地依靠自己,并通过自己,就是绝对存在或他所是的东西”。[11](P94、96)在费希特看来,人们不应当游移于各种变化的东西当中,过那种假象生活,而应当依靠自己具有的精神的眼睛,超越一切变化的东西,上升到这样的绝对存在或上帝,过本真生活。他写道,“本真生活的任何一个被爱的对象,都是我们用上帝这一称谓或至少应当指的东西;单纯假象的生活所爱的对象,即可变的东西,则是作为世界显现给我们,而我们也这样称谓的东西。因此,本真生活是在上帝中的生活,并爱上帝;单纯假象的生活则是世界中的生活,并试图爱这世界”。[11](P59)所以,在费希特那里,不仅上帝的概念有了变化,而且崇拜上帝的意义也有了变化。如果说在他的耶拿时期的宗教哲学中上帝是使道德行为必然成功、不道德行为必然失败的最终保证,具有鼓舞众生投身于正义事业的莫大威力,那么在柏林时期的宗教哲学中,上帝则已经单纯变成了人们为了超凡脱俗、怡享天福而追求的最高目标了。
第二,关于道德哲学。在1798年的《伦理学体系》里,费希特从绝对自我出发,推导出人的道德本性或人之内的伦理原则,认为这种原则就是人应当毫无例外地按照独立性概念规定自己的自由;他像康德一样彻底否定了道德他律,而要求独立于外在目的,寻找道德行为的动机,并且像康德一样,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规定道德行为,使之服从于我们之内的道德规律的能力。但在1812年的《伦理学体系》演讲里,推导道德规律的出发点则是作为上帝图像的概念,自由的、独立的自我是由这种概念的根本存在设定的,所以在费希特看来,实现道德规律的高级任务是在客观存在中创造某种作为上帝图像的世界状况,实现道德规律的初级任务是在整个人类中创造一种作为绝对善良意志的道德意志,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过是完成前一项任务的工具,因此,“尘世中的伦理意志的绝对终极目标是一种在这种意志之外的伦理生活”。[13](P83)同样是讲学者的道德,费希特在1794年的《论学者的使命》中认为,学者的本质是笛卡尔式的自我,学者的表现于外的品德是由自我的本原行动决定的,而在1806年的《论学者的本质》中则认为,学者的本质是柏拉图式的理念,学者的表现于外的品德是由这种神圣的理念必然引起和决定了的。
第三,关于法权哲学。在1796~1797年的《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演绎法权规律的出发点是绝对自我,在1812年的《法学》中演绎法权规律的出发点则是绝对、上帝,因为绝对、上帝必然要显现自身,把自身显现为既包含能知主体、也包含所知客体的知识,而只有在这种知识中才能演绎出法权规律。费希特就此写道,“知识要将自身理解为上帝的显现”,这种显现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由许多自我构成的关系”,“这些自我都必须被看作是在一个共同的活动领域里从事活动的”;但“在这个共同的领域里,一个人的自由会妨碍别人的自由,而只有法权规律得以消除这种妨碍”,[14](P7、8)换句话说,在道德规律无法支配的地方,由知识推演法权规律就成为必然。尤其是在法权规律支配的领域如何建立政权的问题上,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里主张,全体公民与当选的国家行政官员签订契约,将执行公意的权力赋予他们,同时又推选出监察官员,监督行政官员执行这项契约(即行宪)的情况;但在《法学》中费希特则由社会契约论转向集权整体论,不再讨论全体公民选举国家官员的问题,而在讨论造就一种能在心中爆发出实现法权规律的意志的统治者的问题,认为这种意志来自作为上帝的显现的知识,是要实现上帝的蓝图,所以“建立法权制度的课题是不能由人的自由解决的。这是一个上帝统治世界的课题”。[14](P155~156)因此,费希特也就同时放弃了他过去关于划分行政权与监察权的主张,他说,“作为宪法的一个环节,民选监察权力的实施是不可行的,因为整个来说,人们都太坏了;不过,在他们整个变好以前,却必须产生出一部宪法,而这部宪法是不需要什么确实建立起来的民选监察权力的”。[14](P153)这样,在费希特的晚期法权哲学中,国家权力就是一种强制执行来自绝对、上帝的法权规律,而自身不受公民的监督的权力,一种带有神学色彩的集权整体论的产物。
四
关于1804年的知识学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费希特在1806年谈到《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关于学者的本质》和《极乐生活指南》时说,“它们全部是我六七年来以更多的空闲时间和更成熟的年龄,在哲学观点方面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修养的结果;这种哲学观点我在13年前就已经获得,尽管它像我希望的那样,可能已经改变了我的某些东西,但它本身从那个时候就没有在任何一个部分发生过变化”。[11](P47)这就是说,他只承认以知识学为基础的各门学说可能有某些改变,而决不承认知识学本身有任何变化。但是,对于一位哲学家的思想的评论决不能以他的自我度量为依据,而是要看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究竟讲了些什么。与黑格尔不同,谢林在当时就指出,1804年的知识学是“得到改进的费希特学说”,而这种改进的关键在于,“费希特公开声明,人靠其自身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不是人爱神圣理念,而是神圣理念在人之中爱它自己;哲学的根据绝对不是主体,不是自我,而是神圣理念”。[15](P54)同时,弗·施莱格尔也揭示了知识学从耶拿时期到柏林时期的演变,明确地区分了它的“早期形态和晚期形态。”[15](P133)所以在事情过去一个世纪,人们对问题认识得更加清楚以后,亨·海涅也这么写道,“费希特的全部体系经受了最为令人惊讶的修改”,但“这个倔强的人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这种巨大变化,他认为他的哲学是始终如一的,只不过表现方法有了改变和改善,而世人是从来都不了解他的”。[16](P329)这个看法符合于费希特知识学的演变过程,也在当代费希特研究中得到了肯定。因此,我们在讲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时,也就不应该只讲它的早期形态,而不讲它的晚期形态了(注:本文作者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北京1984年10月)译序《费希特哲学思想简评》中,由于对他晚期的著作缺乏全面的研究,只谈到他在宗教哲学、道德哲学与法权哲学中的观点变化,而未涉及知识学的演变,希望本文能弥补那篇译序的这个不足之处。)。
收稿日期:2003-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