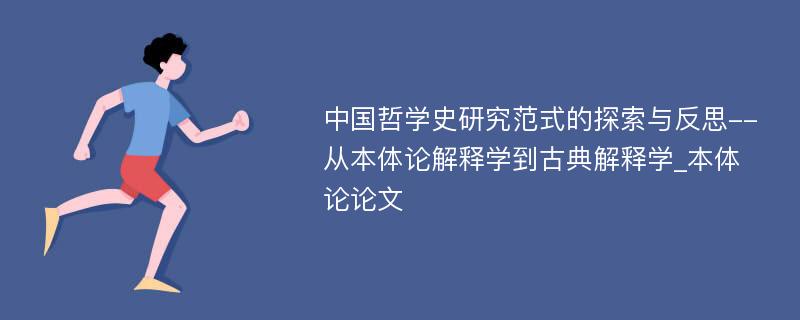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探究与省思(专题讨论)——从本体论诠释学到经典诠释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伽达默尔坦言,“像古老的诠释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序”[1](《第二版序言》),他所关注的是“超越我们的意愿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明言之,就是在理解过程真实地呈现在我们意识之中的东西,亦即构成人的此在的存在状态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人人生而平等,自有其存在的根据与合理性,那么,构成人的此在的理解就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坚持认为:“事实上,理解并不是优越的理解,既不是主体由于具有更清晰的观念从而有更优越的知识这种意思,也不是意识对于创造的无意识本性具有基本的优越性这种意思。只消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1](P381)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这种表述,也许只能将其定为一种相对主义的理解观。不过,伽达默尔本人并不认为他的理解观是相对主义的,也不赞同这样的理解观。
伽达默尔理论必须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在我看来,其理论贡献就在于阐发了理解本体论。在他那里,理解问题属于“精神科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人类精神世界,亦即广泛意义上的“文本”(包括语言性与非语言性的“文本”在内的一切理解对象)。显然,“文本”也可以被当作认知对象,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认知性诠释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套合适的方法论来正确把握作者或文本的原义。与此不同,伽达默尔理论的目标设定并非揭示“文本”的真正原义,在他那里,对“文本”的理解只是一个“中介”,理解者乃是通过对“文本”的理解而达到自我理解与持续的自我塑造[2](P146)。此乃本体论诠释学与认知诠释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理解作为本体显然不同于传统哲学的任何一种本体范畴,以往本体概念乃是标志着终极的、稳固不变的、外在于认知主体的、隐匿于现象背后的实体或本质性的东西,而理解却是在整个理解过程中变动不居、并伴随着理解的深化而不断地被重构的东西。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理解不是主体切近被理解对象的行为方式,而是主体自身的自我塑造。
伽达默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考察本体论问题的独特视角,这就是真正地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来探讨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问题。在传统的认识论中,人乃是作为客观意义上的认知对象,先于认知过程而存在,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作为认知对象的人,一如既往地被置于主、客二分的框架中,作为认知对象,人在这里与其他任何东西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都是认知的客观对象。研究对象的不同,所适用的方法也不同。适用于作为客体的人的研究方法确实是独特的,但是,再完善的方法论也不能改变其作为“客体”的性质,事实上,传统认识论所缺失的东西就是“主体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认识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避免自己的主观意愿的干扰,以便能客观、严谨地进行观察与分析,惟其如此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研究;至于被认识的对象,则永远是客观的、业已存在的东西,即便人在探讨“主体性”,也一定是将其视为人的不依赖于认知主体为转移的客观属性,才能发现关于“主体”或者“主体性”的客观知识。而在伽达默尔那里,所有的对象性的存在及其性质都已转化为构成人的存在之内在要素。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其意义并非独立、客观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在与理解主体的互动中被赋予的。就此而言,理解不是正确把握文本、发掘隐含于文本中的固有意义的一种方式,而是意义的创造与生成。此意义直接汇入了理解主体的生命洪流之中,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
这样一种理解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也许就是伽达默尔的思想能够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理解与认同的原因了。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流行”。用“流行大化”来指“道”之化生万物,并育万物而使之各得其所,是其一义;另外一义,见于《明儒学案》:“心不是别物,就是大化流行”[3](卷58)。朱熹也曾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4](《先进》),乃是从主体的层面来谈论“流行”。此二义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流行”乃是“道”或“心”或“理”的化育之功能。而在王阳明那里,心、理与良知,更是合而为一。正是出于这样的“前理解”,国人在接触到伽达默尔的学说就会产生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来自于理论上某种相似的立场:与西方传统哲学立足于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划分与坚硬对立相反,而主张两者的互摄互动。
检视中、西方哲学的思维理路,王阳明之心学与伽达默尔诠释学最为相契。王阳明认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诚发见也,皆所谓贞也。观天地交感之理,圣人感人心之道,不过于一贞。”[5](卷26)“天地交感之理”与“圣人感人心之道”虽为“一贞”,然其“一贞”之根源,却又落实于“心”。他这样说道:“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5](卷3)所谓“心外无物”,显然不是指在心外没有“他物”之存在,而是说,我们所能谈论的只是“心内之物”。王阳明的观点所显现出来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意义世界。若转换到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语境中则可以这样表达:“花”(广泛意义上文本)之形、色,无非在我们的意识中呈现之物,它是被构造出来的意识现象,一个真实的、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的存在。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角度看,意识之中的存在乃是对客体的一种反映;而在伽达默尔,意识现象本身就是构建起来的东西,是一种创造物。因此,他的诠释学理论从来不是为了提供正确理解文本的方法论,他所关注的不是客观意义上的、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而是呈现于意识之中、在意识中被构建起来的文本。如此被构建起来、被理解的文本之意义,按照利科尔的说法,是一个“放大了的自我”[6](P188)。如此说来,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先于理解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在理解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说,文本因理解而获得了意义,此意义是理解者所赋予的、随着理解而展开的,并标志着理解者自身存在的意义。就此而言,“意义”表征着一种生命的关联。漠然寂处之“花”,乃至整个对象性世界,由于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而鲜活起来,与我们融而为一,我们也因之不断得以充实与升华。
若就“意识之中”的存在来界说“花”的意义,则完全不同于作为认识对象而被认识的“花”。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花”的意义与人的存在之意义构成了一个整体。由花开感悟到美与勃勃生机,而观叶落而悲秋,表达出来的恰恰是人的生命体验及其存在状态。正因如此,伽达默尔称,“此在在它的存在与它的世界中进行的理解,并非是指向某种认识客体的行为,而是其在世之在(In—der Welt—Sein)本身。”[7]由于主体在其存在关联上的差异性,被理解对象在意识中的呈现也会因人而异,这便是“此在”的在世之在的差异性。
在这里,王阳明与伽达默尔理论的交叉点,从王阳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感”或“交感”这一概念。伽达默尔所说的意识之中的呈现,实质上就是一种由“感”而发的意识创造物。而“感”从何来?其动力之源是“心”。虽然意义之实现有赖于“心”与“客体”之互动,但“心”无疑是绝对的主宰。王阳明与伽达默尔的区别正在于此:王阳明将“心”设定为终极的本体,它是宇宙的本原,主宰着万物之化生;更为重要的,它同时又是道德与价值的本体。作为后者,它便是“良知”。言其“更为重要”,是因为王阳明的“心学本体论”乃以道德论来涵摄宇宙论,直接将“良知”认作“天理”。这就意味着,在王阳明那里,“感”是有价值取向的,这个取向是“心”所规定的,“感”的真正功用正是“心”或“理”或“良知”的“流行大化”;而在伽达默尔的理解理论中,并不直接包含这样一种道德与价值向度,他想说明的是理解如何构成了“此在”的在世之在,即便在他关于“教化”论述中,所侧重的依然是主体如何被塑造,而未指明根据什么来塑造,因为他不承认有什么更“优越”的理解。也许这种做法更为明智,因为我们实在难以确定永恒的、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是什么。
在我看来,异曲同工的王阳明心学本体论与伽达默尔理解本体论是有说服力的。它们尤为关注人的在世之在(当下之在)的存在方式,表明了其理论的鲜明的实践品格,直至今天仍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然而,这两者又都未给予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以足够的重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在西方,本体论诠释学与方法论诠释学已成对立之势,我们的诠释学研究是否必须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作出选择?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以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使得对立的双方在更高的层面上整合为一个整体。在此整体中,对立的双方都能得到合理的安顿。诠释学研究的这一努力方向,笔者名之为“经典诠释学”。这种主张难免会受到质疑,特别是对于了解诠释学史的学者来说,该主张无疑是一种倒退。众所周知,诠释学原本就是用于经典解释的方法论,现代诠释学便是在“圣经注释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最初形态就是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一种适用于解读所有文本的方法论诠释学。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的推动下,伽达默尔创立了本体论诠释学,使诠释学转化成了一种实践哲学的体系。由此不难看出,就形式而言,回到经典诠释确实是倒退到了施莱尔马赫的古典诠释学。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对于诠释学的发展来说,此一回归有其必要性。其实,理论探索的回归之路与其经历过的发展之路并不是同一条路。回归乃是对理论出发点及其整个发展历程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在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进行的,其中必然包含着某一理论原本并不具有的新因素,这如同今日国人研究中国的解经传统或西方诠释学,要常常借鉴不同的理论资源一样。
前面所提到的“经典诠释学”,就是在中、西诠释学研究的现代大视野中来重新审视诠释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回归”实质上是在一个新视域中的重构,并且,只有通过有效整合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思想资源才能够完成。但是,我们要构建的为何是“经典”的诠释学,而不是某种意义更为宽泛——比如说“文本”——的诠释学呢?
首先,“经典”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传统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典乃是人类智慧之树上结出的硕果,它们被视为“经典”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诠释”而流传于世,这一事实本身已说明其存在的意义与重要性:它们构成了归属于某种文化的那个集体的自我意识的核心,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形成与发展的主线。因此,立足于经典的诠释,实质上已经包含了一种被社会所认同的道德与价值取向,在其引导之下,诠释活动的实践功能(“大化流行”、“教化”等)获得了积极的、正面的意义,进而有益于社会在精神层面的提升。
其次,“经典”本身就是语言性文本,可以说是文本中的范本。综观历史,经典对于人们的影响不仅是观念上的,也包括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解读一般意义上的文本技术性层面的东西,均可以包含在“经典”的诠释理论中。毋庸置疑,诠释学研究的真正用力点应当是经典诠释。事实上,在整个诠释学史上,对于经典的诠释一直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由上所述,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经典诠释学”的研究要旨可以简略地作如下概括:
1.本体论部分应当是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综合,通过此一综合,提炼出“经典诠释学”的诠释理念:(1)理解在本质上是意义的创造活动,是理解主体的自我塑造与实现,也是我们的精神世界之构建;(2)理解内在地包含着一个被社会所认同的价值取向,通过理解,达到个体与集体的精神境界之升华。此即体现了诠释学的实践性之宗旨:“流行”、“教化”。
2.社会成员的共同信念最集中地表现在被认可的“经典”中,唯有通过正确地解读经典才能使之明晰起来。如此,理解的方法论便成为诠释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虽然西方诠释学在理解方法论研究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到了贝蒂那里已裹足不前;特别是他的理解方法论中并未考虑到中国悠久的诠释实践,这是否直接适用于解读中文经典,仍是一个有待于研究的问题。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建构适用于中国经典的理解方法论,不仅要借鉴、消化西方诠释学现有的方法论体系(特别是贝蒂的方法论诠释学),而且必须对中国解经传统中的诠释经验进行深入反思。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建立更为完善的方法论体系。就此而言,中国解经传统的诠释经验,将是推动止步不前的西方诠释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动力。
3.鉴于任何方法论体系都不足以对诠释的真理性要求作出担保,诠释方法论应定位于尽可能地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而非“真理性的”或“正确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