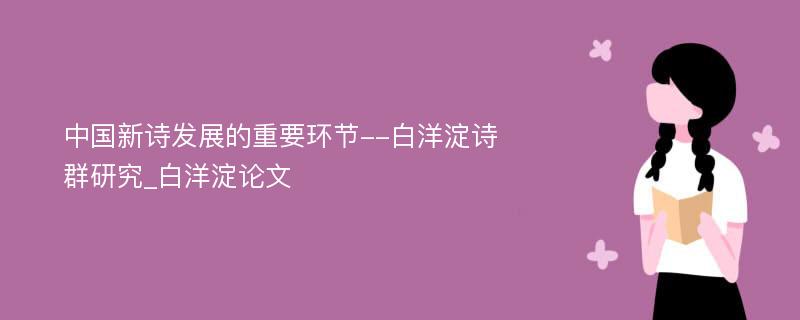
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洋淀论文,新诗论文,一个重要论文,中国论文,环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白洋淀诗群”是形成并存在于“文革”中后期的一个诗歌群体。一群在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开始了他们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歌,与此前的中国新诗有迥然相异的风貌,并对此后的诗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对这一特殊的文学史现象,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些讨论。有人把它命名为“白洋淀诗派”(注:如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有人把它命名为“白洋淀诗群”(注:如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或者“白洋淀诗歌群落”。也有人把它看作是“朦胧诗”的一部分(注:大量“朦胧诗”选收入这些诗人的诗作。如谢冕、唐晓渡编:《在黎明的铜镜中》。)或者笼统地称其为“新诗潮”诗歌(注: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新诗潮诗选》收入许多这些诗人作品。还有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实验诗歌”(experimen tal poets)(注:见〔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Research School CNWS,Leiden,the Netherland,1996年。)……。本文采用“诗群”的概念,则是基于“群体”的意义。这些诗歌,在本文中被称为“白洋淀诗歌”;鉴于许多诗人离开白洋淀后仍然从事诗歌创作,并且诗风有所改变,本文将他们在白洋淀插队或常住时期称为他们的“白洋淀时期”,这里讨论的正是这个时期的诗歌。
“白洋淀诗群”受到关注,是在“朦胧诗”的热潮之后。但大多研究者仍然是将“白洋淀诗群”作为“朦胧诗”的“附属”或背景来观照,把它视作“前崛起”、“前朦胧”。本文则认为,两种诗歌有着实质性的差别。“白洋淀诗歌”更接近于一种诗歌写作的“原状态”。也就是说,它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接受群体的口味左右,更不受传媒或商业化因素的诱导,而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个人化写作”。在这个意义上,与作为诗歌运动的“朦胧诗”相比,“白洋淀诗群”更具先锋性和预见性。
一、“白洋淀诗群”的形成
1968年底,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969年,北京一群中学生经过多方考虑,甚至实地“考察”后,陆续来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其中就包括“白洋淀诗群”的成员芒克(本名姜世伟)、多多(栗士征)、林莽(张建中)、根子(岳重)、宋海泉、方含(孙康)(注:方含在安新县毗邻的徐水县插队,但与白洋淀知青交往颇多。)等人。他们安顿下来后,陆续有旧朋新友来访甚至长住,在“白洋淀诗群”形成及存在过程中,他们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参与彼此的文艺交流,可以说成为“白洋淀诗群”的“外围”,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
在“白洋淀诗群”的形成中,诸多因素都起到一定影响。而且,在“文革”中后期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这些因素本身就是比较独特的,以下试从几方面加以论述。
(一)白洋淀的乡村读书
“白洋淀诗群”的“根”在北京。进入70年代的北京,随着政治斗争的转入上层,市民阶层所受的思想控制有所缓和。从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中跌落下来的年轻人,纷纷寻求别样的生存方式。一部分人堕落,一部分人则在精神领域苏醒。针对后者,多多说:“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注: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8年第3期。 )在这个“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过渡的”“思想极端活跃的时期,一批城市文化艺术沙龙开始出现”(注: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 3、4期。)。在北京,影响较大的是徐浩渊的沙龙(约1968—1972)。正是由于与北京这种“沙龙”的紧密联系,“白洋淀诗群”的成员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读物,接触更多的西方文学信息,在“沙龙”朗诵自己的作品并获得反馈。
这些知青诗人大多出身于高干或高知家庭,阅读经验比同龄人更复杂、更丰富,也更敏锐。这种阅读状况并未因文革而中断,而是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发展成为一种乡村读书活动。朱学勤描述1968年前后上海一批中学生状况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北京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精神阅读史……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各自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注: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第10期。或许朱文所列书目与“白洋淀诗群”的阅读不同,但这种状态应该是相似的。)
但乡村读书与正常读书是不同的。在读物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们的阅读内容驳杂,不成系统,并且因时间和知识结构的限制,又常常是囫囵吞枣,甚至误读。阅读范围除了一些经典读物——如当时所谓三本“必读书”即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及曹雪芹《红楼梦》——之外,更能激起“吃禁果”般读书兴趣的则是一些“内部”读物(包括“黄皮书”、“灰皮书”等)。政治学方面,有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秘史》、《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共产主义运动史》、《赫鲁晓夫主义》等;哲学及文艺理论方面主要有加罗蒂《人的远景》、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科学院文学所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内附袁可嘉后记长文)等;文学方面小说有加缪《局外人》、萨特《厌恶及其他》、凯鲁亚克《在路上》、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阿克肖诺夫《带星星的火车票》、沙米亚金《多雪的冬天》;散文有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一~四册)等;诗歌则更多,影响较大的有波德莱尔、叶甫图申科(主要是诗集《娘子谷及其他》)、梅热拉梯伊斯(组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特瓦尔朵夫斯基(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等。(注:以上书目据有关回忆文章、研究著述辑出,主要有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贝岭《作为运动的中国新诗潮》(载于纽约《华侨日报》,1986年12月25日)、潘婧(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并参阅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外国文学图书目录(1951—1990)》、中华书局编《1949—1986年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等。少量据林莽、宋海泉等人在笔者采访中的回忆。有些说法有出入,如甘铁生《春季白洋淀》一文(载《诗探索》1994年第4期)谈到他们读艾略特, 但多多在《雪不是白色的》一文(载《今天》1996年第4期)中谈根子《三月与末日》一诗, 认为当时根子“绝无可能知道世上有艾略特其人及其作”。故本文暂不列艾略特。)“白洋淀诗群”正是通过阅读领略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从中发现了某些新的理论解释及表达方式,并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接纳。这不仅因为某些思潮、流派直接与激进的社会运动甚至社会主义运动相关,如存在主义、“垮掉派”,而且一些具体的现代主义表达技巧,充分迎合了“白洋淀诗群”抒写内心感受及独立个性的要求。
(二)食指诗歌实践的“启蒙”及“十七年”诗歌的“遗风”
在论述“白洋淀诗群”形成过程中外来人文思潮的冲击的同时,并不能忽视一些当代中国新诗对它的潜在影响,比如食指诗歌和“十七年”诗歌。或许从表面上看,“白洋淀诗群”对它们是扬弃或反叛,但从更深层的诗歌结构上讲,接受与拒绝并无截然的界限。对食指的诗歌实践与“十七年”诗歌,“白洋淀诗歌”有表面的继承、发扬、厌恶、拒绝,也有潜在的背弃、遗留。
食指(郭路生)是谈到“白洋淀诗群”时必谈的一位诗人,他是他们“一个小小的传统”(注: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8年第3期。)。 “白洋淀诗群”是由食指的诗歌实践给予诗歌“启蒙”的。食指的诗歌在当时跳出了文革文学虚假浮夸的标语口号模式,“充满着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激情”(注: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0页。),使诗歌不再只是政治的附庸,而是力争实现其独立性,并因此散发出艺术的光彩和极大的感染力。可以说,食指诗歌中包含的这种诗歌思想,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从“白洋淀诗群”此后的写作来看,诗人们的确是沿着个人化写作的路子前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白洋淀诗群”成员写作略早的食指(他于1968年写诗),成为他们的启蒙者与引导者。但事实上,白洋淀诗歌与食指的早期诗作(从时间上讲,“白洋淀诗群”所受影响应来自这部分诗),——以《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儿三部曲》、《海洋三部曲》等为代表——,从阅读效果看有很大不同,那么,这个“传统”又当如何理解呢?
就整体而言,食指的早期诗歌是一些明朗的、浪漫主义色彩浓重的作品。《相信未来》(注:此诗发表于《今天》第二期,后收入《食指、黑大春抒情诗合集》,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其中略有不同,这里采用《今天》版。)(1968)一诗算得上是“食指式诗歌”的典型。诗中采用诸多当时诗坛少见的温情字眼,还有哀伤缓慢的节奏,都使作品显得清新感人。但其抒情结构的“走向”是预设的,定要迂回至“相信未来,相信生命”收尾。这其实显示了一种早已定型的诗歌思维模式,或者说,是循守了“十七年”理想主义诗歌的窠臼。“白洋淀诗群”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食指。他们的诗中,理想主义的影子已非常模糊,而代之以反叛与嘲讽;并且,随着这种信念的缺乏,他们摧毁了建国以来诗歌(包括食指诗歌)的整饬形式,打破了节奏、押韵,甚至语法规范,从而使诗变得晦涩、怪诞,以传达独特的内心感受及生命体验,更多呈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诗歌风貌。
中国新诗自发轫便带有一种感情过盛的“感伤情绪”。进入50年代后,感伤得到控制,代之以昂扬激奋,但主流诗学原则仍然推崇诗歌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注:参见洪子诚:《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之第一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十七年”诗歌(尤其是风行一时的朗诵诗)却又存在一种自身的悖论。一方面,诗中充满感情,甚至是夸张的激情;另一方面,诗歌又被强加了某种意识形态化的理念。也就是说,这种感情并非“自然”流露,而是受控制,有预谋的设计。白洋淀诗歌抛弃了理念对感情的人为控制,同时,也不同于西方现代诗歌全然的“反理性主义”,而是在诗歌中融入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与感情抒发相融合,创作出更合乎中国知识者心态的诗歌样式。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对“十七年”诗歌规范的另一种阐释,一种反叛式的接纳。
(三)自为的写作姿态与“小圈子”传播方式
不同于呼唤读者的作者,白洋淀诗人们的写作姿态,是一种“自为的”姿态。这是由当时的写作环境造成的。50年代末以来的文艺政策,不断向专制的权力话语靠拢,至“文革”时期更是登峰造极,民间的个人写作不可能合法化。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白洋淀诗歌”的写作无从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写诗只是出于个人表达的需要,因而成了一种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甚至构成生存方式。这样的写作姿态,使得“白洋淀诗歌”具有真诚的品格,忠实于个人情感,将关注更多地投射到个体的内心和体验。
当然,自为的写作姿态并非意味着完全没有交流者。“白洋淀诗歌”的阅读者除了诗人自身,还有诗群本身及北京“沙龙”的写作、交往圈子。但这不是诗人与一个接受群体的交流,而更多是诗人与诸个体的交流。这种小圈子传播方式,与诗歌形式、技巧的实验性探索常常互相激荡,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白洋淀诗歌”在艺术方面的追求。小圈子传播常常是互相传看、传抄,使得“细读”式赏析、讨论成为可能,诗歌的“听觉功能”相对减弱,诗歌朗诵的激情让位于相对冷静的回味,细品,诗歌从“朗诵诗”转化到“书面诗”。这样,“白洋淀诗歌”可以打破格律,不讲押韵,并且可以更多地采用非线形、不平衡的结构,以及富于跳跃性的,看似无序的诗歌语言排列,表达复杂的内心感受。
二、“白洋淀诗歌”的文本风貌
研究“白洋淀诗群”这样独特的文学史现象,必须将一些文本“之外”的梳理作为分析“白洋淀诗歌”文本风貌的切入点。另外,鉴于近年来研究者往往把“白洋淀诗歌”纳入到“朦胧诗”的实绩中去,这里的论述将有意把二者加以比照,使“白洋淀诗歌”从“朦胧诗”中剥离出来,确认其独立的文本价值。
(一)现代主义诗歌色彩
“文革”时期,尤其是到文革中后期,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理想主义的崩溃,使现代主义风格文学的出现成为可能。但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我们很难用纯粹西方式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对“白洋淀诗歌”亦是如此。这里更适合以“白洋淀诗歌”对“两结合”式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背离为着眼点,分析其现代主义诗歌“色彩”,寻找它与作为文学思潮的现代主义之间的精神血脉的一致性。
“白洋淀诗歌”将关注点从现实世界转向内心世界,抒写个人内心生活。即使有现实反映,也是通过抽象或变形,转化为心理符码,传达情感或思考。如多多的诗《无题》( 1974):“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荧(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这样的诗很容易被今天的读者读解为对文革暴力的描述,然而此诗最具震撼力的中心意图则在于通过“空漠”、“阴魂”、“变质”、“荒漠”等非现实指涉的语词传达出的废墟感。至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所标榜的理想主义,在“白洋淀诗歌”中则渺茫到几乎看不见了。
在对“两结合”背离的同时,“白洋淀诗歌”中出现了不少现代主义诗歌技巧。比如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中的“客观对应物”的创作原则,在“白洋淀诗歌”中就是常见的,较明显的是芒克的一系列短诗。如《酒》:“那是座寂寞的小坟”;《太阳》:“你又一次地惊醒,/你已满头花白。”前者用“坟”来暗示寂寞孤单的饮酒心情, 后者以“满头花白”的太阳来抒写人在时光流逝中的失落。再如西方理论中的“嘲弄”(irony,现通译为“反讽”), 在“白洋淀诗歌”中也有对应。像多多诗中对“太阳”的调侃式表述:“太阳像儿子一样圆满”(《蜜周》,1972),“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夏》,1975),“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致太阳》,1973)还有芒克富于“垮掉派”风格的《街》(1975),运用类似意识流手法的长句摹写虚无的心态……
另外,20世纪的俄罗斯现代诗歌,为白洋淀诗歌提供了人文精神及人格建构的引导。5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解冻”时期(1953—1963)的到来,一些曾被“封杀”的俄国向苏联过渡时期的诗人及其诗歌的“复活”,如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通过“内部发行”渠道进入中国,并唤起了“白洋淀诗群”的共鸣。尤其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两位女诗人,影响是极大的。无论是俄罗斯现代诗歌,还是“白洋淀诗歌”,都无法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样持有决然的批判性,而是弥漫着悲哀、灰色然而深情的基调。
(二)反抗的声音
你的眼睛被遮住了,
你低沉、愤怒的声音
在阴森森的黑暗中冲撞
放开我!
——芒克《太阳落了》(1973)唐晓渡评论这首诗写出了“当代诗歌中最早出现的反抗者形象之一”(注: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3期。 )。不只是芒克的诗,“白洋淀诗歌”中常常发出这样反抗的声音。如林莽“庙宇倒塌了/迷信的尘埃中,有泥土的金身/没有星座、没有月亮/只有磷火在游荡/废墟上浮起苍白的时代”(《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1974),诅咒的是专制的思想钳制。多多的许多诗更是通过象征手法来揭示当时反常、暴力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这些现象的极端厌恶与否定。
但“白洋淀诗歌”的反抗,仿佛只停留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控诉这一层面上,并进而表达一种对于宿命的皈依或更多的迷茫。芒克《太阳落了》一诗的第二节就“出人意表地一变而为深挚的挽歌”(注: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3期。 );“太阳落了。/黑夜爬了上来,/放肆地掠夺。/这田野将要毁灭,/人/ 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
这样的表达,似乎削弱了诗歌“反抗”的力度,但同时也加深了诗歌的沉郁感,蕴含了更为复杂的心理内容。白洋淀诗歌产生的年代,思想上的怀疑主义虽已弥漫开来,但整个局面毕竟还不像四五运动时那么明朗,“白洋淀诗歌”也就不可能像“天安门诗歌”那样痛快淋漓地控诉、讨伐,不可能像北岛那样凛然宣告“我不相信”!另一方面,这种反抗又使得“白洋淀诗歌”在批判“现实”之外,隐约地显露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指向,证实了“白洋淀诗歌”在文化上的敏锐性。
(三)内省与孤独
使“白洋淀诗歌”在当代新诗史上不同于以往诗歌的是它内省的诗歌特征。面对一个混乱、令人怀疑的现实,诗人既不能热情地“放声歌唱”,也无法大声抗议。“白洋淀诗歌”更多地沉入诗人内心,把握其精神存在的智性因素。但是,这种“内省”并不等于“朦胧诗”时期那种“痛定思痛”的历史性反思,因此,也就不具备后者所具有的明确的价值判断,而只是通过个性化的体验与感悟来传达的一种缺乏明确出路的内省,更多呈现情绪化色彩。如林莽“城市冒着浓烟,乡村也在燃烧/一群瘦弱的孩子/摇着细长的手臂说/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们什么也不要。”(《悼一九七四年》,1975)思考的是一代人的失去了渴望的生存状态。芒克的诗句“果子熟了,/这红色的血!/我的果园染红了/ 同一块天空的夜晚。”(《秋天》)交织着成熟与罪恶感。在多多的《祝福》(1973)中,对祖国命运的思索是这样的:“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 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 ”在这里,“祖国”的形象从“母亲”变成了“孤儿”,渗透了关于民族国家的危机感。
这样的内省缺乏价值判断,缺乏对某种理论的皈依,它使诗人的感受孤单地悬浮在半空,从而营造出“白洋淀诗歌”的孤独感。但与北岛式“英雄的孤独”(注:参见王干:《悲剧:理想的痛苦与英雄的孤独》,此文认为“朦胧诗”中的孤独是“英雄的孤独”。《文艺评论》1988年第6期。)不同,这种孤独是个人的孤独,是作为存在者、 思想者、写作者的孤独,体会他们的诗句,孤独是隐藏在所有诗句下的内心基调。“夜深了,/风还在街上像个迷路的孩子/东奔西撞”;“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啊,你这蹲在门口的黑夜——/我的寂寞”;“那向我走来的黑夜对我说:/你是我的”(以上芒克)。“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留下少年, 面对着忧郁的向日葵”;“海,向傍晚退去/带走了历史,也带走了哀怨”; “我写青春沦落的诗/……/ 我那没有人读的诗/正如一个故事的历史”(以上多多)。
这种孤独或许是包含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悲凉”(注: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风格当中,但放在文革中后期的背景中考察,就不仅限于文本风格意义了。
由于被逐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文革中的知青一方面有被“放逐”的感觉,一方面又拥有相对宽松的个人自由,而两种心态都助长着孤独感的滋生及蔓延。大而言之,文革也是中国知识者获得孤独感的一个时期。他们从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位置被彻底推向边缘,却阴差阳错地实现了一种自我发现。可以说,孤独的心理机制是个人化写作这一现代性写作得以成长的前提条件之一。孤独使“我”从“我们”之中游离出来,并且从外部世界转入内心世界。
“白洋淀诗歌”中存在的“拟孩童”式的叙述风格也正是孤独感的一种体现。在这些诗中,总是隐藏着一个任性、孤独又纯真的孩子的口吻。这个孩子一面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梦幻般的个人世界中,一面又以他的任性与幻想试图打破成人现实世界的丑陋与压抑。“姑娘,如果你去山里/请找到我的马儿/它是被光偷去的/我的影子”(方含的《谣曲》),“我喃喃梦呓/熄灯吧,妈妈/接着讲/你昨天讲到/奥涅金叔叔”(根子《白洋淀》),“啊,北方的树林/我总是对你恋恋不舍/但母亲在召唤/我要和她一起去收割”(芒克《我是风》,1975)。 这一类的诗,一直到“朦胧诗”中都大量存在,如“童话诗人”顾城、梁小斌等人的作品。虽然这些孤独的孩子气的诗在今天看来似乎太幼稚,以至于做作,但它们正是当代新诗个人化写作走向成熟的起点。
(四)“异国情调”
“白洋淀诗歌”的新奇,还在于它们有种可称之为“异国情调”的审美效果。
荷兰学者柯雷在分析多多的早期(1972—1982)诗歌时,选择的角度(angle)之一是所谓“中国性”(chineseness),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多多的某些诗,譬如《日瓦戈医生》,就“不是一首中国诗——如果说区别的话,它是一首俄国诗”(注:见〔荷兰〕柯雷(Maghiel van Crevel)"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Research School CNWS.Leiden,the Netherland,1996年。)。
建国后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日益狭隘的理解,使新诗“欧化”倾向得到制止,但也走进了所谓“民族化”的误区。而“白洋淀诗歌”更是有意识地急于摆脱旧的诗歌套路,努力突破“民族化”的束缚,向西方诗歌靠拢。不过,由于诗人们对西方文艺思潮接受上的偏差及过于求新求异的态度,在弥补新诗的浅陋同时,这种对“异国情调”的追求也使部分白洋淀诗歌显得生硬、浮泛,感觉隔膜。
在白洋淀诗歌中,多多的诗可能是“异国情调”最浓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日瓦戈医生》,还有《玛格丽和我的旅行》等。诗的前半部分,诗人铺开笔墨大写“玛格丽”和“我”周游世界,黑海、夏威夷、威尼斯、英国点心、西班牙牛排等词语充斥诗歌的“A”部分。 诗的后半部分(B)有一个转折,“呵,高贵的玛格丽/无知的玛格丽/和我一起, 到中国的乡下去/到和平的贫寒的乡下去”。如果说, 这种前后对比的构思表达的是“中国沉重的现实留住他们思想感情的脚步,在走出一两步之后,终于又回到中国这无辜然而苦难的土地上来”(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第406页。), 那么就难以解释这诗的异国情调十足的结束部分:“麻脸的妻子在祭设感恩节/ 为孩子洗澡,烤热哄哄的圣糕/默默地举行过乡下的仪式/就开始了劳动人民/ 悲惨的圣洁的晚餐……”因此,本文认为,基于当时封闭的文化氛围,与其说这首诗旨在回到现实中国,不如说是“异国情调”这种审美追求的一次集中展示。
“白洋淀诗群”这一文学史现象是独特的。尽管这些诗受到时代环境的种种限制与影响,但并不妨碍它们拥有成熟的、独立的诗歌品质。不过进一步考察也会发觉,它的某些“独特”之处,又是文学史中具有延续性的线索或环节。比如“白洋淀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当然有文革的催生作用,但同时它又是中国新诗几十年来在现代主义领域探求的一个部分;再考虑到那些同期或更早尝试新型写作的人们,如食指、黄翔、依群、昌耀、老诗人郭小川、穆旦等,就可以发现,一种艺术形式,往往是一种艺术思维,它受时代制约,但也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越这种制约。这种潜在对抗,是文学史中不断重复的现象。再比如“白洋淀诗群”接受外来影响的具体情形,在新诗史上是独特的,但仍然没脱离新诗诞生以来与西方诗歌形成的冲击和回应模式。白话新诗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没有这一模式,它是没有能力自我完善的。
也许,再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沉淀,“白洋淀诗群”会和“朦胧诗”、“后朦胧诗”等一起泯灭其独立价值,而共同作为中国新诗的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思潮进入文学史,但是现在,作为在特殊背景下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仍然有必要对其独立性进行梳理和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