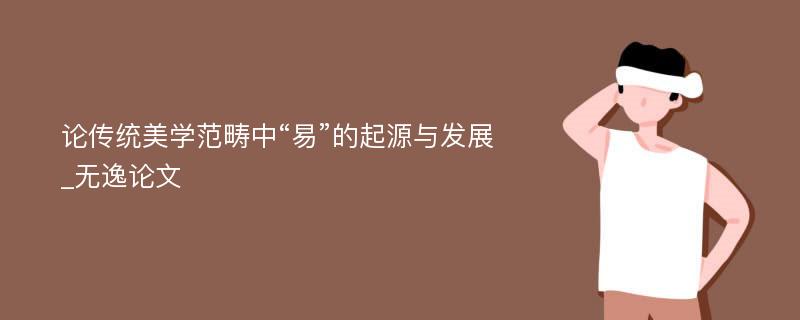
传统美学范畴“逸”的源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美学论文,范畴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式,“逸”是一个始于人物品藻的中国传统美学范畴,是具有中国思维习惯的审美把握方式,尤其是文人艺术追求的审美典范。在起源阶段,其审美对象主要是隐于山水的人和由此发端的山水艺术;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 “逸”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美的概念、范畴”存在,甚至连“美的形容词”都不是;在东汉之前,“逸”几乎都是一个具负面含义的评价语汇,指代“逸豫”等生理欲望的享乐与满足,“逸民”在大众眼里是一些贪图享乐、不劳作的人。不过在孔子、老庄等人的学术著作中已有了正面的指代,且对他们的人格品质都加以褒扬。到了魏晋时期,伴随自然美的被发现以及文人的自觉和对生命的审美体验,“隐士”、“逸民”们的生活得到社会的推崇;这样,随着人们对人物的品赏从政治才学视角转向审美鉴赏的方向,“逸”就逐渐发展成为“美的形容词”并最终发展为“美的概念、范畴”。 “逸”的字面含义在最初也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闲适、安逸。《说文解字》中云:“逸,失也,从辵兔,兔漫池善逃也”。可见,“逸”最初是一个动词,其含义是指奔跑、逃跑。如《国语·晋语五》:“马逸不能止”;《左传·桓公八年》:“随师败绩,随侯逸”;《北史·齐高祖纪》:“见一赤兔,每搏辄逸”。它的引申义为散开、弥漫。如陶渊明:“少时壮且厉,扶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杂诗其五》)。也就是说,不管是指人,指动物,还是指思绪;“逸”都是作为动词,表示跑开、飞散。 那么,它是如何演变成“美的形容词”进而成为“美的概念、范畴”的呢? 朱光潜先生说,“想明白一件事物的本质,最好先研究它的起源”①。所以,想要厘清“逸”的内涵以及它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审美范畴的,就得追究它的源流。 一、“逸”的最初涵义 “逸”作为一个形容词,一开始主要用于形容人的散漫状态和不关心社稷、贪图自我享乐的行为。如《诗经·十月之交》:“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这里的“逸”,意思是身体的懒散和生理的享乐。 基于这层含义,《尚书》中专有一篇《无逸》,是周公专门为告诫周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而写的一篇从理论高度否定“逸”的文章。周公上来就开门见山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意指君王只有亲身经历过耕种劳作,才能理解“小人”之所以贪图安逸的缘由就在于父母只顾自己劳作,而忽略了对孩子的教诲,导致其“乃逸乃谚、既诞否则”(即安逸、跋扈、自大,还不守规矩)。周公在文中进一步列举了诸多身为帝王应该“无逸”的理由,表明“逸”是贪图享乐表现出来的状态,它的对立面是“勤谨劳作”,所以应该否定“逸”。也就是说,“逸”作为一个形容词在早期是一个负面的词,最常用的是“逸豫”。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白驹》,云:“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意思就是王公贵侯们沉浸在无限期的安逸享乐之中。 由此可见,就“逸”的本义而言,它是一个贬义词,用以形容统治阶级贪图享乐的人生。《汉书》中多次提到周公的《无逸》一文,书中称之为《母逸》、《亡逸》;另外,书中凡出现“逸”、“逸豫”、“逸民”等字样多伴有否定性评价倾向。如“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故官无废事,下无逸民……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丽,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汉书·成帝纪第十》)又如:“有逸民,兹谓不明,蒙浊,夺日光。”(《汉书·五行志第七》)周寿昌注曰:“逸,安也,怠惰之意,故其字亦作佚,逸民废事,对举见义。”“逸民”是指贪图享乐、不事劳作的人,“逸民”多了就会造成农作物遭受虫害而无收成。“逸豫”就是贪图奢侈物欲——“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丽,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就是现在说的“物欲横流”,就会败坏社会风气。“逸”的这一层涵义在道德批评领域一直延续在中国历史中,直至今日。北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有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这个观念与周公的《无逸》篇是一脉相承的。跟“逸豫”相通的是“骄奢淫逸”,出自《左传·隐公三年》:“骄、奢、淫、佚,所自邪也。”文中的“佚”即“逸”也,这是卫国大夫石蜡劝告庄公时说的话,意指“骄横、奢侈、荒淫、好逸”是人之四大恶习。 自有周公作的《无逸》篇,一直到两汉时期,“逸”大多集中于享乐的本义——生理享乐——而被置于负面评价之中。但随着有德行隐士的大量出现,“逸”、“逸民”的含义开始了它们的延伸、扩展,即华丽转变和升华。 二、逸豫之逸向审美之逸的转变 与大众对“逸民”的评价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理论著述中,对“逸民”的评价多是肯定倾向的,他们摒弃了“逸”贪图享乐的负面含义,将之引申为闲适,用于形容人的安闲悠然、放松自由的精神状态或气质风度。“逸民”也随之特指具有这种气质状态且甘愿在野为“民”的人。我们可以从儒、道两家的著作中对此窥得一斑。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逸民”做出明确界定并给予了肯定评价。他在《论语·微子》中有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何晏《集解》云:“逸民者,节行超逸也。”朱熹在《四书集注》注曰:“逸,遗逸。民者,无位之称。”并进一步解释道: “七人隐遁不污则同,其立志造行则异。伯夷、叔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盖已遁世离群矣。下圣人一等,此其最高与!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而不枉己,虽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伦,行能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则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权而适宜也,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乱大伦者殊科。是以均谓之选民。” 由此可见,在儒家那,这些“逸民”虽然“隐”的动机不同,但他们立身行事合乎廉洁的社会行为准则,是一群为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放弃对俗世权力的追求具有高尚品行的“有德之人”;而不是贪图物质享乐的“逸豫之人”。“逸”不再是主体外在行为方式的形容词,而转向指代主体更高的理想追求的精神层面。 “高士”(它与隐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隐者等称呼一样,都指同一类人)的称呼是根据《易经》来的。孔颖达《易经注疏》对《易经》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卦辞释曰:“最处事上,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耸高慕,尚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高尚其事”是他人的评价,而以“高士”、“隐者”、“逸民”们自己的心态来看,“不事王侯”是顺应本性的自觉选择,其目的就在实现个体生命的自由。对于这一点,同为“逸民”的老庄作了深刻的理论阐述。 老子认为富贵如浮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九章》),告诫人们要珍重个体生命自由,不可为名利所缚。否则,就会“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其结果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庄子·齐物论》)。例如后来秦朝的李斯,位列人臣,集富贵荣华于一身,可由于他被名利所束缚,最终不免与“仓廪之鼠”一样,沦为阶下之囚。 庄子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庄子列传》) 为了个体生命的自由,宁曳尾于污浊之中,自甘清苦,而不企慕庙堂之上的光鲜亮丽。如果我们认为这似乎有些“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是当时科技、生产力低下造成的生存困境之下所作的“白日梦”。这当然是一种曲解,是我们现代人所犯的一种病——认为精神的富足依赖于物质的丰富。因为,他们并不是消极、被动的选择者,而是积极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觉地坚守内心至高的理想——“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所好也”(《庄子·刻意》)。所以,基于本性的追求,他们自然就不会束缚于高官厚禄、受制于“有国者”,从而得以“自快”,得以充分享受生命的自由。这与汉代成帝时期民众企慕的“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丽,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的“逸豫”是完全相反的价值观。“逸”之于老庄,已成为了自由、闲适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企慕“千金”等“重利”和“卿相”之“尊位”的“逸豫”享乐。 至此,“逸”从针对统治阶级的负面评价转化为针对士人阶层的正面评价;即完成了满足外在物欲的享乐快感向满足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快感的超越,发展成为了标志顺应本性、追求自由的“适性”之“逸”,用来形容那些远离俗世利禄、有文化教养且具独特价值追求的隐逸人士。这种“逸乐”显然与物质财富无关,富也好、贫也罢;贵也好、贱也罢,那都是“外物”。老庄之“逸”之所以能超越“逸豫”,让他们的“德性”能摆脱儒家的虚伪性,就在于他们秉持“自然”的“天道”②。 孟子将“逸”的这种正、负两面加以明确区分:“人之有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即当人们衣食足之后就应当施以教化以区别于禽兽。孟子对教养、修身的强调对“逸居”之民去除“逸豫”是相当重要的。这对汉代隐士大量出现后,随着魏晋之际老庄思想的复兴,隐逸人格之所以能得到推崇和褒扬是相当重要的。试想一下,如果这些隐士“逸居”而无教养,与禽兽无异,又怎能有人格魅力?唐朝的颜师古可以说是接着孟子讲的,他给“逸民”下了个定义,在注《汉书·律历志》时写道:“逸民,有德而隐居者也。”颜师古没有把“逸民”简单地归类于“隐士”,而是明确了“隐”只是“逸民”的外在行为方式;有德行才是“逸民”的身份标志。这样,儒家强调的“逸”的正面含义和道家发掘的“逸”在“圣人”、“神人”、“真人”等高人逸士的自然品性就在颜师古的这个“逸民”定义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唐人编撰的《北史》“隐逸”篇已开始引述了《周易》、《诗经》、《礼记》、《论语》等文献的相关论述并指出“逸民”是这样一群人:“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贫贱。或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或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将“逸民”从怀有“兼济天下”情结的“士”群体中区分出来;篇末再次指明了这一人群的特质:他们“非伏其身而不见者,非闭其言而不出者,非藏其智而不发者,盖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北史·卷八十八·隐逸》)。强调了“逸民”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内在精神品质,而不是外在的生存方式。至此,“逸民”的形象就非常生动鲜明且积极正面了——即“逸民”是具隐退倾向且有文化、有品行的人,他们“安时处顺,与物无私”,他们所成就的“隐逸人格”正是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生存方式的主要价值追求。他们在这种审美把握方式中体会到了审美的快感,证明了当“逸”停留在生理享乐层面时是负面的,与禽兽无异;当“逸”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审美享乐层面时就是正面的,是一种美的品质,是生命存在的价值和乐趣。 三、“逸”作为审美范畴的基本确立 隐、逸在历代文献资料中常伴随出现,在历代史书中也几乎都专有“隐逸”一章。在现实历程中,“逸”的审美转变是伴随“隐”而产生的,“逸的基本性格,系由隐逸而来”③。生命的表征就是个体活生生的生活。个体的生动具体的生活方式是个体价值体认的实践途径;也就是说,个体所追求的精神世界或者超越俗世的心灵生命是可以也必须寓于有限、具体的基于现实经验的生活方式的。从这个视角来谈,“逸”是前者,“隐”是后者。 “逸民”是具有隐逸倾向的人,但他们与“隐士”还是有区别。《说文解字》云:“士,事也”,又云:“事,职也”,也就是说“士”首先是一种职业人群。又有云:“仕,学也。从人从士。”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学也。训仕为入官,此今义也。古义宦训仕,仕训学。……是仕与士皆事其事之谓。学者,觉悟也。事其事则日就于觉悟也。若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仕于朝也。”指出“士”就是在朝为官且具有一定觉悟——学且优的人。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如《左传》中有一段关于16位“才人”的记载,这16人,首先自身都有渊博的学识——“齐圣广渊”,高尚的品格——“明允笃诚,忠肃共懿”,还有高超的情怀——“宣慈惠和”;修炼了这些“学养”之后耐心地等到帝王的赏识和举用,就像“臣尧之舜”一样成就一番家国天下的事业。这段文字中还显示了另一重要信息,那就是帮助帝王教化万民乃是“八恺”、“八元”这样的文人的职责,即他们主要的“事”(《左传·文公十八年》)。 孟子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他们如果“失业”了,就丧失了存身立命的方式。所以,对于“隐士”而言,“隐”就是他们“失业”或“待业”又不肯放弃“学”还想“独善其身”而选择的一种行为方式。历史文献中对于“隐”的解释不尽相同,《论语·微子》中详述了儒家关于“隐”的含义的理解。这是《论语》的第十八篇,主要讲述了当时与孔子“道不同”的各位世外高人、圣人。其中,长沮、桀溺二位“隐者”知孔子一行人身份后对问路的子路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朱熹注曰:“辟人,谓孔子。辟世,桀溺自谓。”《说文解字》云:“隐,避也。”《晋书·王嘉传》里的“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指的就是这个含义。可见,“隐士”最初的身份标志是一致的,那就是肉身远离世俗社会、退避山野。随着社会发展,“隐士”未必一定是远离俗世、隐居山野之人,他们的群体构成也越来越复杂,并出现了分化:有“大隐”、“小隐”之分;有“朝隐”、“吏隐”、“中隐”之分等;他们之中有为“道”而隐,有保身而隐,有彻底的隐士,也有半隐半仕之人等。在这些类别划分中,还有深层次的区别,如杨雄在讥讽自称“朝隐”的东方朔时就说:“昔之隐者,吾闻其语矣,又闻其行矣。”((汉)杨雄:《法言》)可见,在杨雄的眼里,“隐者”已有真、假之分了:真正的“隐者”应该是有学养、有规范行为的,而东方朔则是“假隐”。 儒、道两家对个体选择“隐”的动机有不同解释。儒家的“隐”是与“仕”相比较而存在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即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夫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夫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儒家之“隐”带有保身、存命的功利需求,是做官不成后的无奈选择,遵循的是“人道”。也就是说,未必所有的“隐”都能“逸”,更多的“隐”是为了“出”,是主体的一种“政治选择”:如伊尹、傅说、姜尚是待时而隐——“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仕”也;伯夷、叔齐是将“隐”当成了不满当朝者的政治抗议手段。道家之“隐”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需求,带有“逸”的属性,是身处自然且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因而发自内心地享受“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庄子·刻意》)的世外生活。即道家的“隐”不是出于外在压力的迫不得已;而是出于主体对至高理想追求的主动选择,遵循的是“天道”。从历代史书中“隐逸”章节记载的人物传记来看,这些人群中有许多并不是自觉追求精神人格的独立自由而选择“隐”,更多是因为入仕不得、无奈退避山林的现实人生中正好凸显出了对“闲适、逸乐”的自由精神价值——“逸”的体认;当然,也有真正的“隐者”、“逸民”——即有德行的隐者——对“逸”的自觉追求。 可见,“隐”和“逸”两者各有独自含义。首先,从历史形态上来说,“隐”有真假之分,如元代文人张养浩在昭告自己“隐”的理由时说:“也不学严子陵七里滩,也不学姜太公磻溪岸。也不学贺知章乞鉴湖,也不学柳子厚游南涧。俺住云水屋三间,风月竹千竿。一任傀儡棚中闹,且向昆仑顶上看。身安,到大来无忧患;游观,壶中天地宽”(张养浩:《雁儿落兼德胜令》。张养浩明确指出了历代“假隐”类型:严光是独善其身,姜子牙是走“中南捷径”之徒,贺、柳是迫于时运、避祸之隐,都带有自身功利目的;自己则是和陶渊明一样的“真隐”——身安田园、亲近自然。“逸”则无真假之说,它在经历了含义的华丽转变之后,主要用于指代有文化、有德行而优游山水泉林的人士。其次,从本质内涵来说,“隐”是主体反抗外在压力的一种行为方式,但这种行为在很多时候,伴随着内心对主流价值观的难以割舍,其心理基础是无奈、压抑。如所谓“朝隐”之士就是对世俗功利难以割舍且难以忍受寂寞、清苦但又向往山水寄情的人,他们的“隐”带有强烈的无奈感。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文人的“仕、隐”煎熬也是由于“隐”的这一心理基础造成的。而“逸”则主要用于指代主体内心精神体验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价值追求自觉影响下的一种行为方式,当其含义从物质、名利等外物带来的享乐转向内在独立精神的快乐,相伴随的是自我独立人格的被肯定、被彰显,其心理基础是享受、畅快而无丝毫的无奈感。如两晋时期张华德一首招隐诗《赠挚仲洽诗》中有言:“君子有逸志,栖迟与一丘”,又如被后人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返回自然”就是“适性而为”的自觉选择的行为。 “逸民”的主要身份特征不是具体行为方式上的“隐”;而是内在精神上的“高尚其事,不事王侯”。一句话,“逸民”是在“野”的有修养的“无位”之人。也就是说“逸民”是超越了政治上得意与否、物质上富足与否的知识分子,是泛指一类人,这一类人具有“逸”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隐”对于“逸民”而言,不是反抗外力的被动选择,而是本性使然。“隐士”和“逸民”在这个层面上的区别就是,“隐士”还是“士”,是退避山林、乡野的“过去之士”或“未来之士”;“逸民”则是“民”,没有当官的愿望,是悠游山水林泉的“有德者”。“隐士”的“隐”是被动的、后天的;“逸民”的“逸”是主动的、先天的。“逸”是传统文人去群体化的生活审美化的产物,彰显的是主体对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审美追求。也正是这一点使其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自然选择,并发展成为重要的审美范畴。 注释: ①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1页。 ②《庄子·在宥》篇有云:“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老庄之“逸”是他们自然本性之理想追求的自然表征;而不是出于对外在世事的对抗、对高洁品行的刻意追求的结果。也就是说,道家提倡人们追求的是“天道”,摆脱了一切“外物”的束缚,尽享身心俱自由的“逸乐”;不会因为“有为”的刻意而感到“系累”。 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