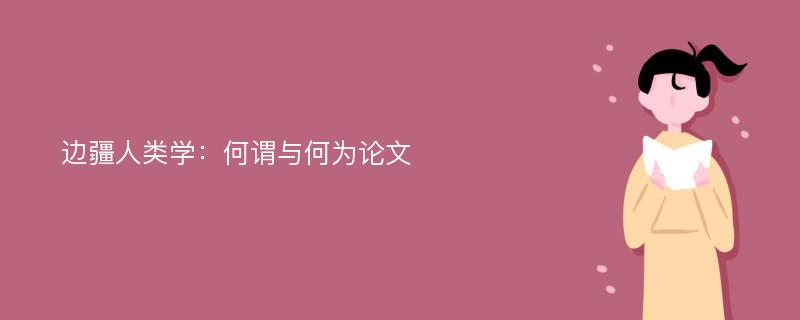
边疆人类学:何谓与何为
何修良 牟晓燕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 20世纪中叶以降,全球化成为理解国际边疆社会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概念,促进了边疆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与分殊化。以黑斯廷斯·唐南、T.M.威尔逊为代表提出了边疆人类学,随后一大批人类学家参与研究,旨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中重构边疆理论。边疆人类学无论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都提供了新知识与新范式,多角度、全方位地拓展了边疆研究,形成了人类学视野下与众不同、斑斓多彩的边疆观。
关键词: 边疆;边界;边疆人类学;跨界民族
一、边疆人类学提出的背景
边疆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客观存在,在人类学早期,研究者迷恋于“自我知识之谜”的学科探索,预设“他者”文化所指之后,主流叙事下的边疆被幻化成 “蛮荒之地”、“落后边缘”、“蒙昧群体”的固化的常态意象。边疆似乎被遗弃为一个虚无存在的概念,其误解在于前提性地对“他者”魅惑化的简略理解和粗线认识,进而忽略了所在的不同社会背景和人文地理空间。梳理边疆知识发展谱系,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边疆在人类学学科背景中,有着不言自明的切中肯綮的内在联系,不论国外经典边疆学名著,还是我国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研究,两者都蕴藏着源远流长而且意义深远的知识交叉的学术思想史。但真正意义上的边疆人类学兴起是近二十多年的事情,在“科际”整合与时代发展相互激荡的学术知识交流与增长中,边疆研究以自身特殊知识生产背景和内容进入到了人类学关注的视域与讨论之中。在学科发展史上,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和人类学的研究起步基本处于同一个时代,都肇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人类学逐步由体质人类学的狭窄视域走向了广阔的文化人类学,经典著作整体涌现,研究学派琳琅满目,理论与方法日臻完善。边疆理论也不断深化,形成了陆边疆、海边疆、高边疆、底土边疆、利益边疆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两者理论研究齐头并进的纵深发展奠定了边疆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产生的知识基础和发展态势。
在研究对象上,边疆研究本身极具历史特性和现实向度。全球化发展使边疆从原来的边缘地带走向了备受重视的前沿区域,偏远、落后和神秘化的边疆认知被人们重新解读、建构与赋意:边疆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图景,多样边疆观相互辉映。传统封闭的边疆被重新激活与唤醒,边疆区域民族、宗教、语言、习俗、亲属等边界主体往来频仍,边疆如“罅隙”[1],在最为严密之处也能穿越过去,边疆区域的文化对话、经济往来与互动场域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坦荡开阔。人类学以文化为核心展开研究,采用田野实证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边疆、边疆人群、民族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共生互依,且又与人的行为和在地环境相关,因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边疆研究的内容指向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和相向性。人类学理论内容和方法为边疆研究提供了新视野,边疆之地因融合多样民族和交织的多元文化,与倡导多样性、特殊性和异质性研究的人类学出场提供了特定研究对象和叙事内容:边疆领土、地方性、互动与交往等研究取向与“人类学主题相近一致,都立足长时间段的定居研究,突出民族志在社会研究中的文化角色”[2]。
(5)加强缺陷处理后的养护,防止出现二次缺陷,已处理混凝土表面快要出凝时在表面涂刷一层养护剂,保证涂刷均匀,不漏刷。
根据可靠性维修理论,在设备故障前采取恰当的事后小修及预防性维修措施,能够降低设备故障率,保持或恢复其固有可靠度,防止其性能衰退。但若预修周期太短,过于频繁的维修会导致设备可靠性迅速降低,过早更换,增加预防维修费用,造成过度维修;若预修周期过长,虽然能节省预防维修费用,但维修次数的减少也可能使设备不能得到及时修理而增加故障隐患,导致事后维修费用与停机损失增高,造成欠维修。因此,应合理确定有限使用时间内的最佳预修次数与弹性维修周期。
从学科发生学看,20世纪中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构和地缘政治学的重新崛起,民族国家边界的性质与内容发生了急遽变化和巨大变迁,边疆与边界成为了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人类学的出现是边疆研究和人类学发展共同的需要,理论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边疆内涵的理解日益多元而深刻,边疆民族与多样文化的互动越来越活跃,“危险的边疆”(The Perilous Frontier) 性质褪色,边疆地带日益成为了最有活力的区域。这反过来也需要人们更具体地理解边疆,其突出表现在越来越多的边疆民族志和田野调研成果不断涌现,“位于东欧、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亚、北美和南美区域,涵盖殖民时期、前殖民时期、本土、前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边疆的案例研究正在铺开”[3],边疆研究越来越具体化和生动化,文化交往、族群身份、边疆社会生活与实践成为了观察、认识边疆形态的重要内容。边疆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日益凸显出特殊地位,“边疆成为人们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和互动的完美实验室”,吸引着愈来愈多的人类学学家进行反思与追问:“边疆研究如何增进我们的知识并加深对当地民众和文化实践的理解?如何将这些知识吸收到我们的分析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发现对于人类学学科认识论又具有怎样的意义?”[4],对边疆现实的书写及实践问题的回应研究方兴未艾,为人类学学科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和开辟了新场域。
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使人类学学家逐渐认识到,边疆不再是一个区域,而是一种社会形态,一种社会体系。边疆人类学研究视角从关注宏大议题转向了更多关注边疆日常生活实践,地方性展演及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构成了主要内容,边疆人类学“展示了地方研究的价值……边疆地区之间、国家以及政府之间的双边关系优先于将国家视为背景的地方文化”[31]。通过不同边疆区域的地方意义描述,深描边疆变革、边疆互动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给边疆社会带来的影响,边疆社会性空间在不断交往与交流中改变与融合,研究内容也发生了根本转向,“对来自边疆地区的声音的汇集和承认激发了对人类学标准的再评价,并且引起了一场在全球性语境背景下关注地方层面的行为、生活以及境况的创造性争论”[32]。人类学家利用边疆生活并越过边界边民的能动性去思考边疆是什么、能做什么并且在何时被改变、维系和消弭。在具体途径上,一是站在政策制定者视角去思考边界施于民众行为的影响;二是从基层社会的角度去理解边界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前者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角度,更多只是聚焦在制度性的行动者上,而后者“自下而上”的过程,则是通过居住在边界边民的日常行为的功能模式中表现出来[33]。人类学家眼中,边界被视为边疆社会生活模式研究中的重要变量,已经深深镶嵌在边界两侧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行为中,人类学的研究也从最初的“理论构建”走向了“行动主义”。另一方面边疆人类学立足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边疆实践,注重地方性研究与在地化治理的微观呈现,在美墨边界深处,“边民的经济行为深深地镶嵌在墨西哥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反映出了传统的移民输出社区的居民在切身(或亲戚)的跨国经历中,进而产生出对美墨边境较为复杂的自我感受”[34]。进一步理解,边疆区域中不同边疆主体对同一种行为投射出共同的行动倾向,但又根据各自不同的“国家/社会”场域中长期所形成的文化积累而显现出多元化形态,在多元性中逐渐发展出某种秩序的同一与共生的一致。
二、边疆人类学的提出与内容
边疆是什么构成了边疆人类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在知识考古学脉络中,边疆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既受益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进展,也深受意识形态、族群、宗教、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为此唐南指出,边疆人类学发展“从关注边疆包含什么转向边疆本身以及他们所参与其中的边疆过程”[5],其边疆观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特征,这构成了人类学家边疆研究的切入点。在分类上,他们认为边疆内涵包括三方面,“边疆是隔离和连接国家的法定边界线;存在着划分和捍卫边界线的国家实体结构,是由凝结在国家领土的公民和机构组成;具有着变动的幅度,或拓展开来或分离过去的边疆领土地带,人们以此交往各种行为及其与民族国家身份相关联的内容”[6],与传统认知相比,边疆内涵日益多样性和模糊性,不仅局限于政治边疆意义,文化边疆的含义也日益凸显。在对爱尔兰边疆和新教徒身份研究中,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边疆的文化性质,指出边疆是“矛盾的、模糊的、能够替代和混杂性区域。作为转换、违抗和文化实验的象征等构成了人类学及有关学科的边疆内涵”[7]。与传统研究相比,人类学家眼中呈现出不一样的边疆研究视角和观测点:边界外人群眼中,边界是国家间相遇与分割的分界线,而人类学家则把边界“看做无数互动的点”[8],视角的转换使得传统研究中所理解的静止或较少变化的边疆性质日益式微,流动的、不断变化的边疆特征初具,“边疆越来越被视为‘过程’而不是‘结果’,是内部和外部机制性关系之间一种波动性张力的结果”[9],边疆内涵从原来单维的、静态平面化走向了多元的、动态立体化性质。另一层面上,他们强调,边疆不再是一个孤立性的地理与物理意义存在,边疆内涵逐步彰显出多种因素相互塑造的内在关联性和复合型特质,边疆逐渐被“视为能够通过经由文本、话语、实践和事件这些日常生活中各异的表述性的形塑和再造而一直浮现的事物”[10]。边疆复杂的社会面向在人类学细致解剖和描记中铺展开来,开始不断关注和描述边疆混合性和关系性的多样形貌。由此理解边疆,唐南和威尔逊集中研究了文化边疆、领土和政治边疆、社会和象征边疆等三个方向,他们称之为“边疆效应”( Frontier Effect)。
20世纪9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黑斯廷斯·唐南(Hastings Donnan)、T.M.威尔逊(T.M.Wilson)率先提出了“边疆人类学”,拉开了从人类学视角观察、理解和重塑边疆的序幕。作为边疆人类学的拓荒者,他们初步想象和勾勒了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观和研究取向,被冠以边疆人类学的第一代研究者,随后一大批学者接踵跟进参与研究,共同构筑了边疆人类学发凡。
文化边疆存在于各种跨文化及所形成的不同物质流动、交换与增殖中,“边疆和边地不仅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边缘,而且存在于文化相遇的任何地方”[11]。“边疆”成为了全球文化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特殊隐喻,文化是以共享、一体和互融的整体性特征进入到边疆隐喻之中,蕴含着不同边疆内涵与身份认同差异的碰撞、联系等结构性张力。与实体边疆相比,边疆隐喻的能量与影响愈来愈大,为此他们强调文化边疆研究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文化和实体意义边疆之间联结、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政治意义的边疆突出表现在对边界空间地理场域与主权承认与作用的过程与功能描述,从时空视角记录地方社群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研究“集中在社会关系层面,这些关系部分是由国家界定的,但也超越了国家的领土限制,而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本土国家的结构及其与邻国的关系”[12]。地缘政治标定的物理意义领土边疆,立足现实主义分析,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的地方社群、跨界民族活动与边疆生活等地方性行为以及这些如何影响民族国家权力,走进了人类学议题中,进而获得了在更大的政治架构、更广阔的政治进程中观察与思忖,强调研究集中在边疆地方和地方之外的影响因素分析。象征边疆的分析是建立在人类学家巴斯的族群边界研究基础上的,“族群的共同性部分是由相互之间的尊重和互补性的文化特征构成,互补性可以提升族群间文化的独立性和共生性”[13],通过边疆两侧和跨越边疆视角界定边疆社群成员资格以及形成的社会关系秩序是关切的重点,为此唐南和威尔逊特别强调社会边界的关系性本质,认为族群互补性使得边界是能动的,是可以跨越与交流的。作为人类学家就是要阐释族群边界内部、外部类别及更广泛的结构性影响,描述出不同主体在象征层面得以区别开来的边疆内涵。
目前在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选择中,利用自身积累的自有资金占比48.40%,通过银行贷款筹资占比38.89%,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融资仅占2.39%,其他方式不足13%。不论企业处于哪个阶段,仍然非常依赖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试验的玉米品种统一为五谷568,由甘肃五谷种业有限公司选育。玉米配方肥均由甘肃省云蓝磷复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氮+磷+钾≥35%,15-16-4)。普通地膜由甘肃振海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宽1.2 m、厚0.01 mm。可降解地膜由兰州鑫银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宽1.2 m、厚0.01 mm。
主体性描述主要表现在对边疆主体文化特征的追问与反思。阿瓦拉兹将边疆人类学划分为两类,“写实主义者”(literalists)所关注的是现实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定居、环境、身份认同、劳工以及健康议题。 “反写实主义者”(a-literalists)则关注地缘政治边界的社会界线以及行为中的矛盾、冲突及身份转变问题[18]。埃曼主张通过两种视角关注边疆,即政策问题路径与边界意象路径[19]。无论是“反写实主义者”的身份与行为的关注,还是“边界意向路径”的文化叙事取向,都体现了边疆研究聚焦边疆群体的主体性文化描述。由此边疆浪漫性质的阻隔结构与功能渐渐褪逝,这对注重经验性和异质性叙述的人类学学家而言,其研究从一般意义上抽象的文化论争走进了边疆存在、可供体验与观测的多彩文化之中。他们认为,边疆是文化习俗的社会建构过程,“在文化生产上充满着危机和创新,成为文化实践、实验、驾驭和控制的开放地方”[20],凡文化接触相遇之地,皆可谓边疆,这一点,维克多·特纳则更为深得其趣旨,“边界可能是文化被明显地拆解的地方,此处是文化加文化,而不是文化与文化”[21],人类学视野中的边疆,文化以复数面貌呈现,夯实了松软的边疆,也建构了实在的边界。与此,“文化社区”因不断跨越边界的人员流动增加而不断涌现,这种边疆文化的“共生现象”因全球化的“时空延展”和“时空压缩”而显得更加鲜明,“边界被缩压为一个(文化)意象时,若是该意象象征着广泛的政治或理论态度时,对边界的认知就会变得缩小和非区域化”[22]。原有清晰的边界愈来愈模糊,边境社区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不再是不可穿越的,边疆观逐渐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结构性紧张,“纵横交错的相互联系大量发生,加之以时间变迁,可能消除各种持久的差异和认同身份……当人们一起跨越某种社会或文化分界线时,新的集团就会形成,并且由此明确他们之共有某种与众不同的性质。”[23]这种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思维方式表明,边疆文化是建立在互惠往来的基础上,是通过交互性的、互为主体性的方式实现,边疆主体从“我在”走向了“共在”。同样也可理解,边疆以人类学之名实现了边疆文化的“间性”勾连和弥合。
三、边疆人类学的承续与发展
人文空间的地理场域与社会属性塑造了不同的边疆风景,人类学视野中的边疆景观摇曳多姿,这构成了边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知识特征。全球化时代,边疆日益作为一个消解性词语,稀释着传统理论认知中边疆与政治、文化互为隐喻的前提性理解,边疆内容的差异性描述成为研究的显著特征。“第一热边”的三千多公里的美墨边疆、发展程度相同有着平行故事的欧洲边疆、相似历史遭遇和文化际遇的第三世界边疆研究构成了边疆差异性叙述的热点对象。当然,边疆治理特征也截然相异,美墨边界和欧洲边界由于世界最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相遇而呈现出大概相同的边疆治理意蕴:主权立场明显、管控边界严密、边界双方交流受限等,凸显出具有强制性特征的“硬边疆”性质;第三世界边疆由于历史因素承袭,语言、宗教、文化等相互差异性不大,主权意识淡化而文化意识突出、管控相对宽松、边界双方交流频繁,有着相对弹性的 “软边疆”意蕴。边疆现实情形的差异直接带来研究关切点的不同,美墨边疆巨大落差的政治经济边界关系促使学者们着墨于边界作为一种制度和机制如何进行流动的管理;欧洲复杂的边界关系使得学者们更为关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内外部边界的此消彼长以及边界的界限问题和网络化问题[16],第三世界边界则是另一番景象,聚焦边疆族群主体性的表达与抗争等相关内容成为了学者研究追逐的焦点[17]。由此管窥,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研究被放在了一个时空交错的宏大视野中:边疆研究不仅要关注传统形成的“时间之维”的历时态因袭演变,也开始关注现实的“空间之维”的共时态同在面向,政治视角、文化视角、社会视角的边疆研究互相交织。政治边疆观描述了边疆渗透性的特征,文化边疆观立足当地人视角感受与想象进行边疆解读,社会边疆观则注重边疆区域地方性实践和知识的发现与重绘。边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背景带来的相互交织境遇的差异绘就了边疆观多样的现实类型,描述与塑造了风格迥异、饱满多样的边疆图景。
(一)边疆的差异性
回顾与梳理唐南和威尔逊的边疆人类学研究,其理论研究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边疆人类学的第一代研究在很大意义上是以地方的、特定的及聚焦于领土的边疆概念为中心”、“尤其是涉及民族国家政治边界的研究,并未能系统发展有关理论”[15]。此后,边疆人类学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研究,一是研究视角不断扩大,从地方到全球,美墨、中东、欧盟、非洲边疆等逐步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强化民族志书写,微观呈现边疆社会发展;二是愈来愈关注边疆运行过程,从外部到内部,分析国家权力在场、族群互动、民众日常生活交往等与边疆的关联、塑造与影响。三是借用人类学理论发展边疆研究,从概念到方法,研究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在内容发展上,人类学家紧紧围绕边疆的“差异性”、“主体性”、“渗透性”和“在地性”四个特征论述展开,边疆所赋予的目的性事实转向了意义性存在,以此将边疆区域破碎的景观连缀成一幅相对多彩而完整的画卷。
(二)边疆的主体性
这些构建起了“边疆人类学”的基本内容和整体面向,“强调关注边疆如何被建构、协商和从‘下’往上看,这三个研究方向相互汇聚,成为评价和区分边疆人类学的基础”[14]。人类学视野的边疆是理念重新调整与边疆观重塑的过程,“再开放”了边疆研究视野,“再观念”了边疆理论认知,在全球化时代命题中,为边疆研究灌注了新能量,推动了边疆研究发展。
(三)边疆的渗透性
在政治边疆的研究取向上,人类学边疆研究不再仅仅局限在对边疆塑造过程的批判性审视与考察,也日益地“洞察边界和更广阔的空间之间政治想象的关系”[24],边界谓之“混沌边界”(fuzzy frontiers),“需要清晰明确边界的政治能量和民族国家所执行的政策对于边界两侧群体所带来的影响,这样才能清晰认识边民在复杂的民族、国家、语言的文化认同体系之中形成统一意见的过程,并能理解是如何建构自身认同”[25]。边疆的政治想象更为活态,空间不断扩大,不仅呈现出区域化意义的边疆,也逐步显现出世界意义的边疆。这表现在,边疆不仅仅被限制在固定区域中,而且延伸和扩展到“边界/中心”以至国家内部的整个范围内,表现出“高度流动的、延展性的和扩撒性的”[26],边疆不再是区隔与阻碍的象征,而是联结起双方日益紧密的生产生活和政治社会关系,“边界好像一层高度渗透性的薄膜”[27],博安南则更极端地认为,在跨国跨界流动的时代中,边疆空间特征消失,始终“围绕在我们身边”(all around us)[28]。在现实中的直接表现为,边界在不断地位移,可以在两国口岸地标处,也可以在一侧国家的内部出现,甚至不断地向国家内部更远的地方蔓延,人们对社群边界进行创造和再创造,常常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在瓦哈卡(Oaxaca)、墨西哥城和洛杉矶之间;中墨西哥(Central Mexico)和芝加哥之间;海地(Haiti)与纽约之间,可谓是“处处是边界”[29]。边界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增加了治理难度,边疆成为需要“那些对流动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地方”[30]。换句话说,人类学视野中的边疆像一个不断变化的潮标(tidemark),随时出现与转瞬即逝,此时 “边疆”就是不同文化、群体与社会之间相互交流、交往乃至交融的场域或状态。人类学在左右贯通的意义上实现对边疆周边共通性的认识,边疆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政治体验相渗透相融合,完成了边疆“政治场域”与“生活场域”的同构与聚形,所承载的边疆公共性内容得到了有效讨论。
(四)边疆的在地性
那么,什么是边疆人类学?包括哪些内容?具有什么样的学科性质?未来如何发展?回答和思考这些问题,对于边疆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采用Microsoft Excel进行数据整理,试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 SAS9.2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在图表中用不同字母上标来表示显著差异(p<0.05)。
在发展途径上,利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推动边疆研究成了显著特征。其中“阈限(liminality)”理论的运用是重点。在过渡仪式中,一般包括分离、阈限、重合阶段,阈限则是指有间隙和模棱两可的状态,阈限阶段的人群状态模糊不清和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认为边疆地带是一个特殊观察多元文化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借助特定的过渡仪式理解边疆民众经历的一场场阈限,理解他们身份的变化与行为的转变以及充满生成的力量和潜能。作为多元文化汇合的“中间”意象,边疆的阈限性、可沟通性和“之间”性的社会性空间有着更多的自由性和象征性,对此人类学家普遍认为美墨边疆是一条模糊的文化领域带,能够更好地观察边疆的跨境主义现象,美墨边疆也被称之为“阈限边疆”[35]。阈限理论大量地用于有效分析边疆群体行为的模糊性、离散性、过渡性、区隔性、暂时性以及被拆分的两侧社会特性,进一步拓宽了边疆人类学的理论空间。
在方法上,边疆人类学立足民族志分析,以整体性全景视野、历时态的演变视角、共时态的比较眼光关注和描述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们行为。随着研究推进,边疆民族志呈现出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和文本的多学科性。前者突出表现为“个人中心民族志”的出现与应用,人类学学家自身参与边疆的批判性与实践性特征昭著,代表作品有塔玛·戴安娜·威尔逊的《美墨边境上的“意象”:哈里斯科乡村的诉求》[36],作者深入墨西哥中西部地区的哈里斯科乡村地区,展现了边疆村民的所思所想所行,描述了边疆地带移入美国的移民个人史、家庭变迁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文化生态。文本的多学科性突出地表现为新民俗学的文化诗学的出现和运用,阿瓦拉兹在《美墨边界:边疆人类学的诞生》一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新民俗学的案例来描述边疆本土叙述者声音的“在地性”。写文化(writing culture)模仿——新民俗学运用,“新民俗学——一种文化诗学——已经成为了边疆文学和人类学的一部分”,描述了边疆一些“民谣、歌谣、音乐、文学与诗歌”等这些“小传统”,展示了双语(bilingual)、双文化(bicultural)和双国家(binational)的声音[37]在塑造变动边界中的新特征与新意义。边疆人类学叙事视角的多样与转变,因研究主体的拓展、文本的开放性、叙事方法多样化和关注内容细部而显得生动全面。
四、余论
边疆人类学从提出到发展至今,始终沿着理论与实践两条路线演进,通过对边疆地区深度描写,阐释了边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而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现有边疆社会形态演变和理论知识缺陷,形成了新理念与新范式。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理论特殊旨趣,拆除了束缚边疆理论研究想象力的知识障碍和学科壁垒,赋予了边疆与众不同的学科属性、研究取向与内容范围,进而勾勒出较为完整的、波澜壮阔的边疆历史与现实样态。
边疆理论研究始终存在着碎片化和弥散化倾向,在全球化时代,越发需要从学科上总结边疆研究的总体性情形,边疆人类学的产生满足了边疆社会的时代背景中对更加具有解释力、更为整体性的边疆理论知识吁求。近20年来,边疆人类学从提出到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作为一项新兴研究,毕竟有着“较长但并不深厚的历史”[38],还处于探索阶段,涉及一些实质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构成了研究者的新使命与新挑战。
参考文献:
[1]查日新.空间转向、文化协商与身份重构——霍米·巴巴后殖民文化批评思想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11(3).
[2]T.M.Wilson&Hastings Donnan.Nation,State and Identity at International Borders,in T.M.Wilson&Hastings Donnan(eds.),Border Identities :Nation,State and Identity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8.
[3][5][9][10][14][31](英国)黑斯廷斯·唐南.边疆人类学概述[J].袁剑,刘玺鸿,译.民族学刊,2018,(1).
[4][18][32][37]R.R.Alvarez,Jr.,The Mexican – US Border:The Making of an 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4,1995,p.447-470.
[6]T.M.Wilson&Hastings Donnan.Nation,State and Identity atInternationalBorders,in T.M.Wilson&HastingsDonnan(eds.),Border Identities :Nation,State and Identity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9.
[7]H.Donnan,Material Identities:Fixing Ethnicity in the Irish Borderlands,Identities: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Vol.12,2005,p.74.
[8]H.Donan&T.M.Wilson,Ethnography Security and the :“FrontierEffect” in Borderlands,in H.Donan&T.M.Wilson(eds.),Borderlands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Security,Power and Identity,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10,p.7.
[11][20]Hastings Donnan&T.M.Wilson,Border:Frontiers of Identity,Nation and State,Oxford:Berg,1999,pp.19-41.
[12]Hastings Donnan&T.M.Wilson,Border:Frontiers of I-dentity,Nation and State,Oxford:Berg,1999,pp.19-41.
[13](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5][38]张峰峰.论边疆人类学的提出及其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14,(7).
[16]赵萱.全球流动视野下的民族国家转型——基于海外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的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1).
[17]施琳.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J].广西民族学学报,2017,(2).
[19][22]Heyman,Josiah.“The Mexico-United States Border in Anthropology: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Vol.1(1994),pp.43-66.
[21]U.Hannerz,Border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49,Issue 154,1997,p.541.
[23](瑞典)乌尔夫·汉内斯.边界[J].肖孝毛,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4).
[24]Heyman,Josiah. “Constructing a Virtual Wall:Race and Citizenship in US-Mexico Border Policing”.Journal of the Southwest,Vol.50,No.3,Fences(Autumn,2008) ,pp.582-587.
[25]A.M.R.Pastor,Shame and Pride in Narrative:Mexican Women’s Language Experienc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4,pp.3-4.
[26]Mountz,Alison and Hiemstra Nancy.“Spatial Strategies for Rebordering Human Migration at Sea”.In T.Wilson and H.Donnan,eds.A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Wiley-Blackwell,2012,pp.455-472.
[27]劳伦斯.A.赫佐格.在全球城市时代的国际化城市结构:美国-墨西哥边境大都市[J].国外城市规划,1992,(6).
[28]Bohannan,P.Introduction.In:Bohannan,P.Plog,F.(Eds.) ,Beyond the Frontier: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Change[M].New York: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1967.
[29]Paasi,Anssi.“Bounded Spaces in a ‘Borderless World’:Border Studies,Power and the Anatomy of Territory”.Journal of Power,2009 (2) ,pp.213-234;Balibar,Etienne,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Verso,2002;R.R.Alvarez,Jr.,The Mexican –US Border:The Making of an 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4,1995,p.447-470.
[30]Guild,Elspeth. “Danger – Borders under Construction:Assessing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Border Policy in an Area of Freedom,Security and Justice”.Freedom,Security and Justice in the European Union:Implementation of the Hague Program(2006),pp.45-72.
[33]Paasi,Anssi.“Boundaries as Social Processes:Territoriality in the World of Flows”.Geopolitics,vol.3,no.1(1998) ,P.1-24.
[34][36]Tama Diana Wilson.Images of the U.S.– Mexico Border:Voices from a Rancho in Jalisco[J].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2003,18,(2).
[35]M.Kearney,Borders and Boundaries of State and Self at the End of Empire,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Vol.4,No.1,1991.
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What is and What Can Do
HE Xiu-liang MOU Xiao-yan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n important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borderland society and development,promoting the diversity and specialization of borderland research topics.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 was proposed by Hastings Donnan and T.M.Wilson,and a large group of anthropologists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aiming to reconstruct borderland theory in the grand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 provides new knowledge and new paradigm both in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in research content.It expands borderlands researc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in an all-round way,forming a distinctive and colorful borderlands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Key words: Borderlands;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Borders;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1-0113-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一般项目(批准号:18BMZ002)、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度国家基金预研学术工作坊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项目等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10-08
作者简介: 何修良(1980-),男,河南南阳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治理研究。
牟晓燕(1985-),女,山东烟台人,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族经济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胡成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