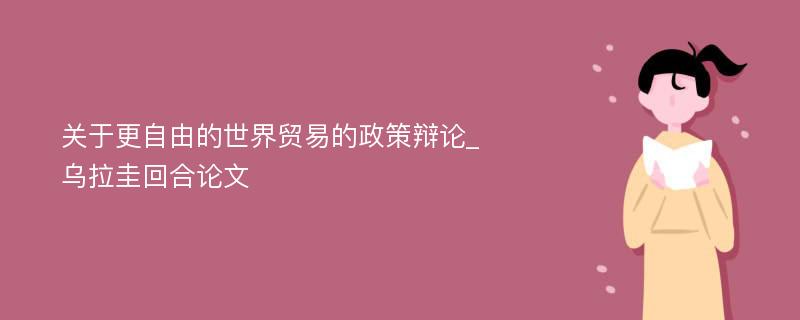
关于更为自由的世界贸易的政策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世界贸易论文,政策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论方面,美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确定世界新秩序的方法。在此新秩序下,交易、公司和技术是全球性的;但制度、文化和管理规章仍具有本国特征。
美国民主政体现正重新评估更为自由的贸易政策。在过去的47年间,凭借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庇护,贸易得到了自由发展。但是,GATT与世界银行或联合国不同,它不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GATT没有自己的成员——只有签约各方,没有宪章或条约性地位,它只是一个多边协定。杜鲁门政府依据“贸易协定法”(TAA)缔造了这个国际协定,此法授权总统进行双边协商以减少特定的关税。这些双方妥协进而推广到其它GATT签约各方。
1993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大学百年庆典的一次演讲中,就美国对于自由贸易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承认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对于目前全球性经济所有的……机遇,美国人在把握时不可能不带有亦喜亦悲的情感。”他承认,自由贸易使失业率上升,工资收入降低。但他进而指出,“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危机,因为这个新的贸易网将形成全球性的繁荣或贫困,而且各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与和平的前景皆决定于此。”接着,他向美国公民发出警告,如果他们想为自己的下一代期冀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他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向外拓展。
然而,大多数的美国人并不认为GATT能为其孩子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许多人认为,遍布全美的贫民窟和犯罪统计数字就是我们贸易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当美国人慎重考虑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影响时,有关就业、贸易和主权方面的辩论成为1993年的头版新闻。成百万的美国人把电视调到CNN,观看副总统戈尔和商人H·罗斯·佩罗就NAFTA展开的辩论。尽管后来通过了NAFTA,反对者们发誓要惩罚那些赞同NAFTA的立法者们,而且要经常让公众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新闻媒介的支持,在这些新闻媒介描述中,贸易政策并非作为各国各民族间互惠互利的交换,而是一种竞争。电视和广播新闻谈及美国与日本和中国的贸易“战争”,并且把欧洲共同体描述为“壁垒森严的欧洲”。报纸就“GATT之疾”和“美国愈发依赖他国”发出了警告。受公众这种喜恶相互交织的复杂情绪的影响,以及媒介引起的关注和特殊利益团体的活动,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就乌拉圭回合和倡议中的WTO寻求国会的批准。
对WTO的争论
尽管GATT卓有成效地运作了30年,但决策者们直到1980年才认识到,缺少一种正式的制度性结构阻碍了GATT的发展。随着GATT发展壮大到包括100多个国家,就越难达到有共识的决定。此外,GATT签约各方还找到了一些创造性的途径来绕过或歪曲GATT法则。国际商业董事长、专家学者、国会议员和贸易政策官员断定,GATT缺少一个正式的结构,是一种需要纠正的“先天性缺陷”。
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贸易决策者们认识到,GATT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立法支持。但是,他们对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支配世界贸易却不怎么热心。尽管如此,他们仍同意把为GATT创造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作为乌拉圭回合的一项重要目标。但是,乌拉圭回合拖延了七年多的时间,却未达到什么共识。为了使协商获得进展,GATT总理事长亚瑟·邓肯于1991年12月把协议草案公诸于众。这样,他就迫使贸易谈判者们把其对草案的看法与本国人民联系在一起。邓肯这种告之于众的做法具有变革性的意味。GATT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能够随时明了谈判的进程,并可以发表评论。许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多边贸易组织新章程的尝试性草案上。
尽管美国的谈判者的心态矛盾,并且各国对倡议中的WTO的权力实际分歧很大,117个国家最后终于在1993年11月15日达成了乌拉圭回合协议,以及替代GATT的新组织结构(称之为WTO),WTO宪章授予秘书处、总理事长和工作职员合法的权力。它还包括一个加强了的、统一的解决争端的机制。克林顿政府认为,新的WTO是GATT的进化,它将“包含现有的GATT结构,并扩展成以前从未充分包括的新法则……,WTO……协议将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相媲美的国际组织。”该组织在特征上将不会与现存的GATT秘书处有何不同之处。法律学者约翰·H·杰克逊总结说;“与现有的GTAA一样,WTO同样不会拥有实际权力。”
但是,许多著名的团体和个人并未把WTO看作是GATT的一场简单演变。他们联合起来,对把非正式的GATT变为正式的WTO提出质疑。环境学家和保守派担心WTO可能会影响联合国通过自己的法律和制定其环境与健康标准的特权。对WTO解决争端程序的改革,建立一种较正规的合法程序,并以其审核和解决争端,一些行业的代表表示了担忧。世界公民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拯救主权组织、保守派专栏作家帕特·巴恰纳、民主党众议员杰朗,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兰尼·普诺斯勒,杰西·哈雷姆斯和拉里·克雷格对新的WTO可能会不民主、可能会独断专行、可能会充塞些冷漠迟钝、平平庸庸的官僚表示了关注。55个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要求克林顿把对乌拉圭回合的表决权推迟到1995年7月。
到1994年8月,一个由GATT的共和党支持者和民主党与共和党反对者所组成的国会男女成员团体,赞成推迟表决权。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于9月31日宣布,他将通过在其委员会中控制立法完成的速度以阻止参议院对乌拉圭回合进行表决。众议院通过了把对乌拉圭回合的表决推迟到选举以后进行,对霍林斯的倡议作出了响应。推迟表决为WTO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国家的利益上赞同和否决WTO提供了一次机会。
主权问题
许多反对加强GATT基础建设的争论与那些坚定反对ITO(译注:指已流产的国际贸易组织)的言论引起共鸣。此外,WTO的反对者(同ITO的反对者一样)结成了一个擅长影响华盛顿决策的广泛联盟。WTO的反对者包括奉行类似人民党主义的人、孤立主义分子、工商界领袖、人权活动家、自由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和社区活动家。维系这个多派联盟在一起的力量就是主权。甚至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都担心GATT对美国法律的影响。例如,众议员纽特·金瑞琦直接从保护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把倡议中的WTO与“波斯尼亚地区的混乱和联合国的无能”联系在一起。他质问美国人是否“真的想要建立一个世界贸易的联合国吗?”
由一个新的、全球性的每每是不负责任的决策机构取代地方的、州政府的和国家的民主决策体系,这一主题恰好与GATT文本相呼应。按照前加州州长埃德蒙·G·布朗的观点,“这与我们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下的民主决策不同,在GATT和NAFTA之下,我们将要受制于一个由非选举产生的贸易官僚们所组成的超级政府。”反对者承认,公众的行动通常是沿着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国家这条线自下而上地进行的。他们想知道,在GATT这一高度上,消费者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呼声是否可以听取。正如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的马克·里奇和卡伦·尔恰蒙所指出的那样,WTO也许“极难让公民不断运用民主程序以推动时代进步。”
WTO反对者所使用的最有趣的论点之一就是州政府权力——州政府持有公众健康和安全的标准。1994年6月27日,22州的首席检察官给克林顿总统写信,要求克林顿总统“就各州在WTO专门小组前该如何捍卫本州法律免受外国法律的挑战这一问题,向公众作出解释。”他们还询问,进行立法是否能保证联邦政府接受贸易制裁,而非强迫州政府改变其法律。因州法律成功地接受了WTO的挑战,正如塞拉社的律师帕蒂·戈尔蒙所言,“现有的结构通过优先权授予联邦政府权力——即扣留联邦基金,以及通过法律诉讼强迫改变那些与贸易协议相冲突的州法律”。尽管美国贸易代表会就州的标准问题跟州政府磋商,但是,联邦政府享有向州政府“甩王牌”的权力。塞拉社在反对WTO的一则广告中指出,外国政府将利用WTO/GATT向美国法律挑战。该广告提醒人们“每一个州都会受到波及”。州政府权力的论点似乎很合美国公众的胃口,因为它关注我国控制环境、健康和安全标准的能力。
克林顿的反应
尽管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上半年采取了各种手段来赢得国会和公众对WTO的支持,但政府官员们仍然视公众的舆论为当然之事,他们没有听到在WTO辩论中公众在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对我国影响方面的担忧。决策者将其“营销”努力定位于制造舆论者,而非普通大众。他们推断,主权问题与中美洲无关。出现于电视专访节目中的主要的贸易政策官员跟学者们交锋时闪烁其词,他们更少与普通大众接触,倾听其呼声。与政府极力推行健康计划的努力相反,克林顿政府并未在帕瑞、潘沙可拉或匹兹堡等地举办WTO辩论会。
相反,克林顿政府重弹有关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老调,以此捍卫WTO。克林顿政府在一些演讲、信函和官方文件中强调,GATT协议将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并可以建立起一个更加有效的“繁荣基础”。商务部为每个州和产业部门就GATT在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作了估计。但是,每当克林顿政府以经济术语谈论起GATT的利益,左右翼的反对派便以政治术语表达自己的论点,指出GATT是非民主的。因而,就像关于堕胎的辩论一样,GATT的辩论者在用语上并未找到一致。此外,克林顿政府仰赖经济利益的论点,正好让GATT的反对者抓住了一个政策上重大的依据——一个引起许多美国人共鸣的争论点。
此外,克林顿政府依靠商业社会,而非一般民众有组织的行动,来推销GATT/WTO。根据组织商界力量支持GATT协议的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副总裁约翰·K·博道克所述,商业社会“在慢慢偏离目标”。除此之外,依赖商业团体可能会疏远许多美国人,他们早已认为NAFTA主要是出于公司的利益考虑,而非大众利益。因而,GATT/WTO的反对者告诉公众“公司对通过GATT施加了极大压力”就变得毫不奇怪了。
为了对主权问题作出反应,克林顿政府给每个国会议员散发了一份信件,强调法律学者约翰·H·杰克逊,尼克松政府官员皮特·撒切曼和遗产基金会组织的经济学家乔·考布都赞同WTO,并坚信WTO对美国主权将不会有任何不利影响。为了加强这种论调,克林顿政府把“保守”法律教授罗伯特·勃克所作的一项分析公诸于众。它旨在“掩盖”共和党和保守派所关心的主权问题。但这些举措也只限于华盛顿这块弹丸之地。
民主问题
大多数美国人对GATT/WTO秘书处将扮演的角色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WTO的职员是否将由一群无知名度、冷漠无情的官僚所充任,或如何选择GATT专门小组。GATT专门小组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我国制定本国健康和安全标准的能力。环境主义者将这类专门小组决定解释为对美国制定本国健康和安全标准的能力“打了一记耳光”。
对乌拉圭回合的辩论恰好与波澜壮阔的“民主化”贸易政策和改革“GATT之疾”运动相偶合。联合服装纺织工人工会主席杰克·欣克曼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督促,GATT应当“包括工人的权利和最低限度的工作标准,以作为贸易法规的一部分”。他指出,美国人理所当然地拥有这些权利。
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者呼吁公众更广泛地参与贸易政策。例如,格布公司的执掌人和总裁道纳德·G·费雪指出,零售商“呼吁国会制定公平的法律程序,让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并且一直被告知行政当局有关GATT的行动。”竞争性政策委员会的史蒂夫·夏洛兹建议,应当设立一个“消费者法律顾问”以便代表贸易决策中不为人所知的消费者和使用者的利益。
国会议员对这些要求使GATT更对普通大众负责所付出的努力作出了反应。1994年8月5日,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乌拉圭回合立法行动的总结。该委员会指示贸易代表“寻求修改GATT和WTO的规则,以便将GATT理事会、WTO总理事会和争端解决机构的会议向有资格的非政府代表敞开”。但是,“民间团体在乌拉圭协议的条件下不能直接提出诉讼或进行辩护。”这就意味着个体不能以法律诉讼的形式修正GATT法则或决定;只有本国政府才可以做到这一点。该委员会在探讨州法律时建议,“假如美国政府的贸易代表发现,州的标准与乌拉圭回合协议不符,那么,他们应该咨询州政府,从而获得双方相互认可的答复。”
克林顿政府已经采取了几项措施来使美国贸易政策更对人民负责,并且有助于“民主化”拟议中的WTO。例如,尽管商务部和商界一些人士反对;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凯特建议将顾问委员会会议向公众敞开。克林顿总统于5月份组建一个贸易与环境顾问委员会,以便向他提供涉及到贸易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该顾问委员会在民族、种族、性别和地区方面越发呈现出多元色彩——“更像美国了”。此外,克林顿政府呼吁GATT采用新法则,给更多的公众了解其决策过程提供方便。美国建议,把更多的GATT文件公诸于众,并且寻求赋予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地位”的认可。这些变化是使GATT更负责任而采取的最初步骤。
决策者的责任
当经济史学家依据历史来对当前的政策选择下定义时,永远必须格外谨慎。带着这种告诫,我建议,自由贸易政策在拼命解说贸易如何创造了工作机会的同时,必须承认贸易破坏了就业。有关于就业机会的增长与损失,对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付出的代价与获益,对于美国人的健康和环境标准所带来的利益与付出的代价,以及自由贸易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影响方面,他们必须让自由贸易政策的记载自行验证,对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分配后果,贸易政策的拥护者必须使其得到发展完善、有效的机制来帮助承受贸易自由化代价的那些工人、地方和产业。他们必须实事求是。可以肯定地是,我们对于主权的担忧就是担忧美国政策目标和制度生存能力的问题。
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的许多政策问题实质是全球性的问题。为了充分解决如何反应的问题,我们必须设计全球性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要求重新平衡我们的政策工具和前提条件。我们正在认识到,尽管美国过去是支撑世界银行和GATT等国际性机构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这些机构并非按照美国的平等、开放、人事组织和民主决策标准来发挥其功能的。多边贸易解决办法除了自上而下以外,还必须自下而上地进行。拉尔夫·纳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指出:“当史学家回顾这段时期的时候……他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国会抵制反民主的WTO时刻,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国会把捍卫本国及其居民的利益拱手交给这个新的专制性国际组织的时刻”。但是,关于WTO的争论也为协调自由贸易和美国民主提供了机会。随着公众进一步熟知全球性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他们将会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来促进民主理想,或者找到新的工具,从而使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经济变得井然有序。
译自(美)《挑战》1994年11-12月期
杨滨译 东北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