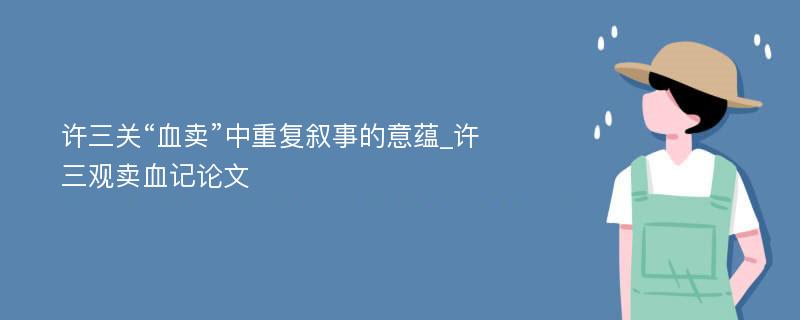
《许三观卖血记》重复叙事的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卖血论文,许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余华的小说中叙述具有本体的地位。什么是叙述?余华说叙述“在确立之前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困难,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和它们相遇的过程,不断地去克服它们的过程,最后你会发现一个完整的叙述成立了。”[1]叙述方式的变革一直是余华小说创作中自我反叛的努力向度。
从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逐渐认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样,对暴力、死亡和血腥的客观化叙述开始融入对世界的宽容,对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的追求和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直面苦难并在其中领悟生存之意义,揭示人类生存之精神气韵的主题,代替了揭示现实荒诞性和批判人性凶残、卑怯的主题。浓重的血腥味被逐渐稀释,更多的超越感力透纸背。
这种创作主题的变化使他对叙述方式做了相应的大变革,在《细雨中的呼喊》之前,余华小说里的人物,不过是他叙述中的符号,人物的声音被作者的叙述给压抑了,他曾明确表示:“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阳光河流等一样,都只是道具而已。”[2]这种将人“物化”为“道具”的观念被他贯彻在早期的作品中,作者的“声音”大大超过了人物的“声音”,使人物没能获得相对独立完整的生命质感,没能敞开其丰富的心灵世界,以致产生了以小说图解人性主体的偏向。到了《细雨中的呼喊》,作者开始意识到人物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应该尊重人物自身的声音,而且人物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要丰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文版自序中,他写道:“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只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作家对人物的理解加深了,而理解的结束也就是小说的结束——贴着人物写,成为余华新的叙述风格。这使得其小说中的人物音容笑貌就越来越清晰,对生命意义的阐发也随之愈显丰厚深邃了。
《许三观卖血记》是关于“活着”的叙事,关于“生命”的叙事。主人公许三观有着困苦不堪、历经坎坷的一生:他承受了一个非常历史时期所施与的种种打击和折磨,为了摆脱这些困境,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去卖血,他倾尽力气得到的血汗钱无以为继,他的人生大事和家人的生存:娶妻,养子,“报恩”却要以他生命的“血”的代价去换取,以此抵御住苦难的暴虐。陈思和指出:“许三观一生卖血惨剧,正是从农民光靠出卖劳动力还不够,必须出卖生命之血的生存方式中继承而来。”[3]为了救养子一乐,他一路卖血而去,成为最感动人心也最为悲怆的一幕,引发人的不仅仅是同情,是漫着泪的深思。“活着”对于许三观是艰难的,但他努力承受着这生命的沉重,虽不乏无奈和悲怆,但直面苦难的胸襟和生存勇气得以叙述和袒露。他的“活着”确证和维护了人的尊严和高贵。小说对许三观反抗苦难的坚韧意志表达了应有的嘉许和敬意,对他在步入老年后内心获得安宁表现了一定的钦慕和追思,对超越了世俗纷争、剥去了历史迷雾后留下的本真生命的终极追问。他不仅是某些苦难历史下每个生命体的痛苦和挣扎,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和煎熬的象征。小说以对整个人类的永恒生存境界的象征性表现,抒写出人在这种境遇里所秉有的生存意志和精神气度——“对一切事物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2]
正是这种对现实世界和生存价值的理解和思考的深化,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对叙事艺术作了自觉追求和大胆创新。虽然说小说同样以死亡和鲜血为内在结构线索,但高超的叙事技巧并没有像先前的作品那样使死亡和鲜血湮没读者的眼睛,而是把苦难推到背景的位置上,让许三观站到前台,喊出他自己的“声音”,突现他的生存精神,开掘出了小说特有的审美意味。
重复成为这篇小说耐人寻味的亮点,使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有一种反璞归真的单纯和明净。这种单纯和明净却又蕴育着那样深厚的情感和思想内涵,这让人想到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
许三观的生活比较简单,循环不止的“卖血”构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他第一次卖血娶到了老婆;第二次卖血支付了被儿子打伤的方铁匠儿子的医药费;第三次卖血是在心理极度失衡与林芬芳偷情后,为了感激她;第四次卖血是在饥荒之年为了全家渡过难关;第五次卖血是为了改善儿子许一乐在乡下的苦境;第六次卖血是为了巴结儿子二乐下乡所在的生产队队长;为筹集一乐的医药费,在去上海的途中连续多次不要命地卖血;以至在晚年,他想为自己去卖一次血,未能遂愿。每次卖血都是一次乞求乃至被嘲弄、羞辱。虽然许三观每次卖血的用途越来越承载着更深的无奈和苦难,但人物丧失的东西却没有变——失去了维系生命的血。就是每次卖血的过程都是酸楚的大同小异:先去拼命喝凉水以稀释血液,然后就是低声下气找血头卖血,再就是到胜利饭店吃上一盘炒猪肝、喝二两温黄酒,并且每次都是:“酒要温一温”。每次的一盘炒猪肝、二两温黄酒,让他找到一丁点儿卖血的“豪迈”。但这也只是为了下次卖血吃的微薄的“草料”。最后小说写道:许三观的妻子连为他点了三盘炒猪肝、三瓶黄酒,许三观才感到这是他一生中吃的最好的一餐饭。“卖血”(包括“卖血”后的喝黄酒吃炒猪肝)是一个最大的叙事重复,也是意义不断增值的过程。在循环往复的九次“卖血”中,许三观的生命历程不断得到拓展和延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次苦难的打击,每一次生命本能欲望的冲决,每一次对正当生活的欲求,都赋予了“卖血”以不同的生存意蕴,让其不断折射出人性与政治、文化、伦理、本能等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卖血”的叙事重复编织出复沓回环的叙述旋律:单纯省净却意蕴深广,平实平静而又深沉深邃,苦难的倾诉中包含着对生命的真诚和尊重。余华曾在听完《马太受难曲》后深有感触:“我明白了叙述的丰富在走向极致以后其实无比单纯,就像这首伟大的受难曲……仿佛只用了一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和篇幅表达了文学中最绵延不绝的主题”[4]。许三观的生命历程犹如一首优美而悲怆的受难曲,令人久久聆听和回味。那么余华是如何使《许三观卖血记》拥有了“音乐”,除了语言本身的魅力之外,对于重复的营造显然是这部小说节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九次卖血是重复的,但这种重复是一种变化的重复,变化和重复是融为一体的。“许三观一生多次卖血,有几次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如三年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运动,但更多的原因是围绕了民间生计的‘艰难’主题生发开去,结婚、养子、治病……一次次卖血,节奏越来越快,旋律也越来越激越,写到许三观为儿子治病而一路卖血,让人想到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歌谣,包含了民间世界永恒的辛酸”[3]。拿许三观卖血后吃爆炒猪肝、喝二两黄酒的情节来看,每次重复都有新的内涵。再比如,许三观给全家人“精神会餐”,吃红烧肉。一般看来描述一遍就够了,但余华却让许三观重复了四遍。通过重复,吃红烧肉本身反而变得不太重要了,而文本的抒情旋律和情感节奏却凸现了出来,并由此形成了特殊的效果。陈思和曾说:“许三观过日子这一段,是用想象中的美味佳肴来满足饥渴的折磨,这是著名的民间说书艺术中的发噱段子,进行移用后,恰当地表现了民间化解苦难的特点。”[3]
小说里余华用不避重复的叙述语言讲述平凡人的平凡故事,使我们回复到那似乎没有经过文明修饰过的岁月,领略无故事无波澜、自生自灭的人生状态。这里作者除了重复一些简单的动作、语言之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规定,他让人物矗立在生命之流中,不为其指明方向,也不保证任何进展的程序,反面让重复使进展成为不可能。在《许三观卖血记》里,几乎看不到静止的行动描写、心里描写,人物所有的行动都是可听可见的。“说”和“走动”是作品提供给主人公们的两个基本方式,而“流泪”也是主人公们共同而唯一的表达情感的动作。小说中多次出现人物流露激烈情感的场景,但主人公们的行为几乎都是重复和程式化的。比如小说写许一乐吃不到养父的面条又得不到亲爹的承认的悲伤,许三观最后一次卖血失败而又遭讥笑的酸楚,作家就用了相似的方式来表现,赋予了他们两个共同的动作:“走”和“流泪”,“走过城里的小学,走过电影院,走过百货店……”“混浊的眼泪涌出眼眶,沿着两侧的脸刷刷的流,流到了脖子上,流到了胸口上……”这样的描写是外在的,但其中饱含的情感冲击力却更令人震撼。余华用重复的语言也避免了语言的肆意泛滥,让我们进入到没有被语言掩盖的赤裸的现实。当许三观得知妻子许玉兰与她原来的对象何小勇有过性关系后,重复的对白构成叙述语言,充分表现了许三观受了委曲伤害之后的神情、动作及其简单的内心活动。
许三观躺在藤榻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许玉兰走过来说:
“许三观,家里没有米了……,去粮店把米买回来。”
许三观说:“我不能去买米,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一回家就要享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享受吗?就是为了罚你,你犯了生活错误……”
许玉兰说:“许三观,我正在洗床单,这床单太大了,你帮我揪一把水。”
许三观说:“不行,我躺在藤榻里,我的身体才刚刚舒服起来,我要是一动就不舒服啦。”
许玉兰说:“许三观,你帮我搬一下这只箱子,这一个人搬不动它。”
许三观说:“不行,我躺在藤榻里享受呢……”
许玉兰说:“许三观,吃饭啦。”
许三观说:“你把饭给我端过来,我就坐在藤榻里吃。”
许玉兰说:“许三观,你什么时候才享受完呢?”
许三观说:“我也不知道。”
许三观对待妻子不忠一事,分别予以了惩罚,对男方何小勇他告诉二乐三乐长大后去强奸何的两个女儿,让当时还很小的二乐三乐都乐了,为了惩罚许玉兰,采取了“罢工”行动,用“躺在藤榻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的“享受”、“舒服”来弥补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最后以偷情来企图摆脱压在心里的屈辱。他曾有一点儿古人的血气方刚,也曾有一点儿现代西方的洒脱通达,但最终就是用最简单的重复语言、最简单的重复行动来表达他的痛苦和不满,用自己能有的肉体享受来弥补,来要求得到简单的补偿。这就是许三观无奈的生存境遇。由于反复的叙述,表达了许三观那种对生活没有奢望,也没有远大目标,只是被一种简单的生存欲望支配着,仅仅是生存着,就连现代人视为最痛苦的事情,也只是在心里留下浅浅的印记。
而他小说语言出现的大量空白,为衍生出象征意义提供了前提。“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3]由于简单的重复,作者没有提供确定句子意义的前后关联的语境;由于丧失了语境,语言的意义失去了坐标,因而许多的句子的意义都是未规定的、是多义的;由于语言之间缺乏意义上的关联,语言所示的物像也由日常经验中削离开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个体面貌。这种物像和面貌不是一个可以匆匆而过的世界,而是一个能唤起你的新异感、让你伫立凝视深受感动而又没有丝毫故弄玄虚的平凡世界。余华在单调中找到了丰富,在平凡中发现了拽住人心的东西。叙述语句的重复,余华大胆采用了富有童趣的、简单循环的叙述方式。叙述语句一次次简单重复,回环复沓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童话韵味。如“他们去告诉许三观说:‘许三观,你家的一乐呜呜哭着往西走;许三观,你家的一乐不认你这个爹了;许三观,你家的一乐见人就张嘴要面条吃;许三观,……”;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面已引用的:在饥荒年里,许三观过生日,他用嘴给三个儿子“炒”菜吃,让儿子们“用耳朵听着吃了”,这一回精彩的口头烹饪表演,一次一次重复产生的一种令人震惊也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在重复中实现了深度推进。这也令人想到《诗经》里回环往复的那特有的审美韵味。
除了作品的主要事件的重复,《许三观卖血记》中细节处的重复也是随处可见的,如许三观给儿子取名:许一乐、许二乐、许三乐,许玉兰生孩子的呼叫和她每次受到委曲后坐到门槛上的哭喊,都颇具意味。
小说在重复叙述的舒缓优美而不乏苍凉的旋律中传递出作者对许三观卖血的怜悯和敬慕,对人类苦难承受能力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之情。
其实重复叙事在余华的许多作品中都是结构的主要手段,也是构成细节的主要手法之一。从他的第一篇实验性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写“我”漫无目的地在路上漂泊,“像一条船”、“像一匹马”,始终在游荡,沿途的风景是丰富而单调的不断重复。《河边的错误》就因运用事件的重复凸现主题而引人注目。《偶然事件》叙写的是不同的人物都沿着命定的路线,在重复着相同的命运悲剧。转型后的长篇小说《活着》,重复仍是主要手法,以连续不断的死亡事件而进行着不断的重复叙述,而且较之从前更为精致。其“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是借用了民间叙事歌谣的传统,有意偏离知识分子为民请命式的‘为人生’的传统,独创性地发展起民间视角的现实主义传统。《活着》是叙事者下乡采风引出的一首人生谱写的民间歌谣。”[3]《在细雨中呼喊》也处处可见叙事的重复。这无疑都是余华为实现深度推进而有意制造出来的叙事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