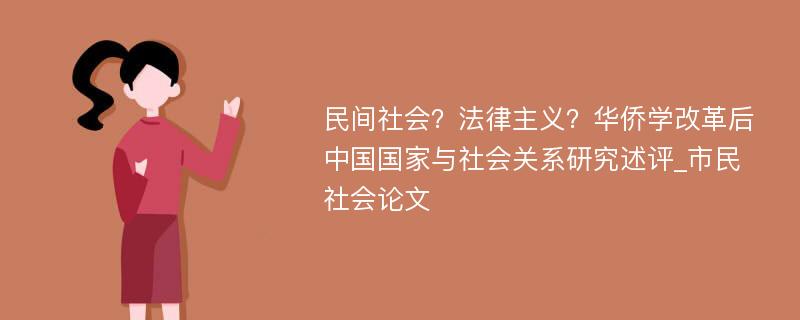
市民社会?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社会关系论文,国学论文,中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改革前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海外中国研究当中有两种代表性的理论框架: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理论①和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理论②。前者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的主动性,后者则认为真正的政治活动是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极权主义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分强调国家的绝对控制而备受争议与批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学者——包括那些极权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的现实情况并不像极权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走向总体控制的最极端,而且整个国家也并非无时无刻地处于一种政治总动员的状态中。相比较于极权主义来说,利益集团理论则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它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的主动性,置国家于被动地位,认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政治生活现实”③,而“国家只是不同利益集团追逐各自利益的舞台与背景”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多元分化调整和重塑了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这一背景之下,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利益集团的理论框架都显得陈旧与不合时宜。为客观描述中国改革后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出现的新特点,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的解释框架,在此当中,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框架逐渐盛行。
一
驱动市民社会理念复兴的一个较为深久的原因,主要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显并于20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人们寄希望于市民社会的重塑来捍卫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⑤。市民社会被人们寄予如此的厚望,主要在于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多元主义理论前提。多元主义假定权力的分布是分散的、非单一集团控制的,社会中包含许多在利益和价值方面相互冲突的群体,它们由个体组成,个人通过参加群体集中利益、影响政策。在竞争性的政治市场中,各种群体依据自己的资源即支持率取得影响力⑥。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多元主义将社会视为先于国家产生、外在于国家、具有不受外界影响的独特运作逻辑的一个自主和独立的领域。在没有国家强权侵扰的情况之下,社会民众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利益需要组成各种利益团体,各利益团体相互竞争并以竞争的过程和最终结果来确保自身利益能够获得实现,而社会则可以从利益团体的竞争中获益。此外,多元主义还认为国家应当是社会意志的代表机构,应当是经由社会赋权而获得合法性的。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当国家主义潮流下社会被国家权力挤压和侵蚀的时候,市民社会强调要确保国家与社会的明确边界,要确保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运作,同时也强调市民社会对日益强势之国家权力的制约。社会政策的制定不应当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应该是社会利益团体利益表达和相互竞争的结果,市民社会正是其表达和竞争的舞台。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就被一些海外学者应用于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出现的新变化,包括部分并没有使用市民社会这一字眼的研究者⑦。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更是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关于市民社会的大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不管能不能称之为市民社会,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国家体制之外的社会空间的出现,这是一种“社会自身非国家整合结构的复苏”(the resuscitation of a society's own non-state structure of integration)⑧。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必将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渐发展和壮大。
持市民社会萌芽和发展论的研究者们试图在改革之后中国社会中新出现的那些结构性变化因素当中寻找证据,以支持其论点。比如怀特通过浙江萧山地区民间社团的研究论证道,从前中国社会组织基本不具备自主的能力,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改革后,首先是经济组织具有并且体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权利,尽管国家的支配和优势依然明显,但这预示着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孕育与发展⑨。倪志伟则认为中国经济制度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将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秩序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直观表现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倪志伟也据此对中国未来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有一个乐观的预期⑩。赵文词也认为,公共领域或者是市民社会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后政治秩序所出现的新趋势和动向,市民社会的概念与理论将会对今后的当代中国研究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11)。何包钢则提出改革后中国虽然并没有出现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是如下的现实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依靠社会组织实现社会控制,而社会组织依靠政府的权力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在中国的现实中,无论是国家进入社会还是市民社会成为国家的要求,两者的边界是清晰可见的。由此,何包钢认为中国将孕育和发展一个“半市民社会”(12)。弗洛里克则通过对“希望工程”、浙江萧山的社会组织、农村选举和厦门商业组织的分析,指出在中国基层社会出现了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尽管短期来看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不能因此就对中国市民社会的长远发展作否定性的判断(13)。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学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这与中国市民社会的出现和成长有重要联系(14)。
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不同,大陆一些学者对市民社会的关注源自于他们对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强烈关怀。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做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15)。因此,本土市民社会论者并没有像西方论者那样仅仅强调作为国家对立面和国家权力“监督者”的“市民社会”;而是试图通过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在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外,寻找到另一条中国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建设路径。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之路是:第一个阶段要初步建立起市民社会,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第二阶段要实现市民社会对国家决策进行正面意义的影响,即积极地参与(16)。
但是,也有一批学者对中国出现市民社会或者是将市民社会框架应用于理解中国社会并不乐观。比如针对市民社会论者强调最多的,中国的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催生了国家体制之外的力量,并由此导致市民社会孕育和发展的观点,皮尔逊就反驳到,中国改革后所出现的合资企业相比较于国有企业来说,可以被认为具有更多的非国家成分与色彩。但其研究表明,合资企业并没有完全从国家体制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不仅无法联合起来与国家“对抗”和“谈判”来更多地为自己牟取利益,甚至其生存与发展在决定性的层面上依然依靠国家体制。从中,我们看不到所谓市民社会空间的成长或是力量的壮大(17)。除此之外,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市民社会的概念或是框架根本不适用于理解中国社会,其他的一些概念框架似乎更加准确。比如许慧文认为历史上中国形成了一种自身独特的、互相分割的、类似细胞状的地方结构。尽管表面上国家全面控制整个社会,但分割的地方主义结构一直存在甚至有所加强(18)。按照许慧文的思路,这种蜂巢状的地方分割结构显然与市民社会相去甚远。戴慕珍则认为,在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地方社会层面,代表国家的县政府、代表市场的企业与代表社会的村庄,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彼此合作、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格局,这一结构形态显然不像市民社会所描述的那样,她称之为“地方性的国家法团主义”(19)。黄宗智更是直接指出,市民社会预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两分的对立,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是从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类型,它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适用于中国现实的一个更加准确的概念应当是“第三领域”(20)。
这样说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解释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难以回避如下的问题: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视角是将国家和社会视为相互对抗的两个角色,对抗关系决定了社会整合的结构与政治秩序。但是,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单向度的强调,都很难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当下状况。市民社会是一个彻底的西方概念,在将其运用到中国研究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应该从“实体建构”的角度还是从“解释模式”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21)。然而,无论是从哪个取向上将市民社会的概念运用到中国的经验研究当中,我们都会发现,作为市民社会概念基础的某些假设具有明显的西方特征,中国实际却不具备这样的特征。正如周雪光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有这样两个与市民社会有关的、基于西方的假设在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存在问题,一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存在分明界限;二是私人领域内的结构具有市场化倾向(22)。显然,在运用市民社会框架考察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缺乏现实基础。
二
其实在前面如皮尔逊、戴慕珍、索林格等人的研究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法团主义的一些端倪。尽管与市民社会理论一样,法团主义框架与多元主义同样有着割裂不断的联系,但是两者的理论前提却不尽相同。法团主义认为国家是影响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应当寻求在利益团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重视利益团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作用。因此,法团主义大量使用的词汇是中介(intermediation)或调整(regulation)。在以往的社会发展中,各个社会组织都在其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社会分工位置,它们各自的职能得到了社会认同。但当社会进入组织化的资本主义阶段后,为了避免团体争斗危及秩序,国家需要把它们吸纳到体制中,让它们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发挥作用,同时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法团主义者称,这个协调体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市场过程的自由竞争,不会出现一个对各个集团都公正的政策结果。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因此成为法团主义思想的核心(23)。虽然法团主义框架也承认正式体制外利益组织化为利益集团的“合法性”,但是较之市民社会框架而言,法团主义框架视利益集团与权威当局的联系为一种制度化上传下达的渠道,而不是一种“压力”。
法团主义框架被引入到认识和解释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题上来,同样源于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探讨与认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使得西方学者去寻找到底是什么理论模式和政治理念在指引着人们的政治生活。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较之以前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法团主义的理论框架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为经验案例来验证法团主义框架的研究也不断涌现(24)。中国发展的独特性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将法团主义的框架应用于改革后中国社会整合结构与政治秩序,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论及运用法团主义框架研究东亚及中国社会,就不得不提到昂格尔和陈佩华。在他们那篇著名的文章中,两人提出,学者们数十年来所使用的社会科学范式已不能恰当地适应90年代的中国,而一个有帮助的概念是“法团主义”。这一概念虽然并不能包容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但是,似乎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倾向具有诠释的价值。昂格尔和陈佩华认为,在改革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法团主义组织。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建国后照搬的苏联模式。这一模式的前提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与被领导、管理者与工人,大家都为了建立繁荣的社会主义这一使命而团结一致。在此模式之中,法团主义地方分支诸如工会和农协等相当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纽带”。它们是党中央与某一群体之间的双向通道,自上而下的传递是为了国家的集体利益动员工人和农民增加生产;自下而上的传递是表达基层的权利和要求。改革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上进一步放手,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也进一步弱化。因此,需要更多的机制来补充因此而出现的控制上的不足,从而创出大批新的团体,来充当法团主义的中介机构和代理人。昂格尔和陈佩华敏锐地指出:同东亚新经济国家的情形相对照,中国是从另一个方向朝国家法团主义发展的。这时,国家法团主义已不是用来作为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一个机制,它所起到的反而是放松控制的作用(25)。此外,陈佩华还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分析提出:中国改革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主导,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可能是充满冲突的。而法团主义可能是一条出路,它可以继续原有社会体制的路径,同时通过法团主义团体在中国的双重地位获得自身的发展。这是一种通过统一结构增进组织利益的方法,沿着这个路径发展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法团主义”模式(socialist societal corporatism)。它的最终发展趋势不是从国家当中分离出市民社会,而是一种新形式的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结。而这一模式,能够将中国改革的代价即转型所导致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26)。
另外,针对市民社会论者所寻找到的那些证据,法团主义论者也提出了反驳。皮尔逊发现,中国合资企业渴望有机会独立发展,但是它们不能建立完全独立的社会联合体,而必须依赖于国家。因而,这些组织与其说具有自主性地位,不如说是法团主义式的(27)。裴敏欣通过对在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登记的民间组织(civic association)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改革后大量民间组织的出现,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的出现。实际上,这些民间组织具有明显的“国家法团组织”(state-corporatist)特征(28)。古德斯坦则通过比较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认为法团主义的模式较之市民社会的模式更准确地解释了中国转型的实质(29)。
法团主义框架还影响了不少中国本土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与提问方式。张静通过对企业职代会案例的研究说明了社会基层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渠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基层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她认为这种“中介”与“联结”的研究视角正是属于“法团主义式”的(30)。顾昕在其关于民间组织的研究中提到,改革后中国社团空间的监管体系具有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高度强调国家的控制,同时在社团的唯一性、代表性、垄断性等方面,施加严格的控制。而作者认为理想的发展路径是,国家担当能促性角色,走向社会法团主义,推进民间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中发展,反过来可以有效增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31)。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发展的讨论当中,亦有广泛地强调国家在非政府组织发展当中重要作用的声音——尽管他们并没有使用“法团主义”的字眼,但是这其中也很容易看到法团主义框架的影子。
然而,法团主义框架在解释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并非没有问题。从理论路径上来说,当遵循法团主义的思路去探讨当代我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来源与基础的时候,我们仍然走到了与市民社会理论相同的道路,即组织化的体制外利益通过“中介”上传到正式体制之内,通过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来谋求自身利益要求的实现。不同的只是法团主义将国家对利益团体的“领导”作为基本和重要的前提。在这样的理论路径下,法团主义框架同样无法回避如下的问题:首先,法团主义关注的是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通过什么机制进入国家的决策结构,其必要前提是社会结构分化基础上的利益代表范围及权利界定的相对发展。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作为前提的社会结构分化基础之上的代表范围及权利界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在当前我国社会当中。其次,与市民社会理论一样,法团主义框架无法解释当前我国社会体制外利益不曾广泛聚合的现实,甚至可以说体制之外的利益集团化程度远没有达到法团主义之标准。作为利益集团化程度重要指标的“集体行动”在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基于利益组织化的有意识和理性的过程,不如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导致的大量个体自发行为的聚合体,它不仅不是出于利益的组织化,而恰恰是源于利益的未组织化(32)。既然法团主义基础之利益集团尚未完全形成,那么又如何去谈论是国家法团主义还是社会法团主义呢?再次,法团主义框架虽然强调基层社会与权威当局之间的“中介”与“联结”机制,但是它往往将上述“中介”与“联结”机制置于正式体制与基层社会之间。而就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基层民众与权威当局之间具有“中介”与“联结”作用的结构性机制表现得并不清晰。此外,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当前的中国,无论是法团组织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还是法团组织对于国家政策执行的参与程度,都已经达到了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要求。因而,我们可以说当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某些法团主义特征,尤其是在法团主义所强调的体制内外制度化联系与沟通的渠道方面;但这些暂时还没有定型的特征是否就说明中国已经走上了国家法团主义的道路,还值得商榷。
三
早期的极权主义理论与利益集团理论虽然已经被证明在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时的错误,但是,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却为后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给出了一个基础性的思维框架。这一思维框架具体表现为将国家与社会置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s)的两极,国家一极意味着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社会一极则意味着自由多元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任何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或者处于这两极当中的一极,或者处于两极中间连续统的某一个特定位置。其位置的确定,依赖于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因此,通过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以确定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情况,并由此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虽然后来的学者往往都会在其研究中说明,他们的研究框架与极权主义和利益集团理论有何不同,更多的时候,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是作为他们研究的标靶;但这些研究却仍然落入到了上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续统当中去了。比如华尔德使用“非正式网络”的概念,侧重于理解社会利益诉求达至国家决策层面的渠道(33);戴慕珍使用“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概念,侧重分析地方政府的独特运作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34)。其实从最为基本的思维模式看,上述论者依然是在国家与社会连续统的框架之下讨论问题。这样说的意思是,无论是“非正式网络”还是“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的概念,背后都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两极,而与极权主义和利益集团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并没有静态地讨论国家与社会孰强孰弱,强到什么程度、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是动态地分析国家与社会之联系渠道与互动的关系形态。但依照此逻辑分析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必然是落入到连续统中的某一个位置。
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逐渐盛行于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更加清晰化了上述连续统的观察视角。市民社会论者强调的是社会对于国家的制衡与影响;而法团主义论者在强调社会对于国家政策影响的同时,同样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这两者的共同点是关注社会转型之后,体制外利益聚合体的形成、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社会出现和发展的可能、以及在上述两者的基础之上“社会”对“国家”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国家与社会关系连续统的预设加上市民社会或者法团主义的框架,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假说被设计为“全能主义模式→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社会法团主义模式→市民社会模式”(35)。这一预设本身已经决定了其所能够得到的结论。从市民社会或法团主义的立场来看待改革之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家从社会领域的撤退以及与此同时社会自主性增强带来的社会领域的崛起。同时,这亦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必然道路。就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无论是强调国家控制社会、社会影响国家还是同时强调上述两者,都从一个角度把握了这种关系的实质,但是都不能说全面和真实。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作为描述与理解改革后中国社会结构与秩序的两种主要和流行的框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可以从这样两个意义上来说明。一是从实体建构的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法团主义,都是源自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独特性。它们被应用于理解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信度与效度都有赖于中国是否具有市民社会或法团主义的独特历史、文化与政治特征。二是从解释模式的意义上来说,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的制度安排预设了国家与社会两极对立的连续统,而如果这一连续统并非现实当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存在形态的话,无论是市民社会还是法团主义——这种在两极对立连续统当中确立国家与社会关系位置与形态的做法便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转轨逐渐引发了社会体制的转型。在这一背景之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塑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对这一主题进行理论阐释的过程中,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都存在无法克服和逾越的障碍。产生这一障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远比“市民社会”或是“法团主义”所提供的解释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经验相对于这两者产生的西方背景所具有的独特性。虽然这两个概念已经被证明了其应用于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有效性;但是必须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进行“概念再造”(reconceptualization)(36),新创造的解释框架必须来自于中国自身的经验。或许,对源自西方的概念框架进行“实体建构”与“解释框架”的区分揭开了“概念再造”的序幕,但是我们应当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注释:
①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ed.,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②H.Gordon Skilling,"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Revisited",World Politics,Vol.36,No.1.(Oct.,1983),pp.1-27.
③[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④Jean C.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2.
⑤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总第3期。
⑥Christopher Ham and Michael Hill,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Calitalist state,Harvester Wheatshef,1993.转引自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⑦Baogang He,The Ideas of Civil Society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1986-92,Issues & Studies,June 1995.
⑧Mayfair Mei-hui Yang,Gift,Favors 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287.
⑨Gordon White,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lfairs,No.29.(Jan.,1993),pp.63-87.
⑩Victor Nee,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ume 101,No.4(Jan 1996),pp.908-49.
(11)Richard Madsen,The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Modern China,Vol.19,No.2,Symposium:"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Ⅲ.(Apr.,1993),pp.183-198.
(12)He baogang,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Macmillan Press Ltd,1997,p9,p13.
(13)B.Michael Frolic,State-Led Civil Society,In Timothy Brook and B.Michael Frolic eds,Civil Society in China,M.E.Sharpe,Inc,1997.
(14)Ruth Hay hoe and Ningsha Zhong,University Autonomy and Civil Society,In Timothy Brook and B.Michael Frolic eds,Civil Society in China,M.E.Sharpe,Inc,1997.
(15)邓正来:《导论》,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16)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创刊号,1992年11月。
(17)Margaret Pearson.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1 (Jan.,1994),pp.25-46.
(18)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9)Jean C.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No.144,Special Issue: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Dec.,1995),pp.1132-1149.
(20)Philip C.C.Huang:"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Modern China,Vol.19,No.2,Symposium:"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in China?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Ⅲ.(Apr.,1993),pp.216-240.
(21)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1-634页。
(22)Xueguang Zhou,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8,No.1.(Feb.,1993),pp.54-73.
(23)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24)Samuel L.Popkin,Corporatism and Coloni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Change in Vietnam,Comparative Politics,Vol.8,No.3,Special Issue on Peasants and Revolution.(Apr.,1976),pp.431-464.
(25)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3 (Jan.,1995),pp.29-53.
(26)Anita Chan,"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 (Jan.,1993),pp.31-61.
(27)Margaret Pearson,"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1 (Jan.,1994),pp.25-46.
(28)Minxin Pei,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An Empirical Analysis,Modern China,Vol.24,No.3.(Jul.,1998),p.285.
(29)Steven M.Goldstein,China in Transition: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Incremental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No.144,Special Issue: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Dec.,1995),pp.1105-1131.
(30)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1)顾昕:《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32)Xueguang Zhou,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8,No.1.(Feb.,1993),pp.54-73.
(33)[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34)Jean C.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35)李略:《市民社会和社团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总第25期。
(36)Marie-Claire Bergere,Civil Society and Urban Change in Republica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50,Special Issue:Reappraising Republic China.(Jun.,1997),pp.309-328.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