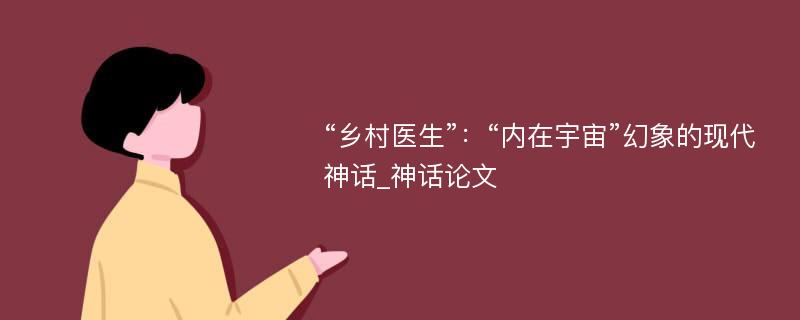
《乡村医生》——“内宇宙”幻化的现代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宇宙论文,神话论文,医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乡村医生》是卡夫卡本人最珍惜的少数作品之一,晚年他嘱咐他的挚友勃罗德在他死后 要把他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时,只对六篇小说表示有所留恋,其中就有《乡村医生》。 这篇小说诞生时,正值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时期,表现主义运动也方兴未艾。当时文艺界许多 人正热心于尼采美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卡夫卡也曾一度对后者较为着迷。在卡夫卡的主要 短篇小说中,《乡村医生》无疑是颇有资格为卡夫卡与弗洛伊德学说之间的那段“暧昧关系 ”作证的作品。
一、奇幻的梦境结构
《乡村医生》全篇是由梦境的结构方式写成的:
风雪之夜。医生听到要求急诊的门铃声,立即让女仆罗莎准备马车。但他的马在前一天就 已冻死了。村里又没有人肯借给他。医生焦急中下意识地一脚踢开了闲置多年的猪圈的门, 只见一个嬉皮笑脸的马夫从猪圈里爬了出来,同时两匹高头大马从墙壁里挤了出来,以供效 劳。马夫趁罗莎走过去递马具之际,抱住她狠狠亲了一下,以致脸颊上留下一排牙痕。医生 见状感到愤怒,但身不由已地上了马车,像在潮水中漂游似地很快到达,一路上却为罗莎的 处境担忧不已。
到了目的地,病人——一个少年——却声称没有病,他悄悄地请求医生:“让我死吧!”医 生见他一切正常,又想到应赶紧回去救罗莎,这时两匹马分别把头探进了窗子。医生正欲走 时,见一家人苦苦恳求他救救这孩子,尤其当他见到病人的姐姐手中晃着血手绢,他感到也 许孩子真的有病,重新检查,发现少年右腰间果然有一手掌大的伤口!粗壮而“红润的”蛆 虫 在血脓里蠕动——病人没救了!但病人的家属、村中的长者们都赶来对他不客气,一支由教 师组成的合唱队唱道:“剥光他的衣服,他便肯治了/要是他不肯治,就打死他!”于是, 一顿拳脚后,医生的衣服被剥得精光,并被抬到床上,让他对着病人的伤口躺着,然后大家 统统退出房间,把房门锁上。病人说,“你不但没有帮助我,反而挤了我的临终床。”病人 带着医生的安慰安息了。这时医生想到该救自己了,便赶紧收拾衣服、医疗器具,顾不上穿 戴,越窗跳上马车,不料那件皮大衣的袖子却挂在车后头的钩子上,怎么也够不着,而那两 匹马却偏偏不听使唤,在雪地上慢吞吞地磨蹭着。许多路人看着他挨冻,却无动于衷,而他 们都是曾经被他治过病的人!于是医生惊呼道:“受骗了,受骗了!听信了一次不准确的门铃 声,想不到永远无可挽回!”
叙述中梦的碎片劈头盖脑而来:两匹骏马“无中生有”,不招自来;马车像“木头在潮水 中漂流”,以致十英里之遥的雪路就像去“邻家院子”,瞬间到达;病人垂危,却否认自己 有病,而富有经验、且历来恪尽职守的医生开始竟发现不了他有病;病人家属又如此不近情 理地虐待一个医生;医生在寒天中光着身子、处境尴尬;大衣被钩在车后“可望而不及”( 这是卡夫卡人生体验的典型图像);“神马”不愿快走的反常行为……这一系列梦境幻象破 坏了我们习惯了的现实感,不时斩断固有生活逻辑的因果链条,从而使故事显得荒诞(这是 现代主义作家尤其是卡夫卡的常用手法),令人感到陌生,也就是与我们经过“训练”而形 成的“理性”相反。但作者绝不是对梦境进行简单的、照相式的实录,而是把梦的材料加以 改造,使之聚合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巧妙的艺术品,借以表现人在某种特定的情 势下所反映出来的特定心理境况。因为卡夫卡从来不把讲故事作为创作的目的,也不把梦作 为“玩”形式的手段。对他来说,“一切艺术都是文献和见证”。在他笔下,任何非理性的 荒诞形式中都包含着极严肃的意蕴,而且这意蕴如同它的五光十色的外衣一样,是多层次的 ,一言难尽的。
二、三重拯救的焦虑
先看一下主人公的三重使命,或曰“三重拯救”。
一救侍女罗莎。罗莎作为侍女在主人公乡村医生的家里已生活了很长时间了,但这位医德 高尚、事业心很强的单身汉却从来没动过这位“美丽的姑娘”的念头。直到那个莫名其妙地 从猪圈里冒出来的下流马夫强行把她拥抱和亲脸时,这才唤醒他的保护人的意识,并斥骂马 夫 是“畜牲”。罗莎立即跑回他的身边,并预感到面临的危险,一口气跑回自己的房间,关上 屋子里所有的灯。她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向主人暗示,她是非主人莫属的。但对医生来说,夜 铃的鸣响就是最高命令;外出急诊是他此刻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当他在路上听到马夫追逐 罗莎的那种粗暴声音时,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罗莎可能要成为他的职业的牺牲品,也 就是为那两匹马付出的沉重代价。于是,拯救罗莎成了他取代行医的当务之急。所以到了病 人身边时,他心急如焚。一心想回去救罗莎。甚至在衣服被人剥光的情况下,为了马上跳上 马车回去搭救这位姑娘,他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但是晚了,命运似乎在对他进行惩罚:平 时漠不关心,现在就该吞吃这个苦果!因此不管他如何心急如焚,归心似箭,但没有人同情 或支持他,连那两匹来时“黑旋风”似的骏马此刻也不愿与之配合,故意怠工。于是,刚刚 唤醒的情欲,又被强行压制下去。对罗莎的拯救失败了!
二救那位负伤的少年。救死扶伤是一个医生的天职,也是他工作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之所 在。我们的主人公对自己职业的神圣感是无可怀疑的。只要有求诊的信号,风雪之夜也在所 不辞,以至把自己的马都累死了。但奇怪,那位年少的病人有偌大的伤口,却没有求生的欲 望,只有求死的念头;他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夫,你让我死吧。”仿佛他降生到 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错误,不如回到冥府。绝望使他公然对医生表示“很少信任”。而伤口 是他绝望的根源,这是他的不治之症的象征,面对这一病症,医生不得不告诉病人没救了! 这无疑对医生的职业及其存在根据是一个嘲弄,一个否定——这一层拯救也失败了。
三救医生自己。这位兢兢业业的乡村医生,不管他的职业道德多么高尚,如今人们不仅不 领受他的高尚,反而恩将仇报,剥光他的衣服,还要让他与病人躺在一起,仿佛要让他为病 人 殉葬!这时,医生才领悟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必须起而自救,他发出“现在是考虑如何拯 救自己的时候了”的惊呼。是的,他必须赶回去夺回他的家,他的床,救出他的侍女和 他拥有的一切。但不行!他无法突破尘世的和非尘世的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不但那两匹 “神马”不与他配合,故意磨蹭,连那些被他救助过(医治过)的四肢健全的乡亲们也无动于 衷,他不得不驾着“非尘世的马”,坐着尘世的车在茫茫的雪原上乱跑。于是,这位医生响 应夜铃的召唤的结果,不但一无所获,反而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东西:他的职业尊严——如今 已威风扫地;他的“乐善好施”的荣誉感——受到无情的嘲弄;凡是尘世的、伦理的、感官 的一切都被剥夺殆尽。在这个雪原茫茫的世界里,凡尘的、友爱的气氛是不存在的,超验的 、实 验的神秘力量却证明着它的有效性,它不但把医生从家里引诱出来,还把他从职业中驱赶出 来,让他的以目的和雄心开始的行为,结束在彻底的失败和鲜明的怪诞里。有人说,两匹非 尘世的马拉着尘世的车,载着一个老头到处乱跑,这是“普罗米修斯和西绪福斯神话的被动 变奏,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存在幻象。”(注:保尔·K.库尔茨《现代文学论》,法兰克福/美茵,1972年,第1卷,第194页。)就是说,他经历着无法克服的思考与现实的矛盾。 正如E.海勒所说:“智力使他做着绝对自由的梦,灵魂却知道那可怕的折磨。”(注:埃利希·海勒《卡夫卡的世界》,见拙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
前面已经说过,表现主义者习惯于用一种“陌生化”手段,掀去蒙在现实生活表面的习俗 观念的“覆盖层”,揭示我们所熟悉的生活背面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是令人陌生和惊 异的,但它能起“醒世”作用。卡夫卡写长、短篇小说往往一开始就突然将主人公推入一个 令 他猝不及防的陌生而孤独的境遇,他为摆脱这个尴尬的环境进行种种挣扎和努力,逐渐认识 到这就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处境,并为此感到绝望。而他为摆脱困境而进行的挣扎和努力的过 程,就是他重新体验和经历这种真实生活的过程。长篇小说《诉讼》主人公一开始突然被捕 ,短篇小说《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萨一开始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乡村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处境极为狼狈”,都是一开始就给人以祸从天降、大难临 头的感觉。接着层层叙述“我”如何陷入焦头烂额的困境不能自拔。卡夫卡在梦的魔幻掩护 下对主人公这种长过程、慢速度的生存经历来了一番“高浓缩”的处理,把他一生中种种不 顺 利的、倒霉的、失败的记忆压缩在一个夜晚的一件事情里,使他在接二连三的无法承受的事 件中,在面对异己世界的一再惊愕中对自己长期以来的存在提出疑问,或诉诸于争论,诉诸 于尘世社会的法庭。从而表明自己正陷入一种尘世的无穷诉讼之中。奥地利血统的美国学者 、卡夫卡研究专家瓦尔特·H.索克尔对《乡村医生》的下述分析可以作为这一“诉讼”的注 脚:
两幢房子形象地代表了医生生存方式的两个相反方面:在他自己的房子——自我的房子里 ,医生放弃了情欲满足的可能,在另一所房子——病人的房子里,他献身艺术(即医术—— 笔者),这艺术就是对付人类先天的创伤。主人公的矛盾心理,在于他在哪一边也不满足。 在家里,他把姑娘牺牲给使命;而在目的地,他后悔付出的代价,又想再回去。
而门铃的夜响,则是向主人公发出的挑战信号——这里阐述的是存在主义世界观,卡夫卡 与存在主义有着不解之缘,离开存在主义的尺度去考察卡夫卡的作品就很难切中肯綮。
但是,卡夫卡对人的生存处境的绝望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入观察和否定中形成的,因 此 ,那些隐晦曲折地表达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过程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 它们。于是我们在《乡村医生》中看到的就是一幅传统价值观念崩溃、人们一时无法 适应、无所适从的图景。小说中明白无误地写道:“他们(指市民,老百姓——笔者)已丧失 了旧有的信仰;牧师正坐在家里撕拆法衣,拆了一件又一件”。(注:卡夫卡《短篇小说集》,费歇尔出版社,1977年,第127页。)可是这位一心扑在事业上 的医生却仍是书生气十足,他看不到世风的这种变化,觉察不到一个古老的时代正在告别, 他甚至不能从全村人都不肯借马给他应急的这一事态中悟出点什么,而依然坚守他“慷慨大 方、乐善好施”的固有美德,一腔古道热肠,对病人有求必应。殊不知如今的病人,尤其是 青少年,有了不同的生死观,像这位十六岁的少年,似乎早已“看破红尘”,看到人类与生 俱来的致命伤口的不可治愈性,惟求早死,不再恋生,因此对医生“很少信任”;医生对他 成为多余的了。但在病人的父辈和老一代的“长者”们心目中,医生的职业仍然是“圣职” ,如今这位“救星”在病人面前竟然如此无能为力!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是不 可原谅的。于是这位正直、善良的医生在这个村子的新旧两代人中都不讨好,可谓“好心不 得好报”。这样他作为医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剧,这个悲剧 可以说是由随着时代观念的剧变而出现的“代沟”造成的。
奥地利的一位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E.费歇尔曾研究过卡夫卡, 他对《乡村医生》从社会学角度作了分析。
在《乡村医生》里,“社会的运转失灵被体现为个人的失败和无法确定的罪责。产业工人 能够通过团结来对抗一种与个性无缘的职业活动所引起的失望;而尚未沉沦于麻木不仁、却 仍在生活、仍在思考的小资产阶级面对这种虚空只能无可奈何。他们是社会的牺牲品,带着 一颗负疚的心,在一个社会猪圈里做一位循规蹈矩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有罪的。乡村医生, 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孤独者,在其广泛的交往圈子里是一个救助者。他陷入了啼笑皆非的思 想 矛盾而不能自拔,他所能使用的手段可怜而有限,他处处感到力不从心,而又无法摆脱成为 一个救助者的想法,他绝不听天由命,他时刻准备着为其职业道德而牺牲他私人的生活;可 是他不得不令人酸楚地觉察到,他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徒然……那两匹幽灵之马一开始很快将 他驮去,病人死后却又那么慢吞吞地、那么不情愿地拖着他通过茫茫雪原,这时我们听到了 抱怨和抗议……这是对其职业尊严和生活意义的欺骗者的抱怨和抗议。”(注:E.费歇尔《卡夫卡学术讨论会》,见海因茨·波里策编《弗兰茨·卡夫卡》,1972年, 第372-373页。)
三、图象的象征性
卡夫卡曾经说过,他的作品是通过“图像”表达的,而且“仅仅是图像”。因此,它们也 可以看作是他的“象形文字”。这一特点使我们获得了一把通向卡夫卡作品内部的钥匙,这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作品所显示的图象中去追寻它们所象征的内容。
《乡村医生》的总体画面是破碎的,但构成它的一些局部画面却是完整的图像,并且都被 赋予了某种含义。其中较突出的首先是赤裸的图像:茫茫雪原,无遮无盖,彻底的裸露,而 奔走——不,挣扎——在这片雪原上的主人公,显得特别醒目,他成了失去任何保护的生物 。有趣的是主人公自己也被剥光了衣服,以全身的裸露与外界的裸露相呼应,这使他的孤独 具有了极端的意味,从而揭示出他的总体存在的荒谬性,这种荒谬性包含着他生活中许多滑 稽的、带有讽刺性的处境。比如,他被人们扯得一丝不挂。躺在一个濒死人的身边,却不是 躺在他内心深处爱着的罗莎身边,而此刻,躺在罗莎身边的却是另一个“畜牲”!你看,这 个一心为了事业,为了责任甚至“过了分”的“书呆子”,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里多么不 明世道的变化,他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算,还得“牺牲一个罗莎”!小说中这一荒诞的 场面或图像,不啻是“黑色幽默”的一笔!
其次是主人公与马车的图像:他坐着尘世的车,驾着非尘世的马,在茫茫的雪原上,一心 想尽快赶回去,既摆脱眼下尴尬的处境,又救出遭难的罗莎。但那两匹“非尘世”的马却偏 偏不肯快走!这种情境在现实中是荒诞的,但在梦境中却是真实的。这一梦境图像无非是作 者内心经历的外化,它透露了卡夫卡的形而上思考与他所经历的形而下现实的矛盾,正如前 面已经引用过的E.海勒所说的:他在超验领域做着绝对自由的梦,灵魂却在经验领域经受着 那可怕的折磨。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记中找出这一图像的注脚。卡夫卡在1922年1 月16日的日记中概叹道:“两个时钟走不到一块儿了,内部世界那个钟走得飞快,像是着了 魔,中了邪,不管怎么说,它以非人的方式在疾驰;而外部世界那个钟却仍按老样子,停停 走走。”(注:见卡夫卡《1910-1923年日记》,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美茵,1984年,第3
45页。)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实际上这才是人类世界的常规,因为思想可以插上翅膀 ,而现实的脚步总是拖泥带水的。
第三个图像是病人的伤口,这是小说的中心图像。伤口一般都跟血与脓,亦即跟污秽相联 系,因此毫不奇怪,几乎没有人认为它是美的。但在小说中,它却被称作一朵“鲜花”,而 且是一朵玫瑰花。玫瑰花的德文原文叫罗瑟(Rose),与人名罗莎(Rosa)近于谐音,因此它与 医生家那位名叫罗莎的少女联系了起来,也就是与“美”联系了起来。病人说:“我带着一 个美丽的伤口来到世界上,这是我的全部陪嫁”。这个伤口真可谓“恶之花”了。
但这个伤口图像有着多重的象征含义,既暗示作者的生理伤口,又喻示着作者的精神伤口 。卡夫卡与柏林姑娘菲莉斯长达五年之久的曲曲折折的恋爱婚姻问题对他来说既是幸福,又 是泥潭;既是美的花朵,又是恶的创伤。创伤原来是精神上的,后来又导致肉体上的:1917 年7月他与菲莉斯第二次订婚,同年12月又告吹。在这期间,也就是小说诞生时的9月初,他 患 了肺结核,咯了血。这场疾病显然不是偶然的,跟他多年潜心于写作固然不无关系,但同他 在恋爱婚姻中的矛盾与苦恼显然也有着必然的联系。1917年9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真如你(指卡夫卡自己——引者)所断言的,肺部的伤口无非是个象征,伤口的象征,F .(菲莉斯)是它的炎症,辩护是它的深度,那么医生的建议(光线、空气、太阳、安静)也都 是象征了。抓住这个象征吧。(注:见卡夫卡《1910-1923年日记》,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美茵,1984年,第329页。)
比这篇日记早十来天,9月5日他致信勃罗德说:“我不抱怨。我自己也曾预言过,你记得 《乡村医生》中流血的伤口吗?”(注:见卡夫卡《1902-1924年书信集》,法兰克福/美茵,1975年,第160页。
)九月中旬,他在信中又对勃罗德说道:
显然,这里的还是那个伤口,其象征仅仅是肺之伤口。(注:见卡夫卡《1902-1924年书信集》,法兰克福/美茵,1975年,第161页。
又过了几天,10月初,在一封致勃罗德的信中他把他的“肺之伤口”概括为“一般死亡迹 象的加强而已”。 (注:见卡夫卡《1902-1924年书信集》,法兰克福/美茵,1975年,第177页。
)可见,小说中这个喻比乃是作者的一种精心构思。正如主人公在三重拯 救中其职业使命和道德使命无不宣告失败,因而其存在价值也成了疑问一样,作者在现实生 活 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两难选择而弄得焦头烂额,仿佛陷在“荆棘丛”(这是他的一篇小故事)中 不能自拔,心力憔悴,或曰灵魂受着“可怕的折磨”,那么,他的伤口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 的了。这也就是说,他既然在形而上领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依据,那么他在形而下领域也 就无法维持生存的可能。因此,我们通过卡夫卡肺部的伤口反射在小说人物身上的这个伤口 ,可以窥见它后面隐藏着的多重丰富内容。从作者这一重来说,除了他与菲莉斯之间难分难 解的爱情纠葛之外,还包含着创作与职业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他对父辈威权的诅咒;他对 “目标虽有、道路却无”的苦恼;他对障碍重重、难于迈步的焦虑;他的“异化”感、恐惧 感、负罪感、孤独感、漂泊感等等。从小说主人公这一重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求助者 的自我失落。从人物中的患病少年这一重来说,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普遍生存处境。——这当 然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
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但如果他的这一特点是凭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得的, 那他就算不上是个艺术家;卡夫卡的杰出之处,是他善于将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和感受,通 过各种幻化的艺术手段暗示出来,鲜明而强烈。通过《乡村医生》,我们可以区别出“写作 ”与“创作”来。
四、“现在时”的叙述方式
一篇出色的小说,除了巧妙的构思,还必须有相应的、恰到好处的表现技巧,尤其是叙述 艺术。
《乡村医生》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叙述的。但这个“我”不是小说事件的旁观者或 目击者,而是它的主人公。他也不是叙述以往发生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正在经历的事情 ,所以采用了“现在时”的叙述方式。他仿佛一头兽,突然被人们围住,于是随即紧张起来 ,开始到处奔突、抓攫,以致几乎连向读者交代几句都来不及,只顾不停地、“内心独白” 式地讲他的遭遇。整个过程不过几个小时的功夫,却衬托出一个已经“失去了信仰”的“不 幸的时代”。奏效的秘诀是,作者赋予他以梦的手段。在梦的外衣下,他——即“我”—— 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领域来去自由,并将过去的事情推入现在;他将彼处的事情拉近到此处, 利用梦的材料自由地拼接现实的碎块,并赋予它以意义,使其取得独到的艺术效果。例如, 尘世的车与非尘世的马组成的怪诞图像,医生出发时的瞬间到达与结尾时的迟迟“不到达” 的 滑稽对照,都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意味。又如,有了跟随“神马”出现的马夫的下流行为的刺 激,身为单身汉的医生才突然意识到多年来他忽视了一位姑娘,他心中深爱着她,却又眼 睁睁看着她被别人强占!而光着身子与一个垂死病人共床则更加强其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诞感 。可以说,没有梦的材料,便不可能组装起这一系列奇诡的图像,那么,《乡村医生》凭其 有限篇幅,便不可能蕴含那么丰富而深邃的内涵。无怪乎卡夫卡曾经跟青年朋友雅诺施说过 :“梦揭示真实,在这真实后面滞留着想像,这是生活的可怕性之所在——艺术的震撼人心 之所在。”
五、“内宇宙”幻化的现代神话
《乡村医生》是一篇寓有深奥思维的非理性作品,属于荒诞文学。荒诞文学是一种神话的 现代形态,和古代神话一样,都是幻想的产物。不同的是,古代神话的幻想性基于人类童年 时代的普遍观念,而现代神话的幻想性则基于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或感受,并不遵从习俗的 理性观念或约定俗成的生活逻辑。例如,两匹神马的突然出现为医生救急,而医生心爱的美 丽侍女却遭难在马夫的胯下。如果说,神圣的使命与下流的恶行这两个极端对立的不谐和音 响所讽喻的现代商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助的不可能,这未必是卡夫卡所独有的观点,那么 ,神马为什么偏偏从猪圈里冒出,而不是从庭院、马厩或从门外闯入呢?这就同卡夫卡一贯 对 性行为的鄙视有关;他认为这种行为是“肮脏”的,而肮脏的猪圈就象征着马夫的感官欲念 的下流粗鄙,含着诅咒的意思。别的作家就不一定会这么写。再如,小说中少年腰上的那个 伤口,如前所述,是作者肺部伤口的外映,而这个肺部伤口扭结着他一生多少苦恼与烦愁! 显然,这个伤口的象征内容也是别的作家所无法分担的。因此我们不妨这样来概括和比较古 今神话的区别:古代神话是古人的幻想在外宇宙的驰骋,现代神话则是今人的幻想在“内宇 宙”的飞翔;前者的幻想一般不破坏客体,而后者则是要破坏的。因此还可以再简括一些: 一个是“幻想”,一个是“幻象”。《乡村医生》就是一篇被赋予了象征含义的、深层内 心幻化的产物,是一篇具有现代特征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