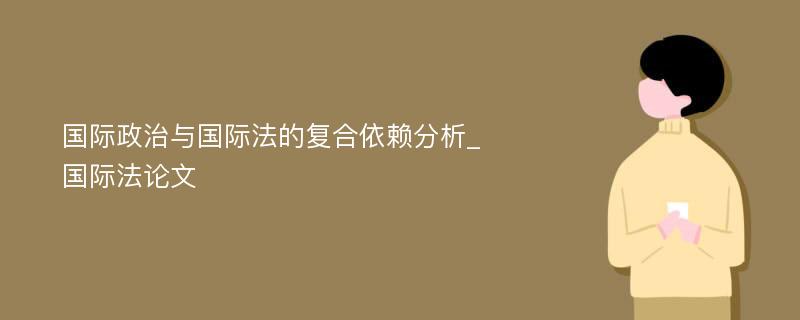
试析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复合依赖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10—0049—07
法律与政治是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两者产生大体同期、性质彼此一致、内容相互交叉、变化彼此互动。① 即所谓“法律是政治的工具,但同时政治又被期望在法律的框架内变化。”② 与此同理,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也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关国际政治的实质,摩根索曾较为极端地提出,国家间政治无非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而斗争。③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权力和利益斗争可能仍然是国家间政治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世界是一种建构”,世界政治体系结构除了物质结构外,还存在社会结构,国家虽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建构而成的”。④ 况且,除了国家利益外,国际社会还逐渐发展了人权、环境、贸易等共同利益,因之,国家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它不能为所欲为,必须遵守基本规范。“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与物质现实同样重要、同样有影响”。⑤
就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来说,两者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产物,国际政治决定国际法的体系结构和发展方向。其二,既然国际政治决定国际法的结构和走向,国际法的发展就必然要体现、反映国际政治的利益和要求。其三,从反向看,国际法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制约国际政治的制度因素,国际政治须沿着国际法的既有轨道运行。缘此,本文试图着力从上述三个向度对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结构依赖关系展开论述。
一 国际政治为国际法提供社会基础和组织保障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⑥ 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⑦ “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进一步指出,“人虽然也是动物,但他是非常的动物,他和动物的差别要比动物与动物的差别更大……人类的特征是需要社会,就是需要和他的同类交往,而且需要和平的、合理的共同生活,所以,一切的动物生来只求自己的利益,这句话是不能适用于人类的”。⑧ 人不但有利己的一面,更有通过群体和组织谋取生命安全与内心安定的一面。有关政治政府的起源,分析法学的奠基者奥斯丁就曾反对社会契约的国家起源论,而坚持边沁的国家起源于“习惯性服从”理论,⑨ 认为社会大众对于政治政府的起源具有一种功利观念,或者说,社会大众不喜欢无政府状态:政治政府形成于自然社会的大众急切地想逃离自然或无政府状态。而所谓政治,即是特定阶层或社会集团为实现其利益和目标,运用特殊公共权力(国家、政权),整合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使社会纳入一定秩序,并得到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现象。
就法律与政治关系而言,简单地说,两者其实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法律的背后总是政治。美国政治学家诺依曼曾经指出,“法律并不能统治。只有人才能行使支配他人的权力。只强调法律的统治而不强调人的统治,结果势必导致人统治人的(政治)事实被掩盖。”⑩ 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其权威和效力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在此,我们虽不能把政治的作用过分放大,造成所谓的“泛政治化”,但作为共同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说,法律由政治决定、为政治服务却是无疑的。法律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治、社会秩序的需要,虽然其背后涌动着经济的动力。可以说,有何种发达程度的国际政治才有何种发达程度的国际法。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影响和决定可以归纳为:
其一,国际政治决定国际法的体系内容和发展方向。政治的作用是整合社会,协调矛盾,法律只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方式。虽然现在一般认为,法律不是统治者的命令,而是像经济的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过程,立法者的所谓命令,也只是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要求进行归纳、反映而已,但政治架构不但决定法律的生成样式,而且影响法律的发展方向。可以认为,没有国际政治就没有作为其工具的国际法,没有国家间的同意和协调就没有国际法作为“法”的效力。什么是国际法?《奥本海国际法》认为,“国际法是对各国在它们彼此交往中有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11) 中国学者一般也认为,“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12) 明显地,国际法是国际关系的产物,并且为调整国际关系而服务。与当今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现状相适应,国际法的约束力并不强大:国际法的两种主要渊源——条约和习惯——需要国家的明示或默示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家间意志的妥协。国家的“自治”和“同意”仍是国际法的本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只是国际政策的法律化而已。例如,战后形成的联合国体制,这便是当时国际格局和政治现实的反映。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实际上是大国政治的结果。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苏联对自身势力的担忧使“否决权”的拥有成为其参与联合国的重要前提要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之所以必须进行修订,是因为公约规定的生效签署国数目虽然早已达到,但大多数是中小国家,在世界政治的版图上不够分量,加之具有深海海底资源开发能力的美、欧、日等大国和地区的拒绝批准,因而使该公约的实际效力被束之高阁。公约的修订实际上是国际政治长期博弈的产物,是对现状的妥协。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制定过程中,有关“国家罪行”的规定曾经成为各国争论的焦点。(13) 事实上,为逃避将来为可能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国际法上规定“国家犯罪”的概念。由于各国分歧较大,草案第二阶段特别报告员詹姆士·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不得不采用迂回的折中办法,将原草案第19条国际罪行的内容转移到其他条款中,而代之以“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性强制规范承担的义务所产生的国际责任”,以删除“国际罪行”的概念及其所涉的刑事问题。如此种种,最终无疑都是政治对比演变成法律样式的反映。
其二,国际政治影响国际法的执行模式和效力权威。国际政治不但影响“国际立法”,而且影响国际法的执行。国际社会是一个所谓“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国家之上缺乏一个至上权威,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主体,既参与制定法律,同时又是法律的执行者和实施者,此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治现实使得国际法的效力从来不如国内法那般神圣、权威。实际上,近代国际法的源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4) 即已规定了有关执行、批准的条款。(15) 例如,关于洛林问题的争执,和约规定的处理原则是,“应提交双方提名的仲裁人,或由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签订一项条约,或采取其他某些友好的办法来解决而不使用武力”。和约还明确提到条约必须遵守,对违反者要科以处罚等。(16) 然而,国际政治的现实——“国家间体制”以及相应为各自私利的争斗,使得国际法虽经数个世纪的进化,其执行效力虽有很大改进但依然缺乏强制力的约束。《联合国宪章》第43条有关联合国部队组建的规定,由于各国利益的分歧,至今难见其端倪。同样,国际法院不具有强制管辖权,其判决的执行主要依赖国家的自愿。世界贸易组织号称“经济联合国”,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赞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但其通过“报复”或“交叉报复”解决争端的执行模式却仅仅只是被世界贸易组织授予合法权力而已,其最终解决还须依赖国家的实力。国际社会的发展虽然已今非昔比,国际组织的决策也不但为国际法的执行提供了法定依据和判断标准,而且争端当事方之外还有了第三方仲裁的通道,但此种执行模式和执行效力实质上仍是国际政治现实影响、制约的结果,是国际政治结构的法律折射。
其三,国际政治为国际法提供遵从“确信”和组织保障。法律的运行需要有行为主体的“法律确信”,这使得一部健全的法律不仅需要合法性,而且需要正当性。国际法比较国内法是一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它需要通过国家的“纳入”或“转化”将其转变成国内法,其自身强制效力的阙如使得世人对其法律属性产生了质疑,此种状况亟须培育,因而需要强化国际社会的“法律确信”。从国际法发展的轨迹看,所谓“共处”国际法更多体现的是其合法性的内涵,而所谓“合作国际法”,却在合法性之外,具有了更多的正当性追求。因此,当代国际法虽然仍免不了追求秩序和平的首要目标,但正义、发展、人权等理念却逐渐成为其重要的价值指向。2005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做的题为《大自由:为实现人人共享的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报告就体现了这种价值指向。如今,联合国体制内升级后的人权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相提并论,便是这种趋势加强的表现。但实际上,国际法这种正当性的加强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正是国际政治通过不断达成新的决策动议,推动国际法向合法性和正当性兼具的方向发展,国际法才逐渐加强了其在人们心目中的“法律确信”,从而促使其能健康有效地运行。人权理念的成形便是世纪之交国际社会“保护的责任”(17) 不断发展、演变、规范的结果。
实际上,在次级规则的意义上,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确信”影响甚至更加深刻。例如,通过规定普遍性的法定适用条件和程序,国际政治为国际法指定了应该运行的方式和范畴。《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6款规定,“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联合国宪章》本来只是一个多边条约,根据条约“对第三国既无损也无益”的原则,《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非会员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然而,由于《联合国宪章》是国际社会的根本性规范,其所约许的是关乎国际社会整体的重大利益,更由于世界的普遍“和平与安全”是战后世界政治的基本诉求,从而使国际社会对此例外规定的许可或“确信”成为可能甚至必须(当然,不能排除条约规则的习惯发展对第三国的后继拘束力(18))。另外,在政治架构上,国际政治还从制度上为国际法的运行提供了组织保障。国际法不仅是观念的构建,它还有实际机构的运行。国际政治通过提供必要的组织平台、裁判渠道、执行力量和必要的经费保障,为国际法的有效运行搭建了必需的组织框架。舍此,国际法可能成为空中楼阁,有法难依。
二 国际法体现和确认国际政治的利益和要求
如果说国际政治决定了国际法的生成、执行和遵守,那么国际法体现和确认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要求就成为必然。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其对国际政治的体现和反映要更为明显和划一,并且这种体现和反映贯穿于国际法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
历史表明,“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19) 15世纪后,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文艺的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进,这些都给欧洲国际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在探寻国际政治中的秩序问题时,赫德利·布尔指出,实际上有三种相互竞争的思想传统,贯穿于近代多国体系历史的始终:(20) 强调通过国际法来规范和指导国家间关系的“格老秀斯主义”,主张用道德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共和制与民主化来培育世界和平的“康德主义”以及主张通过权力追求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衡的“霍布斯主义”。
“格老秀斯主义”实际上就是国际法主义,它兴起于17世纪,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西方大国一直坚持通过权力政治的视角来观察国际关系。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短暂时期之外,“格老秀斯主义”从来不曾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占有过重要位置。相反,“霍布斯主义”长期以来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根本不同。国内社会以宪政为基础,权力政治受到法治与民主的有效约束,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权力互动不仅常常超越法律,而且比法律关系更可靠。(21)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选择,因为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国家利益的实现主要依靠国家的自助,国际法只是对现状的记载。在国际关系激烈变动的历史长河中,国际法的滞后性和软散性使它不可能对国际政治进行提前“勾勒”。
然而,尽管如此,“霍布斯主义”还是要借助“国际法主义”进行必要的确认和保障,以使国际关系的进行能具有某种预期。因为正是“由于国际体系本身是无政府的,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稳定性和确定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缺少一个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国家在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时是相对不受约束的。国际条约创设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规则,包括一种预期结构……据此主权国家在某种预先确定的范围内形成规范的合作关系便是有可能的”。(22)
比如,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实际上确立了近代国际法发展的源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法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开创了通过国际社会的行动制定一般国际法规范的先例。”(23) 同时,该和约也是近代通过国际法大范围确认政治现状的开始,其所创立的三大原则:国家主权概念、国际法原理、实力均衡政策,(24) 事实上成为了此后国际社会发展的支柱。例如,政治上的国家主权原则被确立为国际关系中的“宪法性准则”,规制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成为“有约必守”的规则制度,而实力均衡政策被运用为确保前两项原则的重要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具体法律上的确认和反映表现在,宣布荷兰和瑞士独立、重新划定边界,承认国家平等原则等等。在此过程中,荷兰国际法学家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因为符合这一时代趋势而成为模范标本,各国首脑人手一册,据此进行交战与和谈,格老秀斯因此成为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获得“国际法之父”的美称。其实,就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体现和反映来说,此后无论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制”,还是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或者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莫不如此。
国际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国际政治关系往往被视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被等同于国际关系,这是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政治力量历来是控制的力量、支配的力量,虽然国家的经济力量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已日趋重要。(25)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过于偏执地提出,“国际政治的铁的法则是,法律义务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完全否定国际法的制约作用就有替强权主张之嫌,因而招致学界的猛烈批判。然而,就体系变迁、格局转换等根本政治层面而言,国际法又无疑是附属于政治变化的。“世易时移,变法宜也”,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493年,迫于西班牙、葡萄牙海上势力的强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宣布在两国之间分割世界海洋。一个世纪后,“海上马车夫”荷兰崛起(1609~1713年),随之对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进行了坚决抗辩。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成为新的世界性旗帜。1714年,英国成为全球占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后,也随即抛弃了约翰·塞尔登(Seldon)的《海上禁锢论》立场,转而大肆推行开放海洋说。20世纪后半期,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独立道路,要求以经济主权巩固政治主权,在它们的大力斗争和推动下,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领海制度、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甚至海底资源进行了新的法律确认或创设。很明显,国际法的改变无疑是政治变化的结果而已。
美籍华裔教授熊玠主张,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着一定的“体系价值”,这些价值来源于某些观念或理想。“如果规范可以被看成是‘游戏规则’,体系价值则为特定时期国家间关系这一游戏本身下了定义。例如,在18世纪,君权神授的观念是压倒一切的体系价值,在19世纪,主要的体系价值则是创建殖民帝国的要求。出于同样的原因,在20世纪,民族自决及相关因素成了主要的体系价值。”(26) 体系价值其实是政治文化的反映。因此,体系价值对国际法的影响也就是政治意识对国际法的影响。例如,《联合国宪章》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确认来源于列宁和美国总统威尔逊之间的政治宣传战,“起初含义很窄,第二次大战后,受政治价值的影响,开始成为全世界为之奋斗的理想”。凡此种种,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确认和反映都是不言而喻的,所有这些都是法律作为政治工具意义的表现。然而,应该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律规定都是所谓的政治工具的表现。像有关技术标准、医疗卫生和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法律,就不是政治的直接体现,虽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它的政治意蕴。
总体而论,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最大体现表现在宪章性文件的结构安排上。宪章性文件是国际政治对国际社会的总体布局和框架规划,是一般国际法的“母法”,一般国际法不得僭越宪章性文件的效力。例如,《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对于有关区域办法,第53条规定,“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区域行动,“不论何时应向安全理事会充分报告之”(第54条)。另外,《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6款还规定,“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有关宪章的修改,《联合国宪章》本身也规定了2/3的会员国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的较高门槛。(27) 因此,如同国内宪法是国家国体、政体及各种基本制度的根本一样,《联合国宪章》也通过反映一定时期的格局特点和政治要求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和行动指南。如此,宪章性文件成为体现、反映国际政治利益和要求的最大“橱窗”。
三 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制度约束
前已述及,既然国际政治影响和决定国际法的发展,而国际法又相应地体现和确认国际政治的内容,那么两者的影响是否是单向的,或者说法律是否仅仅只对政治进行记载呢?笔者认为,国际法之所以成其为法律,必然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国际法的价值意义不仅表现在它是各国意志的协调,从而具有合法性,而且还表现在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具有自己的法律拘束力,能对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提供制度约束,这种约束表现在:
第一,国际法的政治调整。对国际政治进行调整应该是国际法的首要功能。利益的追求使政治永远处于一种争斗状态。但是,政治斗争又有其策略和原则,它追求妥协共存,本质上要求“斗而不破”,而不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毁灭,从而冲突与合作成为国际政治的两种典型状态,并由此需要国际法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国际法的适时调整能确保社会的更新和达成新的权力平衡,推动国际社会朝和平、稳定与有序方向发展。此种调整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28) 一方面,遇体系变迁,例如大规模国际冲突引发格局转换,国际法往往通过对战争结局进行固定,剔除不合时宜的旧内容,创设反映现状的新制度,来对国际局势进行调控。由于这种调整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或不可抗拒的社会变革而引起,失势的一方往往无力抗拒,因而调整的力度较大,强制性更高,有效性更持久。这种状况可以说是由“社会质变”引起,即危机引发变革,如前述威斯特伐利亚战争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格局、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维也纳体制、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制和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等。另一方面,“社会量变”也需要法律调整。对于发展失衡可能导致体制失效、无能甚至崩溃的情况,国际社会往往通过“局部改良”来适应新的变化。当然,由于这种变化不是体制内激烈动荡、冲突的结果,其演进相对缓慢。然而,不管怎样,国际法正是通过对国际政治的调整、改良来推动波折起伏的国际政治不断迈过沟壑丛林向前有序挺进的。从反例来看,一般认为,国际联盟的失败与其不能有效调整二战前的政治形势直接相关。由于未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真正纳入(美国从未加入,苏联后期加入旋即又被开除),非对称的权力现状导致它对大国施行制裁时的软弱无力。“因为若以军事方式制裁一个大国,势必要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若以经济方式制裁一个大国,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可能给那些同意制裁的国家造成困难。”(29) 制裁尚且不能,调整更无从谈起,因此国联被赋予新机制的联合国取代成为时势必然。
第二,国际法的政策规范。法律是政策的规则表达。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有两个:习惯法和条约法。在国际社会的早期,各国各地区少有联系,国家对习惯的法律确信需从国家的行为中反复寻找、辨别。现代以来,由于两次世界性战争的激荡、全球化的推进特别是交通、通讯的发达,使得国际社会的联系愈益紧密,协调更易达成,条约便逐渐取代习惯成为国际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例如,有关国际法的适用,如果条约法与习惯法同时并存,一般要求首先适用条约法,除非条约与随后形成的强制性习惯规范相抵触。值得指出的是,国际习惯并不等于国际惯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丑项规定,国际习惯,即“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包含客观和主观两大要素,即类似行为的反复实践以及心理上的法律确信。而惯例仅指某种行为的惯行,行为者并未确信其具有法律拘束力。然而中国的外交文件和国内法却一律不加区分地将“国际惯例”一词替用“国际习惯”。但是,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却“应使‘国际习惯’作为国际法的渊源”。(30) 与习惯相比,条约具有更为明晰、规范的特点。通过条约的规则表达,能使国际行为减少模糊,增加明确,形成预期,使国际社会真正“有法可依”。同时,国际法的规范作用,能指引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朝规则、秩序的方向演进,因为通过条约形式把各种规范法制化,实际上等于确定了建立秩序的指南。更重要的是,如此行为是通过各当事国的多边谈判平等实现的,它不但能克服法律的空缺或模糊性,而且能防止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专横强制,从而促进行为主体的合理预期,保证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
第三,国际法的行为评价。法的评价作用主要是指法律判断、衡量他人行为的合法与否。相对健全的国际法规范能为行为主体的行为评价提供客观标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的遵行程度往往不能与国内法相比,国家特别是大国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可能不时违犯国际法的规定,从而出现所谓“强权立法”的现象。然而,此种情况,即使大国也往往不是要否定国际法,每当它们违犯时,总是以国际法为标准,辩解其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或不敢公然否定国际法,因为从长远来看,规则、秩序实际上符合每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在某些违犯情况下,国际法虽然不能完全进行强制阻止,但它至少能为国家行为提供可资辨别的尺度,从而使违犯行为昭然若揭。正如前国际法学会会长、《国际联盟盟约》起草人之一的尼古拉斯·波利蒂斯在一战后所论及的,“如果国际法不比其他的法律更为先进,就必然和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样有着同样的起源、同样的基础和同样的目标。像个人一样,国家只有在其被授权的社会允许它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有行使合法权力的自由,而且该权限仅在与这一社会的目标相一致时才是合法的;当它与社会的普遍利益相冲突时就是非法的。”(31) 国际法作为普遍秩序的“以规则为导向的体系”,其效力虽时有欠缺,但其规则却有如明镜,能照出国际社会的美丑善恶。
第四,国际法的法制约束。国际法过去常被称为“软法”,由于各分支部门各自为重,某些法律规范出现了偏颇甚至矛盾(例如国际贸易法、国际知识产权法与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的冲突),(32) 更由于缺乏立法机关、具有强制司法权的法院以及集中组织的制裁,使得人们或多或少对国际法的法律属性产生了质疑。(33) 然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国际法的建构、约束作用已日渐突出。国际法既然是国际政策的规则表达,是各国意志的最后协调,其遵行一般就会符合各国的利益,其违反也就一定会受到某种机制的制裁,不管是正式法律的还是基于法律的其他强制。《联合国宪章》序言宣告,“……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第2条规定,“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保证全体会员国由加入本组织而发生之权益”。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规定条约必须遵守: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34) 由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国内法的规定可以与国际法的规定不一致,但如果因此导致国家对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违反,则国家须承担国际责任。此等国际责任一般包括限制主权(如二战后盟国对德、日的军事管制)、恢复原状、赔偿和道歉等等。
如今,随着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增长,国际法约束力的加强已成为必然的趋势。1970年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力设施案”中提出了“对一切的义务”。(35)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正式提出了“强行法”的概念,其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强行法的出现使国际法逐渐显示出了“位阶”,凡与强行法相对抗的法律,其效力当然归于无效,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维护具有根本重要之利益的决心,也表明了重要基本国际法的神圣不可侵犯。正如国际刑法的发展,基于二战后纽伦堡、东京审判和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刑事法庭发展起来的国际刑事法院俨然成为高悬于严重违法犯罪者头上的一把利剑,一有相关情事违反(灭绝种族、危害人类或战争、侵略罪),无论官职、不问国内法律规定为何,一律同等问罪。同样,人权的保护也逐渐深入到国家的“传统管辖领域”,“保护的责任”正式确立。各种国际性司法、仲裁机构效力增强,次级规则增多。凡此种种,都是国际法强制约束力加强的明显表现。国际法已经长出了“牙齿”。
四 结语
国际法的发展不是奥斯丁的所谓“命令”式发展。狄骥指出,法律既不是命令的形式,也不是意志的表现,它纯粹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为社会成员所自觉遵守的一种纯粹的事实。社会的统治者只需把它制定到各种法典和条约中。(36) 波利蒂斯也认为,法律只是人类生活的映像而已,与人类的生活一样,法律同样处于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其形式代表着一种社会形态,但却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社会状态。(37) 如此,法律的“制定”和“遵行”就是社会发展水到渠成的一个客观情势,国际政治既不能人为排除国际法的作用,国际法也无法跳出国际政治的背景。两者相互强化,共同建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无水不能生存一样。
就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相互关系来说,国际政治影响、决定国际法的内容与结构,国际法体现、制约国际政治的运行及走向,这是其实质。然而,进一步想来,就两者所产生的影响程度而言,国际政治影响国际法无疑更为根本和主动,国际法制约国际政治则相对被动和表面。作为上层建筑,质而言之,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际法,其发展又必然以经济为基础,以社会为导向。
注释:
① 参见卓泽渊:《论法政治学的创立》,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3~4页。
② Onuma Yasuaki,“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4,No.1,2003,p.27.
③ 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NcGraw-Hill,1985.
④ Peter 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in Peter 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2.
⑤ 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128;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228页。
⑥ 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⑧ H.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amsterdami,1646,latin texts & translation by francis w.Kelsey,et al.,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London:Humphrey Milford,No.1-i,I 1925,p.15.
⑨ 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第312页。
⑩ F.Neumann,“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Freedom,”Cohonbia Law Review,Vol.53,No.87,1953,p.910.
(11)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陈公绰等译:《奥本海国际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2) 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另见端木正主编:《国际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3) 有关国际罪行的争论,详见贺其治:《国际责任法及案例浅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5页。另见古祖雪、陈辉萍等:《国际法学专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269页。
(14)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神圣罗马皇帝和瑞典女王以及他们各自的同盟者之间的和平条约》(即《奥斯纳布鲁克条约》)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神圣罗马皇帝和法兰西国王以及他们各自的同盟者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明斯特条约》)两部分组成。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
(15) 《明斯特条约》第104~128条。
(16) 《明斯特条约》第5、97、111、112、122条。
(17) “保护的责任”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保护本国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族裔清洗、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则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有权代位行使保护责任。“保护的责任”使相关人权的保护具有了双重保障的可能。有关“保护的责任”参见李杰豪:《保护的责任对现代国际法规则的影响》,载《求索》,2007年第1期,第101~103页。
(18) 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第38条相关规定。
(19)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0) 相关论述详见[美]熊玠著,余逊达、张铁军译:《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224页。
(21) 参见朱锋:《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法律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35~138页。
(22) 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第235~236页。
(23) Leo Gross,“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648—1948,”in Charlotte Ku and Paul F.Diehl,eds.,International Law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Boulder Co.:Lynne Bienner,1998,p.60.
(24) [日]山本宣吉主编,王志安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4页。
(25) 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6) 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第42~44页。
(27) 见《联合国宪章》第109条及相关修订案。
(28) 参见肖凤城:《试论联合国体制的走向》,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61页。
(29) 叶宗奎、王杏芳主编:《国际组织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30) 参见余民才、程晓霞编著:《国际法》教学用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另见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66页注释1;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5页。
(31) [希腊]尼古拉斯·波利蒂斯著,原江译:《国际法的新趋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2) 有关论述详见古祖雪:《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5~147页。
(33) [英]H.L.A.哈特著,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的概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34) 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第27条。
(35) 参见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417页。
(36) 尼古拉斯·波利蒂斯:《国际法的新趋势》,第4页。
(37) 尼古拉斯·波利蒂斯:《国际法的新趋势》,第20~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