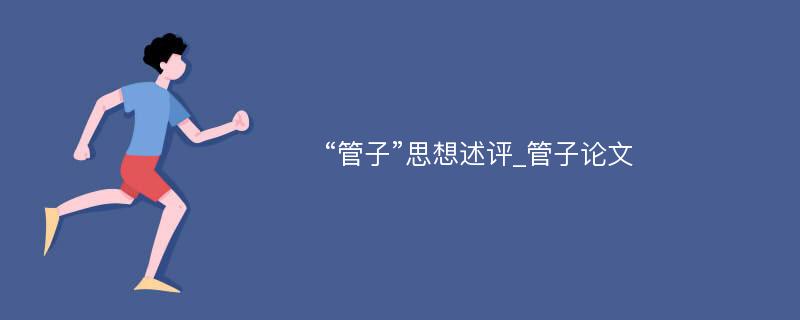
《管子》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仲的执政实绩,深得后世景仰。孔子曾称赞管仲为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仁爱之人,对子路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对子贡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司马迁也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②鞠躬尽瘁于蜀汉的诸葛亮隐居隆中时,也“每自比管仲”③,对管氏的功绩,充溢着景仰之情。凡此,皆可见出管仲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管仲逝世后,流传着一部《管子》,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曾详研细读。司马迁就说过:“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④这时的《管子》不但“世多有之”,而且已有多种版本。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整理《管子》,在其《校录序》中说:“所校雠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按:当为四百七十八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刘向整理后的《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八十六篇,《隋书·艺文志》著录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八卷,《唐书·艺文志》著录十九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十四卷。今本《管子》名为86篇,但《王言》、《谋失》、《正言》、《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等10篇有目无文,实存76篇,而且部分章句已经驳杂难辨,似已失去刘向校编本原貌。再加上词义古奥,简篇错乱,文字夺误,因而已成“难读”之书。但细绎内容,却又可以谓为一部颇为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大凡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自然科学思想等等,无不包容,其中不乏精辟的议论,深邃的见解,至今仍深有启迪。拙作拟先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粗加述评,以期抛砖之效。
先谈政治思想。
《管子》的作者十分强调治政要“以民为本”,明确肯定民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霸形》说:“齐国之百姓,公之本也。”《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五辅》说:“人之不可不务也,此天之极也。”作者显然确认,民众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根本,重视民众的作用,是完全符合最高天道原则的。作者还认为,作为执政者,不但应该十分重视民力,而且必须十分注重民心。《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向背,可以决定政权的兴废。执政者务必明察民心向背,顺乎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唯其如此,施政才能得到预期效果,“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若是一味威压,不但“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反而会弄得“令不行”而“上位危矣”。总之,“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执政者务必深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最后一句说得至为明白,只有顺应民心,给予人民以必要的物质利益,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使之尽心效力。
与此同时,作者又明确提出,取用民财民力必须“有度”、“有止”。道理很简单,因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⑤。君主绝对不应为了满足于一己的无穷之欲,采取竭泽而渔的愚蠢办法而导致政权“必危”的恶果。《管子》的这些高论,与孟子的“民贵君轻”、贾谊的“民无不为本”、黄宗羲的“民主君客”、王夫之的“民心之大同”等见解,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疑已呈现出后先辉映的光芒,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观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
《管子》十分强调君主集权,认为立法、决策、行政及人事任免等大权君主尤须独揽,不可须臾旁落。《立政》篇就颇为具体地论述了君主制定与颁布法律、政令的制度:“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宪籍分于君前。”这种作法,旨在保证法出于一孔,令出于一型,不致中途增损异样。而后,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立即出朝,将宪令传达到乡官、乡属、游宗,一直发布到民众之中。留令者、违令者、增令者、亏令者,一律“罪死不赦”。很显然,这是为了维护法律、政令的威严及其传达的准时和准确。
作者认为要使君令畅通,还需有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⑥。“主”,是指军中统帅;“长”,是指朝廷辅相。二者在国君统领之下,分理军政大权。至于地方乡里,则须按行政区划设置官吏。“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⑦,“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⑧。从中央朝廷到地方乡里,作者提出要建立这样一个较为严密的行政管理系统,此无他,目的就在于加强君主专制。
治政尤须注意选拔人才。在这方面,《管子》提出的原则是选贤任能。“备长在乎任贤”⑨,国君在人事任免方面必须持审慎的态度,务必注重臣吏的素质,使德义与其爵位相称,功绩与其俸禄相称,才能与其官职相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农业),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⑩。很显然,这个原则的提出,是为实现长治久安、富国强兵而王天下的大目标服务的。对于任人唯亲、世卿世禄的用人制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否定。
什么是贤?《管子》提出了两条标准,一是“义立”,二是“奉法”。“千里之路,不可以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以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义立之谓贤。”(11)这就是说,大人之行没有先例常规,合乎义者即为贤。又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12)这些内容,主要是属于道德方面的要求。“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13)这些内容,主要是属于行为方面的要求。“经臣”也就是贤臣、法臣。“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就是以奉法为贤。两项标准,前者侧重于贤臣的主观素质,后者侧重于贤臣的客观行为,二者得以兼顾,任人的标准是很全面的。
贤在何处?如何求贤?《管子》的高明处不但在于认识到了“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这个客观事实,也不但在于制定了一份颇为完整而缜密的人材普查提纲(14),尤其在于提出了一个“下什伍以征”(15)的选拔贤才的崭新观点。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所谓贤才,不但存在于贵胄之中,也同样存在于平民之中。这正是《管子》求贤理论中闪光的民主色彩。《山权数》提出“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黄金一斤”,“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民之知时‘且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此国策之大者也”。这种重奖在农事、畜牧、园艺、医药、历法、养殖等方面有贡献的科技人才的措施,并把它作为一项重大国策的作法,也正是奖掖贤才的指导思想的具体运用。
其次,谈经济思想。
《管子》主张经济治国,认为“民富则易治”(16),则国安。“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17)。只有加速发展经济,才能称霸天下。如何实施经济治国的方针呢?《管子》认为必须以地为本,以农为本。作者把土地问题看得至为重要,认为“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18),因而首先必须采取“正地”措施;调动农民的务农热情。“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必正。”(19)只有核实了田亩,授田才能“均平和调”。农民知道了耕地多少、缴税多少、自得多少,“乃知时日之蚤宴,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才会“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不惮劳苦”(20)而勤于农事。其次,必须不断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生产才能发展。作者明确指出:“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21)。“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22),焉能安国而王天下?因此,《治国》一文反复强调“辟地”、“垦田”是“富国多粟”的前提,一再指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也正是基于欲实现“国富”、“兵强”、“战胜”而王天下这个总目标,因而《管子》重农重地而不轻工商,认为工商之业可为农事提供资金,可为农副产品找到销路,认为工商之民同样是建设国家的基石。《小匡》篇说得十分明确:“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所谓“石民”,即为柱石之民,亦即国家之基石。将工商业者和农民提到与“士”平列的地位,同称之为“石民”,正是着眼于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实施经济治国的方针,作者还提出了“务本饰末”的主张。《幼官》篇说:“务本饰末则富。”“本”,指农事;“末”,指“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23)之类的奢侈品生产。“饰末”,即对奢侈品生产加以整顿和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务本”,以期促进农业发展。在作者看来,个中道理很简单,因为“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24)。
《管子》的经济思想中,最有新意的部分是“轻重”学说。“轻重”学说的内容,主要反映在“轻重十九篇”之中。其中《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等已是有目无文,因而实际上现存的只有16篇。这是一组专门阐释财政经济问题的著述。作者已经认识到客观的价格规律的自发作用对于民众生活的重大影响,已经认识到人们的生产劳动与物价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凡将为国”,不可“不通于轻重”,国君必须认识价格规律,并自觉地动用这一规律来“调通民利”,控制市场,采取“以重射轻,以贱泄平”(25)的措施来积累资财,平衡物价,稳定民心,巩固政权。
如何运用价格规律来获得高额利润、积累资财、充实国库呢?《管子》提出国君必须注意两个要点:一是要“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26),即掌握黄金刀币这个流通手段来调动民力,促进五谷食米的生产。生产发展了,理财就好办。否则,纵有“巧妇”,也将难为无米之炊。正如《轻重己》篇所说:“通轻重”固为治国妙术,但若无四时所生之万物,则虽有妙术,也将无法施展。二是要坚持“利出于一孔”(27),即实行高度集中。粮食、盐、铁是广大民众维持生活、扩大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当由国家调剂掌握。国家掌握了财利、资源,控制了货币发行,有了充裕的经济实力,方能有效地控制流通枢要,控制市场物价,方能达到避免动乱和“无籍而赡国”的目的。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眼光不但看到了国内,而且看到了国外。在《地数》、《轻重甲》诸篇中,作者提出善于治国的君主不仅要善于掌握天财地利,及时调控物价,经营国内流通,而且要借助对外通商手段,善于汲取国外资金,利用国外劳力,使“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并通过加强同各国的贸易往来,以期造成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这种理财见解,是十分可取的。总之,《管子》的重视经济治国的这一思想,在诸子百家之中确实是独具特色的。
再次,谈哲学思想。
《管子》的哲学思想,也是兼容各家,其主体则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其中,关于“道”的论述最为详尽。比如,《心术上》说:“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枢言》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内业》说:“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形势解》说:“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这些论述,颇为清楚地说明了《管子》所谓“道”,即源于老子之“道”,又已有别于老子之“道”。《管子》之“道”,已经包含着两个层次:其一,“道”是“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合络天地,以为一裹”(28),并且包容着“精气”这一物质实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其二,“道”的活动具有“人不能固”的规律,谁也不能违背。“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29)此中所谓“天道”,就自然观而言,是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社会观而言,则是指治国治民的基本法则。很明显,相对于老子之“道”而言,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改造、补充和发展。
《管子》对“法”的论述也颇详尽。《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法法》说:“法者,民之父母也。”《权修》说:“法者,将立朝廷者也。”《禁藏》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重令》说:“治民之本”,“莫重于令”。这些论述,简明扼要地阐释了“法”的巨大作用,强调了“法”的极端重要性。国君以之为治民的根本,百姓以之为活命的依凭,都是不可须臾废离的。继而作者将“法”的“准则”这一概念加以扩展,衍为“法令”、“法律”、“法制”。《明法解》说:“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欺也。”《七臣七主》说:“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心术上》说:“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些论述,进而将法、术、势融为一体,无疑是对法家思想的综合与补充。
但《管子》的“重法”思想的特点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通过对老子哲学的改造,为“法”提供了哲学论证,实现了“道”与“法”的结合。《七法》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未”。这些论述,从“常则”的角度论证了“法”的客观性。《版法解》说:“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形势解》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形势》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这些论述,从“天常”、“地则”即“道”的永恒性,论证了“法”的常存性。正因为《管子》既重“道”,又重“法”,视“道”为宇宙之大法,视“法”为社会之大道,因而“道法并重”、建常立仪的思想成了统帅全书的主线。
《管子》虽重道、法,但并不排斥礼、义。《牧民》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很重要,是巩固国家政权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那么,礼、义与道、法的关系怎样呢?《心术上》有一段颇为通盘的解释:“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大(30)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礼出乎理,理出乎义,义因乎宜者也。”(31)这就是说,万物禀“道”而生成之后,便各自具有其一定的形状和性质。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义”。将各种不同事物、人事关系制度化,就是“礼”。将这类关系、制度统一起来,用政权的强力加以保证,就是“法”。而仁、义、礼、法的结合点,则是“道”。这四者都是以“道”为本体的。尊虚静,尚变化,重道、法,容礼、义、将齐鲁之学的旨义熔铸一炉,这就是《管子》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总之,《管子》的内容很丰富。若就其思想派系而言,则兼容着道家、法家、儒家、兵家、阴阳家、农家、医家等学派的思想和主张。但细绎起来,却并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各家,而是有所交汇、贯通。完全可以说,它是博纳百家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家派系。命之曰“杂家”或者“通家”,也许更符合《管子》全书的实际。
注释:
①《论语·宪问》。
②④《史记·管晏列传》。
③《三国志·诸葛亮传》。
⑤⑥⑦(21)(24)《管子·权修》。
⑧⑩(23)《管子·立政》。
⑨《管子·版法》。
(11)(28)《管子·审合》。
(12)《管子·五辅》。
(13)《管子·重令》。
(14)参见《管子·问》。
(15)《管子·君臣下》。
(16)《管子·治国》。
(17)《管子·牧民》。
(18)(19)(20)《管子·乘马》。
(22)《管子·七法》。
(25)(26)(27)《管子·国蓄》。
(29)《管子·形势》。
(30)小大,原文为“小末”,据丁士涵说校改。
(31)“礼出乎理,理出乎义,义因乎宜者也。”原文为“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据王引之说校改。
标签:管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