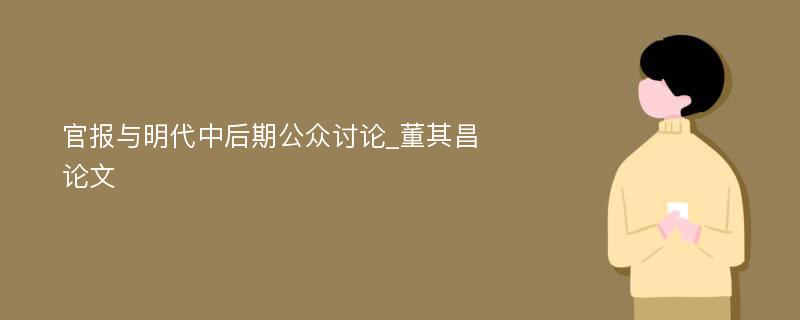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晚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邸报多被今日新闻学研究者称为报纸的前身,亦有档案学研究者视其为档案的,并于报纸与档案之名义上引发的相关问题探微索隐,展开争议,实则多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唯日人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将邸报与言路即“议政”联系起来。在笔者看来,邸报实为明代中央政府的政务公开和议政公开的渠道——这里,我们必须审慎地使用我们今日所见之相关事物如报纸、档案等急于给其定性,否则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纠缠。而邸报所包含的政治内容之广泛,及其所覆盖的地域空间之广阔,使明代政治保持了高度的公开性、透明性,为明代士大夫与士人公开议政提供了必要条件。鉴于古代政治制度的复杂性,本文之论域仅限于明代邸报,至于宋与清的邸报则不在其内。 明之邸报,未载于《明会典》与《明史·职官志》之中,看似是一项无关紧要的政治制度架构,实则不然。如研究者多提到的明末清初两大儒顾炎武和王夫之均曾论及邸报,且非在无关紧要之情境中论及。顾炎武(1959)于论清修明史之事时提及邸报:“修史之难,当局者自知之矣。求藏书于四方,意非不美,而四方州县以此为苦,宪檄一到,即报无书。……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官修历史,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后代修前朝之史,抑或是下一个君主修前一个君主之实录。修史之原则首先在于“信”、“实”,这一原则对于超然于清修明史这一事件之外的儒家士大夫顾炎武而言,自不待言。在恪守此一原则的前提下,而以为修史“止可以邸报为本”,则“邸报”之可信性几乎是毋庸置疑的。邸报之可以为修史之“本”,说明了它的另一个特征,即作为原始史料,它所涵盖的内容非常之全面——特别是以政治史为核心内容的正史所需之政治史料。 邸报之可以作为官修历史之依据,并非仅出于顾炎武一家之说。在有明一代,邸报实曾作为官修实录的一个来源。如《明史》所载崇祯年间修天启实录事:“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探事迹于四方。(钱)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张廷玉等,1974)此则见于议论。而时获纂修官任命的董其昌则曾奉旨往南京采辑邸报,以参订实录:“天启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圣旨,董其昌题充纂修官,俟泰昌实录稿成,前往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董其昌,1997)。而曾在翰林院目睹实录之纂修过程的蒋德璟(1983)则如此说:“作史难,读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见所纂实录,皆采科抄章奏与《起居注》两者。而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删润,以诸曹掌故与邸报参补而已。”当然,蒋德璟在此主要检讨的是实录修纂包括邸报在内的诸般原始资料的缺陷,但无论如何,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邸报是修纂实录时进行“删润”、“参补”的主要依据。综此可知,明代所修万历始的后三朝实录,均曾以邸报为重要原始资料。 王夫之(1996)是在《噩梦》一书中提及邸报的,此书主要内容是反省明代政治制度之得失,所谓“因时之极敝而补之”,并借此而希望于“礼乐百年而后兴”有所垂鉴。在这样一个篇幅很短的反省政治制度得失的著作中有一大段论及邸报,可见在王夫之心目中,邸报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政治建制。王夫之在此段话中虽主要讨论的是邸报于制度上可能造成的漏洞①,然他对于邸报之核心意义认识得非常清楚和明确,所谓“公是非得失于天下”(王夫之,1996),寥寥数字,尽得其髓。 那么,这既可以作为官修历史之凭藉,又可以“公是非得失于天下”的“邸报”,究竟是怎样一个事物呢? 一、作为“议政”公开的邸报及其边界 在谈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首先须明白邸报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新闻学研究者虽有聚讼,但如果说邸报主要是登载奏章与诏旨的,当无异议,如以四部分类法而言,就是“史部”之“诏令奏疏”类。而明代邸报之主要或直接来源,就是六科之“科抄”,这一点对于研究邸报的新闻学者而言,亦多无异议。诏旨不在本文论域之内,因其乃国家之正式政策命令,其公开是一种必然。2奏疏则有所不同,它并非国家正式之政令,无论是出于职守的“题本”,抑或以个人名义进呈的“奏本”,除奏事而外,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议政”。那么“议政”的公开是否有一个边界呢? 或许有的研究者会质疑笔者提出了一个假问题,因为这个所谓“边界”是很明显的,如王夫之(1996)所言:“题奏得旨,科抄下部,即发邸报,使中外咸知……”此中明谓“题奏得旨”,既已得旨,则亦具有了政令的性质,当已摆脱了“议政”的属性。王夫之这里所言,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如《明史》所载何楷(崇祯八年)之疏言:“故事,奏章非发抄,外人无由闻,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张廷玉等,1974)然而,“得旨”、“奉旨”意味着什么方是理解此一问题的关键。“得旨”、“奉旨”并不必然意味着“议政”的终结,有时候反倒恰恰是“议政”的开始。 有一类奏疏所“奉旨”,如“某部知道”、“该部知道”、“某部议了来说”、“某部议行”等等类似的措辞,就是议政的开始。这类奏疏一般而言,所议之事,乃某部、某衙门之事,故而“旨意”下达只是让有关部门并行议处。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言之,凡各部、各衙门“题覆”之疏,一般而言即议行、议处此类“旨意”的。 这是从“奉旨”、“得旨”的意思来思考“议政”得以公开的边界。如果我们换一种提问方式,这个问题也许会更为清晰,即什么样的奏疏不会“奉旨”、“得旨”从而公开呢?除“密疏”而外,只有一种情况,即“留中”。然而,“留中”虽在明代时有发生,而以万历一朝为甚,但“留中”并非一种正常的情况。万历初登大位之时,高拱内阁上疏指出: 凡官民本辞,其有理者,自当行;其无理者,自当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当惩治;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则不知果经御览而留之乎,抑亦未经预览而有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系紧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再陈,岂不有误? 今后伏望皇上于凡一切本辞尽行发下,倘有未下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请乞明旨。其通政司封进外来一应本辞,每当日将封进数目,开送该科备照;倘有未下者,科官奏讨明白。如此庶事无间隔,而亦可以远内臣之嫌,释外臣之惑,其于治理,所关非细。(高拱,2006) 高拱内阁首先指出,上疏所言无论允当与否,均须有所措置,“留中”于理无据,且无此必要。并进而言及“留中”所可能引发的弊端,除有误于“紧急密切”之事而外,或会引起中官从中作梗,“未经御览而有留之”即指此而言。须指出一点的是,疏中所谓“官民本辞”,依明朝制度,上疏言事并不局限于官员,除生员而外,一切人均可以上疏言事。 为了避免“留中”情况的发生,高拱内阁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即由通政司③每日统计章奏数目,并将此数目交送六科,以与奉旨发下章奏之数目相对照。二者如不相符,六科要“奏讨明白”,即追究章奏之所以未发下的原因。 高拱内阁此疏曾被收入《春明梦余录》以说明明代内阁之职掌,因而非常具有代表性。从此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政治正常运转的状况下,所有章奏都应该“奉旨”发抄。而通政司与六科奏章数目须能核对得上这一点,更直观地说明了此一问题。也就是说,“疏不留中”应该是一种政治原则,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一点,高拱内阁提出了制度上的建言,增加了通政司与六科核对章奏数目这一环节,并由六科这一本来即担负政治监察责任的政府部门来审查“留中”这一可能会发生的行为。从该疏末尾所附“奉圣旨”之“都依行”(高拱,2006)可知,此制度上的建言至少在当时已经获准施行,成为一种制度。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在政治运行保持常态时,官员们议政之章奏当会经由科抄,而最终以邸报的形式完全公开。“奉旨”并不能对章奏公开形成障碍,“奉旨”只是在有的时候意味着朝廷对于章奏所议之事给出定论,但无论此定论是指其为有理、无理乃至加以惩处,章奏议论之公开与此定论之公开也是同步的。正因为如此,“公是非得失于天下”的理念在制度层面获得了必要的保障。 “公……于天下”须有一个前提,即它所覆盖的地域之广泛性。新闻学研究者对这一点多有论述,明代的邸报当覆盖于国家版图的全部,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地方上,它可以下到县一级政府机构。兹举几个边远地区的例子,如王阳明晚年嘉靖六年巡抚两广之时与弟子方献夫信中提到:“昨见邸报,知西樵、兀崖皆有举贤之疏”(王阳明,1992)。而何孟春在巡抚云南之时更即藉邸报之相关消息而参与“大礼之议”,其正德十六年九月初七日所上《乞明典礼疏》有云: 邸报中司礼监传奉圣旨,朕既以兴献王长子入奉大统,王坟在藩府,其立祀并称号,尔礼部便会多官详议了来说,钦此。臣待罪边遐,不获预闻事迹。报中一条,进士屈儒奏内有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妃,圣父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圣母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等语,则恐是礼部会官之所议。屈儒此奏,奉圣旨,该部看了来说,钦此。则是礼部所议,尚未奉俞命也。(何孟春,1983) 何孟春此疏中即体现了一种“议政”的典型方式。此“议政”的发起人是嘉靖,于圣旨中就其父的“立祀并封号”,要求由礼部主持朝臣会议。何孟春所看到的邸报,有屈儒之奏,该本已“奉圣旨,该部看了来说”,故而见于邸报。这“看了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虽有旨,仍处于“议政”的过程之中。何孟春上此奏时,从屈儒的章奏中判断,礼部会议已有了结果,并将结果上奏,然此奏很可能遭遇了“不报”,也即“留中”的命运。故而礼部会议的奏疏并未反映在何孟春此时所见之邸报上。何孟春进而据邸报中屈儒章奏中的“进士屈儒奏内有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妃,圣父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圣母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文字,判断其即为遭“不报”的礼部会议之结论,故而于此疏中就此事进言。观其后之议论可见:“陛下天纵聪明,此礼自应谙悉,今日多官详议,更复奚疑?事上未报,岂非皇叔考之称尚未当乎。”(何孟春,1983)至如礼部廷臣会议之疏既“不报”,屈儒怎么能在奏疏中言及其相关结论,此事倒好理解,礼部主持者本为“会议”,朝臣自可知晓。嘉靖之“不报”,并非要隐秘礼部会议之章奏,只是对礼部会议结果的不认可的一种非直接的表达方式。从何孟春此疏所引邸报及相关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邸报使议政得以公开,同时也可以看到邸报之公开促进了议政的进一步开展。可以说,如无邸报,当时巡抚云南之何孟春是不可能参与到“大礼议”之中的。而何孟春奏疏中所议,全然依据邸报,则邸报之信、实亦可于此表现出来。 两广、云南,距京师之道路不可谓不远,然邸报成为其获知政治信息的重要工具。至于邸报至县,如孙绪(1983)所云:“绪僻居村落,去县四十余里,或有事抵县,岁二三焉,故邸报绝不闻。”此可证县一级当可以读到邸报的。 得阅邸报之群体,自以各级政府官员为主,然邸报本身并无保密制度,禁止政府官员将邸报相关内容外传。如王夫之所担心的邸报可能发生的“泄密”情况,在明人中即有议及,但是他们所质疑的只是邸报刊载的内容本身可能会“泄密”,而不是质疑邸报外传所造成的泄密,以邸报之用意就是公开,政务与议政的公开。当然,因种种原因,一般人获读邸报当有一定的难度,这一点不是非常重要,我们只要知道邸报无禁止政府官员向外传播的制度就可以了。 就议政的意义而言,“邸报”的时效性非常重要。事实上,邸报也确有其时效性,从一些官员通过邸报获知相关之升迁信息可以知道。如时任广东左布政司右参政的张岳(1983)即首先从邸报获知升任的消息的:“又接邸报,伏蒙圣恩,升臣前职,续接吏部咨文,就在广东起程前来到任”。而吏部之正式公文反而后至。而胡世宁(1983)在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途中,亦于邸报中又获知“升臣刑部尚书”的任命。这些都足证邸报传递之及时。 二、万历时“留中”之疏藉邸报得以发布 前面我们提到过,万历一朝,章奏“留中”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则因万历皇帝因立太子问题与朝臣发生龃龉,借“留中”而加以消极抵抗,使国家政治运转几陷入半停滞的状态——只有在既定组织架构内的行政,而无政治。举凡需要“得旨”施行的无法付诸实现,最直观的影响包括对于官员的任命。然而,有确切的资料表明,万历时期“留中”之疏大量出现在邸报中。前引董其昌之疏有云: 天启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圣旨:“董其昌题充纂修官,俟《泰昌实录》稿成,前往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就彼支给,完日回馆供事。该部知道,钦此。”臣闻命自天,感恩无地。于十月前往南京,将河南道所藏邸报,摘其未奉旨者,一一录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写,仅得十分之三。缘事出创见,应天府例无工食。而其书充栋,就结为难。臣仍归里,大集书佣,给以纸笔。虽奉有支给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书沈僎亦录七年,通共若干张,装为三百本。但据原本对录,以备史官取材征实,无所点窜。随蒙钦命,翰林院待诏宋启明、中书朱正色守催。实以私家作事,孑身独力,侵寻岁月,不自知其罪莫逭也。但臣有删繁举要之义,兹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传,言不以人而废。凡关于国本、藩封、人材、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议论精凿,可为后事师者,别为选择,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而其他……略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别表进呈外……(董其昌,1997) 首先需说明的是,董其昌所奉圣旨,是至南京采辑邸报等材料,以备参订,当主要是用以参订《神宗实录》。南京之资料之所以完备,以南京在明代亦为一中央政府。依董其昌之叙述,邸报在南京为河南道御史所藏。而董其昌的主要工作是摘录邸报中之“未奉旨者”,亦即其后所谓“四十八年留中之疏”。依此可以逆推,北京史馆编纂实录所依据之史料,此部分当有很大的缺陷。这一点可以从相关制度上得到证实,史馆之编纂实录,主要的原始资料即经六科抄送的章奏,“留中”者不在其列。 从董其昌的叙述中可见,万历一朝,邸报所发布的“留中”之疏在数量上是触目惊心的。他首先请太常寺之祠祭司督促“僧道”帮助抄写,仅得十分之三,后不得不归里(董其昌为松江华亭人,去南京未远)大量雇佣写手,以完其事。最终所得,“通共若干张,装为三百本”。《明史·艺文志》收录有董其昌之“《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张廷玉等,1974),当即指此而言。此部分是“但据原本对录,以备史官取材征实,无所点窜”。与此同时,董其昌又据此而“删繁举要”,另编辑四十卷书,“别表进呈”。此表亦见于其文集中,题作《进神庙留中奏议彙要表》,表中亦道出此书之史料缘起: 日系月,月系年,即是近时之邸报。顾三馆之挂漏已甚,而旧京之藏副差完。微臣宠藉輶轩,书成渔猎。(董其昌,1997) 并于表中道出其编纂此彙要用意之所在:“盖真主求贤,将留为再世之用。而荩臣陈善,或借诸异代之言。”借助于“异代之言”以“陈善”,并希望天启能“时以万几之暇,略垂乙夜之观”。其事亦载于《明史》本传: 天启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毎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张廷玉等,1974) 然《明史》之叙事较于董其昌自身所言,略有偏差。谓“三百本”之来源乃其“广搜博征”,据董之《报命疏》,史料来源实亦为邸报,而其对象亦如四十卷本,是“未奉旨者”,实即“留中之疏”。换言之,四十卷本与“三百本”所录对象全同,均为邸报之中的“留中之疏”。此事亦载于《明熹宗实录》,可参证《报命疏》所言不虚: (天启四年夏四月己丑)礼部右侍郎董其昌以奉旨前采万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又仿史赞例,各附笔断,共四十卷。且荐南京太常寺卿李维祯史才,上是之。(原本小字注云:《两朝从信录》,礼部侍郎董其昌差竣复命,上曰:“录完邸报并选订奏章多卷,见纂辑勤劳,送史馆采用。李维祯既称宿学史才,即与推用。”)(朱纯臣等,1990)④ 此“上曰”中所称“录完邸报”即指叙事中所说“万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者,可证《报命疏》所言不虚。而“三百本”不仅供史馆参订《神宗实录》,且亦曾以《万历事实纂要》独立成书,惜此书今或已不传于世。然而从董其昌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万历一朝“留中之疏”曾大量在邸报中公之于世。而董其昌自天启二年八月奉旨,至天启四年四月复命,历时一年半多,亦可证其工作量之大。这足以使我们质疑王夫之与何楷所谓“题奏得旨,科抄下部,即发邸报”、“(奏章)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的说法于制度上而言,是否成立——至少在万历一朝,此制度成立与否,是大有疑问的。关于这一点,亦可以由发生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邸报之相关禁令得到进一步证实。小野和子先生亦曾注意到此次关于邸报的禁令,然因误读相关文献,而忽略了相关问题,尝试论之。 如小野先生所言,此次禁令述之于顾宪成为吴亮之《万历疏钞》所作序中。顾宪成于序中论及“国家之患莫大于壅”,有所谓壅在上下之判,而以“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报”为“壅在上”,此上即指“君上”而言,“格而不报”即指“留中”。并进一步追究“壅”之原因云: 说者以为,下不自壅,殆有为之上者然。上不自壅,殆有为之下者然。丁丑纲常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馆,遂迁怒于执简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留中以泯其迹,令言者以他事获罪,不以言获罪。至于迩年,且欲并邸报禁之,其故可知已。(顾宪成,2002) 顾宪成之序作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公元1609年),此中所言“至于迩年,且欲并邸报禁之”实有特指,即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因王元翰之奏,而引发的邸报之相关禁令。时任吏科右给事中的翁宪祥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月所上《时禁疑于防口,人情愈加阨塞,恳乞圣明,亟通章疏,以存清议疏》言及其事: 近该川省用兵一节,阁臣、省臣有疏,颇关中国情形,科臣王元翰触事陈言,请禁发抄。即已奉旨严禁,靡不凛凛矣。但科臣所言,惟在军国之机,而明旨所禁,并及未奉俞旨一切章奏。(翁宪祥,2002) 小野先生以误读顾宪成“且欲并邸报禁之”一语,而以其事为“禁止邸钞”(小野和子,2006)。⑤实则顾宪成所云“且欲并邸报禁之”其意并非是指邸报本身被禁止,而是指禁止有关信息在邸报发布。如追溯其前之“不欲宣付史馆”一样,是“政府”(即内阁)不欲使相关奏疏入于史馆以作将来编纂历史之用,至此则更甚一步,并不欲使之公诸邸报。如上引翁宪祥一疏“发抄”语尚嫌模糊——不必然指邸报的话,同年(公元1607年)十一月南京工科给事中金士衡所上《言路宜通,恳乞亟宽时禁,以昭大公疏》中亦引及相关禁谕,所用语则为“不宜传抄”,然此“传抄”在此实亦特指邸报,观其疏中语可见: 况臣待罪留垣,去京师二千余里,南北迢遥,见闻何自?即使道路偶传,终非的据,未敢陈于至尊之前。惟载之邸报,始足准凭。两月以来,音信断绝,贸贸昏昏,如聋如聩。(金士衡,2002) 综此可知,无论翁疏所云“请禁发抄”,抑或金疏所云“不宜传抄”,其所指均为“邸报”。然细忖此事颇有不可思议者,其所禁止的仍然只是“未奉俞旨一切章奏”传抄于邸报,如果我们前面考证的明代相关制度规定邸报所公布章奏的边界是“奉旨”、“得旨”为实的话,此禁令岂非多此一举?真实情况只能是这样的,即如前引董其昌疏为我们展示的一个事实,万历一朝之“留中”奏疏,大量地以邸报的形式公布出来。金士衡疏中语为也为我们道出了这种情况: 夫自皇上垂拱深宫,外庭迥若万里,臣工罕睹天颜。所恃以通一线之脉者,独此章疏尔。乃迩来章疏批发,十无二三,寝阁十常八九。惟章疏多格,而犹幸托诸抄传以流布,俾人人周知洞晓,无有壅閼。庶几主威振肃,公论森严。举者知劝,刺者知惩。消弭奸萌,磨砺顽钝。献谄导谀者莫能文其丑,披肝沥胆者得以关其忠。所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渺小。奈何吐弃之余,复加否塞。清议沉沦,舆情郁结。岂社稷之福哉?(金士衡,2002) 此处申两层意思:其一,万历垂拱,内外暌隔,唯赖章疏以通一线;其二,更有甚者,章疏“留中”者十之八九,奉旨者十不足一二,唯赖邸报(所谓“传抄”)使“留中”者亦得以流布。⑥其中不乏对万历讥刺之语,如所谓“吐弃之余”,即指万历借“留中”对廷臣之章疏不理不睬如“吐弃”之。然既有邸报布之四方,则所谓“公论森然”者犹在,奈何今日于此亦欲“复加否塞”,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清议沉沦,舆情郁结”,所责不可谓不切。 析论至此,笔者仍不认为王夫之所言“题奏得旨,即发邸报”,所谓“得旨”这一邸报发抄的制度规定在万历或万历以前不曾存在过。只是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得旨”在明朝政治正常的运转下,是章奏的必然命运——换言之,对章奏而言,“得旨”发抄与“不得旨”即发抄,正常情况下在数量上不会有什么区别。而在万历之前,章奏“留中”的事情虽时而发生,但以“留中”作为政治之常态,则唯发生于万历一朝。如此而言,则金士衡疏中所云“惟章疏多格,而犹幸托诸抄传以流布”,二者之间实有一种因果关系。这一点在翁宪祥的奏疏之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惟愿皇上不第责臣下之擅抄以禁其流,而先须速于批发,以清其源。盖自来章疏,鲜有不得旨者。纵诸臣所言,未能悉当圣心,而一下部院,自有公议,无庸停阁。其得旨大难,特近年创见,不可为常也。迩者各衙门事体不能恪守旧规,未易緌数,要由上多变局,因下多权宜。即章疏抄传一节,皇上倘不于本原之地亟疏壅滞,仅仅欲禁其末流,恐非所以开言路也。在今日但当导之使言,不必禁之勿传。以后除事干军机者自应秘密外,其余一应章疏,宜与天下共见共闻。每疏必赐批发,勑该部院酌议,覆请可否,从违悉听圣裁,于以昭示海内。岂不明白正大。所谓擅自抄传者,不禁自无矣。(翁宪祥,2002) 从翁疏中“迩者各衙门事体不能恪守旧规,未易緌数,要由上多变局,因下多权宜”之语,我们可以知道,将“留中”之章疏发布于邸报,是不合于“旧规”的“权宜”之计。如翁所言属实的话,则“得旨”发抄之制度在万历之前应当是确实存在的。之所以有万历时大臣们的权宜之计,正源自于“留中”这一不合于政治常态的“变局”发生。如翁宪祥追究于“留中”之源头,同为此一事上疏,兵科给事中吕邦耀于疏中则不再追究于此次发生的禁令,而唯独追究“留中”本身之不合理性。 若夫言路脉络,须凭章奏敷陈。章奏纷披,咸待圣明批发。迩因明旨慎重,章奏未尽允行。事体之不当停留者,而亦概停留。既起丛脞之釁,人情之共疑。寝阁者而果然寝阁,能无猜忖之嫌?莫言密勿机关,难掩舆人指视。众情惶惑,众议纷呶。聚讼盈庭,莫知底止。善哉乎,先臣陆贽之言也曰:“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反复斯言,可为详尽。故机务之不密也,在漏之于外。政令之不行也,在留之于中。皇上之责臣下者,在慎于发抄。臣下之望皇上者,在亟于发票。何也?发票则与天下共见之,亦与天下共酌之。可以知某事之修明,可以知某事之废弛。可以知某言之为正,可以知某言之为邪。可以使予不得借之以市恩,可以使夺不得因之以卖重。可以用贤不至如转石,可以去佞不至如拔山。拟旨责之辅臣,题覆责之部院,纠正责之台谏,奉行责之有司。荡荡平平,堂堂正正。恭己而治,惟德其刑。则南面可以无为,人言何须预杜。声色可以不大,议论岂至烦多。如是而不奏綦隆之理者,未之有也。(吕邦耀,2002) 此八股文体所论有其委婉处,然关键之处并不含糊躲闪。谓“留中”不仅仅徒致众情惶惑、众议纷呶,而实不能如其所希冀的,遮蔽什么,终究只能导致政令之不行。“发票”——即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得旨发抄”之邸报制度,亦如此次“禁令”再申此意——只要对奏疏按政治之常态“发票”,使之得以通过邸报公诸天下,则其间是非得失(疏中所云修明与废弛、正与邪等等,即此意),不惟可与“天下共见之”,且“亦与天下共酌之”。至此,我们不得不强调一个常识,所谓“票”,即指“票拟”、“票旨”,在明代内阁制度化之后,其职掌在于内阁。吕邦耀疏中“拟旨责之辅臣,题覆责之部院,纠正责之台谏,奉行责之有司”所言,则为儒家士大夫逐渐扭转明初之君主专权体制,而为政治走向理性化的治理所规划之建制。这与当崇祯之末世,刘宗周(2007)所言“以票拟归阁臣,以庶政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何其相似。此时的君主就是一个“恭己而治,惟德其刑(刑谓法、则),则南面可以无为”——所谓“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的形象。只是吕邦耀此处所言克就于议政而言,更有其针对性。首先是臣民无人不可以上疏议政,辅臣拟旨,就所议之政付相关部院议处、议行,科道官员行使监察之权,具体办事机构(仍在部院)依议定之事而奉行。同时,由于邸报的存在,这一切完全是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其间是非得失,则最终取决于公论。吕邦耀与金士衡所论,所针对者虽有所不同,然无不以邸报之公开(无论是“得旨”而后公开,抑或“留中”亦不得不公开)为付之于“公论”之保证。只是于吕而言,此公开乃议政之进一步深化,所谓“亦与天下共酌之”,使政治在一种公开议政的理性中不断趋于合理建制,终而达成“荡荡平平,堂堂正正”的“王道政治”。 至于章疏留中而唯藉邸报流布四方的意义则与此略有不同,金士衡所言“庶几主威振肃,公论森严。举者知劝,刺者知惩。消弭奸萌,磨砺顽钝。献谄导谀者莫能文其丑,披肝沥胆者得以关其忠。所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渺小”数语,除“主威振肃”⑦略有应景的意味而外,其他数语则有其确乎不可易者。翁宪祥(2002)疏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况诸臣不避烦聒,固望采纳施行。即使精诚未感,竟从停阁,而尚存一种议论于天地之间,则或于时弊,默有所挽回,人心稍有所警惕。”这有似于今人之所谓舆论监督,只是这舆论的发起者仍然是政府官员,在常规的政治运转中,这些本应该在政治制度框架内行使议政、政治监察权的官员们,转而求之于“天下”、求之于“公论”以监督政治之运转。这就是金士衡所谓的“清议”、“舆情”,或者如翁宪祥所言是“庙堂之上”的“清议”,付之“空言”,以“维世则”。儒家士大夫是相信有所谓“公论”的,如东林钱一本(2002)之为《万历疏钞》所作序云: 盛王之世,善善恶恶,无一不公诸天下,而与天下共善之,共恶之。 顾宪成(2002)于序中亦如此说: 至于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盖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愿以是为台省献求所以信于天下者。 顾宪成“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此语,其意当指:言官乃为天下是非公论之代言者(“言官操天下之是非”),言官之代言其是非如何,则又取决于天下之公是公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而作为议政公开的邸报之存在,使公是公非之评判成为可能。这正是吴亮编纂《万历疏钞》的一个重要理由,如小野和子(2006)所云之“开通言路”。就东林而言,明白了“邸报”在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明代邸报之议政公开实促成了以东林书院为核心的晚明士人之在野议政的可能性。 三、关于邸报制度的几个关键性争议问题 以上我们对明代历史上邸报之存在状态给出一种描述,然因相关史料之阙如或略显模糊,关于邸报制度的一些关键性的、有争议的问题仍有待于探讨,尝试论之。 首先,最关键的问题是邸报之职掌何在?在前面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邸报与科抄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可不可以说邸报的职掌在六科呢?似不能如此说。这就像六科发抄相关章奏至史馆供编纂,然编纂之职掌实在史馆与内阁,而不在六科一样。如新闻学研究者所争议的,与邸报之职掌关系最大的则为“报房”,据笔者所见,亦有称之为“抄报所”⑧的,所指当相同。关于“报房”,《春明梦余录》所载崇祯元年上谕即有此称谓:“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孙承泽,1992)。 然而笔者并不认为邸报之职掌即在报房,职掌云者,一方面是对所承担的事务有处置权,同时,为此权限而承担相关责任。而报房则无此权力亦无此责任,它只是一个奉命办事的机构。如与其对接的政府机构是六科的话,它只是负责把六科所提供的奉旨章奏发布出去,而对其内容并无增删编纂的权力。此“增删编纂”实则是一个很大的权力,如其为有的话,则亦应如科抄所指向的史馆之编纂,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来执行,就像史料编纂其权力在翰林院之史馆,而内阁及方面官员亦对其有监督的责任。⑨对于邸报之发布章奏,科抄的边界即是邸报发布的边界,因此,邸报之发布只要有“报房”这一办事机构就可以了,其办事人员也只是吏,而非政府官员,这也应该是《明会典》不记录邸报、报房之相关信息的一个原因吧。 那么,“报房”这样一个办事机构,其受中央政府什么部门约束呢,是六科吗?笔者并不以为如此,如崇祯元年之上谕,《春明梦余录》是载在“通政司”条下,用以说明通政司相关职责的,而崇祯之上谕亦可能就是针对通政司发布的。从这一表面现象上看,“报房”当受通政司⑩的约束,或与其对接的政府机构为通政司。实际情况也可能确实如此。前面我们看到,万历一朝大量的“留中”奏疏通过邸报而公诸天下,其数量之大,显然不能视之为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当亦通过一正常的制度渠道而得以实现。此渠道不可能是六科,而只能是通政司。通政司是接受奏章的机构,而通政司在接受章奏的同时,亦录有“副本”。(11)如赵志皋即于万历二十四年曾借查验通政司副本,以证实当时借邸报流传的刘世延论赵志皋等之奏疏为伪: 近日又有刘世延一本,论臣及石星与李桢。玩其词,颇不类世延语。因查通政司,并无有副本。乃知憸邪小辈,假此以诬诋善类,其风岂可倡哉。(赵志皋,1983) 正是因为有通政司之副本,为万历中大量“留中”奏疏借邸报发布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而万历三十五年重申邸报之相关禁令的命运,虽未见明确记载,然很可能最终不了了之。延至崇祯元年,邸报发布章奏逸出“奉旨”边界之事时常发生,故有崇祯元年之上谕,再申邸报发布章奏的边界,必须经过“御览批红”(仍是“奉旨”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至于邸报之传播,据顾炎武所言,在崇祯十一年活版印刷应用于邸报之前,一直是通过抄写来传播的。(12)而抄写方式,如新闻学研究者指出的,是地方官员雇佣抄写手至北京之报房抄写。邸报不用雕版,主要原因当为其日常发布的量很大,雕版之成本过高,不似活字,可反复排版印刷。至于地方至中央的抄写方式,则亦有相关费用支出问题。如嘉靖早年《明伦大典》之编纂而发布天下,亦非印好书以后发给中央及地方各机构,而需各机构自备纸墨印刷装订。由此推论,即便活版印刷应用于邸报之后,亦当为地方机构自备纸墨至报房印刷。因为明代之邸报多为抄写,如论者所言,其间发生的与原始资料不合的情况,可以说均由抄写中的人为因素造成。故而当顾炎武得知清中秘所收邸报“乃出涿州之献”的时候,会质疑其“岂无意为增损者乎”(顾炎武,1959),此“增损”即出自抄写手之所为。而前引蒋德璟(1983)所论邸报之作为官修实录之原始资料的缺陷时说: 即欲有所删润,以诸曹掌故与邸报参补而已。又一二载笔,视为烂朝报,不经心,其高者胸臆为政,间规时局所向,行其高下…… 此处“载笔”亦当指邸报之抄写手而言,然这种由抄写手引发的错讹亦不可过于放大,无论如何,从明代政府官员之奏章通过邸报信息而建言之相关现象看,所谓“邸报之抄传有定”(左懋第,1992),当非虚言。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断言的是,明代邸报之发布奏章,当与之对接的中央政府机构为六科时,可供发布的奏章即“科抄”之全部。而当与之对接者为通政司时,可供发布的奏章也当为奏章之全部。至于邸报之编纂,并无相关政府机构执行。或者换言之,政府机构只是提供可以公布的奏章等原始资料供报房公之于众。而“损益”云者,均为抄写中的人为因素造成的,而并非出于制度上的规定。而且经常发生的事情当为“损”,如新闻学研究者指出的,即抄写手根据地方政府官员的需要,于抄写中或有所择。当然,直接的原因还是可供邸报之原始资料量大,而其传播亦有其时效,大多时候很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抄写之多与少,也部分取决于地方官员之财力,或者说地方财政愿意为其支出多少。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无所谓邸报之完本存在,如顾炎武质疑“涿州之献”时,提出可以“访问士大夫家,有当时旧钞,以俸薪别购一部,择其大关目处略一对勘”,在顾炎武眼中,藏于“士大夫家”(当指中央政府官员)者,或可近于完备。而董其昌之所以获旨往南京采辑邸报以修纂实录,当亦以南京这一中央政府所藏邸报,可称完备。(13)这些倒从另一方面暗示出,报房所提供抄录的邸报,不仅仅是一些原始资料,当有其可供抄录的邸报的完本。而此完本如有所谓编纂的话,当只是按既定的格式对原始资料的汇总式抄写。 而邸报在中央政府并未作为档案留存下来(南京中央政府之留存或可弥补此一缺陷),这一点尚容易解释,以邸报之原始资料其档案本有相关部门送交史馆等处保存。但是,即以奏章而论,当史馆乃至内阁对此档案之留存行使“编纂”的权力的时候,它已失去作为档案的原始性的基本特征,故而作为后来官修实录之依据,其缺陷就明显显现出来。此时,作为原始资料汇总之邸报,其优势即显现出来,而逐渐成为官修实录的重要依据。 以上是笔者尝试勾勒的明代邸报相关制度的大致轮廓。然令笔者困惑的是,邸报在明代究竟何时出现的?大行于宋代的邸报,在元代几杳无踪迹可寻,并无相关资料表明,邸报在明太祖之时即已得以恢复。那么,邸报在明代是何时出现的,或者是怎样出现的,就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了。笔者于此亦无所见,尝试以《四库全书》检索之,则《四库》所收明人文集,有年月可考的最早提到邸报的或出于何乔新之《椒邱文集》,其《送方伯李公赴江西序》云:“成化十有二年冬十月,诏以河南参政隆庆李公文盛为江西布政使,邸报至汳……”(1983)而至弘治年间,邸报于明人文集中即很常见了。然明代邸报究竟起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考究。邸报在清朝进一步延续下来,从纸面的制度上而言,清代邸报之相关规定与明代差别不大,然因明清两朝政治运作上的巨大差异,邸报所公布的信息二者之间实有极大的差别,此则非本文论域所关了。 至此,我们对于明代邸报制度的相关情形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邸报之所以能够在明代政治制度中重建,并于言路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基于儒家士大夫对于政治治理的理性化诉求,以及诉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万世”的政治信念。在这一点上,古典与现代,中与西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言路”作为中国古典政治的核心议题,它所对应的政治制度有担负政治监察责任的言官(明为御史和给事中),本文所论邸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奏疏,都可视为“言路”的制度建置。有论者将言官与西方现代政治的议员、议会相比较,这并非一种简单的比附。在履行政治监察责任,审议政治决策、政治运作中的是是非非、合理性等问题上,二者并无实质的不同。言责既为言官的专门职守,同时,所有政府官员在履行职守的同时,亦以言责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官守”与“言责”,作为从政者最基本的两项政治责任。邸报的出现,无疑为士大夫履行“言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 一方面,国家的政治制度、政令、政治决策,乃至其议定过程,假邸报以广泛传布。无论在朝官员、散布各地的地方官员、乡居赋闲的士大夫阶层,乃至一切对此表示关切者,均可以及时获知相关信息。在此意义上说,它是明代政务公开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及时、广泛传布的邸报,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如前所论之舆情。士大夫群体凭借以邸报发布的章奏,营造舆论氛围,影响政治决策。为人们所熟知的淮抚李三才事件中,东林人士吴亮将顾宪成相关私人信件通过邸报公之于众,说明了士大夫们对于邸报这一功能的清楚认识。 在此,我们不妨再次回应一下视邸报为报纸前身的今日新闻研究者的论点,尽管在本文中笔者一再反对视邸报为报纸,但我们并不否认邸报与报纸一样,同样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只是今日新闻的舆论监督隶于社会层面,邸报则是政治制度本身的衍生物。当明代国家政治处于常态化运转之时,它可以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之内,有效发挥其功能。当常态化政治为皇权及其附庸打破时,士大夫们亦打破常规,诉诸舆论和清议,以寻求可能的政治突破口。这一切,都与古典政治的主体,儒家士大夫这一群体密切相关,此不赘论。 最后,须澄清的一点是,本文对于邸报的揭示,并不认为邸报代表了明代政治制度价值取向的全部。比如,与邸报之公开性截然相对的,则有所谓的“密疏”。自明之祖制流衍下来的厂卫政治,虽不似流俗所见如斯大行其道,但的确由此开启了秘密政治这一极大恶端。对于一般史论所言如此诸般的明代皇权“专制”特色,笔者并不全然否认。但是,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生存夹缝之中,儒家士大夫们仍然缔构了诸如邸报这样的政治制度,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在政治公共性问题上,儒家鲜明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我们今天重构政治公共性空间,张大理性政治之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①主要即指因“邸报”之传布天下,而使“用兵大事”,“喧传中外,俾夷狄盗贼得以早测进止乎”(王夫之,1996)。这自然源自明亡这一痛彻的历史经验。王夫之因此希望对于“邸报”传布的内容加以限制,然也仅拘于两端:其一,他认为明代已有的对于“缇骑逮问”等刑拘之消息发布的限制;其二,他所认为明代所无的“用兵大事”消息发布的限制。仅限于此而已。 ②此概而言之,实则诏旨之中亦有发起议政者。如明世宗为其本生父之“立祀并称号”等事,令“礼部便会多官详议了来说”。 ③明代所有章奏均须经由通政司接收并备案,再行上达。 ④四十卷本《神庙留中奏疏彙要》今存于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470影印有该书。该书卷首收录有董其昌《报命疏》,疏后附有“四月初六日奉圣旨:这录完邸报并选订章奏多卷,具见纂辑勤劳,著送史馆采用。李维祯既称宿学史才,著即与推用,该部知道”。准此可知,《两朝从信录》所载“上曰”,实为董《报命疏》所奉之旨。两者相参,更可证其可信性。 ⑤小野和子先生亦于书中指出我们征引的翁宪祥、吕邦耀、金士衡三疏为针对此次禁令而发者,然可能是受误解顾宪成“且欲并邸报禁之”先入之见的影响,惟引金士衡疏中论“一切章奏”一段话来理解此次禁令,以为是禁止一切章奏传诸邸报。 ⑥这种情境在万历一朝是怎样发生的,已不可考。至如“留中”之疏借邸报传布之事发生的时间则较早,如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赵志皋(1983)于《乞振朝纲疏》所言:“夫报房即古之置邮,传命令以达之远近者也,非奉命者不敢抄。今则朝奉疏而夕发抄,不待命下而已传之四方矣。”“朝奉疏而夕发抄”是他为我们描述的邸报当时发布的情形。笔者以为其事发生的时间更早,而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之重新申明“奉旨”之限制,在更早的时候似也曾发生过。如时任吏科给事中的史孟麟(2002)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职居言责,指摘非人,乞赐罢斥,以解党锢,以杜谗谄疏》中所言:“三四年来……台谏忤时,命曰好名,显者杖谪,隐者外转矣。犹惧不足以阻挠之也,于是有未奉明旨,不许发抄之令。而至今台谏,言者如故。”颇疑此处“未奉明旨,不许发抄”仍指“邸报”而言。就明代制度而言,发抄不外乎三种情况,发抄到部,发抄到史馆以及发抄到邸报,前两种均无制度上的漏洞,使发抄可以逸出“奉旨”的边界,故无需申此禁令。小野和子先生则理解其为“史孟麟上疏中所说的不许发抄之令,是指当送六部抄写的上疏被留中。在六科抄写,就有可能以邸报等形式流布,情报可公开”(2006)。所解略嫌屈曲,实则因为没有能够注意到万历时大量“留中”的奏疏被公布于邸报的事实,这也可能是小野先生误解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禁令的一个原因。 ⑦如有实意,当指防止内阁之擅权。 ⑧瞿九思(2002)述其撰《万历武功录》收集资料时,尝“走抄报所,稽其日全报章”。 ⑨新闻学研究者多有引述《大明会典》中的“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本章,逐一抄写书册,五日一送内阁,以备编纂”(申时行,等,2007)以说明邸报的编纂,此则出于文献的误读,“以备编纂”非“编纂邸报”,乃编纂备后来修史之史料。参之《大明内典》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所载:“其诸司章奏,另选讲读并史官六员,专管编纂。……其各曹章奏,六科奉旨发抄到部,即全录送阁,转发编纂。月终,将记注编纂等稿送内阁,公同各官,投柜封锁。年终开入大柜,藏之东阁左右。”(申时行,等,2007)二者所言乃一事,此事出于张居正任首辅时万历三年所议定的制度,可参见张居正(1984)之《议处史职疏》。《大明会典》所载,几全节录自张居正该疏,以其疏已奉圣旨,“都依拟行”,即已成为制度。此不赘论。 ⑩明之初制,曾以六科隶于通政司,而后来二者之间实已无大的隶属关系。李东阳之《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即此)犹记六科于通政司下(实已无严格的隶属关系),万历重修《明会典》时,已将二者分别记录。然二者之间亦非全然脱离关系,如六科官员之俸禄在前书所载尚为“于通政司带支”,后书所载则已为“自行关支”。而“凡各科行移各衙门,俱经通政司转行”这一点前后两部会典并无差别。 (11)通政司录章奏“副本”非明朝初制,此制度自何时开始,笔者未尝考见,然万历时无疑是有此制度的。 (12)“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写本。”(顾炎武,1959) (13)陈懿典(1997)《两朝从信录序》云:“朝家故实,一凭邸抄,而省直流传,详略已异。”“省直”指地方和中央(“直”谓直隶),而“详略已异”,当指直隶详,各省略。按,《两朝从信录》乃明末沈国元所编泰昌、天启两朝编年史,其资料所本,亦以邸报为主。顾炎武曾提及该书:“自庚辰至戊辰邸报皆曾寓目,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当以邸报为主……割补《两朝从信录》尚在吾弟处,看完仍付来,此不过邸报之二三也。”(顾炎武,1959)所云“庚申至戊辰”即为泰昌、天启所值之年代,据此,则顾炎武曾据其所见邸报,对该书进行“割补”,惜所“割补”者已不可见。而《两朝从信录》所载,在顾炎武看来,不过其曾寓目的泰昌、天启邸报之十之二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