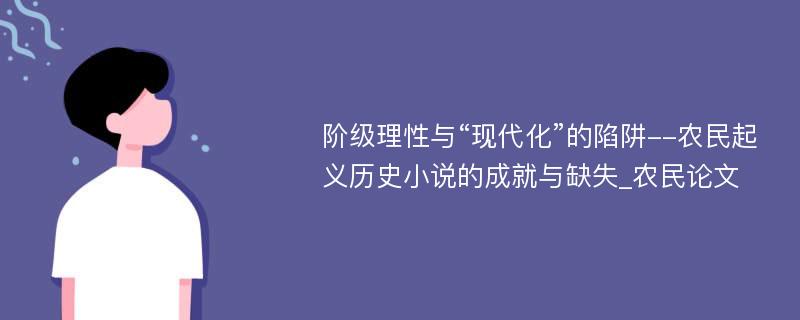
阶级理性与“现代化”陷阱——农民起义历史小说的成就与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起义论文,缺失论文,阶级论文,历史小说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度,农民起义既然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发展,也就必然成为历史叙述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封建正统史观的局限,农民起义在传统历史叙述中往往被歪曲和丑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作为其基本内核之一的阶级斗争学说成为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和叙述历史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农民起义也开始得到正面描述和积极评价。历史观念及其变化具有“散播”功能,会辐射并渗透到其他精神领域。1930年代以后,农民起义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重要题材,并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初。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阶级斗争学说也是历史小说家们基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决定并影响了这一题材历史小说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到叙事风格等方面的基本貌态。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阶级斗争历史哲学风光不再,农民起义历史小说也逐渐淡出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
阶级斗争史观是一种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历史观。当现代历史小说家运用此种历史观观照和表现中国历史时,他们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正确解答了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巨大历史作用的问题,表现了人民群众作用于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式及形态,不仅为现代历史小说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和表现空间,也使人们从阶级斗争的理性化角度认识本民族历史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当充满复杂性和偶然性的农民起义被理性化地阐释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时,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也就在所难免。同时,历史叙述本身应当充满感性,过分的理性化态度,将会使历史叙述变得枯燥乏味。而当作家过分倚重阶级理性意识的认识作用时,将会使历史小说落入“现代化”陷阱。这其中所涉及的阶级理性与历史小说自身艺术规律之间的张力,是研究中国农民起义历史小说的一大关键。因此,辨析和厘清二者各自应当发挥的作用,总结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使这一重大题材重新出现在作家笔下并焕发生机,在为当代读者提供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的精神资源的同时,使当前历史小说摆脱以帝王将相为唯一表现对象的困境,形成多元发展的良好局面和势头,应该成为作家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家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在阶级矛盾激化的特殊语境中发现古代农民起义这一重要题材的。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形成了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找不到摆脱社会困境和文化困境的力量,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革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使他们没有可能直接揭露现实黑暗,也没有可能直接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革命。于是,古代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成了他们表达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憎恶和对农民武装革命期望的象征物和代用品。他们不仅在小说中极力歌颂古代农民英雄反抗专制压迫的斗争精神,还曲折隐晦地借历史以号召现实中那些在残酷的专制压迫下走投无路的人起来反抗。
1929年,孟超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引擎》创刊号上的《陈涉吴广》,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此后,茅盾的《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宋云彬的《夥涉为王》,陆费堭的《陈胜王》,廖沫沙的《陈胜起义》,靳以的《禁军教头王进》,张天翼的《梦》,刘圣旦的《发掘》等相继出现。
在众多的历史小说家中,真正代表着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历史小说最高水平的是茅盾。作为一个从192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作家,茅盾在历史小说中纯熟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和描绘历史人物与事件,不仅将作品中的人物分成对立的两个阶级,二者的斗争构成了作品的情节主线,而且着意强调人物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属性,以此凸现农民起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在《豹子头林冲》中,茅盾创造性地把林冲改写成了农民的儿子。这一阶级属性使他笔下的林冲已不再是《水浒传》中那个受陷害而被“逼上梁山”的武官,而是既具有农民的质朴与自发反抗性,又体现着农民式的狭隘、忍耐、信命等局限性的复杂形象。于是,不仅林冲这个家喻户晓的八十万禁军教头被茅盾的阶级理性意识重新塑造成了广大被压迫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成了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象征,而且,火并王伦的情节也被改造成了对立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林冲的行为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有着阶级根源的正义行动:“在豹子头林冲的记忆中,‘秀才’这一类人始终是农民的对头,他姓林的一家门从‘秀才’身上吃过多少亏!他豹子头自己却又落到这个做了强盗的秀才的手里!做了强盗的秀才也还是要不得的狗贼!”林冲的仇恨与反抗一方面源自农民身上的深重压迫,更主要的是他头脑中阶级意识的觉醒。阶级意识的觉醒促使他认清了矛盾的根源,并意识到身为被压迫者只有反抗才能生存。此外,茅盾还将梁山泊重新命名为“被压迫者的‘圣地’”。这些显然是1930年代阶级论思潮与农民武装革命实践在小说中的投影。作者借助对古典小说中英雄人物的阶级分析和改写,意在指明农民阶级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掘墓人。
在《大泽乡》中,作者把起义的最终原因归结于九百戍卒与两位军官之间的阶级矛盾。前者是被征服的六国闾左贫民,他们没有土地,被秦人所奴役;而后者则是拥有土地的秦国富农,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不同的阶级性质所导致。农民有着自觉的阶级意识,也有着对土地的当然要求:“什么‘陈胜王’,他们不关心;如果照例得有一个‘王’,那么这‘王’一定不应当是从前那样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自己有地自己耕。”而当九百戍卒鼓噪欲反时,两个军官“血液中的阶级性突然发酵了,他们不能束手困在这荒岛样的小丘上,让奴隶们复仇的洪水来将他们淹死”。于是大泽乡起义就成为农民和地主因为土地占有矛盾而引发的殊死搏斗,其结果是统治阶级的覆灭和土地的重新分配:“始皇帝死而地分!”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家的基本思路是:运用阶级斗争观点从正面评价和表现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众的反抗行动,通过对人物的阶级划分,突出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进而揭示出农民起义的根源和必然性。然而,阶级对立这一来自现实政治斗争的思想认识是存在于文本之前的预设主题,作家们在创作时,只是采用了一种论证式思路,即用历史事件作为论据,论证现实斗争中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样,一方面使得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被拉近了距离,互相呼应,历史小说被赋予充沛的现实战斗力,承担起了现实政治斗争的任务;但另一方面,阶级理性的过分膨胀也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
二
从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到新时期之初,以长篇为主的农民起义历史小说极度繁荣。除《李自成》外,还有冯骥才、李定兴的《义和拳》和《神灯》,刘亚洲的《陈胜》,凌力的《星星草》,鲍昌的《庚子风云》,杨书案的《九月菊》,顾汶光、顾朴光的《天国恨》,顾汶光的《大渡河》,蒋和森的《风萧萧》和《黄梅雨》,郭灿东的《黄巢》,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等,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历史都得到了文学上的反映。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十年“文革”甚至“文革”之前,带有那个特殊时代的鲜明印记。
1949年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被明确规定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阶级斗争学说自然成为作家认识和解释历史、反映和表现历史的唯一被允许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武器;同时,在革命领袖“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P588)经典论断的规范下,不仅使农民起义历史小说家在历史认识和阐释上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将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对立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内在逻辑,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阐释历史发展规律的主题思想,也使他们在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上落入了“现代化”陷阱。
所谓历史小说的“现代化”,是指“那种不顾历史固有的客观性和可能性,纯粹按照今天现代人才有的思维习惯、语言行为方式来铸造古人,使其失去了应有的历史质感、实感的极端做法”[2](P273)。具体来说,就是作家运用一套现实阶级斗争的而非历史真实的话语塑造形象,将人物过分理想化甚至拔高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精神境界的程度,使人物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特性而与现代革命战争中的英雄甚至领袖影像重叠,成为高大完美的抽象的寓言品和简单的时代精神号筒,也使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塑写成为对革命历史的平面化、仪式化、模仿化叙述[3]。正如洪子诚在评价《李自成》时所说:“李自成在作品中,以有高度智慧、才干和崇高品德的起义军英雄和领袖的形象出现,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而且是有着政治家和军事家才干的领袖。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以及高夫人等)和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为参照。李自成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及他的天命观、流寇思想等弱点;起义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考察明末那支起义军的思想基点。”[4](P122)
农民起义历史小说在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现代化”倾向有着多重原因。首先是“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当把文艺仅仅看成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要求文艺无条件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当现行的政治气候使作家无法实现真正的创作自由时,就有可能诱使作家误入“现代化”歧途。姚雪垠强调创作《李自成》的目的是:“我想,当前正在深入批判《水浒传》所宣扬的投降路线,《李自成》这部书倘若能及早印行,更能发挥其战斗作用。”[5]这就使作家冒昧而又勇敢地将当时路线斗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直接移植到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身上,使历史小说失去了应有的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性而成为路线斗争的载体和工具。在凌力的《星星草》中,罗晚妹将捻子的先祖追溯到孔子时代的范丹,于是,捻军就不再仅仅是农民起义军,还是批判儒家思想的先驱者。罗晚妹说:“咱们捻子是范丹的后人。那些当官的、豪绅财主们,都是孔丘的子孙,没见他们都供着老祖宗,学得跟他们老祖宗一样狠毒吗?”作者将范丹和孔丘的故事当作捻军起义的历史渊源,显然受到了当时“评法批儒”思潮的影响,而英雄人物也借此获得了来自历史深处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援。
其次,由于这一批作家大多受到政治迫害,促使他们往往将因现实感慨而萌发的理想冲动和政治激情注入小说,通过历史人物来宣泄内心的不满与愤激,进而突破历史真实界限,对英雄人物表现出过分的由衷偏爱。在谈到《星星草》的创作缘起时,凌力说:“在十年内乱中,为了做点事情写成了它。当初没有公诸于世的奢望,不过是为了寄托我对现实、对历史、对社会发展的一点感想和感情而已。”[6](P693)她还说:“‘四人帮’横行时,不允许我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说出我心中的一切,我只好借助于捻军将士的英灵,借助于捻军苦斗的历史,来歌颂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和仍在人间坚持战斗的人民英雄们。”[7]在谈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时,她说:“究其原因,主观上,是因为我把农民英雄理想化,试图把所有起义领袖的美好品质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歌颂他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而不忍心去写他们的错误和缺陷。客观上,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文艺创作上‘高、大、全’的唯心主义创作观念和方法,对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突不破束缚和框框,表现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8](P5)姚雪垠在接受聂华苓和安格尔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在李自成身上反映了自己在1957年受到迫害时的命运、思想与感情[9](P79)。
三
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历史小说在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现代化”倾向使他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评价陷入了“道德至上主义”窠臼,将封建社会具体而又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简单化约成了善恶分明、黑白两别的二元对立格局,从而使道德标准变成了判定历史人物是否具有先进性,是否对社会历史发挥进步作用的试金石,其前提和基础是阶级分析法。英雄或正面人物是农民阶级的代表,是农民起义军及其领袖,而魔鬼或反面人物则是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即封建君主、官吏及其军队。而在道德上也形成了善恶分明的对立模式,一切善良的、高尚的品质和行为都属于农民军一方,一切不道德的、卑鄙的品质和行为都属于农民军对立的一方,其他如勇敢无畏、英勇善战、远见卓识、大公无私等道德品质也都归之于他们所认定的进步的历史主体。“政治变成了道德,道德变成了政治”[10](P1013)。在这一政治——道德模式运作下,复杂多变的历史变得面目清晰,但离真实却愈来愈远。
为了在英雄人物身上涂抹道德光环,作家们极力剥离和祛除人物身上普遍的人性内容。同时,强调因阶级属性而来的道德崇高和人性洁净。《李自成》中关于红娘子这一人物的设置和塑造就反映了这一倾向。姚雪垠认为野史中红娘子将李信掳去“强委身焉”的流行说法是封建文人的诬蔑捏造,并认为:“如果我按照这一说法写,就要将红娘子写成了一只‘破鞋’,江湖上的女流氓。我必须从相反的角度着笔写她出身贫苦农家,不得已幼年学艺,弓马娴熟,武艺出群,虽然漂泊江湖,却不同于一班人心目中的乐户绳妓。她立身清白,性格坚毅豪爽,正气凛然。我努力将她塑造成在封建社会中饱受压迫和侮辱的妇女代表,真正够得上被称为农民革命军的‘巾帼英雄’。倘若她是‘破鞋’,就不会在革命群众中获得威望和领导权威。尽管她是一个野史中的‘莫须有’人物,但是我既然要写古代的妇女起义,就不应该跟在封建文人的后边胡说八道,而要以严肃的态度处理她同李信的关系,通过她的故事写出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11](P26)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虽然使红娘子在道德上完美无缺,但却使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真实可信性和文学感染力。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凌力的《星星草》中。张宗禹与罗晚妹、赖文光与卜玉英、罗立海与青姑等人在共同理想的鼓舞下产生、在艰苦战斗中建立、在生死关头经受住了考验的纯洁坚贞爱情,是他们完美人格和操守的表征,而贪图肉欲享乐的李允、刘守诚、唐日营等,只能成为无耻堕落的投降变节者。这种从历史中抽象出道德训诫的实用理性做法,虽然使“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由于把“自己的精神,算作那时代的精神”的非历史主义态度,又使得这一目的难以实现。黑格尔说:“人们惯于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特别介绍给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12](P40)因此,对于历史小说来说,不仅从历史中引申出的道德训诫在现实中未必发生作用,反而会付出非历史主义的沉重代价。《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历史小说尽管费尽心力和笔墨,渲染并强化英雄人物身上的道德光环,但由于超越了历史真实界限,道德训诫的意图注定要落空,同时也极大损害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艺术性而为读者所诟病。
农民起义历史小说对英雄人物的理想化、“现代化”处理也往往使作家陷入相当尴尬的悖论之中:既然农民起义军从领袖到普通士兵都思想正确、立场坚定、道德高尚、英勇善战,既然农民起义被认定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既然作为农民军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朽不堪,正在做着垂死挣扎,那么,为什么农民起义却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作家充满理性乐观的历史信仰和小说弥漫着英雄主义气息的叙述风格与农民起义必然失败的历史结局之间有着无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对此,作家们既没有从农民起义领导人的历史与思想局限性出发进行总结,也没有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和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思想观念的落后守旧、狭隘封闭及其所承受的历史因袭重负层面进行反思,而更多地将原因归结为战略失误。姚雪垠说:“一个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品质好,不能保证他不失败。运动的成败,有它内在的规律。规律是各种复杂因素形成的,个人的品质只是因素之一。成功有成功的规律,失败有失败的规律,个人的品质起一定作用,但不起最后作用。”[9](P139)他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缺乏财政基础、北伐战略错误、敌我力量悬殊等[9](P98-106)。而在凌力的《星星草》中,这一原因仅仅被归结为“就粮”问题,她说:“我觉得老老实实地围绕‘就粮’来写他们的失败,这样的艺术构思,才符合捻军的历史真实。”[13]很显然,从这样一些外在因素中很难总结出中国农民起义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作家们对英雄人物过分偏爱的创作心理制约和阻碍着他们对历史运动及其规律更为深入的思考,而以歌颂为主的“英雄时代”的历史叙事规范和“两结合”的创作潮流也不允许他们表现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悲剧性。于是,为了化解上述矛盾,作家们只能将重大历史失败改造或置换为等待胜利必然结局的暂时性序幕,以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彩笔为作品留下一个“光明叙述”的尾巴,暗示每次农民起义都为后来者播下了革命火种,哪怕以失败而告终的农民起义,也能为后代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比如,姚雪垠在完成对李自成起义的悲剧性描写之后,暗示150多年之后白莲教起义将爆发,而这一革命火种是李自成起义军中的重要人物红娘子暗暗播下的。革命失败了,革命的火种还在。起义、失败、再起义,直至胜利,农民起义者就这样屡仆屡起、百折不挠,以鲜血和生命换取了历史的进步。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历史小说由于理性化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念的局限,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环境影响,由于作家们主观上对“左”倾文艺思潮的迎合和对英雄人物的偏爱,使他们笔下的农民起义英雄形象出现了明显的“现代化”倾向。一方面造成了历史人物形象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大打折扣,也使他们无法正视农民起义终归失败的历史事实而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强大的历史感,只能成为政治挟持和时代局限下权力话语的牺牲品与合作者,使历史叙述堕落为功利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教育工具。
总之,农民起义历史小说不仅应该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为历史小说的丰富繁荣开辟表现领域和空间,还应该成为考量国人是否具备反思民族文化传统与历史发展逻辑的理性精神的重要参照;不仅应该为民族精神的健全和思辨能力的增强提供资源,也应该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指明可能的途径与思路。然而,历史小说又有着自身特殊的艺术规律,理性认识和道德训诫并不是它的全部功能,甚至不是主要功能。历史小说家在努力达致上述目的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尊重历史叙述和文学表现的感性特征,使二者尽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而不应该使理性意识过分膨胀,以至完全挤占了感性因素和艺术表现的应有空间。但遗憾的是,从1930年代一直到新时期之初,由于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叙述农民起义唯一的历史观,由于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由于作家没有意识到或处理好阶级理性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农民起义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了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载体和传声筒,也因落入了“现代化”陷阱而失去了真实性和艺术品位。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历史观的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其他题材类别的历史小说也繁盛一时并有了长足发展。因此,如何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出既具备思想深度,又不乏艺术价值的农民起义历史小说,是当前历史小说家应该完成的任务。
标签:农民论文; 李自成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化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星星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作家论文; 姚雪垠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