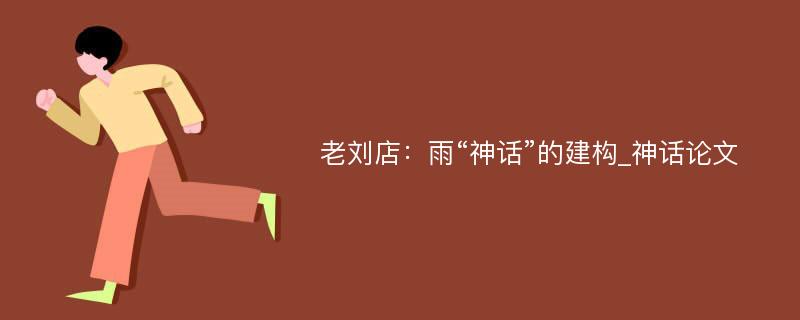
老刘店:一个求雨“神话”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刘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水旱灾害的普遍存在,所以龙王庙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但很多求雨仪式也发生在龙王庙以外的多种庙宇中(赵世瑜,2002:70)。位于豫南泌阳、桐柏两县交界处的盘古山上的盘古庙就是当地民众求雨的一个重要场所。然而,学界对盘古山的关注点在于其丰富的盘古神话与古老的盘古庙会,求雨仪式却至今没有学者提及。求雨一般以村落为单位进行,据说到盘古山求雨最为灵验的是老刘店村。2003年初以来,笔者多次在盘古山一带调查盘古神话及盘古信仰情况,并于2004年10月下旬专门到老刘店村进行调查,先后对16位村民(包括曾经组织过求雨仪式的两位老人)进行了访谈。本文利用田野调查所得材料,对老刘店求雨的仪式过程进行描述,并揭示造成其仪式“灵验”的文化因素。
一、求雨的仪式过程及其社会功能
老刘店村属于泌阳县高店乡,东南距盘古山约10公里,是一个拥有近1500人的村落。该村是一个杂姓村,其中以史姓人口最众,约有500人,另有刘、陈、李、彭几个有100人以上的大姓以及张、赵、韩等十多个小姓。村民以务农为生,拥有耕地2000余亩,农作物为一年两熟,冬季种植小麦作为主粮,夏季种植大豆、玉米、高粱、花生、棉花、芝麻等粮食和经济作物。村落布局呈长方形,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000米。1949年以前村北有一座白马寺,村西北有一座火神庙,村南有一座阎王殿,阎王殿对面有一座戏楼,现均无存。
老刘店与盘古山似乎有着特殊的关系。当地传说,老刘店是盘古爷的老家。解放前,老刘店几乎年年为盘古爷唱戏。1949年以后盘古爷还曾经多次“回家”,以蛇形现身老刘店。一次是本该唱三天的戏唱了两天,结果一条蛇缠住了剧团的车轮不让走,只好又唱了一天;一次是出现在村中的水塘中,引起很大轰动,数十里内前来求药者甚众;最后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求雨回来的路上,一条蛇拦住了道路,求雨人把它装在袋子里“请”了回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蛇就是龙,把蛇当作盘古爷,说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盘古爷视为龙的化身。老刘店村中有一尊小型的盘古爷的塑像,据曾经组织过求雨的李洪成老人描述,这尊塑像为石质,高约尺余,是1953年求雨成功后唱还愿戏时从盘古山请回来的。村民们对它极为重视,平时一般在某位村民家供奉着,但又秘不示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户姓史的人家在自家堂屋后墙上掏了一个洞,把这尊石像藏在洞里又砌好,使之免遭破坏。村民史升才是盘古山的“山主”(盘古庙会组织成员),也是求雨仪式的组织者之一。
求雨仪式一般在农历六七月份举行,正值当地夏季作物如大豆、玉米、高粱、花生、绿豆等种植以及生长的关键时期。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一旦这个时候天气干旱,村民多会组织求雨。
1.准备
求雨前数日,先成立一个指挥部,指挥部一般由五六位德高望重、经验丰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组成,其中一人为会头负总责,其他人分别负责经济、雨棚以及路上事宜。指挥部在求雨前数日确定启程时间及行走路线;通知附近各村;安排各类人员;到村内各家各户收取求雨费用,大约每人一两元钱,用来请乐队及购买香、表、鞭炮、火药等必备物品;准备猎枪、竹枝、旗帜。猎枪需要二三十枝;竹枝数十根,带有竹枝竹叶;旗帜为五色彩旗多面,系在竹竿或木棍上。求雨的前一天,先搭好雨棚。雨棚搭在村西北火神庙旧址上,用箔(一种用秫秸或苇子等编成的帘子,可以苫房或铺床)围其三面,上面搭上雨布而成。雨棚内放一张桌子,桌子上供奉盘古塑像,盘古塑像前边放置一个雨瓶(普通酒瓶即可)和一个香炉,烧上香。雨棚外放两个水缸,盛满水。水缸上贴着一副对联,对联的内容大约是邀请四海五龙共助其事之意。雨棚有专门的护棚人员严加看管,一直要等到下雨之后,或者超过求雨的有效时间以后拆除。求雨前一天晚上,凡准备上山求雨的人要沐浴更衣,至少也要洗洗脚,干干净净地上山。而被选定抱雨瓶的人则不能住在自己家中,必须在棚内住宿。
2.上山
求雨当天上午,吃过早饭后,本村大部分人都到雨棚前集合。由会头宣布一些注意事项,护棚人员留下看守雨棚,其他人就浩浩荡荡出发了。求雨队伍由猎枪队、旗队、乐队、抬盘古像人员、抱雨瓶人员、护雨瓶人员、持竹枝人员以及普通群众组成。凡去求雨的人都带着雨帽,就是用柳条编的圈帽。雨瓶用红布包裹,由一个选定的属龙的人双手抱着。上山过程较为简单,只是在路过每个村子时,吹一通乐曲。附近村子听说老刘店人上盘古山求雨,也会在村外成群结队加入队伍,到山顶后可达2000余人。行至离山顶约一公里的一条河边,抱雨瓶的人将雨瓶浸入河水中涮涮,再把瓶内的水倒掉,然后双手倒擎雨瓶,令其瓶口朝下而行。此后便进入“神路”,所有参与者,包括从村外请来的乐队成员,都必须将鞋脱掉,赤脚走路。神路上不能随便说话,不许小孩儿吵闹,也不许推推拉拉、东倒西歪、时走时停、拐弯歇脚。人群顿时严肃起来。
3.祈雨
到山顶盘古庙以后,抱雨瓶的人将雨瓶翻过来瓶口朝上放置在盘古大殿中盘古像前的神台上。在会头的主持下,大家虔诚地双膝肃跪在院内。庙内住持和尚点上油灯,烧上香。一通鞭炮之后,住持和尚或会头念祈雨辞。祈雨辞一般是临时写在一张纸上,内容大概是向盘古爷陈述当地旱情及百姓的焦虑心情,乞求盘古爷眷顾发雨若干,如愿后如何还愿等等。一般是求雨若干分,一分是十分之一寸,求雨者多求三分雨,够墒即可,五分六分则有余,一分二分则不足。还愿一般是演戏若干天。读罢,住持和尚取一支香,插入雨瓶中,将祈雨辞在灯上烧掉。大家叩头若干次,然后仍旧双膝跪立,祈祷。祈祷之意也是说明天旱之情况,乞求盘古爷发雨拯救子孙。有的人则不停地磕头,不少人磕得额头发红。过一段时间之后,住持和尚将香抽出观看,这时香的根部会湿上些许。据说有时候瓶底还能看见明显的黄水。根据香被洇湿的长度,湿一分,即是盘古爷已答应发雨一分,以此类推。如果不够,大家继续磕头祈祷,有时能持续两三个小时。住持和尚不时取出香来观看,直到香已经湿到某分,宣布盘古爷已同意求雨者的要求,发雨若干分。这时大家再次叩头,然后起立返回。
4.返回
下山前先是鸣炮放枪一通,然后按顺序下山。排在最前边的是持枪人员,他们路上不时地放枪,见什么打什么,看到飞禽走兽一概打死或打走,不许鸟虫之类从上空飞过,不许走兽从前边走过。如果看见有人走在路上,离很远就打招呼令他们让开,总之不许任何东西挡住他们的道路。持枪人员的后边是乐队,乐队不时奏乐。乐队后边是盘古爷的塑像,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由四个人抬着。盘古塑像后边是雨瓶,瓶口向上,由抱雨瓶的人用布缠在身上,同时用双手抱着,两边又有四个人搀扶着。持竹枝的人与持五色彩旗的人紧密包围在盘古塑像与抱雨瓶的人身边,手持连枝带叶的竹子或彩旗不停挥舞,不让任何虫子从上方飞过。队伍的最后是普通群众。返回的道路与去时的道路不一样,这样往返刚好是绕了一圈。路过哪些村子,这些村子的人早就知道了,多数村子村民会提前准备好茶水,放在路边,供求雨人员解渴,但是人却需要远离,更不能把水溅到求雨人身上。回村后,将盘古塑像与雨瓶放入雨棚内。所有去求雨的人,包括外村人,都要到雨棚前谢雨,也就是向盘古爷的塑像磕头拜谢,然后才能回家。
5.还愿
求雨过后,在一定的时限内不下雨,就算求雨失败,这时就将雨棚撤掉。在这个期限内,只要下雨,必须及时还愿。还愿根据许愿的内容而定,一般是请剧团在本村唱几天戏。唱戏越早越好,一般会在下雨后锄罢地人较为空闲时唱,但不能隔年。唱戏在本村进行,仍需在本村收钱作为费用,同时那些因老刘店求雨而得到雨泽的附近村落也有义务出资襄助。演戏时,将盘古爷的塑像放在戏台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意思是这戏是为酬谢盘古爷的恩惠而演的。演唱的剧种是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河南梆子、曲剧、越调等,内容一般是传统剧目,时间是三至四天。
6.求雨仪式的社会功能
求雨看起来是一种又花钱又费力的苦差事,但这种仪式具有相当强的社会功能。求雨仪式对于处于缺雨焦虑中的村民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安慰,刘店人相信他们通过虔诚祈祷和对一套完整的象征符号的“合理”运用就会获得神赐的甘霖,并且在仪式过程中验证了自身与这位拥有强大降雨能力的祖先神的特殊关系,从而获得了一种集体的安全感。在求雨仪式中,平时相互间不时发生摩擦的村民们变得空前团结,为了村落的共同利益,他们在村落长老的带领下抖擞精神,通力合作,从而至少是暂时地使分散的个体变成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实现了社区秩序的整合。求雨仪式还是一次村落实力的展演,规模宏大的求雨队伍,外村人的恭敬态度与依附式的参与,是老刘店强大实力的证明,这给予老刘店人一种不同寻常的自豪感。同时,请戏酬神这种还愿形式也为终日辛劳的农民提供了一种节日般的休闲娱乐机会。因此,老刘店人对这种“苦差事”乐此不疲,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求雨“神话”的建构
老刘店求雨的灵验是出了名的。有人说,老刘店十回求雨九回下。有人说,老刘店求雨都是淋着回去的。有人还将“老刘店”这个名字与其求雨的灵验联系起来,老刘店就是“老流点儿”,只要求雨就会流点儿。老刘店求雨真的这么“神”吗?是什么因素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我们认为,老刘店求雨之灵验,乃是求雨者对仪式象征符号的创造、宽松的效力时限、关于求雨失败的解释、村民特殊的记忆方式等因素共同建构出来的一个求雨“神话”。
1.象征符号的创造与解释
老刘店的求雨仪式是由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组成的。在这套符号体系中,雨瓶以及插在雨瓶中的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符号,也是求雨人与盘古爷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老刘店人正是通过对这两个象征符号的巧妙安排与解释来祈祷和验证盘古爷所赐之雨水的。对待雨瓶必须小心谨慎,毕恭毕敬。瓶子需要用红布缠着,抱雨瓶的人必须是属龙的。雨瓶一开始是干的,在上神路之前用用水涮一下,然后再倒干,瓶口朝下,到山顶后,炎热的天气与并不太近的路程看起来足以使它完全变干。然而,就在众人举行完一系列仪式,跪拜祈祷之时,“奇迹”出现了,插在瓶内的香湿了。香被洇湿,象征着大地被雨水浸湿,因此香被洇湿的尺度就等同于盘古爷允诺赐雨的深度。求雨过后雨瓶看起来还只是一个空瓶子,抱雨瓶的人又有人搀扶着,然而他却总是累得大汗淋漓甚至走不动。抱雨瓶的人汗出如雨象征着神雨洒落。
求雨仪式中与香和雨瓶有关的现象——香被洇湿,抱雨瓶的人汗出如雨——虽然有些玄妙,其实并不难理解。抱雨瓶的人红布缠身,被人团团围着,同时因责任重大而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炎热的天气里不出汗才是咄咄怪事。同时尽管天气炎热,但由于瓶口较小,短时间内瓶内的水汽并不会蒸发殆尽,因此香被洇湿是很正常的。但求雨者却解释说:雨瓶内导致香被洇湿的水气绝非刚才涮雨瓶时残存的“凡水”,而是已经蒸发了的“凡水”引来的“神水”,是盘古爷因为接受了他们所许之愿而赐予他们的;返回时雨瓶里装的是盘古赐予的全部雨水的总和,因此会把有人搀扶着的抱雨瓶的人累得汗出如雨、步履维艰。其实民众对此也非真的不了解,在笔者的调查中,他们往往在说完上述“经典”的解释后补充说:“其实雨瓶里还有水”,“天恁热,他能不出汗吗?”围绕香与雨瓶这两个象征符号所展现出来的现象本身其实是一种象征符号的创造,它们所模拟的是神灵应验的过程,但表达的却是人对神的祈求与愿望。这样,老刘店的求雨人通过香与雨瓶这两个象征符号实现了与盘古爷的交流的同时,又通过香的洇湿与抱雨瓶人的出汗这两个象征符号的创造和解释,验证了盘古爷对降雨的允诺,也就初步验证了其仪式的“灵验”。换句话说,是仪式行为本身创造了神的“灵验”。
2.效力时限的设定
求雨仪式中的奇异现象只是仪式有效的初步证明,而求雨是否灵验最终取决于所求之雨能否及时地、精确地降落下来。弗雷泽曾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某种巫术仪式的完成,它想要产生的结果多半会在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真的产生出来”。(詹·乔·弗雷泽,1987:90)老刘店的求雨仪式也是如此。求雨效力时限的设定(其实是在仪式实践基础上约定俗成的)的相对宽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求雨仪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获得成功。盘古山一带求雨的正常效力时间一般认为是“三天以外,五天以里”,也就是三至五天之内只要下雨就算求雨成功。当然,下雨越早就越显得灵验,最灵验的莫过于淋着雨回家。盘古山一带的气候类型属于北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在850-1000毫米之间,而且多集中于6-8月(泌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4:93-95),求雨的时间一般在农历六七月间,这正是当地雨水最为集中的时间。同时,求雨之前已经干旱了一段时间,加上求雨之后的五天时间,下雨的概率是相当大的。效力时限是在仪式经验的基础之上设定的,它本身也是仪式符号体系的一部分。这种较为宽松的效力时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求雨仪式“灵验”的“保护膜”。
3.仪式失败的辩解
然而老刘店人求雨并非没有失败过,如果因此对求雨仪式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他们就不会再次踏上求雨的道路。实际情况是,对于这些情况,他们总能从仪式本身找到充足的借口,这些借口看起来足以否认对他们求雨有效性的怀疑。
最为尴尬的情况是别的地方下了而本村没有下,或别的地方下得大而本村下得很小。笔者发现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总是由于求雨者不够恭敬或谨慎以致本该下到本村的雨被人截走。2000年,是截止到目前老刘店最后一次求雨,结果本村没有下雨,而离盘古山不远的枣子沿村却下了大雨。对此,主要组织者之一陈文铎的解释是:
最后这回没取着雨,走时候我就不愿意。咋不愿意咧?看你说响儿(乐队)后半儿(下午)来,是不?庄上老少爷们都在说这个事儿哩。半夜三更才来,啥也弄不成,是不?说使个车,到山上脱光脚丫子。人家吹响儿的媳妇子们几十里地人家跑不?叫人家跑人家不跑。那天天也热——是取雨就是天热,干天——弄得狼狈不堪,人家截走了。截到哪儿?枣子沿。枣子沿一个妇女么,在那叫截跑了。咋截的?那好截。看你抱雨瓶的,人家用水泼下儿就中了。枣子沿那回下了,人家花生多强不?芝麻长人把恁深。咱那人跟那打垮的队伍一样,有的乱叫乱喊,有的睡那儿,那就不中了。
类似的例子发生于1988年,那次同样由于求雨的人“心不诚”,队伍不整齐,路过出山王村时被人以请喝茶喝水的名义近前将水泼到抱雨瓶的人身上,结果出山王村下了大雨而老刘店附近只下极小的雨。一位不知姓名的村民说,还有一次是被上二门村的村神“猴爷”截走了:
那回早了,那回是猴爷,二门的。谁知道有个小庙没有?反正有个猴爷。他庄的,那人家在操着心哩,有知道的,叫猴爷请到这个边上,抬到路边上。他们说抬到豆棵跟前嘛,也不是明打明地抬到路上。你像这庄稼棵在路边上,他抬到这庄稼地里。这些人到那儿让你喝茶哩喝水哩,在这儿等着,(求雨的人)到这儿,一喝茶,一喝水,这个队伍呢,去鬼孙了(不行了),散了,一散下子,这猴爷就叫雨弄跑了。自晚儿(马上)那边就下了,下得公路上都恁深的水,那壕里头。
本村没有下雨,而沿途的村子却下了,这说明求雨完全无效。但老刘店人却总能将它解释成由于求雨人不够恭谨而被人使用诡计截走了。
这种对仪式失败的辩解与仪式本身的规定密切相关。老刘店人求雨仪式对参加者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出发前沐浴更衣,“神路”上列队整齐肃穆,赤脚行走,禁止乱说,提高警惕;返村途中,会有邪恶的鬼神化装成各种动物或人来截雨,所以往返要经过不同的道路,要用枪打死或吓走飞禽走兽,用竹枝挥走飞虫,避开行人。不与沿途村落人见面,是为了避免本村所求之雨被外村人截走。老刘店人用种种积极的或消极的措施以保证求雨成功。然而,正是这些求雨过程中的防止雨被截走的仪式行为本身,反过来为求雨的失败提供了借口。换言之,仪式行为本身就暗含着民众对求雨失败的辩解。对此,安德明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民间信仰(宗教)在人们观念中,具有着强大而深厚的影响。围绕着坚定的信仰观念,每一种宗教信仰中,都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逻辑体系。它把一切问题都纳入到了这一体系之中。当相关的仪式举行之后,如果取得成功,则自然会归功于信仰的力量;如果不成功,它也能找到一种为信仰辩护的理由:或者是举行者不够虔诚,或者是仪式的某些规则受到了违犯,等等。总之,信仰的根源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怀疑,相反,人们却会仍然以信仰为基础,寻找“这一次”的仪式所以失败的原因。这样,信仰领域的“灵验”,便总能得到一种自圆其说的证明,并且因为这种证明而不断地在人们心中得到强化。(安德明,2003:196-197)
4.灵验仪式的叙说
对于求雨有效时间与其灵验程度的关系,村民们未必全不了解。然而,有时候雨下得如此及时如此精确,就不由他们不信了。对于那些特别灵验特别奇特的例子,他们不但深信不疑,而且还会被他们经常提起。当笔者问及老刘店求雨如何灵验时,村民们常常是举一些最为灵验的例子来说明问题。1953年的求雨的灵验经常被提起:
特别五三年那一回显灵到哪儿了?取回来以后,人得谢雨。同是取雨的都得到那个雨棚跟前磕个头才能走哩不是?这磕的时候刘明全是主持人,他说“先尽外庄磕,不哩淋了”,一点云彩也没得,不哩旁的都说这是说疯话哩?一会儿起了没多大个云彩打这个东南角,“哗——”大猛雨淋着过来了,下得沟满河平。人家都走到北场就淋了。可是有一点,哪个庄没去哪个庄就没雨,哪庄儿去了哪庄有雨,那一回。(注:报告人:李洪成,66岁,老刘店村农民。)
还有一次,大约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
我记事那二年取雨准头。到屋里老汉们说赶紧洗洗,洗洗赶紧走,不哩有的就走不到屋,叫先尽远的磕头。回来了得磕头知道不?先尽远的磕头,你像邱庄、魏沟这些地方。磕着磕着就哗哗叫。那天那日头毒得就跟现在样哩,热得穿布衫么。回来了,老汉,就七爷说么,“赶紧磕头,先尽远的,近哩了先等着,不哩远的走不到屋。”我说“这老汉说疯话哩”,人家不叫说,当小孩的么,人家不叫说,照头上就打了一巴掌,不叫吭声。我说,“头顶儿连一丝云彩毛都没有会下雨?”谁知道磕了没有一半哩从那西南角上起了一小片云彩,跟个小盆样,说话不及淋得看谁淋得湿。都不相信。回来时候老毛遂就走不动啊,抱着雨瓶,几个人搀着。(注:报告人:陈某某,48岁,老刘店村农民。)
很难确定这种叙述中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仪式一再举行,总会有成功的例子,求雨后巧逢降雨,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一旦发生,就足以让人们传诵多年,作为求雨灵验的一个显赫证明。“人类的记忆对于积极的证据永远比消极的强,一件成功可以胜过许多件失败”,(马林诺夫斯基,1986:69)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效果一般而又没有发生特殊事件的求雨事件就会被人们淡忘,但这些特别“灵验”的求雨事件却会由于不断被提起而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强化,并可能模式化为一种经典的表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述两个人对两次求雨的描述的相似性看出。正是这些强化了的灵验记忆构成了有关求雨结果的集体记忆的框架。这又会使得听众甚至他们自己对其求雨的灵验性产生一种夸大了的印象。
5.村落规模的限制
这样,老刘店人通过仪式象征符号的创造、宽松的效力时限、巧妙的解释话语和特殊的记忆方式等“手段”,保证了本村的求雨仪式看起来总是成功的。此外,老刘店的求雨之所以在盘古山一带的众多村落里被认为是最为灵验的,还应该与其村落规模有关。按照民众的逻辑,真正完全无效的求雨几乎没有,因此求雨较为频繁、声势较为浩大的村子自然会给人们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求雨最为灵验的名声自然会落在这种村落身上。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较大的村落规模作为保证。据老刘店求雨仪式的组织者介绍,一次求雨往往要花上两千多元,还愿的费用更多。这样的人力财力要求,对于老刘店这样一个拥有近1500人的村子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无非是一个人二斤芝麻钱”,但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村子来说就会比较困难。盘古山一带的村落规模大都较小,如位于平原地带的唐河县东王集、毕店二乡,共有361个自然村,9万人(唐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3:70-71),平均每个自然村只有250人;毗邻盘古山的以平原为主的泌阳县陈庄、高店二乡,共有431个自然村,6.4万人(泌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4:72-73),平均每个自然村不足150人;属于山区的桐柏县共有4650个自然村,36万人,平均每个自然村不足80人(桐柏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5:1)。据笔者观察,当地山村多为几十人甚至只有一两户,平原村落人口多在200至600人之间,1000人以上的村子就比较少了,而1500人以上的村子相当罕见。那些小的村子,求雨一般是几个村子联合起来举行,然而这又增加了组织的难度;另一种办法就是依附于一个大的村落,就像老刘店求雨时附近村子的人跟随着上山求雨一样。相对来说,老刘店村的人口规模就相当可观了,它虽不是当地最大的村子,但至少有能力频繁举行盛大的求雨仪式,这应该是其成为求雨最为“灵验”的村落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关于老刘店是盘古爷的老家这一说法,也可能是在老刘店求雨名声远扬之后出现的附会之说。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老刘店村求雨仪式过程的描述,力图揭示其求雨“灵验”背后的文化因素。老刘店求雨的“神话”,是村民对仪式象征符号的创造、较为宽松的效力时限、关于求雨失败的解释话语、村民特殊的记忆方式等文化因素共同建构出来的。仪式中的奇异现象使求雨人初步“验证”了求雨的有效性;相对宽松的效力时间使大多数情况下求雨都能够获得“成功”;求雨的失败则可以从仪式措施中寻找到有力的借口;特别“灵验”的求雨经历在村民的集体记忆中得到强化,扩大了人们对其求雨“灵验”性的印象。这样,老刘店的求雨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客观方面,盘古山一带普遍较小的村落规模制约了大部分村落的求雨能力,这也是老刘店得以脱颖而出,成为求雨“最灵验”的村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众总有办法使他们的神灵膜拜看起来是“有效”的,使他们信仰的神灵看起来是“灵验”的。不然关于神的信仰就会失去说服力,膜拜也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膜拜神灵的仪式被民众一再重复着,关于膜拜灵验的传说也被一再创造和讲述着,正是这些“自我证明”式的仪式实践,以及与仪式有关的话语本身不断地“生产”着人们对于神灵“灵验”的信仰,进而推动着神灵信仰的地方性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