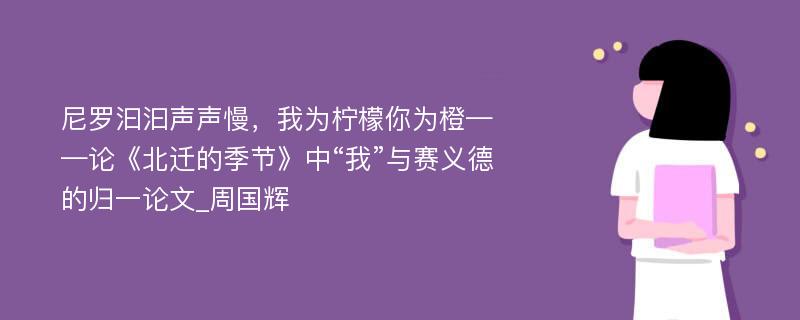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省 昆明市 650500)
摘要:《北迁的季节》中“我”与赛义德是故事情节穿越时空的的代言人,对于作品主题的凸显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文本细读,借助《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对于人类寻爱过程中被劈开的球形人寻找另一半的陈述,讨论文本中二者身份、罪等方面的“同”与出身、心理历程等方面的“异”,呈现出“我”与赛义德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我”与赛义德两半分开的球形人在寻得爱的归宿后归一,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异于后殖民、身份等观点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北迁的季节》,《会饮篇》,归一
引言
1969年出版的《北迁的季节》(后简称《北》)亦被称作《风流赛义德》,是苏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塔耶布·萨利赫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小说,被公认为阿拉伯文坛的当代奇葩。追溯对该作品的研究史,国内外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文本的后殖民理论,主人公赛义德(后文简称“赛”)与叙述者“我”的身份杂糅,文本的空间叙事,赛的拉康式解读等视角,然而鲜有学者窥得文中隐藏的“我”与赛之间的归一问题,本文基于柏拉图《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赞美爱神时对于人的真正本性及人的变化的发言,结合前人的研究及文本细节分析,指出“我”与赛即为阿里斯托芬口中因时空而分开的两半男性球形人,并于文章结尾处,在“爱”这一归宿中,合二为一,觅得最终的完整和幸福。
一,“我”与赛义德的“同”
1,同身份
《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谈到:“最初的人是球形的,有着圆圆的背和两侧,有四条胳膊和四条腿,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孔……后来宙斯把人都劈成了两半……凡是由原是男人切开而来的男人是男人的追随者,这样的男子幸运地碰上了他的另一半,他们双方怎么不会陶醉在爱慕、友谊、爱情之中呢?”在《北》中,“我”和赛有着太多相似的经历,皆为男性,同样从小智力超群,同样生于南边的苏丹,同样于北边英伦求学,赛归国后随遇而安选择了“我”的家乡小镇作为落脚点,最后二者在小镇相遇,另从归乡开始“我”即表现出对赛的强烈好奇,随着文章情节第一次高潮的到来,赛在酒后令“我”大为吃惊地朗诵了一首英文诗,之后被迫向“我”倒出真相,直到最后赛从尼罗河消失;“穆斯塔法都死了两年了,可我还时不时就想起他……这个穆斯塔法,不管我愿不愿意,竟然成了我个人世界的一部分,成了我的一个牵挂,成了一个不肯离去的幻影”,跨越时空,“我”与赛这些相似的经历和互相心照不宣的共鸣即是阿里斯托芬口中未被劈开前的球形男性。也正是时空造就的年龄、出身、地域将彼此分离。
在对文本的身份主题研究中,学者也经常将“我”和赛视为一体共同研究二者的身份杂糅问题。陈涛指出主人公穆斯塔法和叙述者都是曾留学欧洲的东方人,欧洲的文化强制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并造成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吴晓丽则认为正是通过穆斯塔法的引领,叙述者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选择活下去;王春兰试图同时寻找叙述者“我”和赛的文化定位,最后发现二者到死于都没能摆脱殖民化,也没有准确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文化定位。值得肯定的是,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北》中在“我”和赛身份问题上所凸显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宗主国与受殖国间的二元对立与极端的民族主义都不可取,后者取精去糟的包容态度才是一条理性出路。
回到《会饮篇》,对于被分开的男男两半的人,阿里斯托芬补充道:“以后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这样的少年长大以后才能在公公生活中成为男子汉大丈夫,他们自己到了壮年以后……对娶妻生子则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肯定结婚的确只是因为习俗的要求”。在《北》中,回归苏丹后,“我”在政府教育部门任职,而赛更是在农业委员会的职位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我”发小迈哈竹卜认为“他的死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与此同时,“我”和赛都多了丈夫和父亲的身份。至于赛,当“我”问及其妻哈塞娜是否爱他时哈塞娜答非所问地回答到:“他是我两个孩子的父亲啊……他在世时对我们是够好的”,字里行间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婚姻繁衍后代的传统意义而非真正的爱情。而对于“我”的婚姻,文中更是着墨寥寥几乎无迹可寻,这和上述《会饮篇》中的陈述是相吻合的。
关于身份,文本有一问题值得商榷:部分学者将赛义德直接描述为殖民时期殖民者的帮凶。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正如文中当“我”听到青年教师将赛定义为帝国帮凶时的态度一样。“我”在赛的小屋中发现的穆斯塔法﹒赛义德在其作品中反映的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巧取豪夺,以及罗宾逊太太在给“我”的回信中对赛的评价:“他对自己的同胞在我国殖民者监护之下所遭遇的贫困状况进行过许多的揭露,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细节均呈现出赛的民族立场;视角转到“我”身上,“我”同样希望回国为家乡做贡献,却发现“像我这样的小职员是无足轻重的……上司要我们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面对苏丹的国家和未来,面对同为其子民的身份,“我”和赛面临一样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
中途,两半分开的球形人寻到了另一半:“我”和赛建立了友谊。在赛决定消亡之前将妻儿和密屋钥匙、火漆信件托付与“我”都显示出二者之间精神上的默契信任。
2,同罪
阿里斯托芬在《会饮篇》中又说到:“(球形人)他们的体力、精力、品性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实际上想要飞上天庭,造诸神的反。”叛是一种罪,文中“我”与赛皆有罪—对婚姻的不忠。说到罪,此处不得不提及文中明显的宗教背景,“我”与赛在受到南北双重身份困扰的同时同样面临本土伊斯兰教和北边基督教的深厚影响。赛在英国时不时光顾教堂,在小镇时“主麻日聚礼他一次不落”;而“我”的邻居担心我从英国带回一个基督教老婆,同时“我”的家人,尤其爷爷,是小镇上颇具声望的穆斯林信徒。鉴于希腊神话对于基督教的影响,此处二者的原罪,主要从基督教的视角解读。由于各种原因,赛在欧洲以玩弄欧洲女人寻求一种心理平衡,导致她们的毁灭,并最终杀死自己在英国的妻子莫里斯,他把自己在英国的卧室比成“一座坟墓”,英国法庭上的法官对其的宣判词:“穆斯塔法﹒赛义德先生,你虽然才华出众,却是个大傻瓜。你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个黑暗的角落,你滥用上帝施与人类的最崇高力量—爱情。”显然,这是基督教中的原罪显现;至于“我”,回归小镇娶妻生子,但受赛所托后却爱上了赛的遗孀哈塞娜,认定其为“我唯一爱过的女人”,并对于自己的身陷其中无能为力:“我和穆斯塔法、瓦德﹒利斯以及千百万人一样,对于瀛寰躯体上的冶游成癖的传染病毒并没有什么免疫力。”可见,“我”亦难逃原罪的轮回。阿里斯托芬告诉后人:“从前我们是一体的,但由于我们的罪过,神把我们驱散到各地。”至少在肉体上,作为阿里斯托芬口中的球形人,“我”和赛在“被劈开”后,再重合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我与赛义德的“异”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半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求与自己相结合的那一半。”[5]181 在阿里斯托芬口中,“我”和赛作为分开的球形人,在互相寻找对方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时空上的分离和因此造成的差异。
1,不同的出身
同样作为留学归来的游子,相对于平稳安定的“我”,赛的经历更显复杂和耐人寻味,这和其出身造成的赛在性格上的缺陷密不可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个人的变化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的”, “我”的童年家庭和睦安稳,从文章伊始的归国细节是便可见一斑:“大家喜笑颜开,热闹异常地把我围在中间……母亲端着热茶来了,父亲做完礼拜颂毕祷词来了,妹妹与两个兄弟也来了……这是一种只有生活在家人之中才能感受到的温存”,遗憾的是,赛并未有机会体会这样的氛围:“我自幼失去父亲,一无兄弟二无姐妹,只与母亲相依为命”。赛的性格因家庭环境自童年开始便缺乏一种骨子里的安全感,即使与母亲之间仍然没有多少话可谈,作为“我”的另一半球形人,赛在寻找完整的过程中因爱的缺失早早便获得一个反而破碎的精神世界,加上他超出常人的智力水平,被在开罗时的班级同学定义为“一台冥顽不化的机器”也就不足为奇了,诚然如很多学者所言,赛在欧洲对白人女性的玩弄是对白人话语中心的颠覆和复仇,但不妨暂且抛开殖民视角,其自打出身就缺失的亲情不可否认地作为此种结果的内因之一。正如赛在其自传中写到那样“谁生养善良,子孙会小鸟般漫天翻飞;谁生养邪恶,会自食其果痛悔不已。”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赛也早已对自己的结局做好心理准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读者可以细味其中蕴含的宿命味道,赛作为一个苏丹子孙,正如海伦﹒米切尼克指出的那样:“在苏丹和埃及,另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绝对相信命运,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命中注定”。不管吃了多少洋墨水,他有意无意始终要回归自己的苏丹之根后接受命运的安排。
2,不同的心路历程
在面对结局之前,不妨探讨一下“我”和赛在文中所表现的不同的心路历程。显而易见的是,“我”经历了“爱—恨—爱”的心路历程,最终在尼罗河的混沌中获得救赎;而赛在“恨—爱”的心路历程中以一种消亡的方式得以解脱。
“我”生来被家人之爱所包围,爷爷在文中对“我”影响不容忽略,“我一直喜欢爷爷,爷爷喜欢讲故事,当我思念亲人时,常常在梦里见到他。”海伦﹒米切尼克曾在《埃及 苏丹民间故事》中的序里指出:“讲故事在苏丹非常流行……并非所有故事都纯粹是为了消遣娱乐……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要尊重父母和长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要诚实正直,不要失信;关心我们当中的异乡人;以及善良战胜邪恶。”可见“我”在家人的爱中成长起来看,获得了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后北迁英伦求学,踏踏实实地研究英国一个无名诗人的生平,直到学成归来遇到赛,至故事情节高潮处,“我”联想到哈塞娜又成为赛的一个牺牲品时内心“满怀仇恨”,进入密屋“报仇”,黎明离开屋子,“我”跳进尼罗河“去去胸中的愤懑”;最后在尼罗河的生死瞬间,“我”意识到“世上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我愿尽可能地和他们一起多待些时日。”经过一次爱恨轮回,“我”作为球形人的另一半,顿悟生之本能、爱为责任。
赛本质上不算一个幸运儿,自幼亲情缺失以及诸多学者提及的身份杂糅等外在的文化大环境最终将赛塑造成一个心理畸形的有色人种。在开罗求学期间将自己视为己出的罗宾逊夫人却被赛作为性启蒙者,而作为自己彼时欧洲的白人妻子莫里斯,在察觉其对自己不忠之后赛选择以在男女交欢之时“胸膛压着匕首,直至完全刺进她的胸膛”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双方的痛苦。畸形的内心之下掩盖着对整个世界的恨和报复,他是情人和世界眼中的魔鬼;待回归故土,赛娶妻生子,在发现“昧着良心活下去没意思”后毅然消亡,却在火漆信中嘱咐“我”照顾其妻儿,尤其嘱咐“我”照顾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远游他乡,”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赛人格中善的一面以及他在精神世界里对爱的渴望与回归善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赛的消亡,部分国内学者指出是由于赛归国后无法认同苏丹文化而选择自杀,对于此类观点,赛在杀死莫里斯后“生命历程在那天晚上已经完成,而不再有活下去的任何理由……后从一处到一处苟延残喘,虚度时光”可见赛义德在杀死莫里斯后已经处于一种精神死亡状态,回归故土只不过是肉体本能最后的挣扎。
结语:
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没有一个最初的开始,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局……虚空不是运动的条件,而是运动的障碍。”在《北迁的季节》中,赛义德终归变成了跨越时空的一种虚妄,一个幻象,所以“我如果得不到人们的宽恕那我就应当努力让人们把我忘记。”此处的“我”早已不仅仅是叙述者本人,也是赛义德幽灵的呼喊。赛虽然肉体消亡,但已经和“我”在精神上融为一体,他浪子回头,带着过去的负重解脱于无形;“我”带着他的期盼和希望继续,分开的两半球形人在精神上,在爱的召唤下最终超越时空与性别,二者归一,赛义德成了“我”,“我”就是赛义德。诚如阿里斯托芬在《会饮篇》中所说的那样:“爱引导我们找到与自己真正适合的爱人……终有一天爱会治愈我们病,使我们回归原初状态,生活在快乐和幸福之中”。
参考文献
[1]陈雪梅,流散与文化身份重建—《北迁的季节》后殖民主义解读[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3):77-78.
[2]许佳媛,文化杂糅者的悲剧—《北迁季节》的后殖民解读[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2):11,137.
[3]宁显锦,《北迁的季节》的空间叙事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14(8):122-127.
[4]陶李,欲望表征的缺失—对《北迁季节》的一种拉康式的解读[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5):38-39.
[5]柏拉图,会饮篇[M].王晓朝译,柏拉图读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6]萨利赫﹒塔依卜,风流赛义德[M].张甲民译,阿拉伯小说选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7]陈涛,“白色神话”的阴影—《北迁季节》中的种族文化心理创伤[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4):78-80.
[8]吴晓丽,《北迁季节》: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及艰难探索[J].鸡西大学学报,2013(9):103-105.
[9]王春兰,叙述者和穆斯塔法的文化定位—《北迁的季节》后殖民主义解读[J].鸡西大学学报,2012(3):122-123.
[10]海伦﹒米切尼克,埃及苏丹民间故事[M].任泉,刘芝田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11]张传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周国辉(1989年—),男,汉族,云南曲靖人,学生,文学硕士,单位为云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论文作者:周国辉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9/18
